獨家|《八佰》之後,換個視角看戰爭_風聞
第一导演-第一导演官方账号-导演社群2020-09-02 07:29
採訪、撰文/君偉
《八佰》20億了。
我就在想,如果**《又見奈良》**上映了,會有那麼多人看嗎?
它們都關於抗日戰爭,一個寫戰爭初期的故事,另一個寫戰爭後傷痛的延續。
《又見奈良》的視角,放在了日本遺孤身上。

説實話,我從未關注過日本遺孤。
直到今年上影節,看了《又見奈良》,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個羣體。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戰敗的日本軍瘋狂撤退,將大量戰時移民遺棄在中國東北。
這些日本移民的孩子,在抗日戰爭剛勝利時被中國家庭收養,他們被稱作“日本遺孤”。
七八十年代,隨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許多遺孤重回日本。
《又見奈良》講的是一箇中國養母,去日本尋找日本養女的故事。
現實是,雖然很多養母的心願是去日本看看他們的孩子,但種種原因,真正去的很少。
第一導演(ID:diyidy)這次與《又見奈良》導演鵬飛聊了聊這個被忽視的羣體。

鵬飛導演説,他想拍這部電影,去圓這些養母的夢。
本文無劇透,放心看,那些電影之外的現實故事,已經讓人感慨萬千!
01
我想去日本看看我的孩子
我上一部作品《米花之味》參加奈良電影節,獲得觀眾選擇獎。奈良電影節有個傳統,獲獎的人都有可能跟河瀨直美導演合作,讓她來監製影片。

河瀨直美導演
我們要在兩個星期之內,交一個故事大綱。
我當時想,中日文化交流密切,一水之隔,如果我拍一個留學生故事或者愛情故事,會覺得太浪費了。我想以厚重的歷史為背景,這是我感興趣的。
我一開始就確定想拍一個反戰片,但怎麼樣去表現,當時沒有想到。
我以前知道有遺孤這類羣體,但我完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後來我開始查資料,開始買所有關於他們的書,找到的不多,大概七八本,一看就覺得我要寫這個故事。
有的書是寫養母的採訪,有的是回到日本的遺孤所寫,有的是留在中國的遺孤所寫,還有的是整理的書,包括嚴歌苓寫的《小姨多鶴》這本小説,還有《大地之子》(日本NHK出品,中日合拍)連續劇,這些我都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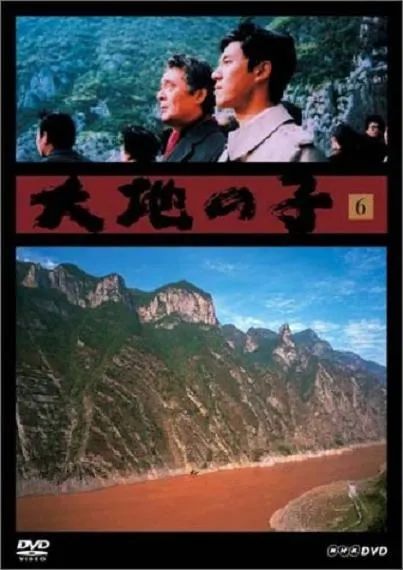
電視劇《大地之子》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養母採訪,很多的養母採訪,作者會問她們,你的願望是什麼?
養母的願望很多都是我想去日本看看我的孩子,看看他們生活的環境,他在老傢什麼樣子,但是真去的養母非常少,可能也就一個兩個。
所以我就想用電影去圓這些養母的夢,現在養母已經很少在世的了,大概是這樣。
02
你從北京來的?終於有人惦記起我們來了
《又見奈良》故事設定是2005年,實際上我去奈良是2019年,已有14年的跨度了。其實很多一代遺孤都已經不在了,養父母就更不用説了。

吳彥姝老師在片中飾演中國養母
我在奈良是想尋找“一代遺孤”,所謂**“一代遺孤”就是1945年前後在中國出生的孩子,8090年代回到了日本,他們是日本血統**。
二代遺孤基本上都是混血兒。我在奈良找到的基本上都是二代,都是四五十歲,五十歲偏上的也有,還有三代能碰到。
包括在我們劇組中幫我們翻譯的張老師,她也是10歲跟他爸爸到的日本,那時是1993年。
但我就想去找一代遺孤,去了解他們的生活。
後來我找到歸國者協會的會長,他叫張文成,沒有日本名,雖然他是日本血統,但不願意接受日本護照。
那次見面還挺有意思的,我跟日本同事來到老年活動中心,一幫日本阿姨們在做飯,裝便當,我看了倍兒好奇。我説:這幹嘛呢?他們説:他們要給更老的人送飯,也就是給孤寡老人送飯。我心想,他們都這麼老了,還有更老的?其實還有更老的,日本的老齡化很嚴重。
這個時候迎面走來了一位身材魁梧的日本男士,西裝革履,拿着包,坐下之後開始跟他講日文。我不會日文,但聽他的口音挺奇怪。朋友介紹我是中國來的導演,準備做什麼什麼故事。那先生説:中國人?中國人那還講啥日語,你幹啥的?你哪的?我北京。北京哪旮沓的?我聽着是很純的東北話那種感覺。

《又見奈良》片場
其實一代遺孤特別少,奈良一共才五六個一代歸國者,就是我用在片中的對白。後來就經過苦苦尋找,得知在一個叫黑龍鎮吉野村有一位,但不知道具體的位置。
後來我們就翻山越嶺,開了兩個多小時車,當然在日本開兩個小時車挺遠的,那蒼天大樹,還有一條土道,對面來車就得往回倒,旁邊又是山澗。終於到了黑龍鎮吉野村的時候,我問市役所,應該就是鄉政府,有沒有遺孤?
那人想了想,拿出資料本打開找找找,説有一個,我們鄉政府給他蓋的房,在哪個地方,大概怎麼怎麼走,就讓我們去了。
日本的村還挺漂亮的,我們在半山腰上找到了那個房子。我就往裏一看,有位老奶奶,白髮蒼蒼、羅鍋、沒牙,她就開門來了,我還按照中國的禮節,帶了最實在的米、油、水果這些。一開門,奶奶還沒説話,我先説:奶奶您好,我是從北京來的,我來看您來了。老奶奶當時眼淚刷就下來了,你從北京來的?終於有人惦記起我們來了。
我説請問劉大爺在哪呢?劉明財,日文名叫山田周作。老奶奶拽着我往旁邊,他們家有一畝三分地,能種點蘿蔔、酸菜、白菜……一邊跑一邊説,家裏來客qiě(親戚)了。
那個老頭正種地呢,説:幹啥呀?我當時覺得特別的有意思。歷史感撲面而來,你就會感覺到腦子中的數字年份在往前捯,開始往1945年倒……
老頭把那個鋤頭一杵地,就開始嘮,從他小時候怎麼到的日本,把他被放到哪家了,然後輾轉反側到姓劉家,給他起名劉明財,他還在村裏當了幹部,在中國挺好,後來村裏的人説他是遺孤,他覺得挺奇怪,他説我不可能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我還打小日本呢等等這些,挺有意思。
得知真的是有這麼回事,他就開始沉默,政府説有機會讓他回去尋親,後來他就見到他的日本父親,那是1991年去的,到了1993年3月份正式回日本了。
回日本的時候,還挺轟動的,有不少的媒體報刊都在講這個事情,就是中國人把日本的孩子養大了,還挺轟動的,機場很多人接機,包括記者,他的父親已經75歲了,記者採訪他父親,他父親非常的激動。
父親提到,我回日本之後又生了兒子,這兒子還沒法生育,當時覺得我這輩子斷子絕孫了。今天我沒有想到,中國人民把我的兒子送回來了,我更沒想到把我的孫子都帶回來了,我萬萬沒想到,我的重孫子都回來了,我一下四世同堂了,我太激動了,我這輩子夠了,他就給我講述他的這段歷史。
在家裏,老人給我看很多他回來拍的照等等。有一個細節是,像中國人請客人到家裏來喝茶,但是他喝咖啡。日本傾向於喝咖啡。當然茶文化日本也是非常濃,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老人當時就給我泡了速溶咖啡。
隨後,老人就給我們看了一張1944年他們吉野村開拓團去中國出發前在村門口合的影,這張我用在了電影中,我覺得是很珍貴的一個素材。
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接觸這些遺孤,不管他們是一代二代,加上我們在尋找過程中碰到的一些故事,就慢慢地把這個故事構建起來了。

鵬飛
遺孤羣體有一個協會,當地政府會安排老師給他們上課,上日文課,就是這些五六十歲的二代遺孤。
有一個蒙古老太太是一代遺孤,80多歲了,還是吭哧吭哧在那學,眼睛看不清楚了,還在學最基本的日語。
我問了一些其他遺孤,説:“您這個學多少年了?”“擱這學10年了”。我説:“學10年了?”“根本不會,到家就忘,回家還是包餃子,弄酸菜去,那誰記得住,日本名字,記不住。”我説:“您回家弄酸菜?”“自己泡酸菜,這邊的酸菜不行,粉條還行,這邊粉條好吃。”其實就是非常民間百姓的話題,沒有聊很厚重的話題。
他們都會每週要交一個作文,用日語寫作文,其實是小學生水平。同事就把這個東西翻譯給我看,基本上都是寫他們在中國的生活、在中國的回憶,比如“我小時候怎麼把柴火垛點着了”,“我小時候犯什麼錯,我爸媽教育我,後來長大了,覺得他們教育得對”,還有其他等等。
説實話,這些記錄讓我挺感動的。**她回到日本已經20年了,但是作文中的回憶依然是在中國,**這就是無法磨滅的命運、文化與記憶。
所以我在劇中安排了一個日本人回到了這個村,要表演節目,他唱的依然是中國的曲子,他是依舊懷有一顆中國心。
03
戰爭讓我們骨肉分離,回國又讓我們骨肉分離一次
你知道他們怎麼看這段歷史麼?
對於這段歷史的看法,我更多是跟一代遺孤聊的,其實還是那位老先生——劉明財老先生,田山周作。我就問他,你對戰爭有什麼看法?有什麼想法?
他説,千萬不能再有戰爭了,有了這次戰爭就讓我骨肉分離了。當時回日本的時候,最開始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只能遺孤本人回來,我們就不同意,一起上訴,説你們發起一場戰爭讓我們骨肉分離,現在我們回來你又讓我們骨肉分離一次,我不答應,要回來就全回來,要不然就都不回來,後來經過一系列的交涉等程序,就讓我們都回來了。
對日本政府來講,他們單方面認為我們是負擔,因為村裏人結婚早,生孩子又多,一個遺孤帶着一老伴,生了4個孩子,孩子又結婚,一回來加起來就三四十口人。但又不能不面對這些事,就要讓他回來,讓他回來就得都承認,因為都是日本血統,都是留下的後代。

《又見奈良》殺青照
劉老先生也提到:這是政治的事情,我一個老人不是很瞭解。當時老先生還説:安倍在擴軍,在增加軍事開支,他不禁疑惑:增加這幹嘛?增加這個不就是又要打仗嗎?你又要打仗不就又有更多我這樣命運的人?
他跟他的太太非常不同意這種做法,戰爭不能再來一次了,因為遭殃最大的一定是百姓,兩國都是。
04
從來不讓媽媽給他開家長會
我自己對戰爭反思的重點,更多的是戰爭遺留下來的傷痛,戰爭對當時的人造成傷痛,而且這種傷痛會延續很久,不是戰爭結束就完了。
《又見奈良》演員英澤、吳彥姝、國村隼
但日本不同,日本是單民族,他們回到日本之後的歧視其實是跟生活的壓力相關的。在中國是從小成長的過程,從小學到大學,但是回到日本後就面臨着各種方面的歧視,比如做底層的工作,會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很多人不敢暴露自己遺孤的身份,有一些甚至影響到了三代。
舉個例子,有個小男孩兩三歲去的日本,身上基本上沒有中國人的影子,家裏邊説中文,他能聽得懂,他也會説,但他不説,到學校,從來不讓他媽給他開家長會,從來不説中文,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媽媽非常傷心。他媽媽是在中國長大的,就説為什麼不讓我去?
他説,如果我讓某些人知道我有中國的背景,那我在學校不好過,日本學校霸凌、抱團這種情況很嚴重,他不願意向他的社交圈表露這些,其實孩子也是無奈的,是沒有辦法的。
05
遺孤想融入日本社會,難!
在日本我所接觸到的遺孤二代、三代,他們實際帶有的中國人的味道更多。就算他説的日語,穿着日本着裝,但是他的氣質是藏不住的,他的味道還是中華民族的,甚至影響到了下一代,比如我們劇組中的張老師。
當然,他們這一代都是混血兒,但是因為在中國成長,接受的教育等等是長大後無法變化的。他們在日本就會講日語,儘量跟日本人融到一起,因為在那邊生活,沒辦法,但是給我的感覺,依然是濃濃的中國味。
從吃飯來講,我看他發朋友圈,去他家吃飯都是肥牛火鍋,當然肥牛是日本的,但卻是中國的那種放很多辣椒的火鍋這是中國的飲食習慣。有時候去他家,問到吃什麼?他説:包餃子吧,酸菜豬肉的怎麼樣?
還有,電影中那個老先生説話,會碰你一下。
日本人不會碰你,但碰你一下在中國人看來就是一種熱情。這種肢體語言無時無刻不傳達出中華文化的感覺。
《又見奈良》劇照
再比如説一個家庭,日本的父母跟兒女之間的關係沒有像中國這麼的親近感覺在隔着什麼。子女要上學的話,一定就要自己想辦法解決生活費和其他問題,他們認為管家裏邊要錢是個很可恥的事情。
而在中國,父母覺得我要培養孩子,我願意為他付出所有東西,是為孩子以後的幸福付出。所以,從這方面看出,他們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日本的孤寡老人很多?我可能用這種方式來解釋更準確一些。在中國,我們廣場舞特別吵,一幫老大媽在那跳得也不好看,歌也不好聽,好像鄉村電音。
但是到了日本,那些公園、廣場等等,特別安靜,沒有老人,有時候沒有人。他們各自在家裏邊,看燈是亮的,看電視也好,幹什麼也好,聲音很小,好像是很文明這種感覺,但其實每個人都是孤獨的,有的老人在房間裏死了一個月,才被人發現。
日本有一個職業是專門清理這些孤寡老人遺體的。有一個紀錄片就拍的這個。我問他們:“晚上吃完飯不出來遛彎?”日本人説:“不遛彎。”“你們不去樹下邊聊會天,打會麻將?”“不行不行,沒有沒有。”
但是中國的老人為相對日本就沒有這麼多因孤獨死去的,是因為我們會去跳廣場舞,就算孩子在外邊打工,但我有我的老伴,我有我周圍的朋友,要不打會麻將,要不我們樹地下乘乘涼聊天。
一開始我覺得很反感的廣場舞,去完日本之後反而覺得很健康,會讓遠方的兒女沒有那麼擔憂,這個社會也會穩定一些,跟日本完全是兩回事。所以我覺得沒有哪個文明或不文明,中國的老人也是非常可愛、非常有意思的。
我給日本同事講中國老人在幹什麼,他們都覺得好可愛,其實這個是真的很健康的。
從這方面反看我們國內的情況,從這件事就能體會到在中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與日本人與之間距離的差異,何況這些遺孤去日本,他們想融入?更難。
06
再瘋狂的年代也有人性的光輝
其實選擇這個題材,倒不至於害怕,只不過中日題材,尤其戰爭題材非常敏感,處理不好就會被人説成是,向着日本説話或者親日等等。
但我是從百姓入手,是在講中國母親真實的人性光輝,故事都是真實的,所以我覺得我是相對客觀地處理這個題材的。我沒有説日本多麼好,而是跳出了思維侷限和道德評判,講人性。
我聽歷史老師講課,講中日戰爭,有句話我覺得講得挺好的,就是“再瘋狂的年代也有人性的光輝”。我覺得中國母親身上完全體現了這個,並不是説我要表現主旋律或者歌功頌德,是因為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又見奈良》演員英澤、吳彥姝,導演鵬飛
我看那些養母的採訪,有些真挺“不可思議”的。一九四五年戰爭剛結束,日軍正在撤退,日本人把孩子就放這了,對於中國的養母來説,這一行為等於是立刻就把敵人的孩子收養了,這是何等的偉大。
有一些養母講到,6個月前,她被日軍一腳踹流產了,孩子沒了;6個月後戰爭結束,有一個孩子留在她家門口了,或者是有人問,這有鬼子的小孩你要不要收養?要。

07
我希望我的電影后勁大
《又見奈良》這部影片的風格還是輕盈的。悲傷的事情,我想把它拍的輕盈一些、生活化一些。
目前已經有很多很犀利的電影、很諷刺、很尖鋭、很批判,我覺得這些電影都有了我就不用再這樣拍了,這類很好的作品已經那麼多了。
我想換一種方式,我希望這部電影後勁大。這個勁不是用在你看的過程中這一腳踹心窩了,那又捅了一刀,不是這種。而是當電影結束,字幕升起,那個後勁在你心裏開始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