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弔詭的奇觀:特朗普的基本盤為何紛紛“逃離學校”?|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09-07 2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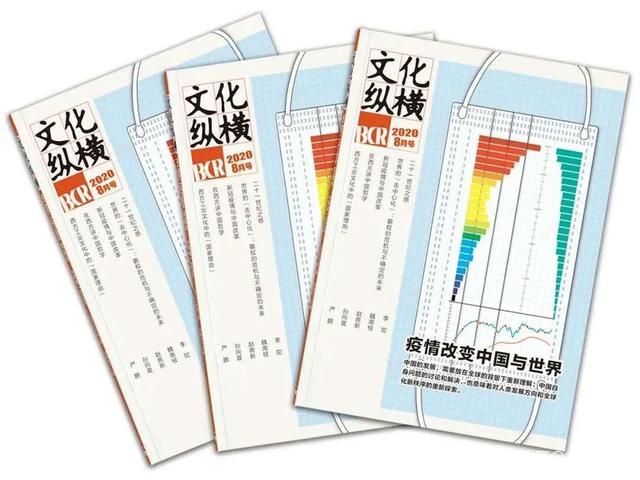
✪ 尚文鵬 | 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
【導讀】對於從小接受義務教育的中國人來説,很難想象一個國家會允許公民拒絕國家提供的公立教育。在美國,不僅父母對孩子的教育被認可為具有同等學力,而且這種“無政府主義”的教育模式已經走向主流,發展成為美國國民教育的一種替代形式。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本文剖析了與在家教育相關的價值觀念、政治經濟、法律體系、宗教與種族等美國社會的諸多面向,為我們瞭解美國社會提供了一個特別的切入點。
在家教育是一種典型的美國文化,它鮮明地體現了美國自殖民地時期就深植的“個體權利高於國家權利”的個人主義價值觀。而持這一價值觀的主要羣體,恰恰是今天日益分裂的美國社會中的特朗普基本盤,即所謂的“白人福音派”。他們所堅持的一系列“老美國”傳統價值,包括對國家和專家的審慎態度、對社區和家庭生活的重視以及對“在家教育”的不懈推動,是在家教育在今日美國得以流行的主要原因。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8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逃離學校:美國在家教育的興起
今天的美國教育中,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越來越常態化。2016年,美國在家上學的學生人數為230萬,約佔5~17歲學齡人口的4%,與70年代1萬多人相比,保守估計每年以7%到12%的速度遞增。很多學者都認為在家上學已經走向主流,發展成為美國國民教育的一種替代形式。1986年,90%的大學沒有關於在家上學學生的錄取政策,但到了2004年,多達75%的大學已制定明確的相關政策。在美國大學申請中,FAFSA(聯邦學生援助)在“高中畢業狀況”一欄中,專門有”homeschooled”的選項。
在前現代社會,家庭教育原本是主要的教育方式。但在今天學校教育已成普遍規範的情況下,它為何在短時期內又被重新發明出來?短短幾十年間,在家教育是如何迅速擴張且被合法化的?其背後有怎樣的社會經濟動因?本文將基於美國的歷史脈絡與筆者的田野工作回答上述問題。
▍從家庭教育到學校教育
歷史學家約翰·迪莫斯(John Demos)曾説過:“美國家庭的歷史是一部不斷退縮的歷史,家庭的功能不斷喪失,讓位於專門的機構。”美國公立學校的誕生不過短短一百多年,而如今,約90%的美國人接受的是公立學校教育。從殖民地時期到19世紀中葉,家庭教育是美國教育的常態,其後教育的場所從家庭轉移到學校,是一系列政治-經濟力量和社會各階層共同形塑的結果。
米爾頓·蓋瑟把1600~1776年間的美國描述作“家庭之邦”(family state)。獨立革命前的美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社會組織和政治控制的基本單位是地方鄉鎮,移民雖然承認英國這一宗主國的權威,但由於遠離歐洲大陸,他們的現實生活更多地維繫在家庭、鄰居、鄉鎮等具體的生活單位上,而不是“國家”這一多少顯得模糊的概念。這種由個體及家庭組成,以自治社區為結社單位的殖民地社會運行了一百多年之後,才有美國國家的誕生。因此,個體權利或者説家庭權利高於國家權利,可稱得上是美國一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政府承認父母的權利和權威,明確主張教育在家庭中進行,家庭既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也是一個學校,不過沒有自治權,而是處於政府嚴格管理之下。因此“家庭教育”體現的是一套自然而為,也是有意為之的政治理念。
“美國公立學校之父”賀拉斯·曼(Horace Mann)於1852年在麻州創立美國最早的公立學校教育體系,主張通過普遍的平等的學校教育,使來自不同背景的美國人享有某種共同的體驗,建立公民間的情感,以獲得民主所需要的共識,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共和國的公民,亦即強調教育的政治整合功能。另一方面,工業社會相較於農業社會具有很強的流動性,並要求不斷創新,勞動力需要具備識字能力,共享一套相互交流的意義體系,以及獲得各種文憑和證書,而這些是自我再生產的家庭教育所提供不了的。教育除了其政治功能,越來越被納入經濟秩序,被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助推器。
公立學校最初遭到大眾普遍的敵對和反感。富人不願意交税支持窮人的教育,教會對賀拉斯·曼的學校世俗化構想深感恐懼,而普通美國人則認為教育是家庭事務,政府不應該干預。這其中尤以普通百姓的抵制最為激烈。直到19世紀80年代,麻州的巴恩斯特堡市(Barnstable)為了對付家長,甚至要出動民兵帶槍護送孩子上學。但隨着美國工業社會的發展,統一性和標準化的公立學校教育最終被接受為一種普遍的規範,不但是國家認同和社會秩序的根基,也成為個體身份認同的內在要求。到1918年,美國所有的州都確立了義務教育法,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都被納入到國家制度的框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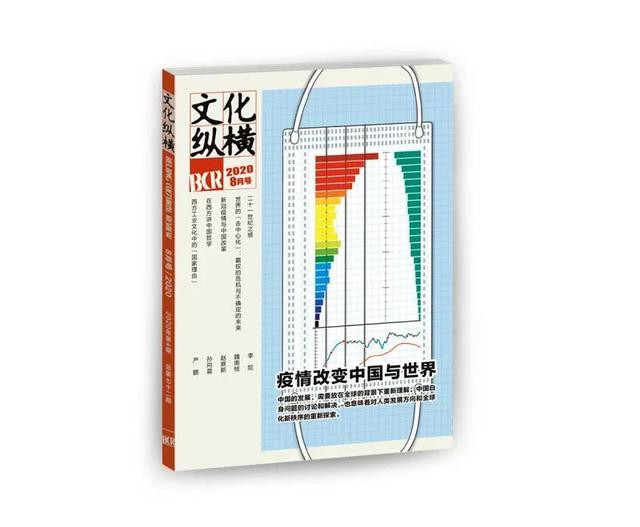
《文化縱橫》8月新刊上市,taobao搜索文化縱橫雜誌訂閲
▍在家教育運動的興起
(一)反文化時代的教育實驗
直到1970年代後期,“在家教育”才從一種罕有的個案快速增多,並逐漸進入大眾的視野。在家教育的擴張被稱為“20世紀下半葉最重大的社會潮流之一”。它的合法化不像大多數法律那樣,自上而下地經由綜合性立法,而是在個體家庭自發組織的草根社團領導下,通過聲勢浩大而又曠日持久的社會運動,迫使國家修改立法。這些公民實踐的目的並非改造更大範圍內的教育制度,而是要求父母在教育上的主導權得到法律層面的正式承認,使在家教育納入合法教育的範圍,從而爭取資源的再分配。
在家教育之所以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被髮明出來,不單純是個人選擇或教育領域的變革,而是一種世界觀和生活方式的表述,是更大的社會文化運動的一部分。60年代席捲整個美國的反文化浪潮裹挾着反政府的情感,延伸到教育領域,表現為對公立教育的失望和幻滅感,一些反傳統的教育形式紛紛興起,如自由學校運動(Free School Movement)。反主流反體制構成了當時的時代精神,但它並非一時的憑空建構,而是植根於美國自開國以來對國家權力有所警惕的政治傳統。公眾對政府和學校的失望帶來兩個後果:第一,公立教育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面臨重大危機,地方主義和社區意識增強;第二,專家主義和知識精英受到質疑,反思之後形成這樣一種信念:父母,而不是所謂的專家,才知道什麼是對孩子最好的。這兩個後果直接導致了在家教育的興起。在一部分美國人心裏,當國家共同體不能滿足個體受教育的需要,兩者的契約就遭到破壞,個體有權利承擔起這項任務。這是美國的個人主義文化在教育問題上的自然延伸。但是,“自己教育”雖然有其文化和道德上的正當性,在當時的語境下仍屬離經叛道之舉,早期的在家教育家庭面臨來自國家和社會的種種挑戰,首當其衝的就是合法性的問題。
(二)法律框架內外的博弈
在家教育是不是受法律保護的權利?這個問題涉及兩個層面:首先是聯邦憲法,其次是州法律。美國憲法沒有與教育相關的條款,更未提及“在家教育”,而各州法律起初在這方面則存在很大差異。在正式法律框架裏,在家教育處於一個曖昧可疑的尷尬位置;作為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它被邊緣化以致被排除出主流話語之外。然而,一旦成為公眾討論的議題,多種解釋的可能性就呈現出來。例如很多人認為在家教育是受憲法保護的,理由是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宗教信仰的自由,而許多人在家上學正是出於宗教的動機,並且第十四修正案保護父母的權利,但與此相矛盾的是,各州法律規定孩子必須上學。這些相互衝突的司法原則使地方法院陷入裁決的困境。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到底誰為孩子的教育負責這個問題沒有真正得到解決,使得公立教育的替代形式有了實踐的空間。
由於美國教育是地方分權制,對在家教育產生直接影響的權力機構是地方學校委員會。換言之,在家教育是否可以進行,怎樣進行,是依學區而異,由學校委員會決定的。後者作為國家權力的代理人,通常在兩者關係中享有支配權,它可以選擇善意的忽略,也可以選擇懲戒,將家長告上法庭,而一旦訴諸法律,家長常常處於劣勢。80年代中期的教育官員通常對這樣的家庭懷有敵意,衝突有時達到非常劇烈的地步,在家教育的父母除面臨罰款,還可能被監禁,孩子從父母身邊被帶走,由政府機構看護。在此情形下,家長們要麼選擇與現有的制度協商,使其尊重差異並默認這一模糊地帶的存在,要麼改變現行法律,使在家教育在法律上得到承認。
在這場運動中,由於在家教育的動機不同,這些家庭逐漸分化為兩大陣營,一派是秉承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思想的左派人士,他們是最早的發起者和實踐者,另一派是80年代開始出現的、有強烈宗教訴求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在這場鬥爭中使用的策略也有差別。左派人士最早是60年代反體制、反工業主義的“嬉皮士”,體制機構是他們不共戴天的敵人,而學校在他們看來是體制同化、政治灌輸的主要手段。他們組成小規模的公社,崇尚簡單有機的生活,希望創造一個主流社會之外的烏托邦。在家教育與在家分娩、母乳餵養一樣,是嬉皮士生活方式的一部分。70年代後期在約翰·霍特(John Holt)的領導下,更多的人對學校教育產生批判和反思,決心與其決裂,在家裏對孩子進行個性化的教育,其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尊重孩子的本性,以孩子為中心。基督教陣營反對的則是學校的世俗化,根據1962年和1963年最高法院的判決,學校不準組織祈禱和聖經學習,這讓許多保守的基督徒非常憤怒,並開始考慮建立獨立的基督教學校,或者讓孩子在家裏學習。在家教育與基督教之間存在親緣性,《聖經》就要求父母親自負責孩子的教育,由此這一羣體從人數和聲勢上逐漸超越左派陣營,成為在家教育運動的主力軍。
面對在家教育在美國不被承認的困境,基督教陣營表現強勢,主張積極行動,爭取合法化。保守派基督徒將公立學校比作“撒旦的温室”,他們與學校當局的關係緊張,導致雙方經常對簿公堂。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孤立的個人與龐大的國家機器之間的對抗,每個二人背後都有有組織的支持和運作。賓夕法尼亞州前眾議員比爾·古德靈(Bill Goodling)驚歎於在家教育的父母們對國會山的遊説能力,稱之為“史上最有效的教育遊説團體”。在家教育之所以被稱為一場運動,不僅因為它有自己的理念訴求,有領導者組織者,還有體現在基督教陣營內部的比較嚴密的組織。如1983年成立的 “家庭學校法律辯護協會”(Home School Legal Defense Association,簡稱HSLDA),通過爭取贊助和繳納會費,籌募了數百萬美元的資金,有幾千名工作人員,免費為會員打官司。HSLDA在基督教陣營爭取合法化的鬥爭中表現出巨大的動員力量和作用,例如遊説政府官員,贏取公共輿論支持等,其效果也是顯著的,如推動密歇根州、馬里蘭州等幾個州通過新的法案。俄勒岡州教育部幾次想使在家教育的法規更嚴格化,都被HSLDA組織聲勢浩大的活動挫敗。

相比基督教陣營謀求專門立法的策略,許多左派陣營的家長更傾向於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與政府協商,他們主張與學校當局友好地協商,而不是對抗。事實上,在保守派基督徒湧入這場運動之前,大多數此類的協商都是成功的。為了避免硬碰硬的衝突,家長們的策略還包括爭取媒體的支持,瑞貝卡·珀爾(Rebekah Pearl)曾栩栩如生地記錄了她的父親如何藉助媒體的力量擊敗教育部門,故事發生在1982年的田納西州:
社會服務部聽説了我們不上學的事,就把我父母告上法庭,法官告訴爸爸,要把我們幾個帶走,由州里照管。爸爸不到半小時就約了三個電視台和三家報紙的記者做專訪。記者來了,看到掩映在森林裏的漂亮房子,當時八歲的我在彈鋼琴,哥哥在幫爸爸幹活,四歲的弟弟在池塘邊盪鞦韆。他們談論着爸爸的大學學歷(科學教育)和職業(風景畫家),參觀我家整潔的書房,互相議論着説,如果孩子的測試結果達到州里的水準,為什麼不能在家裏學習呢?爸爸的辦法特別成功,州里再也沒找過我們的麻煩。
在這個案例中,珀爾家的中產階級地位是改變媒體看法的關鍵,而珀爾的父親顯然對自己所擁有的文化資本有清楚的認知,並聰明地將其用作鬥爭的策略。事實上,在家庭和國家機構的博弈中,個體家庭的能動性實踐涉及多重社會力量的動員和參與,公共輿論的支持是一個重要因素。1985年蓋勒普(Gallup)民意測驗表明,70%的美國人認為在家教育不應合法化,但1995年情況發生了翻轉,70%的美國人認為這是一項正當的教育選擇。在家教育之所以漸漸去污名化,很重要的一點是它內化了美國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我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權利;我們認為‘專家’並非那麼值得信賴;我們擔心政府過於侵入我們的生活,卻不能照顧好我們的利益。”1993年,在家教育在美國五十個州全部被認定為合法,這一結果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個個法庭判決的基礎上。“家庭權利高於國家權利”這一自殖民地時期即牢固確立的觀念,保障或者説加速了在家教育的合法化進程,為它在法庭上贏得支持提供了意識形態資源。
▍在家教育的現狀
(一)新自由主義邏輯下的寬鬆教育管制
現代民族國家一向重視教育在政治整合中的作用,尤其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公立教育素來被視為塑造合格公民的場所,為什麼美國在關於在家教育的立法和法律執行上顯得這樣隨意、甘心讓渡自己的權利到父母手中?除了“個體先於國家”的政治傳統,近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轉向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家教育擴張的這幾十年,正是美國福利國家消退、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和私有化導向逐漸佔據主導的階段。在家教育可謂最具私有化特徵的教育形式,它的出現與教育領域的新自由主義轉向不謀而合。
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的調控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經濟原則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新自由主義不僅標榜個人自由的最大實現,也有功利主義的一面,重視公民的人力資本。在這種邏輯下,好公民的標準是不給社會添麻煩,依靠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功,絕大多數在家教育的父母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中產階級,屬於社會假定的好公民,因此國家及學校可以信任他們,對他們的實行教育做放任式的管理。
全球化帶來的移民問題也對原有的教育制度造成衝擊。今天的美國城市裏聚集着大量經濟上處於劣勢的移民,而公立學校則要“在一個經濟動盪、文化不安的時代教育人數眾多而且不斷增長的移民出身的孩子”。受訪者艾拉住在波士頓附近的薩摩維爾(Somerville),她表示:“薩摩維爾不大,但學校面臨不少問題,這裏的人口非常多元化,學校裏有高達50%的孩子不會説英語,需要上ELL(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課。政府巴不得我們不上學呢,而且不上學也交一樣多的税,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用來支持公共教育的。”
(二)公立學校的衰落
在家教育興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為主導教育形式的公立學校深陷危機之中。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Education Statistics)2016年的調查顯示,多達80%的父母表示,“對學校環境的擔憂”是讓孩子在家上學的首要原因。
事實上,美國公共話語中的公立學校,尤其是城市的公立學校體制,普遍以失敗的形象出現,因此公立教育改革一直在進行之中,總的趨勢是聯邦政府開始更深地介入本是屬於地方事務的教育領域,更多選拔性測試(high-stake standardized testing)開始實施。尤其進入21世紀以來,聯邦政府對教育的干預逐漸增多,2001年小布什總統簽署“不讓一個孩子落後”的教育法案,2010年6月美國教育委員會正式頒佈首份中小學統一課程大綱——通用核心課程標準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試圖將各種各樣的州立課程規整為統一課程。
然而,聯邦政府這些旨在提高教育質量的措施引起了極大的爭議。許多中上階層父母指責這些措施“愚化頭腦”(dumbing down)。許多人認為改革只是加大了老師和學校的壓力,對於教育的主體——學生卻作用甚小,甚至不利於學生。統一課程大綱的核心是學校教師問責制,聯邦政府根據學生學業成績決定學校撥款和教師工資,這使得教師的教育方式越來越向標準化的考試傾斜。
筆者發現,不管是出於何種動機選擇了在家上學,幾乎所有的父母都表達了對以考試為指向的教學範式的反感。反感的根源在於考試所導致的學習工具化和標準化強化了教育的規訓功能和政治經濟導向,服務於國家立場,與人本主義的訴求相牴觸。受訪者託尼曾在公立高中任教,現在是麻州一所大學的老師,他在訪談中指出,“美國教育體制總的趨勢是同質化而不是個性化,儘管我們以為(並被告知)我們是自由的個體,但若你仔細看,並非如此,我們的教育體制就是把方的釘子楔進方形的洞裏,沒有其他形狀的位置。”
在家教育是美國文化特性與現代性擴張下的典型產物。與前現代社會的“家庭教育”不同,它並非自然形成,而是始終伴隨着對公立教育與國家權力的反思和批判。從一個個草根行動者到宏觀層面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和公立教育的危機都極大地推動了它的發展。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萌芽,八九十年代的爭取合法化鬥爭,到21世紀以來的快速發展,在家教育還在以令人難以預料的方式繼續發展着。如今美國的公立教育、私立教育與在家教育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這使得在家教育日益受到國家和市場的兩種拉力。近年來,在家教育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新型模式,比如網絡虛擬學校是一種介於在家教育和學校教育之間的形式,由政府出資,家長監管,學生在家裏學習。表面上看,它的確是“在家”進行的教育,但其學習內容與考核標準的制訂主導權都在政府,而不是父母。還有一種由私人出資聘請老師的自主學習中心,家長可以選擇將孩子每週送去一至五天不等。這種商業化的替代性教育令真正在家教育的父母們擔憂。他們擔心虛擬學校和自主學習中心會拉攏更多家長,改變在家教育的性質。

— 2020年8月新刊目錄 —
▍域外
美國:重回“分裂之家”?
吳 雙
▍特稿
01.21世紀之惑——疫情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問答
李 陀
▍封面選題:疫情改變中國與世界
02.疫情危機與中國思想界的任務
柯貴福 鄭 濤
03.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權的危機與不確定的未來
魏南枝
04.美國長期金融資本向何處去?
唐毅南
05.多難興盟?——新冠疫情與歐盟的秩序危機
章永樂
06.新冠疫情與中國改革
趙鼎新
07.上下聯動:全球化的“義烏模式”
錢霖亮
▍天下
08.在西方講中國哲學
孫向晨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09.公益的“中國式合作”道路——陝西婦女研究會的實踐經驗
高小賢
10.本土傳統慈善文化的價值與反思——以汕頭存心善堂為例
韓俊魁
▍重述世界史
11.西方工業文化中的“國家理由”
嚴 鵬
▍城市政治經濟學
12.城市病是一種什麼病?
譚縱波
▍觀念
13.小康語義的歷史變遷與現代啓示
張 文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8月刊,原標題為《逃離學校:美國在家教育的興起》。篇幅有限,有所編刪,註釋從略。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