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經濟學家選擇自殺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9411-2020-09-07 14:17

"
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來説,永遠是個謎。而面對最後的結果,人們往往只知道去責備他而不是去了解他。
可惜自殺者永遠沒辦法告訴別人,他為什麼要自殺。
" alt=“500” />講述 | 梁捷
來源 | 《別怕,這就是經濟學》
今天我們要來談一個沉重的話題,經濟學家為什麼要自殺。
過去我讀過一篇文章,“詩人為什麼要自殺?”詩人自殺也許還有一些文化上的意義,但是在大眾的印象裏,經濟學家從來都是以長壽而著稱的。
比如薩繆爾森,活到了94歲;弗裏得曼,也是94歲;阿羅,96歲;哈耶克,93歲;科斯不得了,活到103歲。經濟學簡直稱得上是長壽學科了。
但是,近期聽到的新聞卻讓我們開心不起來。哈佛大學的宏觀經濟學家法希(Emmanuel Farhi)教授自殺去世,年僅41歲。

Emmanuel Farhi
他並不是個例。去年,經濟學界就陸續傳出新聞,哈佛大學的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自殺,然後是普林斯頓的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教授自殺。今年前兩個月又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桑德霍爾姆(William Sandholm)教授自殺。而現在,又是宏觀經濟學家法希自殺。
除此之外,在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間,我還聽説哈佛的艾萊斯納(Alberto Alesina)心臟病去世,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新冠肺炎去世。這些都是響噹噹的名字,一大半未來都有可能獲得諾獎,或者已經得到多次諾獎提名了。經濟學界可謂損失巨大。
很多人都在問,經濟學這個行業怎麼了,經濟學家為什麼要自殺?
1.
自殺,不是一個可以扁平化的問題
其實我也想問這個問題。因為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學者的研究領域其實各不相同。
比如魏茲曼是環境經濟學家,他很關心風險和不確定性對於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導致災難的影響。克魯格是勞動經濟學家,主要研究教育、收入分配、勞動力市場。
桑德霍爾姆主要研究博弈論裏的一個分支,叫做演化博弈論。法希則主要研究宏觀經濟學。這些學科相差很遠,所以這些學者的自殺與專業領域看起來沒有直接關係。
但這些學者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他們的學術研究非常非常成功。普通學者想要在頂級期刊上發表一篇論文,都要費九牛二虎之力,還不一定能成功。但對於這些頂級學者而言,發論文就像吃飯睡覺一樣。
上面提到的每一個學者,都已經發表了不計其數的優秀論文。一般的學者如果無法發表足夠多的優質論文,在美國的大學都要面臨終身教職的壓力。而這些學者,早就不用考慮這些問題。按照我們的世俗標準,個個都稱得上是功成名就。
如果這樣,他們為什麼還要要自殺呢?經濟學家以前曾研究過自殺問題。
哈默梅什(Daniel S. Hamermesh)與索絲(Neal M. Soss)兩位學者1974年在頂級學報《政治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一種自殺的經濟理論”,對自殺行為構建了一種微觀經濟模型。
這篇文章後來受到芝加哥大學加里·貝克爾(Garys Becker)的高度讚揚並廣泛引用。人們開始驚呼,原來經濟學連自殺也可以研究,怪不得是“經濟學帝國主義”。
這篇文章今天似乎不太有人再提起。它構建了一個變形的效用函數,然後把自殺行為與經濟收入等因素聯繫起來。
作者最後得到結論,隨着預期收入的不斷增加,自殺率將會顯著下降。這個預測很符合經濟學直覺,但並不符合現實數據。富人也自殺,窮人也自殺,自殺的動機與經濟收入似乎有關,但比這要更復雜。
後來追隨這種思路的研究不多,馬里蘭大學的馬科特(Dave Marcotte)算是其中一個。他找到一類人,就是嘗試自殺而不成,最終活下來的人。
他發現,嘗試過自殺的人活下來以後,就比那些同等想過自殺而未嘗試自殺的收入要高出20%。同時,這些免於一死的人,活下來之後的收入也比自殺前提高了36%。如果自殺可以作為一種經歷的話,它有助於人們重新反思生活,並且有效地提高收入。
到今天,似乎很少再有經濟學家繼續研究這個方向了。
大家都清楚地意識到,自殺性爆炸的恐怖主義者,與考試沒考好而自殺的中學生,他們的自殺動機有着天壤之別,不可能用同樣一個效用函數的模型加以解釋。
無論是用理性選擇模型來推測自殺者的動機,還是把自殺作為一種經歷,都把自殺這件事給扁平化了。
2.
經濟學家們,正在經歷什麼?
自殺的這些學者們,其實都不見得是書齋裏的學者,都有非常多的兼職和社會活動。
就以艾倫·克魯格為例,他先後在克林頓、奧巴馬等幾任政府裏擔任首席經濟學家或者經濟顧問這樣的職務,而他還熱衷於聽音樂,參加演唱會。

Alan Krueger
他實在太忙,過去不可能有時間寫通俗的經濟學著作。就在去年,他終於結合自己的興趣,寫作了第一本科普著作《搖滾吧,經濟學》,今年中譯本出版。
讀過手稿的媒體都給予了高度評價,都在感慨,克魯格終於願意寫書了。但克魯格根本沒看到這本書的出版,他在新書出版前夕自殺了。
這些學者在學術領域和世俗層面都是成功者。但他們仍然選擇了自殺。我相信很多經濟學家都讀過他們的論文,瞭解他們的工作,連我都多少讀過一些。但是我們對於他們的瞭解遠遠不夠。
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來説,永遠是個謎。而面對最後的結果,人們往往只知道去責備他而不是去了解他。可惜自殺者永遠沒辦法告訴別人,他為什麼要自殺。
據説魏茲曼教授曾經在一年前留下一張紙條,懷疑自己是否能繼續產出有價值的學術作品。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環境經濟學,但是沒有頒給魏茲曼。
又有人説,魏茲曼寫了一篇論文,發給同事們看,有人指出了其中的一個錯誤。這些小事當然可能影響魏茲曼的情緒,但是否是導致他自殺的原因,我們永遠不知道了。
引發自殺可能只是很偶然的事。但一般而言,產生自殺這個念頭絕不是一天兩天。自殺的人,往往經歷了長期的折磨,可能是數年,數十年。
而且,越是表現出所謂“高功能”的人士,即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都表現得積極向上甚至能力遠超一般人的人士,如果是抑鬱症患者,他們的所經受的痛苦就越嚴重。
從事過學術工作的人都知道,在學者或者學生中,這樣的比例很高很高。豆瓣或其他社交網站上都有一些互助小組,也許給一些深陷科研痛苦的人士一點點安慰。
不同人面對抑鬱痛苦有不同的表現。我沒有辦法給出什麼意見或者建議。有人會説,如果那麼痛苦,就不要做科研了。世界那麼大,做點其他的不也挺好嗎?科研工作太苦太累,對腦力、體力以及意志力都是考驗,而且是終身考驗。
比如説,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不知道一般人能對自己的文章修改幾遍。很多作者可能會修改一遍,兩遍,我還知道一些名作家拒絕修改自己的文章。
那麼現實中經濟學家面對的情況呢?如果你要在過得去的經濟學期刊上發表論文,那麼一篇文章修改個十遍以上是最起碼的;如果你要在頂級經濟學期刊上發表文章,那可能得修改三十遍或者更多。

我曾看到一個非常優秀的青年經濟學家,發表一篇論文以後,有些感慨,在朋友圈曬了一下他的修改過程。他把每一版都另存為一個文件,最後修改到90多稿,近100稿,文件夾裏就有90多個文件。我估計,最終稿與初稿相比,可能每個字都重寫過了吧。
這種學術制度對於寫作者、研究者的自尊心是一個極大的考驗。所以我見過很多研究者,因為無法忍受學術界的這種制度,毅然退出。
有一位同樣非常優秀的學者,以前曾是大學教師,現在則是某個大數據公司的高管。他經常在知乎上寫文章,也是個網紅。
他表示自己更喜歡在知乎上寫作,因為讀者馬上就能看到,並且作出反饋。以前給學術期刊寫作,要修改幾十稿,前後數年,發表出來其實也沒什麼讀者會看。
所以,這些發表壓力一直在折磨着當代學者。想當年,弗裏德曼、哈耶克等人的那個年代,學術規則沒有那麼明晰,也沒有那麼死板。
很多學術期刊還很靈活,可以主動掌控學術熱點,碰到重要的議題,甚至可以給一些重要文章提供連載的機會。這在今天都絕不可能。而今天頂級學者所要承受的發表壓力,也不是弗裏德曼、哈耶克那時所能相比了。

每一次自殺都是一個絕對的悲劇。我既不想批評死者,也不想簡單歸罪於這個學術系統、學術體制。
現代學術體制存在很多問題,我們以後會慢慢討論,慢慢批判。而對於悲劇,我建議我們不妨更多地去加以理解,加以同情。
3.
不如誠實地接受對人類複雜性的無知
雖然很多人都認為經濟學家是高度理性的,且對於未來有更高的把握,但實際上,經濟學家往往需要比其他人面這個世界更多的本質不確定性。
絕大多數嚴肅的經濟學家都會承認:“我們不會算命,無法預測未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對於未來並沒有肯定性的知識。”
已故的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經開玩笑説,“我們經濟學家們,對過去發生的五次經濟危機,預測準了九次”,這也是經濟學家無奈的自嘲了。
經濟學家可以坦率地承認自己的無知,倒也不是經濟學家的臉皮特別厚,而是經濟學家對這個世界的複雜性有比較豐富的經驗,知道自己的無知,這反而是一種誠實的美德。
“準確”這個概念,跟我們用什麼標準來評估有關。
就像氣象學家會告訴你,如果研究的時間越長,範圍越大,那麼影響天氣的因素就越多。各地的温度,濕度,風向,降雨,都會對天氣產生複雜影響。
相信你也聽説過“蝴蝶效應”這個名詞。在一個足夠複雜的系統裏,任何一點微小的擾動,就有可能產生極為嚴重的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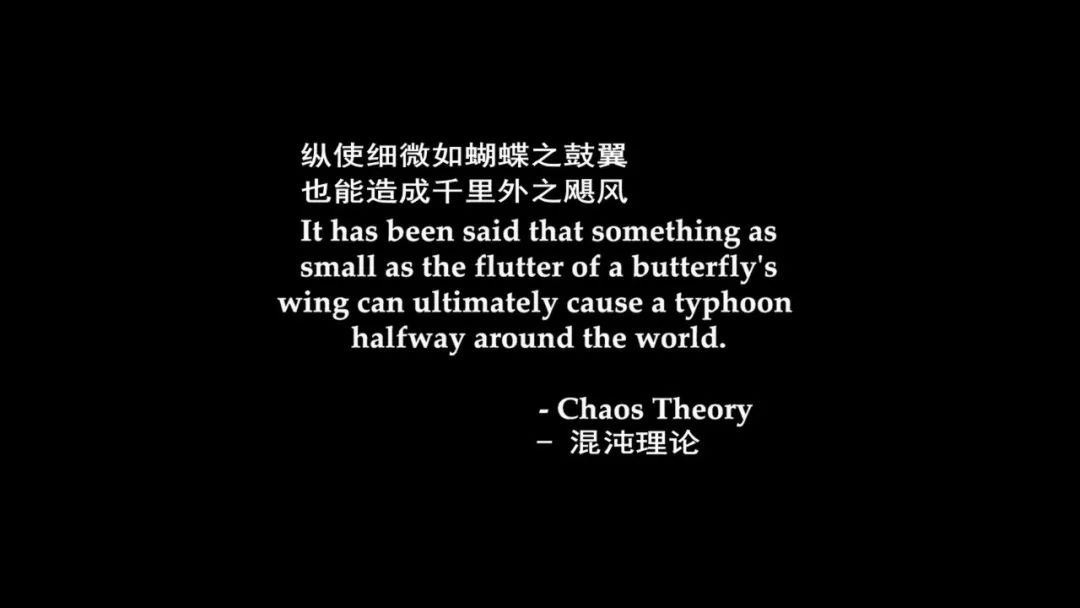
這個世界本身充滿了不確定性。
比如每年的颱風季雖然都是大致確定的,但是它的強度、路線、破壞程度都不一樣,這一切都很難預料。
中國人民已經經歷了千百次颱風了,幾乎每年都要經歷,但我們仍然無法預測下一次颱風的影響和危害,只能利用我們的經驗,儘量讓颱風的危害降到最小,在台風之後又能儘快地恢復。
這是我們面對這個世界最真實、最謙卑的態度。
過去曾有一種批評叫做“經濟學帝國主義”,即有一些經濟學家試圖以經濟學的方法來闡釋世界——到了今天,這種方法早已過時,今天的經濟學家反而希望借鑑各種學科、各種跨學科的方法,來豐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