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藝謀到趙婷:威尼斯的三種華人倒影_風聞
娱乐硬糖-娱乐硬糖官方账号-2020-09-17 07:47

作者|謝明宏
編輯" alt=“500” /> 2017年的多倫多電影節,尚未加冕奧斯卡影后的麥克多蒙德,看完《騎士》後深感震撼。她大聲喊:“誰他媽的是趙婷啊!”
三年後,麥克多蒙德主演並擔任製片人的《無依之地》,拿下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的最佳影片金獅獎。而《無依之地》的導演,正是她當年不認識的趙婷。
趙婷是誰?《無依之地》又是怎樣一部電影?路人的疑惑並不比曾經的麥克多蒙德少。從1989年的《悲情城市》到2020年的《無依之地》,共有6位華人導演斬獲金獅獎最佳影片,而趙婷更具突破性的意義在於——她是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中國女導演。
儘管此前萊妮·裏芬斯塔爾、阿涅斯·瓦爾達、索菲亞·科波拉等女導演都得過金獅獎。但將趙婷的名字放在侯孝賢、蔡明亮、張藝謀、賈樟柯、李安的後面,仍然不免驚歎華人導演作品的代際變化,及其背後折射的三十年中國鉅變。
除了《斷背山》,過去叩開金獅獎殿堂的華人導演作品,都在講中國人自己的故事。蔡明亮和侯孝賢的《愛情萬歲》和《悲情城市》展現台灣地區的城市化進程,張藝謀和賈樟柯的《秋菊打官司》和《三峽好人》描摹內地圖景,李安的《色戒》轉向近代洪流中的個人情感世界。
趙婷的《無依之地》跳脱了前一種路徑,選擇以“旁觀者”的方式解構美國社會的變遷,不得不説是華人導演徹底國際化的嘗試。一箇中國女性自編自導了一部無家可歸的美國婦女的故事,這在以前很難想象。
她沒有用自己更熟稔的中國文化去迎合外國人的好奇心,也沒有通過精心打扮去凸顯自己的東方之美。問題是,一個新的華人導演電影時代會被開啓嗎?或者,她的成功對於國內導演的培養體系是否有借鑑意義?
牛仔與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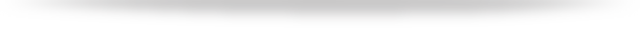
儘管金獅新貴的標籤更炫目,但國內媒體的報道,總少不了“宋丹丹繼女”這個前綴。
1997年,宋丹丹與趙玉吉結婚,成了趙婷的後媽。宋丹丹在節目上公開談過,趙婷第一次看到她時,用恨恨的眼神從牙縫裏擠出了“宋丹丹”三個字。
趙婷與巴圖的關係,就像《家有兒女》中的小雪和劉星。至於兩人後來關係破冰,趙婷喊宋丹丹媽咪,宋丹丹賣力在微博為女兒的電影宣傳,則是這對“半路母女”的後話了。
國內媒體糾結宋丹丹繼女的標籤,但從趙婷的成長經歷來看,恰好可以解讀《無依之地》中對自我身份的尋思。她好像一直在尋找自己的“無腳鳥”,從小叛逆,愛看漫畫還寫過同人小説。
高中時赴美留學,是她對自己的第一步自證。酒吧的打工經歷,讓趙婷學會了和各色人等的交流方式。紐約的Tisch學院畢業後,她離開了一直生活的城市。Vogue的採訪裏,趙婷説:“我想把自己建立的所有身份都剝離掉,去一個沒有人知道我是誰的地方,這樣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誰。”

趙婷去了美國西部南達科他州的印第安保留地,拍攝了關於拉科他族人的處女作。她的狀態有多沉浸呢?當地人把她叫成“那個有中文名字的拉科他族姑娘”。
正是這種心靈深潛,讓她可以拍出類似早期泰倫斯·馬力克的靜止美與永恆感。而當馬力克同意審閲《無依之地》的樣片,趙婷感受到了與偶像同行的欣喜。兩人的緣分妙得很,馬力克47年前的處女作《窮山惡水》也是在南達科他州拍攝的。
《無依之地》講述喪夫的Fern在石膏廠倒閉後失去了工作,她生活了一輩子的內華達小鎮,將從地圖上的郵編除名。年逾六十的她,不得不住在麪包車裏打起季節工,並一路穿越美國,成為現代遊牧族。
為期四個月的拍攝中,趙婷與《無依之地》的劇組成員過了一把Fern式的遊民生活。趙婷緩慢滑動鏡頭,讓人感受到壯麗與抒情的同時,又不失去真實與堅毅。麥克多蒙德的表演固然神乎其技,但執鏡的趙婷沒有試圖煽動觀眾為Fern感覺難過,只是白描出她的孤寂和悲傷。

正是這份真實與灑脱,讓她擺脱了人們對於華人女導演的刻板印象(她的上一部長片《騎士》就非常有地道第牛仔風韻),握住了超越文化藩籬的人性之光。
即將執導漫威新片《永恆族》的趙婷,從小就是漫畫迷,她還給房車起名“阿基拉”。什麼樣的一個人,可以用淡定自信的方法拍一個遠離自己文化根基的故事?趙婷給出了答案。
西部與三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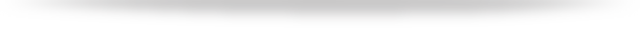
華人導演上一次拿金獅獎最佳影片,要遠溯到背靠背的2006年《三峽好人》與2007年《色戒》。和趙婷完全“走出去”不同,賈樟柯與李安是“一隻腳在門檻內”的一代,即便身子出去了,題材也要尋根。

《三峽好人》的主題是尋找。山西煤礦工人韓三明,終於在奉節找到了分離十六年的妻子,兩人共同離開奉節。山西護士沈紅到奉節尋找做生意兩年未歸的丈夫郭斌,最終兩人分手,沈紅獨自離開奉節。
電影中似乎所有人都在經歷聚散。高音喇叭大聲播放“前往崇明島的移民請注意”,船上的廣播放着《女駙馬》的“為救李郎離家園”,拆遷辦職員擺弄着死機的電腦嘟囔:“我們搬遷到廣東、遼寧到處的都有。”
這是發展的陣痛,是國家和個人為求生存幾乎必經的一種離散。想想每年的“春運”,除了中國,在哪裏能看到這樣大規模的人類遷徙?片中小馬哥用發哥的話説:“現在的社會不適合我們,因為我們太懷舊了。”

自詡“電影民工”的賈樟柯,用《三峽好人》展現了世紀之交城市轉型中的底層人物羣像,試圖還原大時代下被忽視的邊緣羣體。但他沒有懷揣着對過往的惡意,也沒有對痛苦控訴。
這與定位在美國經濟下滑背景的《無依之地》似乎有着內在傳承,只不過旁觀的趙婷比賈樟柯更冷眼。與處處廢墟待重建的賈氏不同,趙婷習慣用長鏡頭拍攝美國西部的壯麗地平線,用詩意去反襯生活的荒蕪。
《三峽好人》是中國西部,《無依之地》是美國西部。李安的《斷背山》,也發生在美國西部。
華人導演想要在好萊塢立足,必須要用地道的美式題材自證。李安對自己的定位是遊離於中西文化的邊緣人,基於這種定位使得他在2005-2007年這一時期選擇了《斷背山》這樣的西部+邊緣題材。

西部風光下,《斷背山》呈現出了一種縱深感:表面上表達了對愛的期盼,可以歸結為愛情主題。但從作品的最終指向看,主角對愛的渴求,正是來自於社會邊緣的人生狀態。他在邊緣狀態獲得了同性之愛的慰藉,然後終其一生都將被這一慰藉所照亮。
趙婷的《騎士》也是邊緣的:受傷的主人公,酗酒的爸爸,阿斯佩格綜合徵的妹妹,受傷癱瘓的朋友。與李安相比,趙婷並不依賴好萊塢的戲劇性,也不屈從於文藝片的虛無,而是選擇了一種坦誠的敍述手段,最終讓故事比西部還西部。
城市與農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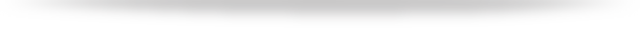
1989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獲金獅獎時,趙婷還是一個四處蹦躂的北京小妞。不像她可以大方地講美國故事,侯孝賢、蔡明亮和張藝謀當時有太多的中國故事要呈現。

唯一的分野是,侯孝賢和蔡明亮講城市,而張藝謀講農村。《悲情城市》通過展現基隆林氏家族的興衰,來折射時代變遷以及台灣人民在變化之中所面臨的身份認同焦慮。
電影開頭營造的喜悦氣氛,轉瞬就被接二連三的死亡所衝擊,林家的四個兒子沒有一個逃脱政權更迭帶來的悲劇。大哥死於流氓槍下,二哥下落不明,老三被釋放後發瘋,老四捲入紛爭被捕。
《悲情城市》中的家庭悲劇是切近日常體驗的悲劇,在面臨身份認同危機時,人民只有被迫接受上層建築變遷的後果。知識分子老吳説:“當初也是清朝把我們賣掉的,《馬關條約》有誰問過我們願不願意?”
侯孝賢用電影留下了一個缺口,當身份焦慮成為纏繞孤島的幽靈,悲情之後又該走向何方?城市的悲情看不見,農村的問題卻摸得着。在《秋菊打官司》中,權力和情理是鄉間古老秩序結構的主要成分。秋菊因為不甘心臣服於村長的權力,而固執上訴。

張藝謀真實地再現了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個人與社會法律之間的微妙關係。秋菊的固執最終換來失落與尷尬,撕裂了其樂融融的鄉間酒宴圖,可見個人存在於社會法律結構之間的疏離。
而在《一個都不能少》中,張藝謀將淳樸真誠的鄉村,與世俗冷漠的城市進行對比。雖然水泉小學處於缺錢的困境,但這個世外桃源還在關注着每一個人的命運,追求“一個都不能少”。但在喧囂的現代都市,則是少一個也無所謂。
從侯孝賢到賈樟柯再到趙婷,三代華人導演在威尼斯電影節留下的印記,似乎是身份與視角不斷剝離的過程。生根黃土地的侯孝賢與張藝謀,把城市與農村的真實光影帶給世界,既是紀實的也是隱喻的。
見證台灣地區經濟騰飛的李安,與見證內地改革開放的賈樟柯,則有了外部審視的可能;80後的趙婷十幾歲出國,最終蜕變為文化遊民。即便左手拍《無依之地》裏破碎的美國,右手拍漫威的新階段的超級英雄,也不會讓人感到奇怪。

張藝謀無法拍出《騎士》這樣的美國西部片,趙婷也不可能造出新時代的《秋菊打官司》(科恩嫂大鬧聯邦法院也許還行?)文化根源使然,並不讓人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