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年,我接觸了兇殺、家暴、詐騙、販毒,也接觸了電話接生、落葉歸屬這些事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9515-2020-09-17 07:42
來源:一席
王篪,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講師。
你能想象到的事件,你想象不到的事件,可以説從生到死,這兩者之間的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出現在911應急電話裏面。
不在場的救助
2020.8.23 杭州
大家好,我叫王篪。我是社會學博士,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是我在美國911應急中心做的研究。
2011年我在美國東岸、西岸兩個調酒師培訓學校做調酒師的培訓, 我
當時 對這個職業非常感興趣。進入田野以後,我發現有一個方面是我沒有預料到的,就是這個工作需要做很多判斷和決定。
因為美國合法喝酒的年齡是21歲,但是很多21歲以下的人會想方設法在酒吧購買含酒精的飲料。培訓老師當時拿出了大概20多種假ID,有假的軍官證、假的州政府ID、假駕照,説這些都是他們會用來騙我們的手段。
他還教我們怎麼問問題,比如問了顧客的生日以後馬上問星座,或者先跟他聊一聊,放鬆他的心防,然後突然一下問,你哪年生的。
這個研究結束以後,我就對這種在複雜情況裏做判斷的工作非常感興趣,就想做這方面的博士論文。我當時對11種職業做了比較,決定要研究 在千變萬化的情況裏做判斷的集大成者——911應急中心。
1967年,美國把消防、警務、醫療這三個力量統合起來,把報案電話統一為911。到2016年,就是我這個研究完成的那一年,美國共有5893個911應急中心,全美國當年的911應急電話報案量是2.4億。
不管是消防、警務,還是醫務,這三種案件都會通過911這個號碼到達應急中心。應急中心的接線員必須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做出判斷並與派遣員交流。派遣員會根據事件性質派遣前線人員到案發地點,前線人員就是火、警、醫療這三種力量,人和車輛的各種排列組合。
這三年時間, 我在這個應急中心接觸到了搶劫、火災、風災、雪災、兇殺、家暴、詐騙、販毒、車禍、傷病、電話接生這些事件,也接觸了鄰居吵架、小偷小摸、派對噪音、違章停車,以及落葉歸屬這些事件。
這些事件都是我在一箇中等城市的911應急中心接觸到的。我當初申請這個中等城市,是因為覺得它那裏接到的案件會足夠複雜,但是案件又不會特別密集,這樣我還是會有時間跟他們做比較深入的交流。
經過前期一系列的準備,最後一步就是要獲得倫理委員會的批准了。2013年4月15號,這個日子我記得特別清楚,那天早上我接到一封郵件,倫理委員會的人就説,恭喜你,你的這個研究被批准了。
當時我心裏的石頭終於落了地,可以到911應急中心開始我的研究了。當天下午,我住的這個城市,波士頓,發生了恐怖襲擊,有恐怖分子在正在舉辦的國際馬拉松上引爆了兩顆炸彈。

當時我沒有意識到這對我有什麼直接影響。他們鎖定了犯人以後,就把城市封鎖了,然後開始追緝這個犯人。他們在搜索的時候,我發現恐怖分子住的地方離我住的地方特別近,所以就有直升飛機在我公寓的上空盤旋。隨着螺旋槳的旋轉,我就可以看見窗口忽明忽暗。
後來他們把恐怖分子緝拿歸案了,這個城市就慢慢恢復了平靜。然後我就發現自己不太對勁,我當時什麼狀態呢?走到外面馬路上,看見停着的車和垃圾桶, 我就很害怕,覺得它會爆炸。當然這種推測是非常不理性的,也沒有什麼邏輯,因為當時恐怖分子也不是這麼犯案的。
但是我就因為這種幻想,經受着非常真實的恐慌。那個時候學校也給大家發郵件,説你們剛經歷重大案件,有需要心理疏導的可以打什麼什麼電話。所以我就人生第一次打了求助電話,就是打哈佛校醫院的心理諮詢,跟那些專業人士聊了聊。
我記得他們也沒有給我提什麼特別具體的建議,但是在跟他們聊完以後,我 就感覺好了很多,慢慢地,我的這種幻想就消失了。
5個月以後,2013年9月,我就開始了三年的田野研究。這個應急中心每個接線員面前大概有9到12個屏幕。節奏轉換也很突兀,有時候可能突然進來好幾個電話,過一會兒就戛然而止,什麼也沒有,他們甚至還有時間閒聊一下,開個玩笑什麼的。 因為需要保密,這不是我當時所在的應急中心的圖片。
應急中心給了我一個工位,還給了我一個只能聽但不能講話的電話,這種電話他們一般是給實習生和試用期的人用的。當然他們也跟我約法三章,比如不允許錄音,不允許錄像,不能帶電子的信息出這個應急中心。所以我所有的電話記錄,還有我的田野筆記都是手寫的。
我會跟應急中心的人值早班、晚班和通宵。這個是我當時的值班表。
這個應急中心有40個接線員,男女各一半,除了三個黑人,一個拉丁裔的人,其他都是白人,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大概佔1/3左右。 在和這40個人都比較熟悉以前,有那麼一個人,叫James,我進去的時候,他剛進去工作不久,等我研究結束,他成功跳槽去做警察了。 他的同事叫他hard-charger,這個詞是當兵的人用的一個詞,形容表現特別突出,特別有積極性。
James特別喜歡跟人分享他的案件,講自己的思路。他這種健談的性格幫助我很快進入了狀態。所以今天我這個演講裏,會有很多James的例子,當然我也選取了很多別的例子,這些都是我認為 的 911 應急工作裏面比較有共性的例子。
判斷
從一個電話打進來,到應急行動完成之間,這裏面最關鍵的一步是什麼?就是確定這個事件是什麼事件——判斷這個事件的性質。
這個判斷一般是在幾秒鐘到幾十秒鐘之內完成的。因為時間是應急工作裏最寶貴的要素之一,時間就是機會,是逃跑的機會,是生存的機會,是從各種各樣的困境中解脱的機會。
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做這麼重要的決定,卻是在沒有任何視覺信息輔助的情況下完成的。什麼叫沒有任何視覺信息輔助呢?就是所有關於這個案件的信息,全都是通過語言來交流的。但語言所表達的事情,它和這個事件的實質之間,經常是有一道鴻溝的。這個鴻溝就需要911應急人員,用他自己的智慧、同理心和經驗去逾越。
比如有一次James接了一個電話,有一個人説,我和我的伴侶在家裏用氨水和Clorox做大掃除中毒了,希望你們能派救護車來,給我們一些醫療救護。James就問,你們家的窗户是開着的還是關着的?這個報案人就説是關着的。
James把電話掛了以後,就判定這是一個吸毒過量的案件,然後派了救護車,還派了警車。我當時就比較驚訝,問他為什麼派了救護車,還派了警車?救護車為什麼不夠?為什麼判斷這是一個吸毒過量的案子?
他説,你聽沒聽見我剛才問他,你的窗户是開着的還是關着的。誰家大掃除還要把窗户都關上?還説什麼用氨水和Clorox做掃除——Clorox是美國一個清潔用品的牌子,其實他們肯定就是被海洛因搞翻的。 這個情況就是報案人為了逃避法律責任,有意隱瞞了事件的真相。
但是有時候因為各種原因,這個報案人可能沒有真實表達案情的自由,這種情況就需要這個接線員對報案人的語氣,甚至電話裏的環境進行解讀。
比如有一次一個接線員接到好幾遍從同一個號碼打來的電話,每一次她都説不好意思,我打錯了,沒有什麼事,都挺好的,謝謝。這個接線員就覺得不對,他最後還是跟派遣員説了,然後他們就派了人去。
後來前線反饋過來的信息是確實有事,打電話報警的這個人她常年受到家庭暴力,幸虧派人去了,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我就問這個接線員,你當初是怎麼覺得有事情的? 他説我就是覺得她的語氣不是特別對,而且她有一次説完了以後沒有馬上掛,過了幾秒鐘猶豫了一下才掛的,我就覺得這個是有問題的。
實際上有的時候,報案人沒有因為主觀或者客觀的因素隱瞞這個事件的性質,他比較誠實地反映了事件的性質,但是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個什麼事件。
比如有一次有一個人打進來説,我現在在一個飯店門口等我的披薩,我發現一個人就在那兒開車轉圈,放下一個人再接一個人,每一次車上都是坐着不同的人,我發現他已經跟六個不同的人在一起了。
他這個事情説完後,我就完全不知道他説的是個什麼事。當時處理這個案件的人是那個小組的主管,她把電話掛了以後就往應急中心其他同事那個方向喊,説這是個販毒的,這是個販毒的。
這是他們根據工作經驗進行的判斷,有的時候可能這個報案人沒有隱瞞,這個事件也不像剛才我舉的這個例子這麼隱晦,但是報案人的情緒可能會造成對事件判斷的困難。
我們可以把911應急中心想象成一個小概率事件的集散中心,就是在別人人生之中發生的小概率事件,重大的有人生轉折性質的惡性事件——我希望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在大家身上,這種事件會以一種批量的、很密集的方式,發生在911應急中心的電話裏面。
人在遇到這種事件的時候,他的情緒可能是我們處於常態的人不太能夠理解的。 James就跟我講,你很難通過報案人的表面情緒來判斷這個事件的惡劣程度,你必須懂得怎麼挖掘他深層的情緒。
比如有的人其實就是車停錯位置,他早上起來發現車被拖走了,然後就打911報警,大喊大叫,好像天塌下來一樣。其實這個事件它連一個應急事件都不算,你打保險公司電話,打拖車公司電話就解決了。
有的人打電話進來,好像要去跟人玩兒命。後來問問他是個什麼事兒,就是秋風掃落葉,落葉到誰家院子裏面了,該誰掃,落葉的界限在什麼地方,就這麼一個事。
但是有的人可能親眼目睹或者親身經歷一些特別嚴重的情況,他打電話來的時候,情緒卻很理性,很平靜。
比如James有一次就接了一個電話,有個人發現了一個熟人的屍體,而她離這個屍體也不遠,她打電話來的時候語氣很平靜。James就跟她説,你別掛電話,我也不會掛電話,你就跟我一直説話,説到我前線的同事到你身邊為止。
後來James就跟我講,人在受到身體重創的時候,一開始幾秒鐘是沒有感覺的,然後可能才開始感受到劇痛。他説人在受精神打擊的時候,道理是一樣的,前面有一段很短的時間,你可能沒有什麼感覺,然後才開始有沉重的打擊或者消沉的感覺。他説他當時覺得這個報案人就處在那一小段時間裏面。
他想做的就是在這個電話裏面,盡他自己的可能把這一小段時間延長,至少延長到他前線的同事趕到她身邊為止。
最難的事就是從一個不好的電話裏走出來
時間長了我就發現James有一個特點,就是他想象一個事件特別負面,而且特別具體。比如有一次他接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是一個大學生失聯,當時這個案子還沒有結,事情還正在調查之中,我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James把這個電話掛了以後就跟我説,我覺得她死了。
我就很驚訝,然後他馬上給我描繪了一個非常詳細的場景,就是這個人她想了些什麼,然後到她的房間裏面,播放她最喜歡的音樂,然後怎麼樣結束了她的一生。
後來這個事件的真實情況是什麼?這個大學生沒有事情,這個案子也結了。
但是James描述的場景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後來我就發現應急中心別的人也有這種思路,我就很想知道是為什麼。
等到我開始參加他們的新人培訓的時候,我就慢慢理解了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想事情。新人培訓大概要培訓一年時間,我發現他們在這個培訓裏面特別重視強化一種“最差情境原則”。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所推測的那個事件,一定要比這個事件本身差,而且最好是最差的,這樣才能夠保證你派出的力量,足夠應付實際發生的情況的,所以這個應急中心裏比較有經驗的老員工都會非常熟練地使用這個技能,他們就會用最差情境原則來推測事件。
這種最差情境具體、惡劣,對應急工作不可或缺,同時給人帶來的心理創傷也是非常劇烈的。
應急中心的工作人員,他們的心理創傷其實是有兩個來源的,一個來源就是實際的事件,就是交流的過程中實際的信息,包括交流的氛圍給他帶來的創傷。還有一種創傷,就是他們用這種最差情境原則去推測事件,這個想象的事件也會給他帶來的創傷。
而且他們這個創傷是很難癒合的。為什麼?一般來説,因為分工的原因, 他們是沒有機會去接觸這個事件真正的結局的。加上他們非常忙,可能一個事件還沒結束他就要處理下一個事件。他也不可能説我在這個事件裏面受到了一些打擊,現在心情非常不好,我先把工作扔到一邊,要去休息一會兒,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沒有這個條件,所以他們這種創傷是不斷加強的。
當時培訓的時候就有實習生問一個老員工,你覺得這個工作裏面最難的事情是什麼?那個老員工就説,最難的事就是從一個不好的電話裏走出來。
在我整個研究的過程中,有很多人跟我講他們面臨一些什麼樣的心理問題。比如有人跟我説,如果這個電話裏面的受害人有小孩,他就受不了。 還有的人跟我講,他好幾年都在做噩夢,還有人説他可能要費很久很久才能忘掉一個電話。他們有很多這方面的心理壓力,我當時就把這些情況也都寫到了我的博士論文裏面。
就在我這個研究進行一兩年的時候,這個應急中心的主任給我發了一封郵件,他説我就是想告訴你,我們這個應急中心現在增加了很多提高他們精神健康的舉措。
比如我們現在推薦或者要求他們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去冥想,然後又給他們提供了很多關於心理健康和精神衞生方面的知識。我當時就覺得這件事情特別好,應該去推廣。
職業偏見
我後來有機會和一個精神健康方面的專家合作,他就告訴我他是怎麼成為這方面專家的。他説他姐姐就是一個911接線員,她常年受到這方面的精神壓力,有很多心理問題,他就是希望通過這一生的工作,幫助像他姐姐這樣的人。所以他當時找我的時候我就想,這樣的事情我肯定要加入,他請了一些專家合作,來出版和911整個羣體有關係的一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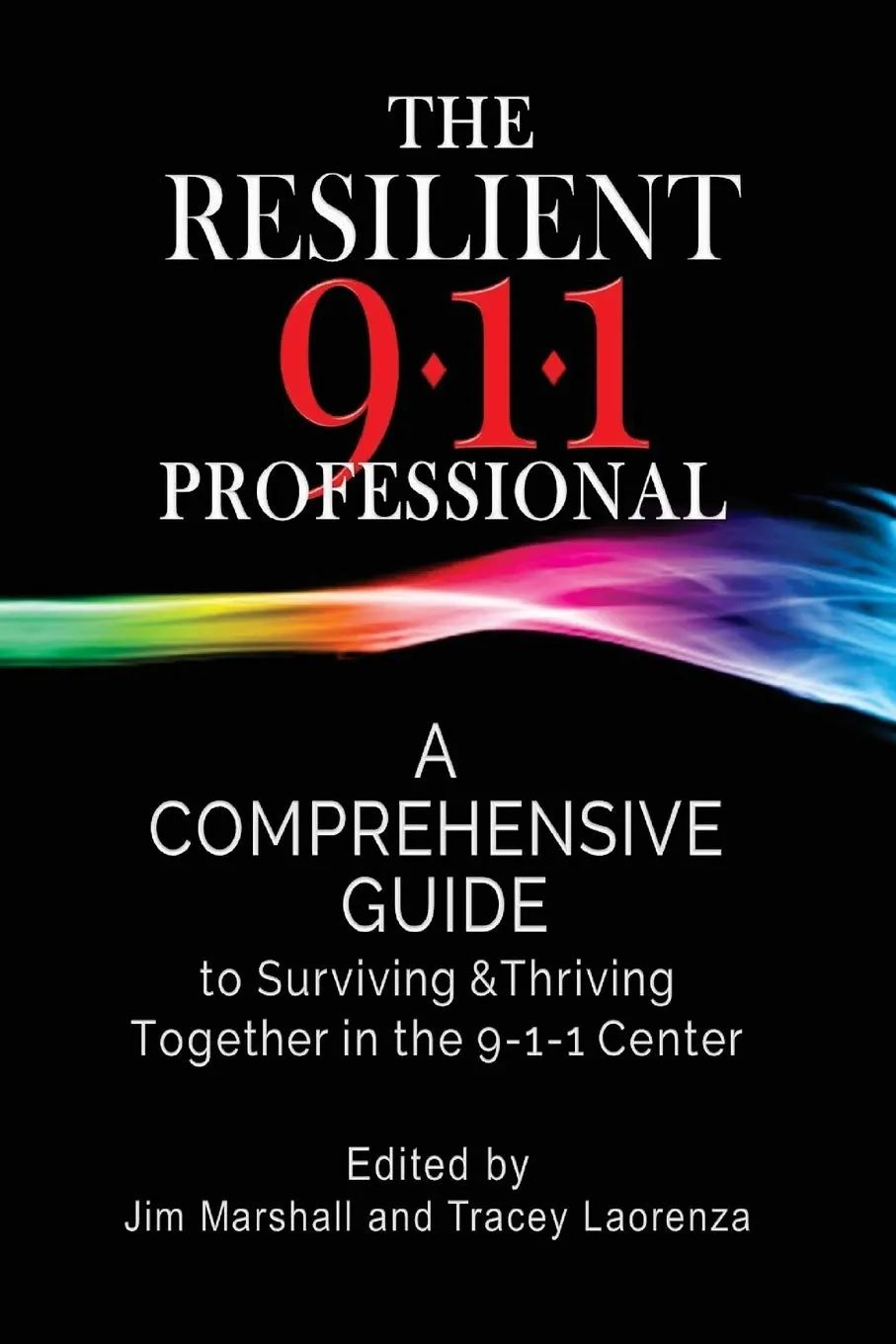
我們在這個書裏,不僅探討了剛才説的精神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問題,還把這些問題都置於一個整體的框架裏面來看。這裏面涉及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問題,第一就是關於911應急行業的不平等。
通過我剛才的描述,大家可能覺得911應急中心的人員,和他們派遣的人——消防員、警察和前線的醫療救護人員,他們都是同事。他們確實是同事,但實際上在美國民眾眼裏他們不是的。
美國大眾管911應急中心的人叫911-operators,這個operators其實就是和總機、客服差不多的一個工種,應急中心內部的人員是很反感這個詞的。 大家都覺得應急中心的人就是在一個有空調的房間裏面坐着,不需要冒生命危險,就是傳話的。這不光是美國公眾的偏見,也是美國政策制定的人的偏見。
從職業的角度來講,這種偏見不光是名義上的,它還有很具體的影響。比如911應急中心的人,他們的工會和火警、醫療就不是一個工會,他們在議會的代表能力、遊説能力也是要弱很多的,他們的工資更低,退休年齡一般來説要比這三種職業晚5年。就所有這些很實際的方面,他們其實都是處於劣勢的。
生死之間
我在這三年裏面,接觸到了各種事件,你能想象到的事件,你想象不到的事件,都有可能在911應急中心的電話裏出現,可以説從生到死,這兩者之間的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出現在911電話裏面。
這個生和死不是修辭,不是誇張或者比喻。這個“生”是什麼意思呢?剛才我説到電話接生,比如你或者你的親屬,因為什麼原因來不及去醫院,但是孩子要生出來了,你就可以打911,他們也有這個訓練,911的接線員也會一步一步指導你,怎麼把這個孩子生出來,包括怎麼把臍帶剪了。
除了處理這些事情以外,他們還要處理自己人生的危機。剛才我説的那個接家暴電話,對方説沒有事但還派人的那個人,他後來告訴我,他的三個姐姐都曾經在自己的親密關係裏受到精神或肉體的虐待,所以他就有這樣一種直覺。
那麼他自己的人生有什麼問題呢?他的兒子當時已經做了好多次開顱手術,可能還要再繼續做開顱手術。但不管他是值哪個班,總是拿這麼大一個保温杯,裏面都是冰咖啡,笑呵呵地到應急中心來工作。
這三年的研究,首先就是幫助我認識了我自己的經歷,現在回頭看,我就明白了在波士頓爆炸案以後,我當時那種反應是什麼,它應該是叫急性應激反應,就是在受到了重創以後會產生的一種反應,那種急性應激反應如果長時間得不到有效療愈,就會發展成創傷後應激障礙,就是PTSD。
因為這個工作,又因為和那些專家合作,我就瞭解了很多這方面的知識。他們就跟我説人的腦子是有分工的,有的區域它會產生這種消極的或者受重創的情緒,有的區域它會負責去控制這樣的情緒,但是這兩個區域有時候它不交流。
那麼怎麼激活它們之間的交流?就是用語言,不管是説的還是文字的。激活了它們之間的交流,負責控制這種情緒的區域就會散發一種物質,讓你受創的這種情緒得到控制。這個也解釋了為什麼當初我打了學校的求助電話,雖然他們沒有跟我説具體要怎麼做,但是我説完了以後就好多了。
這三年的經歷也讓我認識了現在,在我做了這個研究以後,我是用什麼樣的眼光去看疫情中的110、120和119的這些前線人員,包括和病人接觸的醫護人員的?我想他們和我的研究對象是一樣的。
他們處理的首先是一種高不確定性的事件,也是非常緊急的事件。對於個人來説,如果他自己或他的親屬得了新冠肺炎,那他肯定會覺得打擊非常大,但是120、119這些前線人員,還有醫護人員,他們就要很密集地大批量地處理這些事件。
他們肯定也不能説我處理完了一個病人,現在狀態非常不好,我要去休息一下,放空一下,再處理下一個病人,他們也是沒有這個喘息的機會的。
當然這種理解,這種視角,也是因為我做了研究才得到的,這個視角可能是非常侷限的,如果將來有機會,我也期待用研究的方式去擴展這種視角。
説到最後,這三年的經歷對我來説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每天都在同時見證人的無力和力量,同時看別人跟命運抗爭和妥協。這樣的經歷,讓我從自己這個非常侷限的肉體和精神裏解放出來,和別人的世界產生了連接,所以我感覺自己可以用更廣闊、更慈悲的方式,看待自己和他人人生中的種種經歷,還有世界上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情。
希望我今天的演講能對大家有一些幫助,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