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國家歧視程度更高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1051-2020-09-22 1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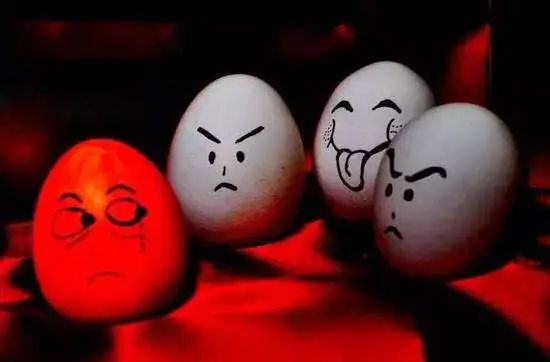

摘要:比較各國的歧視程度可以提供一個通向被形容為歧視根源的大規模社會和政治因素窗口。然而,由於難以測量,各國在僱用歧視方面的差異很少得到證實。作者通過對歐洲和北美9個國家的97個實地歧視實驗進行的元分析來解決這一差距。在分析中發現,所有國家對非白人本地居民的歧視都很大;對白人移民的歧視雖然存在但很低。然而,不同國家的歧視率差異很大:在高歧視國家,本地白人得到的報酬幾乎是非白人的兩倍;在低歧視國家,本地白人得到的報酬大約多25%。法國的歧視率最高,其次是瑞典。作者發現英國、加拿大、比利時、荷蘭、挪威、美國和德國之間的差異較小。這些發現挑戰了一些傳統的宏觀層面的歧視理論。

這是社論前沿第S1764次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種族和族裔不平等是現代社會的一個普遍特徵。特別是在勞動力市場上,少數族裔和本地白人之間的鴻溝顯得巨大而持久。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2015)指出,在比利時、法國、德國、荷蘭、挪威、瑞典和英國的白人多數羣體中,本地出生的移民子女(15至34歲)的失業率大約是同齡人的兩倍;和美國的非裔美國人與白人之間的失業率差距驚人相似(Austin, 2013)。
對一些人來説,這些差距僅僅是通往融合和同化道路上的短暫摩擦。特別是在移民率高的歐洲國家,許多人期望第一代人的劣勢將被享有全部公民權的後代所取代(Jonsson, Kalter & Tubergen, 2018)。在美國,對當代種族不平等的解釋也將歧視最小化,該解釋強調的是歷史經驗的痕跡,而不是當代障礙(Heckman, 1998;Wilson, 2012)。相反,其他人指出,持續的歧視是當代種族-族裔不平等的根本原因(Feagin & Sikes, 1994; Sidanius & Pratto 2001)。因此,歧視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種族和族裔少數羣體所能獲得的機會,這一問題仍有很大爭議。
儘管各國在這些爭議中有相似之處,但有理由認為,歧視的程度可能因國家背景而有很大差異。各國在種族和移民史、當前的經濟和社會背景以及公共政策方面存在差異( Alba & Foner , 2015 )。雖然這些條件在國家範圍內有所不同,但歷史、文化和政策的許多方面主要是在國家/地區層面上構建 的。然而,關於各國勞動力市場歧視程度的差異以及哪些少數羣體受到影響的問題,幾乎沒有定論。在歧視方面建立國家差異是更好地理解影響歧視的宏觀社會、文化和政策因素的先決條件。
背景
作為這項跨國研究的框架,作者首先考慮為什麼可以用理論來支持西歐和北美國家之間歧視程度的相對相似,或者支持在歧視模式上存在重大的國家差異。西方發達國家在其種族歷史、當前的經濟和社會背景以及政策方面有足夠的相似之處,因此作者預計會出現歧視少數羣體的共同矩陣。但在這些方面也存在着重要的差異,在缺乏關於歧視原因的強有力理論的情況下,歧視可能是相當統一的,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現代種族分裂和偏見在作為早期羣體接觸的一部分而發展起來的意識形態中有其歷史基礎,特別是國際奴隸貿易和殖民主義(Fredrickson, 2002)。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是以歐洲生物學家的遺傳思想為基礎,後來又與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相結合(Gould, 1996)。其結果是一系列關於非白人種族自卑的信念、想法和偏見,這些在西方國家通常很相似(Winant, 2001)。
近年來,西方國家在世界移民體系中的地位以及西方國家之間牢固的文化聯繫表明,他們對移民的反應相當相似。的確,來自全球南方的移民在許多西方國家激起強烈反對(Semyonov, Raijman & Gorodzeisky, 2006; Golder, 2016),歐洲民粹主義反移民政黨的興起和Donald Trump的當選就證明了這一點。對移民的看法也同樣受到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有關的恐怖襲擊的影響,特別是2001年9月11日在美國的襲擊以及隨後在幾個歐洲國家的襲擊(Branton et al., 2011; Legewie, 2013)。最後,歐洲和北美的少數民族面臨着許多類似的問題,特別是失業(Heath and Cheung, 2007)。如前所述,歐洲的非白人和北美的黑人的失業率往往是白人本土失業率的兩倍左右(OECD, 2015)。
北美和歐洲國家有關種族和族裔的立法與慣例也有許多類似的內容。各國傾向於模仿其他國家的立法和慣例,反映出國家之間強大的組織同構性(Meyeret al., 1997)。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北美和許多西歐國家採用了一套相當類似的反歧視法。2000年,歐盟通過了一系列種族指令,要求所有成員國採取一系列反歧視措施,將其關於種族歧視的立法框架置於高度相似的地位(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2008)。
另一方面,這些共通點還伴隨着各國在種族和僱用做法方面的顯著差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儘管歐洲和北美國家都受到歐洲殖民主義和奴隸貿易的影響,但他們並沒有平等參與。 在我們所考察的國家中,美國的獨特之處在於有大量的奴隸制後裔。一些研究發現,奴隸制參與與現代種族不平等之間存在聯繫(O ’ Connell, 2012)。而且,儘管一些歐洲國家擁有廣泛的殖民歷史,例如英國、法國和比利時,但瑞典和挪威等國家對殖民主義的參與卻較少。最後,雖然世界各地的國家都受到民權運動的影響,但是以美國為中心和最有影響力。
測量國家歧視程度
關於歧視如何因國家而異的情況我們還知之甚少,這主要是因為存在測量上的困難。過去旨在評估各國歧視程度的研究通常採用基於種族差距的間接方法或代理報告。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缺點。
評估歧視最常用方法通常稱為殘差法,其基於統計模型的殘差來進行命名,該統計模型旨在控制可觀察的因素,這些因素可能會區分多數和少數族裔成員,例如年齡、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無法解釋的差距或殘餘通常被解釋為歧視的影響。當然,許多其它未觀察到的因素也可能導致此類方程式中殘差的大小,導致研究人員高估(有時低估)歧視的真實影響(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4; Quillian, 2006)。
第二種方法依靠來自潛在歧視目標的自我報告,這些報告通常是通過調查收集的。儘管自我報告的歧視現象很普遍,但是很難將對歧視的看法與實際的歧視行為充分地對應起來。鑑於當代歧視的微妙性和隱蔽性(Bonilla-Silva, 2006),歧視對象往往不知道發生了歧視事件。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出於歧視性目的而誤以為是普遍敵意或服務不佳。協調觀念和行為之間的脱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可能會在不同的背景下有所不同(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4)。
第三種方法使用正式的歧視投訴或指控歧視的訴訟頻率。這種方法也只能捕獲受害者意識到的歧視,而正式的投訴或訴訟會受到阻礙,或受到官方申訴程序的體制因素的強烈影響(Pager, 2007)。最後,也可以使用歧視者的報告。這樣的報告面臨一個明顯的問題,即歧視者很可能低估了他們的歧視,這也使其成為一種不可靠的方法(Pager, Quillian, 2005; Pager, 2007)。以上這些方法都有嚴重的缺陷,削弱了清楚理解其結果的能力,從而無法很好地測量歧視,並限制了研究者可靠地比較各種國家背景下歧視模式的能力。
在過去的15年中,一種具有較好因果(內部)效度的方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使用,即實地實驗法。僱用歧視的實地實驗是實驗性研究或準實驗性研究,其中虛構了來自不同種族或族裔羣體的求職者申請工作。這些研究包括簡歷審核研究以及面對面審核研究,其中虛構的簡歷通過郵件、電子郵件或網站(如,Bertrand, Mullainathan, 2004)提交。在面對面審核研究中,除族裔不同外,由其他方面與受訓測試人員相匹配的人來申請工作(如,Pager, Bonikowski & Western, 2009)。
過程
實地實驗已成為一種越來越受歡迎的方法,其結果是大量此類研究提供了許多國家對種族和族裔羣體歧視程度的估計值。對於與招聘有關的大多數實地實驗研究,主要結果是回訪(要求應聘者返回面試或要求提供更多信息),表明用人單位有興趣。在整個申請過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審核會一直遵循申請流程直到最終的招聘決定,但數量太少無法支持各國之間的比較。
元分析是醫學和心理學領域廣泛使用的一種方法,通過對實驗研究結果進行二次統計分析來彙總實驗研究的結果(參見Borenstein et al., 2009; Cooper, Hedges & Valentine, 2009)。使用元迴歸方法,並通過一個包含所有可用的種族和族裔歧視實地實驗研究的數據庫,作者對作為國家、少數羣體和其他研究特徵的函數的少數羣體相對歧視率進行建模。
研究程序遵循三個基本階段:首先,確定所有現有的僱用歧視實地實驗;第二,制定編碼規則並進行編碼研究,以建立其結果數據庫。第三,進行統計元分析,從合併結果中得出結論。
結果
作者首先從描述性的角度研究歧視程度如何因國家和少數羣體而有所不同。他們對每個國家的少數羣體(包括國家、目標羣體以及國家與目標羣體的互動)使用隨機效應元迴歸,沒有進行其它 控制。每個國家的歧視比率預測水平如圖1所示。點是國家和目標羣體平均歧視率的點估計值,線是95%的置信區間。每個置信區間 下方的數字是用於計算效果的研究數量。歧視比率是白人原住民與指定少數羣體之間的回訪率。作者關注的是圖中的 總體模式,而不是單個國家/ 地區分組單元的顯著性(或無意義)結果。
(圖源:原文; 温馨提示:點擊查看大圖)
該圖顯示了對種族和少數族裔羣體的普遍歧視: 對於圖中26個目標羣體中的25個羣體,歧視率的點估計值均大於1,表明對少數 族裔羣體存在歧視(一個例外是荷蘭的白人移民,值為 0.95)。沒有證據表明對白人 原住民有“反向”歧視。在這 26個目標羣體中 ,有幾個羣體 其影響在統計學上與1並沒有 顯著差異,但是更仔細的考慮表明,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些羣體的估計效果不佳。基於四項或更多的現場實驗研究,作者 對15個羣體歧視估計有較高的評價權。 其中有 13個 歧視比率為 1(無 歧視), 在95%的置信區間外,表明在p <0.05( 雙尾)上具有統計學顯著性。這兩個羣體的估計值 (基於四項或更多研究)對歐洲/白人移民(在加拿大和英國 )不顯著 ,這表明對歐洲/白人移民的歧視程度低於非白人。 這些結果支持對非白人羣體普遍歧視的結論。相比之下,對於白人移民,歧視程度較低,而且通常在統計上不 顯著 。
為了進一步探討國家和羣體差異的來源,並考慮實地實驗研究之間的其它測量差異,作者建立了一個以國家、目標羣體和其它因素為函數的歧視比率元迴歸模型。當同一研究中存在多個歧視估計時,標準誤差將被調整為相關效應。
在最簡單的模型中,將對數歧視比率分析作為一個國家和目標羣體效應的累 加和。表3 和 模型1 是基本估計 。美國是國家虛擬變量的參考組,非洲/黑人是羣體效應的參考組。
在 表3的模型1中,有兩個結果 比較突出。首先, 法國的歧視程度最高 ,歧視比率比美國高33.6% ( exp[0.29]-1 )。第二, 來自歐洲原籍國家的移民羣體比黑人或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受到的歧視要少得多 。 非洲/黑人、中東/北非和亞洲少數羣體的歧視程度 非常 相似 。
(圖源:原文; 温馨提示:點擊查看大圖)
這些模型不能控制可能會混淆羣體 和國家差異的研究特徵的差異。在模型2中, 作者增加了對申請人性別、申請人教育水平、研究是親自進行還是通過郵件或互聯網進行的、實地工作年份和職業類別的控制。這些控制大多數都不重要,但是作者在面對面研究中發現了比簡歷研究更有力的歧視證據 。可能是因為面對面的申請比起簡歷上的名字提供了關於種族身份的更強有力的信號(參見Gaddis , 2017)。另外,意識到研究目的的演員可能會無意識地產生偏見,這可能是一個因素(Heckman & Siegelman 1992)。 作者還發現, 對需要大學學位的工作的歧視要比僅需要高中學歷(或全國同等學歷)的工作更少 。分析不能確定為什麼會這樣,但一種可能性是,受過大學教育的申請人簡歷中的材料往往更廣泛,包含更多細節,從而減少了僱主對申請人特徵的不確定性。
與模型中的大多數其他協變量相比,國家差異很大:它們往往大於少數羣體效應或大多數對照組。國家影響如 圖2 所示,以闡明 差異的程度。圖中的係數被指數化以增加可解釋性:它們可以被解釋為相對於美國參考類別國家的歧視比率的比率。例如,1.26表示歧視率比美國高26%。
在基礎 控制的模型中(表3,模型2),法國的歧視率比美國高43%(p <0.001)。瑞典緊隨其後,歧視率比美國高30%(p <0.1)。其次是加拿大 、英國、比利時、荷蘭、 挪威和美國。這些國家之間的差異在統計上並不顯著。最後,德國的歧視程度低於美國,歧視比率比美國低約8%(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基於表3中模型2中的少數羣體系數的指數,在圖3中給出了少數羣體效應。圖3中的係數與對非洲裔/黑人的歧視有關,可以解釋為相對於非洲/黑人目標的歧視比率。研究結果顯示,對歐洲移民的歧視程度低於非洲/黑人。相比之下,非洲/黑人 、 中東/北非和亞洲少數羣體 之間的歧視程度似乎非常相似。對拉丁美洲或拉丁美洲裔羣體的歧視似乎比其他非白人羣體少,但多餘 歐洲羣體,儘管在p <0.05時,這與其他羣體相比沒有統計學意義。
模型3增加了一些外國特徵的控制,申請人是外國出生的或有外國證書。這些都沒有顯著預測結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措施的低變異性(大多數研究中的申請人都是土生土長的)。控制 變量基本上沒有改變國家和羣體效應估計值。
最後,模型4增加了兩個 背景 特徵作為控制:當地失業率和移民在當地人口中的比例。 兩者都不是具有統計學意義的預測因子,且係數都較小。這與關於這些特徵在羣體威脅文獻中重要性的一些假設相反。 作者 本希望能夠包括具體種族-族裔羣體在當地的 佔比,但由於缺乏關於種族和族裔的可比跨國數據報告,因此無法做到這一點。這些協變量都不能解釋任何國家或少數羣體的差異。
討論
在 作者 考慮的每個國家中,與具有類似工作相關特徵的白人相比,非白人申請人在接受面試 回訪 方面遭受極大的不利影響 。 這種差異是由種族而不是移民身份驅動的 ;作者對本出生地和移民出生地的測量在預測歧視方面不顯著。 白人移民(及其後代)相對於白人原住民也處於不利地位,但比非白人少得多,而且白人移民與白人原住民之間的差異通常很小,在統計上 不顯著 。作者發現, 針對非白人羣體的歧視水平相當相似,無論其具體來歷如何:非洲人後裔 、 中東或北非人以及亞洲人後裔(在數據中大多為南亞)遭受的歧視程度大致相同 。從廣義上講,研究 結果與諸如社會優勢理論(Sidanius & Pratto , 2001)之類的觀點相一致,該理論強調了在歐洲和北美普遍存在針對非白人的歧視。在這些方面, 作者 發現歐洲和北美國家之間存在一種普遍的歧視模式 。
然而, 研究發現,各國對少數羣體的歧視程度差別很大。平均而言,在法國和瑞典,白人收到的回訪 比非白人少數民族多65%至100%;在德國、美國和挪威,他們收到的 回訪 比非白人少數民族多20 % 至40 % 。與國家/地區相比, 作者所包含的大多數衡量社會和研究因素之間的差異更大,且更顯著。在招聘方面,一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歧視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