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瀋陽之後,我開始召集那些落魄的武士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9515-2020-09-25 07:36
來源:一席
柳迪,動畫導演。
我突然發現街上空無一人,才意識到明天就是2019年了,我即將迎來我的30歲。想到這我突然輕鬆了,原來《風雨廊橋》並沒有承載多麼沉重的東西,它只是一個人,一個年近30的人的自我表達。
風雨廊橋
2020.08.23 杭州
大家好,我是一個定格動畫導演,我叫柳迪。今年6月份我們在網上發佈了定格動畫短片**《風雨廊橋》**,片子講的是唐朝末年一個久病纏身的老俠客去救一個小女孩故事。
説起定格動畫,大家或許會感覺陌生。它的另一個名字大家一定會很熟悉,就是木偶劇。在數字特效還沒有出現之前,定格技術被應用在許多真人影視當中,比如《星球大戰》《金剛》《星際穿越》,還有中國的《倩女幽魂》,都用了一些定格動畫的視覺效果技術。
在三四十年代,中國動畫的鼎盛時期,出現過非常多的大家耳熟能詳的定格動畫作品,比如:《神筆馬良》《阿凡提》等等。
尤其是《大盜賊》,我小時候特別喜歡看這部定格動畫片。因為那時候很小,我看完這個動畫片之後就一直吵吵着要吃土豆泥,但是東北似乎都不吃土豆泥,都是吃整塊。
▲ 定格動畫《大盜賊》吃土豆泥片段
定格動畫後來在中國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視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國外的定格動畫,比如説《小雞快跑》《殭屍新娘》等等,大家應該都看過。
定格動畫雖然古老小眾,但仍然有一部分人在堅持,沒有拋棄它,我只是其中之一。從我2012年開始進入這個行業,到今年已經有8年時間,常有人和我説:你真幸運,找到了你的興趣作為工作。慶幸的同時我也在想,是什麼原因讓我進入到了定格動畫這個行業呢。
/ 01 /
我的思緒就回到了20年前。2000年,那個時候院線、網絡、電腦都還沒有普及,大家都會買一台DVD播放機,然後或租或買一些DVD在家裏看。那時候恰巧我的外公開了一家影碟出租的小店,所以四年級的時候,那個地方就成了我課餘時間最常去的一個地方。
▲ 柳迪手繪外公家的影碟出租屋
在長時間的挑碟看碟的過程中,我摸索出了一個“規律”,那就是封面上有“花”的都是好電影,後來我知道了,那個“花”就是得獎的標誌。在一個秋天,我按照這個習慣拿起一個帶有很多“花”、封面上是幾個美國大兵的碟片,這部電影叫《拯救大兵瑞恩》。兩個多小時的時間裏,我幾乎全程瞪大雙眼,季節並不是冬天,我卻全程打着冷戰,牙齒不自主地相互撞擊。
四年級的我被電影裏戰爭的殘酷驚呆了,我第一次知道電影不僅可以直擊人心,還能造成生理反應。從那時起,我開始更加瘋狂地去看電影,因為我覺得電影這個東西簡直是太吸引我了。
之後我家就從小城的最東邊搬到了最西邊,我失去了一起玩的夥伴,也不能經常去外公家看電影了。但是我太想看了,所以那時候就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寫電影。
我開始用筆寫下那些看過的電影,因為在寫的過程,就可以在腦海裏一遍又一遍地回憶那些細節、那些激動人心的時刻,這給了不能看到電影的我一些撫慰。
我記得我寫的最多的是一部叫做《U-571》的電影,它同樣是展現戰爭的殘酷,展現人性,只是把戰場搬到了水下。
於是,電影就成了我看似虛無縹緲,卻又有跡可循的理想。也是帶着這個理想,我2008年考上了一個藝術院校,進入到了數字媒體專業。我當時並不知道數字媒體到底是什麼,就只知道它是和電影有關的,這就足夠吸引我了。入學之後,我又開始瘋狂地看電影。我記得那時候學校也有一個影碟出租的小店,叫西區故事。那裏成了我每天都會光顧的地方。
閲片量的增多,讓我有了越來越強烈的表達欲。那個時候我做了很多小短片。
▲ 柳迪大學時期作品《喪鐘為誰而鳴》
畢業做選擇的時候,一部叫《開心小鎮》的動畫片出現在了我的視野。《開心小鎮》是繼《阿凡提》之後,時隔36年,中國製作的第一部定格動畫劇集。大家可能都沒看過,它和當時一些主流的動畫片不一樣,特別的淳樸,所以我就應聘了這家公司,然後順理成章地入職了。
入職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是非常興奮的,成熟的定格動畫製作就像一個充滿寶藏的世界,每天都在等待我去探索。我接觸到了定格動畫的每個環節,學習瞭如何製作人偶、如何翻模、如何做金屬骨架等等。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用成熟的技術來自我表達。
但是這一天似乎遙遙無期,我和理想之間似乎永遠有一個隱形的高牆,我看不見它,也無法逾越它。
/ 02 /
到了2016年,也就是《風雨廊橋》開始的那一年,因為有高牆存在,所以我索性就等待一個時機。在等待的過程中,我決定重新開始學習電影,第一步就是寫劇本。我買了很多書,做了很多學習,之後我就想我要用一部短片,來檢驗我這一階段的學習成果。在選擇題材的時候我偶然間看了胡金銓導演的老版《龍門客棧》。
這部電影它沒有那些華麗的動作、絢爛的特效,但是你仍然會為它的劇情所感動,仍然會為它的俠義精神所震撼。反觀現在的武俠,武俠最重要的俠義精神已經所剩無幾了,變成了單純的武打片,所以我想,我是不是能嘗試着寫一個我心中那種純正的武俠。
《風雨廊橋》就這麼開始了,我查了關於“俠”的定義,研究歷史上俠客活躍的年代,有一句話讓我思考了很久,“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在盛世的時候,俠客才有可能被定義。那如果在亂世呢?沒有法律,沒有所謂的道德,人們不需要正義,只需要活着,那個時候俠客該何去何從呢?
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長時間,這是《風雨廊橋》的起點,也是它的核心所在。然後我需要一個地方讓亂世裏各個階層的人相遇。這個地方肯定不能是客棧了,因為客棧已經很多了,所以我也沒有想太多,就在一個破本子上寫下了四個字,“風雨廊橋”。
“風雨廊橋”這個名字最初是在我母親的嘴裏聽到的,她是一個開茶店的,很喜歡茶文化,所以茶馬古道、茶商、風雨廊橋,這些詞經常會從她嘴裏説出來。
創作的過程和時間是成正比的,沒有那種靈光一閃。這部片子時長只有22分鐘,劇本只有2000多字,但我卻花費了一年半的時間去寫。
我最開始寫它的時候就是當做一個練習,並沒有打算要把它拍出來,直到我寫到最後一句話:
雨腳在河面上盛開,
水流變得湍急,
河中之刀被水流漸漸衝倒,
沒入河水中,
隨波逐流,
蹤跡全無。
我當時並沒有設計這個故事的結局會是什麼樣,但這句話就像活了一樣自己就蹦出來了。寫完這句話,我就決定一定要把它拍出來。
我畫了300多張概念圖和分鏡。我都是用生活中最常見的一些東西去畫,一些複印紙、一些黑色的水性筆,所以這也是最終《風雨廊橋》的呈現是黑白的原因,因為我從來沒想過它會是彩色的。
▲ 柳迪為《風雨廊橋》繪製的分鏡手稿
包括之後的一些人物設計,大家能看到強盜和軍人的形象是和成片不一樣的,期間我們做了很多次更改。
做完這些前期準備,我很快就迎來了人生的一次低谷。堅持,還是放棄?大多數年近30的人都會面臨這樣一個選擇題,現在它無比近距離地擺在了我面前。
當我即將要放棄的時候,我老婆成為了守護我的最後一道屏障,她説如果你覺得這個劇本挺好,那就再堅持一下,咱們還有房子可以賣。
當時聽到這句話我感到無比心酸,但是也給了我很多力量。所以我就帶着我的劇本,帶着我的畫,第一次去了北京。當時沒有預約,大家現在都知道的一些視頻公司,我就挨個進。勇氣確實可嘉,但是沒有任何收穫。
他們的疑問就是,定格動畫最終呈現的是什麼效果?因為他們還停留在《阿凡提》那個視覺效果上,這個劇本用《阿凡提》表現出來的樣子,他們想象不到。
所以2017年的時候,我就在家裏反思了很久,我決定要做一個宣傳片出來。第一步我就要把二維的概念稿變得立體,我需要知道這個形象在三維空間裏面是什麼樣。所以我先做了老俠客的一個動勢。
然後緊接着把它做成了實體,用各種綜合材料,讓它儘量靠近原片所展現的形象。
然後做了一些場景的測試。因為我的畫是黑白的,所以我在樹葉原有的基礎上做了一些描邊,最終呈現的效果是這樣,目的就是為了讓它更多地靠近我的概念畫。
包括唐刀的設計,現在我們可考證的唐刀很少,基本上沒有,因為唐朝是不允許兵器作陪葬的。現存的唐刀只能在一些國外的博物館或者一些石刻壁畫裏能看見。
所以我在唐刀的基礎上做了一些設計,讓它更有利於實戰。這是刀做出來的樣子。
因為這個宣傳片是我一個人做的,我不能做一些太激烈的畫面,或者是我能力之外的東西,所以我就抽出了兩個元素,“恐懼”和“反擊”,儘量去詮釋正片的主旨。拍出來的宣傳片是這樣的。
有一個“恐懼”一直追着老俠客,這個“恐懼”可能是他的敵人,也可能是他的對手,還可能是他的心魔。拔不出來的刀,其實就是代表着他年邁的身體。我用了有限的東西來詮釋這個片子,最終的效果其實也還挺好的,然後就有更多的人主動來找到我。
於是我就第二次去到北京,去見一些有意向的投資人。這一次其實我是切身感受到了那句話,就是“如果你做對了一件事情,全世界都會幫你”。他們都會對我伸出援手,告訴我一些經驗。所以在從北京回到瀋陽的路上,我發了一條朋友圈,就是這個: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結識了好傳動畫。好傳對《風雨廊橋》的投資其實是讓我特別驚訝的,我進入好傳不到一個小時,這個事情就定下來了,讓我有點措手不及。所以在這裏再次感謝一下好傳,感謝我的老闆尚遊。
/ 03 /
回到瀋陽之後,我就像《七武士》中的勘兵衞一樣,開始召集我那些落魄的武士。他們有的在定格動畫行業從事了十年甚至十多年,空有一身抱負沒法施展。有的已經在轉行了,有的正在轉行的過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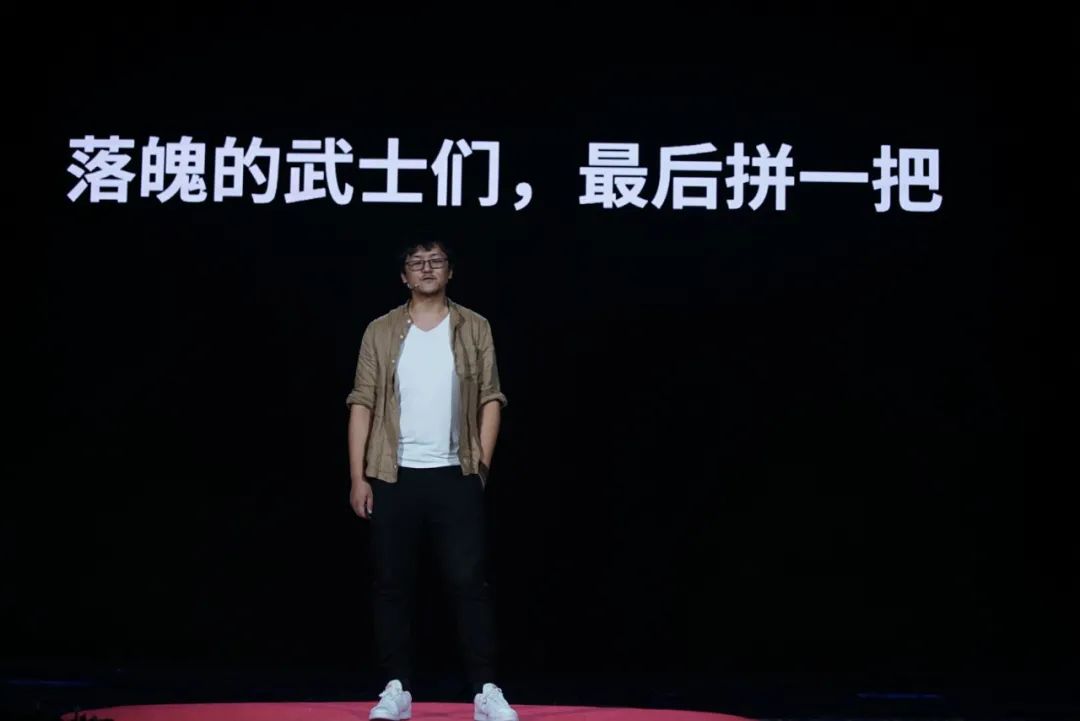
我把他們一個一個找來,我説我們再最後努力一把,算是對自己有個交代。就這樣我彙集了幾個人,開始了《風雨廊橋》的製作。這就是我們當初的那個團隊。
最左邊那個抽象的是我,左起第二位是我們的道具師,《風雨廊橋》的內外景,還有所有的兵器都是他製作的。中間兩位是我們的動畫師,最右邊這位是我們的萬金油師——因為他什麼都能幹。
《風雨廊橋》前期準備了兩年,是很充分的,再加上我們的工作默契度非常高,所以製作起來是非常順利,也是非常快速的。但是很快,第一個很致命的問題就出現了,就是我們人手太少了。
定格動畫的製作流程是很多的,比如人偶的製作就分好幾個步驟,需要做原型、做表情、植髮、做服裝、做一些配飾等等,所以我們這幾個人其實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每個人都擔負了兩到三個環節的工作,製作時間有十個月,幾乎每天都在超負荷地工作。
今天我也把我們的一些演員請到這來了。這個就是老俠客,大家能看到他的身體、衣服,還有材質都是和實物比較像的,不像大家之前看到的一些定格動畫或者木偶劇那樣,質感會有差別。我們會盡量去追求真實,比如説頭髮,拍的時候會一幀一幀地擺拍,讓它有一些飄動的效果。
這個是《風雨廊橋》裏面的軍人,它的盔甲是魚鱗甲,我們當時製作的時候是一個甲片一個甲片縫上去的,很小很難縫。而且劇中人物換表情都是這麼一幀一幀地換下來的,它的表情是都可以拿下來,然後我們需要別的表情的時候就一幀一幀地換,挺有意思的。
這個唐刀也是可以拔出來的,是按照真實的環首刀的樣子去做的。
我們在繼續進行下去的時候,又遇到了第二個難題,那就是場地的限制。在預算範圍之內,我們能租到最好的地方,就是這樣一棟聯排別墅,只有300平。
300平是什麼概念呢?住宅別墅的空間利用率是很低的,我們挑選了這套房子裏最大的一個屋子來做廊橋的內景,這個橋大概有5米長,整個鋪開在屋子裏面,旁邊就沒有多少空間了。
然後我們在拍攝的過程中,旁邊還需要架設一些機器、架設燈光、架設電腦、架設相機,每天我們拍攝時都像是走在空間站裏一樣,什麼東西都不敢碰,低着頭很小心地在裏面穿梭。
我們的第二個場景就是樹林,樹林我們只有一個2.5米乘以2.5米的空間可以去做,但是在這樣狹小的空間裏,我們需要分出三個場景和拍攝一個長距離的奔跑。
如何實現這個長距離奔跑成了一個問題,我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去思考拍攝的可能性。於是我把場景變成了一個U型,然後用相機的搖鏡頭代替平移的跟鏡頭,再用各種調度來做強行越軸,讓後面的背景反覆出現來實現長鏡頭的效果。
這是我們拍攝那個長鏡頭時的花絮,我們的器材其實很簡陋,但是我們還是想做一些更高質量的鏡頭。
這是當時我們的工作狀態,夏天的時候我們都不敢開空調,因為這個空間太小了,空調距離場景特別近,一開空調落葉全部都開始動了。身後還有好好幾個幾百瓦的大燈在烤着,夏天幾乎每天的工作狀態都是這樣的,渾身都是汗。
這個就是長鏡頭最終拍攝出來的效果。
在片子整體的節奏方面,我們也是考慮了很多。《風雨廊橋》的節奏是整體向上的,所以我會在幾個方面去實現它的節奏。其中之一就是加入天氣的敍事,晴天、陰天、暴雨,天氣隨着劇情的推進而變化。
在鏡頭方面,我們會在前面的鏡頭速度上做一些慢速的處理,讓鏡頭時間拉長,讓人物的動作變得很慢。然後隨着劇情的深入,我們會把鏡頭切得越來越快,到最後老俠客在橋裏反殺軍人的時候,每個鏡頭平均只有零點幾秒。
然後在打鬥方面,我們也是有思考的,我會讓這些角色是迫不得已才廝殺的。因為我看多了其他武俠電影裏面那些毫無意義的打鬥,生命是很珍貴的,不會有人動不動就去打架,即使他是一個俠客。
包括在動作設計上也是,我們其實最初定的動作風格是“街頭械鬥”風,我們不要那些華而不實的起手式,不要那些漂亮的動作,不要輕功,不要內功,不要連環腿,我們就是要讓角色以最簡單粗暴的方式,在最短的時間殺死對方。
但這確實很難,因為我們是在《黃飛鴻》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所以很難割捨掉這些對於武打的固有認知,但是還好我們是東北人。
/ 04 /
現在回想起那個別墅,我覺得有點做夢一樣的感覺,我覺得那一年過得特別不真實,因為我那一年每次到這個地方來之後,都是投入到劇情當中,投入到工作當中,很少去體會那個房子,除了我養的幾個小動物。
我的貓叫四點,是我早上四點的時候在我家陽台下邊撿的。那個時候下着大雨,它渾身發抖在那叫,我以為是狗,但其實是個貓。我把它抱回我們的工作室,它就一直跟着我們,現在它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媽媽了。
這是我的龜,它已經六歲了,也是跟着我們到處跑。
這是我的鳥,叫大劈叉,因為它小時候腿受過傷一直劈着叉,所以叫大劈叉。
這些動物從2018年開始就一直跟着我們,從那個別墅到我們現在的工作室,都一直陪伴着我們,除了我的狗。
我的狗在拍《風雨廊橋》裏面老頭死去的那一天去世了,它得的是犬瘟,特別痛苦,一直在抽搐,然後吐沫子。我幫不上任何忙,只能看着它生命耗盡就那麼死了。
我把它埋葬之後,就把它臨死之前的狀態賦予在了老俠客的身上。我覺得其實一部作品,它承載的不僅僅是劇本當中所體現的情節,還承載着你的一些人生經歷,你製作時候的心態,你的一些人生感悟。
這個是老俠客臨終的時候,我拍了一張照片,做了個紀念。
這個是殺青了,演員們在合照。因為當時覺得故事確實是太沉重了,我們想用一種方式來緩和一下心情,所以就拍了這張照片。
從2016年開始,老俠客就一直在我的腦子裏奔跑,到2018年年末他倒在廊橋裏,經歷了整整三年的時間。我時常會想,《風雨廊橋》這長達三年的自我表達,我能留給觀眾的是什麼呢?是對英雄遲暮的一種哀傷嗎?還是對亂世中人性的一種恐懼?有時候捫心自問,也許我能帶給觀眾的只是一種悲傷的情緒。
我記得片子最終渲染是在天津,好傳的總部,成片渲完第二天走在去公交車站的路上,我的心一直放不下,片子拍完了按理説應該很輕鬆,但是我卻一直輕鬆不了。
我突然發現街上空無一人,才意識到明天就是2019年了,我即將迎來我的30歲。想到這我突然輕鬆了,原來《風雨廊橋》並沒有承載多麼沉重的東西,它只是一個人,一個年近30的人的自我表達。
這張照片是我們當時要離開那個別墅時拍的照片,所有人都笑得很開心。
所以今天我獨自站在這兒,是萬不敢將《風雨廊橋》當作我一個人的作品向大家講述的。我覺得我就是一個代表,我是他們五個人的代表,也是《風雨廊橋》製作團隊的一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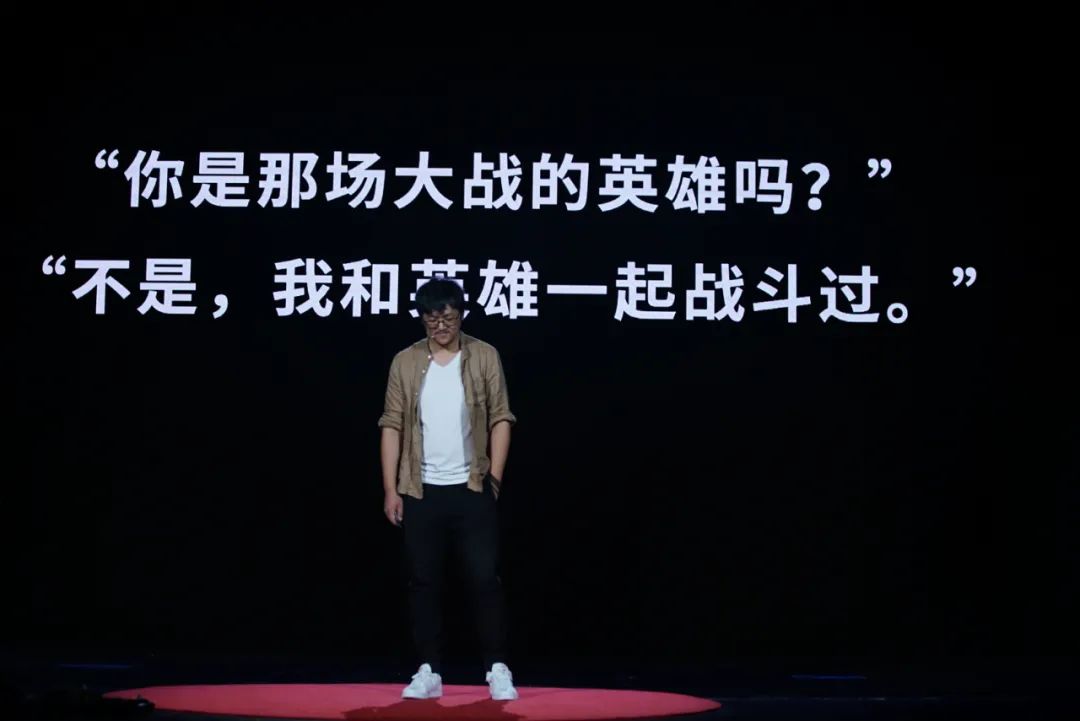
我記得斯皮爾伯格的另一部作品《兄弟連》中有一段台詞,老年温特斯的孫子問他,“爺爺,你是那場大戰的英雄嗎?”温特斯説,“不是,我和英雄一起戰鬥過”。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