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炮轟的不止是拜登, 還有精英政治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09-30 17:47

✪ 牛可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導讀]美國當地時間星期二晚上,特朗普與拜登進行首場辯論,由於辯論逐漸淪為人身攻擊,主播華萊士無可奈何:“紳士們!我討厭高聲説話,但我為何不跟你們一樣呢?“ 他勸導,如果少點打斷,辯論會對觀眾更有意義。觀眾的反應也剛好印證:69%的豆瓣網友對這場辯論的最大感受是,“煩”。
不少人回想起4年前的特朗普當選:他先是向失敗者希拉里發去了問候,隨後便開始讚頌上帝、國家、以及他所有的家人。在這串冗長的名單裏,觀眾聽到了他過世的父母與大哥的名字,也聽到了他女兒未婚夫的名字。每當他念出一個名字時,台下的人們都會像聽到“上帝”與“美國”的名字那樣,發出如雷般的歡呼。
自打特朗普當選,有關他的調侃不絕於耳。他口含金湯勺出生:在二十世紀初,父親弗雷德·特朗普就已成為成功的地產商人,而特朗普本人畢業於沃頓商學院。但特朗普的詞彙量被調侃只有“4000不到”。有網友編撰特朗普母親的名句,“他(特朗普)是個沒有常識的白痴…但他是我的兒子,只希望他永遠不要從政,他會是個災難!”
特朗普的當選,衝擊了美國百年來的精英政治傳統,即賢人政治。在宗教衰落後,精英們需替代教士來界定、體現和實現政治上的善即正義,構成對財富的“抗衡力量”,從而實現公共關懷。伴隨富豪統治逐見聲勢, 精英政治遭受衝擊,而我們也發現,以往美國精英的性狀和氣質所塑造的“自由民主”正逐漸瓦解,美國夢也隨之消退。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讀者參考。
▍以公共性和普遍性界定精英
資本和權力在社會成員間的分配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均等的。
精英,就是那些在各個類型和層級的共同體或社會場域中佔居優越地位,擁有並能夠運用巨大的,甚至是壟斷性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資本和權力來實施安排和作出決定,以實現自身的和公共的目標和利益的人羣。
關於精英,有下面的一般性評斷可以申説:精英的性狀和氣質反映和塑造共同體和民族國家的性狀和氣質;精英的作為、意志、偏好和品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共同體或者民族的生存狀態,決定着共同體和民族的公共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性狀和質量;精英的抱負、胸懷和能力決定着一個民族的歷史主動性和變革能力的大小;精英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精英和非精英社會成員之間關係的狀態、以及社會其他部分對其精英成員的態度和評價大體上決定和反映着社會認同、社會共識和社會正義的狀態。
進而言之,對一個民族的成功和偉大抑或失敗和悲哀的根源的探究,實際上大部分可歸結為對其精英部分的考察。偉大的民族必然擁有總體上可敬的和光榮的精英人羣,正如在窳敗而沒有希望的社會和政治生活中,人們總是可以有足夠的恰當理由指責其中的精英。
民族造就精英,精英乃為其所處的民族的社會體制和文化場域所歷史地生成。但精英或者更準確地説是好的現代社會的精英,也是自我塑造的,他們在歷史變遷中不斷地自我匡正、自我變革和自我塑造。他們必須獲具歷史主動性、超越性、公共性和普遍性。他們必須不斷超越自己的利益、眼界和積習的狹隘性,超越社會和文化的規定性。他們必須經由超越性達至公共性。
現代民族國家是政治的民族,現代民族國家的公共性必然也必須指向和體現為政治性。精英階級必須要打破地域、階級、小共同體和宗教的侷限性而成為全國性的政治階級,成為產生“國士”的階級。在宗教的傳統精神權威衰落之後,政治化的精英必須替代教士來界定、體現和實現政治上的善即正義,為此他們不能是功利主義的和世俗主義的,而要在“公民宗教”中充當佈道士的角色,在價值、文化、道德和意識形態上擁有自己的強固基礎和制高點。
精英必須是個具有歷史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社會物種,不能在盲目和順從中受制於現代社會的自然趨勢和所謂鐵律。他們必須在自己身上超越和克服現代社會的分化和原子化,而擔負起融通和整合的責任,跨越和貫通多個場域,善於融匯和運用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資本;為此要自覺和有效地抵制專業主義、工具主義和技術至上的思想。
它必須超越、抵禦和駕馭主導現代社會的經濟法則,本着政治高於經濟的原則思考和行事,對如不加以匡正和制約則必然會凌駕於其他力量之上的財富的力量構成匡正和制約,也就是像加爾佈雷思所説的那樣構成對財富的“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雖然財富在現代社會是孕育精英的最重要的母體,但政治化的精英卻往往會以某種形式接續所有偉大文明和宗教的精神傳統中共有的一個要素,即對財富的不信任和戒懼。它要疏離甚或背叛財富。
精英必須擔當得起“公”和“通”兩個字;精英必須“喻於義”而不“喻於利”;精英必須不能是唯利是圖、蠅營狗苟、目光短淺的。準備、造就和擔當了“美國世紀”的正是這樣的美國精英。
▍波士頓婆羅門與美國的“貴族政治”傳統
美國是商業和商人的國家,沒有世襲貴族和貴族政治,美國的政治在根本上是平民主義的和地方性的——對發端於托克維爾的這些通行看法須得有所保留有所補充。在美國的早期政治史特別是在國父們、聯邦黨人和高等法院身上,其實不難找到“理想類型”的貴族政治的要素和氣質。
正如小亞瑟·施萊辛格所指出的,好的貴族政治具有某種將家族的尊榮與對國家的使命感結合起來的特性,貴族在統治的同時會生髮出對被統治者的公共責任感,而且會超越金錢的利益去徵詢其他利益集團的意見。
民主政治在與商業階級的媾閤中,容易具有粗鄙、瑣屑、反智和盲目的秉性,而貴族政治會以其長處對民主政治構成某種彌補和匡正,在特定情形下有助於民主制下的精英政治(meritocracy,亦可譯為“賢人政治”)的生成。而民主政治只有同時也是精英政治,或者説只有由良善、睿智和有胸襟的人所擔當和運轉的民主制,才成其為好的政治。
美國的確沒有歐洲那樣的貴族,但也有一個重要而有趣的替代物,就是所謂“波士頓婆羅門”(Boston Brahmin)。這是新英格蘭地區那些擁有自馬薩諸塞殖民地創建和波士頓建城以來的悠久世系和顯赫聲望的上層清教徒家族。在早期美國,新英格蘭是經濟和文化都最為發達的地區。這些世家望族不僅在貿易中積累了巨大的財富,而且以貫通經濟、文化和政治以及具有全國性的眼光和抱負為特性。
在刊載於1860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裏,這個美國式貴族階級的一個成員創造了“波士頓婆羅門”這個詞並驕傲地宣稱:這個“種性”兼具財富、智識和美德,在“發展和領導藝術、文化、科學、政治、貿易和學術上有極大的影響力”。
這些名門望族綿延不絕,在一個多世紀裏為美國造就了總統(如約翰·亞當斯、約翰·昆西·亞當斯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大法官(小奧列弗·霍爾姆斯)和眾多全國性政治家(如温德爾·菲利普斯和亨利·卡波特·洛奇),以及大批有文化和政治影響力的學者和教育家(如愛默生和查爾斯·埃利奧特)。
在教派主義和地方主義盛行並排擠美國認同的19世紀,這個羣體引人注目地執守和承載着美利堅民族認同和全國性的眼界抱負。在美國固有的傑克遜式平民主義的和商業階級的“反智主義” 傳統。之旁側,這個擁有財富的羣體也以培育和提升美國的文化、學術和教育自任,並且致力於向政治灌注文化和智識的養分。新英格蘭望族所生發出來的政治不是財富統治,而是賢人政治。
哈佛大學在很大程度上是波士頓婆羅門的產兒,而哈佛在美國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是波士頓婆羅門的秉性和氣象的一個映照。哈佛甚至自殖民地時期開始就立志擔當“全國性的”大學,而不是以新英格蘭、馬薩諸塞州或者新教公理會派(Congregationalist)的教育學術機構自命。
哈佛歷史上任期最長影響也最大的校長查爾斯·埃利奧特在其1869年的就職演講中宣稱:哈佛將秉持“代代相傳的主流精神……這應該是一種普世的(catholic)精神……這所大學熱切地盼望能夠通過培育知識上誠實、思想上獨立的人來服務於國家……(而)大學不是由一個教派,而是由一個國家來建立”;哈佛“將培育一種公共責任感,而正是這種偉大的美德才使得共和國成為可能”。美國精英之“公”和“通”的氣象,哈佛之塑造美國精英的使命感在此躍然於字裏行間。
在19世紀晚期以後激盪的思想潮流和政黨政治演變的歷史中,波士頓婆羅門和哈佛在總體上成為現代民主黨自由主義的支撐和堡壘。而波士頓波羅門、新英格蘭地區和哈佛在智識上的卓越性,與其社會和政治上鮮明的自由派立場之間有着深層次的相關性。對美國的歷史大勢以及對美國精英的演變和性狀,這種相關性是有深刻而重要的意味的。
文化縱橫10月新刊上市,可在微店訂閲:https://k.koudai.com/Qm5fRm=W
▍反“富豪統治”的現代民主黨自由主義
在有着根深蒂固的洛克式反國家主義思想傳統、習慣於以財產權和私人利益來界定自由的美國,在內戰以後迅速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中財富力量急劇膨脹的“鍍金時代”,追求公共性和普遍性的最主要的障礙來自金錢的社會力量、金錢的政治以及佐證金錢霸權的意識形態。
在被稱為“美國世紀”的20世紀,有歷史正當性的美國精英(或者説其主體)必然是要在反對“富豪統治”(plutocracy)的鬥爭中重新塑造自身。美國自由主義長期運動的要旨正在於從公共性的角度重新界定和擴展自由的意義並建立現代福利國家,對富豪統治的反對和批判也正是題中應有之意。
1870年代以後,曾經代表自由勞工的共和黨演變成了大財團和富人的政黨,藉助金錢的力量長期在國內政治中享有對民主黨的優勢。大蕭條的爆發將羅斯福新政推進美國曆史,才有效地削弱了共和黨保守主義的力量。共和黨人的典型標語是:“美國的事業就是商業”(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1923至1929年任總統的共和黨人柯立芝語),“對通用公司有利的就是對美國有利的”(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國防部長威爾遜的名言)。
而無論是進步黨人,還是承續了進步主義的民主黨新政派,都以今日政治生活中已然見不到的率直和激烈反對財富統治,以致於羅斯福被認為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每天都吃一個烤百萬富翁”。按照今日流俗之見,國家權力的擴張必然導致腐敗的蔓延,但事實上“新政施行之清正廉明令人驚歎”(克魯格曼語),正説明了新政精英羣體的公忠有質和道德優越性。
戰後美國政治發生了新的複雜變化,自由主義變得温婉恭讓多了,新政派逐漸被邊緣化,已不可能出現進步黨人和羅斯福那樣激烈的反富豪政治。但戰後新政自由派的主要發言人和思想家,如加爾佈雷思和施萊辛格等,也都把譴責富豪統治作為自己的主要使命。
施萊辛格在作為戰後自由派宣言書的《至關重要的中心》中對富豪統治的狹隘、委瑣、勢利和庸俗表現了極大的蔑視和憎惡:“富豪統治的思想出發點是階級而不是國家,是私人利益而不是社會責任,是商業交易而不是戰爭,是苟安而不是榮譽”;富豪統治的結果“是閹割統治階級的政治能量”。
代表公共性、普遍性和變革精神的20世紀美國精英的成長史,是與開啓於進步主義運動,經羅斯福新政再到肯尼迪、約翰遜的現代民主黨自由主義的歷史變遷聯繫在一起的。20世紀美國政治精英和精英政治作為理想類型,與民主黨自由派多有重疊,而不太容易與共和黨保守派在印象上聯繫在一起。
在據説沒有社會主義的美國,民主黨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替代物,抑或可以説是美國式社會主義。也可以説它是“非美國的”:是超越美國的主流傳統和侷限性的產物。這樣的思想和政治運動只能產生自一個普遍主義的(universalistic)階級的母體。這樣的階級也只能是一個基於智識和理念的階級而不是基於經濟和利益的階級。
在現代商業社會,智識和理念的階級與商業和財富的階級之間的對立比它們之間的合流更合情理,對社會也更有益。
現代美國自由主義正發端於智識和理念對鍍金時代的背叛。在鍍金時代,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嚴重不公,世風低俗墮落,流氓大亨(Robber Barons)和惡人政客(spoilsmen)成為最為耀眼的成功者,政治生活中“沒有領袖,沒有原則,沒有政黨”。進步主義運動的推動者是一些學者、記者(所謂“黑幕揭發者”)和社會工作者,以及一些有學者背景也有“理念人”特性的青年政治家(最典型的是西奧多·羅斯福)。
進步主義政治家共同的特性是:追求超越物質利益和狹隘利益集團之上的社會理想,陽剛而浪漫的民族主義,以及對富人階級的公開鄙視;而進步主義學者和社會工作者則有一種質樸而鮮活的科學主義信念和改革精神,相信“社會工程”和“社會技術”,致力於開發和推進“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尋求將政治和學術界的力量結合起來改善社會。
也正是在這個時代,以所謂“威斯康辛理念”(the Wisconsin idea)為標誌和範例,大學和現代美國自由主義的結盟開始形成,智識和權力的關係的美國形態也由此生髮。1900年,著名進步主義政治家拉福萊特(Robert M. La Follete)當選為威斯康辛州州長,向威斯康辛大學的學者大開參與州政之門,使這所名校一時成為社會科學介入政府事務的平台,號稱“一所統治着一個州的大學”。
絕非偶然的是,正是這一時期在威斯康辛大學經濟、政治和歷史學院,埃利(Richard Ely)和康芒斯(John R. Commons)創立了美國的老制度經濟學,而這是一種上承德國歷史學派、下接凱恩斯主義的大政府主張,反對自由放任的、因而也是“非美國的”經濟學,是一種高度契合後來民主黨人的福利國家和社會正義理念的經濟學。
同樣絕非偶然的是,新政時期羅斯福大批吸收知識界人士進入白宮,“智囊團”(brain trust)成為民主黨政府乃至於美國政治的一個標識;而肯尼迪、約翰遜時期的聯邦政府更是湧進大批常青藤名校教授和前羅茲學者,成為所謂“出類拔萃之輩”(the best and brightest)的匯聚之地。
對説明美國精英的特性有豐富含義的一個事實是,20世紀以來,美國知識界已然形成所謂“左翼傳統”,總體傾向於民主黨,大學教授中自認為是民主黨人或者“自由派”者常在百分之七八十。而在大學和知識界範圍之內,更容易生髮普遍主義和公共關懷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術領域裏的大學教師的自由左派比例最高,自然科學次之,而與商業有聯繫的應用性學科的成員則更多地是共和黨的支持者。
民主黨自由派與學術界的親和與聯盟,共和黨保守派與財富集團和反智主義的關聯與重合,這種基本格局大體延續至今,此中固有可資深思之處。
▍學術生活與政治精英的生成機制
智識階級與民主黨自由主義的聯盟和共生也需置於現代美國學術生活的背景中加以審視。智識階級——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要成為政治化的國家精英,就要超越知識生產者的單一身份和“為學術而學術”的現代知識行業的準則。然而實際上,現代的智識階級並不必然是公共的和普遍主義的階級。和現代社會的其他領域一樣,現代學術生活要受到分工和專業化的鐵律的宰制,它本來更傾向於製造工具主義的專家而不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理念人”。古老的智識階級到了現代社會要遵從職業主義、客觀主義和價值中立的工作倫理,要經歷去公共性和去政治化的洗滌。
19世紀後期以來也是美國大學勃興和學科分化的制度體系確立成型的時代,沒有學科規制的知識和沒有專業的知識人被廢黜,知識生活傾向於“在越來越小的領域知道得越來越多”。不可否認,為學科規制所主宰的知識生活有一種內在機理,會貶抑和消蝕對基本的、深刻的、重要的問題的追問,進而有消解知識和知識人的公共性和普遍性的效應。的確,20世紀初的美國也有人(如赫伯特·克羅利和沃爾特·李普曼)預言,掌握美國未來社會的精英階級將由技術專家所構成。
然而,美國知識生活的機制,以及政治化的精英階級的生成機制,並沒有完全為偏狹的專業主義和僵硬的工具主義所主宰。眾多的美國知識界領袖洞悉專業主義對美國民主和公共生活的複雜後果,就當時知識生活細碎化和去公共性的趨勢提出疑慮和批判。比如杜威就探究了專家和共同體生活之間的緊張關係,號召專家承擔“知識大眾化”的公共道德責任。
1920年代以後,社會科學領域裏出現了旨在強化知識的貫通性和公共價值的制度性努力,而這一努力的一個初始方式就是鼓勵跨學科研究。1923年,在一些社會科學領袖(特別是查爾斯·梅利亞姆)的主持和號召下,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建立,其宗旨在於針對美國社會科學研究越來越細瑣和脱離現實的取向,提倡和贊助跨學科、綜合性的和麪向現實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研究。
這個機構以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巨大財力支持了眾多社會科學家,極大地推動了美國社會科學在20世紀上半葉的風尚和走向。同時,哈佛和其他一些頂級大學紛紛設立“校席教授”的最高教銜,授予那些“作出跨越知識的常規界限的智力貢獻的”學者。
而哈羅德·拉斯維爾等則開始開發“政策科學”的觀念,指向“克服現代生活的分裂傾向,創造私人和公共生活的目標和手段之間更大程度的整合”。不難理解,知識生活,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知識風尚與政治化的精英集團的構成和性狀之間存在着微妙而重要的關係。特別是在民主黨執政時期,美國大學教授中多有在政府和學界之間“進進出出的人”,在此深有根由。
對生成精英的機制更為直接和切題的是大學教育。在現代社會諸領域中,最有必要,也最有可能在順應分化和專業主義的同時又能有效地對這一律令構成反思和制衡,並在新的基礎上達成普遍主義和公共性的制度領域只有兩個,一是大學,二是國家。大學的政治功能是向國家和社會輸送公共性和普遍主義的理念和人員。
就此而言,20世紀美國精英大學 “通識教育”承擔着極為重要的使命。在美國研究型大學主宰高等教育的時代裏,“君子不器”的精神並未全然泯滅,通識教育接續了古典文明和英美傳統學院中培養特權階級或者“紳士”的“自由教育” 的精神,從根本上説是一種對專業化和職業主義的背反和匡正,是社會保留和養育普遍主義精神的基地。通識教育宣佈培養“民主社會的公民”,但精英大學的通識教育所產生的無疑不是一般的公民,而是其中的精英成員,包括“統治者”。
當然,生成美國精英的機制並不全然在於大學。在進步運動以來的政治和思想變化的大勢之下,鍍金時代爆發起來的富人階級似乎在效法老的波士頓婆羅門,開始急速地提升他們自己的智識和審美,也開始更多地向社會顯示他們的向善之心和公共服務精神。他們開始捐贈,開始設立推進社會福利、社會智能和人類和平的立旨高遠、目光遠大的基金會。
企業家階級在根本上無法成為普遍的階級,但他們通過改變自己和提升自己而獲得了更多的普遍性,或者向普遍主義的精英階級輸送人員。所謂的“勃登布洛克動力學”開始起作用了,起家富豪的第二代、第三代進入政治領域,且總體上不乏莊嚴正大的氣象,有些甚至是有英雄氣概的人,典型的是肯尼迪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
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走向全球性大國的過程中,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華爾街和商界一批有國際經驗和視野的商人和律師成為推動美國放棄源遠流長的孤立主義、建立全球性視野和抱負的中間力量。他們不僅致力於塑造和促成美國精英中的“自由國際主義共識”(而這與內政中的民主黨自由主義在根本上是趨於一致的),而且以各種方式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繼而構成冷戰初年急劇擴大的“國家安全權勢集團”的核心和砥柱。
賴特·米爾斯所批判的軍事、企業和政治領域裏的權力精英高度同質化的情形, 以及所謂“軍事—工業—學術複合體”的浮現,從我們的角度看來,也正映照出美國政治精英之跨越貫通多個領域的良性特徵。而在20世紀美國民主黨自由主義構築福利國家、管理型國家和“國家安全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歷史長波中,美國精英的這種貫通的特性以及與之相輔相成的政治取向是一個基本的條件。
— 2020年10月新刊目錄 —
▍域外
美歐跨大西洋關係的中國挑戰
任希鵬
▍封面選題:美國的百年未有之變局
在試圖理解中美關係的變化及未來走向的同時,我們也驚異地發現,我們自以為熟悉的美國彷彿變得陌生了——美國不僅成為當前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並且隱藏在其社會內部的階級、族羣、政治意識等不同類型的矛盾,也在疫情蔓延之時不斷湧現為各種激烈的社會衝突。顯然,美國正在同世界一起,經歷一場百年未遇的變局。
中美衝突:國際經濟層級體系的裂變
封凱棟
尋找新的“敵人” :美國對華戰略加速調整的國內根源
潘亞玲
從“帝國”到“國家”:美國國家能力轉型進行時
歐樹軍
里根政體的衰敗與美國重建的特朗普道路
左亦魯
疫情後大國關係新格局
紀明葵
▍城市政治經濟學
全球化時代城市的轉型發展
周偉林
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已有一兩百年曆史,要了解其城市演化,需要讀書、看博物館。而今天,我們非常幸運地經歷着一個“濃縮版”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變化過程,可以通過持續的觀察,編織動態畫卷和邏輯鏈條,藉助一些觀察點(村、鎮、縣區、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新區新城,老街古城),觀察空間、功能、權力(利)等結構的變化。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美國國家構建過程中的科學公益
牛 可
現代美國公益不能和美國社會歷史環境割裂開來加以觀察,它連帶、匯合了現代美國曆史的諸多重大潮流和事態,呈現、張揚了美國資本主義、美國公民社會、美國精英生態的關鍵特性,是現代美國曆史的樞紐性事物,也是“美國世紀”的重要篇章。
▍技術革命與社會變遷
近年來,新的信息技術工具正日益深刻地捲入國家治理之中,為治理過程提供了更高效的信息收集、認證和流通機制。對此,許多意見往往擔憂新技術將賦予國家更加強大而不可控的權力,因此可能會帶來侵犯隱私、加劇歧視等負面後果。本期“技術革命與社會變遷”專欄刊登的兩篇文章,則以更樂觀的態度和客觀的分析,觀察、思考和想象了新的技術工具為個人和社會福利與國家治理帶來的積極變化。
“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實踐及其理念
戴 昕
區塊鏈與國家治理的融合重構
李雯佳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進行中的開創:華為實踐的工業史意義
宋 磊
完全在當下的國際關係之中理解華為實踐,可能會低估華為實踐的意義;過於強調具有排他性的技術進步,則可能會掩蓋具有公共性的組織形態創新。
▍社會結構變遷
精細分層社會與中產焦慮症
熊易寒
中產階級的焦慮症與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從扁平社會到精細分層社會,社會階梯變得越來越長,社會不平等加劇了人們的競爭心態和焦慮心理。
當小農户邁向大市場
譚同學
在邁向大市場的過程中,小農户的生活經歷了從工作、經濟收入的變化,到社會關係網絡的重構,再到價值觀念的不斷重塑,較之過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狀態,不確定性急劇增加。
▍學術評論
文科為什麼要交叉——兼論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
錢乘旦
文科交叉已經是大勢所需。雖説死守原有的學科邊界,在研究課題上繼續深究,仍然可以做出成績;然而,要使文科獲得質的發展、更符合時代的需要,交叉就是舍其不可的。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拉丁美洲的未竟工業化
程文君 鄭 宇
要想擺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國家不僅需要經濟改革來重新找到經濟增長動力,更需要綜合的政治解決方案以突破既得利益羣體的限制。只有在強大的新興利益聯盟的支持下,持續性的產業轉型和升級政策才可能推行。而在許多拉美國家,這種解決方案是無法靠政府更替來獲得的。
“弱國家”困境和埃及的再工業化前景
段九州
埃及的工業化進程之所以緩慢,正是因為國家能力建設的不足以及國家自主性的缺失,制約了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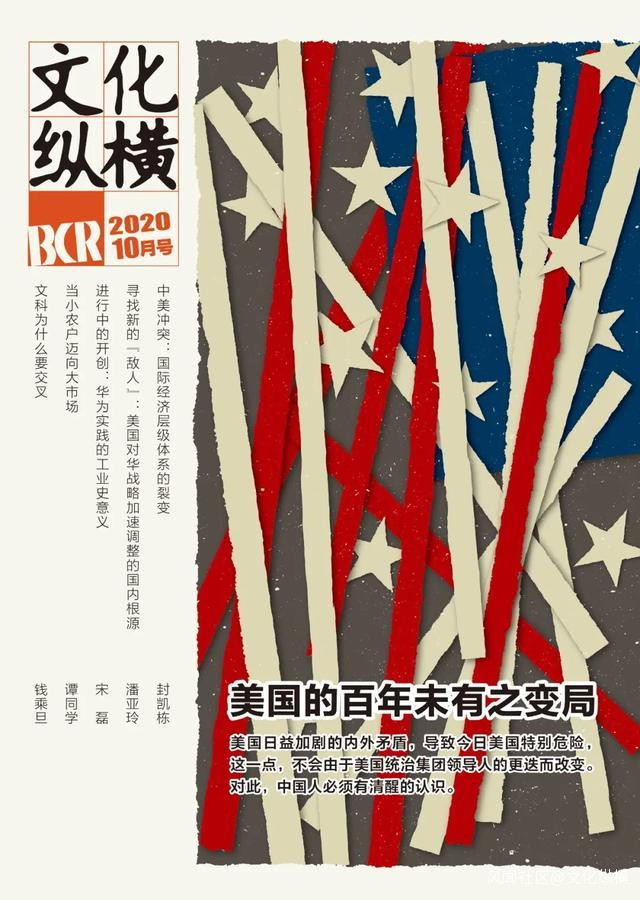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雜誌2008年12月刊, 原標題為“美國精英的品質及其生成機理”。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所有,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回復此微信獲得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