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乎想象:兩彈一星元勳背後的艱辛故事 (下)_風聞
铁中堂-公众号:老铁讲故事 (id:sheyingtt)2020-10-09 15:00
因字數限制,下一部分發在這裏。
上一部分,請看這裏:超乎想象:兩彈一星元勳背後的艱辛故事

他們要趕在冬季到來之前做好新一輪爆轟物理實驗準備。
當時生活極為艱苦,大家餓得狠,也沒野菜來煮湯充飢,組裏不少人餓壞了胃,往往在做關鍵性實驗時胃痛發作。
王淦昌只能這樣勉勵組員:「饑荒歲月,都餓呵,只要餓不倒就要堅持幹,不幹就沒出路。」
09
1961年1月,肯尼迪上台。
也從這年開始,美國密切關注中國的原子彈研製進度。
美國情報部門還發射了許多間諜衞星,並且攜帶改進的高分辨率照相機,帶有充足膠片,得到了國內的許多清晰照片。
當時中央獲悉,美國會採用手段破壞蘭州的核燃料工廠,便準備了兩個對策,一個是從蘭州拆遷到西南山嶽地帶;另一個是加速蘭州廠建設,爭取儘快生產鈾燃料,即使被炸燬,也得到足夠的核燃料。
中央採取了後一對策。
當時大家都很謹慎,那年,有一種外號叫「黑寡婦」的美製高空偵察機,飛行高度2.2萬米,可以無所顧忌、長驅直入中國腹地羅布泊,具有打擊核基地的能力。
當時只有蘇聯產的「薩姆2」導彈,才能打中黑寡婦,但中蘇已經交惡,所以中國只能加快自制導彈的工作進程。
這個重任,便交給了錢學森。
1963年初,位於青海金銀灘的核武器研製基地基本建成。
二機部黨組決定,從3月起,核武器研究所科研人員,從北京陸續遷往位於青海的核武器研製基地,為了適應大規模的試驗要求。
金銀灘海拔3200餘米,屬於高寒缺氧地區,平均氣温在零下4度,最低氣温可達零下30度。
由於當時的基地建設,是搶建科研設施和生產線,最後才是宿舍等生活設施,不少科研人員去後,還得住在簡易的坯房和軍用大帳篷裏,條件十分艱苦。
張愛萍知道那裏環境艱苦,便作了10分鐘的動員報告,激情澎湃,充滿了感染力:
大西北,我去過。那裏一片茫茫,人跡罕至。這個地方苦不苦?當然苦!因此,有些同志怕去了不適應,影響研製原子彈,這也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不過,也絕對不是像王維所説的「西出陽關無故人」,連一個人也見不到,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1958年,解放軍工程兵部隊就已經進駐那裏,建設核試驗基地了!他們正等着你們,準備歡迎你們呢!他們已經為你們建了宿舍和實驗室,你們現在去的生活條件,要比他們去的時候好多了!
我會和你們一起去西北,我打前站。我向你們表示:我願當你們的服務員,做好你們的後勤保障工作。
確實,解放軍工程兵初到戈壁灘時,條件更為艱苦,就連李覺將軍也只能住地窩棚,用黑毛氈蓋頂,用土木圍牆,沒有暖氣。

甚至很多士兵只能喝「蚊子水」,因為時間長了,就會堆積很多蚊子,在杯裏有厚厚的一層,但如果把蚊子都撈出來,水也就所剩無幾了。
經過了三四年建設,工程兵部隊大大改善了高原的居住環境,終於在荒涼地帶建起了一座新城。
由於人多,樓房不夠分配,李覺帶領機關行政幹部住進了地窩棚,讓科技人員住進暖樓,讓人敬佩。
此時,國際上又發生了一場大變故。
1963年7月25日,美蘇英三國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這個條約全面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一切核武器試驗。

同年10月,聯合國通過該條約。
這個條約的真實意圖顯而易見。
條約公佈後,周恩來對毛澤東説:「赫魯曉夫公開講,必須對富有野心的中國施加壓力,讓中國遵守條約規定,並且採取措施,從各種渠道阻止中國得到一切有關核武器的技術。」
周恩來又説:「主席,這個條約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試驗。也就是説,美、蘇、英三國,可以繼續通過地下核試驗發展核武器,而中國要進行一般性核試驗的權利被剝奪了。」
毛澤東問:「我們搞原子彈,能搞地下核試驗嗎?」
周恩來搖頭:「目前條件下,中國還不能進行地下核試驗,我們第一次核試驗只能在大氣層進行。」
毛澤東有點生氣:「欺人太甚!三家條約,想讓我們停下來,沒那麼容易!我們要發表聲明,揭露這個條約的歧視性。原子彈哪怕100年也要造出來,有什麼辦法?沒有那東西,人家就説你説話不算數!」
1963年11月,美國和蘇聯已經做出作戰部署,一同對核試驗基地羅布泊進行核打擊,試圖將實驗設備和人員全部抹去。
美國甚至在沖繩部署了多枚戰略導彈,作戰半徑覆蓋中國大部分區域,包括北京,上海,西安,香港等大部分重點城市,而蘇聯對此保持默認。
局勢十分緊張。
直到有一件事的突發,徹底打亂了美國的佈局。
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在德克薩斯州遇刺身亡。
10
1963年12月24日,聚合爆轟試驗進入倒計時。
王淦昌、朱光亞、彭桓武、郭永懷、鄧稼先、周光召等人早早來到了實驗場。
一切準備完畢,全體人員進入掩體,陳能寬下達了「起爆」命令。
頓時,火光沖天,巨大的火球翻滾着,示波器上閃出了藍色光亮。

40分鐘後,測試底片被衝洗出來:向心爆轟波理想,點火裝置點火成功!
這標誌着原子彈研製有了重大突破。
只要裝上核部件,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就能進行總裝,距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僅一步之遙。
親臨試驗場的張愛萍興奮之餘,直接賦詩一首:
祁連雪峯聳入雲,草原兒女多奇能。
煉丹修道瀝肝膽,應時而出驚世聞。
到1964年春天,託舉原子彈的百米鐵塔在羅布泊建成。
1964年8月初 ,青海金銀灘,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開始總裝。
裝配開始前,張愛萍看望了全體裝配人員,語氣感慨:「你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目標,第一顆原子彈!現在,你們要像父母愛護嬰兒那樣愛護它呀!」
現場總指揮吳際霖一聲令下:「總裝,開始!」
裝配人員走向各自崗位,緊張有序地開始對原子彈進行總裝。
原子彈總裝進行了3天時間,當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總裝完畢時,在場所有人都流下了熱淚。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即將橫空出世。
1964年9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經過分析,向白宮報告:根據新拍攝的太空照片,有充分理由認為,中國西部一個可疑的設施,是一個能在兩個月內投入使用的核試驗基地。
美國國防部設想了四種打擊中國核設施的方式:
一、由美國進行空中打擊;
二、由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政府派戰機空襲;
三、在中國內部僱用特工進行破壞;
四、空投蔣介石政府的行動小組進行攻擊。
他們認為:動用外科手術來摧毀中國的核工廠,並且使人看來像是發生了一次原子事故,在技術上是可能的。
美國《星期六晚郵報》發表文章:「總統和他的核心顧問們,原則上都認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阻止中國成為一個核國家,讓中國共產黨在核方面絕育。」
總指揮張愛萍回憶道:
在1964年8、9月間,夜間常在空中看到衞星經過試驗場區上空進行空間偵察。這些情況,總理是直接電話告我注意儘可能隱蔽,我也常接電話報總理,報告試驗現場的一切情況。
他向中央專委提出兩個方案:一是早試,定於10月至11月之間進行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二是晚試,推遲到1965年開春以後進行核試驗。
周恩來最後表態:
最近一段時間,對我國動手的跡象很多,他們對我們情況大體是掌握的,不論是真是假,我們都要做好充分準備。
我們如果現在進行核試驗,美國可能來轟炸,但不管它怎樣轟炸,我們都得試驗。赫魯曉夫説我們搞不出來,美國人也説我們不行,我們搞出來就是為了打破核壟斷。
即使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也在所不惜。至於試驗的具體時間,還要仔細研究。
會後,周恩來立即面見毛澤東,將早試和晚試兩種方案作了彙報。
毛澤東思索良久,説道:
「你們想得很細,有道理呀。帝國主義不希望我們搞成原子彈,修正主義也不希望我們搞響。他們怕嘛,以後中國就更不好欺負了……要我看,原子彈是嚇唬人的,不一定用。但既然是嚇唬人的,就早響嘛!」
於是,中央最終決定早試,並按10月份早試的方案進行。
周恩來還下達指示:為了確保核試驗場與北京之間的聯絡保密,應規定出一些暗語和密碼來,今晚就制定出來。
在張愛萍的主持下,有關人員立即着手編制暗語:
首次核試驗的原子彈是圓形,將原子彈取名為「邱小姐」;
裝原子彈的平台叫「梳妝枱」;
連接火工品的電纜像頭髮一樣長,叫「梳辮子」;
原子彈裝配為「穿衣」,原子彈裝配車間,密碼為「住下房」;
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平台為「住上房」;
氣象密碼為「血壓」;起爆時間為「零時」。
一切都在順利進行。
1964年9月29日,原子彈從青海金銀灘起運。
朱光亞通過專線向北京報告:「邱小姐已上轎。」
路程終點是新疆羅布泊,放在一個測試塔上引爆,塔樓高102米。
原子彈分兩部分裝運,大部分部件由專列火車運抵烏魯木齊,享受國家最高元首的警衞規格。
最關鍵的兩個部件——鈾球和點火中子源,由另一專列運至西寧後,再由改裝的伊爾14運輸機,運往核試驗基地。
10月4日,原子彈運抵核試驗場。

10月8日,原子彈裝配完畢,由裝配間工房吊出,運往鐵塔。

張愛萍向北京報告:「邱小姐已經坐在梳妝枱前。」
10月16日15時,被定為核爆「零時」,得到了周總理批准。
16日凌晨6時30分, 開始給原子彈插接雷管,張愛萍再次向北京報告:「邱小姐開始梳辮子。」
16日10時30分,首次核試驗進入清場程序。

張愛萍、李覺、王淦昌、鄧稼先、彭桓武、郭永懷等人,都進入了距離鐵塔60公里處的指揮所裏。
大家的心情很緊張,當時有不少人問鄧稼先有把握沒有,鄧稼先是笑着,不回答,只是一個勁地吸煙。
當被問得實在躲不過去了,他才擠出一句話:反正能想到的問題全想到了。
16日14時40分,張愛萍發射指令:「K1指令已經發出。」
當時大家的表情異常嚴肅。

11
主控站人員按下了電鈕,10秒鐘後,系統進入自動狀態,倒計時從10到0順序跳動。

遠在數千裏外,首都北京,周恩來和聶榮臻一起,手執電話認真聽着。
他們只聽羅布泊試驗基地傳來的報告,以及開始倒數的聲音:
10,9,8,7,6,5……
這10秒鐘裏,大家陷入很可怕的寂靜,筆直坐在地上,一聲不吭。

「零時」一過,強光閃亮,天地轟鳴,巨大的蘑菇雲翻滾而起,直上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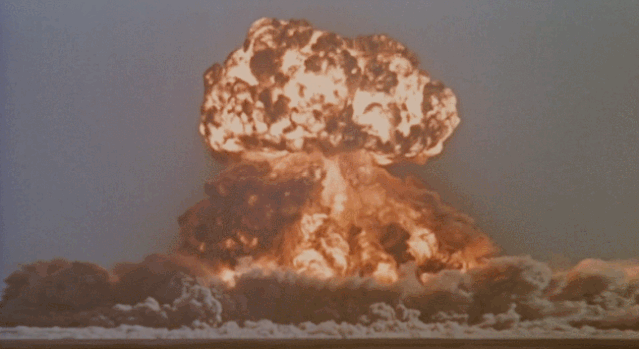
原子彈的衝擊威力,揚起無數沙塵,直接點燃了汽車飛機,將房屋輕易摧垮。

一時間,所有在場的人都毫無反應,許多人張着嘴,先後從愣神中醒過來。
多數人一直到煙雲形成蘑菇狀火球時,才突然歡呼雀躍。

他們舉起雙手,斜着身子順勢倒在沙坡上,用兩腳亂蹬沙石,彷彿任何鼓掌和雀躍都無法泄出胸中的亢奮。
他們跳躍着,眼淚全都流了出來,互相擁抱在一起,把帽子拋向天空。
鄧稼先什麼話都説不出來,只想痛哭一場。
六年煎熬,都隨着原子彈的煙雲一塊升上天空。

張愛萍拿起專線電話,連接着幾千里之外,聲音有些顫抖:「報告總理,原子彈……已經爆炸成功!」
周總理冷靜問:「怎麼證明是核爆炸?」
這時,防化兵已經測得了地面的放射性沾染數據,確認了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張愛萍再次向周恩來報告:「根據多方面證實,確實是原子彈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周總理在電話裏也很激動:「我代表黨中央、毛主席向你們致以熱烈的祝賀,我立刻到人民大會堂去!」
當毛澤東聽到這一報告後,更為嚴謹:「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繼續查清楚,最好讓外國人先報道,我們再發表。」
沉浸在喜悦中的工作人員問聶榮臻:「原子彈爆炸成功了,為什麼不早點公佈消息呢?」
聶榮臻笑着説:「剛才與總理通了電話,總理説,毛主席指示,我們先不忙公佈,要等外電報道證實以後再公佈。」
這天晚上,核試驗基地舉行慶祝宴會,一羣科學家開懷暢飲。
李旭閣回憶:
到晚上開慶祝酒會時,大家敬酒喝酒啊,興奮得很。連平時不大喝酒的朱光亞也喝得步履蹣跚,走路都讓人扶着。朱光亞看了後説,他那不是光喝酒喝的,他一天沒吃飯,沒睡好,累的,所以他讓鄧稼先扶着他走。
反正當時大家都很興奮,在那兒玩啊鬧啊,拿碗大口喝酒。大家都很高興啊,久久鬱積在心中的盼望、緊張、辛勞,隨着596核爆炸成功,一下子釋放出來了,都輕鬆了。
朱光亞後來説,那一天,他平生第一次喝醉了。
當天傍晚,周恩來接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全體演職人員。
誰也沒料到,周恩來滿面笑容地向全體人員説:「今天下午3時,我國在西部地區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核試驗!」
這一消息太過震驚,以至於在場的三千多文藝工作者先驚愕,接着便是歡呼,使勁地跺地板。無論周恩來怎麼示意大家安靜,歡呼聲都沒有消停。

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續播放了《新聞公報》,《人民日報》也印發了號外,北京街頭大家瘋了一般地搶閲號外。
美國總統約翰遜在聲明中表示:「中國原子彈只是一個粗糙拙劣的裝置。」
幾天後,他們不得不改變這種説法。
因為根據雲塵的分析檢測,他們確認中國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使用的是鈾235,表明中國有大工廠生產濃縮鈾235,很快就能製成核武器,而且採用先進的內爆型,在設計上更加完善,威力也更大。
朱光亞在給上級部門的報告中寫道:「連美國原子能科學家也不得不承認,我國這次核試驗已超過了美、英、法初期核試驗的水平。」
美國總統約翰遜詢問,世界各地人們都説些什麼?
美國情報局局長卡爾·羅温表示,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那些國家,表態説應該接受中國參加聯合國。
10月18日晚,約翰遜在全國電視演講中説:「中國的原子彈並不使我們驚奇,從單次核試驗,到有效的核武器系統,要經過一條漫長的道路。而我們美國的力量是壓倒一切的,我們將保持這種優勢。」
香港《新晚報》,以《石破天驚是此聲》為標題,説:「這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1964年10月16日這幾個字應該用金字記載在中國的歷史上!」
香港《晨報》則以《中國人的光榮》為題,説得更加乾脆痛快:「中國之月亮原來也是圓的。」
法新社巴黎10月17日電,內容是:
中國在15日和16日扔出了兩顆影響世界平衡的炸彈,一顆是15日讓赫魯曉夫下台,一顆是16日的原子彈爆炸。
這顆炸彈是心理武器,而不是軍事武器,它使中國獲得了一個核武器國家的形象,在亞洲增加了威信。亞洲那些依附它的人會更加依附它,那些害怕它的人,例如南越人、泰國人,將更加害怕它。
原子彈試爆成功後,中國鄭重建議召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銷燬核武器問題。
也從這一天開始,中國有了在桌子前談判的資格。
12
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是在102米高的鐵塔頂部引爆的,也因此,外媒嘲笑中國的原子彈是「無槍的子彈」。
錢學森着力去解決「槍」的問題。

他用的「槍」是導彈,也就是原子彈+導彈=核導彈,射程遠,命中率高,足以震懾敵人。
但是研發導彈的過程並不順利。
1962年3月21日,「東風二號」導彈在酒泉發射,隨後失去了控制,墜落在六百米遠的地方,發生劇烈爆炸。

現場所有人目瞪口呆,誰都沒有經歷過這樣巨大的事故。這次導彈的失敗,給中國年輕的導彈研製團隊潑了一盆冷水。
錢學森急忙趕到酒泉基地,雖然承受了很大壓力,但仍然鎮定地給大家打氣:「同志們,不就是摔下來一個東風二號嗎?」
錢學森帶領大家在基地附近收集「東風二號」導彈的殘骸碎片,一臉嚴肅,仔細分析着「東風二號」失敗的原因。

這次失敗,也讓他提出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則:「把一切事故消滅在地面上,導彈不能帶着疑點上天!」
這一原則,後來成了中國火箭、導彈研製不可動搖的原則,沿用至今。
改進後的「東方二號」導彈,再也沒有出現事故,成功發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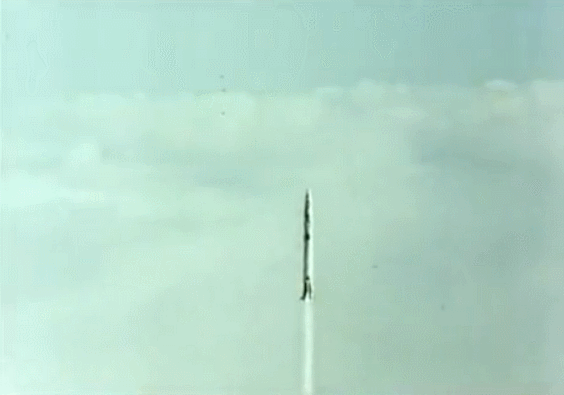
經過周密部署,經中央批准,中國首枚核導彈在1966年10月擇機發射。
核導彈如果失誤,後果會相當嚴重,周恩來主持會議,下達了命令:「這次熱試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要周到細緻,做到萬無一失!」

10月27日9時,載有核彈的「東風二號」點火升空,到達了894公里外的靶心上空,成功爆炸。

從此,中國的核武器,不僅有彈,而且有了一支能夠射向地球各個角落的「槍」。
翌日,錢學森的大名出現在美國《紐約時報》上,報道中這樣寫及他:一位15年中在美國接受教育、培養、鼓勵併成為科學名流的人,負責了這項試驗,這是對冷戰歷史的嘲弄。
馬不停蹄下,氫彈也提上日程。
實際上,早在1961年,錢三強就找到了于敏,將研製氫彈的重任交給他。
于敏後來回憶:「錢三強先生這次談話,改變了我的一生。」
氫彈的威力比原子彈大得多,而且點燃氫彈,必須要用到原子彈。
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先造出原子彈,才可能有氫彈的緣故。
周恩來在會議上説:「當我們沒有原子彈時,有人笑話我們20年也造不出來。現在,他們又説我們有了原子彈不算什麼,離有氫彈、洲際導彈還很遙遠。這話沒錯。但我們呢,就得要爭這口氣。」
不久之後,毛澤東指出:「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要快。」
於是,鄧稼先領導理論部的科學家們夜以繼日地工作,摸索氫彈理論設計方案。

要研究熱核燃燒現象和規律,電子計算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那時,我國只有一台104電子管電子計算機,就是靠着這個小機器,每週十幾個小時,于敏和全組科研人員耗費四年時間,才將氫彈理論涉及趨於完善。
外國人稱之為「鄧一於理論方案」。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這個火球的威力,讓400米處的鋼板熔化,水泥構件的表面變為玻璃體,14公里外的磚房被吹散。

這次氫彈爆炸威力為300萬噸TNT當量,聶榮臻得知後高興地説:「夠了,夠了。」
人民拿着「號外」,在田野裏大聲朗讀,滿是喜悦和激動。

而這時,距離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僅僅兩年零八個月,美國用了七年零三個月,蘇聯用了四年,英國是五年零兩個月。
法國戴高樂總統,直接把原子能總署的官員叫到辦公室,質問法國的氫彈為什麼遲遲搞不出來,讓中國搶在前面了。
在場的人無言以對,因為誰也説不清楚中國這樣超常的原因。
戴高樂當時很憤怒,直接拍桌子。
7月7日,毛主席在接見軍訓會議代表時説:「兩年零八個月搞出氫彈,我們的發展速度超過了美國、蘇聯和英國,現在居世界第四位。我們搞原子彈、氫彈有很大成績,這是赫魯曉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我們走自己的路,應發給他一個1噸重的勳章。」
同年,錢學森研製的「紅旗二號」地對空導彈成型,開始裝備部隊,生產了12000枚。
1967年9月8日上午,一架「黑寡婦」進入浙江嘉興地區偵察,直接被「紅旗二號」擊落。
中國的領空終於安靜。
13
氫彈試驗成功後,地下核試驗成為中國要攻克的下一個目標。
經過兩年努力,也就是1969年9月15日,第一次地下核試驗的各項工作準備就緒。
工程兵開始進行回填、封堵坑道。
這一天,周恩來三次打來電話,詢問有關情況,並問道:「一週時間的回填,能不能再提前一些?」
當時,大家都以為總理在督促工作,但據後來史料披露:
1969年8月20日晚,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緊急約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告知蘇聯準備對中國的戰略目標展開核打擊,奉命徵求美國的意見。
基辛格十分震驚:「不是開玩笑吧?這個計劃太可怕了,大使閣下。」
多勃雷寧告訴基辛格,這是他剛接到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的指示。
基辛格沉默了很久,説:「我本人現在對此無可奉告,但請大使相信,我會立即報告總統。」
美國總統尼克松得知後,立即召開會議,明確回絕了蘇聯,並且想辦法告知中國。
因為在當時西方國家眼裏,中國已經不是最大的威脅,甚至需要拉攏中國一起對抗蘇聯。
8月28日,美國《華盛頓明星報》刊登了一則消息,標題十分醒目:蘇聯欲對紅色中國做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報道中説:「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酒泉導彈基地、羅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長春等重要戰略目標發動外科手術式的核襲擊。」
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判斷,如果蘇聯動手,時間很可能在國慶節,為以防萬一,應取消國慶節羣眾集會,國家領導人也不要在天安門城樓亮相。
毛澤東聽後淡淡一笑:「原子彈很厲害,但鄙人不怕。蘇聯要扔原子彈,那位尼克松總統很緊張呀,我可不緊張。國慶節不搞集會,就是讓人家笑我們有點怕嘛。我還是要上天安門。」
毛澤東又説:「他們讓我們緊張,我們可不可以也放它兩顆?嚇唬一下他們嘛。」
於是,在9月23日,我國首次地下核試驗取得成功。

一週後,也就是9月29日,在羅布泊核試驗場又成功進行了一次氫彈空爆試驗。
兩次核試驗後,中國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保持着沉默。
美聯社為此發表評論説:
中共最近秘密進行兩次核試驗,其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們在這一時刻進行核試驗,並非為了得到某種成果,而很可能是臨戰前的一種演習和檢測……
10月1日,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興致勃勃地檢閲了遊行隊伍。
一切都風平浪靜。
最終,蘇聯沒敢對中國實施核打擊,一場核危機隨之消散。
到了1970年4月,載着「東方紅一號」衞星和「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的專列,秘密抵達酒泉衞星發射場。
孫家棟擔任人造地球衞星的總體設計,他對這顆「政治衞星」的設想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見、聽得到。」
他回憶説:「那個時候老百姓只有收音機,這個頻率短波聽不見。後來想了個辦法,就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給轉播一下。但是聽什麼呢?光聽嘀嘀嗒嗒的工程信號,老百姓聽不懂。最終,我們決定了放《東方紅》樂曲。」

1970年4月24日,中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衞星,高度2384公里,用20.009兆周的頻率播送《東方紅》樂曲。
毛澤東、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錢學森、任新民、孫家棟等第一顆衞星工程研製的代表。

毛澤東緊握着錢學森的手,表示祝賀。
這時,任新民「躲」在後邊。
周恩來發現後,説:「任新民同志,請到前邊來,不要老往後邊躲,你的座位在我這邊。」
周恩來向毛澤東介紹任新民:「他就是我們放衞星的人。」
毛澤東讚歎:「了不起啊,了不起!」
14
兩彈一星元勳,在時代浪潮中綻放了無數光芒,也因為歲月流逝,最終落下了帷幕。
晚年,朱光亞的腿腳不方便,散步的時候經常需要人來攙扶。
但他有一個雷打不動的習慣,那就是每當站崗的戰士向他敬禮時,他會立即站定,將右手的枴杖換到左手,然後正規地舉起右手,給戰士還了一個軍禮。
而80歲高齡的錢學森,走路同樣困難,甚至雙腿疼痛,經檢查,患了「雙側股骨頭無菌性壞死」,不得不坐上輪椅。
接着他又患上「腰椎楔形骨折」,難以久坐,只能卧牀靜養。
錢學森夫婦
由於久卧病榻,他的肌肉萎縮,甚至被懷疑得了「老年痴呆症」。
於是,趁着錢學森住院,大夫對他進行老年痴呆測試。
大夫按照測試流程,問錢學森:「100減7是多少?」
錢學森不假思索:「93。」
大夫繼續問:「93減7是多少?」
錢學森遲疑了一下,答道:「86。」
大夫再問:「86再減7呢?」
這時,錢學森知道大夫在懷疑他的思維能力,竟拿測試小學生數學水平的題目,頓時臉露愠色,大聲呵斥:「你知道你問的是誰?我是大科學家錢學森!」
一生謙遜的錢學森,這一次是被激到了。
負責測試的大夫先是一怔,然後忍俊不禁。如此便能清楚表明,錢學森沒有老年痴呆症。
同樣,看不出是大科學家的還有錢三強。
「他比普通人還要普通。」這是中國科學院機關許多老人回憶錢三強時的感慨。
錢三強的住房,是50年代初建成的三層專家樓,由於年經月久,十分得破舊,而且屋內採光不好,暖氣管也老化,冬天供熱不足,多數情況下,錢三強都要穿着棉衣看書寫東西。
1985年,在許多人勸説下,他才花錢在卧室裝了一台窗式空調,但全年開不了幾次。
他説:「電力供應本來緊缺,開空調既浪費能源,還可能影響別人正常用電。」
事實上,在80年代中期,科學院專門建了幾棟新樓,供老科學家居住,只是錢三強夫妻執意不搬進新房,甚至想出了一個不成立的拒遷理由,説新樓離圖書館遠,不方便。
在工作時,他每天乘公共汽車上下班,風雨無阻。冬天颳風下雪,就身穿長棉襖,腰間繫條圍巾,頭上戴一頂遮耳朵的棉帽,每天往返於中關村和三里河。
在家裏,錢三強和何澤慧過着普通人生活,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飯,自己排隊買菜;衣服破了自己補,補了再穿,捨不得扔掉,他們常説:「笑破不笑補嘛,穿補丁衣服不丟人。」
因為兩人平時穿戴普通,説話又不擺譜,經常被世俗眼光誤解。
錢三強夫婦
有一年冬天,他們一起到西單菜市場買菜,正選購冬筍時,被女售貨員用不屑的口氣指責:「老太太,這是冬筍,很貴的!你要看清楚價錢,不要看錯了小數點啊。」
而讓人扼腕痛惜的,是鄧稼先。
1964年10月,原子彈爆炸後,鄧稼先沒有停下過步伐,組織了幾十次核彈試驗,彷彿永不疲勞。
他經常出入車間,在相當長時間裏,幾乎天天接觸放射物質,受到輻射損傷,幹這一行的人只把這種事叫作「吃劑量」。
在20世紀70年代末一次核試驗中,事故發生了。
當時飛機空投時,降落傘沒有打開,導致核彈從高空直接摔到地上,變成了啞彈。
指揮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點尋找,但始終沒發現核彈痕跡。
鄧稼先決定親自去找,被陳彬將軍阻擋:「老鄧,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錢。」
但鄧稼先只想的是:「這事我不去誰去?」
到了事故區邊緣,他從汽車下來,並且大聲阻攔一行人:「你們站住!你們進去也沒有用,沒有必要!」
如果把這句話完整説出來,應該是「沒有必要去白白做出犧牲」,而鄧稼先認為自己是有必要的。
這位五十多歲的核科學家,向着危險地區衝上去,決然不顧鈈對人體的傷害。
他彎着腰一步步地走在戈壁灘上,四處掃視,邊走邊找。
終於,碎彈被他找到了。
那一刻,他竟用雙手捧起了高輻射的碎彈片。
觀察了一番,他便放心,最擔心的後果沒有出現。
隨後,他拖着疲憊步伐,向吉普車走去,見到趙副部長的第一句話是「平安無事」。
鄧稼先這一輩子,從來沒有主動邀請別人合影,但這一次,他邀請趙敬璞一同合影留念。
左鄧稼先,右趙敬璞
他顯然預感到了什麼。
幾天後,鄧稼先回到北京住進醫院做檢查。
沒有任何懸念,檢查結果表明,他的尿裏有很強的放射性,白血胞內染色體已經呈粉末狀,白血胞功能不好,肝臟受損。
一位醫生説了實話:他幾乎所有的化驗指標都是不正常的。
鄧稼先沒有聽從妻子的勸説,去療養院治療,仍然醉心於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
自從那次吃了特大劑量後,他的身體有了明顯變化。
1980年以後,他衰老得更快,頭直接發白,感覺到身體越來越不行,思維變得遲鈍,工作重擔下,他越加疲憊。
有一次,他和許鹿希到頤和園,準備看菊花展覽,但他們趕去時,展覽已經關門了。
園內,此時的晚霞斜掛西山,他們一同漫步在後山小路上,步子逐漸慢了下來。
還沒走到最高處,鄧稼先覺得有些累了,選了一塊比較乾淨的大石頭坐下來。斜陽餘暉下,萬壽山此時格外安靜。
鄧稼先漫不經意地瀏覽着湖光山色。
忽然,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多恬淡、多悠閒,要能老是過這樣的生活,該多好啊。」
15
1985年7月31日,鄧稼先回到北京,向張愛萍彙報工作。
張愛萍將軍發現他氣色不好,便問:「你怎麼瘦了?氣色也不好,身上有哪裏不舒服嗎?」
隨後,他親自給301醫院的院長打電話,要求安排醫生接診,並派汽車送鄧稼先去醫院。
醫生查完後,認為是惡性腫瘤,生氣地問鄧稼先:「你早幹什麼了?家屬來了沒有?」
「我請兩個小時假來看病,只有警衞員來了。」
「你今天不能走了。」
鄧稼先急忙告訴醫生,他在開一個很重要的會議,不能住院。
醫生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認真地對他説:「這裏不是會議室,這是醫院。」
他立即意識到疾病的嚴重性。
六天後,活體取材檢查手術做完,張愛萍急忙問醫生:「活體檢查怎麼樣?癌是不是擴散了?」
「這個,按常規要在一週之後才能知道結果。」
張將軍急了,他説我就坐在這裏等着,你們儘快拿出化驗結果。半小時後,冰凍切片的結果來了,確診鄧稼先患的是直腸癌。
四天後,即1985年8月10日,鄧稼先做了大手術,清掃癌瘤所侵犯的地方。
5個小時,手術結束,病理診斷是:「腫瘤的病理性質是惡性程度較大的低分化、浸潤性腺癌,直腸旁林巴結個,全部有癌轉移…癌症屬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結及周圍組織轉移。預後不良。」
醫生把從鄧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腸子端給他們,許鹿希用手按了按,淋巴變硬,已經到了晚期(許鹿希曾任北京醫科大學博士生導師)。
手術結束,鄧稼先只能在病牀上靜卧。
一段時間化療後,因為白血胞數目太低,必須中斷治療,醫生同意他回家休養兩三個月。
鄧稼先的生命,已走向了最後的期限。
這時,他反而更加清醒,自己必須搶時間,把幾件重要的事情做完。
他最關心中國核武器事業的發展。
當時的國際環境是,歐美幾個核大國已經接近理論極限,達到了實驗室模擬地步,也就是無需再做核爆,並且他們想用核禁試來封住別國,保住自己的核強國地位。
鄧稼先敏鋭意識到,如果中國不能搶在這個時間內完成既定發展目標,就會喪失在國際政治、外交中的主動權。
出院回家後,他集中全力來幹這件事,找來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雜誌、資料和剪報,請來於敏等人,一起研究起草向中央的建議書。
不久,他再度住院,開始做化療,往血管內點滴藥水,一次要好幾個小時,他只能躺着或坐着,邊治療邊看材料。
坐在身旁的許鹿希,不斷給他擦着滿頭虛汗。
1986年3月14日,他在給同事的一張條子上寫道:「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療,打完後人挺不舒服的。」
3月29日,他又做了一次小手術取活體組織檢查,癌細胞轉移明顯加快,身體越來越差,虛弱得幾乎無法挪步。
他不止一次地對許鹿希説:「我那兩件事必須做完,那一份建議書和那一本書。」
他不斷地約同事們到醫院討論,病房變成了會議室,在兩次治療中的空隙,他常常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
靠着毅力,他終於改完建議書的稿子。
1986年4月2日,由鄧稼先和于敏聯合署名,寫了一份給中央的核武器發展建議書,這封建議書,被實踐證明完全正確,為後十年的核武器試驗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件大事了結,他開始幹另一件事,那就是寫那本預計80萬字的大部頭書,內容是關於原子核理論工具的羣論。
他開了一個很長的書單,讓李錦秀醫生回基地時,一本本從他的書架上挑揀出來,帶到病房裏。
但醫院有規定,桌上不準擺工作用書,放一本都不行。出於無奈,鄧稼先只好把這些資料塞進壁櫥和衣櫃裏,讓懸掛着的衣服作為防護牆。
他很細心,知道晚上8點以後,護士不怎麼進病房,這時就可以寫書了。如此偷偷摸摸,有時回想起來,他自己也忍不住發笑。
5月16日,鄧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術,清掃癌瘤侵犯的部位,但醫生的手術刀已經達不到要害之處了,意味着,他的生命正快速走向倒計時。
第二次手術以後,他疼痛得越來越厲害,汗流不止,「痛起來像用殺豬刀捅一樣。」
友人前來探望,他流着淚説:「老盧,我回不去了!」
「不會的,出了院咱們不幹活了,好好玩!」
「你看,我打止疼針,都打成蜂窩了。」説完後,他努力翻身。
最後,他握着友人的手,放聲哭着:「我死了以後,你要圍着我轉一圈。」
疼痛減輕的時候,他常常回憶起別人的長處和功勞,尤其懷念與之長期共事的犧牲者。
他對別人説:「郭永懷教授死得太早了!要是他在,我們的激光加速器一定會早幾年搞出來!錢晉死得很慘,他貢獻很大……」
他胸中還有許多抱負,一口氣説了很多計劃:「我對規範場很感興趣,想把場論的書寫出來,我還想搞計算機,我還很喜歡自由電子激光,能搞成連續可調控的激光器,非常有意思……」
但他的身體越來越差,虛弱得下牀走幾步就是一身大汗,日夜都要人陪護照顧。
一天晚上,李醫生陪牀,因為白天太累,所以晚間他睡得很死。
半夜過後,一個很重的聲音把李醫生驚醒。
他翻身爬起來,看見鄧稼先摔倒在地上,李醫生這時急得怒斥鄧稼先:「你為什麼不叫我,為什麼啊?你知道我來這裏是做什麼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