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內戰之奧威爾:一場偶爾夾雜着死亡的喜劇_風聞
根号三-根号三官方账号-2020-10-13 12:39
>>> 不自覺的歷史

1937年5月20日,畢加索在巴黎格蘭·奧古斯丁大街的公寓裏畫《格爾尼卡》,喬治·奧威爾在韋斯卡前線捱了槍子兒。
那一天黎明破曉,奧威爾在戰壕裏與等待換崗的哨兵聊天。兩人背對着東邊,倒黴蛋把腦袋探出了胸牆,他的頭部輪廓在朝陽的映襯下清晰地顯露出來。突然,一聲巨響和一道光亮籠罩了他。奧威爾感覺自己猶如被一道閃電擊中,渾身麻木,頭暈目眩,而後,膝蓋一軟,仰面跌倒,就像《格爾尼卡》畫面底部手握斷劍的士兵。
奧威爾嘴裏吐着血沫,發不出聲,但意識尚存。當眾人手忙腳亂地把他抬上擔架時,他迷迷糊糊地聽身旁的西班牙人説,在喉嚨,子彈穿透了他的脖子。
幸運的是,奧威爾沒死。子彈穿透了他的脖子,但放過了他的頸動脈,子彈和動脈之間的距離不到一毫米。在救治他的醫生看來,這位傷兵是以被子彈打穿脖子而不死來證明老天的仁慈。槍傷給奧威爾造成的後遺症是,短時期內一側聲帶受損和右手食指麻木。6月20日,奧威爾回到巴塞羅那。三天後,他拿着英領館的旅行文件,告別了西班牙,也告別了西班牙內戰。
過去六個月,是一段夢想破滅的旅程。
六個月前,奧威爾準備奔赴西班牙時,有着完全不一樣的心氣。那時,他同第一任妻子艾琳剛剛結婚,在赫特福德郡鄉村過着簡樸但尚算安穩的生活,紀實作品《通往威岡碼頭之路》的寫作也已經接近尾聲。對於終身受結核病困擾的奧威爾來説,如果沒有佛朗哥,當務之急是要一個健康的孩子。
可是西班牙內戰爆發,讓他有了赴湯蹈火的衝動。奧威爾想去西班牙,但他不想做煞有介事的觀察者或浮光掠影的漫遊者,幾周之後拍拍屁股走人。他真想去打仗。樸素的動機,令奧威爾比之詩人奧登之流,有了更惹眼的男子漢氣概。不過所謂男子漢氣概,在奧威爾的朋友、作家亨利·米勒看來,純屬愚蠢的、莽夫式的理想主義。
莽夫最初去找英共總書記哈里·波利特,此人控制着國際縱隊裏的英國志願者。但波利特認為他政治不可靠,他的《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有對左派的不敬之詞,遂拒絕了他。莽夫轉而求助英國獨立工黨,獨立工黨把他派發給了西班牙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馬統工黨)。奧威爾成了馬統工黨下屬民兵組織的一名英籍志願者,被編入列寧師,花名冊上寫着:雜貨商埃裏克·布萊爾,33歲。埃裏克·布萊爾是他真實的名字,開雜貨鋪是他正經的營生。
奧威爾於1936年聖誕節抵達巴塞羅那,帶着亨利·米勒送他的皮夾克和僅夠應付飯館跑堂的加泰羅尼亞語。這是一座無政府主義者扮演上帝的城市,看起來既令人吃驚,又無法抗拒。所有的建築都控制在無政府主義者手中,屋頂上都插着紅旗或紅黑雙色旗,牆面上的塗鴉是錘子和鐮刀。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每一座教堂都遭到了破壞,神像都被焚燬。唯一倖存下來的是神聖家族教堂,因為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它“極具藝術價值”。
在巴塞羅那,有一種瞬間進入平等和自由時代的幻覺。人們嘗試着表現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資本主義機器上一個小小的齒輪。每個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藍外套,或不同樣式的民兵制服。服務生的臉上沒有卑微,他們大膽直視着客人的臉,禮節性套話消失了,“你”代替了“您”、“同志”代替了“先生”。所有的店鋪均被收歸集體所有,而妓女被逼娼為良。
因戰爭而導致的物資匱乏和食物短缺,也始終困擾着巴塞羅那。未來的西德總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利·勃蘭特比奧威爾晚45天來到巴塞羅那,他當時的身份是一家北歐報紙的戰地記者。勃蘭特用一種調侃的語調評價眼前的亢奮與貧乏:“你很快就會習慣幾乎沒有東西可吃,拿紅葡萄酒聊以充飢,頂多吃一些橄欖。”

勃蘭特對巴塞羅那所聞所見有感而發時,奧威爾已經離開。奧威爾只在巴塞羅那待了七天,便被派往阿拉貢。在開往阿拉貢的列車上,奧威爾吃着肥皂味的香腸,喝着紅葡萄酒。兩人唯一一次同時出現在巴塞羅那,在三個半月後,準確講是1937年4月26日至5月10日,奧威爾回來休假。短短半個月,他們共同見證了西班牙“內戰中的內戰”——勃蘭特的定義。然而,勃蘭特並不認識英籍志願兵埃裏克·布萊爾,奧威爾對23歲的德國社民黨黨員勃蘭特也一無所知。
在阿拉貢的奧威爾,領略了西班牙人尤其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另一面。他們對很多事情都很在行,唯獨打仗例外。他們的極端低效和反強迫症人格,讓奧威爾懷疑人生。有一位無政府主義者甚至詛咒交通信號燈,因為它干涉了他的駕駛自由。
馬統工黨的民兵組織,是無政府主義軍事風格的集大成者。他們戰訓不足、裝備更不足,即使有也是既老又舊,一戰時的武器已屬上品,絕大多數士兵用的是1890年生產的毛瑟步槍,配發的手榴彈由於導火索不可靠,往往尚未出手就已爆炸。使用劣質武器的,主要是一羣十五六歲的孩子。烏合之眾的戰術,是低配版的塹壕戰。他們蜷縮在初春的戰壕裏,忍受着寒冷、飢餓、睏倦和零星的槍聲,身邊竄來竄去的老鼠比敵人更令人心煩意亂。對於交戰雙方而言,推進戰線幾無可能,拉鋸是常態。畢竟,佛朗哥叛軍也面臨着相同問題:武器和彈藥不足。更何況,叛軍也是由多血質的西班牙人組成。
奧威爾將阿拉貢的經歷稱為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他招供:“從1月到3月底,除了特魯埃爾以外,那裏基本上沒有發生什麼戰事,或者説只發生過幾次很小的衝突。3月,在韋斯卡周圍發生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戰鬥,我自己只在戰鬥中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奧威爾的戰友、比利時人喬治·柯普則説,這不是戰爭,只是一場偶爾夾雜着死亡的喜劇。

蘇聯作家、未經總編批准便擅自前往西班牙的《消息報》記者伊利亞·愛倫堡,有幸成為喜劇的目擊者。1936至1937年,他多次出沒於阿拉貢地區。1937年3月,共和派部隊圍攻韋斯卡時,愛倫堡也在前線。很巧,他採訪的部隊正是奧威爾所屬的列寧師。無法確認愛倫堡是否在前線見過一位上穿黃色皮夾克、下套燈芯絨馬褲、頭戴黑褐色鋼盔、扛着老式德國步槍的高個子英國人。反正,在他給《消息報》發回的幾十篇戰地報道中對奧威爾未着一字。奧威爾也未在回憶中提及愛倫堡。兩人同在前線,互不知曉。但愛倫堡的報道卻佐證了戰事乏善可陳,他寫道:韋斯卡戰役很難稱得上是一場像樣的戰鬥。給愛倫堡留下難以磨滅印象的,是阿拉貢地區光禿禿的山坡和火紅色的岩石。
也許是為了證明自己可有可無,1937年3月底,奧威爾藉手部傷口清創手術的機會離開了阿拉貢,4月底他回到巴塞羅那休假。事實上,奧威爾有着更大的抱負或者説幻想,他想去馬德里投奔國際縱隊,打更帶勁兒的仗。這是奧威爾第二次動加入國際縱隊的念頭,第一次他在英共總書記哈里·波利特那兒碰了壁,第二次他連碰壁的機會都沒有。對於這位當了祖傳銀器來為馬統工黨戰鬥的英國人,莫斯科給出了差評。在莫斯科眼裏,馬統工黨等於託派,等於第五縱隊。眾所周知,莫斯科是國際縱隊的老大哥,也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老大哥。
一廂情願的奧威爾,自然不知道遠在莫斯科的老大哥正注視着他的,他也不知道共和派內部是何等派別林立。共和派內部的矛盾,甚至大過共和派與佛朗哥之間的矛盾,而反對佛朗哥原本是把各個派別勉強捏合在一起的虛擬理由。
好在現實教育了莽夫,讓他迅速成熟起來,變得清醒而冷峻。回到巴塞羅那,奧威爾第一眼就發現了此處的變化:革命氣氛消失了,至少高潮已經退去。民兵制服和藍色工作服已經不見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裁縫精心縫製的時髦夏裝。大腹便便的男人、搔首弄姿的女人、豪華轎車,比比皆是。賓館裏,服務生又穿上了上漿的襯衫,一起回來的是阿諛奉承和小費。
西班牙共產黨控制的國民警衞隊,代表政府收繳民兵槍支、整編民兵武裝。衝突在所難免。
1937年5月3日,戰鬥爆發。觸發點是巴塞羅那電話局,這裏原來由無政府主義者控制,國民警衞隊對電話局的管理不滿,企圖奪取,無政府主義者予以拒絕並開火。戰鬥隨即蔓延到整個城市,街壘戰在城市各個角落展開,巴塞羅那陷入癱瘓。
屬於無政府主義派別的馬統工黨也捲入了戰鬥,儘管他們人數很少,只有60杆步槍。奧威爾於戰鬥爆發次日趕到馬統工黨總部,他被派往總部正對面的波利羅馬電影院執勤。此後三天三夜,他一直蹲守在波利羅馬電影院的屋頂塔樓。透過塔樓小小的窗户,他看到了周邊數英里的景觀:細瘦高聳的樓房,耀眼的彩色瓦片、奇妙而又彎曲的屋頂,向東望去是波光粼粼的淡藍色海面,這是奧威爾來到西班牙後第一次看到大海。
奧威爾在波利羅馬電影院塔樓眺望地中海的那幾天,勃蘭特正在馬統工黨總部收集採訪素材。兩人如此之近,近到可以隔着街道相互喊話。但時空的交集,只有軌跡意義,卻沒有任何社交價值,他們並不自知。
對於“內戰中的內戰”,勃蘭特給出了充滿調和意味的解釋:馬統工黨在一系列問題上的立場都是錯誤的,西班牙共產黨對之鎮壓則顯得用力過猛。勃蘭特的説辭暗合了某種現實的政治邏輯:無政府主義者會成為所有政府的敵人,哪怕執政者是他們曾經的盟友。
後來公佈的檔案表明,勃蘭特抱有太多的善意。早在1936年12月,也就是奧威爾來到西班牙之前,斯大林就已對西班牙共產黨下達了剿滅馬統工黨的密令,“內戰中的內戰”無非在執行這道密令。為此付出的代價是400人喪生、1000人受傷。
血腥一週後,瓦倫西亞的共和國政府派來了人民軍。巴塞羅那的秩序恢復,西班牙共產黨和國民警衞隊成了新秩序的裁判。街壘被清除、武器被收繳、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被扯了下來、他們的報紙被查封或受到嚴格審查。一幅顯然是巴塞羅那地方政府授意的海報貼遍了大街小巷,海報上一位代表馬統工黨的漫畫人物,被撕開畫有錘子和鐮刀的假面具,露出了帶有納粹卐標記的醜陋嘴臉。坐實了,這個不情願地被打上託派烙印的左翼小黨將承擔所有罪責。
在一年後出版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裏,奧威爾不無痛心地寫道:戰鬥結束,氣氛卻變得更加沉重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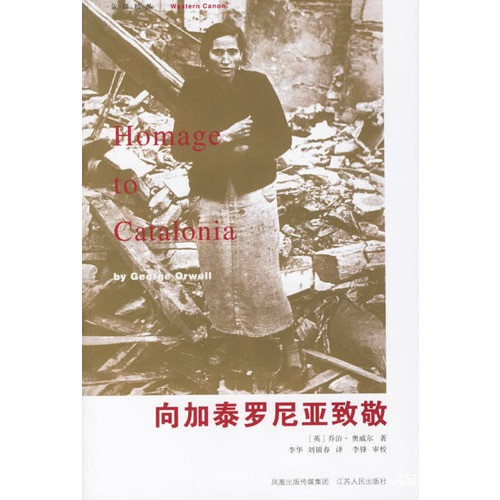
人們不可能像以往那樣,在保留不同意見的前提下跟與你政治立場相左的人舉杯共飲。打倒法西斯、反對佛朗哥,也不是求同存異的理由,共和派的統一戰線名存實亡,西班牙共產黨的號令被定於一尊。秘密警察開始登記、追查、逮捕“暴亂”的策劃者、參與者和“納粹派遣的間諜”,收網有條不紊。
當然,奧威爾在局勢明朗前就離開了巴塞羅那。5月10日,他重回韋斯卡前線。與這位“託派分子”兼“革命叛徒”並肩作戰的,就有西班牙共產黨的戰士。前線是另一個世界,戰壕裏的士兵無暇顧及也無心過問戰壕後方哪怕一千米發生了些什麼。
稍顯遺憾,令人心醉的袍澤之誼僅維繫了10天,5月20日奧威爾中彈受傷。
6月20日,他再度回到巴塞羅那,馬統工黨已成非法組織。當天,他的比利時籍戰友喬治·柯普被秘密警察逮捕;次日,傳來了馬統工黨領袖安德烈斯·寧被處決的消息,行刑者是蘇聯內務部人員……
西班牙再也容不下奧威爾了,更確切地説,奧威爾再也無法忍受西班牙所發生的一切了。在這個被理想火焰點燃的遙遠國度,高個子英國佬不慎窺視到了光芒下的陰影。誠然,他來的時候也如飛蛾撲火般義無反顧。他涉足的地區也僅限於加泰羅尼亞和阿拉貢,甚至沒能前往戰鬥激烈得多的馬德里。但擁有敏鋭直覺的他,還是從西班牙內戰的一個局部洞悉了更具普遍意義的東西,譬如根植於人性的殘暴和虛偽。人性中固有的缺陷,均勻散佈於內戰的對立雙方、各條戰壕。無論是佛朗哥派還是共和派,都有可能失手將內心之惡放出囚籠。有時,天真和單純是可笑的,因為善意也會鋪就通往地獄的路。有時,理想主義以及與之伴生的各種高蹈話語,會讓人失重、叫人沮喪。奧威爾預見到了某種觀念或者立場膨脹到極致的可怕後果,那種專橫獨斷、排斥異己、不擇手段,已與極權主義無異,它終將反噬個人自由。
逃離西班牙的奧威爾,也逃離了從頭至尾都充斥着的謊言和荒唐。此時的他,已經是人們熟悉的、日後寫下《動物莊園》和《1984》的奧威爾,一個因滿嘴政治學怪話而令人着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