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情於大地的人們——寫在《拍攝抗美援朝題材影片應注意這些問題》後面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020-10-25 08:26
寫文章最大的幸運,就是碰到能讀懂並且真心認同你的人。
我那篇“拍攝抗美援朝影片要注意……”,是我在觀察者網對別人的一篇《金剛川》影評的回覆。
沒想到這篇回覆引起的關注和點贊,使得它被小編單獨摘出來成了一篇主帖,題為《拍攝抗美援朝影片要注意這些問題!》
有幾位網友是這樣評論我這篇文字的:
David:直擊要害,寫得真好!
星際旅人:你説你這個為什麼不是第一高贊呢?完全説到點子上了,就是這麼回事!
而網友leroichat則引用了文中的一段話“而八連上去前,師政委因為炮彈不足而憂心忡忡的一句“怎麼得了啊,我們和敵人比賽起鋼鐵來了!”則道出了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的辛酸與無奈。當向八連運送給養的後勤戰士在敵人炮火中一批批倒下,張連長在電話中懇求師長(注意:此處記憶有誤,據網友逍遙居士“提醒,應為通過炊事員老王給師長帶的口信。感謝逍遙居士)不要再送東西了,師長堅決地説:“要送!要送!一定要送!要多送蘿蔔!”這才是真正的戰友情。”
並評論道:
“我居然光看這一段都要淚目了。果然這些故事導演只要把過程原汁原味還原就足以打動很多人了,瞎編亂造一些場面來強行煽情反而讓人感覺吃了一隻蒼蠅。”

而我的好朋友W博士,則在朋友圈裏轉發了這篇文章,並評論道:
“今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估計(肯定)又有一些以之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出現了。我的好朋友驅逐艦博士為此提了一些建議,我完全贊同!特鄭重推薦大家一閲!
驅逐艦博士的建議毋寧説深刻而全面地指出了我們目前大部分所謂“主旋律”影視作品的通病。特別是他説的“反思人性”的問題。—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我們的導演們喜歡起“深刻”來了,結果事與願違,不但沒“深刻”,反而費解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順便説一下,驅逐艦博士是哲學博士,畢業於名校名師,英語極好,研究的是以《人性論》為代表作而聞名於世的大哲學家休謨。”
這些鼓勵讓我很欣慰。
我當然知道這不是因為我寫得多好,而是因為我以一種直截了當的方式,説出了很多和我一樣的觀眾要講的話,或者説它引起了不少人的進一步思考。
既然這樣,我就把它作成一篇日誌,以備感興趣的朋友閲覽和指教吧。
我是一名教師,希望它也能引起我的學生的思考。
尤其是W兄所説的“反思人性”問題,我在文中是這樣寫的:
“比如電視劇《三八線》表現了被美國飛機炸成廢墟屍橫遍地的朝鮮村莊,結果去村裏借糧的志願軍反而把自己的乾糧留給了倖存的朝鮮老鄉——要再強調一遍,這是為了譴責侵略者,表現我志願軍人民軍隊的本色和抗美援朝的正義性,而決不是為了無病呻吟地“反戰”、“反思人性”(西方的“反戰片”是因為西方確實發動了很多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又不便於明確承認,只好籠統地譴責戰爭,説凡戰爭都不好,參戰雙方都不人道,這樣反而藉着“反戰”而推卸和掩蓋了真正的戰爭責任:反正戰爭都是這樣,何必單單怪我呢?這就像你譴責某人打人,他説反正你也還手打了我,所以誰也別説誰)。”
W兄認為寫得很好,其實聽過我課的同學就會知道,這就是我在課堂上引用德國倫理學家鮑爾生的話講過的一個觀點:
“普遍的錯誤宣告自我無罪。掩蓋你的自私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宣稱所有人都是自私的,人性是自私的;掩蓋你的侵略戰爭罪責的最好辦法,就是宣稱所有戰爭都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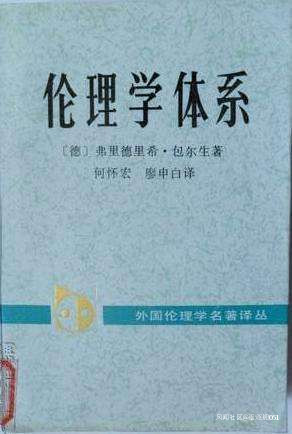
西方拍了那麼多“反思人性”、“反戰”的影片,但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干涉別國的戰爭和戰爭威脅一直沒有停止過,反而愈演愈烈,其奧秘正在這裏,就在於這些影片其實告訴你:
“人性”就是如此啊!難道你能夠反對或改變“人性”嗎?戰爭就是如此啊,你所謂的反侵略戰爭也是要血肉橫飛死傷慘重的啊,哪有什麼正義非正義呢?!
——這種觀點,我們通常叫做“善惡不辨,是非不分”,但在W兄所批評的那些人看來,這就叫“深刻”,叫“反思”,叫“人道主義”。

既然如此,侵略者當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把“符合人性”的戰爭打下去;而被侵略者如果用武力來反抗呢?那對不起,你這也是戰爭,也是“人性的惡”,與侵略者不分軒輊。
當然,如果公然這樣講出來,沒有幾個正常人會接受。
但如果換一種説法呢?
比如:
“哎呀,八路軍當年的游擊戰是軍民不分,拿老百姓當炮灰呀!”
“哎呀,什麼解放戰爭,當年國共內戰是中國人打中國人,苦的都是老百姓呀!”
“哎呀,當年美國打朝鮮,並沒有意圖要打中國,抗美援朝我們是白白犧牲了幾十萬人呀!”
這些論調大家是不是有點耳熟呢?是不是覺得“好像也有那麼幾分道理”了呢?
作為思政專業同學,有沒有想過怎麼反駁這些錯誤思潮呢?還是束手無策,任其氾濫,任其影響你的同學、學生和周圍的人呢?
其實,敵後抗日游擊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都是人民羣眾熱情參與的反侵略或反剝削壓迫的正義的革命戰爭。發動羣眾是贏得戰爭的前提,而這不是讓羣眾去送死,恰恰相反,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教育羣眾,組織羣眾,武裝羣眾,訓練羣眾,正是對羣眾利益的根本保障,因為這正是敵人所最為懼怕的東西——這才是真正深刻的認識,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就是習總書記引用毛主席的話説的,要用帝國主義聽得懂的語言和他們説話,要讓帝國主義懂得“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尤其是抗美援朝戰爭,不管美國當時有沒有打算立即進攻中國,讓它壓到鴨綠江邊,就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這就好像一隻老虎,你不能説“它暫時好像不想吃人”就任它盤踞在你身邊而不把它趕走或鎖進籠子裏——這個道理,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同志當年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老虎總是要吃人的,什麼時候吃,取決於它的胃口。讓美帝國主義壓到中朝邊界,它要發動對華戰爭,隨時可以找到藉口,向它讓步是不行的。”
文藝界的很多場合都是小資當道,這些人想不清楚或不願意想清楚這些問題。而我們思政專業的同學則一定要有正確的立場和科學的方法來認識這些問題,並堅持不懈地進行宣傳引導,才不負自己的責任。
剛才提到的點評和推薦我的文章的W博士,是我在H大讀博時結識的同窗好友,現在是某知名大學哲學教授。他思想學問之深湛自不待言,而且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給對我那篇文章的評論中原來是這樣結尾的:
“順便説一下,驅逐艦博士是哲學博士,畢業於名校名師,英語極好,研究的是以《人性論》為代表作而聞名於世的大哲學家休謨”。
我轉發時覺得這些評語我實在愧不敢當,就刪掉了這一段。
誰知W兄見了,又點評道:
“可以把最後一段補上啊。那可不是恭維啊。言下之意是你是研究《人性論》的專家,為何卻説不要隨便“反思人性”呢?這是值得思考的。”
卻原來W兄並不是隨便寫這話誇我,而是把我當作了一個論據——如此微言大義,不是他親自提點,我還真是駑鈍未解呢。
於是我只能將W兄的原話一字不少地補到日誌裏。
W兄又對拙文繼續評曰:
“其實我覺得你説的每一條建議都很好,本想一一點評,只是時間緊張,只寫了關於“人性”的那條。
比如第一條(志願軍戰士不要有匪氣、痞氣和哥們兒義氣)我就完全贊同。道理很簡單,因為那樣做不符合歷史事實。須知我們的志願軍戰士大多是忠厚朴實的從農村出來的人,他們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悖矣。”平時連開個玩笑都害怕別人説“嬉皮笑臉”,哪裏還有這些“氣”呢?而影視作品中之所以出現這“三氣”,究其原因之一,恐怕是受美國影視作品的影響,也就是你説的戴着“唯洋是從的帽子”緣故。”
不知怎的,W兄這話讓我想起了山東作家王潤滋(我初中時學過他的《賣蟹》一文)。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文學界、學術界一派聲討中國農民的“落後”、“保守”、“狹隘”、“自私”,耽誤了中國變成西方那樣的“文明社會”的聲浪中,出身膠東農村的王潤滋同志卻寫出了大批作品歌頌中國農民的革命、勞動、奮鬥生活,歌頌他們的美德,反思那些把農民和農民傳統美德説得一無是處的觀點。——我曾經介紹過其中的一篇《內當家》。
王潤滋同志説:
“我們為什麼老是要罵農民呢?”
“是祖母與母親給予我作家的情感與良知。祖母是一箇舊農民的典型,狹隘、落後,性格也古怪。可她有一顆愛我的善良的心。”
“中國農民經過幾千年的長途跋涉才走到今天,十分不易。他們,那麼久遠,那麼貧窮,那麼悲愴,卻奇蹟般地沒有墮落,沒有潦倒,沒有毀滅,而是邁着沉重不屈的腳步,走過昨天,來到今天,還要趕到明天去。”
“對於這些人,一個共產黨員作家不應該關注他們的命運麼?不應該對他們寄予深深的同情麼?不應該替他們發幾句心中的呼聲麼?即使99%的農民都富了,還有百分之一在受苦,我們的文學也應該關注他們,我的同情永遠都在生活底層的受苦人。”
我不是農民,但我是共產黨員,我能讀出這是一位農村來的同志發自肺腑的話。這些話説得並不是疾言厲色,寒光凜凜,而是透着一種中國農民特有的温煦和隱忍,但是它頂天立地,無可辯駁,就像茅盾歌頌的象徵着北方農民的白楊樹一樣,默默挺立在那裏,就能反襯出某些數典忘祖絕根忘本的人的卑微、渺小。
我還記得,和王潤滋同事的一位膠東作家,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尋找二嫚》。
“嫚”是山東人民對農村小丫頭的親切稱呼。
這位作家寫的是文革期間,他們這些作家下鄉參加社教運動並體驗生活,住在二嫚家裏。二嫚是根正苗紅的貧農,也是村裏的團支部委員,可她從來也不歧視這些“老九”,她不卑不亢,幫助他們勞動,為他們解決生活困難,也向他們學習文化。大家都特別喜歡這個正派、俊俏、熱情、活潑的農村姑娘。

這個作家説,文革結束後,他逐漸淡忘了這段生活,而寫了一些為所謂在新中國“受迫害”的知識分子鳴不平的作品,也得到了一些名聲。 但是他説,現在回想起來,寫這些作品只不過是根據道聽途説而寫的趕時髦的東西,而當時在鄉下寫的那些表現二嫚和身邊那些農民的勞動與生活的作品,才是真實的,發自內心的,只不過它們當時不合某些掌握了話語權的人的口味罷了。
他説:
這些年的社會現實讓我明白了很多。我再也不寫那種為所謂“右派”鳴冤叫屈的作品了,我要寫工人,寫農民,也寫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的勞動人民進行的偉大斗爭。
他説:
我特別想找到二嫚,想知道當年的二嫚現在在哪兒。但是,找不到又怎樣呢?不知道又有什麼要緊呢?我以後的所有作品,都屬於二嫚和她的鄉親們。
我在W兄的這些話裏,以及他和我交往的一言一行中,能夠看到同樣的深情,同樣的品質:
對農民的熱愛;
對土地的忠誠;
對家鄉的眷戀;
還有對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魂魄的堅守。
我和人交往,從來不在乎他的頭銜怎麼樣,甚至也不是太看重他的學識怎麼樣(有學識當然好),而是看他的人品是不是純正,言行是不是端方厚道,以及是不是像一株掛滿稻穗的稻苗一樣,對我們的大地,我們的故鄉,對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一往情深。
W兄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驕傲自己有這樣的朋友。
我也希望,我的學生們,不管以後學識如何,境遇怎樣,都成為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