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離你有多遠?_風聞
Science_北京-不惧过往,不畏将来!2020-10-29 1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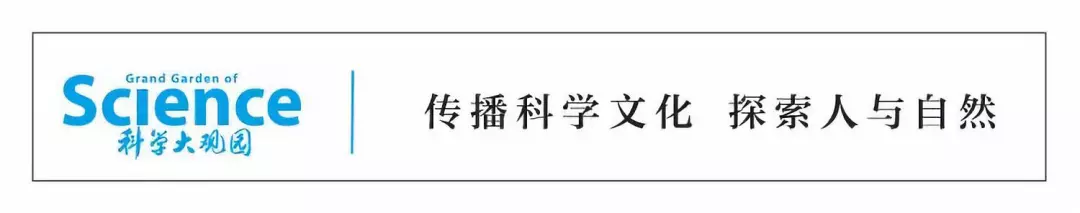
比起日常生活中真正的高風險隱患,人類往往覺得一些陌生的低概率事件更可怕。他們因“遠慮”而精神緊張,對“近憂”卻後知後覺。這種倒錯説來荒謬,但卻可以解釋。
要是讓你比較以下場景,你認為哪一樣更危險?
是開車帶着父母兜風,還是在鯊魚環繞的水中游泳?

是在毒蛇出沒的密林中散步,還是踏上矮凳?

是每週搭乘一次飛機,還是感染流感?

賭一把:你肯定會選鯊魚、毒蛇和飛機……説中了,對吧?
這其實不稀奇,所有人都有着同樣的恐懼心理,而且其他那些選項看起來一點也不嚇人。但是,統計數據卻道出了截然相反的事實真相:我們從矮凳上滑下摔死的概率是被毒蛇咬死的6倍,而死於流感或肺炎的概率是空難的1730倍,被鯊魚吃掉的概率則連交通事故的1/7000都不到。
要知道每天全球有8萬架次航班在安全飛行;縱觀2011年,全球記錄在案的嚴重事故(墜機、劫機、失火、迫降……)僅有107起,且超過半數沒有人員傷亡。儘管如此,機艙中總會有大量憂心忡忡的乘客。難道他們都是瘋子和蠢貨嗎?顯然,這個問題非常複雜。
為了更好地理解人類的心理機制,我們不能忘記,人類的大腦經過數百萬年的進化和發展,能控制機體對大自然的各種危險做出最迅速的反應。原始人之所以能從掠食動物的獠牙、利爪和毒液中逃脱,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深藏在我們大腦中一個器官——杏仁核。它相當於一個生物警鈴,能讓我們在瞬間做好逃跑或格鬥的準備。
無法控制的生理反應
19世紀,達爾文想弄清人的理智能否控制這種恐懼導致的本能反應。
為此,他把腦袋湊到一個裝有兇狠好鬥的蝰蛇的玻璃缸跟前,厚厚的玻璃能有效保護他不受任何侵害。我們的科學家誓言在毒物朝他撲過來時絕不退避分毫。
但事後,他在實驗記錄中寫道:“蝰蛇猛然撞向玻璃的瞬間,我心中的堅強信念被一掃而光,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往後跳了出去。在這樣一種沒有任何知識和經驗儲備的危險面前,我的意願和理智完全無法對抗自己的生理反應。”這很正常,因為這些用於自保的生理反射深深植根於我們體內。
相反,我們的大腦在評估這個技術世界的危險時略顯遲鈍。以放射性物質為例,它們沒有氣味,其輻射肉眼看不見,我們就算懵懵懂懂地抓着放射物,立時三刻也不會有任何不適,怎麼會把它當成危險呢?
確實,20世紀初,人們還認為微量放射元素對人體有益,甚至還用放射性物質製造美容和護理產品。
放射性牙膏
還有,手機、無線網絡及微波爐的電磁輻射,它們危不危險?我們的感官無法察覺這些輻射,因此必須藉助別的方法來評估其危害程度。
計算危險的公式
理論上,這可以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公式:危險 = 事件發生的概率 × 危險程度。比如,得胃腸炎是概率很高的事,但它很少致人死亡,因此胃腸炎屬於低危概率事件。
又如感染H5N1病毒,這算是死亡率高的高危事件(60%的感染者都會死亡),但感染概率很低(2003年全球70億人只有571人感染)。
問題是在實際生活中,要收集這些數據來計算危險程度,實在是一件無比浩瀚的任務。
看看這個問題:“噴灑過殺蟲劑的蔬菜有害健康嗎?”
為了正確評估蔬菜受污染的概率,和因此損害健康的概率,我們得列出一串超級長的問題,就像一本厚厚的年鑑。農藥會滲透到蔬菜中去還是殘留在表面?哪些蔬菜會被污染?有多少農民使用農藥?頻率有多高?附近的菜市場裏有這樣的蔬菜嗎?這些農藥有哪些潛在危害?超過多少劑量會出危險?你能想象日常生活中,事無鉅細我們都要推理論證,糾結再三嗎?
“這是不可能的!”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心理學講師布魯諾·肖萬(Bruno Chauvin)指出,“我們的大腦無法獲取準確評估所需的所有有效信息。”事實上,看到“噴灑過殺蟲劑的蔬菜是否有害健康”這個問題,我們的頭腦在幾秒鐘內就會彈出各種想法:“天殺的,我再也不吃這鬼蔬菜了”,“關我屁事,我只吃炸薯條”或“只要洗乾淨了,就沒什麼危險”。
我們的大腦是如何迅速地做出這些回應的?“靠近似估計。它通過各種認知捷徑並根據情緒體驗來處理相關信息。”風險教育專家大衞·羅佩克(David Ropeik)如此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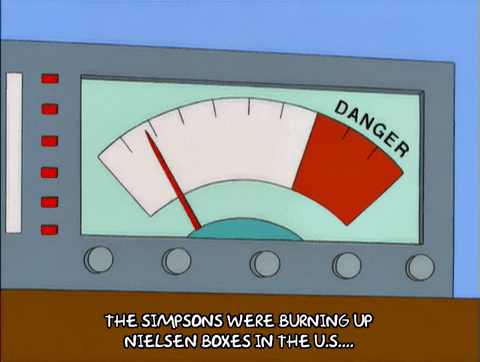
説穿了,我們以一種極為簡化的方式認知真實的世界。比如,如果讓你想象一位高水平的運動員,你腦子裏第一時間浮現的是什麼畫面?毫無疑問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肌肉男。但是,優秀的運動員的隊伍中也有大腹便便的相撲手或身高1.6米的賽馬騎師呀!
同樣,我們也很難做到在分析中排除情感因素。例如,“化學”和“核能”這樣的詞多數時間在我們心目中呈現出與污染、中毒、癌症或災難有關聯的負面形象;相反,“自然”這個詞則讓人聯想到舒適、健康等種種積極的意象。

所以,人們都傾向於認為“天然”物質要優於實驗室裏的人造產品,偏偏忘了鬼筆鵝膏菌、毒芹或蛇毒中的毒素都是100%的天然物質,它們都是絕對致命的。人們還傾向於疑懼新事物:“外來”病毒看起來總是比本地常見的“季節性”病毒更可怕,哪怕前者造成的死亡數量少於後者。
大腦還習慣於這樣一種簡化方式:**為了確定某事物的危險性,我們會傾向於祭出頭腦中最易於找到的意象。**比如,一聽到“鯊魚”這個詞,我們馬上就會聯想到長滿尖牙的大口和噴湧的鮮血,對危險的感知形象而具體。
相反,除了醫生,誰也無法賦予慢性肝病具體的意象,而它們的致死人數比鯊魚多得多!同樣邏輯下,相對於較為常見但受害人數積少成多的事故(如車禍),我們更關注特殊事件(如墜機)。
電影拿我們本能的恐懼反應做文章: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角落,某種爬行動物或毛茸茸的怪獸出現在一個倒黴蛋身邊,把他撕成碎片……恐怖片的導演使用大量此類橋段,只為把我們嚇得一驚一乍。
媒體在這方面更是推波助瀾,它們需要震撼性的消息,所以我們高估相關事件的危險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確實是我們社會中的一個悖論。”布魯諾·肖萬饒有興趣地總結道,“從來沒有哪個時代的人像現在這樣,如此煞費苦心為自己營造安全的生活(改進醫療技術、提高交通工具的安全性……)。人人都越來越擔心自己可能遭受危險。”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使用同樣的認知捷徑,那麼我們的思想不會同化嗎?事實並非如此**。面對複雜的世界,大腦的應對之策也取決於我們瞭解的相關信息、個人的性格,以及其他許多因素。**
每人對危險的感知都不同
危險體驗(被動物咬傷、出車禍……)會改變我們對某種風險的認知。年齡也是關鍵因素:年長的人會更信任藥物的療效,而大部分年輕人從事危險的體育運動(衝浪、高山速降)時無所畏懼。
因為,對於自己選擇去做的事情(如加入某跳傘俱樂部前去跳傘),我們對其危險性的評估往往低於在無奈的狀態下做同樣的事(從一架即將墜毀的飛機上跳傘)。
同樣,對危險的擔憂與我們自認為對事件的控制能力成反比:汽車造成的恐懼遠低於飛機,因為我們把生命完全交託給了飛行員。最後還要考慮到風險所能帶來的益處。
不妨設想這樣一個問題:“電子遊戲會危害精神健康嗎?”如果你是個遊戲迷,你會毫不猶豫地去冒這個險,因為玩遊戲是如此愉快。相反,一個上了年紀、從未碰過遊戲機的人的看法肯定與你不太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