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突破了國度、階級和政治界線的人類精神的豐碑_風聞
西方朔-2020-11-13 14:55
 能睡文史狗/軍迷/文旅老鳥/馬拉松兔550 人贊同了該文章長征是什麼
能睡文史狗/軍迷/文旅老鳥/馬拉松兔550 人贊同了該文章長征是什麼
先看看西方人的看法。
80年前,一位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記者,帶着他當時無法理解的關於革命與理想的問題,冒着生命危險,進入傳言中“紅色恐怖的”陝甘寧邊區,他是在紅色根據地進行採訪的第一個西方新聞記者。在這裏,他採訪了形形色色的人,從他們的口中,他第一次知道長征這件事情。憑藉他對中國地理的瞭解,他認為這件事近乎不可能。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采訪者的語言他的腦海匯聚,長征的事蹟越來越清晰,深深震撼了他。在冒着炮火回到北京後,他把他的採訪整理,彙編成一本書,書名是《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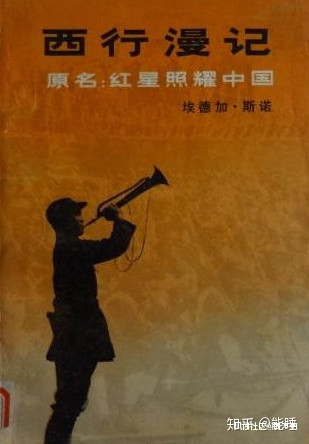 在書裏,他由衷的感嘆道:“不論你對紅軍有什麼看法,對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什麼看法(在這方面有很多辯論的餘地),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最偉大的業績之一。在亞洲,只有蒙古人曾經超過它,而在過去三個世紀中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的舉國武裝大遷移,也許除了驚人的土爾扈特部的遷徙以外,對此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帝都熱河》一書曾有記述。與此相比,漢尼拔經過阿爾卑斯山的行軍看上去像一場假日遠足。另外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比較是拿破崙從莫斯科的潰敗,但當時他的大軍已完全潰不成軍,軍心渙散。
在書裏,他由衷的感嘆道:“不論你對紅軍有什麼看法,對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什麼看法(在這方面有很多辯論的餘地),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最偉大的業績之一。在亞洲,只有蒙古人曾經超過它,而在過去三個世紀中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的舉國武裝大遷移,也許除了驚人的土爾扈特部的遷徙以外,對此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帝都熱河》一書曾有記述。與此相比,漢尼拔經過阿爾卑斯山的行軍看上去像一場假日遠足。另外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比較是拿破崙從莫斯科的潰敗,但當時他的大軍已完全潰不成軍,軍心渙散。
”紅軍的西北長征,無疑是一場戰略撤退,但不能説是潰退,因為紅軍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無損,其軍心士氣和政治意志的堅強顯然一如往昔。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麼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進軍到戰略要地西北去,無疑是他們大戰役的第二個基本原因,他們正確地預見到這個地區要對中、日、蘇的當前命運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後來的歷史證明,他們強調這個原因是完全對的。”
 他叫埃德加·斯諾。
他叫埃德加·斯諾。
1984年,一位來自斯諾同一國家的老人,帶着實現埃德加·斯諾遺願來到中國,他不顧年邁的身子,在他的同樣年邁的妻子陪同下,從江西瑞金出發,將幾十年前那波瀾壯闊的里程重走一遍。他告訴接待他的中國人:年青的時候,他深深受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的影響。不過,長征只是在文字上的,謊言還是真相,在他有生之年,他要親自把長征路走一遍,對中國人提出了他能想到的所有難題及疑問,直到弄清事實為止。 就這樣,他一路跋山涉水,從江西于都一直到陝北的延安。回國後,他按捺下激動的心情,將一路所見認真整理,寫了一本英文的書籍——《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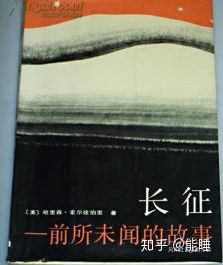 在書裏,他感慨到:可以從某種意義上開始瞭解那些為了中國革命事業而不惜犧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質。他們將從這裏開始知道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事蹟。他們僅僅從統計數值中就開始明白紅軍所作出的犧牲有多麼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萬六千名男女從江西出發,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率領的這支第一方面軍抵達陝北時只剩下大約六千人。現在,在美國,歐洲和世界各地,人們對於幾十年前由一支規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國男女組成的隊伍所進行的一次軍事行動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如果中國讀者對此感到費解,我只能重複埃德加-斯諾就這場“激動人心的遠征”説過的話──-它過去是激動人心的,現在它仍會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欽佩和激情。我想它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於世。
在書裏,他感慨到:可以從某種意義上開始瞭解那些為了中國革命事業而不惜犧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質。他們將從這裏開始知道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事蹟。他們僅僅從統計數值中就開始明白紅軍所作出的犧牲有多麼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萬六千名男女從江西出發,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率領的這支第一方面軍抵達陝北時只剩下大約六千人。現在,在美國,歐洲和世界各地,人們對於幾十年前由一支規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國男女組成的隊伍所進行的一次軍事行動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如果中國讀者對此感到費解,我只能重複埃德加-斯諾就這場“激動人心的遠征”説過的話──-它過去是激動人心的,現在它仍會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欽佩和激情。我想它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於世。
 他的名字叫哈里森·索爾茲伯裏,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的好朋友, 普利策獎、喬治·波爾克獎獲得者。
他的名字叫哈里森·索爾茲伯裏,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的好朋友, 普利策獎、喬治·波爾克獎獲得者。
1952年,大洋彼岸的美國,麥卡錫主義陰雲籠罩整個國家,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為共產主義組織的運動在美國開展。作為這個組織的核心成員,他被指認為“共諜”、“同情共產黨分子”。
面對無休止的內部安全委員會質詢,他被迫一次又一次當着議員們的面宣誓:本人以上帝之名起誓,本人從未加入任何共產黨組織,也未主動參與任何涉及共產黨的活動。
十多年後,歷經各種人身攻擊非難、限制出境的他,與歐洲中國學泰斗崔瑞德共同努力,編輯劍橋中國史,力求將中國的歷史,以西方人接受的方式告訴給西方人。
在中華民國史部分,有關長征,他寫道:“這一史詩般的逃亡,行程約6000英里,在大約一年的時間裏翻越十幾座大山,跨過了二十幾條河流。歷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環境的偉績能與之相比,歷史也不能提供一個更好的不間斷的即時行動的例子。”
 他叫費正清(不是那個愛講段子的歌手)。
他叫費正清(不是那個愛講段子的歌手)。
1995年,還是一位美國人,結合他四十多年的教學研究,以獨特的視角寫出一本代表美國新史學水平的著作——《東亞史》;在這本著作中對於長征,他有如下表述:“長征是個傳奇般的歷史事件,類似於美國曆史中的“福奇谷”(Valley Forge)。這是一個英雄們為理想獻身的時代,長征的精神激勵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他叫羅茲·墨菲 ,費正清的弟子,美國當代亞洲歷史學權威。
曾出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於一九八一年秋天宣佈,他要來中國進行一次“沿着長征路線”的跋涉。他來了,帶着他的全家走上了一九三四年中國工農紅軍走過的路。當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大渡河渡口的懸崖邊時,他被這條湍急的河流和兩岸險峻的崖壁震驚了,他被三萬多中國工農紅軍在十幾萬中央軍的追堵中渡過這條大河的壯舉震驚了。
布熱津斯基後來説:“對嶄露頭角的新中國而言,長征的意義絕不只是一部無可匹敵的英雄主義史詩,它的意義要深刻得多。它是國家統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後東西的必要因素。”長征是突破了國度、階級和政治界線的人類精神的豐碑。無論是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人,無論持有何種意識形態,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給予人類的精神財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滅的信念。
2000年,美國《時代》週刊把長征評選為一千年來影響世界的大事之一。
毛澤東説,“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説,長征是歷史記錄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超限戰》的作者喬良將軍認為“80年前那場中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大轉移,改變了他們自己,也改變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儘管當時的他們在戀戀不捨地離開自己的紅都瑞金時,並沒有哪個人確切地知道,他們將開始一次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史詩式遠征,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人人都懷揣着一個偉大夢想:改造中國。”
國外有人把長征比作《聖經》中古猶太人出埃及,比作漢尼拔揮師跨越阿爾卑斯山,比作拿破崙從莫斯科撤退,比作希臘遠征波斯後的色諾芬大撤退。但比較來比較去,他們認為這些人類的遠征都不能與中國長征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