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攻擊、當街暴揍、燒頭髮……只有90後才知道他們的存在_風聞
影探-影探官方账号-美日韩剧资深鉴赏员,电影专业老司机2020-11-18 14:17
作者| 阿飛
來源| 影探
10月2日,廣東石排鎮有點熱鬧。
在那兒,召開了全國第一個殺馬特大會。
這聚會本來是定在1號的,但當地片警説什麼也不準。
推遲了一天的結果就是,64一晚的住宿費讓很多殺馬特提前打道回府。
最後,羅福興算了算,只來了8個人——還不是他叫來的。
這八個人都不認識羅福興。
“殺馬特教父?什麼屌毛?”
同樣,這結果是紀錄片導演李一凡沒料到的。
為了這個大會,他專門準備了1萬塊錢。
結果,全沒用上。

圖源:藍字計劃
酒店標間裏,殺馬特少年擠在鏡子前,用馬克筆畫着眼線。
大家亂哄哄地瞎侃胡聊。
看着此情此景,李一凡估計也有一陣恍惚。
為了這部紀錄片,他也不知道是怎麼一步一步走到了這兒——
《殺馬特我愛你》
201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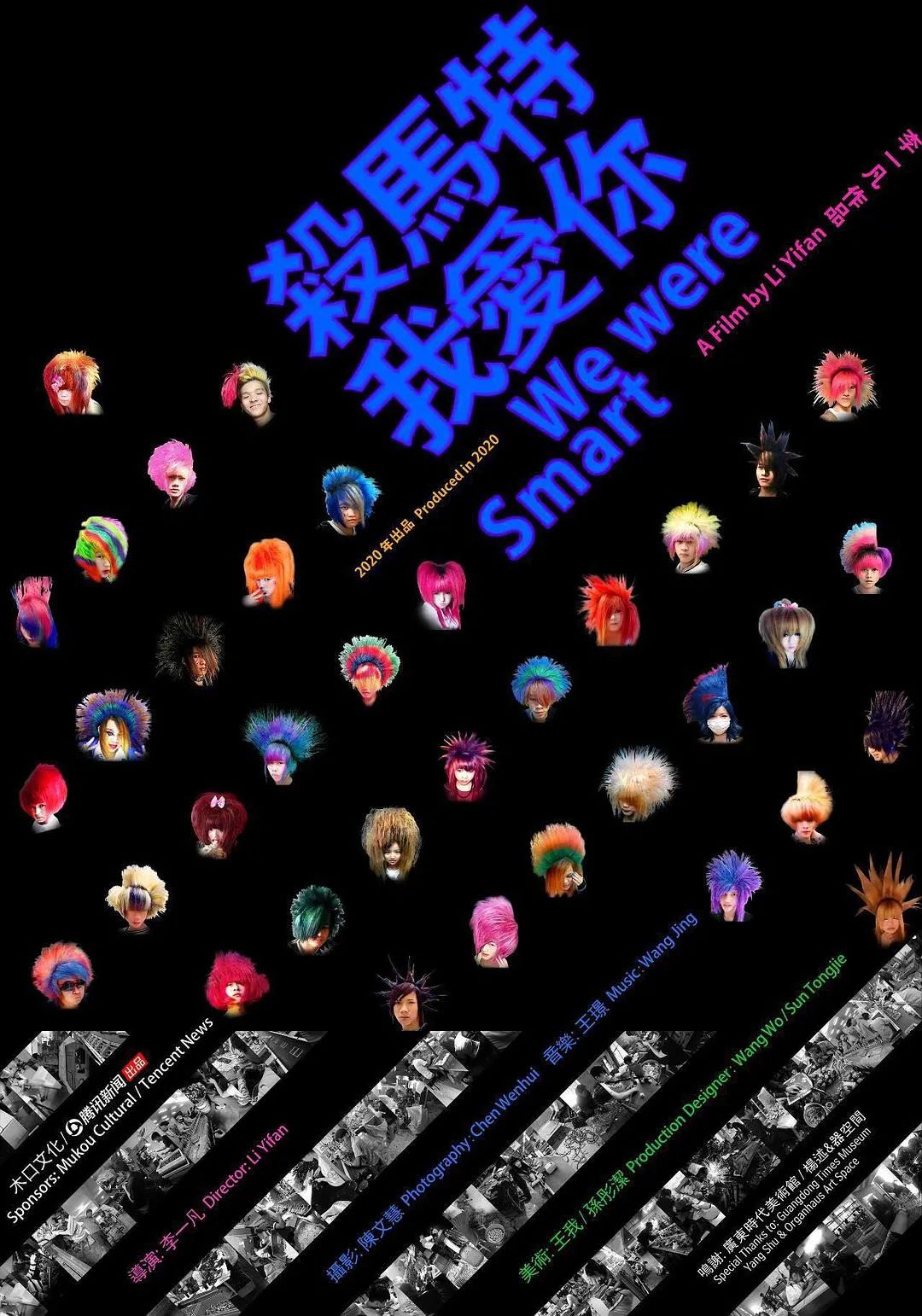
>>>工廠
2012年的時候,李一凡第一次見到殺馬特,激動壞了:
“中國有朋克了!有嬉皮士了!”

李一凡好奇殺馬特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流行文化”。
於是,他發動一切人脈,想融入殺馬特,看看那幫孩子到底在玩兒什麼。
可努力了4、5年,連殺馬特的QQ羣,他都進不了。

直到後來,朋友給他介紹了一個叫羅福興的人。
他再細一打聽,好傢伙,殺馬特教父。

李一凡立馬趕去了廣州。
和“教父”見了面,卻發現怎麼也聊不下去。
兩個人聊着聊着總會聊到一個地方——工廠。
於是,一行人去了石排鎮——殺馬特的聚集地,想看看真實的工廠到底和殺馬特有什麼關係。

李一凡(左)在鐘點房與羅福興(右)交流
圖源:一席
李一凡借這個機會,加了很多殺馬特的微信、快手。
加的人多了,連帶着社交媒體推送也變了。
越來越多的工廠信息包圍着、衝擊着李一凡。
他沒料到,中國社會階層在思想文化上的隔閡居然這麼大。

有了殺馬特們的聯繫方式,李一凡的採訪還是進行不下去。
因為,約不到人。
羅福興知道,他們都在工廠。
後來,李一凡才明白,工廠是每個殺馬特繞不過的一個心結。
不懂工廠就不會明白殺馬特——
進入工廠時,殺馬特們大多不過14、5歲。
年紀最小的,才12歲。
有的工廠嫌棄他們年紀小,就打發了,孩子們沒地方去,就只能撿垃圾,睡橋洞。
有的老闆索性不管年紀了,只要等檢查的人來,把他們藏到箱子裏就好了。
這樣的世界,和他們在哥哥姐姐那兒聽到的,完全不一樣。
廣州是個太大的城市,那些高樓大廈在他們眼裏長得都一個樣,讓人辨不清方向。
冷雲(網名)租好了房子,卻找不到回家的路。
好不容易碰到個“好心”指路的女生。
可聊沒兩句,她便向冷雲訴苦,並借了2000塊。
走之前留下手機號,表示一定會還。
五個月過去了,冷雲主動打了電話過去,才知道是個假號。
一直處在熟人社會的他們,沒料到沒由來的欺騙。
他們以為自己的善良會換來一絲城市的認可。
可到頭來只有傷害。
工廠成了唯一保護他們的地方。
可那個地方也不過是個“絞肉機”。
流水線的工作極其枯燥,一旦慢下來,就會被領班訓,會被同事欺負。
久而久之,大家索性就低着頭幹自己的活兒,什麼也不管。
**“人和人好像不會交流一樣,偶爾説句話,又害怕被領班罰,乾脆就不説話了,”**羅福興回憶着自己當初給微波爐套包裝袋的日子。
可不管怎麼幹,手下的活兒好像沒有窮盡,流水線上的皮帶一直在滾動……
他們沒日沒夜地上班。
除了吃飯,其他時間都在幹活兒。
一天工作12個小時是常態,時不時,通宵也有。
有時,累到站着都會睡着。
但再困,也不敢鬆懈。
因為很有可能打個盹兒的空,車牀上的皮帶就會帶走一根手指。
這是他們最害怕遇到的情況。
平時連工資都不一定按時發,賠償?
想都不敢想。
一次工作中,鍾馗(網名)不小心把手筋弄斷了。
找老闆,老闆不僅不賠,還不屑地説:“你出去也沒人要你。”
有人建議去勞動局討公道。
鍾馗説:“勞動局是什麼我都不知道。”
他們受不了壓榨,就想換工廠。
換了一家又一家,到頭來發現,哪家工廠都在剋扣工資,哪家老闆都兇狠不講理。
天下烏鴉一般黑。
老闆們拿着1、2000的工資壓着他們,走不掉,逃不了。
他們每天都不想去上班,可一睜眼,渾渾噩噩的,不知道怎麼又坐到了工位上。
漸漸,他們麻木到忘記了一切,連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也不知道了。
不會用銀行卡,不會坐公交……
“也上了幾年學,怎麼感覺自己跟文盲一樣?”
大多數工人都患上了抑鬱症。
他們打開窗,目及之處全是工廠防跳樓鋪設的鐵網——死都死不了。
走了,沒錢。
留下,沒命。
工廠的機油味、車牀的轟鳴聲,永久地嵌進了他們的記憶深處。
李一凡提出想去工廠看看。
可如果和工廠協商,拍到的只會是虛假的祥和,以及經過調教的工人。
眾人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有人出了一個招:
讓工人們自己拍視頻,20塊錢一個的收。
這主意好是好,卻不知道怎麼才能讓工人相信。
一旁的羅福興説,只用寫兩句話就成:
“不要押金”+****“日賺千元不是夢”

果然,雪片似的視頻飛來。
李一凡團隊收集到了915條視頻。
每一條視頻裏,都是千篇一律的工作,都是機械的手腳動作。
每一個瘦小的身體裏,都藏着一個蒼老而乾癟的靈魂。
看着他們,你彷彿一眼就能看到他們之後的命運。
祖祖輩輩,一批一批地在工廠耗盡自己,最後悄無聲息地死去……
>>>殺馬特
瘦瘦小小的羅福興從小就被欺負。
告訴老師,老師嫌他學習差還事兒多。
告訴家人,爸爸不着家,媽媽忙工作。
小小的他,經常揣着菜刀去上學。
後來,和校霸混在了一起,路上遇見當初欺負自己的人,看着對方低下了頭。
那一刻,羅福興明白了,只有成為壞孩子才不會被欺負。
工廠的日子無聊而壓抑,再加上外界防不勝防的惡意,讓羅福興想要尋求庇護。
可沒有圈子接納他,這讓羅福興萌生了自己搞一個圈子的想法。
一次偶然,他在網上看到了日本男星石原貴雅的照片:
誇張的髮型、濃豔的眼妝、烏青的紋身。
羅福興覺得這太酷了。
要是打扮成這樣,就沒人再敢欺負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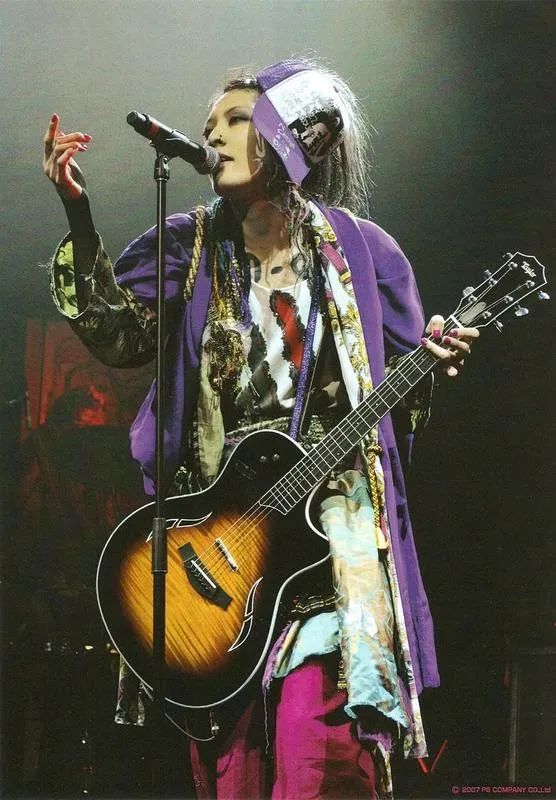
石原貴雅,日本視覺系搖滾歌手
圖源:網絡
羅福興開始模仿石原貴雅,用髮膠和吹風機弄出爆炸的彩色頭髮,在身上紋滿紋身。
他要為這一套打扮起個名字。
在網上搜索“時尚”,頁面蹦出了一個英文:“smart”。
靠着“中譯英”,他念出了“斯馬特”。
但覺得還不夠霸氣,於是,把“斯”換成了“殺”。
就這樣,殺馬特誕生了。
圖源:和陌生人説話
羅福興把自己的照片傳播出去,很快吸引了第一批殺馬特。
大家學着羅福興的樣子,把頭髮弄得要多誇張有多誇張。
逐漸地,爆炸五彩頭,黑色死亡眼線,兩元店淘來的配飾,開始呈病毒式地流行。
線上,他們活躍在QQ空間、勁舞團。
線下,他們去金豐溜冰場、石排公園。
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了一起,找到了久違的發泄快樂以及表達自我的方式。
走在大街上,他們不害怕,也不閃躲。
甚至,他們會扮上最誇張的造型去人最多的旅遊景點。
陌生人驚詫的目光,總會讓他們感到興奮。
“哪怕罵我兩句也行,最起碼有人在跟我説話。”
沒有工廠的枯燥,沒有城市的排擠,一羣人抱團取暖,培養出了家族感。
為了守護好自己的小天地,他們嚴卡進羣標準,讓專人審核。
髮型不夠格,pass。
沒用火星文,pass。
羣內實行嚴格管理,從上到下分總創始人、創始人、族長、副創,總指揮……
殺馬特的家族羣越來越壯大。
羅福興説,巔峯時期,他手下管理20多個QQ羣,是上20萬殺馬特的“精神領袖”。
飄飄然的羅福興給自己冠上了“教父”的名頭。
不過,對於這個稱號,很多殺馬特元老根本不認。

圖源:夢與路
殺馬特下面還有不少家族。
雖是同根,但聯繫並不緊密,時不時也會掐架。
不過,各家族之間定了個鐵律,怎麼打都行,但不能弄對方的頭髮。
頭髮是他們的命。
“只要留這個髮型,你讓我去倒泔水桶我都願意,你給我再高的工資,把頭髮剪掉,我也不去。”
這到底是句賭氣的話。
沒有人會用高價誘惑他們剪掉頭髮。
只不過一語成讖,隨之而來的“反殺”讓他們不得不剪去頭髮。
>>>消失
2008年後,“小升規”讓很多小型企業升級規模。
企業開始加強管理,奇怪的髮型、配飾全部不再被允許。
頭髮和工作,只能二選一。
殺馬特們選擇了前者。
但沒工作,就意味着沒錢。
像乞丐一樣的生活,讓一些殺馬特妥協了。
這事情對殺馬特羣體衝擊不小。
但緊接着,他們開始經歷最兇狠的一次“文化清洗”。
這個行動在2013年達到了頂峯。
先是黑客突破審核,發起無休止地髒話攻擊。
再然後,現實社會里,只要在街上遇見殺馬特,就會有人不分清紅皂白上去毆打。
李學松(音譯)還記得,一次出去吃放。
落座沒多久,鄰桌的人就過來找事。
混亂中,他們把自己一個朋友的頭髮用打火機給點了。
那時關於毆打殺馬特的社會新聞下,沒有對傷者的憐憫,全是一片對暴力的叫好。
線上辱罵,線下被打。
殺馬特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劫難。
他們被整個社會認定為最骯髒的、下流的。
沒有能力去反抗的殺馬特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慢慢地,數十個QQ羣在那一年解散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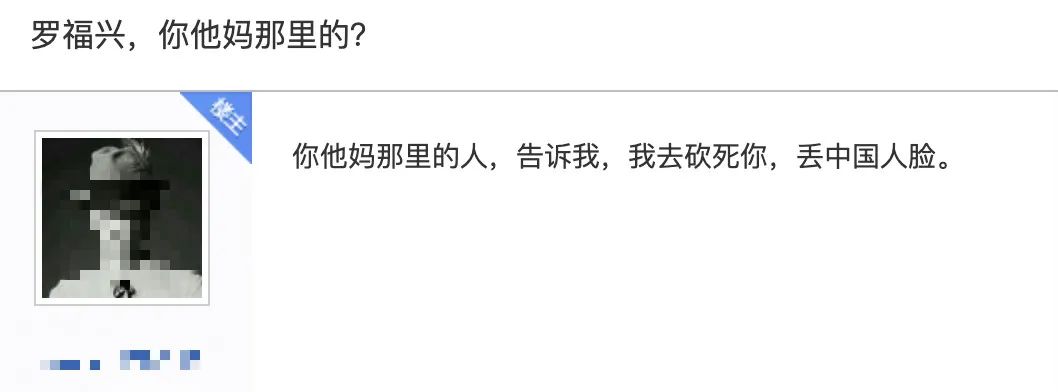
貼吧裏,有人叫囂辱罵
**“恐懼已經嵌入了殺馬特的基因,”**李一凡不無痛心地説。
當初,李一凡團隊聯繫上了採訪一個殺馬特。
可到了之後,那人説什麼也不露面。
一問,才知道,他害怕李一凡一行人是“同城代打”。

接觸越多的殺馬特少年,越讓李一凡察覺到自己的好笑。
他本來以為一幫年輕人是通過糟踐自己來對抗這個時代、對抗這個社會的。
可,哪有什麼對抗。
這幫孩子只是想用虛張聲勢的“壞”來懇求主流社會的一次關注。
結果,沒有絲毫的關心,只有惡毒的嘲笑。
他們就像一個討糖吃的孩子。
可惜只是因為衣衫襤褸,臉上掛着髒兮兮的鼻涕,就失去了被憐愛的機會。

本來一開始,李一凡想好了紀錄片怎麼拍,可這一趟下來,他有些迷茫了。
“我開始反省,我們是不是把美限定得太窄了。”
那些先入為主的偏見和現實中觀察到的悲傷撕扯着李一凡。
他推翻了一切設定。
他決定讓殺馬特們自己講述作為90後農民工二代的辛酸故事。

李一凡採訪殺馬特少年們的時候,只有聊到那段瘋狂的日子,才能在他們臉上看到滿足的笑。
其他時候,他們的臉上只有冷漠、枯竭、無望。
新聞裏動不動是幾千萬的片酬,幾百萬的代言費……
而他們手裏攥着的只有幾千塊的存款。
莫大的孤獨感和無力感席捲每個人。
羅福興説,自己從來不會抬頭看任何一棟高樓。
因為他知道這些跟他沒關係。
“不是沒有理想,有,但大家都不會去談,沒有工作,又實現不了,為什麼要去談論它。”
他們從不觸碰理想。
太奢侈。
誰談,誰就要被笑話。
不是沒有過爭取,羅福興也曾和朋友合夥開了家美髮店。
可沒兩個月,美髮店就倒閉了。
走之前,羅福興在撕破的牆紙上,寫下了一行字:
“明明那麼努力的想要留在這座城市,這個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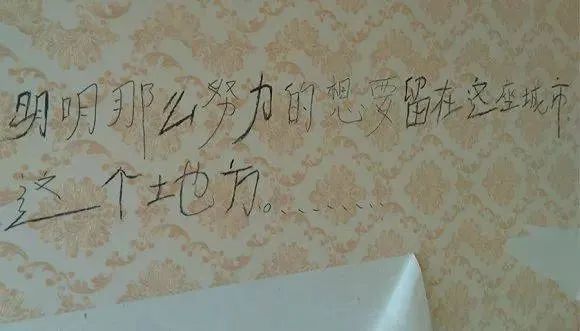
圖源:藍字計劃
後來,羅福興接受過很多采訪,每次他都會説到一句: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這話讓李一凡十分難過。
這幫孩子從沒做錯什麼,卻給自己安上了滔天的罪。
其他殺馬特們也學會用自黑的方式調侃過去,站在主流媒體的角度去嘲笑過去的自己。
那些笑裏,你分不清有多少真正的釋然,有多少巴結的示好。

當年的殺馬特們直言再也不想去工廠了。
對於那個地方,他們始終無法原諒。
有些人回了老家,做農民。
間或玩一下視頻號,想試探性地復興一下自己的青春。
可沒玩兒多久,封號了。
有些人選擇繼續留在城市,嘗試做別的生意。
也有人始終繞不過工廠,只能回到那裏。
只是每次上班前,他們都會把頭洗了,再去上班。
邊洗邊説:“上班,平常一點好。”
回到工位上,他們繼續低頭重複着流水線工作。
一陣微風拂過,他們乾枯的黃髮輕輕擺動了幾下,最後又悄無聲息地落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