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女兒,不過爾爾_風聞
血钻故事-血钻故事官方账号-这里有硬派历史故事。2020-12-02 15:49
誰才是“印度的女兒”?
如果在貿然間提出這個問題,估計不論是誰都會感到迷惑,但喜歡玩腦筋急轉彎的人在思考良久之後則可能得出一個答案:“印尼”。原因很簡單,因為尼字跟“妮”字相通,在中國地方方言的語境裏,“妮”字很多時候就是父母對女兒的稱呼。
如果在看了這篇文章後,你屁顛屁顛地跑去跟一個印尼小哥説這個笑話,那即便被對方痛扁一頓也是活該,畢竟將心比心而言,沒有一個正常人會允許別人把自己的國家稱作另一個國家兒孫。
印尼小哥不可以,那印度小哥總可以吧?於是你又屁顛屁顛地跑到印度小哥面前又講了一遍這個冷笑話。聽完你講的這個笑話,坐在摩托車上的印度小哥發出一聲不屑的冷笑,從你頭頂上方扔下一份報紙。
在隨之響起寶萊塢歌舞聲中,接連不斷跳下摩托車的印度小哥將你團團圍住,在整齊劃一的舞步中向你深情地吟唱道:“張開你的眼睛看清楚,這才是‘印度的女兒’”。
聽了他們的話後,你翻開扔給你的報紙,在報紙上赫然寫着一位美國女士的名字:卡瑪拉·哈里斯。

哈里斯家鄉慶賀“印度的女兒”成為美國副總統
這個時候你不由得大驚失色:什麼?下任美國副總統竟是“印度的女兒”?她跟印度有什麼關係?她怎麼就成了“印度的女兒”了?她又是一位怎樣的女士呢?帶着這些疑惑,原本只是想用冷笑話緩解下尷尬的你,會在求知慾的驅動下繼續閲讀這篇文章以期望能夠從中找到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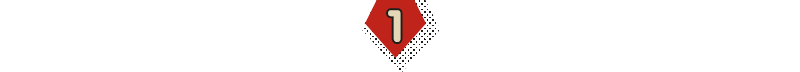
緣起
1958年,孟買。
陽光透過雲霧將整座城市染上色彩,不少人都趁着這個天氣帶着家人出外散心,但站在窗前的P. V. 高普蘭(Gopalan)則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看着窗外正在嬉鬧的幾個孩童,憂心仲仲的高普蘭似乎面臨着一個巨大的難題。他並不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要不然也不會坐上印度勞動、就業與住房部聯合秘書的位置,但這只是針對公務而言,在家務事面前,高普蘭跟大多數人並無二樣。
拉上窗簾將陽光隔絕在外,高普蘭轉身看了一眼站在自己身後的那名年輕女孩,盯着她的眼睛問道:“你已經想清楚了嗎?”
女孩的眼神有些許動搖,但很快就迎着高普蘭的目光對視過去,説道:“爸爸,我已經下定決心了,希望您能支持我。”
看着那名女孩堅決的神情,高普蘭有些無言,房間頓時陷入了沉默。許久之後,高普蘭無奈嘆了口氣,邊踱步邊唸叨:“莎婭瑪拉(Shyamala),如果你真的跑到美國去留學,那就只能靠你自己了,雖然四個孩子中你年紀最大,但也才十九歲啊,我怎能放心得下。”
説到了這裏,高普蘭頓了頓,看了眼一言不發的莎婭瑪拉。高普蘭並不是真的反對自己的女兒外出留學,只是莎婭瑪拉突然説出要到美國留學決定,讓他有些措不及防,思緒也跟着有些混亂。儘管在當時的印度,出外留學的女學生數量少之又少,大部分的年輕女性都會早早地嫁作他人為妻,但高普蘭並不迂腐,不然他也不會娶了拉嘉(Rajam)為妻,要知道她可是一個社會活動家。
隨手拉開旁邊的窗簾,高普蘭用手遮了遮陽光,剛剛在街上玩耍的幾個小孩正牽着他們父母的手準備回家。看着陽光將自己的影子撕扯着印在莎婭瑪拉的腳下,高普蘭理了理自己的思緒,長吁一口氣,笑着説道:“如果你能取得入學資格,那就去吧,其他的不必擔心。”
(P.V.Gopalan
聽到高普蘭的最後一句話,莎婭瑪拉的身體有些顫抖,她知道或許從此刻開始,她的命運已經開始改變了。但隨之而來的念頭讓她的愉悦消散了許多,在真正取得美國的留學資格之前,她需要先完成自己在印度的學業。
帶着剩餘的喜悦,莎婭瑪拉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學校——歐文女士學院(Lady Irwin College)。對於自己所就讀的這所女性大學,莎婭瑪拉一貫感到非常驕傲,因為這所學院即便放眼全印度也能經得起比較,但對於自己所學的專業,莎婭瑪拉又感到十分的枯燥。
坐在教室裏,莎婭瑪拉在紙上無聊地寫着“Home Science”然後又用筆圈起來戳了戳。這個專業如果翻譯一下,那就是“家政學”,如果説得再簡單一點的,莎婭瑪拉學的就是“為家庭服務”的一門學科。説穿了,在這所學校裏,莎婭瑪拉將會被培養成一名取得證書的合格家庭主婦,就算之後能夠擺脱這一宿命,只怕也跟其差不太多。
但對於一名出身於官宦之家,而且自己母親還是個社會活動家的少女而言,這恰恰是她最為恐懼的事情。每每念及此處,莎婭瑪拉的腦子裏便會想起太平洋的另一端——一個能夠改變她命運的“天堂”。
或許莎婭瑪拉也不太清楚,此時一場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像暴風驟雨一般洗刷着美國的土地,馬爾科姆、馬丁·路德·金輪番走上時代的中心,而當她以一名留學生的身份踏上這片土地的時候,在大時代背景下她的命運也將會泛起一絲漣漪。
1962年,加利佛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名來自牙買加的黑人留學生——多納德(Donald·Harris)正面對着眾人侃侃而談,怒批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
在這場由學生組織“非裔美國人協會(Afro American Association)”舉行的會議裏,剛到美國攻讀經濟學的多納德出盡風頭,贏得了不少聽眾的掌聲。會議結束後,一名年輕的女孩急忙衝出會議室,將正準備離開的多納德攔下,説道:“你好,多納德,我叫莎婭瑪拉,來自印度,我可以向你請教一些關於殖民地的問題嗎?”
早在到達美國之後不久,莎婭瑪拉便憑藉着自己來自第三世界的留學生身份成為了“AAA”協會中的一員,而這次會議剛好她感興趣也跑來參加了,兩人的見面純屬偶然,但又似乎帶着一絲必然。
或許是被這個突然竄出來的女孩嚇到了,多年之後當多納德回憶起這次初見時,仍懷念自己當時的心跳加速。在人來人往的大學校園裏,兩個人全神貫注於對方説出的話語,他們的話題也從民權逐漸延展開來,到國家風俗、再到個人的感情,最終多納德成為了莎婭瑪拉認定的愛情。
莎婭瑪拉與多納德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猛烈而又帶着炙熱,年輕的學生將自己熱情揮灑在疾聲高呼與奔走呼號之中。莎婭瑪拉與多納德的戀情亦在奔騰的社會浪潮中急速升温,很快在1963年便步入了婚姻之中。
可惜的是,就像民權運動逐漸走向落幕一般,兩個人的婚姻也並未能夠在熱情之中維持長久,最終在1971年分道揚鑣。就像裝了加速器一般,莎婭瑪拉在時間隧道里快速前進,等到一切塵埃落定的時候,莎婭瑪拉發現自己深愛的丈夫早已離她而去,留給她的只有兩個女兒,其中大女兒便是卡瑪拉·哈里斯。
成為單親母親的滋味並不好受,莎婭瑪拉不得不在工作跟照顧自己的女兒之間來回奔波。雖然婚姻並不圓滿,對於兩個女兒莎婭瑪拉卻是十分重視,把她們看成了自己的全部希望。也正因如此,莎婭瑪拉總會不時拉着哈里斯和妹妹的耳朵囑咐道:“不要讓任何人支配你們”,“要獨立而自信地活着”。雖然缺少了親生父親的關愛,但在母親陪伴下成長起來的兩姐妹卻要比很多完整家庭的孩子都要更加堅強。
在將自己的半生心血都用在女兒身上之後,莎婭瑪拉最終因為癌症而被迫躺在病牀上奄奄一息,大女兒哈里斯就坐在身邊握着她逐漸失去力氣的手。隨着視線的逐漸模糊,莎婭瑪拉知道自己可能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
在席捲而來的黑暗之中,當初那名剛剛踏上美國土地的19歲少女在腦海中一閃而過,結婚、離婚、撫養兩個孩子長大,她的命運在決定了離開印度的那一刻便開始發生轉變。憑藉着自己的倔強與努力,莎婭瑪拉在這片陌生的異域上留下了自己的一抹痕跡。
在即將墮入黑暗的邊緣,莎婭瑪拉用盡全身力氣睜開雙眼,在最後的一絲光明裏,她最掛念的、也是最後一次再見的,是繼承了她血脈的兩個女兒。

高潮的印度
2020年11月8日,位於印度南部的一個小村莊圖拉瑟德普拉姆(Thulasendrapuram)迎來了一件大喜事。
一大清早,村子裏便傳出了一陣敲鑼打鼓聲,在眾人的注視下,寺廟裏的僧侶用牛奶給印度教神祗雕像清洗身體,而後開始虔誠祈禱。孩子們從僧侶的手中接過糖果後,便跑到了寺外的空地聚集。在眾人的注視之下,一名年齡稍大的少年點燃了一掛鞭炮,站在一旁的大人用手裏一位女性的照片極力扇開在噼裏啪啦聲中噴湧出來的嗆人煙霧。
在不久之前,村民們都收到了消息:在美國的大選中,拜登擊敗了特朗普,將會成為下一任的美國總統。當然,讓他們陷入狂喜的並不是拜登這個七十八歲的白髮老頭,而是高普蘭的外孫女、莎婭瑪拉的長女、拜登的副手——哈里斯。
消息傳回村裏之後,下到剛會走的小孩,上到八十歲的老人,每個人手裏都拿着一張哈里斯的照片。老人家一談起這事便豎着拇指説道:哈里斯的祖父和母親都是從這個村子裏走出去的,她是我們“村莊的女兒”,在之後不久,她將會成為下一任的美國副總統!

鞭炮聲停下後,孩子們從大人手裏接過了一疊哈里斯的黑白照片,高高舉過頭頂在路上聚集遊走,與他們擦肩而過婦女則帶着裝滿水果的盤子匆匆往村裏集合的地點趕去。
面對媒體的鏡頭,容光煥發的村長對着記者説道:“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村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讓村民們十分驕傲,而且當選了美國副總統的還是一位女性,這也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成就。”
對於哈里斯勝利的熱情程度,可以説即便是哈里斯在美國最忠實的粉絲也不一定能夠比得上此刻的村民。
當然,對於美國大選的結果,村民們的表達還比較含蓄,相比較之下印度媒體的興奮則顯得更加狂野,哈里斯先不説,印媒把拜登也當成了自家親戚,上去就是一頓吹噓,而且“有理有據”。
按照《印度時報》的説法:早在2013年拜登訪印的時候,他就曾説過他有個遠房親戚住在孟買;2015年的時候拜登又在華盛頓宣稱在孟買也有五個姓“拜登”的,如果再往前去追溯,早在拜登成為參議員的時候他就收到了一封來自孟買的信件,寄信者也姓拜登,從這封信裏,美國的拜登得知他的曾、曾、曾、曾、曾祖父(一共五個“great”加一個“grandfather”)喬治·拜登曾經就在東印度公司工作,在退休之後就住在了印度,還娶了個印度的老婆。

這不巧了嗎?大家都是拜登,那應該就是一家人了,不過秉着實事求是的精神,《印度時報》又在最後加了一個點睛之筆:尚不清楚拜登是不是跟其他五個印度的“拜登”有聯繫,他沒有放到明面上來説。
不過拜登再怎麼親近也只是個“遠方親戚“,印媒總不可能説美國總統是“印度的兒子”或者“印度的孫子”,真那樣的話估計拜登馬上就要跳出來大喊“fake news”。拜登是不行,但哈里斯可以啊!哈里斯她母親在移民美國前還真是個印度人。
於是,在圖拉瑟德普拉姆村莊的村民們狂歡的當天,多家印度媒體直接將哈里斯叫作“印度的女兒”,緊扣住哈里斯的印度血脈這一點進行了詳細報道,《德干紀事報》的記者甚至找到了哈里斯的舅舅進行了一番採訪。
一時之間,“印度的女兒”成為了哈里斯的一個代名詞,因此當有人宣稱“印尼是印度的女兒”的時候,屁股又得要挨一頓揍。當美國副總統的職位與一位帶有印度血脈的女性相碰撞時,最為興奮的不是美國的少數族裔,而是遠在萬里之外的印度人民。

但實際上,將哈里斯稱作“印度的女兒”,不能説八竿子打不着,只能説一竿子橫頂整個太平洋,總讓人覺得有些尷尬。在母親莎婭瑪拉去世之後的十一年時間裏,哈里斯並沒有踏回印度的土地一步,因此將其稱作“印度的女兒”,更像是印度的一種自我宣泄,而這種情緒的根源,往上可以追溯到甘地的身上。
1931年3月。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甘地身上,等待着他做出決策。在一年之前,為了反抗殖民政府的食鹽專賣政策,甘地帶着自己的信徒一路長途跋涉,到海邊自己動手煮鹽,以一種他歷來所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姿態表明自己的態度。不過僅僅三週之後,便為殖民政府所鎮壓,甘地也於5月被捕入獄。月光透過監獄的狹小窗户披灑在被囚禁者的身上,“非暴力”的理念在日月精華中愈久彌堅,但外面的形勢卻發生了鉅變,在印度各地相繼發生了反英起義,近三萬人被捕入獄。
現在,甘地所要回答的問題是:印度的民眾是要以一種徹底的暴力將殖民者趕出印度而後建立起一個不再屈從於西方的新印度,還是繼續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讓殖民者自己從印度的土地上撤離?3月5日,甘地跟時任殖民地政府總督的歐文簽訂協定,英政府同意釋放被捕的非暴力政治犯,亦同意給予國大黨合法的地位,但前提是國大黨停止不合作運動。
這並不是甘地第一次跟殖民地政府妥協。早在第一次不合作運動期間,喬裏喬拉的民眾因為不堪壓迫而拿起武器準備用武力捍衞尊嚴的時候,甘地便以一種救道者的姿態站了出來制止革命的發展,國大黨緊隨其後通過決議停止了第一次不合作運動。
當然,這也不會是甘地最後一次跟殖民政府妥協。1942年,面對日益變化的國際形勢,在甘地的呼籲和發動下,“退出印度運動”應運而生,但不久之後國大黨的領袖便相繼入獄,民間運動在失去核心領導之後開始出現暴力傾向,面對愈來愈多拿起武器的印度民眾,甘地以保外就醫的形式悄然走出監獄,隨之登高宣佈“退出印度運動”正式停止。
我們不妨用一幅形象的場景對此進行比喻:一夥持刀的強盜在闖進了家裏之後,將家裏的錢財奪取一空,把房子佔為己有,原本的屋主人一家成為了強盜的奴僕。家裏不服氣的年輕人準備拿起板凳把這羣強盜趕出自己的家裏。這時候,一位老人大喝一聲,站了出來,用閃爍着智慧光芒的眼神看着他説道:“不能用暴力,我們打不過他們,只要不聽他們的話逼他們走就行了。”等到強盜劫掠一空撤退之後,奪回房子的年輕人幡然大悟,領會到了老人家的思想精髓,但同時他們也學會了強盜的行為。
在印巴分治之後,在尼赫魯的掌控下,印度對於自己周邊的國家開始露出獠牙,從巴基斯坦,到中國,再到不丹,可以説都曾目睹過南亞霸主的“雄風”。
將前後兩個時期的印度做一個對比,如果説此時的印度就像一隻兇猛的野狼的話,那麼甘地時期的印度則更像一隻試圖掙脱項圈的家犬,最後帶來的結果就是,時至今日,對於自己的周邊國家印度仍舊十分傲慢,但面對西方時仍保有一種源於“非暴力不合作”時期的屈從性心態,當世第一“民主大國”在第一“民主強國”面前仍舊是保持着一種奴性的瞻仰姿態。
這正是今日印度媒體和印度民眾會因為哈里斯的勝利而陷入狂喜的原因,因為哈里斯向印度人證明了,即便在當世第一民主強國裏,印度人也能混得很出色,他們所鼓吹的並不是哈里斯本身,而是流淌在哈里斯血液裏面的那一半印度血脈,因為他們從中看到了印度作為一個族羣在地位上的上限,這也是她獲得“印度的女兒”稱謂的價值所在,至於此時,哈里斯血液裏另一半的牙買加黑人血統已經無關緊要。
可雖然印度的媒體與民眾對哈里斯的當選報以了極大的熱情,但對於哈里斯而言,她的印度血脈,真的那麼重要嗎?

政客哈里斯
2003年,舊金山。
當地的華人領袖蘇錫芬正在紙上寫着什麼。不久之前,女兒蘇榮麗想讓他幫自己的好友起一箇中文名字,為此,他可以説是絞盡腦汁。對於蘇榮麗的那位好友,蘇錫芬並不陌生,她正是正在競選舊金山區域檢察官一職的候選人卡瑪拉·哈里斯。
因為蘇榮麗和哈里斯在都是灣區亞裔律師協會的會員,所以兩人關係也不錯,甚至給哈里斯起中文名這個事也是蘇榮麗給出的主意。只不過蘇榮麗是華二代,中文不怎麼樣,就將這件重任交代給了自己的父親蘇錫芬。
蘇錫芬將寫好的紙張折了折後交到了蘇榮麗的手裏,不久之後,蘇榮麗又將紙張交給了哈里斯。翻開手中的紙張,哈里斯翻來覆去地看了幾遍上面的字,最後在一旁蘇榮麗的幫助下,勉強讀了出來:“賀錦麗”。
很快,這三個字便被印成了橫幅和手幅,成為了哈里斯競選的中文名字。走進華人社區後,哈里斯用自己不怎麼熟練的中文對着周圍的聽眾進行自我介紹, 在旁看熱鬧的華人聽眾則在聽到中文的同時, 看到了哈里斯後面印着的“賀錦麗”三個字。
對於華人,尤其是一代華人而言,“賀錦麗”三個象形字確實要比一連串字母的“Harris(哈里斯)”、“Nicolas(尼古拉斯)”這類名字更加容易記住,也比“COCO(蔻蔻)”、“Lily(莉莉)”這類名字更加具有文化親切感,這為哈里斯籠絡到了不少華人的選票,在競選之中助了她一臂之力。
但是,選票歸選票,事業歸事業。按照當地華人後來的説法,雖然不少華人把自己的票投給了“賀錦麗”,但當選的卻是“哈里斯”,“賀錦麗”對華人有親切感,但哈里斯則對華人始終保持着距離,説穿了“賀錦麗”三個字也只不過是她用來粉飾門面的一個工具罷了。
對於一名合格的美國政客而言,在民主遊戲裏如何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才是最原始的驅動力,而哈里斯無疑就是箇中好手。在2003年的這場競選裏,哈里斯所運用的手段不只是取了箇中文名,如果僅僅憑藉於此,那她也未必能夠贏得勝利。
在這場戰役中,哈里斯募集了超過62萬美元的運作資金,遠遠超過了法律所規定的21萬,在這背後威利·布朗為她出了不少的力氣。為了幫助哈里斯上位,作為加州屈指可數的政治大佬,威利親自出馬,在自己的富豪圈子裏為哈里斯作説客,包括蓋蒂家族在內的諸多富豪為哈里斯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鍊,這也為她的勝利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如果我們將時間線撥回到哈里斯剛剛進入加州政治圈的時候,我們會看到這樣一幕:在鏡頭之下,哈里斯挽着威利的手兩人踱步參加一場酒會。已經結了婚的威利並不吝嗇於向媒體展現他的個人魅力,雖然自己是個有頭有臉的政治人物,但在不同的場合裏時常挽着不同的情婦,而哈里斯只是其中一個而已,但對於哈里斯而言這卻是她政治生涯最重要的一步。

對於一個父母都是移民的混血兒而言,哈里斯最缺乏的東西是什麼?是金錢還是名氣?都不是,她最缺乏的是進入遊戲圈子的途徑。在金元政治裏,如果能夠獲得資本集團的青睞,金錢與名望也會隨之而來,在給威利當情婦期間,哈里斯收到的最珍貴的禮物並不是一輛豪車或者在機構掛職的收入,而是她可以開着豪車跟隨威利參加加州上層人物的舞會,或者憑藉着在機構中所掛的職務混跡在各界名流面前,為自己的政治前途鋪路。
2003年哈里斯競選舊金山檢察官的時候,她與威利早已經分了手,但卻仍舊保持着政治盟友的關係,如果用哈里斯自己的話對兩人的關係進行一次總結,那就是:“我並不欠他什麼東西。”説到底,在哈里斯眼裏兩個人也只是各取所需罷了。對於這樣的一個精於算計的美式政客而言,族裔的身份在某種意義上同樣不過是自己用來搭建政治天梯的工具。
可能有些許諷刺,或許哈里斯自己也想不到,比起從小陪伴着自己成長的印度裔母親,雖然自己那位黑人父親不怎麼負責,遺留給她的黑人基因也讓她在美國社會里飽受種族歧視之苦,但在長大之後卻成為了哈里斯用來給自己拉選票的悲情工具。
也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民主黨內部競選的時候,作為全場唯一的一個黑人,哈里斯敢站出來硬懟拜登,抓住拜登在幾十年前的一個議案立場動情地説道:“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和我的妹妹跟一户鄰居相處,鄰居的父母告訴她絕對不能跟我們一起玩耍,因為我們是黑人”。
哈里斯當然不是真的對拜登心懷不滿,不然她也不會在不久之後成為拜登的副手,她只不過是利用自己的種族優勢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罷了。
原本在民主黨內最熱門的副總統人選是白人女性參議員克洛布徹,不少人都將她看做是拜登的最佳助手,但隨着弗洛伊德之死而興起的“黑命貴”運動,克洛布徹宣佈退出拜登的副手名單,哈里斯逆襲而上成為了拜登的參選搭檔。面對種族矛盾日益激烈的美國社會,哈里斯能夠在政壇上平步青雲,這背後除開能力與政治經驗之外,她的黑人血統同樣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選勝利之後,哈里斯被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位置,各類褒獎接踵而來,而其中最為熱誠的當屬來自母親故國的讚賞。
面對印度媒體和印度民眾賦予的“印度的女兒”的稱謂,哈里斯一如祖父高普蘭一般,站在窗前陷入了沉思。看着窗外嬉鬧的白人小孩,哈里斯清楚地知道:比起印度那十多億沒有投票權的民眾,現在的美國還是白人説了算,幫助白人資本在印度獲得更多的利益才是一名合格的美國政客。比起“印度的女兒”,她更愛着生她、養她的美國。

結語
19歲那年,莎婭瑪拉離開印度前往美國求學。
按照正常的流程,她會從大學畢業之後跟大多數印度女性一般,結婚、生子最後在家務之中逐漸老去。在她踏上美國土地的那一刻,她的命運發生了改變,同時改變的還有她的子女的命運。和黑人丈夫離婚之後,莎婭瑪拉盡力將自己的兩個女兒撫養長大,讓她們成為一個獨立而又自主的黑人女性,當然,也是一名印度裔女性。
當其中一個女兒哈里斯在美國的大選中成為拜登的副手並取得勝利的時候,莎婭瑪拉早已經離開了人世,但這並不妨礙這個消息在印度掀起了一陣高潮,印度的媒體和民眾們將哈里斯追捧為“印度的女兒”,把她當做自己國家與族裔的一個英雄,就像數十年前甘地讓印度的民眾看到了自由的希望一般,哈里斯的成功也讓印度看到了自身種族的潛力,還有即將走向甜蜜的美印關係。
但他們忽略的是,生長於美式民主社會下的哈里斯,早已經在票選政治中成長為一名合格的政客。對於哈里斯而言,現在她所在意的並不是自己的血液中是否流淌着黑人或是印度裔的基因,而是要如何利用這些特性幫助自己獲得更大的政治權益,而這也意味着,高舉着哈里斯畫像而陷入狂歡的印度民眾,終將會收穫到巨大的失望。
失望的根源就在於紮根在美洲土地上的哈里斯所忠誠的終究不是她的族裔,而是她的國籍以及利益。
END
本文作者:阿究,血鑽故事研究員。
部分參考文獻:
1《Prayers of gratitude for election of daughter of India Harris as U.S. VP》,U.S.News;
2《The progressive Indian grandfather who inspired Kamala Harris 》,Los Angeles Times
3《Kamala Harris’Grandfather was an Indian Civil Servant Who Helped Refugees in Zambia》,The Better India;
4《How Kamala Harris’s Family in India Helped Shape Her Values》,The New York Times;
5《How Kamala Harris’s Immigrant Parents Found a Home, and Each Other, in a Black Study Group》,The New York Times;
6《See Kamala Harris’ ancestral village in India celebrate her election win》,CNN;
7《When Biden spoke of distant relatives living in Mumbai》,Time of India;
8《Kamala Harris and Joe Biden Clash on Race and Busing》,The New York Times;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血鑽故事”(ID:xuezuangushi),專注於硬派歷史故事,伴你立足中華,勇闖世界。轉載授權請聯繫“血鑽故事”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