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馬特,中國打工少年的保護色_風聞
乌鸦校尉-乌鸦校尉官方账号-2020-12-15 10:23
在今年的流行語裏面,**“爺青回”**三個字註定難以磨滅,隨着一次次地瘋狂刷屏,它當之無愧地成為了B站的年度彈幕。
“爺的青春回來了”,當這句話出現的時候,往往伴隨着舊日的光景映入眼簾,熟悉的事物再次來臨。
然而,在B站打出“爺青回”彈幕的主力軍,並不是倦怠疲勞的中年人,而是正當年的80後、90後,甚至00後們。

儘管他們尚年輕,卻開始自嘲心力衰竭,感嘆青春易逝,當過去的美好記憶驟然穿越而來時,重逢的驚喜都匯聚在這個詞裏。
那些記憶的碎片,是蟬聲無休無止的夏日,小手拍得通紅的水滸卡片,電視裏放映的《神奇寶貝》,課堂上抄過的歌詞本,街頭師傅畫的精緻小糖人。
明明就那麼閃現一下,來如飛花散似煙,而就在恍惚之間,分明看到了栩栩如生與活色生香。
年青一代終究還是沉湎在懷舊的秘境裏難以自拔了。
2009年7月16日,百度“魔獸世界吧”,出現了一篇題為“賈君鵬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的帖子,正文只有“RT”兩個字母,也就是“如題”的意思。

就這樣極其簡單的一句話,霎時間就爆紅華語網絡。
7小時內,底下的跟帖就超過了一萬,到第三天,電腦回帖數量已經有30多萬條,達到上限。
那段時間,大街小巷的廣告,開餐飲的,學英語的,搞房地產的,都跟上了這波熱潮。


賈君鵬究竟是否真有其人,已經不再重要,一場瘋狂的創作巨浪就此開始,“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迅速喚醒了一代人的共情。
值得玩味的是,直到2020年,這個帖子下仍有窸窸窣窣的回覆,從未間斷過。其中自然也不乏“爺青回”這樣的表達。
從一度回憶青春,到二度回憶青春,已經過了十多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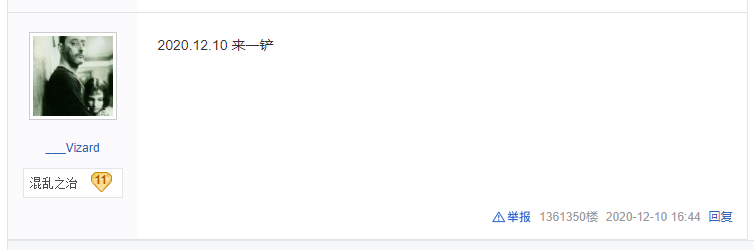
懷舊情緒的產生自然是複雜的,他不僅有當代青年對世界變化太快,物是人非的愴然和感嘆。
另一方面,它還來自於對壓抑現實的逃避。
尤其是那些曾經豪情壯志地覺得將來會怎樣的年輕人,在被生活不斷捶打至扭曲變形,一次次苦苦搏命卻又一番番困頓失意後,往往需要尋個角落自我療傷。
過去的記憶,彷彿就成了一味解藥。將無數複雜情緒高度濃縮的“爺青回”,自然就成了打工一族心照不宣的時代暗語。

殺馬特青年也許最能體會這種感覺。
在十多年前,最蔚為壯觀的一個羣體,就是殺馬特了。
2020年10月2日,在東莞市石排鎮,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活動——殺馬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光聽名字就覺得喜感。
這場活動是由羅福興發起的,這個羅福興來路不簡單,他曾是統領20萬的“互聯網第一大家族”的族長,“殺家幫”的精神領袖,自封為**“殺馬特教父”**。

頭銜金光閃閃,號召力理應不差,結果在現實中,羅福興卻碰了個尷尬。
他本來想與國同慶節日,結果被警察叔叔勸住了,只好識趣地放棄。
但又因為活動推遲了一天,就要多住一天酒店,雖然只是多了幾十元的住宿費,卻依然讓馬特們難以承受。
於是,很多人提前打道回府。
結果,在無數QQ羣聲稱盛況空前的殺馬特大會,最後只來了8個人。
“教父?什麼屌毛?!”這是幾個殺馬特對羅福興的評價。
誠然,這場活動讓羅福興鎩羽而歸。但也給了我們另一層思考,在急速變幻的工業時代裏,城市森林正在吞噬着土地,殺馬特這個羣體,從未消失過。

**2017年,導演李一凡開始拍攝殺馬特。**此時,距離殺馬特文化鼎盛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數年。
在紀錄片工作開始之前,李一凡就遇到了困難,他發現自己根本找不到殺馬特。
儘管他物色到了各類QQ羣,但是裏面有很多門檻,比如進羣需要殺馬特髮型驗證、火星文溝通等等。
好在,李一凡通關自己的三教九流關係網,找到了“教父”羅福興,他們約在了一個破舊的小旅館,開始一場談話。

這樣談話有些沉悶,因為雙方好像不在一個世界。導演想談文化抵抗,審美自覺,消費社會景觀,等等諸如此類學究氣的議題。
但羅福興卻只是談自己的父親,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經歷。
李一凡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2017年,他搞到了錢,就和羅福興説,走吧,帶我出去轉轉,去看殺馬特的世界。
結果他發現羅福興是個宅男,一個現實中的殺馬特都不認識。
羅福興如今身高170,體重只有90多斤,小時候的他更加瘦小。那時,同班同學經常欺負他,沒事就揍他玩,用腳踩在羅福興的手指上,然後轉動身體,嘻嘻哈哈。

他向老師求助,老師嫌他成績太差,把他安排到最後一排,和垃圾桶待在一起。
他想告訴家人,卻發現除了母親沒人會理他,就是唯一能説話的母親,因為忙於打工也常常見不到。
迫於無奈,他找了一把菜刀放在書包裏,如果再被欺負,就可以拿出來,但他終究沒敢拿出來。
後來的人生道路上,羅福興仍被懦弱和自卑包圍着,而這些裏面,還藏着一絲倔強的自尊。
外界的人會以獵奇的視角觀察羅福興,在媒體的聚光燈下,他出名了。
他被浙江衞視邀請去拍《中國夢想秀》,節目組跟他説好,只聊創業夢想,而到了現場,他才發現,嘉賓和觀眾只想看他的笑話。

於是,現場大屏幕上,羅福興殺馬特時期的自拍被放出來,台下幾百個觀眾鬨堂大笑,嘉賓們則不斷用專業名詞調侃他的“時尚”品味。
羅福興憤怒了,轉身奔出舞台,大手一揮,説不錄了。
李一凡打動羅福興的地方,是他對羅福興説,我就想讓你們自己來講講殺馬特是什麼。
羅福興便和李一凡走了,他們用腳步丈量土地,從深圳開始,走遍了廣州、惠州、重慶、貴陽、黔西南州、畢節、大理、玉溪等等地方,去見識真正的殺馬特們。
在東莞的石排鎮,李一凡發現了殺馬特聚集最多的地方。

一位紫發的殺馬特告訴他,自己剛來到城市,租好了房子,晚上下班了,連房子在哪裏都找不到,因為在他看來,所有的房子都一樣。
旁邊有位“小姐姐”走過來,問他,兄弟你在幹什麼,他回答,在找回家的路。小姐姐就告訴他怎麼走,走到一半,問他借錢,説一兩千就夠,領到工資就還。
紫發殺馬特信以為真,把錢給了她,最後等了四五個月,也沒等來還錢,留下的聯繫方式都是假的。

很多出來打工的少年都有類似的經歷,剛下火車,行李就被人拎走了。
在偌大的城市中,這些少年感到的是無助和絕望,以他們所掌握的知識,根本無處伸冤。
殺馬特少年們,在曾是留守兒童的成長過程中,社會、學校和家庭的集體失位。他們十來歲的年紀,就被迫和社會硬生生摩擦,靠着自己獨立支撐下來。
羅福興説,頭髮會給人勇氣,從形象上説,有一種可以震懾人的東西。而在大家的印象中,這就是壞孩子,壞孩子是不會受欺負的。

這幾乎所有殺馬特精神自衞手段——只要造型足夠誇張,就沒人敢欺負自己。
來城市打工的殺馬特們,從小缺乏關懷和陪伴。當他們和老鄉被分配到工廠後,工廠會把他們化整為零,安排到不同部門,以防鬧事。
這些十四五歲的少年,精力正旺盛,而社交卻約等於無,苦悶需要排解出去。

領了工資,就成羣結隊去溜冰場溜兩圈,去迪廳蹦兩下,去慢搖吧喝杯酒,去網吧上上網。
沒錢的話就一起出去炸街,即便路人的眼光中帶着鄙夷,殺馬特們也無所謂,至少他們在別的地方,不會有這樣的回頭率。
現在雲南昆明承包工程的“雲小帥”,回憶起自己的殺馬特歲月,説那時候只想通過穿着打扮來發泄,讓別人感覺自己很獨特,哪怕是被罵兩句,甚至是吵一架,至少也有人跟自己説話。

他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重複機械固定的幾個動作,在工位上打瞌睡是常有的事。
機器不會覺得疲倦,流水線上產品容易堆積。為了不讓這種情況發生,工人們只好用純檸檬汁提神。
與此同時,步步緊逼車間主任,時刻監督,工人們去趟洗手間都要出示方便條。小作坊還存在安全隱患,輕者出點小疹子,重者則會斷手指。

工廠也不歡迎殺馬特,因為他們是叛逆與不受馴服的象徵性。
他們會厭惡工廠,但又想留在城市,這種矛盾時刻鞭打着他們的內心。
羅福興跟李一凡講,他從來不抬頭看一棟高樓,因為這些跟他沒關係。
隨着年紀的增大,技能的匱乏,多數殺馬特慢慢回到了老家,而那是一種更為貧乏的生活。
五彩斑斕的頭髮被剪去,轟隆隆的工廠已經遠離,殺馬特們又不得不落魄地在家鄉面臨新的困境。

回首以前的人生經歷,他們會覺得荒唐,自己做錯了什麼,羅福興總是説,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如今,羅福興把殺馬特和工人權益聯繫在一起,説殺馬特的後退,本質上是工人失去話語權。
“我在工廠裏面,幹十幾年,一直都是普工,沒有上升的機會。但是玩殺馬特,我至少有上升的機會,比如殺馬特貴族,至少能讓我快樂。”一位殺馬特這樣説。

與三和大神一樣,殺馬特少年作為社會的邊緣人,何嘗不是對階層固化和社會規訓的隱隱嘲諷?
2013年,在清理三俗信息的行動中,殺馬特被定義為“低俗”,從而被主流禁止、打壓。
在城市的知識分子和白領階層眼裏,殺馬特無疑被冠上了“腦殘”的標籤。或是以為這是底層青年通過自我踐踏的方式去抵抗主流社會的審美。
當初,李一凡也是認為的,直到他接觸真實的殺馬特後,才轉變看法。
在快手上,我們會見到農村的底層青年,會表演自虐、生吞活蛇、模仿黑社會,這些行為未必和殺馬特們沒有共通之處。

法國有部紀錄片,叫《瘋狂的祭司》,講述當時非洲的桑海人通過跳舞實現被法國殖民者的靈魂佔有。
具體來説,是一種附體儀式,通過對白人官員的表演模仿和其他附體的跡象,如口吐白沫、眼球上翻、扭曲的動作,得到精神上的昇華。

黑人青年模仿總督、將軍、少尉等身份,殺馬特少年用奇異的髮型裝扮自己,前者是希望奪回被歐洲殖民者霸佔的統治權力,後者是對某些可以呼風喚雨的人物的羨慕。
某種意義上,這兩者其實有共通之處。

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羅納德·科斯,寫過一篇經典論文,名為《企業的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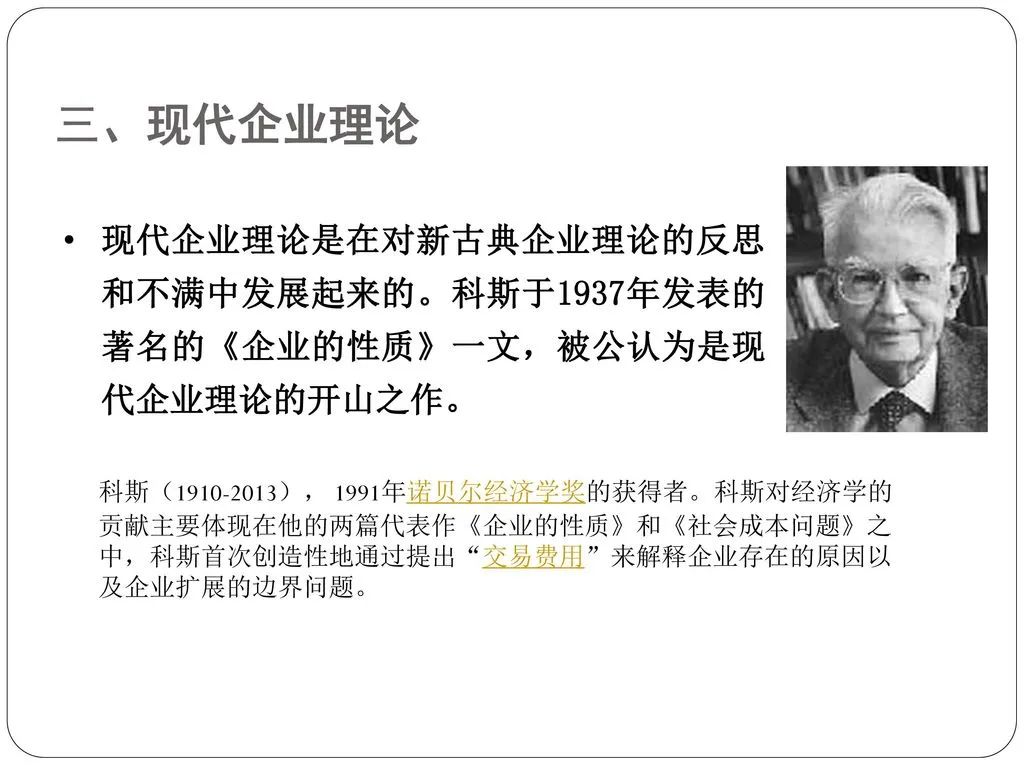
他着重探討了“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主人有權親自或者通過另一個僕人或代理人控制僕人的工作和何時不工作,以及做什麼工作和如何去做。
指揮權才是“僱主與僱員”這層法律關係的實質,這種規定是模糊的,解釋權在企業家,所以在這個關係內,企業家幾乎對員工擁有無限權力,按照科斯的話説,是完全的“主人”。
人們會調侃自己是“碼農”、“PTT紡織工”、“Excel女工”,實際正確的稱呼應該為“碼奴”、“紡織奴”和“Excel奴”。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上映後,85到00後的城市青年羣體對這部電影最有共感。這讓收到反饋的李一凡感到出乎意料。
同為打工人,他們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壓抑。

在“爺青回”的彈幕洪流中,不只是曾經天真爛漫如今汲汲營營的社畜們的青春輓歌,還是他們嚐盡了生活苦楚後的一聲無奈的自嘲和排解。
於知識青年而言,還能在鍵盤上敲幾個字,喊幾聲疼。對殺馬特們來説,就只能緘口不言了。
打工人永不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