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麥科馬克:為了迎接歷史終結的挑戰,福山轉向了公民共和主義
【文/温·麥科馬克 董嶺曉譯】
一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最近發表的研究著作《身份:對尊嚴的需求和怨恨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of Dignity and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希望修改他最著名的論文,這篇論文首先發表於1989年的論文《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然後在1992年發表為一本長達一本書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
他現在説, “終結” 一詞指的並非 “終止” ,而是 “目標” 或“客觀”;與之,“歷史”指的是“發展”或“現代化”的過程,而不是被記錄的時間。馬克思主張,在他自己的解釋方案中,歷史進程將在共產主義烏托邦中達到頂峯;福山説,在他的歷史終結論題中,他在馬克思的論述上提供了更温和、更有條理的解釋,取而代之的是黑格爾對辯證法終點的解釋版:“與市場經濟相聯繫的自由國家”。
這裏錯漏較大。首先,黑格爾不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的倡導者。對於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他均持批判態度,認為二者宣揚一種自私的個人主義,不利於他的最高政治理想——“社羣(community)”。福山的作品取材於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對黑格爾的獨特解讀。科耶夫是俄羅斯移民,他於20世紀30年代在巴黎舉辦了一系列相關主題的著名研討會。

圖為本文作者温·麥科馬克(圖片來源:谷歌圖片)
現代新保守主義思想根源的編年史家沙迪亞·德魯裏(Shadia Drury)認為,科耶夫的黑格爾教義——也強烈引用了尼采的超人思想——對戰後存在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一書中指出,自由資本主義民主滿足了柏拉圖所主張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需求: 資本主義理性的一面促進了渴望獲得物質財富的一方的慾望,而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賦予了其公民政治平等和個人權利的尊嚴。但是,對於尼采模式下,有抱負的超人會對歷史末期的和平造成多大的威脅,福山的態度一直搖擺不定。
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一書中,他事實上將唐納德·特朗普作為一位成功的資本家單獨挑選出來。在該書的論述中,福山認為,特朗普可能仍在尋求超越單純財務成就的肯定,如果他選擇從政,可能會對國家構成威脅。
福山原本是舊的新保守主義學派中的精英悲觀主義者;他在康奈爾大學讀本科時與艾倫·布魯姆(師從利奧·施特勞斯)一起學習西方哲學。但福山似乎終於擺脱了施特勞斯學派新保守派深刻的文化悲觀主義。

著名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圖片來源:谷歌圖片)
**正如福山所指出的,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作為一種普遍信條出現,呼籲將基本政治權利擴大到每一個公民,即使這些權利往往並未得到平等或公正的實施。最近,歷史上被排斥在自由政治秩序之外的亞羣體(subgroups) 組織起來,以實現其作為羣體的平等地位。**其中的一個突出例子,便是同性戀羣體要求身份和承認、爭取同性伴侶婚姻權利的運動。福山還提到了許多其他在歷史上被邊緣化的亞羣體所做出的類似努力,如殘疾人、警察暴力地區的非洲裔美國人、美洲原住民、移民和變性者。他讚揚他們的成就,但也告誡道,如果將美國左翼作為一個運動,或者作為一個整體,以一個不同的、不可滲透的小團體的集合體進行日常工作,是無法運行下去、無法繁榮發展的。
而這正是公民共和主義的用武之地;自由主義作為以普遍權利為基礎的信條的野心似乎屈服於右翼的種族民族主義反應和左翼基於身份的爭取承認的鼓動的壓力,事實證明,共和傳統的特殊、歷史淵源豐富的性質可能更能適應世界不斷變化和激進的政治格局。
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中,自由秩序被設想為政治發展的頂峯,但在那裏,它變得明顯脆弱、守舊和內向,而參與性和地方根深蒂固的共和主義傳統——旨在培養美德和自我犧牲精神,作為對抗邪惡、奢侈和原子式個人主義(atomistic individualism)等腐蝕性力量的公民堡壘——如今正以新的緊迫感向日益脱離的政治時代發出呼聲。
在《身份》這本書中,福山本人也坦言:“民主制度需要公民具有某些積極的美德……”他寫道: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特別警告説,民主社會中的人們很容易變得向內,只關心自己和家人的福利。他認為,成功的民主需要愛國、見多識廣、積極主動、熱心公益、樂於參與政治事務。在這個兩極分化的時代,還可以補充一點,成功的民主還需要人們思想開放、容忍其他觀點,可為了達成民主共識而進行一定讓步。
這是對共和黨政治倫理的完美描述,也是對當今美國政治中最令人遺憾地缺乏的公眾意識的美德的完美描述。
二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92年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的一段中寫道:“實際上,與洛克自由主義的表達是同時代的,這是對由此產生的社會以及該社會的典型產物資產階級的持續憂慮。這種憂慮最終可以追溯到一個道德事實,那就是資產階級主要關心的是自己的物質福利,既不熱心公益,也不講道德,也不獻身於他或她周圍更大的社會。簡而言之,資產階級是自私的。”
這是1989年頗具爭議的論文《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作者提出的奇怪觀點。這本著作最著名的論斷是,蘇維埃帝國(the Soviet empire)及其共產主義制度即將崩潰,標誌着自由民主最終戰勝了所有可能的替代政府制度。然而,即使在該論文最初的闡述中,也有一些線索表明,福山並沒有完全贊同他所聲稱的人類文明所產生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他特別指出了“對自由消費主義社會的客觀性和精神空虛性的普遍不滿”,這暗示着他“自由主義核心的空虛”。
福山還將科耶夫對戰後歐洲國家的判斷概括為“恰恰是那些軟弱、繁榮、自滿、內向、意志薄弱的國家,它們最宏偉的計劃無非是建立共同市場。”科耶夫是福山所提出的歷史終結論的真正創始人,或者更確切地説,他是 G. W. F.黑格爾的一位獨特解釋者。
黑格爾斷言,這位哲學家認為拿破崙在1806年耶拿戰役中擊敗普魯士軍隊的那一刻,正是歷史終結的時刻。科耶夫認為,那一刻標誌着法國大革命原則對歐洲皇室反動勢力的永久勝利。然而,正如沙迪亞·德魯裏所澄清的那樣,科耶夫是通過扭曲的尼采視角來解讀黑格爾複雜的哲學思想的。
黑格爾提出了一種出現於文明開端的主人與奴隸的關係(a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並將歷史的核心動力定義為雙方對人性的共同“對認可(recognition)的尋求”。奴隸沒有得到他想要的認可,因為他的地位低下;主人沒有得到他想要的認可,因為來自下位者的認可毫無意義;只有當他們平等地認可彼此時,他們才能得到所渴望的認可。
科耶夫對黑格爾的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刻的解讀,他將法國大革命解讀為奴隸階級對其主人必然的暴力勝利。和尼采一樣,他也譴責奴隸階級的勝利是原始社會基本動物性的倒退;在原始社會里,人們只關心自己的物質需要,而不關心貴族秩序的更高理想。
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一書中對資產階級秩序的冷嘲熱諷顯然源於尼采的世界觀;尼采對資產階級的嘲諷——“沒有胸膛的人”——在標題“最後之人”的基礎上增加了這個詞,暴露了這場文字遊戲。然而,福山在書中使用的許多術語——如“熱心公益”、“善良”和“更大的社區”——無疑類似於公民共和主義的詞彙。
但在隨後的一本書《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中,他駁斥了古典共和主義作為替代方案的可行性,理由是“它的規模不夠大“。他解釋説,隨着古希臘和古羅馬共和國規模的擴大,“不可能繼續維持將其綁定在一起的苛刻的社羣主義價值觀了。”
**這一判斷是非常明智的,但福山在他的新書《身份》中發現,共和倫理作為一種加強自由主義抵禦身份政治帶來的衝擊的手段,具有重要的價值。**在國外,民族國家主義已經讓以前的民主國家完全反對自由民主,而被美國向多民族社會的快速發展所瘋狂的絕大多數美國右翼白人似乎也想在國內實現同樣的壯舉。
同時,他推測,美國左翼認為多樣性本身就可以被視為一種國家認同。但福山認為,美國的民族身份必須是建立在對自由和民主政治價值觀的堅定信念基礎上。他還認為,僅僅分享一個信念,是不足以完全維持一個民主秩序的: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積極參與的公民,正如公民共和主義所要求的。為此,他建議為所有美國年輕人提供國家服務,這是全美國公民共和黨人衷心贊同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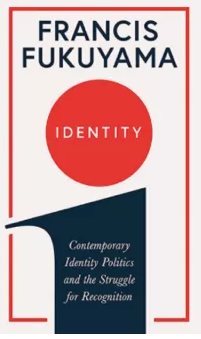
弗朗西斯·福山的研究著作《身份:對尊嚴的需求和怨恨的政治》(圖片來源:谷歌圖片)
“國民服務(National service),”他寫道,“將是一種當代形式的古典共和主義,一種鼓勵美德和公共精神而不是讓公民獨自追求私人生活的民主形式。”或者説,為了迎接歷史終結所帶來的挑戰,我們需要重振歷史上的公民共和主義信條。
(本文原載“法意讀書”微信公眾號,觀察者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