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爾特:美國為何如此不擅長制定外交政策?
【文/斯蒂芬·沃爾特】在剛剛發表的上一篇專欄文章裏,我提到了特朗普政府在中東(尤其是伊朗)問題上表現出的諸多隻有腦死亡患者才具有的特徵。我在文中尤其強調了一點:特朗普政府並不具備“真正的戰略”——清晰的目標以及為了實現該目標制定出的一套能夠將各方可能做出的反應納入預先考慮的條理清晰的行動方案。相反,美國政府在缺乏清晰目標的情況下,只是一味地用蠻力施壓(what we have instead is brute force coercion,divorced from clear objectives),而且主導這一切的還是一位無知而易衝動的總統。

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2020年1月13日在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刊發評論文章:《美國為何如此不擅長制定外交政策》
上任三年以來,特朗普總統成功地增加了戰爭爆發的風險、迫使伊朗逐漸走上重啓核計劃的道路、導致伊拉克要求美國撤軍、在世界各地引發了對美國判斷力和可靠性的廣泛質疑、使我們在歐洲的盟友們陷入驚恐而且還讓俄羅斯和中國看起來似乎成了智慧的象徵和全球秩序的維護者。
特朗普政府顯然認為,刺殺外國官員是實施其外交政策的合法手段(assassinating foreign officials is a legitimate tool of foreign policy),而戰爭罪犯卻被奉為英雄人物(這裏指美國海豹突擊隊員加拉格爾被指控在伊拉克服役期間犯下戰爭罪,他曾在伊拉克街區用機槍進行無差別射擊、持刀刺死一名受傷的未成年“伊斯蘭國”囚犯而且還被控企圖謀殺其他平民以及妨礙司法公正等。2019年7月,美國軍事法庭陪審團認定,對加拉格爾謀殺等罪名指控不成立,加拉格爾最終被降職處理。《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稱,對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陣營來説,加拉格爾事件是轟動的大案,保守派希望把加拉格爾塑造成為戰爭英雄。2019年11月15日,白宮宣佈恢復加拉格爾的軍銜,白宮的這一做法在美國社會引發了重大爭議——觀察者網注),這種做法一定會受到很多流氓政府的歡迎並被他們所效仿。令人遺憾的是,美國的戰略短視(strategic myopia)不僅僅表現在中東地區。
極具重要性的中國問題就是個體現美國戰略短視的典型例證。特朗普政府已經意識到,中國是美國在未來幾十年裏可能遇到的唯一競爭對手(China is the only possible peer competito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likely to face for many decades),特朗普能做到這一點還是值得肯定的。當然,意識到這一點還算不得什麼偉大成就,許多人都能看清這一事實。人們在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挑戰的層級方面也許還存在爭議,但任何一個稍具理性的人都不會不為中國的崛起而感到憂慮。
如果你在中國問題上進行過真正的戰略性思考,那麼你就一定會想辦法讓美國冒最小的風險、以最小的代價對中國的影響力施加限制,你就一定會明白美國無法在不傷及自身的情況下阻止中國經濟繼續增長,你就一定會盡最大努力讓儘可能多的國家在先進技術等關鍵問題上站在美國一邊並防止中國在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等能夠改變遊戲規則的技術領域佔據全球主導地位,你就一定會在亞洲鞏固美國的外交地位並尋找機會在中俄兩國之間打下一根楔子(looking for ways to drive a wedg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你就一定會注意避免被一些次要問題浪費掉寶貴的時間、注意力、資源和政治資本。然而,美國是怎麼做的呢?
首先,特朗普放棄了TPP(即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意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觀察者網注),這一舉動相當於打了其他11個參與國的臉。那份通過努力談判達成的協議本可以給各國帶來經濟利益並讓其他11個參與國在經濟上與美國更加緊密地捆綁在一起。
然後,特朗普對中國發動了貿易戰。特朗普並沒有與其他幾個主要經濟大國協調一致共同對付中國,而是對那些國家也發出了威脅並發動了貿易戰。在中國面前,美國並沒有組織起自己的聯盟,美國手中的槓桿力量被特朗普大大削弱了,美國基本上是在貿易戰的戰場上獨自面對中國。結果自然是容易預料的,兩國達成了挽回顏面的妥協,一切又回到過去,在那些涉及美中競爭的真正重要的問題上,美國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此外,特朗普還在處理美朝關係時上演了一場真人秀。他先是威脅對朝鮮動武,但是在與金正恩的第一次會談之後就被其空洞許諾所矇騙。結果美國在美朝關係上沒有取得任何突破,美國沒能阻止朝鮮推進其核計劃,而且在更廣大的亞洲地區,特朗普的這場真人秀還削弱了各國對美國判斷力的信心。
與此同時,特朗普還在過去三年裏毫無必要地羞辱了一些重要的歐洲盟友並威脅稱美國將脱離北約。不出所料,當美國官員試圖説服歐洲盟友們不要採購中國華為公司的5G通信設備時,許多國家都不予理睬,他們已經沒有心情照顧特朗普的面子了。而一些中國人卻很快抓住了特朗普不斷犯錯的良機,他們向歐洲人表明,中國比美國更支持多邊主義和技術開放政策。此外,中國還特別強調了自己對特朗普曾愚蠢地退出的巴黎氣候協定的支持。“中國人已經公然聲稱,與歐洲擁有更多共同價值觀的是中國而非美國。此外,他們還頻頻對歐洲公眾表示,與美國不同,中國相信氣候變化的事實,中國支持多邊主義。中國人的此類言論在像德國這樣的國家是非常有市場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朱麗安·史密斯(Julianne Smith)説。
下面我們來看另一個領域的問題。當美國在此領域的地位做自由落體運動時,中國的地位卻在迅速攀升。中國如今在全球擁有的大使館、領事館以及其他駐外機構的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前副國務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指出:“國際競爭正在加劇,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外交事務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時代……中國意識到了這一點而且正在快速強化自己的外交力量,而美國卻在進行單方面的外交裁軍”。正如我此前曾指出的,如果美國希望在亞洲平衡中國的影響力,那麼美國就需要與亞洲國家保持牢固的關係,而這就需要美國認真且耐心地展開一系列老練、富於智慧的外交活動。美國應該認識到,外交力量是一種與軍事力量同樣重要的可以依靠的實力。
最後,特朗普政府並沒有十分審慎地以漸進的節奏從中東撤出並代之以權力平衡策略(美國自二戰後到冷戰結束一直成功地應用了這一策略),反而被中東地區的一些附庸國、有錢的捐贈者和鷹派顧問們(local client states,wealthy donors,and hawkish advisors)裹挾着對伊朗採取了毫無意義的對抗政策。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北京的一些外交事務決策者在看到美國竟然跌跌撞撞地自己走入這樣一片沼澤地時一定露出了會心的笑容。
簡而言之,雖然特朗普政府已經意識到一個挑戰美國的中國是其外交議程上最為重要的待處理問題,但他們所執行的一系列政策卻像是為了讓中國取得儘可能多的對美優勢而量身設計出來的。
不過,這還算不得什麼壞消息。雖然特朗普政府把美國“無戰略”的困境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但這個問題並不是特朗普入主白宮後出現的,人們實際上早已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存在。克林頓政府曾認為,美國能夠推動北約東擴、對伊拉克和伊朗同時進行壓制、讓中國過早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bring China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rematurely)、在不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情況下把無所顧忌的過度全球化向前推進(promote hyperglobalization with abandon yet never face serious negative consequences)。小布什政府曾認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中心任務應該是結束世界各地邪惡政權的苛政,而美軍能夠很快將中東地區變為親美民主政權的集中地。克林頓比小布什要幸運一些,因為他任內製造的一些問題的負面影響在他卸任後才逐漸顯現出來。不過這兩位總統有一個共同點——美國的全球地位在他們卸任時都變得更加衰落了。
奧巴馬政府對美國的實力有更加現實的判斷,他在外交領域也用力不少,但他在削減美軍海外行動方面做的並不多。實際上,他認為美國應該積極地使用軍力。奧巴馬曾於2009年向阿富汗增兵、支持利比亞和敍利亞的政權更迭並通過無人機和特種部隊擴大了對恐怖分子進行定點清除行動的規模。奧巴馬政府沒有預料到西方把烏克蘭拉向歐盟和北約時俄羅斯將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奧巴馬政府也沒有在氣候變化和伊朗核問題上在國內取得共識。我們不應忘記,在奧巴馬白宮歲月的最後一年裏,美軍向全世界七個不同的國家一共投擲了約2.6萬枚炸彈。
到底發生了什麼?美國的戰略水平是什麼時候開始下降的?制定對外戰略是一項有挑戰性的工作,不確定性和犯錯都是難以避免的正常現象。但美國並不是天生就不擅長進行戰略性思考的。杜魯門政府曾在二戰結束後面臨大量挑戰,然而他卻成功制定了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出台了馬歇爾計劃、創建了北約、在亞洲構建了多個雙邊聯盟並建立了使美國及其盟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都大受其益的國際經濟秩序。與杜魯門政府相似,老布什政府(1989-1993)也以令人驚歎的敏鋭、專業和剋制態度處理了蘇聯解體、兩德統一以及第一次海灣戰爭等事件。當然,杜魯門政府和老布什政府並不是無可指摘的,不過他們在面對複雜問題和全新情況時的表現證明,他們知道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他們有能力從盟友和敵人那裏獲得希望獲得的反應。換句話説,杜魯門和老布什都是非常善於進行戰略性思考的政治家。
看起來有些矛盾的是,我們今天所遇到的問題部分是由美國在冷戰後獲得的一超獨霸地位所導致的。美國是如此強大、富裕、安全,這使得美國通常能夠免於受到自身行為所產生的後果的影響(it is mostly insulated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own actions)。當美國犯錯時,錯誤所造成的後果往往是由其他國家承擔的(when it makes mistakes,most of the costs are borne by others),而且美國還從未遇到過一個能夠迅速對美國的錯誤加以利用的競爭對手。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給美國帶來的損失可能將不只是6萬億美元的軍費和數千條美軍士兵的生命。由於在此期間沒有進行徵兵,公眾對美軍死亡情況的憂慮情緒並未出現激化。在軍費開支方面,美國是通過在國外銷售債券支付戰爭費用的,雖然這進一步增加了美國的債務負擔,不過為此買單的將是未來世代的美國人。
這就是美國公眾對國外情況以及政府的外交活動缺乏興趣的原因。黛安·黑森(Diane Hessen)自2016年至今一直在對500名美國人進行深度跟蹤採訪,她指出,“大多數美國選民並不太關心美國的對外政策,這的確是一個問題”。此外,近期的一些問卷調查曾要求參加者列出關於美國最為關心的問題,對外政策甚至都沒能進入前10位。當大多數美國人無法就美國的對外政策是成功還是失敗(即便僅着眼於政策的短期可見影響而言)做出判斷的時候,美國的對外政策制定者就不會迫於壓力去制定真正有效的政策,於是他們就僅僅滿足於擺擺姿態而不是真正去追求政策的實際效果(policymakers will be under less pressure to come up with strategies that actually work and posturing will take precedence over actual performance)。
此外,傲慢自大也是原因之一。美國人一直以來都將自己的國家視為全世界的楷模,冷戰的勝利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這一信念,他們似乎相信美國有一種能夠在世界上取勝的魔法。美國人甚至認為其他國家的人們也都與自己有一樣的看法,認為他們都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迫不及待地希望美國能夠帶領他們、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國家也能夠變得像美國一樣。而美國的政治家們也都認為,美國已經站在了歷史的潮頭之上,美國正在推開新世界的大門。當歷史的大勢都在自己一邊時,誰還會去認真地制定一套條理清晰、巧妙複雜的外交戰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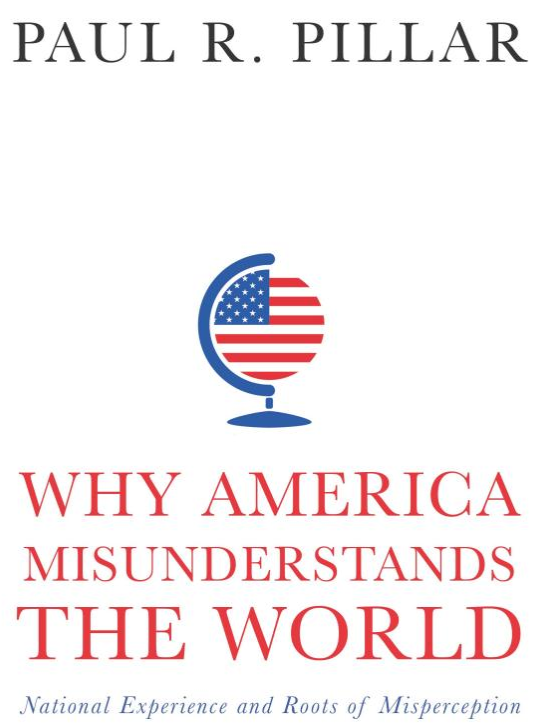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保羅·皮勒所著《美國誤解世界的原因——國家經驗與錯誤認識的根源》一書封面
保羅·皮勒(Paul Pillar)在其重要著作《美國誤解世界的原因——國家經驗與錯誤認識的根源》(Why America Misunderstands the World:National Experience and Roots of Misperception)一書中指出,“美國獨特的歷史經驗、地理上的孤立狀態、龐大的國內市場以及普遍的無知削弱了其制定切實可行的外交戰略的能力”(the United States’unusual historical experience,geographic isolation,large domestic market,and general ignorance has weakened its ability to fashion viable foreign-policy strategies)。若要制定有效的外交戰略,需要決策者對其他國家可能的反應做出預判,但美國的官員們一般來説對那些他們試圖施加影響的國家知之甚少,更不要説一般的美國民眾了。美國社會向來認為,來到美國的新移民願意接受自己美國人的新身份、願意儘快融入到美國社會中去,這種長期存在的“民族熔爐”概念對美國人構成了誤導,使他們低估了民族特性、種族特性在其他社會里的巨大力量,這導致美國人對其他多元社會里的國家認同建設的難度認識不足。此外,美國人普遍認為美國在世界上的行為從動機上來講是高尚的、正義的,美國因此難以意識到其他國家其實有理由質疑美國的動機或有理由認為美國對自己構成了威脅。上述兩點對美國製定有效的外交戰略構成了嚴重障礙,尤其是當面對那些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與美國有着巨大差異的國家時,這兩個盲點導致的問題尤其嚴重。
在另一方面,美國民主體制的一些重要特徵也使得制定和執行有連續性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政策變得異常困難。在缺乏明確的、能夠吸引人們關注的外部威脅時(此時人們不會對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發生的爭議過於強調原則性),情況就更是如此。在社會大眾對外交政策漠不關心的情況下,政策的制定過程很容易受到國內和國外遊説集團的影響,尤其是考慮到在今天這個時代,金錢在政治中正發揮着核心作用。與那些經過仔細誠懇辯論過的政策方案不同,美國的外交政策往往受到那些聲音大、資金實力雄厚的人士或者一小部分富豪捐贈者的個人偏好的影響。我此前曾經指出,在現代世界的歷史上,美國很可能比任何主要大國都更加容易受到外國的影響(the United States is probably more vulnerable to foreign influence than any great power in modern history)。如果那些特殊利益集團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例如增加國防預算、對人權事務更多的關注、撕毀氣候變化協議、對一些附庸國進行無條件的支持等),美國製定出有利於自身國家利益的整體性戰略的能力將遭到極大削弱。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結果不過是美國在兑現對那些特殊利益集團的承諾時有些手忙腳亂,而最壞的結果則可能是為了兑現那些承諾,美國的諸多政策互相矛盾,最終導致美國國家的失敗。
在理想的情況下,負責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的機構應該能夠從過往的工作經歷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但是經過仔細研究後我發現,當今美國的外交部門毫無責任感可言(there is little accountability in today’s foreign-policy establishment)。無論經過多少次批駁,錯誤的觀點仍有市場。多次犯過錯誤的人獲得了升遷,而那些工作表現出色的人卻往往會被邊緣化。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那些構思、兜售“發動一場伊拉克戰爭”觀點的人以及那些把這場戰爭搞砸的人如今都成了備受尊敬的人物,其中一些甚至將在未來進入軍中服役。此外,《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評論版還增加了支持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專欄作者的人數,但對於那些曾正確預測到戰爭將成為一場災難的專欄作者,這幾家報紙卻並沒有給予太多版面。如果制定糟糕戰略的人不付出代價,而提出好建議的人卻得不到認可,那麼誰還會認為這個國家將會變得越來越好呢?
美國已經從一個共和國逐漸轉變為一個在世界上四處干預的全球性帝國,而人們很難不把美國存在的上述問題與這一轉變聯繫在一起。美國的締造者們曾發出警告:一個共和國在被捲入持續不斷的戰爭後必將墮落。他們是正確的。五星上將、前總統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Dwight D.Eisenhower)對這一點也有較為深入的認識。不斷地發動戰爭需要一個國傢俱備強大的國家安全體系、更加嚴格的政府保密機制以及逐漸擴張的行政力量(to wage war constantly requires powerful 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ever greater government secrecy, and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executive power)。在今天的美國,三權分立制度遭到侵蝕,國內法和國際法被無視,部分媒體被操縱,表達不同意見的人被消聲或被邊緣化,總統和他的僕從們則發現為自己的政策贏得公眾支持或保持自己的民意支持率而説謊正在變得越來越容易。一旦公共話語變得低劣進而脱離現實,制定一套能夠在現實世界裏可行的戰略將變得不再可能。
正如我此前在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的,我們已經落入這樣一個境地: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政策更像是一種行為藝術(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more like performance art)。對除了執行具體任務的陸海空三軍將士和外交官們以外的美國領導人們來説,美國國家行為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已經變得不再重要。美國的領導人們唯一關心的是事情在電視上、在推特上、在娛樂至死的選民們(他們對接受啓發、獲得教益不感興趣,對如何選出一位能幹的領袖也不感興趣)面前會呈現出怎樣的效果。美國仍然是一個非常強大、安全的國家,美國沿着當下的道路也許還能向前走很久。但美國無法永遠走在這條道路上。美國將失去很多能夠讓自己變得更加安全、更加繁榮的機會,美國最終將無法成為那個符合自己崇高理想的國家。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1月13日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