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格雷:只有認識到自由社會的脆弱性,我們才能維護它的基本價值
【文/約翰•格雷 翻譯/宋懿達】
全球化的高峯時代已經結束。對於我們這些未能身處“戰疫”前線的人來説,釐清思路,思考如何在一個已然生變的世界中生活,是我們面臨的首要任務。
荒涼的街道將再次人流如注,我們也將蜷縮在屏幕後,獲得一絲解脱。但世界將不同於人們在平常年代裏所想象的那樣——如果這一切沒發生,這世界也許依然處在一種穩定的平衡中。但這也並不是這種穩定平衡中的一個臨時的不均衡點:我們所經歷的此次危機,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
全球化高峯時代已經結束。一個依賴全球生產和長期供應鏈的經濟體系正在轉變成一個聯繫不那麼緊密的體系。流動不息曾是往日生活的主旋律,經此一“疫”,這種狀態會逐步停轉。我們的生活將比以前變得更加虛擬,也更受制於現實。一個越來越碎片化、但在某些方面更具彈性的世界正在形成。
曾經強大的英國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迅速重構。在議會授予的特殊時期權力之下,政府已把正統的經濟觀念拋到了天邊。在多年緊縮政策的刺激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如武裝部隊、警察、監獄、消防隊、護理人員和清潔工)都面臨着險境。有了醫護人員的無私奉獻,病毒總會被制服。所幸的是,英國的政治制度還完好無損,但沒有多少國家能如此幸運——全世界的政府都在控制病毒和拯救經濟之間苦苦掙扎——其中的許多國家可能會被此次疫情擊垮。
在進步思想家所堅持的未來觀中,未來是對過去的美化。毫無疑問,這有助於他們保持清醒。它還破壞了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屬性:適應和創造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全球市場一度陷入了混亂無序之中,接下來的任務是建立更加堅韌,更適合人類居住的經濟和社會。
這並不意味着我們要轉向小規模的地方主義。人口數量太大,地方自給難以實現,此外大多數人都不願重返過去那些遙遠閉塞的小社區。但是,過去數十年的高度全球化也不會捲土重來。新冠疫情揭露出了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改革後的經濟體系的致命弱點。自由資本主義破產了。
在所有關於自由和選擇的論述中,自由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實驗,它試圖消除社會凝聚力和政治合法性,並承諾用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來取代前者。這個實驗現在已經成功了。抑制病毒需要暫時性的經濟停擺,但當經濟重新啓動時,世界各國政府將採取行動遏制全球市場。
當世界上大量的基本醫療用品都來自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時候,這種情況對一個國家而言都是不能容忍的。出於對國家安全問題的考慮,敏感產業的生產活動將重獲支持。無論在現在還是將來,像英國這樣的國家可能會逐步停止農業生產,並依賴進口食品的説法,都是一派胡言。隨着人們出行的減少,航空業將萎縮。邊境管控愈加嚴格,這會成為全球格局的一個持久性特徵。狹隘的經濟效率目標也將不再適用於政府。

中國對外支援醫療物資
問題是,究竟誰將取代不斷提高的物質生活水平,成為社會的基礎?環保主義者給出的一個答案是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中所説的“穩態經濟”(stationary-state economy)。擴大生產和消費將不再是壓倒一切的目標,人口數量的增長也將受到抑制。
與當今大多數自由主義者不同,穆勒認識到了人口過剩的危險。他寫道,一個到處都是人類的世界,將會是一個鮮花遍佈的荒原和野生動物都不復存在的世界。同時他也明白中央計劃經濟的危險。穩態經濟將是一個鼓勵競爭的市場經濟。技術將在這個經濟環境下持續創新,人們的生活質量也會隨之提升。
在許多方面,這是一個吸引人的願景,但它是不真實的。正如沒有一個世界級的權威能對抗病毒一樣,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權威能停止經濟增長。與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最近反覆強調的進步口號相反,全球性問題並非總有一個全球性的解決方案。地緣政治劃分排除了任何類似全球政府的存在的可能。若有這樣一個政府存在,其他國家將爭相試圖控制它。認為這場危機可以通過前所未有的國際合作來解決的想法,是最純粹的異想天開。
當然,經濟不可能無限期持續擴張。首先,經濟擴張會加劇氣候變化,把地球變成一個垃圾場。但由於生活水平的極不平衡,以及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地緣政治競爭會不斷加劇,零增長也同樣難以為繼。如果一個國家接受經濟增長的極限,那是因為該國政府把保護公民作為其首要目標。不論民主的還是專制,那些不能應對這一霍布斯主義考驗的政府都將垮台。
這場疫情也加劇了地緣政治的變化。伴隨着油價暴跌,病毒在伊朗不受控制的傳播可能動搖其神權政體。隨着政府收入的鋭減,沙特阿拉伯也面臨着風險。毫無疑問,許多人都希望這兩個國家都能擺脱困境。假如海灣地區崩潰,一定會發生長期的混亂,但誰也不能保證除此之外還會產生什麼其他後果。儘管多年以來多元化一直在被探討,但這些政府仍然被石油所主導。即便油價有所回升,全球停產對經濟的打擊也將是毀滅性的。
相比之下,東亞的發展仍將繼續。迄今為止,對這一流行病最成功的應對措施是在台灣地區、韓國和新加坡。他們強調集體福祉而非個體自治的文化傳統確實促進了“戰疫”成功。他們還抵制了對最小國家(minimal state)的崇拜。如果他們比許多西方國家更好地適應去全球化的趨勢,那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的立場更為複雜。正如新的NHS南丁格爾醫院所(英國的“方艙醫院”)展示的,可以在兩週內建立醫院的不僅僅是中國。沒有人知道中國經濟停擺的全部人員成本。即便如此,中國正在通過幫助像意大利這樣陷入困境的國家政府,來取代歐盟的角色。
歐盟對這場危機的反應是暴露了其本質上的弱點。沒有什麼思想比主權更能受到高層人士的蔑視。在實際操作層面,主權意味着有能力執行在英國和其他國家正在實施的全面、協調和靈活的應急計劃。這些已經採取的措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任何措施都要大。最重要的是,這與當時的情況相反,當時英國人口前所未有地被動員起來,失業率急劇下降。如今,除了一些核心服務業,整個英國已經停工。如果持續數月,停擺會使英國經濟更加的社會主義化。
歐盟陳舊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是否能做到這一點(各個國家所達成的成就)值得懷疑。如今,通過歐洲央行(ECB)的債券購買計劃和放寬對國家工業援助的限制——過去“神聖不可侵犯”的規則已被改寫。但是歐洲北部國家(諸如德國和荷蘭)拒絕分擔財政壓力,可能會阻擋對於意大利的經濟援助。
雖然意大利比希臘大,不會像希臘那樣經濟全線崩潰,但是如果要拯救其經濟,對歐盟來説代價也將過於巨大。正如意大利總理朱塞佩•孔戴(Giuseppe Conte)在3月份所説:“如果歐洲不能迎接這一前所未有的挑戰,整個歐盟的結構就失去了它為民服務的根本存在理由。”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達•武西奇(Aleksandar Vucic)更為直率和現實:“歐洲不存在團結,這是一個童話。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唯一能幫助我們的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歐盟其它成員國,謝謝你們啥忙也沒幫)。”
歐盟的根本缺陷在於,它無法履行一個國家所具有的保護職能。人們經常預言歐元區解體,這似乎令人難以想象。然而,在他們今天面臨的壓力下,歐洲機構的解體並非空談。人們的自由活動已經被關閉。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最近還以將允許移民過境來威脅歐盟。敍利亞伊德利卜省的淪陷,還可能導致數十萬、甚至數百萬難民逃往歐洲。(社區隔離在規模巨大、過分擁擠和衞生堪憂的難民集中點將變得無法想象)歐元的崩潰,再加上一場移民危機的壓力,對歐盟而言可能是致命的打擊。
如果歐盟得以倖存,它可能會像末年的神聖羅馬帝國一樣,成為一個遊蕩的幽靈——但是它卻不能自主行使權力。民族主義國家已經做出了至關重要的決定。由於作為政治中心的歐盟不再是主導性力量,並且失敗的歐盟項目往往與左翼人士相關,許多政府因此轉向了極右翼領導。
俄羅斯將對歐盟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在2020年3月與沙特產生的關於油價暴跌的鬥爭中,普京展示出了他強硬的一面。對於沙特來説,為了支付公共服務和保持國家償債能力,維持其財政收支達到平衡的石油價格約為每桶80美元,而對於俄羅斯來説,可能還不到一半。同時,普京也正在鞏固俄羅斯作為能源大國的地位。貫穿波羅的海的北溪(The Nord Stream)海上天然氣管道為歐洲提供了可靠的天然氣供應。俄羅斯將利用歐洲對其的依賴,使得能源成為一項政治武器。隨着歐洲的碎片化,俄羅斯似乎也在擴大其勢力範圍。無獨有偶,中國也在介入,向意大利空運醫生和設備,以取代搖搖欲墜的歐盟。
在美國,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顯然認為,重塑經濟比遏制病毒更為重要。1929年那樣的股市下滑,或者比上世紀30年代更糟的失業率,對他的總統任期構成了嚴重威脅。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首席執行官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表示,美國失業率可能達到30%,這一水平要高於大蕭條時期。另一方面,在美國政府的分權體制下,昂貴的醫療保險和數千萬沒有保險的人、龐大的監獄人口(其中許多是老年人和體弱者),城市中大量的流浪漢,加上如鴉片一般已經傳播很廣的流行病——減少停業可能意味着病毒失控地傳播,這會給美國帶來毀滅性的影響(但敢於冒此風險的不止特朗普一人,瑞典迄今為止也沒有實施類似於其他國家的封鎖措施)。
與英國的救助計劃不同,特朗普的20萬億美元刺激計劃主要是另一項針對企業的救助計劃。然而,如果要相信民調結果,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贊成他對這場流行病的處理方式。如果特朗普能夠在美國多數黨的支持下走出這場災難呢?無論他是否繼續掌權,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都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迅速瓦解的不僅是近幾十年來的超全球化,還有二戰結束時建立的全球秩序。病毒打破了人們想象中的平衡,加速了一個已經進行了多年的解體過程。
芝加哥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在其開創性的《瘟疫與人》一書中寫道:一直以來,一些迄今不為人所知的寄生生物都有可能逃離其温牀,使已經成為地球霸主的人類面臨着某種新型的、可能帶來毀滅的死亡風險。
至於新冠病毒是如何離開它的温牀的,目前尚不清楚。儘管有人懷疑販賣野生動物的武漢“生鮮市場”可能是這場疫情的罪魁禍首。1976年,當麥克尼爾的首版著作問世時,人類對外來物種棲息地的破壞遠遠不如今天。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傳染病傳播的風險也在增加。在1918-1910年的西班牙,一個當時大規模航空運輸尚不存在的世界裏,流感也成為了一種全球性的流行病。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表達了歷史學家對瘟疫的理解,他説:“對他們而言,偶發的災難性傳染病仍然是突然且不可預測的,基本上超出了歷史的解釋。”許多後來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然而,這種觀點還認為,流行病只是曇花一現,它並非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背後是一種信念,即相信人類不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可以創造一個獨立於生物圈其他部分的自主生態系統。新冠病毒(COVID-19)告訴他們,不能——只有運用科學,我們才能抵禦這種病毒。大規模抗體測試和疫苗將是至關重要的。但要想在未來不那麼脆弱,就必須對我們的生活方式進行永久性的改變。
日常生活的結構已經改變了,脆弱感無處不在。不穩定的不僅僅是社會——人類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是如此。病毒的形態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人類的缺失。野豬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鎮遊蕩,而在泰國的羅布裏,無人餵養的猴羣在街上打架。在被病毒佔領的城市中,非人的美麗和激烈的生存鬥爭正在上演。

英國遊樂設施無人玩,羊羣“霸佔”大轉盤
正如許多評論家所指出的,巴拉德(JG Ballard)小説中所描繪的“後啓示錄”式的未來已經成為了現實。但重要的是要理解這個“啓示錄”揭示了什麼——對巴拉德來説,人類社會是隨時可能被推翻的舞台道具。當你離開劇院時,那些似乎是建立在人性中的規範就消失了。
在20世紀40年代,巴拉德的童年時代,最令他痛心的不是在監獄裏——那裏的許多囚犯對待他人都是堅定和藹的。身為一個足智多謀、敢於冒險的男孩,巴拉德很享受在獄中的大多數時光。他告訴我,當戰爭接近尾聲,營地倒塌的那一刻,他卻目睹了人們無端的殘忍,以及最自私冷酷的一面。
巴拉德得到的教訓是,這些都不是世界末日——被描述為末日的往往是正常的歷史進程。許多人留下了持久的創傷。但人類這種動物是如此強壯、適應性強,根本不會被這些動盪打倒。就算和以前不同,生活還會依舊繼續。那些宣稱這是一個“巴拉德時刻”(譯者注:指巴拉德小説和故事中描述的反烏托邦的現代性、荒涼的人造景觀以及技術、社會或環境發展的心理影響)的人們沒有注意到,在作者描繪的極端情況下,人類是如何進行調整,甚至得到滿足的。
技術會幫助我們適應目前的困境。通過將我們的許多活動轉移到網絡中,可以降低現實中的流動性。辦公室、學校、大學、全科醫生手術室和其他工作中心可能會永久性改變。在流行病期間建立的虛擬社區使人們能夠比過去更好地瞭解彼此。隨着大流行的消退,人們將舉行慶祝活動,但感染病毒的威脅何時能結束,還沒有明確的跡象。
許多人可能會遷移到像“第二人生”那樣的在線環境——一個人們在自己選擇的身體和世界中相遇、交易和互動的虛擬世界。其他方面的改變可能會讓道學家們感到不適。網絡色情很可能會繁榮起來,許多網絡約會可能包括性接觸,而這些交流永遠不會以身體的相遇而結束。增強現實技術可以用來模擬這種接觸,虛擬化的性行為很快就會成為常態。這是否是邁向美好生活的一步,也許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網絡空間依賴於可能被戰爭或自然災害破壞的基礎設施。互聯網使我們能夠避免類似過去瘟疫所帶來的孤立,但肉身必朽,人類的進步也必然會反噬自身。
病毒不但告訴了我們,進步是可逆的(這一事實甚至連那些進步人士都明白了),而且它還有可能自我破壞。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全球化帶來了一些重大利益,數百萬人擺脱了貧困。但這一成就現在受到威脅,全球化還招致了目前正在上演的去全球化。
隨着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景逐漸暗淡,其他權威和合法性的來源正在重新出現。進步的思想——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都強烈地厭惡民族主義。歷史上的很多例子可以證明它是如何被濫用的。但民族國家正日益成為推動大規模行動的最強大力量。對付病毒需要一種不是為了“全人類”而動員起來的集體努力。
利他主義和增長一樣受到限制。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刻還沒有結束之前,無私奉獻的事例將會湧現。在英國,已經有超過50萬人的志願軍報名幫助國民醫療服務體系。但是僅靠人類的同情來幫助我們渡過難關是不明智的。對陌生人的善意是如此珍貴,以至於它必須定量配給。
這就是保護狀態的來源。本質上,英國一直是霍布斯式的國家。和平與強有力的政府一直是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同時,這個霍布斯主義國家主要依賴於協商一致,尤其是在國家緊急的狀態下。躲避危險,要勝過受到政府幹預所導致的不自由。
當新冠疫情流行達到頂峯時,人們想要多少自由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強制團結毫無興趣,但為了更好地保護自身的健康,人們可能願意接受這項生理監測制度。為了在此次危機中自救,我們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具有高度創造性的國家干預。政府將不得不在發展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上做更多的投入。儘管國家在規模上不會總是擴張,但其影響將是普遍的。按照舊世界的標準,它將越來越具有侵略性。在可預見的未來,後自由主義政府將成為常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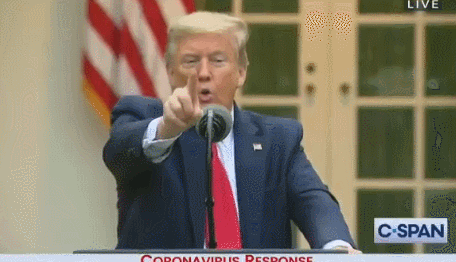
只有認識到自由社會的脆弱性,它們最基本的價值才能得到維護。除了公平外,它還包括個人自由,而個人自由本身也是對政府的必要制約。但那些相信個人自主權是人類最內在的需求的人,卻暴露了他們了對心理學的無知——尤其是他們自己的心理。因為對幾乎所有人來説,(相比個人自由)安全和歸屬感同樣重要——甚至往往更重要。
實際上,自由主義是對這一事實的系統化的否定。隔離的一大好處是可以藉機重新思考。釐清頭腦中的紛亂思緒,想想如何活在一個變化的世界,是我們當前的任務。對於我們這些沒能身處“戰疫”前線的人來説,這段時間足夠了。
文章來源:
John Gray, Why this crisis is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Newstatesman, April 1, 2020.
網絡鏈接:
https://www.newstatesman.com/international/2020/04/why-crisis-turning-point-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