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帕克:我們生活在一個失敗國家
【文/ 喬治·帕克 譯/ 聽橋】
新冠病毒到來時,發現了一個基本狀況危險的國家,並無情利用了那些狀況。腐敗的精英階層,僵化的官僚體制,冷酷無情的經濟,四分五裂且心煩意亂的公眾,——這些慢性病多年來一直得不到治療。我們早就學會了彆彆扭扭地容忍這些症狀。要用如此規模的一場大流行病和與這流行病的親密接觸,那些症狀的嚴重性才得以暴露,使美國人震驚地意識到,我們眼下屬於高風險類別。
這危機要求我們在全國層面快速展開理智的集體行動。但相反,美國的應對是巴基斯坦或白俄羅斯式的,就像是個基礎設施敗壞、政府功能失調的國家,其一眾領導人太過腐敗和愚蠢,乃至於無法阻擋大眾蒙受苦難。行政分支浪費了無法挽回的兩個月準備時間。總統有意視而不見,嫁禍他人,誇誇其談,謊話連篇。從他的喉舌那裏,則冒出一個又一個陰謀論和神奇療法。一些參議員和企業高管行動迅速,但不是要預防即將到來的災難,而是要從中獲利。當有政府醫生試圖警告公眾有多麼危險時,白宮拿走了話筒,把那條消息政治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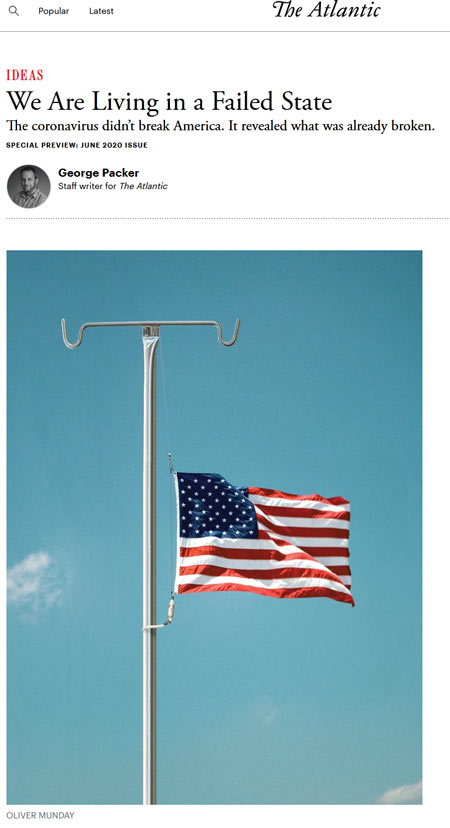
在沒完沒了的3月間,美國人每天早上醒來,都發現他們自己成了一個失敗國家的公民。沒有全國性計劃,根本沒有一以貫之的指導方案:家庭、學校和辦公場所都被告知,它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關閉和尋求庇護。檢測工具、口罩、醫護服裝和呼吸機的供應嚴重短缺,各州州長懇請白宮提供這些物品,遭搪塞後,又向私人企業發出呼籲,而它們無法交貨。各州和各市被迫陷入投標大戰,這讓它們成了漫天要價和企業逐利的犧牲品。民眾拿出他們的縫紉機,竭力維持醫院工作人員的健康和病人的生機。俄羅斯、台灣和聯合國向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國,一個陷入徹底混亂中的乞丐國家,送來了人道主義援助。
唐納德·特朗普幾乎完全從個人和政治角度看待這場危機。因為擔心連任,他宣佈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為一場戰爭,而他自己是戰時總統。但他令我們腦海中浮現的領袖,是法國將軍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etain)元帥。1940年,德國擊潰法國防禦力量後,貝當與德國簽署了停戰協議,隨後組建了親納粹的維希政權。特朗普就像是貝當,與入侵者勾結,將他的國家拋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災難。2020年的美國更像是1940年的法國,已經用一場崩潰令自己目瞪口呆;相較於一位可悲的領袖,這場崩潰來得規模更大、程度更深。
未來,人們在剖析這場大流行病時,可以借用歷史學家、抵抗運動戰士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對同時期法國淪陷的研究,稱其為“不可思議的失敗”(Strange Defeat)。
儘管在全美國,個人展示勇氣和犧牲的例子數不勝數,但失敗是全國性的,而且理當迫使我們提出一個大多數美國人從不曾必須問到的問題:我們是否足夠信任我們的領導人和彼此,可以召喚人們以集體方式應對某次致命威脅?我們依舊有能力實施自治嗎?
從9·11到金融危機
這是這個短促二十一世紀經歷的第三場重大危機。
第一場發生在2001年9月11日,那時,美國人從精神上講還生活在前一個世紀,經濟衰退、世界大戰和冷戰的記憶依舊強悍。那一天,中部農業腹地的民眾沒有將紐約視作理當承受那般命運的外邦移民和自由派人士的熔爐,而是視作一個為整個國家承受了打擊的偉大美國城市。來自印第安納州的消防隊員驅車八百英里,為在世界貿易中心廢墟的救援行動施以援手。市民的本能反應是共同哀悼,齊心動員。
黨派政治和危害嚴重的政策,尤其是伊拉克戰爭,抹去了國家團結的意識,催生了對精英階層的怨恨,這種怨恨從未真正消失。發生在2008年的第二次危機加劇了那種怨恨。在最頂層,金融崩潰幾乎可以被認為是一次成功。國會通過了一項兩黨都接受的救助法案,挽救了金融系統。即將離任的布什的行政官員與即將上任的奧巴馬的行政官員展開了合作。美聯儲和財政部的專家們運用貨幣和財政政策,防止了第二次大蕭條的發生。一些最重要的銀行家遭到羞辱,但沒有被起訴;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保住了自己的財富,一些人保住了工作。沒過多久,他們的業務就回歸正常。一位華爾街交易員告訴我,那場金融危機早就成了“減速帶”。
身處中間層和底層的那些債務纏身,失去了工作、房子和退休儲蓄的美國人,感受到了所有揮之不去的苦楚。他們中間的很多人從來沒有恢復元氣,在那場蕭條中成年的年輕人註定比他們的父輩更加貧窮。不平等作為1970年代晚期以來美國人生活中的一支基礎性的無情力量,變得更加嚴重了。
第二場危機在美國人中間,在更上階層和更下階層、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大都市人和農村人、土生土長的人口和移民、普通美國人和他們的領導人之間,製造出了深刻的隔閡。社會關係承受着越來越大的壓力,這種情況已有數十年,現在它們開始撕裂。奧巴馬執政時期的一些改革舉措儘管在醫保、金融監管、綠色能源等方面意義重大,但僅有權宜之效。過去十年的長期復甦,富了企業和投資者,但欺騙了專業人士,且將工人階級更遠地拋下。經濟衰退的持久影響是,加劇了兩極分化,令權威,尤其是政府的權威,聲譽掃地。
兩黨都遲遲未能領會到,他們的公信力喪失了多少。即將到來的政治是民粹主義的,其先兆並非貝拉克·奧巴馬,而是薩拉·佩林(Sarah Palin),這位毫無準備到荒謬程度的副總統候選人對專業知識嗤之以鼻,並陶醉在名人效應中。她是唐納德·特朗普的“施洗者約翰”(John the Baptist)。(薩拉·佩林,生於1964年,2006年12月至2009年7月間擔任阿拉斯加州州長,是該州歷史上最年輕且為女性的州長,共和黨人。施洗者約翰,是公元一世紀早期的一位猶太巡迴傳教者。——譯註)
特朗普行政分支:謊言和腐敗
特朗普是作為共和黨建制派的反對者登上權力寶座的。但保守派精英階層和這位新領袖之間很快達成了諒解。無論他們在貿易和移民之類問題上有何種分歧,他們的基本目標都是共同的:為謀取私人利益而赤裸裸地開掘公共資產。那些希望政府儘可能少為共同利益做事的共和黨政客和捐款人,可以與一個全然不知如何統治國家的政權愉快共處,而且自己充當了特朗普的僕人。
特朗普就像一個在乾燥的田野上扔火柴的男孩那樣肆意,開始犧牲美國人殘存的市民生活。他甚至從來都沒有假裝自己是整個國家的總統,而是挑動我們,圍繞種族、性別、宗教、公民身份、教育背景、地域,以及——在他上任以來的每一天——政黨問題,互相爭鬥不止。他的主要統治工具是謊言。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人將自己鎖在一個佈滿鏡子的大廳,認為那就是現實;有三分之一的人因堅持認為真理可知,而自己發瘋了;另有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放棄了嘗試。
持續多年的右翼意識形態攻擊,兩黨都在推動的政治化,加上持續的資金缺乏,已嚴重戕害特朗普斬獲的聯邦政府。他開始着手摧毀總統這項工作,破壞專業的公務員隊伍。他趕走了一些最有才華和經驗的職業官員,留下一些重要崗位無人填補,並安插了忠於他的人士充當政委,凌駕於飽受恐嚇的倖存者之上,目的是:服務於他自己的利益。他的主要立法成果是減税法案,作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税行動之一,這部法案為大企業和富人送去了數千億美元。受益者成羣結隊,到他的度假勝地消費,排隊為他的連選提供資金。假如撒謊是他運用權力的手段,那麼腐敗就是他的目的。
這就是呈現在新冠病毒面前的美國景觀:在繁榮的城市,一羣與全球各處聯絡的辦公室工作人員依賴一羣朝不保夕、隱匿無形的服務業工人;在農村地區,衰敗的社區反抗着現代世界;在社交媒體上,不同陣營之間充斥着相互仇恨和無休無止的謾罵;在經濟領域,儘管就業充分,但成功的資方和受困的勞工之間存在巨大且不斷拉大的差距;在華盛頓,一個由騙子和他智力破產的政黨,在領導一個無效的政府;在這個國家各個地方,瀰漫着一股憤世嫉俗的疲憊情緒,你看不到人們有共同的身份或未來。
假如這場大流行病真的是一種戰爭,那麼這將是一個半世紀以來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第一場。侵略和佔領暴露了一個社會的斷層線,誇大了在和平時期被忽視或被接受的東西,澄清了基本的真相,揚起了被掩埋的腐爛氣味。
不平等與政治體的敗落
這病毒本應當將美國人團結起來,對抗共同的威脅。假如領導層不同,美國人是可能被團結起來的。相反,即使病毒從民主黨主政的地區蔓延到了共和黨主政的地區,人們的態度依舊沿着我們熟悉的黨派分界線分裂了。
這病毒也本應成為一個重要的平衡因素。要成為病毒的攻擊目標,你不必在軍隊服役,也不必負債累累,而只需要是一個人。但從一開始,病毒的影響就被我們容忍太久的不平等扭曲了。在幾乎不可能找到病毒檢測方法的時候,富人和有關係的人——模特和電視真人秀節目主持人海蒂·克拉姆(Heidi Klum),布魯克林網隊(Brooklyn Nets)的全部候選隊員,總統的保守派盟友——就能以某種方式獲得檢測機會,儘管許多人沒有症狀出現。這樣的個人零星檢測結果對保護公眾健康毫無幫助。
與此同時,有發燒和發冷症狀的普通人不得不排在漫長且可能已被感染了的隊伍中等待,但只是被拒之門外,因為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出現呼吸困難的症狀。一個網絡笑話提議,要想知道你是否感染了病毒,唯一的辦法就是對着富人的臉打噴嚏。
當被問及這種明目張膽的不公正時,特朗普表達了不贊同的意見,但補充説:“也許這就是生活。”正常時期,大多數美國人很少注意到這種特權。但在這場大流行病爆發的最初幾個星期,如此特權引發了公憤,就好像在一次總動員期間,富人被允許出錢免服兵役,並囤積防毒面具。隨着這場傳染病的擴散,其受害者已經可能是窮人、黑人和棕色人種。美國醫療衞生系統的嚴重不平等,從公立醫院外排隊運送屍體的冷藏車可以明顯看出。
我們現在有兩類工作:必不可少的工作的和非必不可少的工作。誰是必不可少的工人?主要是從事低薪工作的人,那些工作需要他們本人在場,會直接危及他們的健康:倉庫工人、填充貨架的工人、在Instacart為網上下單者買東西並交付的人、送貨司機、市政僱員、醫院工作人員、家庭護理工人、長途卡車司機。醫生和護士是抗擊這場大流行病的英雄,但配有瓶裝消毒液的超市收銀員和帶着乳膠手套的聯邦包裹公司(UPS)司機,是保持前線部隊完好無損的供應和後勤部隊。(Instacart是一家技術公司,創辦於2012年,在美國和加拿大運營,提供當日食品雜貨的送貨和取貨服務。——譯註)
在隱匿了各階層人類的智能手機經濟中,我們正在學習的是,我們的食物和商品從哪裏來,是誰讓我們活着。在亞馬遜生鮮配送(AmazonFresh),下單一份有機嬰兒芝麻菜很便宜,且可以隔夜送到,這部分是因為,種植、分類、包裝和運送它們的人在生病期間必須繼續工作。對大多數服務業的工人來説,病假是一種不可能的奢侈。值得追問的是,我們是否願意接受更高的價格和更慢的交貨速度,這樣他們就可以呆在家裏了。
這場大流行病也明確了,誰才是非必不可少的工人。一個例子是來自佐治亞州的共和黨新晉參議員凱莉·呂弗勒(Kelly Loeffler),她1月份之所以能填補空缺的議員席位,唯一的資質是她的鉅額財富。上任不到三個星期,她參加了一次有關新冠病毒的可怕的秘密簡報會,之後拋售股票,從中獲得了更多財富。然後她指責民主黨誇大了危險,並向她的選民做出了錯誤的保證,這大有可能害了他們。呂弗勒在公共服務方面展示的衝動,是那種危險寄生蟲的衝動。一個可以讓這樣的人擔任高級職務的政治體,已經敗落到了較晚期。
庫什納與特朗普行政分支的崩潰
政治虛無主義最純粹的體現不是特朗普本人,而是他的女婿兼高級顧問賈裏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庫什納被欺騙性地宣傳成了精英和民粹主義者。
1981年,羅納德·里根入主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那個月,他出生於一個富裕的房地產商家庭,是第二鍍金時代的太子黨。儘管學業成績平平,但在其父查爾斯(Charles)承諾向哈佛捐贈250萬美元后,賈裏德仍被哈佛大學錄取。父親用1000萬美元的貸款幫助兒子創辦了家族企業,然後賈裏德繼續在紐約大學的法學院和商學院接受精英教育,他父親向這裏貢獻了300萬美元。2005年,查爾斯因利用妓女構陷其妹夫並拍下了這次會面,試圖用這種辦法解決家族法律糾紛,而被判入獄兩年,當時賈裏德以強烈的忠誠回報了他父親的支持。
賈裏德·庫什納曾擁有一棟摩天大樓,並辦過一份報紙,都未獲成功,但他總能找到人來拯救他,而且他不過是越來越自信。安德烈·伯恩斯坦(AndreaBernstein)在《美國寡頭》(American Oligarchs)一書中描述了他如何採納了一位敢於冒險的企業家即新經濟“破壞者”意見的故事。在導師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影響下,他找到了融合財務、政治和新聞業追求的門道。他將利益衝突當成了自己的商業模式。(默多克,1931年生於澳大利亞,美國傳媒業大亨。——譯註)
因之,隨着其岳父成為總統,庫什納很快就在一個將業餘行為、裙帶關係和腐敗升級為統治原則的行政分支中獲得了權力。只要他忙於中東和平,他那些沒有意義的介入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説就並不重要。但自從他成為對特朗普有重要影響的新冠病毒事務顧問以來,結果就是大規模的死亡。
3月中旬,上任後第一週,庫什納參與撰寫了記憶中最糟糕的橢圓形辦公室演講稿,打斷了其他官員的重要工作,或者已經違反了安全協議,參與到了涉嫌利益衝突且違反聯邦法律的事項中,並做出了很快就化為烏有的愚蠢承諾。“聯邦政府的設計不是要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他在解釋他將如何利用自己的公司關係,在免下車餐廳(drive-through)設立核酸檢測點時這樣説。那些關係從未落到現實中。一些企業領導人説服他相信,特朗普不應動用總統的權威強迫一些產業生產呼吸機。後來,庫什納自己試圖與通用汽車談判達成協議,但未能實現。他對自己沒有失去信心,於是將必要設備和裝備短缺的責任算到了不稱職的州長頭上。
看到這位面色蒼白、身材苗條的票友閒庭信步般介入一場致命的危機,拋開了商學院的行話以掩蓋他岳父的行政分支的巨大失敗,就相當於看到了整個統治方式的崩潰。事實表明,科學專家和其他公務員並非叛國的“陰謀勢力集團”(deep state)成員:他們是必不可少的工人,將他們邊緣化,以理論家和諂媚者取代,是對國家健康的威脅。事實表明,“靈活”的公司無法為災難做好準備,也無力分發救生物資,只有能幹的聯邦政府可以做到這一點。事實表明,所有事情都有代價;經年累月地攻擊政府、榨乾政府資源、消耗政府的士氣,造成的沉重代價是公眾不得不付出生命。
所有項目都被撤資,所有庫存都被耗盡,所有計劃都被取消,這意味着我們已經成了一個二流國家。然後,病毒和不可思議的失敗就來了。
危機時刻的抉擇
制服這一大流行病的戰鬥也必須是恢復國家健康並重建它的戰鬥,非如此,我們眼下正忍受的苦難和悲痛就將永遠得不到補償。
有目前的領導層,什麼都不會改變。如果説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機耗盡了人們對老一代政治當權派的信任,那麼2020年就應當碾滅“反政治”是我們的救星的念想。結束這個政權,是必須的和值得的,但這僅僅是個開始。
我們面臨一個選擇,這場危機讓這個選擇變得清晰到了無可逃避的地步。我們可以長期保持自我隔離,懼怕和迴避彼此,讓我們共同的紐帶消失殆盡。
抑或,我們可以利用正常生活中的這種停頓,留意一下:那些舉着手機,好讓他們的病人可以和親人説再見的醫院工人;那些從亞特蘭大飛去紐約幫忙的一飛機醫務人員;那些要求把他們的工廠改造成呼吸機生產廠的馬薩諸塞州航空產業工人;那些因無法通過電話聯繫到人手稀少的失業辦公室,而排着長隊的佛羅里達人;那些無懼沒完沒了的等待、冰雹和傳染,在黨派立場強烈的法官強加給他們的選舉中投票的密爾沃基居民。
我們可以從這些可怕的日子中領會到:愚蠢和不公正是致命的;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充當公民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團結的替代品是死亡。走出藏身之處,摘下口罩後,我們不應忘記一個人獨處是什麼滋味。
(本文轉載自《大西洋月刊》,是美國最受尊敬的雜誌之一,創辦於1857年。作者是美國《大西洋》雜誌特約撰稿人,著有《 Our Man: Richard Holbrooke and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和《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本文原題“Underlying Conditions”,見於《大西洋》雜誌2020年6月號,提前發佈的網絡版題為“We Are Living in aFailed State”。小標題為譯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