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疫情之下我們為何會有這麼多“想不到”?恐怕是西式思維作怪
【文/王紹光】
昨天電視裏面聽一個醫學專家的比喻比較好,這次疫情,武漢、湖北和全國開始打的是一個遭遇戰,然後才是阻擊戰。我覺得遭遇戰這個詞很好,即在沒有料想的情況下就突如其來的碰上了一場戰鬥,它與阻擊戰不同,後者是已知敵人來襲的情況下開打的。現在疫情得到了一些控制,即使有第二波反彈的話,也不會變成遭遇戰,更多的可能是阻擊戰。
戰鬥、戰役或者是戰爭總會有結束的時候,可能我們離結束的日子越來越近。問題是,結束以後情況會變得更好嗎?新的世界格局會變成什麼樣?我覺得有非常多的不確定性。我看最近各個智庫開的會都和疫情以後的國際格局有關,大概已經開了無數場會。
從歷史上來看,戰爭之後的情況不確定性往往比戰爭期間可能還要更大。作為開場白,我先講一下自己的小小感想。這場疫情以後的情況會更多像一戰以後到二戰之間的戰間期(Interwar period),還是更像二戰結束以後的狀況?
其實,不管是哪一種狀況,都會出現大量難以預料的事情發生,是很麻煩的事情。一戰結束的時候大家都很高興,作為戰勝國,中國人有理由高興。但1919年初召開的巴黎和會,卻將德國強佔的山東半島主權轉交給日本,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引發了“五四運動”。不僅在東亞,歐洲發生的很多事情,也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1922年,墨索里尼領導的法西斯運動席捲意大利;1929-1933年,世界範圍的經濟大蕭條;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東北三省全境;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上台。後來,法國元帥福熙因此回顧説:“這不是和平,而是20年的休戰”。
二戰結束後也是一樣,開始大家非常高興,就跟疫情結束後,我們大家會很高興一樣。但是,二戰剛剛結束,1945年10月9日,奧威爾首次使用“冷戰”一詞;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和平砥柱”演説中使用“鐵幕”一詞;1947年3月12日,時任美國總統拋出“杜魯門主義”,擺出一副與社會主義陣營勢不兩立的架勢,奠定了戰後幾十年的世界基本格局。
所以,疫情結束鼓勵值得慶賀,一定會出現一個短暫的高興期,但是接下來的世界格局會變成什麼樣子?這就要聽接下來各位的發言。

丘吉爾
在這裏,我講一點我的一些最新想法,即關於深度不確定性的思考。
我最近寫了一篇關於深度不確定性的文章,它依據確定性的程度把各種各樣的事件分成三大類。
一類叫確定性事件,就是“已知之已知”,即決策者已經知道那些已知的東西。用我們日常的話來講,可以叫做“曾想到”。2017年美國出了一本書,很快翻譯成中文,而且在中國的影響可能比在美國還大,叫《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灰犀牛”事件就是一種確定性的事件,它有三個特徵:1)可預見,2)大概率,3)影響巨大,雖然“曾想到”,但終究被人忽略了。
第二類是一般不確定性,就是“已知之未知”:我們雖然不知道未知的是什麼東西,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存在這些未知的東西。用日常的用語來講,這種情況叫“沒想到”。2007年出版過一本題為《黑天鵝》的書,“黑天鵝”事件也有三個特徵,第一是出乎意料,第二是影響巨大,第三是事後可以理解的,這個東西是可以想到的,但是當時“沒想到”。
最近幾年,談論“灰犀牛”或“黑天鵝”的人不少,但我覺得人類還要意識到另一種可能性,即深度不確定性,它指“未知之未知”,即有些因素我們連它們是未知的因素都不知道,用日常的話來講,這種情況叫“想不到”。它既不是“灰犀牛”事件,也不是“黑天鵝”事件,我把它比喻成“隕石來襲”,一顆巨大的隕石從天而落,砸在地球上,可能對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人類造成巨大的影響,據説恐龍就是因此而滅絕的。
“隕石來襲”事件也有三個特徵:第一個叫不可預見,第二是小概率,第三是影響超大。這次的疫情就屬於這類事件。同樣,1918年前後發生的所謂“西班牙流感”與本次疫情後的世界變局恐怕也屬於這類事件,它們的共同點是很多情況具有深度不確定性。下面,我就分三個部分來講。
“西班牙流感”與這次新冠肺炎相似點很多。對比這兩次疫情,有些東西是可以確定的。比如口罩的作用。這次疫情初期,歐美很多國家的人不願意戴口罩,彷彿戴口罩是過於謹慎的東方人的習慣。其實,在互聯網上稍作搜索就會發現,“西班牙流感”肆虐時,歐美國家人戴口罩的照片比比皆是,而東亞人戴口罩的照片很難找到。口罩當時在阻止疫情傳播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此外,保持社交距離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有人對比過當時美國兩個城市的情況,一個是費城,一個是聖路易斯。費城開始忽略了保持社交距離的重要性,疫情期間舉辦過一次大型集會,結果死亡人數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另一個城市聖路易斯做得很好,所以很快壓平了疫情上升的曲線救壓。這是100多年前確確實實的教訓,值得人們面對當前疫情時牢牢記取。
不過,即便過去了100多年,到今天為止,當年的大流感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首先,零號病人找不到。疫情到底發源於何處?仍是眾説紛紜,不確定。主流説法是美國,也有人説是英國,近年來也有人把矛頭指向中國,也不排除還有其它可能的源頭,但基本可以排除,不是西班牙。
其次,病原體不完全確定。1918年大流感之後,一直到1933年才有科學家分離出一個H1N1流感病毒,但是現在仍有學者試圖重建當年流感病毒的起源。
第三,病亡人數也是不確定的。最低的估計是1700萬人,最高的估計是9000萬、甚至1億人,兩者相差七八千萬人。感染的人數當然更多,有人估計,當時世界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受到感染,而受到感染的人口裏面大概有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的人死去。這也是估計,不完全確定。
第四,1918年的大流感對短期和長期的世界經濟的影響不確定。如果回看統計數據,兩種情況是比較確定的。一是出現了去全球化的趨勢。比如,1918年以後,商業和金融全球化的指數都呈下降趨勢。如果使用其它全球化指數,情況也大同小異。二是經濟增長率下滑。如果對比世界各地區1918年前幾十年與後幾十年的人均GDP增長率,前者一般都比後者高。直到1950年代出現新一波全球化以後,經濟增速才再次提高。然而,我們並不能據此得出結論,1918年的疫情是造成這兩種情況的原因,因為在此前後,還有很多其它事情發生,比如戰爭、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等。所有這些因素的影響難分難解,不確定。
這次的新冠肺炎也有很多事情我們是想不到的,也具有深度不確定性。
比如説這次疫情的損失之大,很可能大於很多戰爭造成的損失。以死亡人數為例,到現在為止,美國這次疫情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越戰、朝鮮戰爭的死亡人數,僅僅低於二戰與內戰的死亡人數。未來疫情在美國會怎麼發展?按照一些學者的模型模擬,美國這次疫情最終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接近二戰的死亡人數,這都是我們以前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經濟損失也是如此。有人估算過中國2003年SARS造成的經濟損失,大概是千億級的。但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損失肯定是萬億級的。去年中國的GDP總量是將近100萬億,損失1個百分點就是一萬億,損失幾個百分點就是好幾萬億。昨天看了最新的報道,歐盟2020年的GDP可能會下降7.4%,是歐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所以,從世界經濟的重型區看,這次疫情的威力是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
新冠肺炎的防控情況也出現了很多“想不到”。
先看中外對比。有些國家與地區的醫療體系據説比中國大陸好得多,但這次防控疫情的結果十分出乎意料,我們以前都很難想象。比如説福建省人口比台灣地區多,但福建省的確診和死亡都比台灣少。台灣一直把自己鼓吹成世界上抗疫的典範,但是我們福建省比他們表現好得多。深圳市人口比香港特區多得多,但確診和死亡數量比香港少。
另外,蘇州市比新加坡人口多得多,表現好得多。武漢市比紐約市表現好得多,湖北省比紐約州好得多,儘管武漢與湖北人口比紐約市、紐約州多得多。湖北省周邊的四個省,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都比很多國家要大得多,它們有很多來自湖北或武漢的流動人口,防疫照説很難,但它們的表現比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好得多,而這些國家往往被國際媒體看作這次抗疫的明星國家,它們也都自認為表現得不錯。最後,跟歐美所有國家相比,中國整體表現很好,這其實是我們以前想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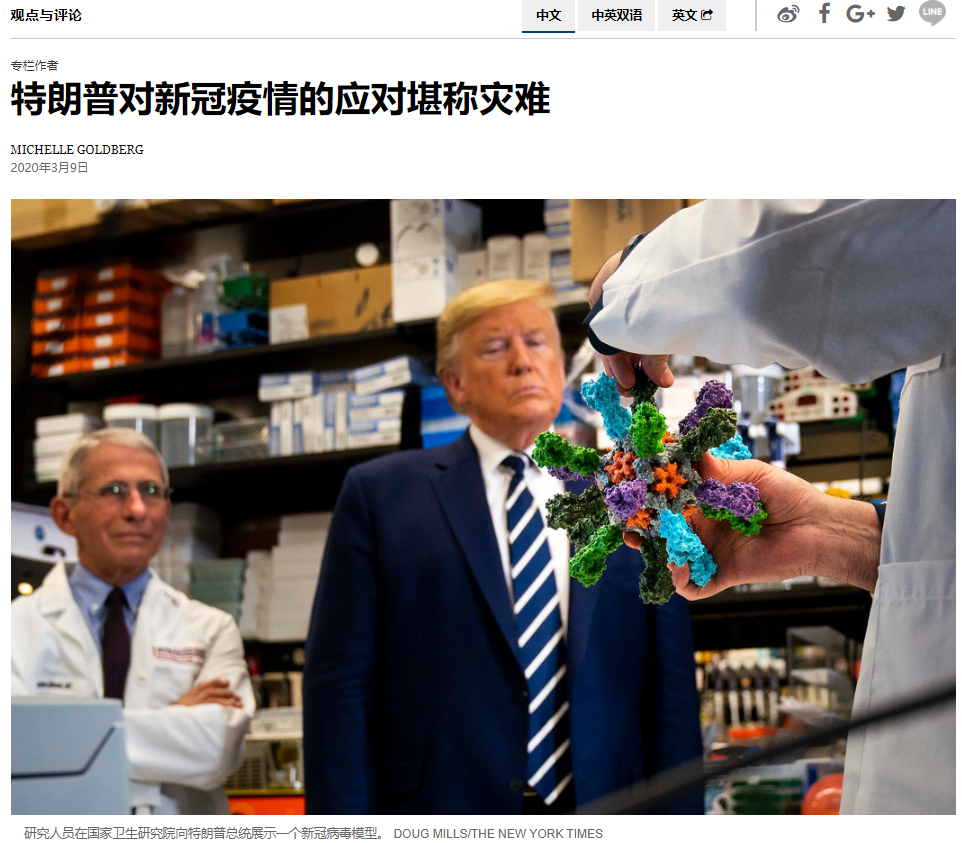
截圖來自紐約時報
不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中外比較有很多“想不到”,外國與外國的比較也有很多“想不到”。比如説越南、老撾、古巴這些地方,要比歐洲國家(如瑞典、丹麥、挪威、比利時)表現好得多,這些都是我們以前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因為不管從人均收入來比,從醫療體制來比,從福利水平來比,後者都據説比前者強得多,但是現在這些社會主義國家表現的都比歐美的所謂福利國家好很多。
還有一個對比我們可能也想不到:非洲整體其實表現的非常好。非洲有13.4億人口,比歐洲大得多,但是非洲現在的感染人數僅僅佔全球感染人數的1%左右。很多人以為這是因為非洲的檢測能力不足,真正的感染情況可能很嚴重。但據研究非洲問題的專家介紹,非洲疫情也許的確沒那麼嚴重,因為非洲歷史就是當地人民與疫情作戰的歷史,他們積累了大量抗疫的本土知識,這次派上了用場。
全球比較,如果以每百萬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作指標,在全球140個有數據可查的國家裏面,頭20位除了伊朗以外幾乎全部都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即便如果按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的死亡率來看,排在中國前面的至少有十多個最發達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這些國家,這都是我們想不到的。
問題是,我們為什麼會想不到?這裏面其實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東西。對解釋世界,歐美有大量看似很“科學”、“合理”的説辭,我們自己以前往往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下來,變成自己思維框架。但是這次疫情撼動了這些貌似“科學”、“合理”的假設,激發我們對它們進行深刻的反思。比如疾控體制、公共衞生體制、醫療體制在防控大規模疫情方面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是否還有其它很多東西在防控疫情方面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行為模式是不是很重要、思維方式是不是很重要?文化傳統是不是很重要?尤其是這次中國和歐美國家比較,也許告訴我們,社會政治體制比什麼都更重要。將這些“想不到”的事情想清楚、説清楚是我們接下來應該做的事情。
疫情之後的世界會出現什麼樣的大變局?現在恐怕誰也説不清,因為涉及太多的“想不到”。很具諷刺意義的是,今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以全球價值鏈為主題。疫情還沒有結束,已經有很多人討論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未來,不少人對此憂心忡忡。其實,在疫情之前,全球價值鏈未來就已經蒙上了一層陰影。相比前40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價值鏈佔全球貿易的份額不僅沒有增長,反倒有所下降。這次疫情很可能會雪上加霜,導致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斷裂。儘管有人比較樂觀,有人比較悲觀,各有各的道理,但總體上,大家也許都同意,這方面具有深度的不確定性。
現在據2049年,我們還有大概30年,這其間世界格局變化的不確定性我覺得會是非常大。講到去全球化,還是再全球化,最近還有一個人提了一個説法,叫慢全球化。世界銀行的《2020年世界發展報告》已注意到,過去十餘年已經呈現慢全球化的趨勢。疫情會不會讓慢全球化變為去全球化?如果出現去全球化,它恐怕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脱鈎,不僅僅是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脱節,還可能在政治上出現一些情況。比如最近在西方已經有政客提出來要在中國周邊拉上一道“鐵幕”。“鐵幕”的説法是丘吉爾1946年3月份提出來的,當時人們還沉浸在二戰勝利的狂歡之間,然而“鐵幕”的預言不久變為了一道真實“鐵幕”。“冷戰”的説法是1945年10月份,二戰剛剛勝利時,《1984》那本書的作者奧威爾提出的,當時很多人“想不到”冷戰最終會變成殘酷的現實,並持續了幾十年之久。
面對深度不確定性,我們不能忽略去全球化的可能。總之戰鬥、戰役、戰爭結束之後,往往會出現具有深度不確定性的局面。這次疫情之後,恐怕也不會例外。會不會出現一個我們十分不願意看到的局面?我們當然看到最好的結果,但與此同時,一定要準備應付最壞的結果。謝謝各位。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