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德雷茲納等:危險不是來自真槍實彈的熱戰,而是“冰戰”-丹尼爾·德雷茲納、羅納德·克雷布斯、蘭德爾·施韋勒
無論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際關係領域有什麼其它所作所為,有一項他可以宣稱的標誌性成就:讓大戰略再次變得有趣。幾十年來,美國兩黨的外交政策精英都信奉自由國際主義,即華盛頓應該維持和擴大能促進開放市場、開放政治以及多邊機制的全球秩序。但特朗普一再攻擊自由國際主義的關鍵支柱,從質疑北約的價值,到摧毀貿易協定,到侮辱盟友。據《華盛頓郵報》報道,2017年7月,特朗普的國家安全團隊在五角大樓一個被稱為“坦克”的無窗會議室裏和他開會,告訴他有關自由國際秩序的優點,結果特朗普斥責他們為“一羣笨蛋和嬰兒”。

《外交事務》5、6月刊發表文章《大戰略的終結》
特朗普的破壞迫使外交政策分析家數十年來首次質疑第一性原則。隨着關於自由國際主義的基本假設被強行去除,圍繞美國大戰略的辯論經歷了一場復興。新的聲音也加入了爭論,從極左的進步分子到右翼民粹民族主義者。緊縮和抑制政策的擁護者得到了更充分的傾聽。為了推進共同議程,不同尋常的聯盟也開始形成。
儘管這些辯論愈演愈烈,但大戰略的概念卻變成了一頭古希臘神話中的怪獸喀邁拉(譯註:意指怪誕荒謬的嵌合體)。大戰略是指導手段與目的進行匹配的路線圖,在可預測的地形上使用效果最佳。在這個地形上,決策者對權力分配有清晰理解,對國家目標和身份認同有堅定的國內共識,同時有着穩定的政治和國家安全制度。到了2020年,這些都不存在了。
權力的本質就是不斷變化,而且權力在國際體系中不斷分散,使美國更難決定自身命運。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和民粹主義對它的強烈反彈侵蝕了共同敍述和身份認同。政治極化已經掏空了國內的政治體制,這意味着每屆新政府都一心要與前任政府的所作所為相背而行。反建制熱已經降低了政策辯論的價值,也放鬆了對保證一致性的行政權力的制約。
我們這三位學者平常寫作時,不太能就政治、政策或意識形態等話題達成一致意見。但是我們一致同意,這些新要素使得任何一項與制定或推行大戰略相關的工作都變得成本高昂,且結果可能適得其反。沒有一項工作會有效,也沒有一項會長久。學者、評論家、智囊團和政策制定者不應為辯論戰略理論而爭吵,而應關注如何以更務實的形式解決問題。從軍事幹預到對外援助,基於個案所制定的政策至少不會比基於大戰略所制定的政策更差,甚至可能更好。現在討論大戰略,無疑是在全世界燃起熊熊大火之際還沉迷於自我反省。是時候在沒有大戰略的情況下運作了。
權力問題
成功的大戰略必須基於對全球實力平衡的準確把握。嚴重誇大敵人或低估威脅的大戰略不適用於當前世界,因為它所引發的政策選擇將適得其反。事實上,過去十年中之所以這麼多人抨擊美國的自由國際主義戰略,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一戰略未能認識到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好處。
全球政治中的權力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國家行使權力的能力、行使權力的方式、行使權力的目的、由誰掌權——這些都發生了根本變化。結果出現一個無極的、混亂的新興世界。這個也不是大戰略能夠玩轉的世界。
當然,很多事情還是維持了原樣。人們還是主要根據國籍來界定自己的身份。各國仍然尋求對重要資源的控制和進入重要海道的機會,並在領土和區域影響力問題上發生衝突。各國仍然希望最大化他們的財富、影響力、安全、威望和自主權。但是,“收割”領土已不再像過去那麼重要。如今的大國對兩件事的決心似乎比對任何事都堅定:一是致富,二是避免災難性的軍備競賽。他們明白,國家如果要在國際上獲得更多權力和威望,要通過建立知識型經濟,以及在全球網絡內推動技術創新和互聯。
與此同時,權力越來越關乎於破壞、阻止、禁用、否決和摧毀的能力,而不是關乎於構建、啓用、修復和建設的能力。想一想中國正尋求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主要是網絡戰技術和反衞星武器,目的是增加在西太平洋作業的美軍面臨的風險。據信,伊朗在波斯灣也在採取相同行動,使用潛艇、反艦導彈和尖端水雷,努力使該地區成為美國海軍的禁區。

5月15日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限制華為使用美國技術設計和生產半導體(圖源:美國商務部)
當權力用於建設性目的時,它會變得越來越就事論事,無法從一個領域轉化到另一個領域。如今,動用軍事力量很少能實現國家目標和解決問題;干預通常只會使壞的情況變得更糟。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結果之間的巨大差距很清楚地説明了這一點。權力並不像過去那樣可互換。例如,難怪特朗普政府試圖把安全事務和情報合作同再次談判的貿易協議進行綁定的努力已經落空。
最後,整個國際體系中權力的不斷分散正在創造一個無極世界。許多人指出,中國以及美國其它競爭者的崛起表明,世界正在迴歸多極化(或者説多極環境中的兩極化),但這一觀點低估了目前正在發生的地殼式轉變。國際關係將不再由一個、兩個或者幾個大國主導。由於經濟和軍事力量不再像以前那樣一定能產生影響力,前鋒將領已經失去了戰鬥力。弱者和強者遭受同樣的癱瘓,也享有同樣的行動自由。此外,從地方民兵到非政府組織,再到大公司,各自擁有並施加各種影響力,這些新的角色越來越多與國家形成競爭。在聯合國有代表席位的國家相對而言較少可以在其領土邊界內聲稱壟斷武力。暴力的非國家行為體不再是配角。民族團體、軍閥、青年幫派、恐怖分子、民兵、叛亂分子和跨國犯罪組織——都在重新定義全球的權力。
這些權力的變化正在產生一個以熵為標誌的世界。一個由數十個權力中心組成的世界會被證明很難駕馭和控制。在新的全球失序之中,即便擁有強大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國家,也可能無法讓別人按他們的意願做事。現代國家無論在軍事和政治上多麼強大,基本上不可能阻止暴力團體在無人監管的太空或互聯網上繁榮。這些角色不僅沒有提供明確的威脅或摧毀目標,而且很多角色的動機是出自不容協商的關切,例如建立哈里發國(caliphate)或他們自己獨立的國家。更糟糕的是,對許多人來説,暴力是社會凝聚力的來源。
傳統大國不再像以前那樣能獲得影響力,全球秩序與全球合作的“供貨”面臨短缺。國際關係將越來越充斥混亂的臨時安排。危險並非來自大國之間真槍實彈的戰爭,也不是來自人權、知識產權或貨幣操縱等問題上的激烈對抗。危險反而來自圍繞地緣政治、貨幣、貿易或環境問題的“冷戰”甚至“冰戰”衝突。鑑於戰爭代價巨大,那些無法在談判桌上解決爭端的大國不再有選擇用戰爭來解決的餘地——至少如果它們是理性的。當政治部署成形時,這些情況只會是短暫的。就像成羣結對的鳥或魚,他們承諾會拆散隊形,但磨蹭一段時間之後又會恢復。
大戰略並不適合於一個熵的世界。大戰略思維是線性的。當今世界充滿互動性和複雜性,兩點之間最直接的路徑不是一條直線。一個無序、混亂和不穩定的領域,恰恰無法認識到大戰略的優點:具備實操性、持久性和一致性的長期計劃。要在這種環境中成功運作,所有角色必須不斷改變其戰略。
一個分裂的國家
可持續的大戰略還必須建立在關鍵政治選區的共同世界觀之上。如果每一屆新政府上台時對全球挑戰和機遇的理解都截然不同,那麼任何戰略都不會持久。每一屆新政府都會撕毀前任政府的政策,粉碎一項大戰略的構想。遏制之所以能夠持續,是因為從哈里·杜魯門到羅納德·里根的每一位美國總統基本上都堅持其對全球事務的基本觀點。比爾·克林頓、喬治·W·布什和巴拉克·奧巴馬都信奉自由國際主義的各種變體。
這樣的共識已不復存在。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整個西方對“國家”——用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話來説就是“想象的共同體”——的美德甚至其現實狀況的懷疑在不斷增加,每一個社會都被一種共同的敍事團結起來。這種懷疑的來源是有原因的: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主流敍事可能具有鎮壓性,它們往往反映當權者的經歷,體現他們的利益,而壓制了邊緣羣體的聲音。20世紀70年代初,在越南戰爭即將結束的日子裏,多元文化主義開始佔據主導地位,至少在美國是這樣。這不僅僅是以公平和包容的方式管理多樣性的戰略,這種觀念的基礎在於:越來越多的人懷疑所有社會應當基於共同的身份認知。
這場文化革命的一些影響,比如專門指定幾周甚至幾個月用來大肆慶祝特定民族和種族遺產,在大多數美國人看來是無害的,甚至是有益的。但其中一個後果尤其成問題:如今的美國人缺乏一種共同的國家敍事。很少有人再談論同化的“大熔爐”概念,這是有原因的。2019年,歷史學家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在《紐約時報》上哀嘆道,幾十年前歷史學家們就不再寫關於這個國家的文章了。在這個總統競選季,只要聽一聽民主黨的辯論,你就會發現,自由左翼的美國政客們對美國民族主義的言論已經變得多麼不適。
然而,民族主義已被證明是一種持久的力量,就像人們渴望用一種共同的敍事來理解他們的世界一樣。長期以來,美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一直在挖掘這種精神。他們試圖定義一種文化核心,這體現在《新文化素養詞典》(The New Dictionary of cultural Literacy)等書中。在這本詞典裏,學者艾瑞克·唐納德·赫希(E. D. Hirsch, Jr.)試圖列出“每個美國人都需要知道”的人物、事件和作品。他們發動了反對雙語教育的戰爭,並領導了一場宣佈英語為官方語言的長達數十年的運動,迄今為止在美國超過一半的州取得了成功。他們指責美國正在分崩離析,這要怪新移民拒絕接受美國信條。自由主義者在美國例外論上舉棋不定,比如2009年,奧巴馬宣稱:“我對美國例外論的相信,就像我懷疑英國人相信英國例外論,希臘人相信希臘例外論一樣。”相比之下,保守派則傾向於此。與民主黨人不同,特朗普對民族主義語言運用自如——儘管他對這種語言的使用排除了一半的美國人。
支離破碎的國家敍事的受害者之一就是大戰略。大戰略基於以全球政治為主角的安全敍事,主要講述這些已經做過和將要做的事情,並描述事件發生的全球背景。圍繞宏大戰略展開的辯論,通常是圍繞這些敍事元素中的一個或多個展開的辯論。例如,那些主張深度接觸的人認為,美國和全球安全是不可分割的,而那些呼籲剋制的人則持相反觀點。在缺乏共同的國家敍事所提供的修辭的情況下,制定一項能夠引起不同選民共鳴的宏大戰略就變得不可能。跨多個政策領域實施特定的戰略,並隨着時間的推移維持該戰略,將變得更加困難。
美國敍事分歧的一個表現是鮮明極化,這定義了美國政治,而且不僅僅是在火燒眉毛的國內問題上。在一系列廣泛的外交政策問題上——氣候變化、反恐、移民、中東、軍隊的使用——美國人內部的分界線按黨派劃分。這不是討論大戰略的好時機。首先,它削弱了專家反饋的效用。政治科學家發現,專家的共識可以改變公眾對一些問題的態度,而公眾對這些問題的態度尚未分化,比如如何應對中國的匯率操縱。然而,當公眾已經沿着黨派路線分裂時,就像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一樣,極化使得精英共識變得比毫無用處更加糟糕。來自無黨派人士的專家意見只會讓黨派人士對他們原先存在的信仰更加深信不疑。
政治極化也使學習變得困難。要想改善大戰略,就必須就失敗之處和失敗原因達成一致。在極化的政治環境中,害怕被追責的一方不會接受其政策失敗了這一假設,直到現實得到印證很久之後。例如,共和黨人曾堅持表示伊拉克戰爭是一次勝利,多年之後很明顯美國已經失去了和平。為了支持他們的領導人,黨派人士有一種持久的動機來歪曲事實以吻合他們的論點,剝奪外交政策討論中通常用來框定辯論的公認事實。
最重要的是,極化意味着任何政黨的大戰略只有在該黨掌控行政部門的情況下才能持續。由於國會和法院已經授予總統在國家安全敍事的表述上近乎壟斷的地位,一位總統就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大戰略,來自另一個政黨的下一任總統也可以。
民眾與專家
大戰略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思想市場,有堅實的制度支撐,幫助政策制定者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調整方向。即使是一項持久的大戰略也必須應對戰略環境的變化,即使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也會導致需要扭轉的政策失誤。美國在冷戰期間也犯過一些外交政策錯誤,但當局與批評者之間、行政部門與國會之間的拉扯,最終遏制了美國激進主義中最惡劣的過度行為,避免了遏制政策的用力過猛。
過去的半個世紀裏,一度穩定的權力結構已經受到了侵蝕,美國公眾對聯邦政府、媒體和其它所有主要公共機構的懷疑與日俱增。美國人的這種質疑延伸到了外交政策機構,在這一點上,很難責怪他們。美國的外交政策精英們大多支持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使用武力,而這些干預行動無一能被稱為成功。去年年底,《華盛頓郵報》發表的政府文件合集“阿富汗文件”顯示,在過去的十多年裏,政府官員和軍事將領在阿富汗戰爭的進展情況上欺騙了公眾。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阿拉伯之春讓外交政策精英措手不及。顯然,一些專家的合理懷疑是有道理的。

2019年《華盛頓郵報》發佈獨家調查報告,曝光阿富汗戰爭2000頁機密文件(圖源:華郵報)
然而,過多的懷疑可能是有害的。質疑外交政策專業知識的價值,會破壞一個健康的大戰略思想市場。正如記者克里斯托夫·海耶斯(Chris Hayes)在《精英的黃昏》(Twilight of the Elite)中警告的那樣,“如果專家們作為一個整體名譽掃地,我們就會面臨無窮無盡的江湖騙子。”此外,後來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抨擊已經存在的有關大戰略的共識來推進他們的論點。他們正在拿過去失敗外交政策的説事,辯稱自己不可能做得更糟。正如特朗普在2016年一次競選集會上對選民説的那樣,“專家們很糟糕。他們説,‘唐納德·特朗普需要一個外交政策顧問。’……難道會比我們現在的情況更糟嗎?”
對專業知識尊重的喪失只是21世紀最大的政治故事的一個元素:右翼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作為主流政治的一部分在整個西方擴散。這不是曇花一現,它的興起一部分源於經濟混亂,另一部分(如果不是更多的話)源於文化反應的政治。而民粹主義讓大戰略變得毫無意義。
所有形式的民粹主義的核心都有一個簡單的政治形象。這位民粹主義領導人聲稱,存在一個道德純潔的民族,與腐敗的精英階層形成鮮明對比。他還聲稱,只有他知道人民的意願。因此,民粹主義政治傾向於威權主義。這位民粹主義領導人掃除了可能存在腐敗的精英和機構,削弱了所有阻礙他前進的力量。這位民粹主義領導人向人民宣示了他未經調解的立場,聲稱自己比任何政治程序都能更好地代表人民。批評者變成了敵人,憲法的約束變成了民主的障礙,多數人的暴政變成了美德,而不是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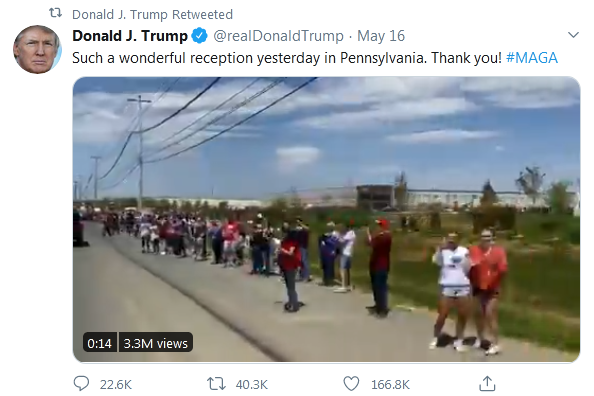
5月16日特朗普轉推一位記者遭到親特朗普者的謾罵和攻擊的視頻,稱這些抗議者為“偉大的人民”(圖源:推特)
民粹主義不適合大戰略。首先,民粹主義加劇了內部分歧。蓄意的極化縮小了所謂遵從本心的人羣範圍,因此無論是領土概念還是法律實體概念的國家內部,不可能有統一。其次,民粹主義政客經常以正義的憤怒動員民眾反對敵人。當激烈的言辭瀰漫在空氣中時,對當前危機的情緒化反應可能會壓倒理性策略。戰略變得不那麼靈活了,因為領導人在冒犯和報復的氣氛中很難採取和解策略。最後,民粹主義將權威集中在有魅力的領導人身上。它剝奪了制約變化無常的統治者、阻止極端的決策的官員和機構的權力。因此,民粹主義政權的政策是領導人的反映——無論是他符合他一貫的意識形態還是他的突發奇想。如果這位民粹主義領導人確實在追求某種類似於宏大戰略的東西,那麼這種戰略不會比他的統治更長久。
我們來埋葬大戰略
大戰略已經死了。全球政治“非極化”的極端不確定,使大戰略的作用更小,甚至更危險。儘管它有助於組織美國應對今天的全球挑戰,但日益分裂的國內政治使其更難實施連貫一致的大戰略。對專業知識的普遍不信任已經侵蝕了有關歷史教訓和未來戰略的理性辯論。民粹主義已經破壞了用來防止戰略劇烈搖擺的制度制衡。
然而,美國的戰略思想家們仍處在為大戰略感到悲愴的早期階段。圍繞戰略選擇展開的激烈辯論表明許多人仍不願面對現實。針對特朗普政府缺乏戰略思考的憤怒説明許多人仍被憤怒所困。我們內部對於該哀悼還是該慶祝大戰略的終結也有不同意見,但我們一致認為,現在是時候進入悲愴的最後階段了:坦然接受。
要在沒有大戰略的情況下繼續前進,需要遵循兩項原則:去中心化和漸進主義。高度不確定的情況需要既分散又相互協調的決策網絡。企業界已經認識到,管理者必須剋制住想控制每一個決策的誘惑,而且要探索如何通過塑造孕育選擇的環境來引導創新。聰明的企業分散權力和責任,鼓勵員工通過團隊合作解決問題,並採取非正式的方式分配任務和責任。各國政府應當以同樣的方式組織其外交政策機制。重視地區性知識、相信專家反饋意見是更好地處理問題點和緊急情況以及在危機轉移之前化解危機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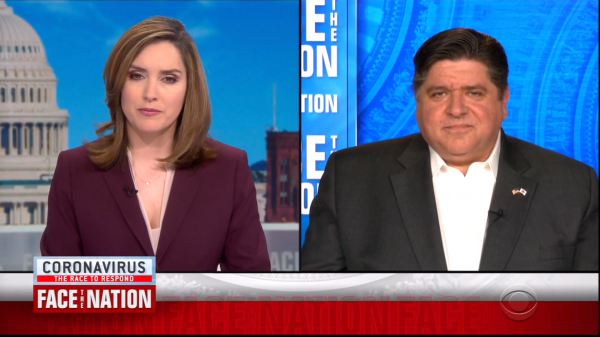
伊利諾伊州長普利茨克表示:我們從白宮得到的很多指導意見都沒有幫助 (圖源:CBS )
組織變革必須與文化變革齊頭並進:要實現自下而上實驗的優點。大戰略押注於中心的精心謀劃能產生最好的結果。它假定操作過於靈活的成本超過操作過於僵化的成本。但當變化迅速發生且不可預測時,大戰略是不明智的。漸進主義是更安全的選擇。這不要求你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不可能依靠漸進主義一蹴而就取得勝利,但它確實避免了災難性的損失,也使快速適應變化的環境成為可能。實際上,這將意味着把責任從華盛頓移交給戰區指揮官、特使和問題專家。換句話説,這意味着相比以往把更多決策權集中在白宮的多屆政府採取完全相反的方針。
有志向的國家安全顧問應該放棄爭奪“第二個喬治·凱南”的名號。為不久的將來,為“遏制”政策打造一個有韌勁的繼任者,既不重要也不可能。改善美國的外交政策,既重要又可能。考慮到美國最近的外交政策記錄,這個目標看起來還不錯。
(觀察者網凱莉譯自《外交事務》)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