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標、徐暢:評《劍橋中國晚清史》《劍橋中華民國史》-中國歷史研究院
【文/馬建標、徐暢】
“劍橋中國史”系列是當代西方學術界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套集大成之作,由多位歐美著名學者執筆。它在中國的出版,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熱烈討論。其中《劍橋中國晚清史》和《劍橋中華民國史》兩本所涉及的時間段,又與通常所稱的“中國近代史”大致相當。這兩本書也繼承了該系列的一貫特點,即站在西方研究者的立場上,以一種“域外”和“他者”的視角,觀察審視發生在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各種現象,並自成一套評價體系和結論。這種體系和結論,雖然“獨特”和“新穎”,但卻未必合理與正確。
先以《劍橋中國晚清史》為例。眾所周知,該書主編費正清對於自晚清以降的中國近代歷史,提出了著名的“衝擊—回應”的認知與分析模式,這一點也鮮明地反映在《劍橋中國晚清史》的體例結構與各章內容的主要議題之中。該書是從分析晚清王朝在財政税收、教育文化、社會流動等方面的衰落表象以及造成中國各種叛亂、民變頻仍的原因入手和展開論述的。這一切入點的選擇看似是在強調發源於中國本土的歷史動因,但實質上卻流露出對於中國社會“充滿惰性和停滯不前”的悲觀情緒和認知基礎:面臨層出不窮的統治危機,中國內部缺乏能夠扭轉局勢的變革動力,在資本主義與現代化席捲全球的浪潮之中,中國被迫走上模仿西方、向現代靠攏的發展道路。但這樣的論證思路即使是在西方學者羣體中,也早已有人提出質疑和批評,美國知名學者墨子刻(Thomas A.Metzger)就認為:“這些關於曾國藩之類的人物和太平天國或鴉片戰爭之類的事件的描述雖然精巧細緻,但對於晚清時期中國(內在)的社會結構、官僚體制和思想內涵卻議論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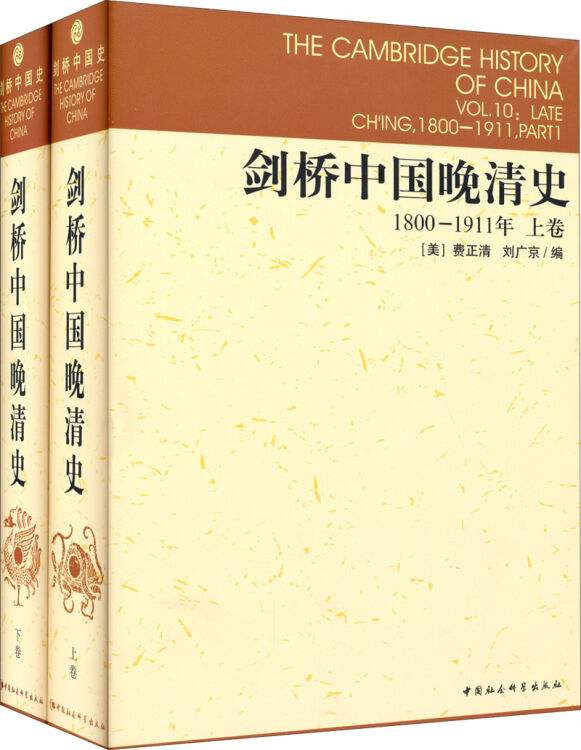
《劍橋中國晚清史》書影
另一方面,正是帶着這種對於中西地位差距的偏見和西方“如此重要”的先天優越感,該書的著者又特別關注尋找西方在中國的痕跡與中國人的西方觀,如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的看法與對外政策的演變,以及中國的政治改革、思想潮流乃至革命運動中的西方因素。這樣的總結或許可以啓發中國本土的讀者和研究者思考,但是,這些因素是否確實居於關鍵和必要的地位?如果離開了這些外因的參與,中國自身的多重變革是否仍會發生或達到相同的程度?實際上,即使是西方學者也承認,在西方人廣泛地與中國人接觸之前,清王朝內部已經出現了政權穩定性的裂痕和危機的徵兆,相較於“外患”,這些“內憂”的衝擊力和引起的關注可能更顯著。
進一步説,如果離開這種西方“衝擊”的理論模式與敍事背景,該書對於晚清之際中國歷史的論述還能否成立?換言之,對於晚清世變的產生與解局,是否還有其他歷史書寫和闡釋的方式可供選擇?
由於文化差異及觀察視角的不同,費正清等人在解讀中國歷史文獻的過程中,難免存在隔膜,甚至有失偏頗。如果把“中國”比喻成一棟大廈,他們雖然可以一覽中國這棟“建築”的“外觀”,卻永遠看不到其中的“內景”。中國學者的優勢就是可以深入考察近代中國歷史的“內景”。歸根結底,一切歷史研究都應先立足於歷史的內在因素,用發展的變化的歷史眼光去把握近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規律。中國近代史研究,真正能打破域外學者的歷史認知侷限,最終還有賴於中國歷史學者的自身努力。
再談《劍橋中華民國史》。該書在表面的篇章結構佈局和內核的問題意識根源上,與前述的《劍橋中國晚清史》相仿,除了統治中國的最高政治實體經歷了從帝制的大清王朝到共和的中華民國的轉變,敍述中國歷史發展邏輯的中心線索並沒有改變,著者還是更傾向於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場上發現中國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所存在的西方因素,從而推論出中國現代化程度的提升與西方的壓力和推力密切相關。尤其是在民國時期的中外關係方面,該書雖然也承認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參與程度和發揮作用日漸增強,但卻更多地歸因於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與英國、美國、蘇聯、日本等其他大國利益關係的權衡,反而很少着墨於中國自身利益的訴求和國內民族主義蓬勃發展的事實。而這一點恰恰對於理解20 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對外關係、外交政策與國際地位的發展變遷,有着至關重要的價值。
《劍橋中華民國史》的另一個特點是在述及由於中國特有國情產生的歷史現象時,慣以貌似中立的局外人身份加以評頭論足,特別是涉及關於中國的民族革命,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兩者的誕生、發展與糾纏的過程,在全書兩卷本的內容中佔據了相當大的篇幅。雖然説國共關係的分合及其背後的思想源流的確是貫穿整個中華民國時期的重要線索,但恐怕也與西方近代史研究中更加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不無關聯。概括而言,該書對中國革命總體的評價偏向負面,尤其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等方面,著者片面地突出和指責其“保守”甚至所謂“非正統”的一面,完全無視這些理論提出所針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定時空背景。這種脱離歷史語境敍述和評論歷史現象的做法正觸犯了歷史學的大忌,也是開展任何歷史研究都應當極力避免的錯誤。

中共一大會址
此外,《劍橋中華民國史》同樣有不少因對史料未加認真考辨而造成的史實上的偏差,對此,學術界已有較多論述,這裏不再贅述。這些“硬傷”的出現也勢必影響歷史論述的信度與效度。這對於中國的民國史乃至全體史學研究者而言,同樣無異於一種警示:在歷史研究和著述的過程中要竭盡所能保證史料來源和歷史事實的確實可靠,這是一條必須恪守的基本底線。
綜上所述,從“異域”的外部視角研究中國歷史,固然有可能得出“新觀點”“新結論”,但正如汪熙先生曾精闢地總結的那樣:“任何外來衝擊不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只有通過中國內部的因素才能起作用。中國社會內部自有其運動的規律,它必然會向前運動發展,並且最終決定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與結局。”儘管他同時也強調了在歷史研究中“外因與內因不可偏廢,這兩種取向應有機地結合起來”,但相較於外因,內因對於歷史演進卻具有決定性影響,這一點是任何人都不能避諱和必須牢記的。中國近代史是在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展開的,因此,當我們審視和研究這段歷史時,需要秉持長時段的、發展的、全局的眼光,防止史學研究成果流於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既不能教條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也不能盲目崇拜和迷信西方的學術觀念及其論著。由此,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國自主的歷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