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敏:弗洛伊德事件雖然鬧得兇,但社會抗爭力量已被馴服
【採訪、整理/觀察者網 朱敏潔】
觀察者網:美國黑人弗洛伊德被虐殺事件仍未平息。其實回看這幾年的新聞,類似黑人遭過度/暴力執法的新聞或是種族對立事件不斷髮生,為何這次會觸發如此大規模抗議?
**賈敏:**弗洛伊德虐殺案反應如此激烈,一是這次明尼蘇達州安納波利斯市警方暴力執法手段極其殘忍,長時間鎖喉的舉動突破執法底線,時間長達8分46秒。儘管當事警察會表示弗洛伊德此前有一定程度的拘捕和輕微暴力行為,但最終結果顯然讓公眾絕然無法接受。
二是本次事件因明尼阿波利斯市民在邊上用手機近距離拍攝整個暴力執法全過程並上傳社交平台,釀成病毒式網絡傳播。毋庸置疑,該視頻給人以巨大的畫面衝擊與震撼,刷新我們對殘忍的理解和認知。我們常説,世上最為殘忍之事,無異於將美好事物在你面前毀滅,而讓生命終止於眾人面前,更何以堪。被警察跪壓的弗洛伊德呼喊掙扎哀嚎,窒息昏迷前的無數聲“媽媽”令人心碎。這樣一番場景對毫無心理準備的人羣帶來的恐慌和震撼無法估量。遵循大眾心理學意義上的推演,最初的心態可能是惶恐、不安、進而產生難以名狀的憤怒和非理性情緒。在這個過程中,社交媒體所發揮的傳播作用無可替代。
三是與跟整個美國疫情狀況直接相關。弗洛伊德案5月27號發生,此前美國各州在特朗普政府鼓動下解除封鎖狀態,逐步解除暫停社會活動禁令。可以説民眾在家中足足兩月,這對生性喜好走動的美國人而言是極為複雜的感受,中國民眾應該有所體悟。面對新冠疫情,很多美國人失業並失去生活保障,心態扭曲,而此時又接受大量負面消息的縈繞衝擊,特別容易產生社會性聚集效應。我們看到事件爆發後絕大多數黑人社區全部動員起來。弗洛伊德之死好比一根點燃的火柴,把深陷疫情之中的美國瞬間點燃。
觀察者網:確實,您提到新冠疫情因素疊加這一點也很重要。有一個情況是,當地時間6月3日晚,美國官方發佈弗洛伊德的其中一份屍檢報告顯示,他已感染新冠病毒。這次抗議活動不能脱離的大背景是美國一直無法壓下去的新冠疫情,有統計顯示,黑人的病死率和失業率明顯高出一截,這其中是否是一連串的反應和升級?
**賈敏:**我們所能看到的美國困境只是冰山一角,關鍵是數據背後折射的意義。權威數據顯示本次新冠疫情非裔感染率和病亡率都大大高於白人民眾,真實情況可能更糟。失業率同樣如此,非裔美國人大多從事的是中低端服務與製造業。他們大都沒有條件居家辦公,不像都市中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白領人士,只能困守家中。疫情之下,他們是經濟上最脆弱的羣體,也是最容易受到其他階層歧視的羣體。
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疫情期間註定會發生的社會悲劇。不是弗洛伊德死,也可能是另一個非裔美國人,這是美國社會悲劇的縮影。人們之所以如此普遍憤怒,因為他們認為弗洛伊德是替他們受死,是整個美國社會對待非裔美國人不公平的必然結果。

觀察者網:弗洛伊德案發生後,6月3日前總統奧巴馬站出來呼籲,美國民眾引發真正變革,他的講話兩方面都很兼顧,一是覺得執法人員很艱難,對此表示理解,同時他又鼓勵黑人抗議才能改變現狀。這裏有一個問題是,現在很多黑人都在説要抗議,但問題是究竟抗議什麼?因為種族問題背後更大的問題是階級問題。這些街頭抗議會觸及到深層的社會結構或者制度矛盾嗎?還是説表達一下公平訴求就結束了?
**賈敏:**現在很難找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非裔美國人領袖。奧巴馬是黑皮膚的美國總統,但美國精英都認同他是一個接受過完整美式教育的知識精英人物,他的理念和綱領更為凸顯所謂的白人左翼陣營的色彩,儘管他的膚色是黑色。當然,問題是指奧巴馬能否真正代表非裔社區羣體的利益,能否真正喚醒和引領處於中下階層的非裔羣體。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通過近百年的努力,自內戰與重建時代以來得而復失的政治權利重新回到非裔手中,民權法案徹底終結了法律和社會意義上種族隔離存在的正當性,這自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經濟賦權上,作為整體的非裔羣體並未取得長足的進步,甚至全球化時代出現令人惋惜的倒退。過去六十年以來,非裔美國人在個體層面上不斷融入主流社會,精英輩出,湧現了最高法院法官、州長、聯邦參眾議員、四星上將、國務卿、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乃至黑皮膚的美國總統,這些都是非裔的榮耀。但整體上非裔羣體在社會經濟整體中的弱勢地位,讓非裔精英的成功始終面臨缺憾。
弗洛伊德悲劇發生後,看到包括奧巴馬在內的非裔精英幾乎傾巢而出發表言論,抨擊暴力執法,要求嚴懲當事人。但概而言之,非裔精英領袖大都還是號召一種激情抗議、尋求變革、通過達成交易和妥協來實現捍衞種族利益的應對策略,因為他們非常清楚,美國深層次的種族差異和歧視結構很難改變,弗洛伊德之死觸及很多,但難言推進系統性變革已經到來。
我們也能看到部分非裔意見領袖看待弗洛伊德事件站在和主流敍事的對立面,比如坎迪斯·歐文斯女士,她是共和黨保守派支持者。她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表達,弗洛伊德之死固然令人憐憫,但他不應被歌頌為英雄。她的觀點背後延續持保守主義立場的非裔精英的觀點,比如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的知名經濟學家、公共知識分子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所堅持的自由至上傳統。在索維爾看來非裔羣體不應被主流社會和其他族裔區別對待,被特殊化的非裔羣體將失去自身的特色與傳承,膚色不能永遠成為羣體的擋箭牌和換取食物券的便利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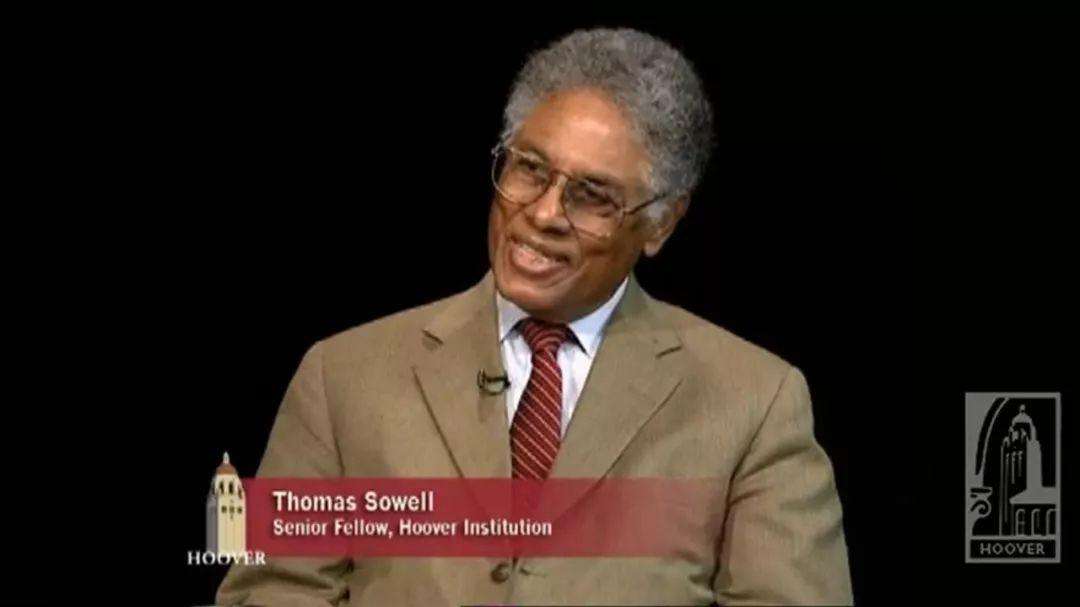
托馬斯·索維爾
60年代以來,美國非裔羣體爭取權利過程中逐漸開始走向分裂。通過大規模社會抗爭、社會運動方式爭取權力並加以鞏固的路徑,逐漸被精英羣體摒棄。非裔精英主流話語還是希望在既有框架下尋求利益的鞏固與擴大。如果我們把弗洛伊德之死看作是美國悲劇,那麼悲劇結尾上演內容的大概率事件是新一批非裔精英被權勢階層所吸納和展現,在聆聽他們為羣體發聲呼籲之後,下一輪悲劇循環又將開始。從美國曆史來看,非裔只有通過真正的社會抗爭,加之有利的國內外政治大氣候支持才能取得突破。這種力量當下很大程度上已經被資本馴服,進退維谷。
這也道出特朗普在弗洛伊德死後喋喋不休話語的原委:這位白人至上主義者並不掩飾自己的茫然與困惑,因為在他任期內,美國非裔的就業率創歷史新高(不算新冠疫情期間),非裔人均收入也再創新高,你們憑什麼説我對非裔一事無成呢?特朗普為什麼能拍胸脯這麼説?因為這是建立在他民粹主義政策之上的操作,比如特朗普跟中國打貿易戰,嚷嚷要讓製造業迴流,威脅跨國企業把中低端就業崗位帶回本土。那麼受益人是誰?當然是包括非裔羣體在內的美國中低收入和藍領勞工。事實上,非裔羣體與部分的美國紅脖子羣體是非常相似的,他們所處的社會與文化教育環境無法讓他們真正擺脱社會流動性枯竭帶來的詛咒。
從這個角度而言,以奧巴馬為代表的非裔精英提出的社會變革,只能是一個崇高的夢想。現實狀況是這種社會結構難以觸動、難以改變、難以化解。當然弗洛伊德之死,可能會成為一個嶄新的觸發點,這點未嘗不可能。但就當前美國社會整體而言,況且都對變革莫衷一是,爭論不休,缺乏一股真正主流的社會改革力量去推動進步,故而在短期內我並不看好。未來,弗洛伊德之死會成為一個象徵、一個隱喻,但談不上真正改變美國社會。我們找不到像上世紀60年代那般的NAACP(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組織,找不到有意推動美國社會進步的新政自由主義力量。當下的美國更多的是想借助弗洛伊德之死擴大己方陣營話語權,以及隨之而來對民意和鼓動大選投票的政治營銷手段。我們當然樂見美國在種族議題上能夠打破堅冰,但現實並不樂觀。
觀察者網:這就好比是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為黑人爭取了一些權益,解除了種族隔離,但無形的隔離仍舊存在,甚至到現在可能加劇。就此而言,現在美國社會中的黑人精英或黑人政客對於黑人社區的引領性有多大?還是説相互之間存在巨大脱節?
**賈敏:**我們都知道“美國夢”。如果換一種表達形式,那麼“美國夢”也可以理解為實現夢想的人脱離、或是退出原有社羣或階層,實現新身份的轉變。比如説通過個人奮鬥實現成功的非裔羣體。無論是奧巴馬伕婦,還是華盛頓特區現任市長鮑澤女士,他們都有共通特徵,即父輩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和不懈投入支持,因為他們堅持唯有通過教養來改變命運的信念。
這個信念同樣在美國非裔歷史上留下印記,比如20世紀初著名的非裔教育家布克·華盛頓,他同樣強調黑人的自立自強,特別是通過學習技能和教育改變命運。他説美國黑人不能乞討白人給予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美國黑人只能通過改變自身的方式,通過學習技能、學習白人的生活方式,最重要是通過教育來改變自身,融入主流社會。當然華盛頓的觀點後來受到嚴厲的批判,但我相信華盛頓懂得漸進變革的道路,在他哪個改變社會結構幾乎不可能的時代,他至少為非裔羣體贏得了體面和尊嚴。
弗洛伊德事件爆發前,民主黨陣營還出過一個不小的紕漏,網上還為此爭論過,即拜登陣營放言將會把非裔選票全都包攬,因為民主黨就是為非裔代言的。這就惹惱了部分非裔人士,他們在網上怒斥民主黨政客一直利用非裔選票,然而口惠而卻往往實不至,這場爭辯自然逃不過特朗普的點贊和煽風點火。弗洛伊德事件後拜登趕到休斯頓和弗洛伊德家屬私下會晤;儘管沒有參加追悼儀式,但是通過現場的大屏幕和錄播視頻,藉此表達他的族裔理念和競選主張。僅就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這種政治營銷策略來看,拜登無疑是加分的。
非裔政治精英與普通非裔之間的差距是在不斷拉大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歐文斯女士,在本屆政府中擔任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部長的非裔醫生本·卡森,他曾參加2016年共和黨黨內初選,後被特朗普延攬入閣。他的觀點和立場與共和黨保守翼完全一樣,所以説膚色並不能決定政治立場。美國特有的兩黨競爭模式是極為排斥第三股政治力量的出現,當然這是另一個大話題。

觀察者網:此前有一種觀點認為,種族隔離政策被解除之後,很多黑人精英開始脱離原來的黑人社區,希望更多地融入白人社區,這反而加大了黑人之間的裂痕,這些精英也沒有辦法對黑人社區起到實質性的模範作用。這就陷入您前面提的悖論,精英希望在社會中得到一定的權力和地位,只能脱離原本的黑人社區,產生一種階級性跨越。
**賈敏:**這種現象可以被稱為“退出”(exit),他想要成功就必須退出原本的社會階層。我前面提過的美國夢也包含這層涵義,對美國移民而言都是一樣的。大家應該還對楊安澤(Andrew Yang)印象頗深吧。他在疫情期間拋出的對華裔身份和膚色表示愧疚的言論相信大家一定記得,那麼所謂的“退出”概念就可以容易理解了。
在北美地區大規模的黑人奴隸貿易可以追溯到17世紀,這對非裔而言是一段巨大而無法根本彌補的悲傷歷史。從美國內戰結束到距今的150多年曆程中,數代非裔美國人尋求自由與解放之路,其中支流頗多,但主流是希望能夠融入主流白人社會,得到尊重和認可的。但正如我之前所談,非裔實現夢想之時,就是其脱離原有身份而跨入到另一羣體。然而一旦跨入後者,那就很難在回到黑人社區進行抗爭。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中就有一批人士看到了這種困境,提出了黑人權力(Black Power)口號,認為黑人必須掌握與白人鬥爭的力量和權力,才能徹底獲得解放和自由,代表人物有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 X)這樣的人士。當然之前還有一批親蘇和親中國的非裔知識分子。但這部分力量在70年代後就迅速解體分化了。現在我們耳熟能詳的非裔精英,他們留下的除了膚色外,與白人政治權力精英並無兩樣,有些人士表現的甚至更為極端,原來在彭佩奧手下工作的美國務院政策研究室斯金納女士就是一個非常有趣而荒誕的案例。
觀察者網:過去類似事件發生後,會激起美國右翼保守派(“紅脖子們”)的情緒高漲,並穩固特朗普的基本盤,但這次似乎沒有明顯跡象,為什麼?是話語失勢,還是特朗普基本盤在鬆動?
**賈敏:**特朗普的基本盤是不會動搖的。而且從各種民調綜合來看,特朗普的基本盤相對穩固,穩定在41%-45%之間,稱得上是“特朗普恆定值”。
至於説弗洛伊德事件沒有引起“紅脖子們”情緒高漲,應從兩方面來看。弗洛伊德之死是違反基本人性原則、洞穿底線的事情,所以對該事件的定性沒什麼爭議,確實是警察暴力執法,手段卑劣,是美國社會的悲劇。但是,隨後的街頭抗議中出現了很多打砸搶事件,包括衝擊政府部門,在白宮外圍遊行示威,已經引起白人右翼的不滿。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毫不掩飾地表示,要動用聯邦軍隊結束騷亂。科頓是哈佛畢業的新鋭南方政治精英,他的説法其實代表部分南方共和黨、特別是極右翼白人的想法。
最終美國軍方迫於各方面壓力選擇撤軍。但只要騷亂、反社會秩序活動存在,就一定會引起“紅脖子”的反感。特朗普高喊要秩序、要權威、支持警察的執法權,還是得到大部分“紅脖子”的認同。弗洛伊德之死是悲劇,但是不能因此衝擊正常的社會秩序搶劫商店,這也符合全世界對解決社會問題的一些普遍看法;既然是悲劇,那就通過司法判例、政治改革的方式去解決。
觀察者網:目前大選選情撲朔迷離,近期有幾份民調顯示,在幾個搖擺州拜登目前略高於特朗普。您此前舉過幾個關於美國現任總統因為國內抗議而連任失敗的例子,您對此次情況有什麼判斷?
**賈敏:**回顧歷史經驗,可以舉三個例子,一是1932年大蕭條最嚴重時期,美國爆發了一戰退伍老兵進軍華盛頓、提前領取退休金的行動。當時,胡佛政府派遣麥克阿瑟指揮彈壓,老兵們傷亡不小。這個事情對胡佛的政治形象衝擊很大,因為胡佛一般被認為是通過自我奮鬥成功的“美國夢”典型。1932年美國大選,民主黨大獲全勝,胡佛連任失敗。自威爾遜後,哈定、柯立芝再到胡佛,是共和黨長期執政的12年。1932年這場衝擊堪稱壓垮胡佛連任的最後一根稻草。
第二個例子就是1968年。1968年是美國歷史上極為動盪年份,學生運動、反戰示威此起彼伏。上半年先是約翰遜宣佈放棄連任,接着小肯尼迪在加州被刺身亡,接着又是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旅館陽台被刺,引發全美非裔的一系列憤怒聲討。8月,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大會場外又引發大型騷亂,一系列事件從根本上撕裂了佔據優勢的民主黨陣營。最終1968年大選,尼克松打着我代表“沉默的大多數”的競選口號入主白宮。充滿理想激情色彩的肯尼迪-約翰遜時代開始落下帷幕。
第三是1992年。老布什被認為是繼里根之後的又一位老派共和黨人,在他執政期間,最大的政治成就,一是終結冷戰,二是打贏第一次海灣戰爭。因此老布什在美國政治史上的地位很高。他的人品、個人修養都是政治家的典範。但不巧的是,他任期內的美國經濟遭遇到了拐點。1992年上半年的洛杉磯大騷亂,同樣因為警察毆打非裔青年,後被判無罪而引發眾怒。老布什隨後宣佈派遣聯邦軍隊進入加州平叛,出現不少人員傷亡,也損害了民眾對這位老派紳士治理內政與經濟的疑慮。這讓他當時的競選對手克林頓找到了機會,他指責老布什不懂經濟,提出“笨蛋,經濟才是問題”的競選口號。最終老布什惜敗於年輕的克林頓。從里根開始的近12年共和黨長期執政也宣告終結。

1992年洛杉磯大騷亂,美國軍警逮捕示威民眾。
從這三個歷史事件中可以發現一些共性:大選年出現大規模的社會騷動和族裔衝突,進而引發國家動盪和世界矚目的話,那麼對連任總統的政治壓力不可謂不大,其連任的可能性也要大打折扣。目前的一系列民調已經初步顯現出這種跡象。當然,歷史不會重複,馬克思認為,歷史第一次往往以悲劇出場亮相,而第二次則是以悲喜劇上演,這個隱喻用在特朗普身上再恰當不顧。特朗普絕對是美國歷史上最不尋常的總統,沒有之一。現在距離大選還有5個月不到,我們關注的或不是最後白宮誰能端坐西翼橢圓形辦公室,而是想象一番特朗普團隊究竟會祭出哪些驚世駭俗的大招來提升民意,震懾對手。至於拜登,我們看到他的支持率正在上升。我的觀點是,這不是因為他做什麼好事,而是幾乎沒做什麼事(疫情期間)。
我只能説從歷史經驗來看,凡是選舉年出現大規模社會性的種族衝突事件的話,對連任會非常不利,這是我的一個觀點。
觀察者網:確實,拜登近日民調支持率上升明顯得到這次種族衝突事件的加持。在此之前,民主黨選情一直呈現頹勢,拜登高調錶示要打“反中牌”,甚至比特朗普更強硬,這個策略會奏效嗎?換句話説,對民主黨來講,到底是應該“反特”還是“反中”?
**賈敏:**拜登對本屆中國政府領導人比特朗普認識更早,應該説交情不淺。事實上,就今年美國大選而言,雙方打“中國牌”基本上都算同路人,只不過略有差異。民主黨在針對中國進行打壓霸凌的記錄上,跟共和黨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涉及到宗教、民族和人權領域的議題,歷來咄咄逼人。
拜登要打“反中牌”,就要看他打的“反中牌”跟特朗普目前打的貿易戰、科技戰、地緣博弈等有什麼區別。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候選人在競選期間的政治綱領,跟他執政之後具體施政內容,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從這點上來講,拜登仍然是一個傳統的老牌美式政客,説什麼和做什麼之間有不小的差距。
可能我們現在過於適應特朗普“言必駟馬難追,行必不計後果”的執政風格。他基本説什麼就會努力去實現什麼。但我們得明白,特朗普的風格不是美國政治傳統的風格。如果拜登當選,美國政治有很大可能性回到原先的狀態。因此,我並不認為拜登會比特朗普更反中,也不認為他會比特朗普在某些時候更加討好中國。拜登更會去平衡民主黨陣營內的各種涉華議題和利益集團的想法。拜登的政治行為更可預期,拜登也會施壓,但會把“極限”兩個字拿掉。拜登會延續奧巴馬當年應對中國崛起而推行的亞太(現已升級為印太)戰略,安撫、利用並加強與地區盟國的軍事和安全合作,通過構建環繞中國周邊的聯盟體系鉗制中國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輻射。
觀察者網:確實,有一個問題是,美國普通民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關心中國問題、和他們本身面臨的問題有多大關聯,最終兩黨可能還是要回到美國自身問題上去?
**賈敏:**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沒有疫情的話,今年上半年的一個既定劇目可以這麼判斷:中美達成第一階段協議,雙方按協議進行,然後第二階段的科技戰可能開始重新興起,美國經濟表現良好,特朗普基本穩操勝券,然後對手民主黨可能會拋出特朗普的一些醜聞,經濟、個人生活等等。
按這個劇本節奏,中方跟美方其實都沒有想過在今年上半年大打“中國牌”,當然蓬佩奧一定會咬住中國不放,這和他的個人職業規劃有關。但疫情改變了一切,中國疫情從最初極為被動的形勢,到現在成為全球動員政府和民眾協同抗疫的典範,不想紅也得紅,你取得成功即便自己不想説,大家也會評論,中國必然成為一個榜樣,不去抹黑就是讚美,那麼美國政客做不到讚美,就只能抹黑。由此來看,炒作中國話題,可以説是美國政界的一個共識,因為他們不可能跟美國民眾説我們要學習中國,否則美國民眾會認為這是自我顛倒,他們必須要維持對中國的那套話語修辭的方式。
最近國務院新聞辦發佈了中國抗疫報告,非常詳實,就是用數據説話,不摻雜情感因素,前期確實有處理延誤、官僚主義的現象,但隨後迅速改善,一步步做的非常細緻與紮實,這其實非常符合西方人的客觀主義態度,有一分事實説一分話。但部分美國人無法接受,因為他們心態很矛盾。反過來,我們也要理解美國人的焦慮狀態,這種情緒瀰漫在美國精英階層中。可能普通美國民眾沒有這種感覺,但精英們的失落感、失敗感是非常強烈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消費中國可能也是西方精英找尋藉口,自我減壓的一種方式,可以理解但無法苟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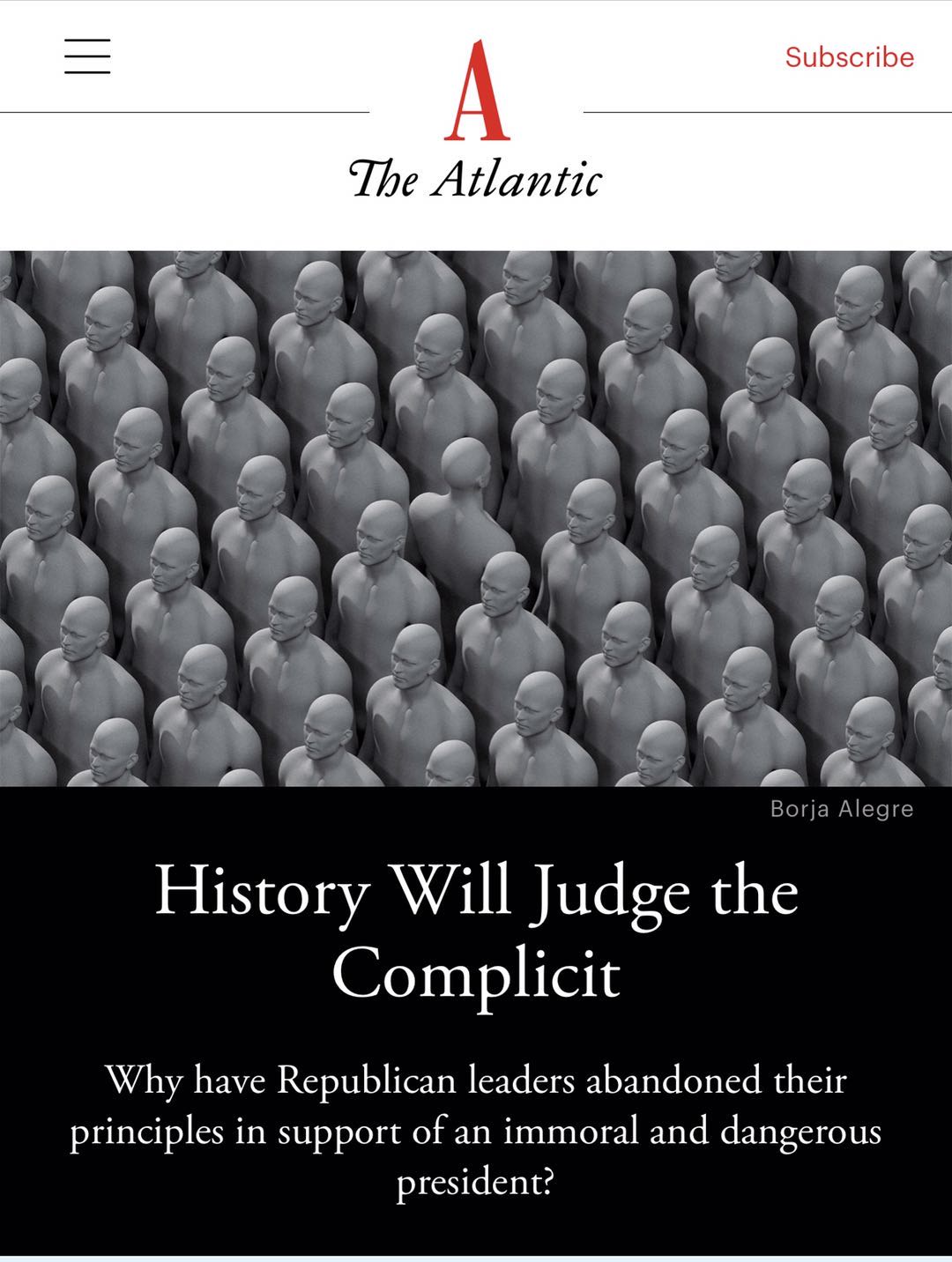
Anne Applebaum發表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
觀察者網:共和黨現在選情不樂觀,內部也有分裂;最近大西洋月刊發文批評共和黨4年前為了拿到政權,可以説“飲鴆止渴”,如今特朗普因為疫情和種族問題中的表現而遭反噬,如果連任失敗,會面臨官司或調查“清算”嗎?假設“清算”牽連到體制本身,會“默契地”停止嗎?
**賈敏:**大西洋月刊這篇文章的作者Anne Applebaum是一位波蘭裔作家,曾寫過《古拉格》、《鐵幕》等暢銷作品,在推特上一直批評痛罵特朗普。在我看來,這篇文章其實是在討論2016年以來共和黨人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真的甘心讓共和黨徹底“特朗普”化。
共和黨的“特朗普”化也是讓美國保守人士憂心忡忡的話題。現在的特朗普儼然可以通過推特賬號和向他的御用媒體(如福克斯電視台)等發出即時口號和各種評論,來掌控、引領、煽動整個共和黨。一些年輕輩的共和黨議員以得到特朗普的讚許和支持為榮,成為他們快速累積政治影響力的捷徑。這引起共和黨黨內相當一部分人的不滿,但懾於特朗普的民意基礎和旺盛的鬥爭態度,加之他確實在為共和黨基本支持者陣營的利益“帶貨”能力上無人可比,因此黨內大佬都默然團結在他身邊。這種在現代美國政黨政治中罕見的個人“獨裁化”傾向,引起美國知識精英的憂慮,是可以理解的。
文章批判的是共和黨人支持特朗普究竟是出於怎樣的一種心態,是利益投機、還是真的相信特朗普能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個問題戳中了大多數人心中的軟肋。我們看到,即使在特朗普犯下了一系列明顯違憲、危害國家利益、侮辱女性、拋出帶有種族歧視的言論和各種反理性話語的時候,絕大多數的共和黨議員們是保持沉默的,在頭頂的道德發展和內心的利益取捨之間,大多數人選擇了後者。已經去世的麥凱恩是共和黨老牌政治家中骨頭最硬的,他對特朗普的抗爭延續到了生命最後一刻。還有就是猶他州的參議員羅姆尼。其實還有很多人私下裏已經根本無法容忍特朗普的言行,但是為了政黨的利益和可能帶來的選票前景,多數共和黨人都樂於扮演“沉默的大多數”,學會聰明的容忍。
但是任何容忍都是有限度的,何況在美國這樣一個宗教與道德傳統極為深厚的國度。Applebaum的文章是在拷問共和黨,究竟你們能夠容忍白宮到什麼時候,那麼這次弗洛伊德之死還真的有可能變為壓垮特朗普和支持他的共和黨人的最後一根稻草。
實際上,共和黨內部的分裂從2017年美國大選結果揭曉後就存續至今。尤其是,去年年底美國非常著名的一份福音派雜誌《今日基督教》(Christian Today)公開發文反對特朗普引發軒然大波。紐約時報也刊登過共和黨內部林肯聯盟的反特朗普檄文,其標題為“我們是共和黨人,我們決心擊敗特朗普”,從道德高度和政治操守方面,呼籲黨內同仁與特朗普儘快切割,從國家利益角度寧願把票投給民主黨。這種表態其實在弗洛伊德事件後已經不斷在發酵,多位共和黨資深人士都公開宣佈將投票給拜登,星星之火,可以認為正在密切燎原之中。
我相信,某些共和黨人士會持如下觀點,“儘管特朗普不是一位有道德的人,但不道德的人依然可以實現有道德的目標”,所以無論特朗普做出多麼出格的事情,共和黨大佬們依然會團結在他身邊,矢志不渝。這種堅持選邊,不分道德是非的政治行為,凸顯了數十年間美國政治極化對政黨政治肌體的不斷腐蝕,同時也凸顯美國政治中不道德現象的普遍存在。薩繆爾·亨廷頓認為,美國政治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與張力,就是理想與制度之間各種關係博弈的結果。如果按照亨廷頓劃分的標準來看,當前的美國政治制度正在遠離政治理想和所曾牢固打下的憲政基礎,美國政治正在走向冷漠、自滿和自欺欺人的道路上,他們竟然能夠心安理得去接受,用非正義和非道德的方式去實現所謂的公正和道德目標,這不免讓某些西方人士愕然,一個老大黨如何能夠變得如此墮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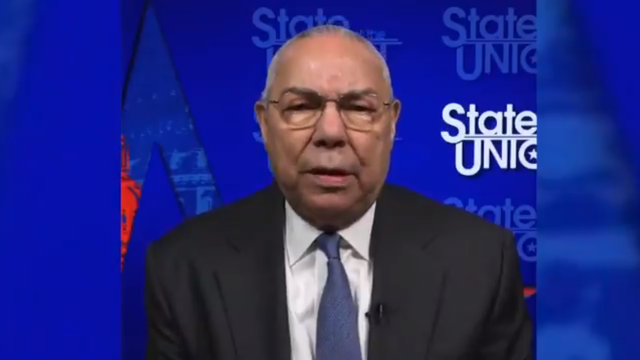
前國務卿鮑威爾痛批特朗普違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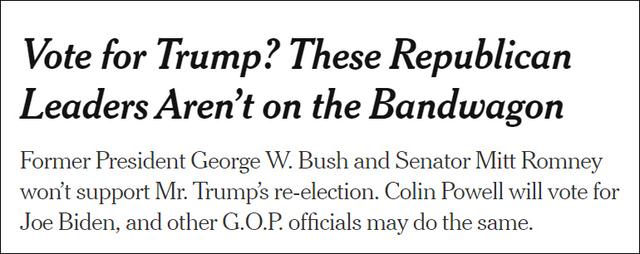
前總統小布什和共和黨參議員羅姆尼表示不會支持特朗普連任
觀察者網: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中美關係,毫無疑問疫情改變了世界秩序,也改變中美關係,最近有很多觀點,比如接下來近半年時間將是中美關係“至暗時刻”,世界秩序將永遠改變,中美實力處於關鍵轉折期等等,您對此有何看法?大選結束後,中美關係會因為當選者不同而發生變化嗎?
**賈敏:**我們之前認為今年影響大國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的因素,應該説有三個週期。首先是美國國內政治週期,包括兩黨博弈與2020年大選,其次是中美關係發展週期,包含兩國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邏輯,有交集有碰撞。第三則是新冠疫情週期。可以説,三個週期目前來講依然是互相疊加、相互影響的。
現在有種觀點覺得第一輪疫情在中美兩國都已退潮,可以不談疫情影響直接切入中美兩國間的戰略競爭和博弈,以及深度關注美國目前白熱化的大選競爭。事實上我覺得這種看法過於樂觀,我們需要聆聽來自專業人士,和歷史經驗的警示。比如上海的張文宏醫生,他一直提醒我們第二波疫情的必然到來。又比如1918年爆發的大流感,一共在美歐和世界其他地區出現了三輪大規模傳播,持續將近兩年事件。因此第二輪疫情的爆發是大概率事情。那麼起源地會在哪裏,是北美還是亞洲,會對脆弱的全球經濟復甦形成怎樣的影響?對此我們應該要有充分的認知預期,新冠疫情是當今思考國際秩序變動的最大不確定性,我認為談任何關係都得首先明確這點。
就上半年而言,疫情讓中美關係進入了新低谷,暫時想象不出還有哪些更糟糕的情況會出現。但是我們仍然需要一些想象力。中美關係的大格局變化,依然有確定性的存在。中國依然在崛起中,經過新冠疫情的重大考驗,中國的治理能力不斷完善,特別是針對公共衞生、傳染病防治和人民羣眾健康領域的制度設立和經驗總結,是值得充分褒揚的。我們可以非常明確的説,中國希望通過加強和改進國內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來塑造新的國家形象,進而引領全球治理的有序變革。外交政策始於國內變革,抗擊疫情提升了中國領導層和民眾對於治理的新認知,這種新認知帶來的感知變化也一定會傳導到中國人看待美國的態度中。
美國疫情應對如何自有公論,我們可以試着期待美國國內政治週期出現的傾向和變動。比如這次弗洛伊德事件是否會深刻改變美國的種族關係,綜合之前我討論的,系統性改變非常困難,但事件引發的漣漪和間接影響對下半年的選戰還是會有諸多衝擊的,進而對兩黨各自內部陣營產生影響。比如民主黨是否會趁勢追擊大打種族和膚色牌,拜登是否會選擇一位黑皮膚的競選搭檔;共和黨內是否會出現新的分裂,反特朗普力量是否會走向明處,而特朗普團隊又會祭出什麼新的大招,這些都是我們所關心和矚目的。
由戰略對抗、戰略競爭而形成的中美大國競爭態勢,很大程度上會延續下去。當然,大國之間最好的態度是既競爭又合作。第一波疫情中美兩國因國情不同應對舉措各有利弊,但兩國之間基本沒有合作是不爭的事實。從第三者角度來説,當然希望中美大能互相諒解,發揮真正的領導力,帶領全球共同抗疫情,分享經驗與成果。目前第二波疫情已經隱隱出現在地平線之上,那麼中美兩國發揮大國擔當,能否再次重新展開競爭,為後疫情時代的國際秩序做出新的貢獻呢。想象這種可能性需要很大的勇氣,但至少中國已經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全球衞生健康共同體的決心和動力擺在枱面上。我想這就是中國的態度,那麼美國這邊,暫時還看不到邊際,這就取決於美國國內政治週期如何轉變,取決於兩黨究竟如何看待美國的國運,取決於美國民眾究竟如何看待自身,以及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道路選項。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