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雨子:為何中國多年來一直拍不好體育電影?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聆雨子】
備受關注的《奪冠》,因為疫情影響,從春節一直延宕到9月底,終於和觀眾們見面了。
從賀歲檔重頭戲,到國慶檔前奏曲,這裏面的定位差異,難免讓人擔心。畢竟,所謂檔期,從來都指向特定節令特定的觀看訴求,前者重在閤家歡,後者重在獻禮,衝着前者去的電影忽然投奔後者,能不能順利地對接預期?
好在《奪冠》有其特殊性:賽場爭光、稱雄世界、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這樣的題材,反而與“十一”前所需的民族驕傲感珠聯璧合。
被動調整,成了價值本位的迴歸。
值得關注的是,去年國慶有《中國機長》和《攀登者》,今年則是《奪冠》,電影質量先不論,至少題材上指向的都是特定的職業或運動項目,上面所説的“獻禮”這件事,已在不知不覺間,從偉人領袖建功立業的革命史詩,外擴到了每一個領域裏的、由普通人創造的光輝業績。
只要好好幹,誰都有資格成為這個國家的“主旋律”,這當然是讓人欣喜的、該由電影普及給整個社會的時代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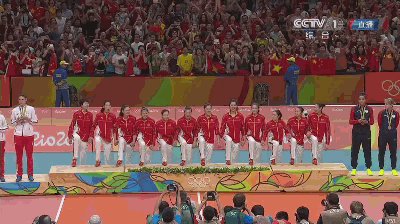
亟待突破的類型盲區:運動題材的中外對比
從類型劃分來看,《奪冠》當然屬於“運動題材”——耐人尋味的是,這一直是國產電影相對貧瘠的區域:銀幕上的中國體育形象非常單薄,與國際賽場上爭金奪銀的強勢地位嚴重不匹配。
謝晉執導的《女籃五號》產生過不小的社會影響,但它屬於一個過去的時代和一種過去的文藝樣態:一對母女在解放前後經歷截然不同的事業境遇,該敍述模式散見於“十七年”時期各種作品內部,體育只是表現新舊社會落差的一個背景板,把它換成工業、醫療、文藝等等,故事一樣能講順溜。
這之後的《沙鷗》、《跳水姐妹》,再之後的《女足九號》、《京都球俠》、《女帥男兵》,近年的《我是馬布裏》以及韓寒的《飛馳人生》,體育電影零打碎敲、時有時無,翻來覆去計算,也就數出十部左右,總量少、關注度低、沒有經典也沒有爆款,都是不爭的事實。
只有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出於應景,體育題材有過一個小陽春式的扎堆,但從質量上看:《大灌籃》羣星雲集卻成了公認的爛片,卡通二次元向的風格也沒多少推廣意義;《一個人的奧林匹克》講述往昔的屈辱歲月,屬性上更接近歷史人物傳記;《買買提的2008》口碑尚可,但它與其説是運動題材,不如説是兒童題材和鄉村教育題材。
僅有的幾部帶來過一些新氣象的作品:《翻滾吧!阿信》、《破風》、《激戰》,還都來自香港或台灣。

電影《翻滾吧阿信》動圖
有人統計過,一整部中國電影史,體育類作品幾乎沒有獲得過任何主流獎項,也幾乎沒有躋身過任何一年的票房排行榜前列。
作為對照,自1977年史泰龍主演的《洛奇》摘得小金人開始,體育電影便始終在奧斯卡保有穩固的席位,《憤怒的公牛》、《百萬美元寶貝》和《弱點》先後捧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多項桂冠。
這背後,自然是好萊塢極其強大的生產機制和創作能力,總能將全美先進的電影產業與根基深厚的體育基礎多維結合,醖釀出跌宕起伏的情節、呼之欲出的表演與精良的視覺效果,將運動本身特有的激情澎湃和百折不撓,發揮到淋漓盡致。
即使是中國周邊近鄰們,日韓不乏《哭泣的拳頭》、《馬拉松》、《菜鳥總動員》、《棒球夥伴》等佳作(這還只是説電影,還沒把構成幾代人成長記憶的《灌籃高手》、《足球小將》以及《排球女將》計算入內);俄羅斯票房冠軍《絕殺慕尼黑》去年登陸內地院線,看得觀眾驚心動魄;至於印度的《摔跤吧!爸爸》,那更是現象級神片。

印度電影《摔跤吧!爸爸》動圖
以人觀己,委實汗顏。
情況何以至此?
許多人做過分析,可在我看來,那些被分析出來的理由,反而愈發證明了我們對體育電影缺乏正確認知。
比如有評論講,中國運動題材的癥結在於“體育人不懂電影,電影人不懂體育”,這幾乎是一句廢話。隔行隔山,體育與電影本就是兩撥從業者,普世皆是如此。也沒見美國哪位導演是運動員出身,或者歐洲哪位奧運冠軍棄武從文、折桂柏林戛納威尼斯。
比如又有評論講,中國體育電影煽情過度、不是把自己當催淚彈就是當勵志雞湯,這次《奪冠》開映,這類批評再次甚囂塵上。平心而論,真有點刻板印象與欲加之罪。國產片確實常走入説教和灑狗血的誤區,但要説這世上最不怕“情緒飽滿”的,還就是體育題材,畢竟運動天然和腎上腺素、和多巴胺、和“上頭”、和“熱血中二魂”有關,信任、友誼、勇氣、理想、堅韌、勵志、動情,這些看着老套的關鍵詞,從來都是這個類型的基準訴求和本體特徵。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問題在於視野,以及格局。
第一,各位不難發現,上述國產片多是些化整為零的細碎故事,其發生地或在古代、或在校園、或在鄉村、或在社會邊緣,它們更像是“和體育有關的電影”,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體育電影”。
現實當中,奧運會亞運會世錦賽世界盃各種國際最高競技舞台上,那麼多被體育迷們津津樂道的比賽、那麼多耳熟能詳的明星健兒、那麼多熱血沸騰的榮耀時刻,電影人始終沒勇氣去正面觸碰。
成功的運動題材,除了“一個人在一項比賽中找回自我”及“勝負不到最後一刻總是未定的緊張刺激”這些標配,往往還會附着於一個更加宏大的東西之上,除了對手和錦標之外,它往往還要去戰勝一個其它東西,或者説,建立一個其它東西:
《光榮之路》和《成事在人》是種族平等、《摔跤吧!爸爸》是性別平等、《點球成金》是數學和智慧、《鐵拳男人》是生活與責任、《馬拉松》是走出自閉症、《一球成名》是與誘惑和人性弱點共存。
第一點是“迴歸那些最具有現實土壤、最具有社會認知度的、打動過最多人的經典的體育”。
第二點是“從體育走向那些可以建立在體育之上的、起於體育又高於體育的價值本體”。
誰能做到這兩點,誰也許就能改寫中國體育電影的命運。
當女排遇上陳可辛:羣體記憶的銀幕重建
陳可辛一直是那種特別聰明和敏鋭的導演,以至於你很難為他的主體風格下定義,“我是一個生意人”是他的夫子自道,傳遞的核心信息是:觀眾們最需要什麼而市場上又最缺什麼,那我就去拍什麼。
尤其他北上內地之後,從《中國合夥人》、《親愛的》到《七月與安生》,無不如此。
所以他一定會捕捉到近兩年愛國情懷持續發酵的大環境,然後為這個大環境,找到一個恰當的釋放端口。
有意思的是,呼喚本土運動電影的突圍時,不少專家和影評人都提起中國女排:唯一稱雄過世界的團隊項目和大球項目,時代號角,巾幗英雄,全民族的興奮劑。
要拍體育,還有誰比她們更當之無愧?

於是,陳可辛遇到中國女排,意料之中。
“最具有現實土壤、最具有社會認知度的、打動過最多人的經典的體育”,這個命題一下子被這場邂逅解決了。
事實上,他也確實承擔起了填補類型空白的責任,拍出了“體育電影”裏必須要有的東西(而不再僅僅是“和體育有關的電影”裏裝進了一些和體育搭邊的東西):
一個人和一羣人,對一項運動、一份職業的精神信仰,彼此的支撐和喚起,個性飛揚的理想主義,見證歷史,積極且堅韌的生活態度……
平行剪輯行雲流水,幾條線之間互文工整。比賽內部的起承轉合。大量筋肉、傷痕、汗珠、淚水的特寫。適時的消聲,適時的現場聲。恰當的細節道具和細節台詞,在特定場合的復現來鋪下動情點,比如很多年後,再次於電視機前穿上那件一人織了幾針的毛衣,比如隊友葬禮上的重逢,袁偉民依舊斬釘截鐵“別掉隊,都跟上”。
但這還不夠,類型的必備要素夯實之後,還要有提升要素,規定動作完成之後,還要有加分動作。
於是就牽出了前面所説的:“從體育走向那些可以建立在體育之上的、起於體育又高於體育的價值本體”。
那個更加宏大的東西是什麼?在言説中國女排的同時(背後),電影還可以言説一些什麼?
從合格走向優秀,就看這一步。
《奪冠》裏那個更加宏大的東西,叫做“中國和中國人走過的這三十年”,在言説中國女排的同時(背後),電影還在進行羣體記憶的打撈與温習。
從這個意義上,《奪冠》有一種年代圖文志的意藴,它以中國女排為線索,幫我們想起了很多很多:曾經那些樸素的、真摯的、純粹的、發自肺腑的感動和激昂。
我看《奪冠》的時候,身後坐了好些老阿姨,她們一直在啜泣。想必都是來同一個記憶符號裏,啓封青春的。
用一些真實的人物,在其半生沉浮裏擴展出許多許多真實的年代,這是陳可辛在《中國合夥人》裏就做熟了的事情。
雖然這些年對唯金牌論的反思也提供了許多理性的有價值的聲音,但必須承認也必須理解,對一個曾被烙上過東亞病夫惡名的國家來説,用競技體育的勝利來自證民族尊嚴的渴求(甚至可以説是執念),這種羣體情緒的歷史合法性並不應該被嘲諷。

所以“被體育點燃的愛國情緒”成了本片不變的底色。
但這個底色的不變裏,依然有漸變存在,畢竟這個底色洇過了太長的歷史時區:
上世紀80年代剛剛重返國際賽場的榮譽飢渴,那是極致的艱苦和勵精圖治,不知道對手已經走到了哪一步的焦慮,只能用玩命來賭一場籌碼不明的局。
雅典登頂的君臨天下式的黃鐘大呂,和08年猝不及防的失敗與低谷,那是拿到了一切之後,註定要到來的調整、回潮,甚至“都什麼年代了,體育不過是一場遊戲”的自我懷疑和消解。
里約的王者歸來背後,是更加直接更加多維也更加外向的情緒,是“休息,去談戀愛吧”的理念革新,是新鮮的營養、管理、訓練、經費使用模式,是個性十足的許多人:朱婷的家境、惠若琪的性格、曾春蕾的委屈、張常寧的習慣、陳鹿的選擇。
它們的呈現形態是不一樣的。它們裹藏着三個階段不同的羣體情緒。我們都以自己的方式走過這三個階段,我們都參與過這不同的羣體情緒。

《奪冠》劇照(圖/豆瓣)
值得注意的是,它使用的符號,或者説話語體系,是“為國爭光”這個抽象的、甚至是老派的表述,但這個符號下歡欣鼓舞熱血沸騰的,卻是一代代實實在在的、依然保有內心青春熱情至少是青春回憶的人。
要把這些實實在在的人的生命體驗裏和中國女排相關的部分、把這些青春熱情和青春回憶裏被中國女排所引領所撫慰所激發的部分,給整體複述出來。然後,它就會兼有當下的神聖與過去的鄉愁。
可以説,它為很多現實生活中稀缺與急需的、擺出來一本正經灌輸又顯得説教味過濃的品質,提供了一個舞台化的情境,讓它們變得非常自然而動人,重新被大家估定了價值並給予了敬重。
勇敢、熱血、堅強、合作、信任甚至是一根筋的執拗和有點目中無人的霸氣,這些東西被日常性的功利因子所間隔了。體育給了它們一個迴歸的理由,而且迴歸得那麼自然、那麼水到渠成。
所以很多人才説,體育是和平時代的戰爭。因為它自帶一種史詩味道。
還有一點很難得的是,在電影裏,這些情緒並不帶有攻擊性。僅有的一次民族主義憤怒稍縱即逝,而且指向的也是最終的英雄郎平。
它不是要去戰勝誰、碾壓誰,更不是要去羞辱什麼或者向什麼討回公道,它只是要超越和實現自己、只是要去呈現一種力量和風貌。這毫無疑問,更符合健康積極的體育精神。
誰都知道她們贏了,那懸念從哪裏來:敍述困境及突圍策略
是時候探討一下《奪冠》的敍述難度了。
很多人想當然地覺得,沾了中國女排這種金牌IP,五連冠、漫長的低谷、再次崛起、換帥、逆轉、登頂,這麼多現成的戲劇性、這麼多現成的情緒爆點,都給你準備好了,“換了我去都能拍好”。
殊不知,這些要素,全是雙刃劍。
“為當代修史”引發的來自真實人物的顧慮和異議,直接導致了之前的改名風波,這個見仁見智,各方立場不同,此處姑且不提。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羣像戲不利於聚焦,可能會拆散本來就缺乏凝聚力的劇情動能。
好在有郎平,還有陳忠和(尊重當事人的異議,影片裏從沒坐實其具體姓名,儘管大家都知道)。
用郎平串聯,這個選擇不需要評價為恰當,因為沒有更合適的選擇:從選手到教練,從離開到歸來,當過主心骨當過救世主甚至還當過對手,連際遇都跟中國女排高度同步,第一次爆發之前的長期沒球打,第二次逆襲之前的被責難被懷疑。想不出還有誰更合適,來把三個時代接續於一身。


現實中的郎平與鞏俐飾演的郎平
陳忠和則從一個初始的外來者視點,逐漸滲入到內在者視點,再抽離成“比內在者更加富於責任感的旁觀者”,在各個角度裏詮釋冠軍為什麼可以成為冠軍,提供了另一種故事節律和韻味。
三場比賽,兩個人,他們亦師亦友,甚至還“亦敵”過。他們當初都很邊緣,後來都創造過輝煌。他們鬥智時知己知彼,講解戰術高度同步。她的改革,他是第一個甚至唯一一個支持者。他主動退出競選推她上位。他幫她的隊員找回初心。
陳可辛導演在被問到電影中他最感動的橋段時,給出的答案就是郎平帶領年輕的中國女排獲得奧運冠軍後,打電話給陳忠和讓他聽國歌這段。
這一刻,他們實現了合體。這兩個人,是《奪冠》故事的節拍器。
另一個問題則更加麻煩:這電影打一開始就“沒有懸念”。
中國女排這一路走來的波峯和低谷,觀看者早已如數家珍。文體不分家的時代,郎平和一干隊員無不是高曝光率的公眾人物,經歷甚至性格、情感也都被大家熟稔。
在故事被拿出來講述之前,就已經“誰都明白這個故事裏的每個人是怎麼樣的,誰都明白這個故事的結尾會發生什麼”。就連具體的起承轉合都被提前公佈了,反正那一屆屆大賽一場場決賽,我們都追過直播。
那我們還看什麼?
答案有兩個:我們曾經激動過,我們想等等看,能不能在電影裏想起那個曾經激動的自己,甚至,能不能在電影裏再激動一遍;我們知道她們贏了,我們想仔細挖掘一下,她們是怎麼贏的。
對前者而言,觀眾們這次要的不是一個結果,而是這個結果對某種高光情感體驗、對某種感動與榮耀的喚起,就像它曾經在賽事直播時喚起過的那樣。甚至,有了文藝渲染的加成,這喚起還應該更刻骨銘心、感人肺腑一些。
有一種懸念是what(很多商業電影),有一種懸念是why(很多作者電影),有一種懸念是how(電視劇),這裏的懸念大概是when:我什麼時候,才能重温歡呼。
“結果延遲”變成了“滿足延遲”:騰躍、扣殺、攔網、反吊,一次次做成慢鏡頭和升格鏡頭,一次次插入閃回,用每個比分牌上的落後來蓄勢,賽點時刻總是主動靜音一片死寂,歡呼以後,又會全程播放國歌。
俗套,但是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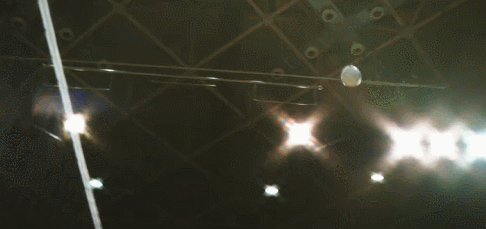
對後者而言,這回在大銀幕上看比賽,看的不是怎麼跌倒爬起在輸贏之間反轉(這些當初都看過了),而是怎麼佈局怎麼做戰略怎麼知己知彼怎麼調動怎麼給自己打氣怎麼形成凝聚,看的是鬥智、鬥心眼、乃至於鬥氣場。
這也幫助陳可辛在商業性之外,一定程度地堅持了他的作者性。當然,負面影響就是,對於完全奔着“爽”走進影院的觀眾而言,這片還是有些“文”。
每場比賽前的一大段會比較温吞,進程的緊張刺激度也略顯不足(如果和《絕殺慕尼黑》那樣的文本相比),跌宕起伏不是特別明顯,連大高潮都不是登頂冠軍的那場。
但如果把自我預期管理建設成:看的就是幕後、是發展、是堅持、是成長,那它依然提供了一種更禁得住咂摸的厚度。
當然,本片絕對不是完美的,很多情節、很多角色都給人一種“往深處挖一下本可以更好”的遺憾。可我依然不想否定它在很多場景裏的動人。
一支隊伍幾十年的跌宕起伏,無數的集體回憶,幾代人的花樣年華,歷史給了最佳的故事藍本了,體育題材獲得了開疆拓土的補課,有這些,也夠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