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洛聞:多此一舉的香港“記協”,誰最需要?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常洛聞】
香港警務處9月22日發函,修訂了《警察通例》中關於“傳媒代表”的定義,新規定之下,在香港政府新聞處等級的傳媒機構,和在世界範圍內受到認可的非本地媒體簽發的記者證方可視作有效。
如果還記得去年“修例風波”以來香港記者以及所謂“自有媒體人”的舉動,應該對香港警方的這條修改深以為是。香港政治和社會深受所謂“言論自由”之害,是到時候撥亂反正了。
當然不出所料,函件發出後,香港記者協會、明報等利益相關方反映強烈,再次指責香港警務處、香港政府“破壞新聞自由、削弱第四權”等,並聲稱將申請司法複核,以推翻警方的決定。

明報對警方函件的轉述基本準確,即使只看明報縮略節選的要點也能看出,要通過香港政府新聞處登記並不難,最低要求僅需要一名編輯,一名記者即可,連打麻將都要兩家這樣的“傳媒機構”全勤才能成台。但標題偷換概念,將修訂記者證的許可範圍,變成了警方不承認記協這一組織和合法性。
為什麼明報、記協異口同聲地指責香港警務處和香港政府呢?香港警務處並非不承認“記協”,而是點破了記者協會尷尬的小算盤——如果是服務於傳媒機構的全職記者,無需通過記協一樣能以記者身份工作;如果服務於網絡媒體,或以自由撰稿人身份服務於多家媒體機構,仍然可以以所服務的機構名義,通過政府新聞處註冊,取得采訪資格。記協作為行會,為何要多此一舉,給記者發放記者證?除了記者之外,到底誰需要記協?
玄機在記者證之外。

表面上,落款裏這些“聯會”“行會”和傳媒機構、出版社之間互不相關,每個機構都標榜自己如何“獨立”,實際上他們對很多近親繁殖式的勾連根本不加掩飾。所謂的“新聞自由”不過是壟斷解釋權和財權的遮羞布。
記協2018-2019的“執委會名單”中,立場新聞與蘋果日報均是鼓譟黑暴的始作俑者,在其中工作自然是與黎“同氣連枝”。包括現任主席楊健興先生在內,標稱供職於其他媒體的幾位“主筆”,基本都是因為“理念不合”而從TVB和南華早報“離職”,實際上與壹傳媒關係匪淺。之前的幾任“主席”,如李月華、岑倚蘭等,更是黎先生愛將,在香港或台灣蘋果日報長期身居高位,在台灣、香港兩地來往穿梭。
落款當中落在最尾,但卻能與明報、壹傳媒平起平坐的“眾新聞”是鏈接這些人的一個平台。眾新聞自稱是一個通過“眾籌”資金運營的“獨立媒體”,核心人員是“一羣資深傳媒人”。這羣人包括誰呢?包括了“資深新聞工作者李月華”,“前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前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2019香港記協執委會主席楊健興”等。名單是不是很熟悉?
眾新聞自稱靠眾籌生存,“無黨無派”,可是2017年成立後,目標300萬,二十多天只籌集到了30萬港幣——不過是目標的十分之一,結果在香港這樣一個成本高昂的商業社會不但沒有倒閉,反而連連得獎,一直做到了2020年。它的運營成本從何而來呢?
先給各位看官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眾新聞”得的是什麼獎呢?這個獎的名頭大了,叫做“人權新聞獎”。獲獎內容中一沒有難民在歐洲國家的身影,二沒有日韓等美國盟友的新聞,三沒有美國少數族裔遭遇的不平等問題,彷彿在他們的眼中,西方國家沒有人,也就沒有了人權問題。

人權新聞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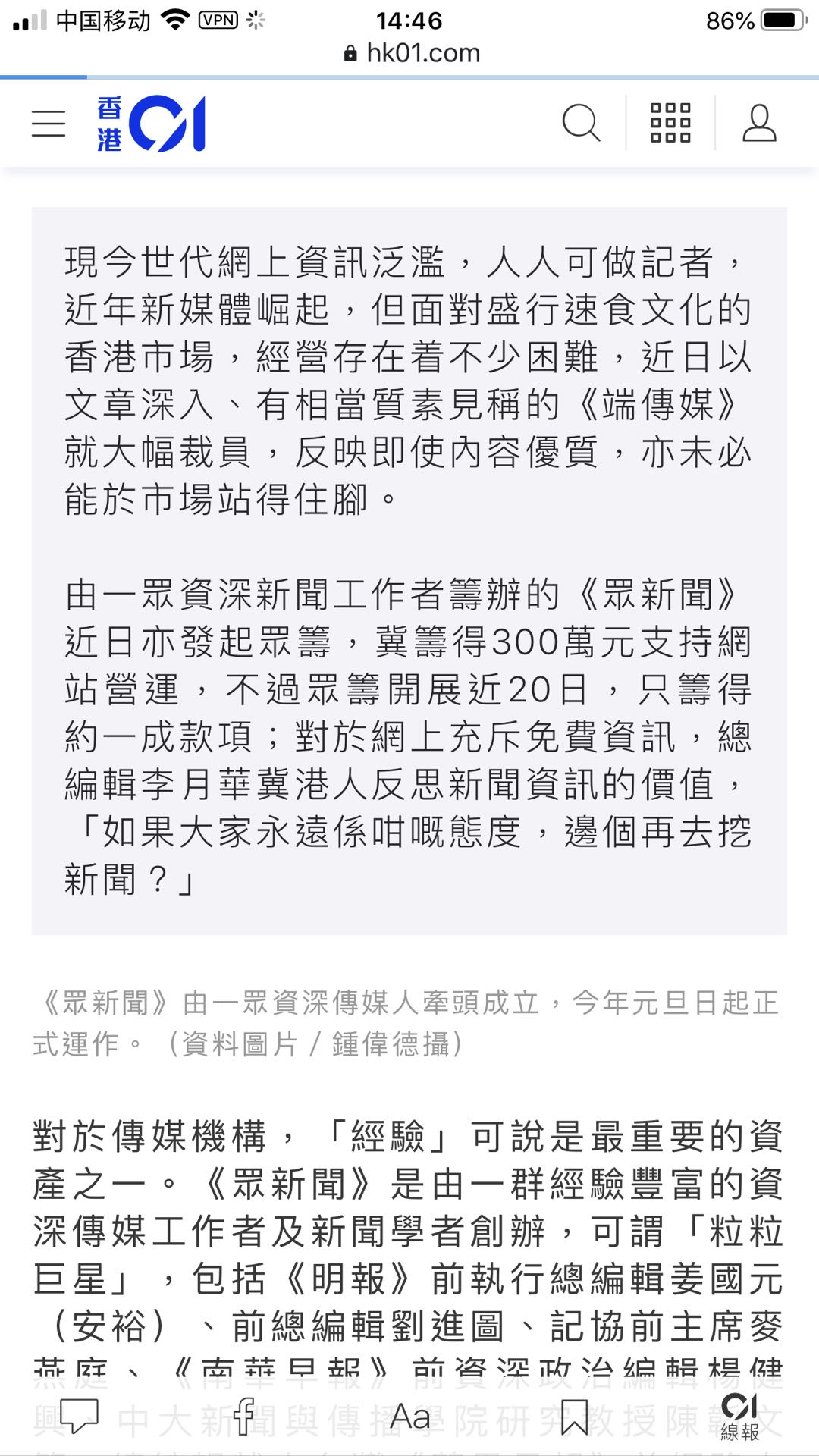
眾新聞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篩選結果?是因為“專業”嗎?不,是因為人權新聞獎的籌辦機構是這幾個:香港外國記者會,香港記者協會,國際特赦香港分會。
前兩個不用説了,國際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也翻譯為大赦國際,是一個總部設於倫敦的非政府組織(NGO),一直在世界範圍內推動“人權事業”,包括推動廢除死刑等。在此引述兩條外界對這個組織的評價:
印度學者Arun Shivrastva撰寫的《Helping or Hurting》中指出,大赦國際與無國界記者等組織一樣,用NGO外衣為西方利益服務,輸出意識形態,採取雙重標準,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北愛爾蘭獨立運動遭到血腥鎮壓,南非種族隔離,波多黎各獨立等問題上長期刻意消音,卻對某些國家的事件有着異乎尋常的熱情。
伊利諾伊大學的Francis A. Boyle曾經擔任大赦國際美國分會董事,他長期批判猶太復國主義,在他的《NGO與顏色革命》一書中,他認為大赦國際董事會和捐助者的親以色列傾向,以色列與英國密切的資金關係,導致大赦國際和美國分會對1950年以來,以色列的屠殺和軍事行動無所作為,大赦國際背後的首要動力不是人權,而是政治、宣傳,其次是金錢,增加成員,再次是內部勢力爭鬥,然後才是人權。
這一機構曾頒發良心大使獎予昂山素季,後來在2018年撤回。2019年5月,該組織秘書長因為無法忍受“有毒的工作環境”自殺,高層地震,數名高級員工收到了“慷慨”的遣散費,同一時間段,有多名基層員工因為預算不足被解僱。
記協和外國記者會自稱獨立,且收入主要來自會費和賣書,那這個“人權獎”的金主是三家機構中的哪一家呢?説好的“無黨無派”,“保衞民主”,“持平公正”,怎麼變成了記協主辦評獎,然後發給記協的人掌管的機構,再用這個獎反過來作為記協標榜“爭取人權”的證明,自產自銷,自投自搶?如此拙劣的把戲玩得不亦樂乎,真的只是可笑嗎?
記協的主要收入是會費,正式會員常年在600人上下,設立若干委員會給正式會員們參加,附屬會員(不以新聞工作或記者收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公關會員(公關行業從業人士)、退休會員數量不定,對外宣稱的“學生會員”只有59人。正式/附屬/公關會員會費100元港幣/年,學生會員會費20元港幣/年。

“修例風波”中並不乏“學生記者”
“次要收入”是什麼呢?香港記協是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的會員,如果香港記者需要赴國外採訪,理論上必須花600多塊港幣申請記協發出的國際記者證,但以我自身的經驗,只要機構具有足夠的影響力,名片和工作證,最多加上機構出具的函件,足以滿足工作需要,不需要記協額外“開光”。而港澳台記者赴內地採訪,一般有對口機構發出按年註冊的港澳記者證,以及活動、會議期間有效的工作證,記協無法幫助香港記者跑得更快。
根據這些公開的數據,不難算出香港記協每年的收入。只有“賣書”一節,交易是現金居多,印數、銷售額、碼洋折價比例無從查起,賬本數字無法做準。如果真的“獨立自主”,還要供養這麼多委員會,發放如此多出版物,以香港一份報紙十塊錢的物價,恐怕香港記協一邊要在本地賣到人手一本會刊,一邊要遷址到北緯30度以北地區,才有足夠的西北風喝。
這次警方修改《通例》針對的,恰恰是記協濫發的會員證。所謂會員,只需要一名現任會員推薦,交表交錢即可。黑暴動員的主力“學生”只要以學生證副本應付即可過關(文匯報對此有深入報道),即使是會員也並不是新聞工作者,不過沖鋒陷陣之後會有記協出面“罩住”,甚至提供法律援助、通知家人“收拾東西”等一條龍服務,增加警方的成本,令警方逮捕難起訴更難。
進入記協成為正式會員之後,如何評選執委會“主席”,如何進入核心,並無民主過程,從不公佈投票權的人數、比例,也不公開執委會選舉應到、實到的人數,至於是否有投票選舉,有效、無效、棄權票各是多少,更是諱莫如深。與其説是“介紹”之後“評審”是否足夠專業,還不如説是“招募”之後“篩選”,看是不是“自己人”,能扮演什麼角色。整個模式與其説是行業工會,不如説是香港一直盛產的“社團”更為恰當。
香港記協附着於記者這樣一個不賺錢的行業上,到底要幹什麼?
1991年,香港迴歸近在咫尺,港督衞奕信全面接受《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快速通過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將立法局、港督權力大幅度稀釋,1993年,末代港督彭定康為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力,一夜之間忽然民主,針對新聞、廣播、電視、報紙等媒體的審查大幅度放寬,例如刪除了行政部門基於保安理由撤銷電視運營牌照的權力等。
行政權力消解帶來的空白被英國、美國資助的NGO迅速攫取。記協在其1994年“香港言論自由年報”中,曾名為“擔憂”實為威脅,以“香港本地並無對等概念”為由,批評保密、國家安全立法,這一立法確如記協所期望,在港府遷延23年,釀成大亂後才由人大以全國立法的凌駕性方式強行處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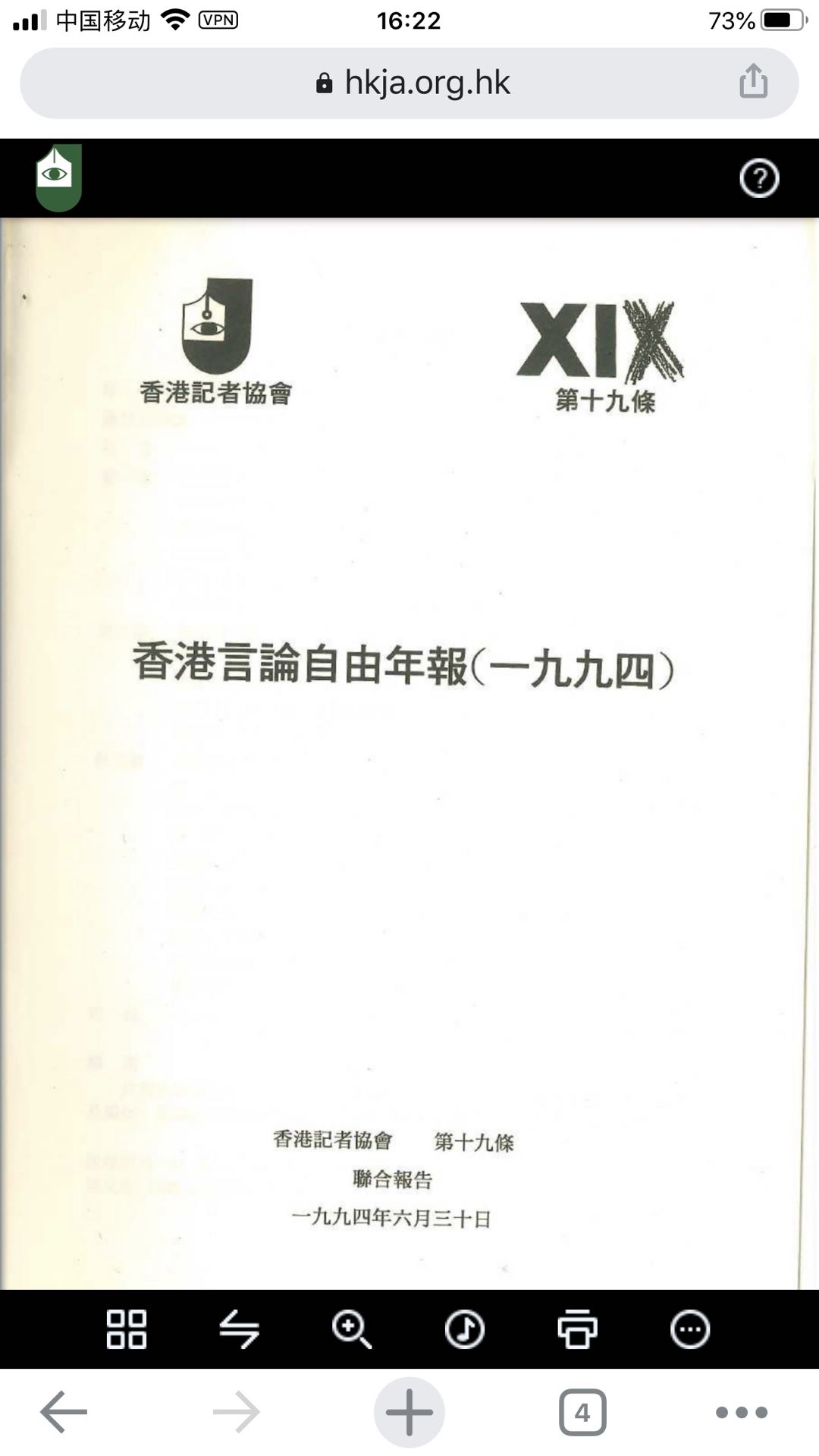
同一份報告中還毫不避諱地説明,記協認為基本法不能凌駕於香港本地法律,香港最高法院的權威不能受全國人大制約,無論是港英政府還是迴歸後的香港政府,都必須在記協表達“失望”後,“知所決擇”。所謂“第四權”參與爭奪治權的企圖,從來都是陽謀。
之後幾年,記協並未將“報告”全文公開於網上,僅列出部分標題如下,導向如何,不言自明:

以人均GDP計,香港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但也是世界上最封閉的市場之一;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落後的生產關係仍然苟延殘喘的“孤島”之一。在被動開放的過程中,本地的既得利益者,和倚靠壟斷、准入門檻、制度壁壘發財吃飯的人,必然會為了維護利益而維護現有的落後制度,甚至為了短期利益與另有心思的勢力合作,“記協”所販賣的是一張薄薄的卡紙,這張卡紙居然就成了“解釋權壟斷許可證”、“話語權高地准入證”,證件一出,公權畏手畏腳,私人避之不及。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不改變“許可證”、“准入證”的土壤,就算“記協”歸正,以後也會有其他“邪”再現香江。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