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那些曾經對深圳的批評
【文/張軍】
在深圳特區成立以來,人們對它的批評就不絕於耳。這當然並不難想明白,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左”的思潮依然流行,因此在深圳實行特殊的制度試驗和開放,引入“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和生產方式,在政治上是有一定風險的。在姓“資”姓“社”的問題仍然是一個核心理論問題的時候,爭論的焦點自然首先在特區的制度是否符合社會主義的性質上。于光遠先生的回憶提供了一個小小的片段:
“當然事情並沒有完。1982年的1月,冷空氣大量南下了,北京有一個單位制定了白頭文件,題目是‘上海租界的由來’,説的是清朝末年由於上海道台的腐敗,帝國主義在上海設立了租界,我們因此喪失了主權。這是攻擊搞深圳特區的人的語言,意思是説搞特區不是搞社會主義,有一段時間這樣的輿論鋪天蓋地而來。另外,又發生了一個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問題。1982年4月22日到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專門為廣東深圳而召開的會議,主持人最後講話説,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方針必須進一步統一認識,我認為深圳搞那麼大的規劃是不現實性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無邊,深圳特區面積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特區的總面積還要大,這麼大的一塊特區面積,全都搞起來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吳南生説他手邊有這個人講話的原件,他是按照這位同志的原件唸的,原件中還説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人想和計劃經濟脱鈎,想割一塊出去自己搞,我認為搞計劃經濟是客觀需要,不是哪一個領導想怎麼搞就怎麼搞,你想的是不可能的。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日本、美國、法國認為要搞計劃經濟,南斯拉夫搞得太自由化了。事實説明不搞計劃經濟是不行的。計委的主要任務是搞好綜合平衡,按客觀規律辦事,計委工作要有全面的觀點,不要怕困難,不要怕得罪人。”1

經濟學家于光遠
於老自己認為深圳特區的制度是符合社會主義性質的。1983年第2期的《經濟研究》發表了於老的文章《談談對深圳經濟特區的幾個問題的認識》。他的主要理由是,深圳特區不是政治社會制度的特區而是經濟政策和管理的特區,而且特區裏仍然有公有制企業的主導地位。可以想象,他的這個看法並不會得到多數人的認同。有的學者認為深圳特區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受到社會主義國家和政府的控制。大多數老一代經濟學家比較傾向於認為深圳特區的性質就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個論斷。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先生在《北京週報》1984年1月21日發表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他認為,設立深圳特區的目的是通過收買政策實施同國外資本和華僑資本的合作,引進他們的技術和管理,最終是發展社會主義。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政府靠收買政策發展與民族資本主義的合作在性質上是一樣的。2
當中國內地的老一代經濟學家正在為深圳特區紛紛定性的時候,1985年5月出版的香港《廣角鏡》第152期發表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陳文鴻的文章《深圳的問題在哪裏?》,也開始對深圳特區5年來的試驗結果進行評估和質疑。有人稱這是打響“特區失敗論”的第一槍,而且揭開了深圳“第一次大圍剿”的帷幕。
陳文鴻的文章得出的結論是:中央和深圳政府對深圳經濟特區的期望,是建成能發展成為以工業為主體的綜合體經濟,可是,深圳事實上直至目前而言,工業仍從屬於貿易,經濟是以貿易為主。就這方面而言,深圳這方面的成績還未如理想。這個結論來自他的簡單而“定量”的分析。
根據他的分析,第一,資金以外資為主、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是中央給深圳定下的發展目標,深圳特區尚沒有做到所説的三個“為主”。1983年進口大於出口,引進的主要是被中國香港、日本淘汰不用的設備;引進的外資只佔30%,這30%中又主要是港資;1983年深圳工業總產值7.2億元,而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為12.5億元,做生意賺的錢比工業掙的錢多得多。
第二,陳文鴻指出,特區其實賺了內地的錢。他在文章裏詼諧地説:“更妙的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買了一把折骨傘,發現竟是從上海送去香港,又轉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興,説是比在上海買少花了幾塊錢;深圳人也高興,説賺了幾塊錢。香港百貨公司也高興,同樣説賺了幾塊錢,真不知誰見鬼了!阿凡提到井裏撈月亮。”
第三,陳文鴻又對深圳的貿易模式提出了批評。他認為深圳的經濟是依賴貿易的,而在貿易中又主要是對國內其他地方的轉口貿易,無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轉口商品主要是進口商品或包含相當比例的進口商品。外引內聯的資金之所以投資深圳,主要是因為這個龐大的貿易和由此而來的高利潤。深圳5年多發展以來的表面繁榮,也主要根植在此。
有意思的是,陳文鴻文章所引用的數字,幾乎全是摘自內地或者特區報刊公佈過的。陳文鴻通過對這些數字的邏輯推理和估算來得出結論。例如,陳文鴻實際上是根據深圳公佈的1983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和人口總數來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會購買力高達4170元人民幣的結論的。而在同一時期,上海的人均社會購買力為912元,北京為896元,廣州為504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廣州高出七倍多。這顯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文章得出結論認為,深圳的市場繁榮,主要是靠內地顧客來維持的。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的經濟學家還多以概念和定性分析見長,而陳文鴻的文章雖然簡單,但卻是“讓數據説的話”。所以,文章雖然沒有涉及深圳特區的性質,但卻提出了讓那些關注深圳特區性質的人感到鼓舞的問題與結論。而且,顯然讓人耳目一新的文章風格在那個時候肯定最具殺傷力、影響力和傳播價值。於是,文章一發表,引起譁然。而如果是在互聯網的今天,陳文鴻的名字定會紅遍中國大江南北。
其實,根據我的記憶,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不僅僅是陳文鴻,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對深圳特區有相似邏輯的批評。這裏讓我想起1992年9月我初到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時與華大偉教授的一場對話。華大偉教授不幸在2007年8月病逝於英國。我前面曾經提到,華大偉先生在那個時候正在從事關於中國特區和沿海發展戰略的研究。我到了薩塞克斯大學之後就去辦公室找他。他對我説,那個時候正在為世界銀行準備一個評估深圳特區的背景報告。他拿出了一些他寫就的有關的文章。他對我説,希望我能幫助他收集一些資料和數據,同時也能參與他的這個項目。我問他對特區的基本評價是怎樣的。他直截了當地説,經濟特區是一個扭曲的環境。它像磁石一樣把內地的資源吸引過去,在短時間裏產生耀眼的光芒。
正在這個時候,在成都的《經濟學消息報》的主編高小勇先生與我聯繫,希望我在英國期間能為《經濟學消息報》寫點評論文章或者開一個專欄。我答應了並開始動手寫一些評論。有一次我對華大偉建議,也許我可以把他關於深圳特區的文章編譯出來,在報紙上發表。於是《經濟學消息報》不久在第一版就發表了華大偉的文章。題目是《發光的並不都是金子》(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他説這是他在中國的報紙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那是1993年。
他的這個觀點,我當時並不十分同意。我認為他總是無法擺脱西方主流的概念和框架來審視中國,因而在研究中國問題上總是持批評態度的。不過,他對中國非常友好,這些批評也顯然是善意的。我們從那時候起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每年在中國和英國多次見面。我還策劃並編輯出版過一本他的研究文集。只是我們之間並沒有任何研究上的合作。

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再次來到深圳。
總之,在深圳特區建設的最初階段,尤其是特區的試驗在黨內和政治上還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深圳遭遇到這些來自學術界的批評自然就備受關注了。在這種背景下,鄧小平1992年1月的“南行”中才再一次來到深圳,發表一系列針對深圳特區試驗的講話,而且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這之前的那場爭論的火藥味。
鄧小平1992年1月19日再次來到深圳。他在深圳參觀過程中説:“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1月23日鄧小平在深圳開往珠海的快艇上還説:“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説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變。”
他最後説:“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願意幹就幹,幹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3
不搞爭論,那是政治上的務實和策略。但爭論的過程確實讓更多的人去思考了這樣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局部性的改革和試驗改革,儘管有其策略性的意義和價值,的確會產生局部與整體經濟體制的落差,如果處理不當,將引發普遍的“尋租”現象。事實上,在一些經濟學家批評深圳特區的管理體制時常常會用發達國家的“企業園區”(enterprise zones)或者國際上流行的“出口加工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s)作為參照組。深圳特區在當時顯然已經超出了“出口加工區”的概念,也不再是完全封閉的管理體制。不僅如此,深圳特區還在鼓勵和促進與內地省份和內地企業的經濟聯繫(所謂“內聯”)上大做文章。這本來是一個推動深圳特區的善意想法,但在實際上誘導出了越來越嚴重的內地企業利用深圳這個特區而尋求“直接非生產性尋利”(UDP)現象。這算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
我清楚地記得,1993年我還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時,我的同事陳志龍教授也參與到華大偉教授的研究項目中,並受邀專程來英國考察“企業區”,瞭解英國一些老工業地區實施特殊政策待遇的“企業區”(類似於我們的“開發區”)的體制和管理模式。後來他回到上海寫了不少內部研究報告遞送政府部門。也就在這個時候,中央政府醖釀多時的關於擴大開放地區的政策也出台了。在我的印象中,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早期那種備受關注的尋租現象逐漸消退了,説明在深圳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特區試驗所產生的局部扭曲效應基本消失,更大範圍和地區的體制趨同在加速發生着。這就是特區試驗的目的。
註釋
1.歐陽薇蓀,《于光遠談鄧小平與深圳特區》,http://www.hznet.com.cn/kjdt/hzkj/2004/0004/hk2404t02.htm。
2.轉引自[韓]樸貞東著,《中韓經濟特區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頁。該書在1997年還出版了英文版:Jung-Dong,Park,1997,The Speical Economic Zones and Their Impact o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Praeger Publisher。
3.轉引自蘇東斌主編,《中國經濟特區史略》,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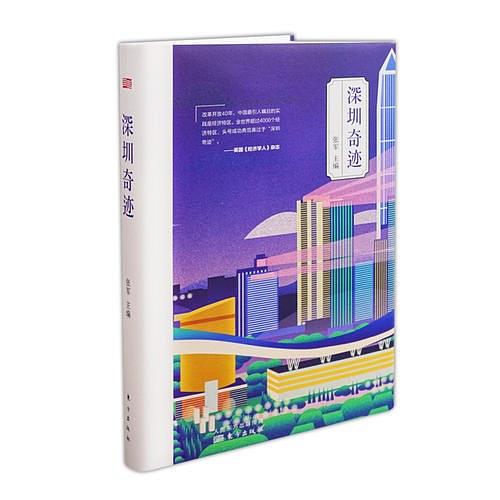
《深圳奇蹟》,張軍主編,東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