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美援朝70週年特稿 | 劉小楓:戰爭紀事與戰爭的歷史真相

歐洲歷史上的戰爭數不勝數,畢竟,“歐洲的版圖是在戰爭的鐵砧上錘出來的。” [1] 但直到19世紀,歐洲人關於戰爭的紀事或史書並不多見。德意志30年戰爭(1614-1648)在歐洲現代史上非常著名,相隔100多年後才有席勒(1759 - 1805)的《三十年戰爭史》(1793)問世,而席勒恰好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第二年(1790)動筆撰寫此書,這恐怕不是巧合。
畢竟,德意志30年戰爭還有另一個史學名稱——德意志“宗教戰爭”,而席勒開卷就提到,儘管這場戰爭讓德意志顯得退回到“古老的野蠻習俗”,一種可以稱為“普遍的國家同情”的新政治意識的產生“足以抵消世界公民在這場戰爭中所遭受的驚嚇”。在席勒眼裏,德意志30年戰爭無意中為法國大革命的“文化火炬”播下了火種,以至於歷史的“勤勞之手不知不覺地再次抹去了戰爭所留下的災難性痕跡”。[2]
法國大革命爆發那年,米肖(J. F. Michaud,1767-1839)才22歲,當時他是堅定的保皇派政治記者。拿破崙稱帝之後,米肖追隨夏多布里昂(1768-1848)追慕中世紀,花近10年功夫寫了三卷本《十字軍東征史》(Histoire des croisades,1812-1817),很快被譯成英、德、俄文,因敍述生動且富有文采“竟得以摻進聞名全歐洲的詩人、作家的著述之中”。為了完成這部史書,米肖效仿希羅多德那樣遠行各地收集史料,但要説他的這部戰爭史有多符合史實,還真難説,因為他把11至13世紀的十字軍東征視為法蘭西民族成長史的一部分,以至於把它描繪成了法蘭西人民的歷史驕傲,而現在(拿破崙戰爭展開之際)“西方人再次轉向了東方地區”。據説,米肖的這部戰爭史“在一代又一代革命中經受了決定性的考驗,這些革命能夠改變或修正人們的品位、道德和制度”。[3] 這無異於説,即便拿破崙戰爭最終失敗了,它也與十字軍東征一樣成了法蘭西民族成長史的一部分。

陷入薩拉丁軍隊包圍之中的十字軍(1877)
要記敍一場歷時多年的戰爭,需要獲得大量相關信息,現代通訊出現之前,要做到這一點相當困難。20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關於這場戰爭的紀事書和史書也不算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資訊業急速發展,新的戰爭紀事寫作羣體——記者形成了,戰爭紀事和史書隨之猛增。最早的中印邊境戰爭紀事,就出自一位澳大利亞籍的英國記者之手。[4]
由此出現了一個政治史學問題:戰爭紀實與理解戰爭是一回事嗎?戰爭是人世間最為複雜、最為極端的政治行為,理解一場戰爭意味着理解人世間的極端政治現象。在歐洲歷史上,記敍戰爭的作家都獲得了史學家兼文學家的聲譽:席勒既是文學家也是史學家,撰寫《華倫斯坦傳》的蘭克(1795-1886)既是史學家也是文學家。記者出身的紀事家也得收集大量史料,敍述同樣得講究文學性的謀篇和敍述,從而既是史學家又是文學家。倘若如此,與傳統的戰爭紀事相比,記者身份的戰爭紀事最為明顯的特性便是更為逼近戰爭的年代和真相。問題來了:什麼是一場戰爭的歷史真相?
美國的“修正主義”朝鮮戰爭紀事
朝鮮半島上的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際(1952年3月),美國著名的“左翼報人”斯通(1909-1989)出版了一本小書《朝鮮戰爭內幕》(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史稱第一部關於朝鮮戰爭的“史書”。其實,這是一部新聞報道類作品,“依據的完全是美國政府和聯合國的文件和英美兩國著名報紙的報道”,儘管斯通自己覺得,他記敍這場戰爭的歷史“就像在寫小説”。畢竟,當時戰爭還在進行之中,他“周圍是一種全面戰爭的氣氛”(斯通,“作者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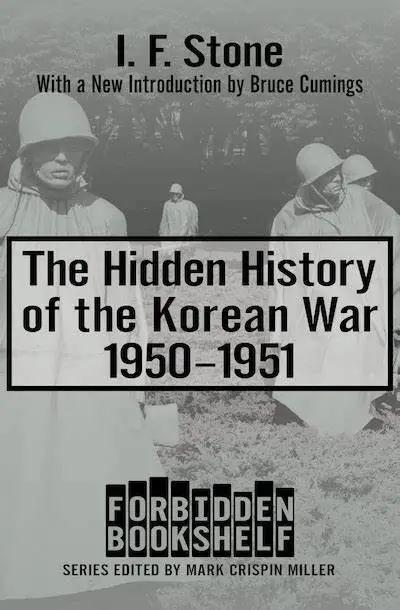
斯通運氣不好,這本小書出版時撞上了“麥卡錫專制”的風口浪尖:麥卡錫神志不清地指控説,美國在朝鮮半島上遭遇重創,首先應該歸咎於羅斯福(1882-1945)在雅爾塔會議上“把中國和波蘭出賣給俄國”。由於麥卡錫及其追隨者的壓力,美國的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使國內外感到震驚的禁書和焚書事件”。[5] 斯通認為這場戰爭是李承晚(1875-1965)在美國的暗中幫助下挑起的,《朝鮮戰爭內幕》很快被扣上“通共”嫌疑的帽子遭到查禁,斯通本人也被牽涉進“維諾那計劃”引出的共產黨間諜案受到調查。直到“維諾那計劃”被證實是美國中情局搞的一個陰謀後,斯通的“通共”嫌疑才得以洗清:他的確是“親共”的美國左翼報人,但談不上是“間諜”。[6] 筆者很久以後才知道,斯通就是那位70歲開始學古希臘文,並以此年齡窮10年之功寫了一部蘇格拉底傳的“斯東”。[7]
《朝鮮戰爭內幕》出版差不多20年後(1971),美國在越南戰場深陷泥潭,知識界甚至軍界的“反戰”之聲此起彼伏,斯通的這部紀事作品重獲新生,成了名副其實的“史書”。因為,該書引用了大量1950年6月至1952年元月美英媒體對這場戰爭的報道。
出版社重版《朝鮮戰爭內幕》時用了這樣的推介語:
斯通先生的這部著作是控告書,它確實是有史以來對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最為強烈的控告書之一,而它現在卻仍鮮為人知。[8]
美國海軍學院的戰爭史教授艾姆布魯斯為斯通的書撰寫了重版序言,其中寫道:
中國人從來不希望戰爭,他們也不想支持北朝鮮,是麥克阿瑟逼迫他們這樣做的。俄國人的情況也如此,他們都沒有介入最初的戰爭。這場戰爭的起因只能從朝鮮北南之中去尋找,而不是有人所説的,是克里姆林宮或北京的擴張陰謀導致的。這場戰爭沒有在1950年底就結束,麥克阿瑟可以説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罪魁。(斯通,頁3)
這位戰爭史教授憑靠軍事常識知道,朝鮮半島戰爭不可能是“克里姆林宮或北京的擴張陰謀導致的”。但這場戰爭的起因是否“只能從朝鮮北南之中去尋找”屬於政治史學問題,他的説法未必正確,畢竟,“戰爭的起因”絕非僅僅是軍事問題。克勞塞維茨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原話為“戰爭無非是政策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未必恰切,或者説,人們對這句名言的理解有誤:毋寧説,戰爭意味着政治通過暴力手段來解決靠其他手段無法解決的問題。[9]

美國國內的“反越戰運動”
至於“麥克阿瑟可以説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罪魁”,恐怕會冤枉這位五星上將,儘管麥克阿瑟剛愎自用,且因極端“反共”而不惜與日本法西斯政客合作,對戰爭的擴大化罪責難逃。原因在於,
自從美國積極捲入世界事務以來,朝鮮戰爭第一個成為考驗文官統治的主要實例。在朝鮮戰爭中,由憲法和制度規定的文官統治受到了徹底的考驗——非常徹底,事實上幾乎經受不住考驗。[10]
這無異於説,美國介入朝鮮半島內戰表明,美國的民主政體本身有問題。為此提供證明的是,麥克阿瑟與杜魯門的衝突事件觸發了年輕的亨廷頓(1927 - 2008)從“軍政關係”角度考察美國的憲政制度及其與美國分裂的意識形態的關係。[11]
隨着“反[越]戰運動”升級,美國人越來越覺得,朝鮮戰爭是美國打的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斯通的《朝鮮戰爭內幕》問世30年後(1982),美國的政治作家古爾登依據美國官方解密文件和軍政要人的憶述以及對諸多當事人的採訪寫了《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Kor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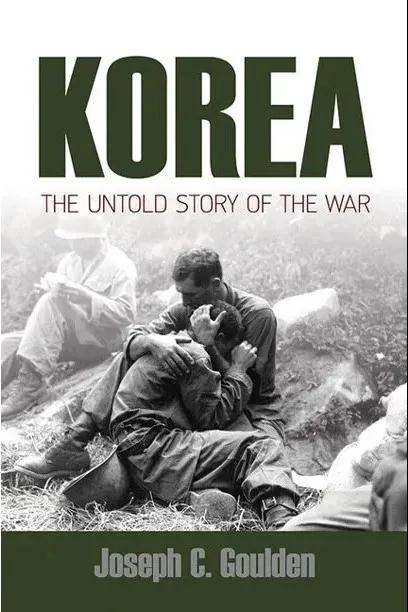
古爾登曾長期在軍方從事情報分析,後投身新聞業。在他看來,朝鮮戰爭是美國的恥辱,因為它是美國國家領導人“魯莽輕率”“傲慢自大”的結果,即便腦子清醒的參聯會也應該“對戰爭中出現的失誤負有重大責任”。
朝鮮戰爭是美國第一次沒有凱旋班師的戰爭。美國使朝鮮處於僵持狀態,同中國這個龐大而落後的亞洲國家打成了平手。儘管美國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所有武器,但中國以人海戰術和對國際政治巧妙的縱橫捭闔,制服了美國無比強大的技術力量。[12]
這是古爾登對美國介入朝鮮半島內戰的基本評價。“愚蠢的戰爭”也好,“在美國公眾看來”朝鮮戰爭“不受歡迎”也罷,古爾登僅僅要表明“美國在一幫平庸之輩的領導下備受磨難”(古爾登,頁7)。
過了不到5年(1986),亞歷山大依據美國軍方檔案和軍史材料撰寫了一部朝鮮戰爭戰史,他為自己的書選取的書名是“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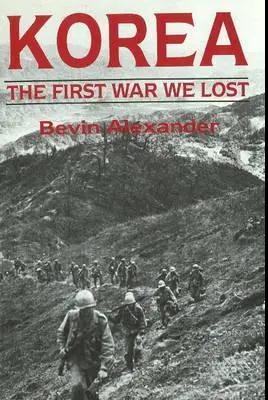
亞歷山大親歷過這場戰爭,他從軍事史的角度得出如下結論:
美國未能打贏朝鮮戰爭,這使美國領導人深感不安。因此,他們在戰後20多年的漫長歲月裏,總在想方設法地傷害阻撓美國取勝的紅色中國。[13]
亞歷山大寫這本書,並非因為當時中美正在走向“貿易伙伴”關係,兩國即將開始長達20年的合作期。
如果我們以為這類持“反韓戰”立場的戰爭紀事書在美國佔據主流,那就錯了。美國著名軍史學家米勒特(Allan R. Millett)獲得過“終身成就獎”,他撰寫的兩卷本朝鮮半島戰爭史的書名並非如中譯本書名那樣富有詩意,而是具有直白的政治含義——《他們為朝鮮而戰》(Their War for Korea: American, Asian, and European Combatants and Civilians, 1945-1953)。副標題“美國、亞洲和歐洲的作戰人員和文職人員”清楚表明,所謂“他們”指聯合國軍。
在概述文獻時,米勒特不屑於提到這些具有“反韓戰”立場的戰史紀事,僅僅籠統地稱之為“修正主義”史書,它們“反映出美國人民對朴正熙將軍在韓國的獨裁統治以及口是心非的約翰遜政府幹預越南的不滿和憤怒”。[14]米勒特轉彎抹角的修辭不外乎要説,這類紀實作品帶有政治立場,所謂“紀實”未必符合史實,似乎他才具有客觀立場,儘管他承認,要做到這一點的確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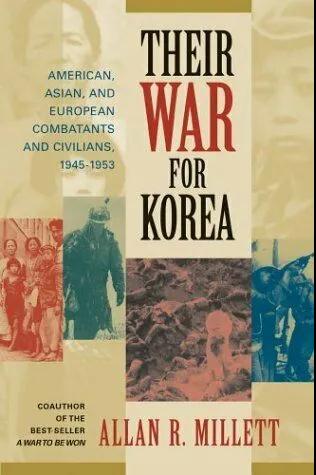
“修正主義”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説幾乎完全陌生,上年紀的人才會在塵封的記憶中回味到這個語詞帶有的尖鋭鋒利。米勒特用這個語詞一筆帶過1970年代至1990年代美國人寫的朝鮮戰爭紀事,意味着此前曾經有一個關於朝鮮戰爭的正統敍述,但被“修正”了。
的確,自1950年代末以來,美國知識界不斷有關於朝鮮戰爭的追憶或研究問世。據説,美國朝野對朝鮮戰爭患有“國家性遺忘”(national amnesia),關於越戰的出版物汗牛充棟,而關於朝鮮戰爭的書籍卻寥寥無幾——這種在我國坊間長期流傳的説法並無根據。
據麥克法蘭的《朝鮮戰爭研究文獻錄》(1986)所載,從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美國關於朝鮮戰爭的出版物(書籍和文章)已多達2300種,儘管從軍事角度記敍或研究的居多(亞歷山大,頁594)。[15]不難推想,所謂“修正主義”式的朝鮮戰爭紀事在美國恐怕僅僅算是一種“聲音”。所謂the Forgotten War[被遺忘的戰爭]或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未曾透露的戰爭真相]一類書名,並非指關於朝鮮戰爭的書籍很少。毋寧説,此前美國關於朝鮮戰爭的紀事或研究講述美軍遭受打擊時的悲慘遭遇的書籍很少。
在美國,朝鮮半島戰爭史的正統敍事的基調是“為了自由民主而戰”——米勒特的《他們為朝鮮而戰》遮遮掩掩地與此一脈相承。萊基的《衝突:朝鮮戰爭史(1950-1953)》出版於1962年,迄今還是美國施行政治教育的權威讀本(甚至有了電子朗讀版),該書的扉頁題辭是:To Those Who Fought for Freedom in Korea[獻給那些曾為朝鮮的自由而戰的人們]。[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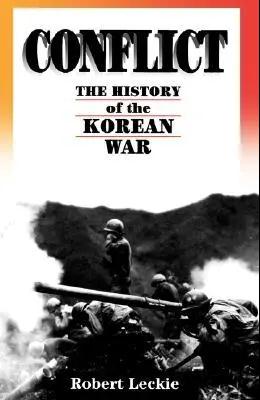
萊基把美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對手一律稱為“共產主義者”,事實上,麥克阿瑟的確是帶着與“共產主義者”決一死戰的信念堅持要打一場清教式的“全面戰爭”,甚至不惜“把戰爭擴展到中國本土”(斯帕尼爾,頁219)。我們若以為這僅僅是所謂“冷戰意識形態”的反映,那就錯了。畢竟,麥克阿瑟是“充滿魅力的人物”,他“同幾乎是宗教性質的神秘主義聯繫在一起”(亨廷頓/2017,頁348)。
美國作家託蘭(1912-2004)因撰寫20世紀的紀實性政治史而聞名於世。除了善於敍事,託蘭撰寫戰史注重對親歷者的採訪。用今天的話説,託蘭的戰爭紀事基於口述歷史——他的朝鮮半島戰爭紀事就屬於這類作品(米勒特/下,頁568)。
這並不意味着託蘭撰寫的戰史紀事就具有所謂的客觀性。他的《生死之戰:朝鮮1950-1953》(In Mortal Combat:Korea,1950-1953)出版(1991)後,隨即被譯成了中文。託蘭也許並不知道,中譯本的書名加了一個副標題“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否則,他恐怕會表達不滿。因為他明確説,“我並非以一個美國人而是以一個世界公民的身份來寫”這本書。[17]
我一直試圖作為一名不管國籍和意識形態如何的超黨派人士來探討歷史,並試圖通過普通的和非凡的人們所遭受的苦難,以慘痛的詳細情節來描寫戰爭的恐怖。(託蘭,頁663)
託蘭確實是美國人,但他又自視為“世界公民”。這種人在美國可能不在少數,中譯者(或出版社)加了“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 這個副標題也不算錯。問題在於,一個“世界公民”看待戰爭的目光真的就客觀嗎?
託蘭在結束他的戰爭紀實時説:
這場朝鮮戰爭值得打嗎?對於參戰雙方的高、中、低層的人民來説,它都是一場殘酷、愚蠢、錯誤、誤判、種族歧視、偏見和兇暴的戰爭。只有各個層面上大量富有人性的事例——戰場上的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對敵人個人的仁慈和同情——才使得書寫這場戰爭可以承受。(託蘭,頁6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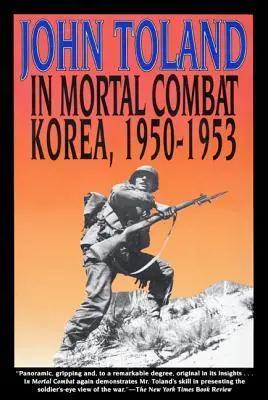
這場戰爭的確殘酷,歷史上也沒有不殘酷的戰爭。但我們值得問問託蘭:這場戰爭“對於參戰雙方的高、中、低層的人民來説”都是“愚蠢、錯誤、誤判、種族歧視、偏見和兇暴的戰爭”?“世界公民”如此不辨是非、不分青紅皂白地把這些語詞加諸於“參戰雙方的高、中、低層的人民”,讓自己站到一個超歷史的道德高度,他的靈魂就“能夠承受”(bearable)書寫這場戰爭,讓人匪夷所思。
無論南北雙方的朝鮮人民還是中國人民,都不會同意説,這場戰爭是“愚蠢、錯誤、誤判、種族歧視、偏見和兇暴的戰爭”。參戰雙方的人民不是“世界公民”,“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對敵人個人的仁慈和同情”也不屬於“世界公民”,而是屬於某個國家的戰士。各個國家記住自己的英雄及其自我犧牲精神乃至對敵人個人的仁慈和同情,屬於政治的自然。[18]
託蘭不分青紅皂白把“愚蠢、錯誤、誤判、種族歧視、偏見和兇暴”加諸給交戰雙方,恰好證明這位“世界公民”的頭腦“愚蠢、錯誤、誤判”,因為他不能辨識什麼是“種族歧視、偏見和兇暴”。
要辨明歷史上的政治事件的是與非或道德與不道德,從來不是容易的事情,這涉及到具體而又複雜的歷史處境。何況,“人們對道德世界的基礎存在着深刻的、顯然是永無休止的爭論。”儘管如此,“我們卻生活在道德世界的表層結構中。”[19]換言之,人是道德的存在,儘管人世間的糾葛無論在哪個層面都是非難斷,仍然需要儘可能明斷是非。否則,道德世界這個“表層結構”就不復存在。因此,通過學習辨析歷史實例來培育道德判斷力,還是西方和中國的古典文明都相當看重的教育方式。對於我們今天的高中生來説,這種政治教育尤其重要。
18世紀的盧梭已經説過:
儘管人與人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什麼自然的和普遍的社會,儘管他們成為社會人的時候變得十分不幸而又作惡多端,儘管正義和平等的法則對於那些既生活於自然狀態的自由之中而同時又屈服於社會狀態的需要之下的人們來説,全都是空話;但是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就不會有德行和幸福了,上天已經把我們無可救藥地遺棄給人類的腐化了。讓我們努力哪怕是從壞事裏面,也要汲取出能夠醫治人類的補救辦法吧。[20]
也許是受到這段話的激勵,沃爾澤在他的《正義與非正義戰爭:通過歷史實例的道德論證》中列舉了諸多20世紀的戰爭,並勇敢地堅持區分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但他沒有提到朝鮮半島戰爭,讓人頗為費解。畢竟,與20世紀的諸多戰爭不同,直到今天,史學界還在為朝鮮戰爭雙方誰是正義一方之類的問題爭議不休。也許,由於沃爾澤把“承認和尊重個人權利以及由個人組成的共同體的權利”的“人權論”作為區分正義與非正義戰爭的唯一尺度,他才無法面對朝鮮半島戰爭這樣的“歷史實例”。
“朝鮮戰爭”概念的歧義
姚旭將軍的《從鴨綠江到板門店》可能是我國“新時期”以來帶史學性質的抗美援朝戰爭史的開端之作,儘管具黨史敍述風格,卻限內部發行。[21]自那以來,風格各異的或回憶或記敍或研究抗美援朝戰爭的書籍日漸增多,而且絡繹不絕,史學界也不乏高質量的實證研究成果,紀實性作品明顯更多。據統計,1995至2009的15年間,“有關朝鮮戰爭的專著、譯著及回憶錄等”已經多達100餘種。[22]
在筆者目力所及的戰史回憶或紀事中,唯有雙石的作品名為“開國第一戰”。[23]這個書名暗含的意思是:歷史上的中國重新“開國”已有多次,唯有這次“換了人間”。
《開國第一戰》採用中國民間文學傳統的“章回”紀事體,修辭風格與新中國直到1970年代都還保持着的戰爭狀態一脈相承,如今的年輕人讀來會直接感受到在那場戰爭中志願軍戰士纏滿繃帶的英勇氣概。如實呈現那個年代的戰爭氣氛和頑強鬥志,就是對歷史客觀性或歷史真相的一種揭示。
這種品質的作品構成了我國抗美援朝戰爭紀事的主流。但隨着改革開放日漸深入,我們的一些知識人也開始“修正”正統敍事。據説,朝鮮戰爭的成因不是因為“美帝”侵略朝鮮,而是蘇聯慫恿北朝鮮“入侵”南朝鮮;新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無異於打了一場不僅莫名其妙而且得不償失的戰爭。這種“修正”史觀與美國“正統”的朝鮮戰爭史觀不謀而合,發人深省。
1951年4月11日,麥克阿瑟被解職後,美國參議院特別委員會曾舉行聽證會,調查麥克阿瑟公開聲稱“‘參謀長聯席會議完全同意’他擴大戰爭”的説法是否屬實。二戰期間的美國名將布萊德雷將軍(1893-1981)在半島戰爭期間任美軍參聯會主席,他在5月15日的聽證會上作證説,“擴大同赤色中國的戰爭是錯誤的。”按布萊德雷自己的説法,他當時的原話在後來遭到誤解:
“坦率地講,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這一戰略將使我們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敵人打一場錯誤的戰爭。”後來,許多粗心的作者認為,這一説法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朝鮮戰爭本身的看法。[24]
誤解也來自同一部傳記的中文“編譯”版:
得知朝鮮戰爭結束的消息,布萊德雷頗為感慨,他説了一句後來被奉為經典的話:“朝鮮戰爭是我們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敵人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戰爭。”[25]
看來,布萊德雷將軍的確有過這一斷言,但他究竟是在美軍進犯38線以北之前這樣講,還是停戰協定簽訂之後才這樣講,對追究戰爭責任而言確實有很大差異。儘管如此,這一斷言的性質不會因此而有什麼不同,總之是“一場錯誤的戰爭”。無論如何,這話成了名言,迄今傳誦不衰。
2010年6月25日下午,《文史參考》雜誌社在北京舉辦了“朝鮮戰爭六十年暨半島形勢研討會”。隨後,該刊推出“六十年前血與火:朝鮮戰爭”專題,雜誌社編輯部為此撰寫了“專題導語”。這篇“專題導語”引用這句名言後緊接着就説,這句名言“説的不僅僅是美國人眼裏的朝鮮戰爭,對捲入戰爭的南北雙方,對中國、對聯合國其它15個成員國來説,又何嘗不是這樣”。[26]

《文史參考》2010年第12期
這話讓人覺得,我們的《文史參考》編輯部似乎也成了“世界公民”。人民日報系統的雜誌社編輯部竟然認為,對新中國來説,這場戰爭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敵人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戰爭”,如果不是讓人匪夷所思,那就是國家意識出現內在裂變的表徵。
朝鮮半島戰爭的主角是分裂的朝鮮南北雙方和中美雙方,唯有美國有官方人士(布萊德雷將軍)明確承認,美國介入半島內戰是“一場錯誤的戰爭”。[27] 即便作為“世界公民”的美國人也承認,美國介入的這場戰爭是“近40年來在美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場沒有被國家樹碑立傳的戰爭”(託蘭,頁662)。其餘三方從未承認,這是“一場錯誤的戰爭”。《文史參考》編輯部代表朝鮮南北雙方和中國承認這是“一場錯誤的戰爭”,難道不讓人匪夷所思?
事情還沒有完。為了反駁這種觀點,有軍史學家提出,應該區分“朝鮮戰爭”與“抗美援朝戰爭”。畢竟,這兩個概念“既有聯繫又有重大區別”。[28] 也許可以説,“朝鮮戰爭不該打,抗美援朝戰爭卻不能不打”——或至少可以説,朝鮮半島爆發內戰是否算錯另當別論,“抗美援朝戰爭”則不能説是“捲入一場錯誤的戰爭”。
“朝鮮戰爭”與“抗美援朝戰爭”這兩個概念的確有區別,但區別並不在於“該不該打”的戰爭性質,而在於當事者的政治身份差異。對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來説,“朝鮮戰爭”是“祖國解放戰爭”,對新中國來説,“朝鮮戰爭”是“抗美援朝戰爭”。即便對於李承晚來説,“朝鮮戰爭”不僅該打,而且還應該打到底,否則他不會堅決拒絕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僅僅對於美國來説,朝鮮戰爭才有“該不該打”即“該不該介入”的問題,否則,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將軍不會説那句是基於美國實際利益的話。
政治史學家曾用歷史社會學的統計方式統計過德意志30年戰爭以來至1980年代世界史上發生過的戰爭,唯有朝鮮半島戰爭同時有三個不同的名稱,堪稱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戰爭實例:朝鮮與韓國的戰爭、美國與朝鮮的戰爭、中國與美國的戰爭。[29]

嚴格來講,“朝鮮戰爭”是以戰爭地點來命名戰爭的史學習慣,與當事者各有各的表達式並不矛盾。若有史學家説金日成發起統一祖國的戰爭“有錯”,那麼,馬上就會有人出來問:是不是也得説解放軍打過長江“解放全中國”也“有錯”?在日本的某些史學家看來,朝鮮的“祖國統一戰爭”是中國內戰的延續或者説中國革命的延續,恐怕不無道理。畢竟,金日成對“毛澤東道路”不僅敬佩不已,還非常羨慕。[30] 何況,“熱血同流”的抗日戰爭已經把中國和朝鮮的抗日誌士緊密維繫在一起,而戰後的統一祖國同樣是“熱血同流”,儘管不是需要聯合解決的問題。我們總不至於會忘記,《八路軍進行曲》(後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作曲者鄭律成(1914-1976)出生在朝鮮半島西南,19歲(1933)才來到中國,加入朝鮮人的抗日組織“義烈團”,“7·7事變”後即奔赴延安。
史學家沒有理由説,朝鮮半島內戰因引發了國際戰爭而是“一場錯誤的戰爭”,至多隻能説是一場運氣不佳的內戰。歷史上的內戰何其多,絕非現代才有,只不過現代意識形態給現代式的內戰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但“革命”式的內戰誕生於17世紀的英國清教革命,而非1917年的俄國革命。[31]
就在《文史參考》雜誌社舉辦研討會的當天晚上,一篇題為“朝鮮戰爭的真相”的“網文”在網上廣為流傳。作者這樣開頭:
最近,原蘇聯國家檔案資料有部分解密,關於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劃發動朝鮮戰爭的經過終於泄露出來。原來侵略者並非“美帝”李承晚匪幫,而是金日成、斯大林。但是由於信息封鎖,至今多數人仍沿襲過去的思維模式,認為朝鮮戰爭是“美帝”挑起的。
這才是“朝鮮戰爭”概念引發歧義的關鍵所在:作為內戰和作為國際戰爭的“朝鮮戰爭”有本質上的區別。問題在於,朝鮮半島的內戰僅僅持續了不到三天,美國就發動了另一場戰爭——清教徒“十字軍西征”式的戰爭。

1950年6月27日,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美軍前往朝鮮
平壤時間27日(美國東部時間6月26日),美國遠東空軍已進入半島空域作戰。這天晚上9點,白宮召開緊急會議時,空軍參謀長“范登堡將軍彙報説,美國空軍擊落了一架雅克-9”,艾奇遜則希望美國空軍的行動不受38線限制,杜魯門沒有同意(米勒特/下,頁144)。實際上,這一天美國遠東空軍在漢城上空共“擊落了七架雅克-9”,而“美國空軍持續不斷的空襲還使朝鮮集結在公路周圍的地面部隊損失慘重”(米勒特/下,頁159、106-107)
有位移居美國的華僑作家在講到朝鮮半島戰爭時信口開河:
1950年6月,“心比天高”的金日成,以其手中僅有的三個勉強拼湊的步兵師,揮戈南下,解放“被壓迫同胞”。[32]
金日成發起攻擊時,手中不是僅有“三個勉強拼湊的步兵師”,而是由蘇軍訓練並提供裝備的“7個師和2個裝甲旅”,並且“每個師的組織結構表包括4個炮兵營”(米勒特/下,頁14、41)。[33] 按照1950年6月韓國情報部門的説法,北方軍“有10個步兵師、1個坦克師,1個空軍師和1個高射炮團”,則可能有些誇大其詞。[34]
金日成的確有充分把握一舉擊潰李承晚的韓國軍。他的作戰方案是,兵分五個方向同時突擊,針對漢城和漢江流域的突擊力量有3個精鋭師,由80輛T-34坦克作嚮導,儘管李承晚方面“有8個師,其中有4個師集結完畢,並進行了頑強抵抗”(米勒特/下,頁15)。3天后(6月28日),人民軍攻克漢城,李承晚的政府機關撤到大田,緊接着又撤到大邱(7月)。
從常規戰爭的角度看,如果排除“美國承諾出兵拯救韓國”這個因素,人民軍最初的攻擊從表面上看,北朝鮮已摧毀了韓國。(米勒特/下,頁106)
要説金日成“心比天高”,只能説他萬萬沒想到美國人會介入半島內戰。與此相反,1年多前,人民解放軍的兩個集團軍羣已經打過長江奪取南京正逼近上海時(1949年5月23日),毛澤東電令二野集團軍羣首長警戒美國:“二野目前的任務是協助三野應付美國可能的軍事幹預。”[35] 5天后(28日),毛澤東又電令各集團軍羣首長,警惕西方各國聯合武裝干預:“美國正在和英、法等12國會商統一對華政策,青島增加了美國軍艦……”(同上,頁574)。

1949年4月23日,毛澤東閲讀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的報道
當然,金日成的疏忽並非沒有原因。毋寧説,他萬萬沒想到,人類文明的“楷模”美國半年前才公開宣佈自己的遠東防禦範圍不包括朝鮮半島,竟然出爾反爾得如此之快。
話説回來,在政治鬥爭中、尤其戰爭狀態下,必須把最壞的可能性考慮殆盡。若在戰場上遭遇敗績,事後説“萬萬沒想到”,僅僅表明對敵人的個性缺乏足夠的認識。
這位華僑作家緊接着還説:
1950年夏天,金日成氣衝牛斗,發佈“8月底將美國侵略者趕出朝鮮”的命令。中國也在邊境“集中12個軍以便機動”。剛從連續12年戰禍喘過一口氣的中國,又要把自己的子弟往戰場上送了——只為了老大哥心儀的“冷戰”(我們現在已經清楚知道,這場戰爭,斯大林是非打不可,而且非由別人出面打不可)。
金日成發佈“8月底將美國侵略者趕出朝鮮”的作戰命令時,正是釜山戰役膠着之時,他必須“氣衝牛斗”——他要“將美國侵略者趕出朝鮮”難道有錯?
美國介入半島內戰後,新中國在邊境集結的不是“12個軍”,而是12個師即4個軍(加強一個炮兵師)。當時,中國的內戰還沒有結束,美國借朝鮮半島爆發內戰介入台海,新中國集結戰略預備隊(一個集團軍)應對東北邊境的戰爭威脅,難道不應該?
用“又要”兩字無非表明,在作者看來,中國共產黨再次為了莫須有的戰爭“把自己的子弟往戰場上送”。上一次是哪次?抗戰結束後共產黨打國民黨?作者沒有這樣説,否則她筆下的張東蓀也會從墳墓中起身反駁:挑起內戰的是蔣介石。這位華僑作家不至於會認為,共產黨北上抗日是“把自己的子弟往戰場上送”吧。
與這位華僑作家的説法相反,史學家們現在已經清楚:朝鮮戰爭不是斯大林要“非打不可”,而是金日成要非打不可——仍然是那個問題:完成自己國家的統一難道有錯?

彭德懷與金日成在前線交談
作家可以免責於學術上的無知,卻不能免責於無視基本的歷史事實。美國的史學家承認,早在二戰結束之前(1944年12月),“一些美國官員就已經把蘇聯視為下一個敵人”了。[36]華僑作家本可以很容易從美國史學家那裏得知,“二戰”剛剛結束還不到半年,“大街小巷和投票站發生的一切令美國官員大傷腦筋”,因為,“在歐洲的每一處,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支持率都在攀升。”當時歐洲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甚至認為,奧斯威辛“是20世紀30年代歐洲資本主義危機的副產品”,而斯大林格勒保衞戰“則代表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37]
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大使館代辦的凱南給國務院發了一份8000字的長密電,把蘇聯心態刻畫成狂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沙俄擴張主義的混合體,並據此提出了強硬的“對蘇遏制”戰略。[38]凱南的長密電要給美國國務院領導傳達這樣的見解:“由於不曾受過盎格魯-撒克遜式調和折中傳統的陶冶”,克里姆林宮政權對世界事務的看法太過神經質,這根源於俄國傳統的、出自本能的不安全感,“因為他們出身於俄羅斯-亞細亞世界。”[39]其實,這封長電報本身恰恰證明,凱南自己對世界事務的看法太過神經質,要説出自本能的不安全感,恰好屬於盎格魯-撒克遜式的美國傳統。用當時的一位美國政治家的話來説,凱南“無異於用關於美國的一相情願的幻想來支持希望蘇聯崩潰的幻想”。[40]

1952年4月,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宣誓就任蘇聯大使
的確,若把凱南電報中的“克里姆林宮”換成“白宮”,把“俄國”換成“美國”,並非不恰當。美國的政治地理位置雖然與自古以來戰火不斷的歐亞大陸隔着兩個大洋,美國政治人並沒有覺得可以高枕無憂:
在地緣政治分析的框架內,美國在地理上受到包圍。實力資源的分佈,為舊大陸提供了比新大陸更多的施展武力的可能性。(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頁79)
美國的不安全感難道不是既傳統的又是本能性的?隨後發生的“麥卡錫專政”事件正是這種不安全感的體現:
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大恐慌”是一場由普遍存在的缺少安全感引起的,這是美國人民本身的一種病態心理。這種不安全感體現在對國家安全、美國價值觀以及自由主義體制脆弱性的擔憂上。(《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信出版社,2013,頁382)
1948年元月,在涉及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問題時,“遏制戰略之父”凱南在日記中寫道:
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更有資格獲得這份殊榮,因為他比我們都付出了更艱辛的努力和更多的精力,去追求他所在乎的那種與眾不同的和平。[41]
在公開場合,凱南不會這樣説。而且,他在日記中馬上補充了一句,“一定要問清楚:‘哪種和平?’‘誰的和平?’”這句補充再次證明,“心儀”冷戰的是促成美國採取“遏制戰略”的美國政治家凱南。朝鮮半島上的內戰變成了國際戰爭,正是因為美國對世界事務持有神經質的看法,而這種神經質不外乎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心理,即著名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所説的“反共偏執症”。直到今天,美國的國際戰略家仍然沒有擺脱這種神經質:
由於中國至少在名義上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所以我們應當希望聽到這一觀點:由於中國依然執著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而中國是一個嚴重的威脅。[42]
如果對世界事務的神經質看法以及出自本能的不安全感屬於美國政治人,那麼,我們就需要調查這種神經質從何而來。由於我國史學界的“親美”心態相當普遍,這種調查迄今無法展開。
從美國的“正統”史觀來看,朝鮮半島戰爭是美式清教主義與東方共產主義的殊死一戰。杜魯門相信,“美國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傳播道德和民主”,因此他認為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不應心慈手軟”:
美國的使命是上天註定,上帝授權,是美國人無法放棄的責任。杜魯門不是加爾文主義者,但他堅信對於美國公民宗教至關重要的預定論教義。為了爭取美國人對聯合國和北約這兩個與美國氣質不符、與美國曆史格格不入的國際承諾的支持,杜魯門多次説到“這個責任我相信是上帝打算讓這個偉大的共和國來承擔”,這個“責任是萬能的上帝”賦予美國的。這與林肯所説的天意何其相似:美國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工具,無論美國人自己是否意識到這一點。[43]
由於有“道德和民主”乃至“對人權的深切關注”之類的語詞,杜魯門動用武力的決斷讓人以為美國很“正義”。一旦人們意識到這些語詞的歷史含義來自清教信仰的界定,那麼,我們“過去的思維模式”認為朝鮮戰爭是“美帝”挑起的,又錯到哪裏去了呢?

1951年,彭德懷(右3)在朝鮮成川郡檜倉與鄧華(右1)、陳賡(右2)、甘泗淇(右5)、王正柱(右7)等合影
2010年年底(11月24日),名為《往事》的網刊(第103期)刊發了某個志願軍戰士撰寫的回憶文章。“編者的話”一開始這樣説:
抗美援朝60週年,官方高調紀念,稱之為保衞和平反對侵略的正義戰爭。這與其説是歷史判斷,不如説是意識形態的宣言。實際上,朝鮮戰爭是在斯大林支持下由金日成發動的,中國是不得已也不情願投入了這場戰爭。
這樣的聲音早在1990年以來就出現了。[44]我國的某些知識人改變對朝鮮戰爭的認識與其説是蘇聯和美國相關檔案解密的結果,不如説是因為1990年代以來中美日漸成了最大的“貿易伙伴”:既然“夥伴關係”如此之好,40年前何必兵戎相見!
甚至美國也有政治史學家這樣認為:
跨過三八線的決定使美國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美軍在戰爭中的全部傷亡中有五分之四發生在聯合國軍跨過三八線以後。這場戰爭使得美國的冷戰姿態在此後20年裏被凝固下來,特別是使得中美關係嚴重癱瘓。正如一位觀察家所指出的,“7億潛在的消費者轉而以7億危險敵人的面目出現了。”[45]
不過,即便有美國人認為朝鮮內戰變成國際戰爭錯在美國,也未必因為他們是中國人的“貿易伙伴”。毋寧説,他們會記得,在“美國崛起”的年代(1890-1910),荷馬李(1876-1912)就已經嚴詞警告美國人必須區分“工業主義”與“重商主義”:發展工業化是實現讓國家偉大這一目標的手段,“但不是目標本身”——正如人活着需要吃飯,卻不是為了吃飯。

荷馬李(1876-1912)
工業是一種生計、一種食物,建立起國家並賦予其維護理想的力量,並在世界強國之林中開拓出國家的事業:戰勝或者輸給其他國家。[……]一個人活着沒有願望和目標,只是為了吃,這樣的人會被別人厭惡。當國家把工業主義作為目標時,國家就變成了一個貪吃鬼,下流、卑鄙且傲慢,其持續的時間相應地不會超過人類中的貪吃鬼。國家工業的過度發展就是重商主義,是個毫無目的的貪吃鬼。國家工業與重商主義之間的區別在於:工業是人民努力用來滿足人類的需要,重商主義則利用工業來滿足某個人的貪婪。[46]
荷馬李的嚴厲目光看到:一旦重商主義“把控了美國人民”,那麼,它不僅會毀滅這個共和國,還會毀滅人民的品德。
重商主義只是本能地吃和吐,一旦維持要素不存在時就徹底消失。地球上所有國家的建立都要歸功於軍事發展或者國家發展,後續的演進及人類的和平也要歸功於此。人最珍視的是生命,還有同樣寶貴的原則和忠誠。(荷馬李,頁16)
由此看來,與我們的國家意識的內在裂痕相比,美國的國家意識的內在裂痕實在算不上什麼。
肅劇式的政治史學與戰爭真相
為了揭示戰爭與文明的關係,古典學家漢森從世界史上發生過的無數戰爭中挑選出9個戰役(從薩拉米斯海戰到1968年越南人民軍的“春季攻勢”),通過敍述這些戰役,漢森完成了一項在他看來有教益的世界史研究。
漢森沒有以朝鮮半島戰爭中的某個戰役為例,但在説到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半島戰爭志》時,他將美國介入朝鮮半島內戰與修昔底德筆下的“西西里遠征”相提並論。[47]漢森的類比似乎不經意,但並非不準確。畢竟,“西西里遠征”是雅典民主政制的本質導致的結果,也是雅典城邦走向衰落的開端。漢森未必想要説,美國介入朝鮮半島內戰是美國民主政制的本性導致的結果,也是美利堅帝國走向衰落的開端,但他的説法難免讓人有這樣的聯想。因為,在與漢森的大著同年出版的一部文集中,漢森的文章《古代和現代的民主戰爭》被排在了首位。
這部文集來自美國威爾遜國際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舉辦的一次學術研討會(1995),讓筆者感到驚訝的是,會議主題“民主與戰爭:朝鮮戰爭與伯羅奔半島戰爭比較研究”出自古典學研究的目的,與會者中的古典學和古代史學者佔一半以上,其餘為研究國際政治和東亞文化的學者。文集編者在“引言”中説:
這種比較研究讓我們首先回到了一個對古典學者來説是持久的問題:古代希臘與現代西方究竟相似還是截然不同?[48]
美國的古典學者正確地看到,朝鮮半島戰爭與伯羅奔半島戰爭最大或最為根本的相似之處在於:兩者都讓民主政制面臨考驗(test of democracy)。畢竟,在修昔底德筆下,伯羅奔半島戰爭無異於把雅典民主送上了審判台(Athenian democracy on trial),同樣,朝鮮半島戰爭無異於把美國民主送上了審判台(American democracy on trial)——儘管在具體提到這場戰爭讓美國政體面臨的問題時,美國古典學者的表述未必準確(同上,頁1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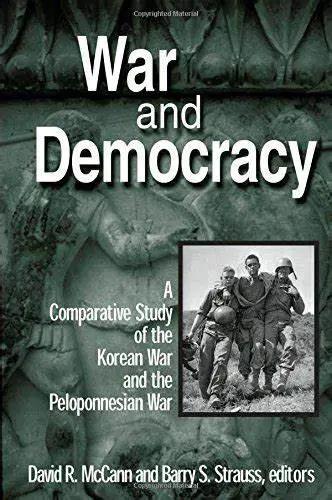
荷馬李有良好的古典學養,即便他讚揚美國的民主政制,他也沒有忘記修昔底德的政治見識:
一個人民有選舉權的國家,其品性並不比人民的品性更高。沒有哪個共和國能擺脱民眾的動機、激情、野心、仇恨或不法行為。(荷馬李,頁50)
漢森還説,修昔底德“對西西里戰事的記載,就像是一出索福克勒斯式的悲劇”(漢森,頁572),這讓筆者感到驚訝。“悲劇”這個語詞用在這裏未必恰當,若用“肅劇”的譯法更為恰當:朝鮮半島戰爭不是歷史悲劇,而是歷史肅劇。
古希臘的三大史書直到今天仍然是人類文明的瑰寶和紀事作品的最高典範,而它們無不具有戲劇品質。荷馬的兩部“史詩”基於特洛伊戰爭,但敍述的主線並非編年體式的紀事。若將《伊利亞特》與《奧德賽》合起來看,人們還可以説,荷馬筆下的敍事重點並非是特洛伊戰爭的過程本身。畢竟,通過記敍奧德修斯在戰後返鄉的歸程,荷馬呈現了政治哲學的重大問題。[49]
希羅多德的《原史》記敍了距離他僅半個世紀之遙的希波戰爭,而這場戰爭的具體過程在他筆下僅佔全書三分之一篇幅。如果説修昔底德筆下的紀事具有肅劇性質,那麼,希羅多德的紀事則具有諧劇性質。通過“萬花筒”式的敍事,希羅多德的紀事(史書)與荷馬的紀事作品一樣,將戰爭志提升到了政治哲學高度:不同文明政治體具有何種德性品質,是戰爭紀事要揭示的最重要的歷史真相之一。
對於如何通過記敍一場戰爭來探究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問題的歷史真相,修昔底德有更為明確的自覺意識。[50]《伯羅奔半島戰爭志》第一卷中的一些説法表明,修昔底德已經意識到後來亞里士多德對詩 – 紀事[史] – 哲學的區分。史學家記敍歷史上的個別事件或人物經歷(所謂“已經發生的事”),很難觸及普遍性的問題;哲學探究普遍的、理想的東西(嚴肅、高貴的事情),從而遠離或超逾個別事件或人物經歷。詩介乎兩者之間,通過虛構個別而且偶然的事件(所謂“可能發生的事情”)來呈現普遍而又嚴肅的事情。因此,詩要比史述更熱愛智慧、更嚴肅,筆下的事件更具普遍性。[51]
修昔底德雖然算得上親身經歷過伯羅奔半島戰爭,但他的史書不是編年史式的紀事,或者説他並不是僅僅關注戰爭過程本身,而是關切更為普遍的戰爭真相。記敍戰爭就得述及對戰爭進程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事件、戰役、條約、談判等等,而修昔底德所挑選的事件往往並沒有對戰爭進程產生直接影響,至多隻能説折射出整個戰爭。比如,他所記敍的演説辭佔全書五分之一篇幅,雖然對展現戰爭實況談不上重要,卻對理解這場戰爭甚至理解其他戰爭十分重要。
霍布斯年輕時閲讀修昔底德就注意到,撰寫史書最重要的是將“真相”和“修辭”結合得天衣無縫:
因為,真相是其史書的靈魂,而修辭則構成其史書的身體。只有後者沒有前者就僅僅只是史實的片段,只有前者沒有後者則無法給人教導。[52]
從今天的史學分類來看,收集史實屬於實證史學式的研究(包括查閲檔案),敍述性的紀事屬於霍布斯所説的“修辭”。[53]我們如今能夠看到的朝鮮半島戰爭史學主要呈現為兩種樣式:要麼是敍述性的紀事,要麼是實證史學式的研究。無論紀事還是實證研究,都得憑靠各類史料,只不過前者偏重記敍戰爭(戰役-戰鬥)的具體過程,後者偏重考證戰爭的起因及其演化的關鍵環節。能將兩者結合在一起的並不多見,遑論結合得很好。如今,史學家面臨的實證史學的壓力相當大,肅劇式的歷史探究還有可能嗎?
19世紀的古代史家考克斯(1827-1902)是英國人,他不像後現代的古史學家那樣,致力於憑靠考古學或人類學的實證研究重構希波戰爭的歷史真相,而是通過重述希羅多德的敍事,把正在走向世界帝國的英國説成希羅多德筆下的雅典。
按照考克斯的敍述,在希波戰爭之前,泛希臘城邦幾乎還處於半蠻夷狀態,“由一套各自獨立的單元組成,除了各自城邦社區的成員之外,他們懷疑、嫉恨、討厭一切。”[54] 希波戰爭迫使泛希臘城邦必須擺脱城邦的孤立和無序,形成一個將所有希臘人組織在一起的“普遍秩序”,而這種秩序的形成標誌着“政治和智慧的成長”。説到這裏時,考克斯突然插入説:
希臘人未曾覺悟到這種成長是事情向好發展的前提。這種政治和智慧的成長倒是在大不列顛的土壤上結出了最豐碩的果實。(考克斯,頁10)
考克斯接下來就這樣讚美雅典:
雅典在強盛時期建立了帝國並竭力穩固帝業,這時自然會削弱甚至取締[有礙城邦彼此之間交流的]古老偏見。雅典做到了,它將傳統的觀念踩在了腳下,建立了一個被普遍承認的專斷政權,試圖將一些視孤立為生命的城邦捏合成一個整體社會,將法律平等的恩施波及每一個公民。然而,這一企圖冒犯了一些人,他們無法接受自己城邦之外的人,認為那已超出法律的界限。(考克斯,頁13)
考克斯不外乎要説,19世紀的大英帝國正在做的是當年雅典城邦要做的偉業,即把地理大發現後西歐人所認識到的世界上各自孤立的所有政治單位“捏合成一個整體社會,將法律平等的恩施波及每一個公民”。為此,雅典城邦必須先完成一項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使命,即戰勝“東方專制主義”的代表——波斯帝國。
對於19世紀乃至20世紀的英國人來説,俄國就是“東方專制主義”的現代繼承人,或者説有礙大英帝國實現世界的“普遍秩序”的絆腳石。因此,考克斯的“序言”一開始就説,希羅多德的《原史》是“東方的專制主義與西方的自由、法制之間的偉大斗爭”(考克斯,頁iii)。
美國取代大英帝國的世界主導權之後,美國的史學家自然會覺得,這話應該由美國人來説才對:雅典城邦的政治和智慧的成長在美利堅的土壤上才結出了最豐碩的果實。倘若如此,中國和美國的朝鮮半島戰爭史學要共同面對的歷史真相,就不僅是這場戰爭的過程本身,毋寧説,西方的自由民主倫理與東方的德性差序倫理的歷史衝突才是根本。古典學家漢森對西方文明因將自由民主倫理與軍事優勢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而天下無敵充滿自信,儘管如此,他仍然不無憂心地承認:
美國在這個時代擁有前無古人的全球影響力,但美國人民對於他們文化的道德水平與實力,可不像希臘人、羅馬人或者意大利人在幾乎被滅絕時那樣充滿自信。(漢森,頁648)
這無異於承認,與古希臘-羅馬文明乃至近代的意大利文明的道德水平與實力相比,美國文化並不在一個量級。接下來的問題自然便是:通過記敍這場歷史上頗具偶然性的戰爭來探究更具普遍性的世界政治問題的歷史真相何以可能。
不可同日而語的歷史分水嶺
1992年,美國著名的大學和圖書館出版商Facts on File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題為America at War[戰爭中的美國]系列叢書,企望美國年輕人對自己的國家所經歷的戰爭有正確的政治認識,相當於為美國大學生提供公民素質教育讀本。
艾澤曼撰寫的《朝鮮戰爭》篇幅不大,紀事與論析結合得頗有章法,還附有“術語表”介紹軍事和地緣政治的常識性概念或歷史用語,就公民教育的教科書而言,算得上小巧精緻之作。[55]在修訂第二版(2004)中,艾澤曼甚至提到美軍在漢城以南的一個村莊“屠殺約400名南朝鮮難民”,儘管他為此開脱了兩句(艾澤曼,頁46),畢竟沒有迴避實證史學家的考證。
艾澤曼的目的是希望美國年輕人不要忘記這場戰爭,因為“參加過朝鮮戰爭的那一代人正在逐漸離開我們”,而他們當年遭遇“壓倒多數的中國軍隊”的打擊時“實現了傳奇般的撤退”,其英勇表現可歌可泣(艾澤曼,頁2)。
艾澤曼在這樣説的時候沒有提到,美軍的飛機、坦克、火炮以及後勤支援能力對中國軍隊具有壓倒性優勢。憑常識也不難判斷,以如此壓倒性的軍事工業優勢對付僅在血肉之軀的數量上佔“壓倒多數的中國軍隊”,要説美軍被包圍後脱身是“傳奇般的撤退”,從軍事上講幾乎等於不知羞恥。軍人出身的亞歷山大倒是説得正派:
最令人感到沮喪的是,紅色中國人用少得可憐的武器和令人發笑的原始補給系統,居然遏制住了擁有大量現代技術、先進工業和尖端武器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亞歷山大,頁579)

上甘嶺戰役中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哨兵
對比兩種不同的史述修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國家意識的內在裂痕:對於施行怎樣的公民素質教育,美國知識人並不意見一致。艾澤曼在他的教科書中這樣為朝鮮半島戰爭定性:
朝鮮戰爭成為了美國曆史的一道分水嶺。正是從這時開始,美國才真正地成為一個超級大國,開始出現干涉全球事務的意願,並逐漸發展出相應的手段。(艾澤曼,頁11)
“干涉全球事務”(global intervention)顯然不是褒義詞,如今,不少美國政治家和知識人會用另一個語詞來表達它的實際含義:全球化。
[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選徵兵役製法案擴大了徵兵範圍,徵來的士兵被派到朝鮮打仗。這項法案後來一直實行了20年。海外軍事設施數量劇增,截止1960年代中期,美國在世界各地大約有375個主要軍事基地和3000個小型設施。[56]
史學家顯然不能説,這不是“全球化”的基本面相之一。197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雖然從越南戰場抽身,卻並沒有放棄“干涉全球事務”的習慣。[57]對有正義感的美國人來説,理解朝鮮戰爭對美國有何歷史意義涉及到一個迄今懸而未決的問題:美國作為世界性大國究竟具有怎樣的文明德性品質。
1986年10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與美國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在燕園共同舉辦了“1945-1955年中美關係史學術討論會”。自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這是新中國學者與美國學者首次坐在一起探討兩國關係“非正常化”時期的那段特殊歷史。畢竟,1954年4月,在蘇聯的倡議下,中、蘇、美、英、法以及相關國家在日內瓦召開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1893-1969)曾拒絕與新中國總理周恩來(1898-1976)握手。美國政治家相信,中國人會“對杜勒斯的傲慢失禮耿耿於懷,儘管他們嘴上經常説那件事無關大局”。[58]這話恐怕言過其實,事實上,如今的絕大多數中國人興許早就忘了歷史上曾經有過這麼回事。
美國史學家波拉克教授給燕園會議提交的論文題為“朝鮮戰爭和中美關係”,他以這樣一段話開篇:
朝鮮戰爭不論對美國還是中國都是歷史的分水嶺。中美軍隊捲入戰爭時,北京新政府成立才不過一年。一場痛苦的、代價巨大而無結果的衝突由此開始,並損害了兩國之間整整一代人的關係。[59]
這聽起來似乎是説,朝鮮半島戰爭對中美雙方來説都既是一場歷史誤會,也是一個歷史的不幸。
的確,“朝鮮戰爭不論對美國還是中國都是歷史的分水嶺。”然而,這個“歷史的分水嶺”對美國和中國來説顯然不具有相同的歷史含義。
對中美雙方來説,這場戰爭的確都很“痛苦”,而且“代價巨大”,但它“無結果”嗎?

美國政府受到朝鮮戰爭的震撼,它完全放棄了原先“一個世界”的思想,代之以超級大國在國際舞台上展開無情鬥爭的概念。[60]
朝鮮半島爆發內戰時,美國不僅干涉朝鮮人的內戰,還趁機干涉中國人的內戰——更確切地説,朝鮮半島內戰為美國插足台灣提供了難得的契機。畢竟,自1948年末以來,美國就一直擔心中共解放台灣,“因為這意味着蘇聯能利用台灣,在戰時有效地攻擊從日本到馬來半島的海上航線,加強它控制琉球羣島和菲律賓的能力”,而美國則失去一個“可用來集結部隊、發動戰略空中行動和控制鄰近航道的戰時基地”。因此,“美國以軍事手段阻止中共解放台灣不僅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不可避免,而且即使沒有這場戰爭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61]
美國東部時間6月25號那天下午,白宮高層商討半島上的突發事件後,對是否派地面部隊介入半島內戰尚未作出決議,“相反,為了不讓共產黨奪取台灣”,杜魯門“根據艾奇遜的建議下令第七艦隊由菲律賓和沖繩開赴長崎佐世保待命,以備保護台灣”。[62]於是我們看到,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甚至早於美國地面部隊投入半島作戰:6月28日,美驅逐艦布拉什號(USS Brush)駛入基隆港(該艦於1969年移交國軍,更名為襄陽號),以示軍事存在。
6月30日,杜魯門下令美軍地面部隊介入半島內戰。7月1日,美國遠東空軍的運輸機將史密斯中校率領的一個團級戰鬥單位從日本九州緊急空運到漢城南面的水原前沿,7月3日即投入作戰,阻擊朝鮮人民軍南進(米勒特/下,頁166-167)。
7月28日,美國太平洋艦隊派出巡洋艦朱諾號(USSJunesu)及潛艇鯰魚號(USS Catfish)和梭魚號(USS Maddox)組成“台灣巡邏部隊”(Taiwan Patrol Force)開始在台灣海峽巡邏。
直到今天,朝鮮半島的戰爭狀態並沒有結束,僅僅處於停戰狀態——台灣海峽兩岸同樣如此。事實上,中蘇兩國邊防軍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1969年3月)之後,美國政府趁機緩解中美關係時,僅下令第七艦隊將在台灣海峽的“連續定期巡邏,改為包括作戰及輔助艦的隨機巡邏”(1969年11月),並沒有取消巡邏。由於美國的干涉,東亞的兩個文明古國的分離狀態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波拉克教授作為史學家沒有問一下,這在現代世界史上是否算得上史無前例?反法西斯戰爭已經結束大半個世紀,而遭受日本帝國欺凌的兩個東亞國家迄今沒有實現統一,反法西斯戰爭是否算得上徹底勝利?我們被迫接受現狀雖然不等於承認現狀,但久而久之,人們習慣了被幹涉狀態,也就沒誰再追究被幹涉的法理。

2020年2月,一艘Arleigh Burke級驅逐艦Stesem號、一艘Lewis和Clark級乾貨船USNS Cesar Chavez駛過台灣海峽。
波拉克教授還説,“當然,中美捲入[這場戰爭]都是為形勢所迫”(哈丁,頁288)。的確如此,但他顯然不能説,兩者的“被迫”出於相同的政治理由。由於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脅,新中國被迫阻止國際聯軍干涉朝鮮半島內戰並進逼中國邊境,美國干涉朝鮮半島內戰又是出於什麼政治理由而被迫呢?
人們甚至還可以問,沒有朝鮮半島戰爭,美國是否就不會成為全球干涉的超級大國了呢?按照美國的文明理念,美國是不是必然會成為這樣的超級大國?
“超級大國”(superpower)是國際政治學中的專業術語,[63]但在我們的用法中一直是貶義,相當於“帝國主義”的代名詞。1980年以前,我國知識界對美國的看法基本上還停留在戰時狀態。隨着中美建交(1979)以及兩國合作關係逐漸加深,美國的政治形象在我國知識人的心目中開始發生深刻變化,1990年代以來甚至成了不少知識人心中的理想之邦。即便發生了美國軍機轟炸我國駐南聯盟使館(1999年5月7日)以及美軍EP-3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空域與我國軍機相撞(2001年4月1日)這樣的嚴重事件,情形仍然如此。中美兩國之間一旦有事,一些中國知識人會不假思索地認為:一定是中國政府不遵守國際規則。
並不是所有的中國知識人都無視政治常識成了“親美者”,1990年代流行的一句俏皮話表明,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中國知識人對美國德性抱持疑慮心態:“帝國主義夾着皮包回來了。”這絕非意味着,有些中國知識人仍然眷戀封閉的時代。畢竟,抗美援朝戰爭之後的20年,不是新中國自我封閉,而是被美國軍事封鎖。
1991年3月,美國提出由韓國將軍擔任“軍事停戰委員會”首席代表,朝方拒絕了美方的提議,並撤走駐“軍停會”代表團。中國方面鑑於“軍停會”已實際停止工作,決定撤回駐“軍停會”的7人小組(9月),志願軍的名稱從此才真正成為歷史,與我們生活的時代並不是那麼遙遠。

1990年代是新中國意識的一道歷史分水嶺,我們的共同體意識在開放時代逐漸走向分裂。2010年的那個春天,我的“朝鮮半島戰爭甲子祭”講演雖然遭到唾罵,但也博得了稱讚,這讓我對我們的共同體意識的內在分裂感觸良多。畢竟,中國意識有舉世無雙的歷史文明基礎,如今竟然會因為一個新生的世界帝國而產生內在分裂,這本身就算得上是一個歷史事件,更是一個政治史學問題。
國家意識由於對美國的態度而出現內在分裂,僅僅聽起來就頗為不可思議,卻並非是我們的共同體獨有的現象,毋寧説,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世界歷史現象。倘若如此,一個政治史學問題就出現了:這種世界性現象究竟是怎麼回事?從世界史或者説“全球史”的角度看,美國這樣一個國家的誕生和成長意味着什麼?
除非從世界史的角度先澄清這一問題,我們的共同體意識在看待朝鮮半島戰爭這一歷史事件時的分裂很難有彌合的可能。如果説朝鮮半島戰爭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道分水嶺,那麼,這道分水嶺不僅在於這場戰爭本身,更在於如今的我們如何重新認識這場戰爭的世界歷史意義。
自覺承擔歐洲文明命運的尼采曾痛心疾首地感嘆:對歐洲人來説,“古代世界的全部工作都白費了!”
希臘人為了什麼?羅馬人為了什麼?……希臘人!羅馬人!本能的高貴,趣味,方法上的探索,組織與管理的天才,信仰,對人之未來的意志,對於所有作為羅馬帝國而清晰可見之物、對於一切感覺可見之物的偉大肯定,不再僅僅是藝術、而是成為實在、真理、生命的偉大風格……所有這些,並非由於自然的事件,一夜之間被埋葬![64]
我們還不至於發出這樣的感嘆:中華民族“最具洞察力亦即最具後顧與前瞻眼光”的那個階層在古代時期的“全部工作都白費了”!儘管如此,中國文明“本能的高貴和趣味”、“組織與管理的天才”稟賦,尤其“生命的偉大風格”在今天確實面臨“一夜之間”被“全球化”普世倫理埋葬的危險。
可以肯定,如果我們的中學和大學缺乏正確的政治史教育,那麼,我們將越來越難以面對既開放又複雜的國內知識狀況和已經進入又一個世界歷史關鍵時刻的國際政治處境。
注 釋
[1] 霍華德,《歐洲歷史上的戰爭》,褚律元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1。
[2] 席勒,《三十年戰爭》,沈國琴、丁建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2。
[3] 米肖/普茹拉,《十字軍東征簡史》,楊小雪譯,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頁1-3。
[4] 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陸仁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
[5] 張紅路,《麥卡錫主義》,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頁61、75。
[6] 海因斯、克萊爾,《維諾那計劃:前蘇聯間諜揭秘》,吳妍妍,吳錫林譯,北京:羣眾出版社,2004,頁301-303。
[7] 斯東,《蘇格拉底的審判》,董樂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8] 斯通,《朝鮮戰爭內幕》,南佐民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1。
[9] 赫伯格-羅特,《克勞塞維茨之謎:戰爭的政治理論》,韓科研、黃濤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20,頁167-169。
[10] 斯帕尼爾,《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衝突和朝鮮戰爭》,錢宗起、鄔國孚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頁10。
[11] 亨廷頓,《軍人與國家:軍政關係的理論與政治》,李晟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頁148-173。
[12] 古爾登,《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於濱等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頁6。
[13] 亞歷山大,《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郭維敬、劉榜離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578。
[14] 米勒特,《極度深寒: 朝鮮戰爭:1950-1951》,秦洪剛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頁4-5(以下簡稱“米勒特/下”,隨文注頁碼)。
[15] 參見A. R. Millett,The Korean War:The Essential Bibliography. The Essential Bibliography Series,Dulles,VA:Potomac Books Inc.,2007。
[16] R. Leckie,Conflict: The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3,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62.
[17] 託蘭,《漫長的戰鬥: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孟慶龍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5。
[18] 比較L. Lin et al.,“Whose History?An Analysis of 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 Textbook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Japan, and China”,in Social Studies,100.5(2009),pp. 222-232.
[19] 沃爾澤,《正義與非正義戰爭:通過歷史實例的道德論證》,任輝獻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前言,頁28。
[20] 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2003,頁193-194。
[21] 姚旭,《從鴨綠江到板門店: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2] 鄧峯,《近十餘年朝鮮戰爭研究綜述》,見《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9期,頁112。
[23] 雙石,《開國第一戰:抗美援朝戰爭全景紀實》,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
[24]布萊爾整理,《將軍百戰歸:佈雷德利自傳》,廉怡之譯,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85,頁837。
[25] 布萊爾,《布萊德雷》,杜朝暉編譯,北京:京華出版社,2008,頁319。
[26] 《文史參考》雜誌編輯部,《六十年前血與火:朝鮮戰爭》,見《文史參考》,2010年第12期,頁13。
[27] 比較R. J. Foot,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28] 徐焰,《朝鮮戰爭對中國及其他各方的影響》,見《文史參考》,2010年第12期,頁118-120。
[29] 霍爾斯蒂,《和平與戰爭:1648-1989年的武裝衝突與國際秩序》,王浦劬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238。
[30] 平松茂雄,《中國與朝鮮戰爭》,東京:勁草書屋,1988,頁24-32;和田春樹,《朝鮮戰爭》,東京:巖波書店,1995,頁23-29;亦參和田春樹,《朝鮮戰爭全史》,東京:巖波書店,2002,第一章。
[31] 沃格林,《政治觀念史稿(卷七):新秩序與最後的定向》,李晉、馬麗譯,賀晴川、姚嘯宇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頁92-97。比較費爾斯,《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清教徒革命》,曾瑞雲譯,北京:華文出版社,2020。
[32]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194。
[33]亦參哈伯斯塔姆,《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王祖寧、劉寅龍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頁1。
[34]施納貝爾等,《美國兵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後》,王天成等譯,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4,頁39。
[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569。
[36]孔華潤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冊),張振江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247。
[37]萊弗勒,《人心之爭:美國、蘇聯與冷戰》,孫閔欣等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47-48。
[38]張小明,《喬治·凱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頁11-14。
[39]凱南,《美國外交》,葵陽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頁87-88。
[40]李普曼,《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研究》(1947),裘仁達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頁7。
[41]凱南,《凱南日記》,科斯蒂廖拉編,曹明玉、董昱傑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頁193。
[42]凱南,《美國大外交》,雷建鋒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米爾斯海默“序言”,頁23。
[43] 普雷斯頓,《靈魂之劍、信仰之盾:美國戰爭與外交中的宗教》,羅輝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頁456。
[44]對各種貶低甚至歪曲抗美援朝的觀點的列舉和反駁,參見楊鳳安、孟照輝、王天成主編,《我們見證真相:抗美援朝戰爭親歷者如是説》,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9,頁2-97;張文木,《重温毛澤東戰略思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頁27-41。
[45] 拉費伯爾,《美國、俄國和冷戰:1945-2006》,牛可、翟韜、張靜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頁99。
[46] 荷馬李,《無知之勇:日美必戰論》,李世祥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頁16。
[47]漢森,《殺戮與文化:強權興起的決定性戰役》,傅翀、吳昕欣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572。
[48] D.R. McCann / B.S. Strauss (eds.),Democracy and Wa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orean War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M.E. Sharpe,2001,p.14.
[49] 參見賀方嬰,《荷馬之志:政治思想史視野中的奧德修斯問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50]參見施特勞斯,《修昔底德如何寫作戰爭志》,李世祥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第一講。
[51] 參見沃爾班克,《紀事與肅劇》,劉小楓編,《西方古代的天下觀》,楊志城、安蒨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9,頁27-60。
[52]霍布斯,《修昔底德的生平和歷史》(戴鵬飛譯),林國華、王恆主編,《羅馬古道》(“海國圖志”第5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148-149。
[53]施拉特,《霍布斯與修昔底德》,婁林主編,《拉伯雷與赫耳墨斯秘學》(“經典與解釋”輯刊第41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頁140 -158 。
[54]考克斯,《希波戰爭:文明衝突與波斯帝國世界霸權的終結》,劉滿芸譯,北京:華文出版社,2019,頁9。
[55]艾澤曼,《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陳昱澍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56]曼德爾鮑姆,《國家的命運:19世紀到20世紀對國家安全的追求》,姚雲竹等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頁124。
[57] 比較哈爾伯斯坦,《出類拔萃之輩:聰明人在越戰中的錯誤決策》,齊沛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3。
[58] 基辛格,《論中國》,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頁235。比較錢江,《周恩來與日內瓦會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頁139-149。
[59] 波拉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係》,見袁明、哈丁主編,《中美關係史上沉重的一頁:1945-1955年中美關係史學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287。
[60]肯尼迪,《大國的興衰》,蔣葆英等譯,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頁453。
[61]時殷弘,《杜魯門政府的對華政策和台灣問題》,丁名楠主編,《中美關係史論文集》(第2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頁475,487;時殷弘,《敵對與衝突的由來:美國對新中國的政策與中美關係(1949-1950)》,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137。
[62]呂迅,《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337。
[63]布贊,《美國和諸大國:21世紀的世界政治》,劉永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52-53。
[64]尼采,《敵基督者:對基督教的詛咒》,吳增定、李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第58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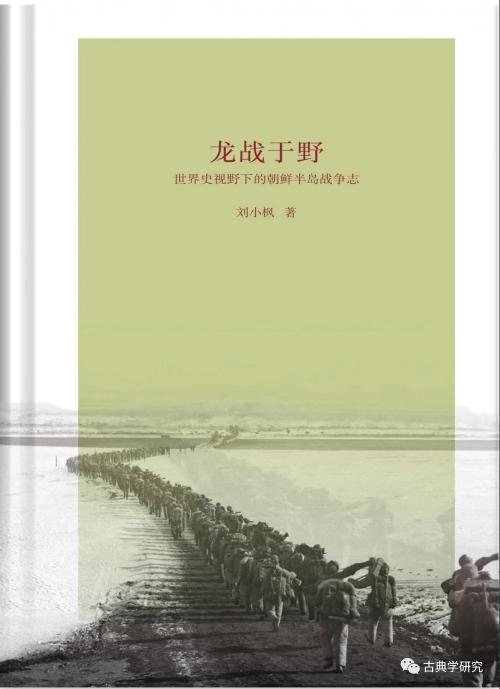
上溯自1840年以來,一切為抵抗外來侵略者而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毛澤東,《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
兼通中西之學,於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瞭然於胸中。雖閉門讀書,而已神遊五洲,目營四海。不必識其器而能考其法,不必睹其物而已究其理。
——皮錫瑞,《南學會第十二次講義》
龍戰於野
——世界史視野下的朝鮮半島戰爭志
劉小楓
目 錄
引子 開放時代的歷史靜觀
提要及文獻説明
卷一
緒論 作為政治史學問題的朝鮮半島戰爭
一 不可同日而語的歷史分水嶺
二 馬漢史學的文明自覺意識
三 太平洋兩岸的文明裂變
四 普遍歷史與太平洋戰爭
五 文明衝突抑或文明德性間的戰爭
六 朝鮮半島戰爭與文明德性
七 戰爭紀事與戰爭的歷史真相
第一章 “世界大同”夢與商貿精神
1 全球史與普遍歷史
2 韋爾斯與康德
3 “永久和平”的歌聲
4 商貿精神才能讓世界變得“温和”?
第二章 抗美援朝與新時期的精神內戰
1 何謂中國式的狄森特
2 何謂“反共偏執症”
3 張東蓀事件
4 美國國會如何整肅“親共分子”
5 中國的狄森特與美國的使命
第三章 從歐洲秩序到全球秩序
1 國際秩序與國家德性
2 國際秩序與世界歷史
3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歷史神話
4 國際聯盟構想的歷史神話
第四章 大西洋革命與全球化均勢的嬗變
1 法國大革命與歐洲均勢
2 拿破崙戰爭的世界史意義的含混性
3 “大國協調”的歷史神話
4 “民族自決”的地緣政治差異
5 美國進兵西太平洋
6 大西洋革命的“渾濁”之水
第五章 抗美援朝與全球化均勢的新起點
1 朝鮮半島與希臘半島古今對觀
2 和平主義者威爾遜如何走向戰爭
3 “冷戰”的清教起源
4 列寧時刻與中國的選擇
5 抗美援朝的前奏
卷二
第一章 世變滄桑:朝鮮半島戰爭的歷史種因
1 “託管”的政治史學含義
2 侷促的冷戰史視野
3 從“舍門將軍號”事件到“辛未洋擾”
4 日本與美國聯手遏制俄國
5 萬曆抗日援朝戰爭與全球化的東亞開端
第二章 強鄰蔑德:古代中華秩序的瓦解
1 “明治維新”如何重新開國
2 朝鮮如何脱離中華秩序
3 大韓帝國在夾縫中開國
4 “山東事件”與“世界大同主義”
5 “華盛頓會議”與全球化的東亞階段
第三章 三韓為墟:三八線的政治史學含義
1 美國如何獨佔日本
2 誰是國家主權的承擔者
3 “熱血同流”:朝鮮抗日義勇軍在中國
4 朝鮮戰爭如何走向內戰
5 美國突然更改的遠東防禦線
6 越過三八線與國際干涉的新含義
第四章 命世之英:跨過鴨綠江
1 將外國軍艦逐出長江
2 為什麼必須丟掉對美國的幻想
3 封鎖台灣海峽對新中國意味着什麼
4 新中國三面受敵
5 “唇亡則齒寒,户破則堂危”
6 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遭遇戰
第五章 懿維我祖:戰爭中的政治德性
1 長津湖畔的冰與血
2 三八線上的拉鋸戰
3 第180師的榮與辱
4 鐵原阻擊
5 上甘嶺上的德性較量
6 世界史上史無前例的停戰期
後記 政治史學與啓蒙
參考文獻
朝鮮半島戰爭史文獻編年
朝鮮半島戰爭史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