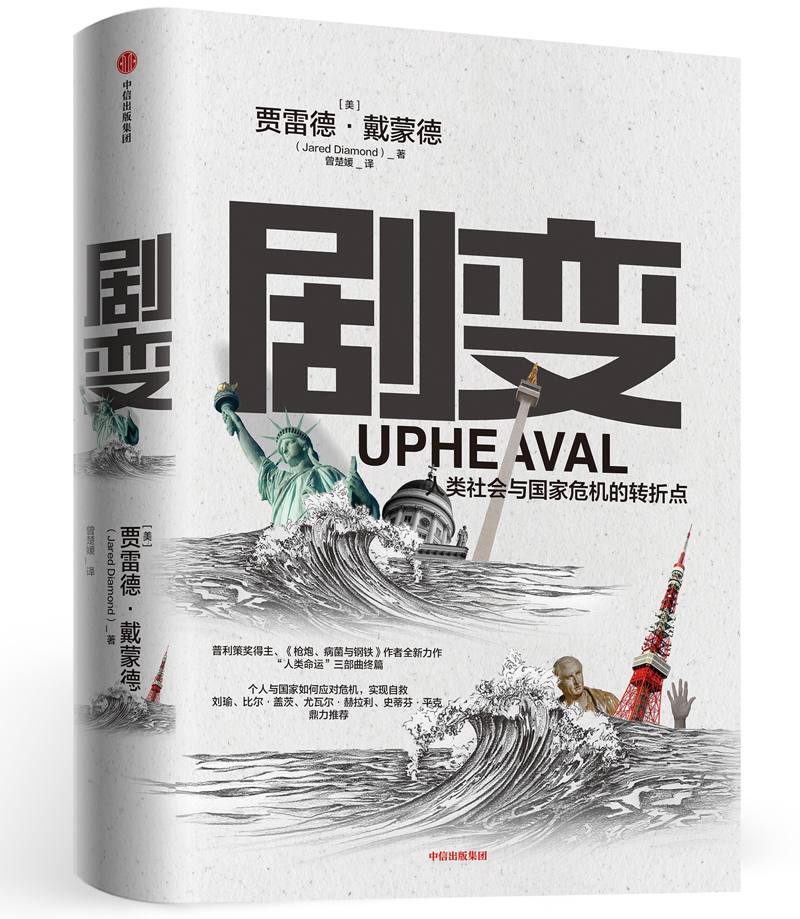賈雷德·戴蒙德:只有我們美國人具備摧毀自己的能力
【文/賈雷德·戴蒙德】
儘管我們已經將分析對象從美國政治家的極化立場擴展至美國全體選民的極化立場,在探討美國今日的政治極化問題上,我們的思考範圍還是過於狹隘。因為這種邏輯僅將極化現象侷限在政治層面。事實上,極化現象涉及的範圍不僅於此:在政治層面以外,美國的其他方面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極化、偏狹和暴力趨勢。
40歲以上的美國讀者不妨思考一下你親身經歷的變化,比如美國人的電梯禮儀問題(如今人們在等電梯時越來越不願意遵守先下後上原則),交通禮讓行為不斷減少(駕駛者之間互不相讓),登山步道和街道上的善意不斷減少(相比40歲以上的美國人,40歲以下的美國人更不願與陌生人打招呼)。除了這些以外,在不同圈子中,各式各樣的“語言”暴力越來越多,尤其是在電子通信平台上。
我從1955年開始進入美國學術界,在這個領域也經歷了類似的趨勢變化。比起60年前,今日美國學術界中的辯論變得更加充滿惡意。
早在我剛剛開啓學術生涯之時,我就經常會與一些學者意見相左,現在依然如此。然而,曾經的我會把那些在科研問題上與我持不同意見的科學家看作朋友,而不是敵人。比方説,我記得有一次參加完一場生理學會議之後,我在英國度假,和一位友善、温和的美國生理學家一起遊覽了西多會修道院遺址,儘管我和他在那場學術會議上就有關上皮細胞的液體傳輸機制持截然不同的看法。
這樣的關係在今天已經不太可能了。相反,我如今不斷受到來自和我意見相左的科學家的起訴或威脅,而且他們還會對我使用語言暴力。邀請我去講課的主辦方曾經不得不僱用保安人員,以免我受到那些極端反對者的攻擊。在針對我的一本書所發表的書評中,一名學者以“閉嘴吧!”這樣的字句作為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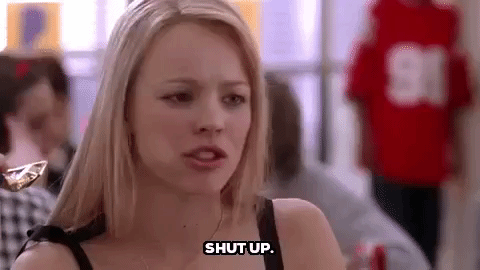
美國的學術界和我們的政治家、我們的選民、我們的電梯乘客、我們的汽車駕駛人、我們的行人一樣,都反映出了美國人的整體生活狀況。
以上這些代表了同一個現象的不同方面,這個現象就是被廣泛討論的“社會資本”的衰落。
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在《獨自打保齡》一書中給“社會資本”下了定義:
“社會資本指的是個體之間的關聯—社會關係網絡、互惠性規範以及由此產生的信任。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資本和被有些人稱作‘公民美德’的概念密切相關。”
社會資本是指人們通過積極參與併成為各種羣體的成員而建立起來的信任、友誼、羣體從屬感、施助和受助的期待感,這些羣體可以是讀書會、保齡球俱樂部、橋牌社、教會組織、社區組織和家長教師協會,也可以是政治組織、職業協會、扶輪社、鎮民大會、工會、退役軍人協會等。
參與這樣的羣體活動可以培養人們之間普遍的互惠特性,即為他人服務,和他人共事,信任他人,並相信他人以及團體中的其他成員也會為自己提供幫助。可是,美國人越來越少參與這種面對面的羣體活動,卻越來越熱衷於加入各種線上的羣體,這種線上羣體的成員之間從來不會碰面,看不見也聽不見對方。
對於帕特南和其他許多人提出的美國社會資本的衰落問題,其中一個解釋是,以犧牲直接溝通為代價而崛起的非面對面交流。電話於1890年出現,但直到1957年前後才在美國市場得到普及。收音機從1923年出現,到1937年達到市場飽和。電視機則是於1948年出現,到1955年就被普及。而最大的變革發生在近期,即互聯網、移動電話和電子短信的興起。
我們使用收音機和電視機進行娛樂和獲得信息,後來使用電話和更現代的電子媒介來達到相同的目的,只是多了一項通信的作用。可是,在書寫被髮明之前,所有的人類信息傳達和通信都是面對面實現的,通過人與人之間交談或者一起觀看(或聆聽)表演者(演講者、音樂家和演員)來完成。
儘管1900年以後出現的電影院沒有提供面對面式的娛樂方式,但它至少讓人們走出自己的房子,融入社會羣體,而且相約看電影的通常是朋友,這正是人們一同欣賞現場演講、音樂會、表演的延伸形式。
然而,現在我們的許多娛樂載體—智能手機、iPods(蘋果公司的數字多媒體播放器),還有電子遊戲,使人們更傾向於獨處而非社交。這些往往是為個人定製的娛樂方式,就像上文提到的為個人定製的政治信息。
電視仍然是美國最大眾化的娛樂方式,它使美國人足不出户,甚至和自己的家庭成員之間也漸漸淪為名義上的關係。美國人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比與人交流的時間要多3~4倍,其中至少有1/3的時間是自己一個人在看電視(通常看的是網絡電視而不是坐在真正的電視機前面)。

這樣做的後果是,比起不愛看電視的人,沉迷電視節目的人對他人的信任度更低,也較少加入自發式組織。在把這些行為歸咎於看電視之前,有人可能會提出疑問:究竟哪一個是原因,哪一個是結果,或者這兩組現象之間會不會只是存在關聯,但沒有實際的因果關係?在加拿大實施的一組計劃之外的自然實驗回答了這個問題。
在加拿大的一座山谷中,坐落着三個相似的小鎮,唯一的不同點是,其中一個小鎮恰好接收不到電視信號。在這個小鎮終於接收到電視信號後,其俱樂部和其他集會的居民參與度紛紛下降,直到最終和其餘兩個一開始就能收到電視信號的小鎮水平相當。從這個結果可以看出,是看電視導致了人們羣體活動參與度的下降,並不是人們因為不願參加羣體活動才選擇看電視。
我曾去新幾內亞島上的一些邊遠地區進行野外考察,那裏還沒有出現新的通信技術,當地人們的交流仍是面對面進行且全神貫注的—美國人曾經也是這樣。傳統的新幾內亞人將除睡覺以外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與人交談上。和美國人之間那種不常發生且經常被打斷的對話相比,傳統新幾內亞人的對話從不會因為其中一方低頭看手機而被打斷,也不會出現其中一方因在回電子郵件或回短信而注意力不集中的情況。
我有一個朋友是一名美國傳教士的兒子,他在新幾內亞島上的村落長大,直到讀高中時才遷回美國,當他發現新幾內亞島上的孩子和美國的孩子在娛樂方式上存在差異時,感到十分震驚。他曾向我描述這一發現,在新幾內亞,村裏的孩子會到同伴家串門兒,而在美國,我的朋友發現:“孩子們各回各家,關上門,各看各的電視。”
美國人平均每4分鐘看一次手機,每天至少會花6個小時盯着手機屏幕或電腦屏幕,而且每天有超過10小時(即除睡眠之外的大部分時間)在使用電子設備。這導致的結果是,大部分美國人不再與人面對面打交道,不再能直接看到對方的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不再能直接聽到對方的聲音,不再能直觀地瞭解對方。相反,我們主要通過屏幕上的電子信息來和他人交流,偶爾會通過手機聽到對方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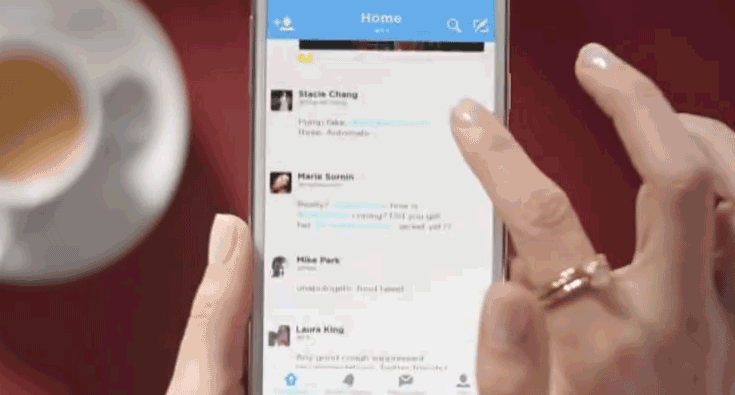
當面對一個活生生的,離我們只有兩英尺,能夠看得見、聽得着的人時,我們傾向於抑制自己的無禮舉動。而當面對屏幕上的信息時,我們更容易做出無禮和輕蔑的回應。一旦我們習慣了遠距離的口頭暴力,那麼對活生生的人施以暴力也就不再是難事了。
然而,以上這些對美國政治妥協的崩潰和社會不文明行為的增加給出的解釋,遭到了明顯的反對。非面對面的通信方式不僅在美國流行,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興起,尤其是在富裕的國家。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對手機的依賴程度不亞於美國人。為什麼在其他的富裕國家中,沒有出現政治妥協崩潰和社會不文明行為增加的情況呢?
我能想到兩個可能的解釋。
第一個解釋是,在20世紀,電子通信和許多其他的技術創新首先在美國嶄露頭角,這些技術創新和由此帶來的影響從美國蔓延到其他富裕國家。由此看來,美國只是第一個而絕非唯一一個面臨政治妥協崩潰問題的國家,像電話和電視機一樣,這種問題也會蔓延到其他地方。
實際上,有英國朋友告訴我,比起我60年前住在那裏的時候,英國現在出現的個人暴力行為要嚴重很多。澳大利亞的朋友告訴我,澳大利亞的政治生活中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妥協崩潰現象。如果我的解釋有一定的道理,那麼接下來其他富裕國家遲早也會出現美國目前面臨的政治僵局。

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早在過去,美國就因為一些原因缺乏足夠的社會資本來抵抗現代科技帶來的去人格化力量,今天也依然如此。
美國的國土面積比起除加拿大以外的其他富裕國家要大25倍以上,而美國的人口密度(即總人口除以國土面積)只有其他富裕國家的1/10,人口密度排在美國之後的只有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冰島。與強調集體主義的歐洲和日本比起來,美國一向更強調個人主義。在富裕國家裏,只有澳大利亞在個人主義的排名上超過美國。
美國人經常搬家,平均每5年就會搬一次。鑑於美國國內各地之間的距離比起日本或任何西歐國家更遠,這意味着美國人一旦搬家,他們和昔日好友之間往往相隔較遠。與之相比,日本人或歐洲人很少搬家,而且即使搬了家,他們和昔日好友之間的距離也相對較近。因此,美國人的社會關係往往較為短暫,朋友的流動性很高,很少擁有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一輩子的朋友。
然而,美國的面積和美國國內各地之間的距離是固定的,不會改變。美國人不太可能擺脱對手機的依賴,也不太可能減少搬家的頻率。上述的解釋將美國政治妥協的崩潰歸咎於社會資本較低背後的隱含因素,如果這種解釋正確的話,那麼比起其他的富裕國家,美國將繼續面臨更大的政治妥協崩潰的風險。
這並不代表我們註定會走向不可逆轉的、越來越糟的政治僵局。但這確實意味着,比起其他國家,美國的政治領導者和美國的選民需要更有意識地去努力扭轉我們的政治僵局。
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智利和印度尼西亞這兩個國家的例子,由於政治妥協崩潰,一方勢力以軍事獨裁的手段上台,其明確的目標是全然消滅對方的力量。在大部分美國人看來,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在美國。當我還在智利的時候,也就是1967年,這種情況對我的智利朋友來説就是天方夜譚。然而在1973年,這樣的事情確實在智利發生了。
美國人也許會提出反駁:“但美國可不是智利!”是的,美國與智利當然是不同的。兩個國家之間存在的部分差異使美國不易像智利那樣淪為暴力的軍事政府獨裁,但另一部分差異會使美國更容易陷入這種狀況。
一方面,使美國不易發生這種可怕情況的因素有:我們有更深厚的民主傳統,我們有平等主義的歷史理念,我們不像智利有世襲的地主寡頭勢力,而且在我們的歷史上從未出現由軍隊發起的獨立政治行動。(在1973年之前,智利軍方確實好幾次短暫地干預過政治。)

左三為1973年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資料圖/維基百科)
另一方面,美國較之智利,會助長可怕情況發生的因素包括:對私人槍支的管制較松,在現在和過去都存在更為氾濫的個人暴力行為,在歷史上曾以暴力對抗部分羣體(非裔美國人、印第安人還有部分移民羣體)。
我認為,如果美國會出現軍事獨裁,那麼其發展路徑定會有別於1973年的智利。美國不太可能會被軍方獨自接管。與之不同,我認為在美國有可能發生的是,執掌美國政府或州政府的黨派將不斷對選民登記加以操縱,往法院裏塞滿串通一氣的法官,從而利用法庭來質疑選舉結果的合法性,然後訴諸“執法機關”,利用警察、國民警衞隊、儲備軍或者軍隊去鎮壓持不同政見者。
這正是為何我認為政治極化是美國當前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它比來自墨西哥的競爭要危險得多,但我們的政治領導者更沉迷於對付墨西哥。墨西哥不能摧毀美國,只有我們美國人具備摧毀自己的能力。
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思考美國所面臨的其他基礎性問題,還有我們為防止這令人黯然的一幕出現而做出選擇性變革時所面臨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因素。
(本文摘編自賈雷德·戴蒙德新著《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