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然在追扶貧劇,敢信?_風聞
娱乐硬糖-娱乐硬糖官方账号-2021-01-25 09:09

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戈壁灘上也能種出蘑菇?原本三塊一斤的蘑菇,為何一夜讓村民賠哭?坐上飛機的蘑菇,價格怎樣不變“貴族”?請收看新一期的《致富經》,啊不,是《山海情》。

從《綠水青山帶笑顏》到《我的金山銀山》,經歷去年口碑褒貶不一的扶貧劇轟炸後,《山海情》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躥紅。忽然間,人人都覺得種好一畝三分薄地、做好一日三餐淡飯是“摸得着”的追求了。
拯救人類的英雄主義,當然是令人羨慕的。但我為什麼沒有變成奇異博士、神奇女俠呢?是因為我不喜歡嗎?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完成自己生活裏的小農任務,踏踏實實當一個《山海情》裏的種田人,就連洋芋撒飯也會有滋有味。
因為本身的政策性宣教較強,背景主要集中在遠離都市的鄉村,劇情又是稼穡之艱難。從類型特點來看,扶貧劇的創作幾乎和當下爆款劇集的元素:流量、神仙愛情、大場面與大製作等格格不入。
把“土味”進行到底的《山海情》,似乎找到了扶貧劇的正確打開方式。既有《鄉村愛情》的喜劇元素,又有李子柒的田園淡泊,更兼大時代羣像的“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全員陝方言的嘗試,除了讓人看到閆妮和王莎莎想起《武林外傳》,更説明了真實給創作者帶來的底氣。
“幹沙灘上花不開,想喊雲彩落下來。”城市化的進程並不能改變黃土地延續數千年的基因,往上翻幾代誰家不是種田人?或許我們看到劇中豐收的笑意,是骨子裏的一種肌肉記憶。
鄉土人情網絡
種田人,種田魂,種田人吊莊有精神。以吊莊移民開啓故事的《山海情》,寥寥數筆就勾勒了鄉土社會的人情網絡。湧泉村的馬得福(黃軒飾),陪幹部讓父親馬喊水(張嘉譯飾),勸逃回來的移民遵守政策,卻遭遇了最不講理的李大有。

“在那兒沙都吃飽了,我在家吃土,土還比沙子細”,在李大有的帶領下,村民充分發揮語言藝術要把吊莊給“攪黃”。與此同時,水花(熱依扎飾)逃婚讓兩村發生肢體衝突,阻斷了吊莊動員大會。從吊莊逃跑、水花逃婚,到通電難題、灌溉糾紛,再到推廣蘑菇、童工輟學,人物關係簡單卻有戲。
**愛情線只有雙箭頭,因為種地太忙難有第三者插足。**黃軒和熱依扎本來互相喜歡,卻因為父親貪彩禮而錯過。雖然早已沒可能,但每次兩人眼神交匯是既尷尬又意難平;馬得寶和白麥苗也是青梅竹馬,但因為得寶丟下麥苗去新疆找尕娃,兩人又是好幾年的糾結。

家庭線只有刀子嘴豆腐心,有雞毛但沒狗血。馬得寶覺得父親馬喊水偏心,闖蕩歸來卻給父親下了跪;白麥苗放不下母親去世的意外,總和父親白校長頂嘴,但逐漸找到了溝通方式;李大有天天罵兒子水旺,煮個雞蛋託麥苗送去外地自己卻哭了;安永富深感殘疾後,是妻子水花的拖累,但水花給了他信念,一家人日子越過越好。
事業線只有一個核心,怎樣快速和“窮”説拜拜。供電局規定60户才給村裏通電,黃軒村裏移民跑了三户只剩59户,就對供電局三顧茅廬;因為供水站和移民村的轄區糾紛,農民無法承受灌溉用水的高價,黃軒又帶着村民去和書記講理。
外出務工的海吉女工,唯一的追求就是不能被城裏人看不起。在白麥苗的帶領下,她們刻苦練習成了技術能手;當然還有郭京飛、閆妮、姚晨等人飾演的領導們,不搞形式主義一切以移民需求為先。

在《鄉土中國》裏,費孝通總結:“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係搭成的網絡。所有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係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山海情》裏的“差序格局”相當明顯,李大有攛掇村民不去吊莊、未知收益大家不願意當第一個種蘑菇的人、農民工去城裏上訪討薪皆屬此類。
但是,由於“扶貧”的聚合效應,這個差序格局也有被打破的時候。當凌教授(黃覺飾)要離開金灘村時,雖然有意隱瞞,聞訊趕來的村民還是給他帶來了各種土特產歡送。質樸的人情,在脱貧的同一目標下顯得尤為可貴。
既是種田文,也是致富經
花了7集講“種蘑菇”的《山海情》,有着鮮明的“種田文”屬性。從村民的質疑,到馬得寶首吃螃蟹的成功,再到全村參與、市場飽和後的滯銷,扶貧劇竟然拍出了一套簡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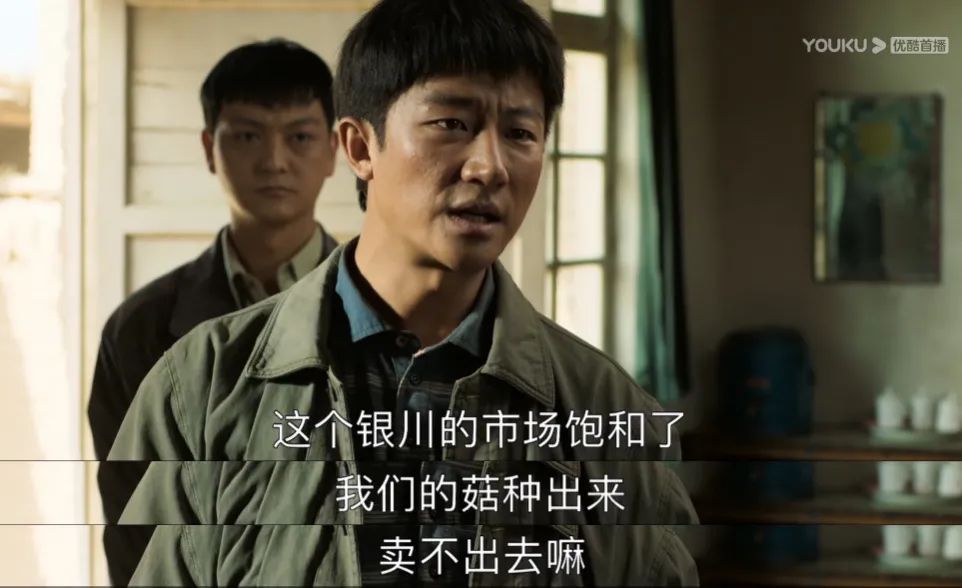
在人教版教材裏,這個故事多以“養雞老人”的案例出現。看到蛋價升高,張老漢投入養雞,賺了一筆。張老漢擴大養雞規模後,蛋價突然下跌,老漢無奈殺雞。可當老漢殺完雞,蛋價又上升了。
經典的故事模板,放在扶貧劇裏饒有興味。戈壁灘上的村民沒見過蘑菇,李大有説:“啥東西末見過,也敢往肚子裏塞呢!”等到全村下海蘑菇滯銷,莫小貝又感慨:“賣不出去只好自個兒吃,可是這東西炒起來費油啊。”大嘴在就好了,至少能給大夥兒創新《雙孢菇的一百種吃法》。
糞肥和秸稈的比例,蘑菇下種子的温度,大棚利用陽光的傾斜角,摘取蘑菇的手法。事無鉅細的《山海情》剪成《致富經》毫無違和感。而這種從無到有的奮鬥模式,正是它作為“種田劇”的爽感所在。

大家都説得寶沒幹成過一件正事,那他就埋頭聞糞種出了蘑菇。那一點點黑土裏冒出頭的白蘑菇,除了是錢更是自信;車間主任嫌海吉女工動作慢,麥苗就和姐妹們開夜車苦練,果然讓主任另眼相看。
看起來是“種田”和“安電子元件”,但是《山海情》給觀眾帶來的卻是釋放束縛的快感。都市日常充斥的職場的、家庭的、經濟的壓力,在輪番運轉之下讓人難以喘息。而在種田劇裏,這些壓力被置換成了怎麼種蘑菇、怎麼加快手裏的速度。
《山海情》裏的困難,其實就是人們日常困境的另類轉化。給出一個相對理想化的解決方式,從而很容易讓觀者產生“我也能行”的代入,以及隨之而來的動手解決問題的“爽感”。

相較於真正的“嚴肅創業”,《山海情》提供的經驗更具有情節性和趣味性,更加淺顯温和。比如海吉女工們哭了一場,車間測速比拼就全部過關了。原本打不下來的航空運費,姚晨交涉就降低了一半。不能説是金手指,但整體上的實用性是略感虛幻的。
以直白生動的語言,講述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以及章節結構對於明清世情小説敍事傳統的繼承,都標誌着《山海情》對通俗世情題材的迴歸復興。扶貧劇裏的種田,映射出了現代人對於田園生活的嚮往。而對人際關係和婚姻家庭的減法處理,則讓觀眾在紛繁現實之外有了自省的契機。
扶貧劇的結構性難題
談到扶貧劇,大家腦子裏浮現的標籤就是“喊口號”、“不真實”、“賣苦情”。這其實反映了扶貧劇(或者地方劇)在創作過程中,一味追求高大全而忽視了觀眾的內心感受。
以地方劇《鄉村愛情》為例,其豐滿生動的人物形象和幽默詼諧的台詞是“接地氣”的。“我劉能一世英名,就毀在你這娘兒們手裏!”
玩方言,《山海情》顯然做足了功課。本來黃軒、張嘉譯等人的陝方言已經夠內味兒了,沒想到還有郭京飛的“閩南語+普通話”,每次開會都要請特別翻譯黃軒。(話説黃軒還演過《親愛的翻譯官》)

凌教授的助理一口灣灣腔,每次解釋技術問題就非常機車;福建電子廠廠長,普通話是有多不好呢?因為説不清“苗”字,每次都繞過白麥苗的全名。李大有更是包袱鬼才,嫌水渠的水小直接説“碎慫(小娃)撒尿,連腳背都到不了。”
以《山海情》和《鄉村愛情》對照,大部分扶貧劇淪為純粹的“任務劇”,便在於娛樂性上做得不好。已經沒有都市劇的光鮮靚麗了,還不趕緊在包袱上抓起來,觀眾還不如點開《致富經》。
扶貧劇的結構性難題正在於:太搞笑別人不把你當扶貧劇,太扶貧又因為缺乏看點而流失觀眾。受限於這種創作特徵,扶貧劇很少取得收視效應,也就不難理解了。
去年的《綠水青山帶笑顏》,本來是要聚焦返鄉青年創業,卻沒有鄉村民宿的質樸底色,把青年創業勵志劇變成了浪漫情感劇。楊爍那麼油,不如開發《綠水青山大油田》。瞧瞧《山海情》裏滿臉土色的黃軒、白宇帆,那才是村裏寡婦會惦記的小青年。

除了抹土,建議年代扶貧劇的演員都把自己餓一餓。《山海情》裏湧泉村一天三頓水煮洋芋,這麼減脂看你怎麼好意思胖得起來?
當然,也不能為了迎合刻板印象就去千篇一律的搞土味。只要按照特定時代真實情況來拍,新時代的農村也可以富饒美麗嘛。
對於真實存在的矛盾,避而不談其實是一種歧途。《花繁葉茂》裏提到的“扶貧鍍金”問題就很典型。“一部分扶貧幹部不是為了羣眾謀發展,而是把基層經驗作為今後升職的跳板。”
《山海情》裏,明明蘑菇已經滯銷了,麻縣長還安排黃軒開現場會歌功頌德,並以仕途作為引誘。黃軒頂住了壓力,在大會上如實上報了真實情況,書記則批評了這種形式主義作風。

《花繁葉茂》與《山海情》裏提到的基層幹部問題,標誌着扶貧劇創作已經進入深水區。既關注扶貧工作裏的先進人物,又不刻意迴避現實矛盾,保證了真實的基調。
扶貧劇想要講得有滋有味並不容易,但它們與種田文的爽點內核有着曲徑互通之處,這或許正是類型突破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