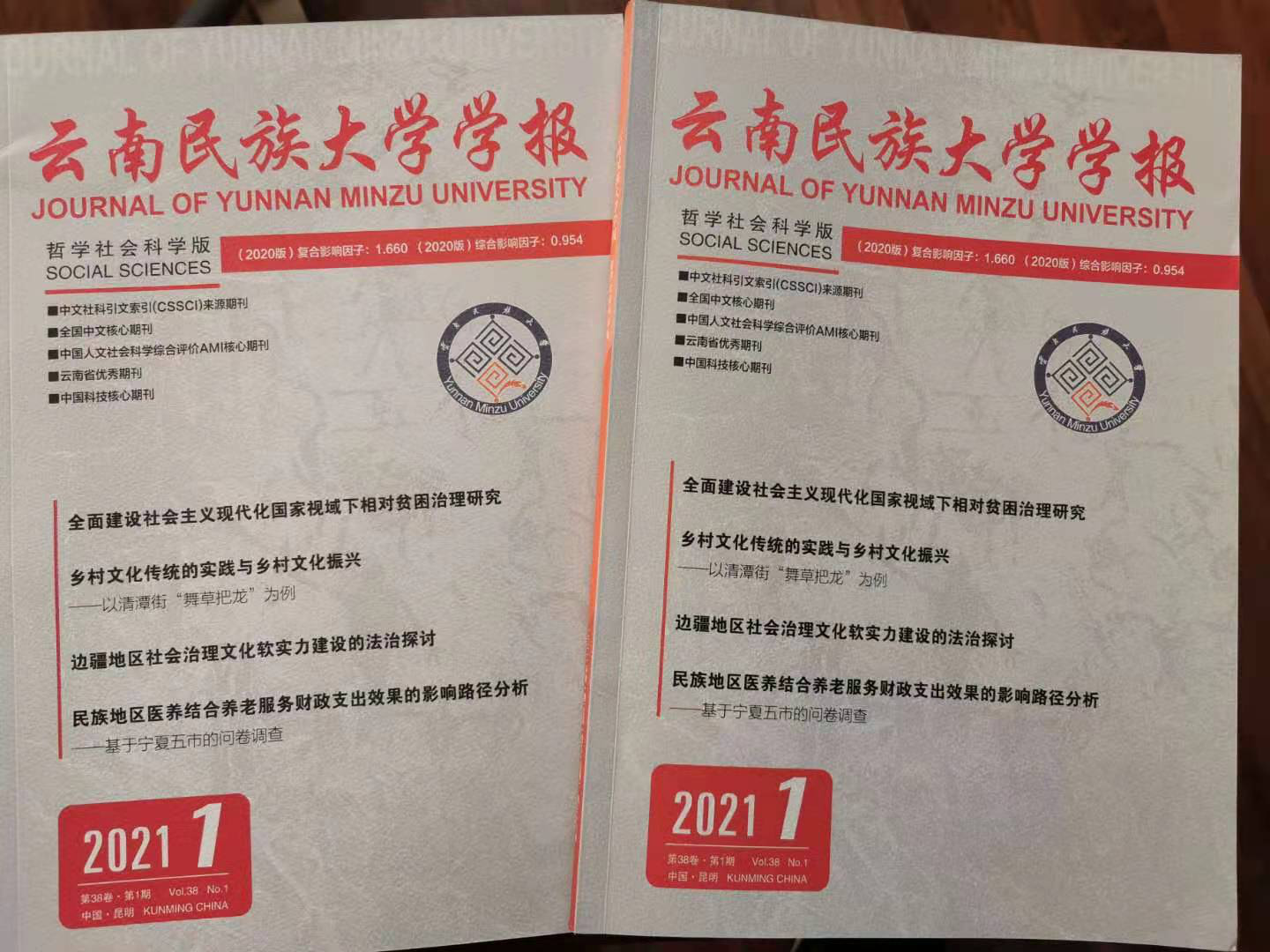宋才發、秦莉佳發表:《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法治探討》論文_風聞
UNAMID-2021-01-26 09:52
北京1月26日電56個民族共同構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整統一的格局。新時代邊疆地區社會治理工作,應當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來捍衞和保障國家統一、民族團結、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是國家規範化的區域治理,文化軟實力是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基石,是邊疆治理文化建設的基本內容。邊疆地區社會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組織化程度極低,精神文明建設不到位,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法治舉措是:動員邊疆地區社會組織廣泛參與,加強邊疆地區法治文化建設,推進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法治化建設。由雲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主管、雲南民族大學**主辦的綜合性理論刊物《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編:張橋貴,副主編:王東昕),2021年第1期發表宋才發、秦莉佳《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法治探討》論文。《雲南民族大學學報》**是中文社科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綜合評價AMI核心期刊、雲南省優秀期刊、中國科技核心期刊。

第一作者宋才發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二級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貢獻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民委首屆有突出貢獻專家,廣西民族大學特聘“相思湖講席教授”,貴州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民族法學學科團隊領銜人,博士生導師。第二作者****秦莉佳系中國政法大學2017級經濟法專業博士生,廣西民族大學法學院講師。
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文化軟實力
建設的法治探討
宋才發 秦莉佳
(廣西民族大學 法學院,南寧 530006)
一、研究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文化軟實力問題的緣起
**56個民族共同構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整統一的格局。**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是當下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最高準則。能否有效保障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既是衡量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成效好壞的最高標準,又是能否實現邊疆地區民族事務治理最高利益的體現。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事務治理的核心是對民族關係的治理,學界所論及的民族事務治理現代化,就是指民族事務治理體系的制度化、科學化和法治化。“中華民族”是由56個具體民族共同創造的精神家園,“中華人民共和國”是56個民族在最廣泛民族認同的基礎上共同創建的國家。這裏的56個具體民族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多元一體”國家體制建立過程的本身,既體現了56個民族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度認同,又體現了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56個民族成員之間的相互支持和相互認同。每個具體民族都明晰各自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的位置和應當擔負的歷史責任,始終秉持中華民族“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優良傳統,在相互尊重彼此存在差異性的同時,自覺地維護國家整體的統一,固守“愛國、勤勞、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中國是一個疆域遼闊、邊疆廣袤的多民族國家。**新時代中國邊疆地區社會治理工作,必須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來達到捍衞和保障國家統一、民族團結、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的目的。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對象和主要任務是民族公共事務,民生改善、人心凝聚和福祉損益,已構成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主要內容和評估治理成效的主要考量。地方政府應當在邊疆社會治理實踐中,依法穩妥處置好邊疆地區紛繁複雜的民族事務問題,通過發揮文化軟實力潛在的功能作用,奠定邊疆地區人民羣眾美好生活的堅實基礎,構築維護國家和中華民族最高利益的鋼鐵長城。邊疆地區基於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文化基因及內部結構的多樣性,逐漸實現了邊疆居民由“自在”到“自覺”質的躍升,逐漸凝成了底藴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孕育的中華文化,滋養了各民族文化發展的沃土,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始終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文化既是邊疆地區多民族文化熔融的現代表徵,又是當代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文化軟實力所在。為貫徹落實習近平2015年3月8日在參加廣西全國人大代表團審議時發表的“要加大對邊境地區投入力度,依法加強社會治理、深入推進平安建設,依法管控邊境秩序、維護邊境地區安全穩定”[1]的指示精神,本人曾率課題組成員3次到西南邊疆的雲南、廣西邊境地區,就“邊境秩序管控”“邊疆社會治理”問題展開深入調查研究。本文擬在調查研究獲得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文化基因這個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軟實力展開深入探討,以請教與方家。
二、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概念及其文化軟實力的內涵
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是國家規範化的區域治理。“治理”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紀晚期,當時治理研究主要是圍繞國家、社會和市場三者之間的關係展開的,重點關注的是公共權力獲得、運行及相關主體參與以及彼此互動的過程。“治理理論”研究在中國肇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它的基本含義是指維護社會正常秩序、促進社會安定團結、激發社會活力、防範社會風險的一系列體制機制、組織安排和工作過程[2]。“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規範化的區域性治理。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重心在基層,把社會治理與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有機地結合起來,可以説是對我國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的深刻總結,凸顯了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治理方法的創新,體現了社會治理局部與整體相統一、標本兼治的現代社會治理辯證思維。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國家致力於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國家與社會關係便成為治理研究的主要內容。有關部門對國家和社會治理經驗進行總結提煉,為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等不同領域的治理實踐提供理論支撐。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情勢下,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所要達到的基本目標和主要任務,就是維護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羣體的社會利益公平,化解各類現實社會矛盾,努力實現邊疆民族地區領土安全、民心穩定、社會和諧發展。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社會問題是邊疆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需要着力化解新的情況下影響邊疆地區社會秩序和民生活力發揮的結構性矛盾,讓生活在邊疆地區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國家崛起與民族復興統一於中華民族主權國家,因而鞏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這個“一母兩體”的結構,是當下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行動邏輯和根本立場。“國家意象”在邊疆地區社會整體形構中,體現為具有領土疆域界定的地理空間、國家整體利益形構的利益空間、歷史文化塑造的情感空間和制度結構形塑的規範空間[3],邊疆安全和邊疆穩定是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歷久彌新的經典課題。邊疆地區社會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特殊對象和重要組成部分,不只是關係到邊疆社會秩序構建的區域性問題,而且關係到國家主權獨立、疆域完整的戰略性大問題。與此相適應的邊疆地區文化軟實力建設,關涉到邊疆安全、邊疆穩定、邊疆和諧和邊疆發展全局,凸顯了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價值導向問題。邊疆地區通過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途徑,加強並強化邊疆居民穩定的國家認知和國家意識,是邊疆地區區域治理目標實現的主要方式。邊疆居民對國家認知和國家意識功能的增強,根源於邊疆居民對國家主權性公共空間的確認、表達與維護,是捍衞這個國家主權性公共空間的雙重力量。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邊疆地區社會治理都必須凸顯邊疆居民的主體地位,構建邊疆居民與內地居民共享的主權性公共空間。即是説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目標的實現,是整個國家與邊疆社會互動的系統過程,國民同創、全民共享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則是這個互動系統過程有效運轉的堅實基礎和情感紐帶。
**文化軟實力是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基石。**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活動,是國家整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活動又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在組織和進行邊疆社會治理活動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它的邊疆性、民族性和系統性。不能把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活動,僅僅看成是某個具體民族地區、具體族羣、具體方面的治理過程,需要在國家治理的整體視域下,科學而合理地研究解決邊疆地區社會問題的方案和措施。尤其是在“非傳統安全”已成為新時代邊疆安全主要形式的前提下,邊疆地區的國家屬性,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國家屬性,凸顯了邊疆地區文化軟實力建設,在邊疆地區社會治理與國家文化安全中的戰略地位。一個以國家文化底藴為基礎構件的文化“軟邊疆”,本質上就是一道以“硬邊疆”為基礎的、牢不可破的國家安全屏障。由於邊疆地區獨有的邊緣性和前沿性特徵,一方面決定了邊疆地區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前沿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決定了國家文化在邊疆地區相對薄弱的現實狀態。從邊疆安全建設的視角看,邊疆安全建設的重要標誌是“國家認同”,認同結構本身就包含着邊疆居民對國家歸屬感的認同,這種認同源自於他們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心理感受與歷史記憶,體現在他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自覺接受,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敬仰、傳承與弘揚。因此,邊疆地區社會治理中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必須遵循與邊疆治理體系相適應的價值體系的指導。這個價值體系的內涵就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為主體,功能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有利於促進社會生存發展、長治久安的文化軟實力體系。説到底就是要促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在邊疆地區社會里得到廣泛傳播與傳承。新時代邊疆地區文化軟實力建設,既成為“文化邊疆”構築的基本環節,又成為國家“邊疆治理”的核心構件[4]。從邊疆治理實踐的角度看,在當下境外敵對勢力仍然在不斷加強對邊疆地區進行文化滲透、宗教干預,極端分子的分裂活動和極端暴力恐怖事件頻發的情勢下,邊疆地區的部分區域事實上已經出現敵我立場的博弈現象。在這種情況下的邊疆文化軟實力建設,實質上就擔負着對內整合和強化治理功能的責任,對外應對文化主權邊疆功能弱化的挑戰。從邊疆治理方式的視角看,文化軟實力建設是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一塊穩固基石,邊疆文化的治理功能與國家文化的安全功能,日益成為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突出的核心問題。“文化軟邊疆”與“邊防硬邊疆”的雙重建設問題,已不再只是一個權衡與抉擇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實現共生共榮、融為一體的現實而重大問題。
**文化軟實力是邊疆治理文化建設的基本內容。**中華民族是當代中國基礎性的政治資源,中華文化是56個民族優秀歷史文化之集大成。它既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系中的核心部分,又是邊疆治理文化建設的基本內容。56個民族文化的精華共同融合成“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精華融為一體的“多樣性文化”。歷史上任何一個具體民族的解體與消亡,從來都是與該民族成員對文化認同的程度密切相關的。因此,當下邊疆地區文化軟實力建設的主軸任務,就是要弘揚和發展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是當下各民族文化存在與發展的母體,它潛藏着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集體良知”和“文化密碼”。從一定意義上説,在“四個自信”當中,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核心價值取向,不是“非邊疆地區”多樣文化的安全取向問題,而是通過邊疆地區文化軟實力建設的路徑,以隱性安全屏障的“文化戍邊”活動,有效地實現邊疆地區的社會治理和國土安全治理。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最終成效的好壞,根源於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文化建設的實際效能,取決於邊疆治理中文化軟實力對內“認同整合”、對外“文化戍邊”雙重功能的有效發揮。邊疆地區社會整體是由各個社會利益主體組成的,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顯著特點,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訴求是不一樣的。在強調邊疆民族地區社會治理整體推進的時候,除了必須按照國家治理任務的需要和進度安排之外,還要注重突出民族地區社會治理的重點和特色,在具體操作上,千萬不能夠像過去那樣搞“一刀切”。需要把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放在國家整體治理的大背景下思考決策,決不能單純地強調治理層次上的“碎片化”“零散化”。在技術操作上,邊疆社會治理必須實現“從分散走向集中、從部分走向整體、從碎片走向整合”[5]。整合國家邊疆治理的多重社會力量資源,有機融合56個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有效整合現代政治理性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形成牢不可破的縱橫協作、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體系,是國家“文化安全”與“文化邊疆”構建的根本路徑。為此就要形成強大的國家文化內部傳播機制,制定邊疆社會的文化教育發展方略,牢固樹立邊疆居民國家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提升他們融入國家主流社會的自信心和能力。與此同時,還要強化邊疆地區居民的當代“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因為“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既包括認知層面的認可和贊同,也包括情感層面的歸屬和依戀以及行為層面的支持和擁護,它是邊疆地區居民安身立命最主要和最現實的政治基礎。要強化以邊疆地區為陣地的邊境文化對外的輻射機制,通過邊疆地區以文化對文化的滲透與反滲透鬥爭,防禦和抵制境外敵對勢力文化對我國邊疆的滲透與輻射。可以毫不誇張地説,邊疆地區文化軟實力這種對內整合、對外輻射雙重功能的發揮,既有利於鞏固邊疆社會的國家形象,又有利於以文化為武器戍守邊疆。國家文化軟實力這種對內整合與對外輻射機制作用的發揮,須臾離不開制度和法治保障,任何不利於中華民族團結、進步、繁榮、和諧、發展的文化形態,都應當依法受到國家法律規範的規制;任何干預、滲透、破壞中華文化建設和弘揚的敵對行為,無論是來自國內還是國外,都必須義無反顧地予以嚴厲打擊。
三、邊疆地區社會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組織化程度較低。**在邊疆地區尚未實現協調發展的情況下,社會組織化程度低、跨境人員往來頻繁,確實加重了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壓力。譬如,本人帶領的課題組在雲南邊境調研中瞭解到,雲南省的邊界就與越南、老撾和緬甸等國家接壤,雲南省境內有4060公里長的國境線;沿國境線分佈着25個邊境縣、1000個邊境鄉鎮、2055個邊境行政村;擁有13個國家一類進出口岸、9個國家二類進出口岸、90個邊民互市貿易通道、103個沿邊“邊民貿易互市網點”,還有無法準確統計清楚的邊民通道、便道、暗道。這些地方都是境內外不法分子尋求偷渡出入境的聚焦點所在,客觀上增加了西南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複雜性、艱鉅性和安全壓力。加之邊疆地區有些社會組織,鑲嵌在地緣和血緣關係網之中難於自拔,對社會治理和公共精神的關注多偏於狹隘,多數社會組織目前還處於“碎片化”“條塊分割”的狀態之中,以家庭、家族為單位的高度同質化現象還相當突出。這種渙散疲軟的社會組織化狀況,很難在邊疆民族地區社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在境外不法分子無法通過邊境口岸偷渡出境的情況下,他們便把目光轉而投向“自然通道”附近的居民身上。他們往往給居民一些物質實惠和豐厚的“好處費”,致使這些邊民便鋌而走險地為不法分子帶路抑或充當司機代駕。中亞各國的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和“東突”分子,陸續從西北邊境秘密轉向西南邊境地區進行偷渡,給西南邊境地區正常的社會秩序造成了極大的威脅[6]。因此,西南邊疆民族地區邊境沿線的鄉鎮,應當通過軍警民共建共治共享方式,提升當地社會治理的政治效益和社會效益;應當不斷強化和優化邊疆地區社會組織的制度環境,依法營造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的良好社會治理氛圍;應當增強邊疆地區黨政幹部鞏固國防的責任意識,引領當地邊民和社會組織提高邊境防控能力。地方政府應當尊重和強化邊疆地區社會組織主體地位,積極塑造和培育民族地區公共精神,營造良好的社會組織生態系統,整合社會治理資源、健全支持保障體系,提升邊疆地區社會組織化程度和社會綜合治理能力。在宏觀環境層面,要逐步解決事實上存在着的“政社不分”問題;在中觀政策層面,要逐步做到工作重心下移、給基層單位賦權增能;在微觀操作層面,要逐漸滿足當地羣眾現實的、多元化的利益訴求。
**邊疆民族地區精神文明建設不到位。**邊疆地區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促使國家意識與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實現良性互動。從邊民文化認同上看,民族文化是各個少數民族羣體對國家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想象和表徵,是這些民族羣體內部相互認同的聯繫紐帶。儘管邊疆地區絕大多數地方已經擺脱抑或正在擺脱惡劣的貧困狀態,邊境地區多數居民家庭已經或正在進入殷實小康水平。但是作為“想象和表徵”的民族文化並沒有同步跟進,有些人不適當地成為某些境外“敵對外來文化”的追捧者,拾人牙慧、總覺得“外國的月亮圓”。從邊民精神追求上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之後,由於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顯著的、根本性的改變,邊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期望值愈來愈高,對幸福生活的需求日趨多元並呈現出超前性。但是居民的自我發展能力和精神素質卻沒有實現同步提升,社會能夠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與普通民眾急遽改變現實生活狀況的期望值之間呈現一定的反差,於是在有些人身上就發生了突破“法治底線”“道德底線”的越軌行為。為此上級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加大對邊疆地區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投入力度,紮實提高邊疆地區精神文明共建、共治、共享水平,着力提升邊疆地區居民精神文明整體素質水平。美好生活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共同嚮往,其中,物質訴求是人們美好生活嚮往的現實基礎。邊疆地區人民羣眾美好生活秩序的構建,既需要全體居民齊心協力、和舟共濟、共度維艱,更需要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和長治久安。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説到底,是邊疆地區美好生活構建的基礎要件。從人們的心理層面看,社會轉型通常伴隨着個體心理秩序的重構,整個社會易於滋生心態失衡和人們情緒的焦慮。從社會治理層面看,社會轉型通常是對傳統社會結構的改造與重建,因而易於導致社會分層、區域分化以及精英羣體與邊緣羣體產生矛盾與糾葛。由於在某個時期內因精神文明建設不到位,往往使得邊疆地區社會治理不得不面臨轉型的危機和發展的陣痛。義不容辭地守護好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既是邊疆地區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又是邊疆地區人民羣眾美好生活的文化基礎。這也即是説,邊疆地區人民羣眾美好生活構建的基本目標,已經天然地囊括對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維護。從社會層面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各民族羣體提供了共享的“文化符號”,有利於推動各民族形成牢不可破的國家共同體。從個人層面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既是所有社會成員安身立命的精神依託,又是每個人靈魂安頓場所和心靈逗留的港灣。再從國家層面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體現為中華民族振興的軟實力,是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石[7]。
邊疆民族地區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禮法合一模式”是當代國際社會通行的一種民族地區社會治理模式,表明法治國家對民族地區民眾的“自主性”給予較大的空間,可以説
它是民族地區社會治理民主化和公開化的重要體現。在以農業生產和農耕文明為主的傳統社會里,無論是在人們的生產領域抑或精神生活領域裏,封閉性往往限制了人們社會交往的範圍,更制約了人們觀察社會問題、分析社會問題的眼界,使得整個生活在農耕社會里的人們,處於相對隔離的自我封閉狀態之中。同時由於民族成份多元、民族傳統各異和民族文化多樣性,如在西南邊疆民族地區的社會治理中,通常並不是“法治”主動納入“禮俗”,而是法治被動地嵌入“禮俗道德”,甚至有部分“從奴隸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居民,居然至今認為自己是“上帝”“神”的子民,對自己的公民意識較為淡薄[8],致使這些地方居民的法治文明程度普遍較低。邊疆民族地區這種人們思想覺悟上的差異性,説到底是由邊疆地區文化的特殊性決定的。譬如,世代生活在邊疆偏僻、邊遠深山地區的人們,他們的“人倫血親觀念”和“宗族意識”一般都較為強烈。他們不習慣於使用法律解決鄰里鄉親之間的矛盾糾紛,而習慣於使用鄉規民約、倫理道德和風俗習慣,來處置鄰里鄉親之間的矛盾糾紛問題。由人們約定俗成的“鄉規民約”,在本質上與法治文明存在着較多的價值衝突,因而人們往往在情、理、法之間的次序上難於協調一致。即使如此,也必須正視和肯定邊疆民族地區社會歷史悠久,尤其是各種社會治理模式更迭交替,如“鄉規民約治理模式”“政教禮法互嵌模式”等,畢竟為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法治化的推進積累了豐富經驗。隨着改革開放40多年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邊疆地區居民物質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升,邊民羣體的權利意識、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也相應得到提升,他們對政治的期許也逐漸由“善政邊疆”轉向“善治邊疆”。在邊疆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始終是社會治理的引領力量和主要責任承擔者,政府的良法善治便成為邊疆地區居民政治期許的焦點。政府依法治邊、居民同心戍邊,是實現邊疆善治和提升邊疆法治文明的關鍵環節,社會治理必須堅持文化認同的法治原則。邊疆地區每個公民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分子,“從嚴執法”“全民守法”,要求邊疆地區牢固樹立對法治的理性信仰,將法律規範作為政府和公民行為不可逾越的底線,自覺地擔負起對邊疆社會治理和邊疆安全的責任和義務。邊疆民族地區要通過文化軟實力建設來消融某些事實上的文化隔閡,建立對於中華民族的國民文化認同,促使部分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人們跟上時代的步伐,實現從他們的“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轉變,在社會交往和日常生活中,自覺地遵守社會公共道德規範、職業道德規範、家庭美德規範和個人品德規範。
四、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法治舉措
**動員邊疆地區社會組織廣泛參與。**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基層社會治理,要發揮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9]。可以説多元參與、共同協作是邊疆善治的精髓。只有藉助社會組織和多元主體之間的通力合作和優勢互補,才能夠產生“1+1>2”的社會正能量,最終實現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績效的最大化和最優化。從公權力運行的視角看,“統治”是自上而下垂直的、單向度的管理模式;“治理”則是憑藉多元主體相互之間的協商與合作,從而實現對社會事務管理的模式。在任何一個法治昌明、治理有序的文明國度裏,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共同治理、共享治理成果必定是其常態化狀態。我國西南邊疆地區由於是一個相對邊緣的異質性社會,同時又是一個包容的開放性社會,各種公益性的社會組織在西南邊疆地區較為活躍。這就需要準確地把握和主動地適應當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促使基層社會治理由過去政府為單一主體,轉變成為政府主導、基層社會組織多元共治的新型治理格局。當下尤其要釐清治理主體和主要治理責任承擔者,依法依規明確地方各級政府是基層社會治理的主要責任承擔者,地方政府要妥善動員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活動,進一步完善治理機制、創新治理方式,主動從原來的“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性政府”轉變,從傳統的“大政府、小社會”向“小政府、大社會”轉變,從過去“管控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實現政府對社會治理由“善政”轉變為“善治”。各級地方政府應當把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作為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抓手,積極引導、充分調動各類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推動形成邊疆地區多元共治、富有活力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尤其要建立暢通有序的各方訴求表達、矛盾調處和權益保障機制,從治理體制、機制、結構、過程和手段諸多方面共同推進社會綜合治理。要在充分利用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力量,繼續發揮以往社會治理優勢和治理經驗的基礎上,整合國家、市場和社會有效資源,以邊疆當地居民為主體、擴大社會力量參與主體,通過軍警民共建、穩疆固邊等社會治理活動,進一步增強邊民羣體的民族認同感、社會認同感和國家認同感,儘快形成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多元共治新格局,實現邊疆地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邊境安寧和人民安居樂業的良好社會秩序。邊疆地區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社會治理活動,有利於撬動沉睡的傳統文化資源,緩解民族地區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能力不足的壓力,有利於解決邊疆民族地區組織化程度不高、社會資源分散的突出問題,可以更好地調動和整合社會閒散資源、提升民族地區基層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造血功能”。還必須提到的是邊疆民族地區的“民族習慣法”,對鄉村治理、對少數民族羣眾具有一定的約束力,能夠起到成文法意料不到的積極作用。譬如,侗族的“侗款”、彝族的“家支”和瑤族的“寨老”,就屬於利用鄉土力量進行社會控制的“民族習慣法”和傳統法治文化。西南邊疆民族地區“四川彝族自治州禁毒協會”,就曾整合彝族“家支”的民間力量,通過“歃血盟誓”等傳統法治方式,為幫助和促進吸毒人員迴歸社會做出了貢獻[10]。
**加強邊疆地區法治文化建設。**這裏所論及的“邊疆法治文化”,是指符合邊疆民族地區政治生態、經濟生態、文化生態和自然生態的諸多特點,有益於邊疆社會治理和邊疆建設的社會主義文化。當下邊疆地區法治文化建設要促進和突出邊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認同,找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邊民的價值契合點、利益匯通點和情感共鳴點,實現邊疆地區法治文化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完美結合。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提高全民族法治素養和道德素質”[11],這裏面自然就包括了邊疆地區法治主體的法治素養和道德素質元素。邊疆民族地區與內地發達地區比較起來,起碼有三個具體問題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1)邊疆地區多處於邊遠山區和深山老林,交通和信息流閉塞、市場經濟不很發達;(2)邊疆地區居民受民族宗教和傳統習俗的影響比較深;(3)邊疆民族地區國民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相比較而言普遍比較落後。要提高邊疆民族地區居民整體法治素養和道德素質,就必須從這三個實際情況出發,決不能採取內地“一刀切”的套路進行。“民唯邦本,本固邦寧”。民生安全和民生保障是當下邊疆民族地區最大的政治,讓世代居住在邊疆地區的居民過上舒心安寧的幸福生活,是當下邊疆地區社會治理和鄉村振興的重要目的之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以解決民生問題為突破口,強調要把國民教育、就業創業、收入分配、醫藥衞生和社會保障,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點和重點領域進行,明確提出要圍繞民生改善實施一系列改革舉措[12]。因此,在依法推進邊疆地區整體治理的過程中,既要加強“法治文化”軟邊疆的建設,更要加強“民生保障”硬邊疆的建設;既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共性規律,又要凸顯邊疆法治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和個性。邊疆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法治文化必須彰顯法治精神、法治原則、法治理念、法治價值的精髓,必須服務於以邊疆地區農村為基本狀況的基層社會治理活動。同時由於邊疆地區畢竟是國家的邊緣地區和特殊區域,其自然條件、生態環境、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與內地比較起來確實存在着諸多根本性區別。因而在構建邊疆地區法治文化體系、解決邊疆地區治理實際問題的時候,還必須從這些根本性區別和實際差別出發,創建一種既適合邊疆地區民生實際情況,又有利於國家主權統一、國家安全、邊疆和諧穩定的法治文化體系。邊疆民族地區本身固有的一些鄉村治理的經驗做法,如“民族習慣法”“鄉規民約”等,本身就是一種輔助國家成文法施行的行為規範,對邊疆居民的行為起到了一定的引領和約束作用,逐漸形成了一套有利於鄉村社會治理的觀念文化。儘管習慣法和國家法分屬於兩個不同的社會調控系統,但是習慣法和國家法又都是人們在社會生產與生活中形成的行為規範,都是為保障實現鄉村社會有效治理和有序發展的重要手段。因而在加強邊疆法治文化建設的進程中,在推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普及提高的同時,還必須關顧到當地傳統文化、民俗習慣的特殊性和適應性,充分發揮“民族習慣法”“鄉規民約”的積極作用,引導和促使邊疆民族地區的宗教法文化、習慣法文化與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相適應,努力探索出一條適合邊疆地區實際的法治文化建設道路[13]。
**推進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法治化建設。**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法治化建設工作,一定要堅持文化認同的法治原則,把邊疆地區居民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結合起來,以文化為根基、經濟為紐帶、法治為抓手抓緊抓實。要倡導和培育邊疆地區的法治文化,引導邊疆地區居民認同和崇尚社會主義法治,注意通過循循善誘的途徑把法治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為推進邊疆地區社會協同治理孕育更多的新型主體。要按照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法治化的要求,科學設定基層社會治理目標、任務、範圍和工作標準,推動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法治化建設深入基層、深入人心,不斷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社會誠信”既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邊疆地區治理法治化建設和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要任務。邊疆地區各級政府和公職人員要率先垂範,自覺地遵守法律法規、社會道德和公序良俗,自覺地成為社會誠信的楷模和誠信風尚的引領者。與此相適應,還要進一步完善對道德失範行為的懲戒機制,嚴防道德領域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淘汰現象。尤其要在總結邊疆地區法治化治理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基層社會治理的運行機制,健全基層網格化治理體系、執法監督體系、協商調解體系和效果評估體系,加強基層社會治理的執法規範建設,為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法治環境。邊疆治理法治化建設的本質,説到底就是實現“法治方式”與“策治方式”的有機統一,促使依法治理成為邊疆社會治理的基本價值取向。從社會規範的視角看,儘管民族習慣法與國家法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價值衝突,但是無論是鄉規民約還是民族習慣法,對鄉村社會治理和社會安全秩序,都具有一定的人心約束力和積極的社會效用。鄉規民約一般都是當地居民在生產生活中,就一些大家共同關心的重要事項,通過村民之間的廣泛溝通、集體討論和民主協商程序,最終確定下來的大家必須共同遵守的基本條款。鄉規民約與民族習慣法具有異曲同工的功效,對當地居民行為規範的形成具有自覺性和權威性,能夠起到國家法律難於達到的積極效果。構建邊境地區社會治理的良法善治,必須考慮居民的民俗習慣,尤其是政府在行使公權力的過程中,需要把當地居民普遍遵守的習慣法與國家法結合起來,培育邊疆地區居民對國家法律的普遍認同、普遍尊重和自覺遵守的良好習慣。在邊疆地區社會治理進程中,還需要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引導和規範居民的認知方式和行為模式,建立健全行政村多元治理的法治規範體系,促使當地的鄉規民約與民族習慣法成為國家法的有益補充,實現法律與道德相輔相成、法治與德治相得益彰。從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視角看,公共服務是政府實施邊疆地區社會治理的一種重要手段,對於推進邊疆地區治理法治化建設、維護邊疆地區社會穩定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由於邊疆地區地處邊遠、交通不便,“流動公共服務”便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深受邊疆地區羣眾歡迎的服務方式。流動公共服務是一種讓公共服務流動起來、活躍起來,由政府部門主動上門為服務對象提供公共服務事項的特殊方式。它作為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一種特殊活動,彰顯了政府對邊遠山區居民“一站式”服務的理念,確實是一種有效、便捷和低成本的優質服務提供方式。因而中共中央第六次民族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着力改善民族地區的民生狀況,促進社會的整體公平[14]。這種流動公共服務方式既可以是政府組織直接上門提供,也可以是由政府向市場抑或社會組織購買服務,既體現了流動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多元化、供給手段的多樣化,也反映了它作為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法治化的多樣性。目前在邊疆民族地區推行得比較好的“流動公共服務”,仍然是以堅持和弘揚法治文化為主體的公共服務,主要有“烏蘭牧騎”“馬背小藥箱”“草原110”等[15]。對於這樣一種有益於推進邊疆地區治理法治化的創新舉措,需要從一開始就對其每一個具體環節制度化,把頂層設計與基層治理實施方案結合起來,為其提供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和堅實的法治基礎。
參考文獻:
[1]習近平講話.轉引自成小龍.探討媒體融合新路 共商法治報業發展大計[N].新法制報,2015-03-23(1).
[2]洪大用.與時俱進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N].人民日報,2018-10-23(7).
[3][4]劉永剛.中國邊疆治理中的文化建設論綱[J].雲南行政學院學報,2018(5):34-40.
[5] 楊松祿.論國家治理視閾下的邊疆民族地區社會治理[J].攀登,2017(3):78-83.
[6]張志遠等.雲南邊疆多民族地區社會治理創新研究——以西雙版納州為例[J].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6(1):68-75.
[7]朱碧波.新時代中國邊疆治理的邏輯體系研究[J].寧夏社會科學,2018(4):72-78.
[8]漆彥忠.民族地區社會治理模式變遷與有效治理——從“禮治”到“善治”[J].廣西民族研究,2019(2):47-56.
[9][1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17-10-28(1-5).
[10]謝勇.促進民族地區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幾個着力點[N].中國民族報,2019-03-22(5).
[12]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3-11-16(1).
[13]陳路芳、肖耀科.邊疆法治文化建設研究[J].廣西社會科學,2018(12):209-212.
[14]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作重要講話[N].人民日報,2014-09-30(1).
[15]白維軍.流動公共服務與邊疆民族地區社會治理[J].民族研究,2017(3):1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