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大鵬:為藝術獻身這事兒説起來還挺害臊的_風聞
娱乐产业-娱乐产业官方账号-带你了解行业的“热点”“盲点”“痛点”2021-02-03 07: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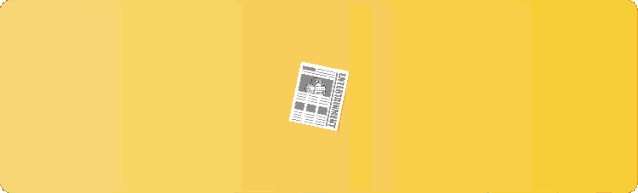
作者 / 耿凌波
《吉祥如意》聚焦的是一段非常私人的情感體驗,作為導演,大鵬在這部電影中記錄了姥姥從生病到離開的最後畫面。在與娛Sir的對話中,他吐露了自己對姥姥情感上的依賴,“小時候,父母不會經常陪我,都是姥姥在照顧我,所以我和她感情非常深,我想起來就會覺得,姥姥是我非常在乎的人。”
可以想象,作為姥姥最心疼的“大外孫”,他會經歷怎樣艱難的創作過程。“説實話,我在操作這個內容的時候,心態非常複雜”,大鵬時常感到自責,攝影機當時為什麼沒有停下,“作為一個家庭成員,姥姥過世的時候,你同時在進行拍攝,這個東西沒有辦法紓解。”
電影當中有一些畫面,剋制地記錄了他的掙扎。按照東北農村的風俗,老人舉行葬禮的時候,一家人要跪在地上,圍着火堆向前爬,大鵬跟在後面,靈魂彷彿遊離在肉體之外。之後他在採訪中回想這一段,“我當時更多的是恍惚”,最親的姥姥去世,但自己作為導演又不能流露崩潰,“那種壓抑,讓我非常受困。”

剪輯過程也是痛苦的,每次投入在素材當中,大鵬都要經歷一場大崩潰,然後放一放,讓自己喘口氣,緩過勁兒來,隔一段時間再投入進去,奔潰之後又停下來……“確實有很多次做不下去,不是技術的層面,是情感的原因”,大鵬告訴我們。一個活生生的人,被冷峻的創作反覆鞭笞,這樣的動作循環,一直持續了四年。
如今電影面向市場公映,任何宣傳期中的普通一天,大鵬都要再承擔答疑解惑的工作,這就迫使他的思緒不斷地“重回”姥姥的葬禮,不斷地陷入攝影機要不要停的糾結,也不斷地籍由發問來拷問自己。從上午十點到晚上十點,“一直在聊這個事兒”,他苦笑。痛感還在持續,甚至大到無形、蔓延到銀幕之外。
互聯網上、影迷羣中、評分網站上,大鵬的這份痛苦,被人們拉片、談論、反思,《吉祥如意》也在一次次解讀中,進入了創作的下一個階段。事實上,不斷被拿來澆灌創作的這種痛苦,大鵬之前也嘗過。
沒有科班背書的情況下,他就闖入了電影行業,幾乎手腳並用地當起了導演,拍出了大銀幕處女作《煎餅俠》;而在音樂電影還是國產電影中的薄弱類型的時候,他又埋頭鑽研這個此前在國內幾乎沒什麼經驗可借鑑的類型;一直沒有停下拓展可能性的腳步,不斷去嘗試各種挑戰難度極大的角色……
閒暇時候,大鵬回想起來,總覺得不可思議,“我是有什麼樣的膽量,開始接觸這樣的事兒”,包括他正在籌備的新電影,也將討論一個全新議題。
他似乎總沉浸在焦慮帶來的創造力中,“我一直都是這樣,會思考很多事兒,就怕沒事兒幹”,在大鵬看來,焦慮才是自己的常態,“沒事兒乾的狀態會更焦慮”。最近一次“沒事兒幹”是2020年上半年,疫情蔓延,幾乎所有人都在居家隔離,雖然“沒事兒幹”是一個普遍的狀態,但他會感到格外難受。
這種荒蕪的感覺,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派在海上漂流的那種狀態,漫無目的,同時也沒有希望。
因此,儘管面對素材對於大鵬而言,可能意味着極大的痛苦,但他還是強迫着自己,重新投入到素材當中,利用2020年上半年,把《吉祥如意》成片剪了出來。而更早之前,在抉擇這部電影是否要繼續拍攝的時候,他雖有過短暫的猶疑,但最終還是做出了不關攝影機的決定。

回溯他之前的創作,也都是誕生在主動製造的“不安全感”當中。
《煎餅俠》是當年為數不多進入“十億票房俱樂部”的導演處女作、一度被評為最賺錢的國產電影,彼時找大鵬拍續集的投資蜂擁而至,但觀眾並沒有看到《煎餅俠2》;《縫紉機樂隊》時運不濟,上映時被誤解、差評,下映後卻得到許多讚美,有人勸大鵬,“觀眾對這部電影有同情分”,但觀眾也沒有等到《縫紉機樂隊2》。
在所有的這些選擇中,他沒想過後果,只知道自己是導演。
在痛苦中浸泡久了,大鵬也有陷入自我懷疑的時候。2018年,《吉祥如意》前半部分《吉祥》拿下第55屆金馬影展最佳劇情短片獎之後,大鵬躲進酒店放聲痛哭。“我那天不知道時間是怎麼過去的,就沒有時間的概念,只有一大段空白。按理説得獎是大家對你創作的認可,應該去慶祝,但我拿着這個獎,其實一點兒都不開心。”
大鵬回憶當時的情境,“我一個人看着那個獎盃,我覺得這是一個獎盃,我們稱它是一個獎盃,那麼獎盃又是在獎賞什麼呢?獎賞你這段痛苦的經歷嗎,還是獎賞你勇於把自己的傷疤揭露出來給別人看?”他想不明白。
我們換了個問法,開頭那個無法紓解的心結,什麼時候才能告一段落?大鵬回到一個導演的狀態,“只要有電影院開着,只要它(《吉祥如意》)能上映,有人看就行,哪怕沒什麼票房,對我來説,這就是這個事兒的一個終結。”
大鵬或許沒想明白,但導演大鵬知道。
以下為娛Sir專訪大鵬實錄:
娛Sir:關於要不要把特別私人的情感體驗展示給觀眾,你最開始糾結過嗎?
**大鵬:**我不是特別糾結。因為大部分像我這個年齡段的人,都經歷過這種大家庭的成長,每一家的具體情況是不同的,但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在過年過節或者聚會的時候,大家會針對家裏面的一個核心問題去討論,所以這個故事具有一定的普適性。
我特別希望把它呈現出來,引發一些大家對個人和故鄉、個人和家庭的一些關係的思考,看看能不能有一個積極的作用,比如改善一些關係。
像我自己,因為操作了這個電影,現在會更加依賴父母,好像比以前更黏着他們,有機會每天都會視頻電話,我就不再像以前一樣,只顧自己的事業,讓聯絡沒那麼密切,這是我自己的改變。我也希望很多觀眾通過看這個電影能夠得到改變,所以出發的時候真的沒有太多設想。
娛Sir:把這部分東西展示出來,在外界引發一定的討論,這對你來説會不會形成傷害?
大鵬:我不主動擔心。
娛Sir:為藝術獻身?
大鵬:也談不上,為藝術獻身這個事兒説起來還挺害臊的,沒有那麼偉大,就是我做的一個選擇。我需要自己更勇敢一點,把這個事情做完,因為我覺得它需要被做完,總覺得(《吉祥如意》)會起到積極的作用,會讓更多人去思考自己的家庭關係。
所以這個小我這件事兒,我沒有考慮太多。可能一直以來,我説實話,就伴隨着我的爭議其實挺多的。我會聽到不同的聲音,所以也不是特別擔心再有新的質疑,因為已經挺多的了,所以對我而言,我只想把它完成。

娛Sir:還能看到《縫紉機樂隊2》?
**大鵬:**這個目前已經不重要了,可能在《縫紉機樂隊》上映的當時,對我而言還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但現在因為它在網絡上有更長的一個時間週期,作品放在那兒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比如為它在豆瓣打分和評論的人數,遠遠超過《煎餅俠》,這意味着過去很長時間觀眾的基數其實是足夠大的,只是大家都是在網上看的,所以我覺得,只要觀眾在就行,這一點我還是挺樂觀的。
娛Sir:不會想要在票房市場上再去證明一下嗎?
**大鵬:**我這個人太複雜了,雖然自己評價自己不太好,但接受了這麼多采訪,別人問我問題的過程,也會迫使我去思考答案,然後就會對自己進行一個梳理,這個東西出來之後,其實也嚇我自己一跳。
比如説《吉祥如意》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它其實就是失控的內容,你出發的時候肯定想不到會拍成這樣,一切都是回過頭來看的時候,確實你遇到了一系列意外,然後你把他拍到電影裏,可是這當中有多少導演技巧的成份呢?
如果你誇張了這一部分,就會顯的特別不近人情,因為它確實有很多天意的成份,但這個天意為什麼被你撞上了而不是別人?所以這其實很複雜。
我自己同時兼具了自信和自卑兩個特點,有的時候我非常自信,比如參加《演員請就位》,節目組説你可以拍一個片子,從他邀請我的那個時刻,我就認為我肯定會拍的非常好,雖然那個時候我都不知道要拍什麼,但自己特別有這個自信。
但同時我又自卑,這個自卑是有很多維度的,比如長期在一個爭議的評價中浸泡着,這對一個人的信念是非常大的挑戰,就導致了我做很多事兒是不自信的,會有非常自省的一面,於是在這兩種強大的情緒衝突之下,我其實在創作上是挺擰巴的。
一方面覺得拍《縫紉機樂隊2》,本身會有一定的粉絲基礎,大家也會期待着你電影裏的人物再去生長出新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會有一點較勁的成份,其實從國內到國外很多優秀的系列電影已經證明了,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商品,但是我就是不想拍。
娛Sir:因為你知道一定能拍好是嗎?
**大鵬:**其實就是自信的部分又湧現出來了,就是我這兩年如果拍續集的話可能不錯,拍另外一個新的電影也可能不錯,為什麼不試另外一個呢?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評價而造成的一種選擇,就是我不想做我習慣的這些事兒。
娛Sir:入行到現在有感覺到被接納的時候嗎?
**大鵬:**我覺得這取決於自己的感覺。我是覺得有很多時候,我是不是被接納,取決於我自己怎麼想,如果我自己覺得大家接納我了,我就覺得大家接納我了。如果我自己開始抗拒,我覺得是不是最近怎麼怎麼樣,那我其實就要警惕自己去懷疑是不是大家對你有任何的一些小看法。
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值得被重視,就是不要特別把自己當回事兒。
娛Sir:在《演員請就位》,你有什麼新的收穫嗎?
**大鵬:**我其實非常享受在那個節目的時候,認識了很多年輕的演員,你會真的感受到他們身上渴望進步和成長,希望多聽你説兩句關於表演的事兒,我覺得那個氛圍確實特別好。確實有點兒遺憾的是,它作為一個真人秀,需要製造出一些看點。

每次錄製都要錄三天,但最後會濃縮成三四個小時,勢必就會有些取捨,針對那個節目也卻是產生了很多的爭議,也會成為我自己新的困擾,就是説為什麼變成這樣,是不是我確實有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同時因為又拍了一個《花木蘭》,大家又挺肯定這個作品,我覺得觀眾也挺可愛的,估計也是同一撥人。
所以後來確實有一些收穫,比如我意識到,未來儘可能做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兒。比如拍電影,你做導演可以自己剪輯、配樂、規定時長,即使最後被別人罵了,你也是應該的,是因為那事兒就是你要去承擔的。
相反有些你做不了主的情況,就會讓你顯的很被動,因為這個被動而來的所有東西,你承擔不起那個讚譽,批評也會有一些曲解的意思。所以我意識到要儘可能做自己更擅長的事兒,因為人肯定有不擅長的。
當一個局面產生的時候,我總會不自主地傾向於場面上比較弱勢的一方,就是希望能夠平衡這個局面。
後來我看有人分析我,説因為我以前有長達十幾年的互聯網公司的工作經驗,做網絡編輯,那個時候沒有微博、朋友圈,往往是起什麼標題就能決定多少點擊量,這在某種程度上,就相當於在無形中訓練了你的思維方式。
所以當一個不平衡的局面出現時,你會不自覺的跳入到那種思維,想讓這個關係平衡,但因為能力的問題,你又沒有辦法做到,我覺得他分析的還是有一定道理。所以像這樣的事情,如果意識到了,以後就儘量少做,把這個短板不要過多得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