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啓蒙的努力,失敗了?_風聞
补壹刀-补壹刀官方账号-为民族复兴鼓与呼,与中国崛起共荣辱2021-02-26 08:03
執筆/李小飛刀
“站在2020年的最後一天,我敢僭越地説一句,過去三十年所有啓蒙的努力,失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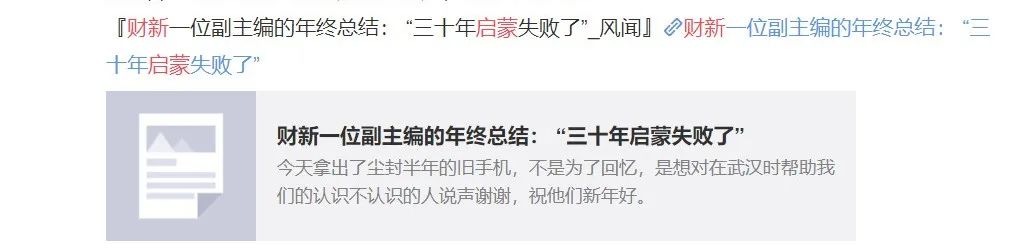
舊年歲末,財新傳媒常務副主編高昱,在社交媒體上貼出以上一段文字,懷抱一種似乎“高大”、悲哀、孤獨的情緒,嘆息“教訓已經被忽略”,“越來越多我們想給予幫助免於恐懼的人,變成了痛恨我們的人,比那些欺壓他們的人更恨我們”,“鍵盤俠們舉着放大鏡,在微博上圍剿着一切敢揭傷疤的人”。
他的這種自居“高大”的口吻,在網絡上激起更多的憤怒和調侃,獲得最多點讚的評論説,三十年來失敗的只是高昱這類公知,而勝利的是人民。
1
三十年前,國門初開,李澤厚一句“救亡壓倒了啓蒙”,引起了不少知識分子共鳴。
他們認為,“新文化運動”本是一場啓蒙運動,旨在喚起個體自覺與個性自由,但“五四”打斷了這一進程。而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接續“新文化運動”未竟的使命,將“啓蒙”進行到底,重新發揚“個人解放”事業,使中國“迴歸”人類文明的大道。
高昱顯然不可能身處這行列中,1975年出生的他,彼時還是個中學生。在河南信陽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長大,母親當了一輩子老師。1995年,從河南農業大學園藝系畢業的他由於成績太差,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正好看見一個師兄在考中國新聞學院,後來也跟着考了這個學校。
高昱記得,有一次和同學,一個山西農民的兒子坐公共汽車,討論“三農”問題。高昱説,他們當時決定一定要為作為記者的責任感努力和奮鬥,因此後來走上了新聞人的道路。

還在新聞學院上學時,高昱就進入《三聯生活週刊》,從記者、編輯一直幹到主筆,其間最為出名的,是對河南艾滋病村的報道。
2002年年初,高昱離開“三聯”,擔綱新創刊的《商務週刊》主編。
2010年5月4日,《商務週刊》雜誌社接到中國新聞出版主管部門的文件通知,指其報道國家電力公司的《國網帝國》一文,“違反宣傳紀律和期刊出版管理規定,將內參內容公開化,造成負面影響”,且“多處內容與事實嚴重不符,使相關單位合法權益受到傷害”,因此勒令停刊一個月。

停刊事件間隔不到一年,《商務週刊》宣佈清盤,高昱在微博上寫到,“這顆子彈飛了11年,終於飛不起來了”,同年,他進入財新傳媒《新世紀週刊》。
作為常務副主編,高昱主持了財新在2014年那段時間圍繞反腐所做的一系列深度報道,包括《周永康的紅與黑》《趙衙內的房產帝國》。公安部副部長原李東生、央視財經頻道原總監郭振璽的“落馬”報道,也都由他擔綱。

2020年1月20日,鍾南山院士在記者會上證實新冠肺炎出現“人傳人”,財新負責人敏鋭地想到2003年的SARS,便要求高昱組織一個團隊去武漢。
駐漢期間,高昱帶着兩名記者和一名攝影師走訪了武漢的大小醫院。其所做的報道,包括對李文亮的採訪以及“骨灰盒”等一些細節,後來成為西方媒體,也就是高昱口中“歪屁股遞刀子”的重要材料,為此沒少挨質疑和批評,也成為他哀嘆“越來越多我們想給予幫助免於恐懼的人,變成了痛恨我們的人”的原因之一。
2
從記者到主編,20年來高昱留下的文字不少,所涉頗廣,也可以從中大致勾勒出,他腦海中的“啓蒙”究竟是個什麼樣。
對社會管理,他崇尚“小政府”,他認為,政府“本身並不具備管制龐大而複雜的社會的能力”,因此需要“監管者的被選擇性,司法救濟與阻嚇的獨立,以及第三方社會組織和‘第四種權力’的實力抗衡”。
其對政府的角色是懷有深深成見的。他認為,“將廣泛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道德權力拱手讓給政府”,“只會產生虛假的安全感”,其“必然結果”是“權力分配資源的權貴資本主義,是權力控制秩序的警察國家,是權力任意揉搓權利的集權依賴”。
像許多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一樣,他認為政府的“良性價值不是提出了什麼宏大戰略、強力打造了多少世界第一”,而是在“嚴格限制和有效制約下,把留給它的少數公共服務工作做好”。
對經濟,他推崇西方自由市場,相對地,他自然而然地把中國的市場經濟看作“由權力主導市場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偽市場”。至於市場經濟中的不合理現象如何抑制,他寄希望於市場在資源配置和價格發現中發揮作用,以及資本家的良心發現——按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所説,“感恩、大度、正直、勤儉、自我剋制才是社會人的根本”。
在高昱看來,無法自由發揮的資本家是值得同情的,如其在財經專欄的第一篇評論中所説,“忍忍忍忍忍。這是馬雲手心裏寫的五個字。企業家,果然是弱勢羣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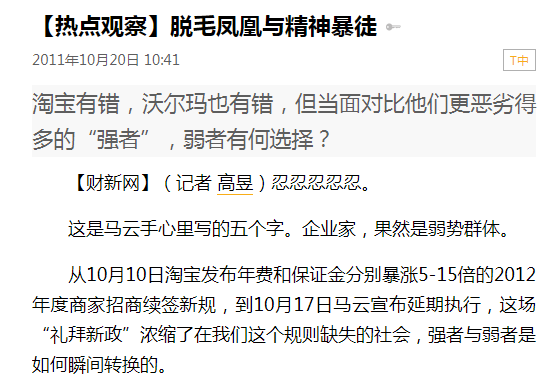
2008年奧運會遭遇西方媒體抵制和歪曲後,高曾給西方媒體寫信,稱中國新聞從業人員以前“懷着恭敬的心情”閲讀過一些來自西方書籍,但“更愛着自己的國家,併為自己是一箇中國人而驕傲”,西方“給予了媒體要公正客觀的價值觀,也告訴無數中國人平等和自由的概念”,如今卻庸俗地使用“自由、平等、博愛”。如果西方“把低頭做小弟作為參加奧運的條件”,中國人會堅定地站在一起,不憚於向一個不願平等接納我們的西方説再見。
高哀嘆啓蒙失敗後,有人拿出魯迅“庶民的勝利”批判他,而“庶民的勝利”也曾高被拿來作為批判公權力的武器,他認為“庶民並沒有勝利”,因為“庶民遭權力不公對待的案例比比皆是,被報道出來的也多有,但絕大部分最後都以被損害的庶民忍氣吞聲而告終”。
那麼高昱眼中的理想國是個什麼樣?2015年10月,改革元老杜潤生逝世,高在報道中借杜的話説,“現代民主國家,既有透明的政府,還有公民社會,組織起來,參與國家事務管理”。
這段話聽起來是美好的,是被稱為“公知”這個羣體的理想國,在中國大幅落後於西方的時候,曾經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很強的吸引力。然而,隨着中國的快速發展,以及民眾在政治上的逐漸成熟,這個理想國裏潛含的對西方體制的推崇,對中國體制的否定等信息,都被人看破,甚至引起了條件反射式的警惕和反感。務實的中國人腳踏實地創造了奇蹟,公知思維的天真和幼稚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
3
有熟悉高昱的學者告訴刀哥,高昱認識問題的根本,是中國選擇哪種發展道路的問題,是誰最終戰勝誰的問題。
這位學者認為,相對於一些徹底投靠對岸的極端分子,高昱是温和的自由派,他有民族立場,但對發展道路的認識是站在西方自由主義那一邊的。他們認為,日本和韓國已經開了先河,中國也最終會奔向“世界主流”,目前現狀只是權宜之計,是最終走向西式“自由民主”道路的中介。
高昱們是缺乏制度自信的,他們從根本上認為西方比中國優越,但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的“冷凍療法”也不可取,西方也要理解中國的特殊性,同時中西方不應該鬧彆扭。
然而,正如高昱自己承認的,西方在新冠肺炎中“愚蠢的反襯”給了他們那一羣人最嚴厲的衝擊,林肯紀念堂前的方尖碑“倒了”,中國的年輕一代不再認同當下的中國不過是將來向西方的過渡,而是正在向世界展示優越性的冉冉升起的國度,人類的未來不再華山一條路,中國人也不需要別人啓蒙,中國正在超越啓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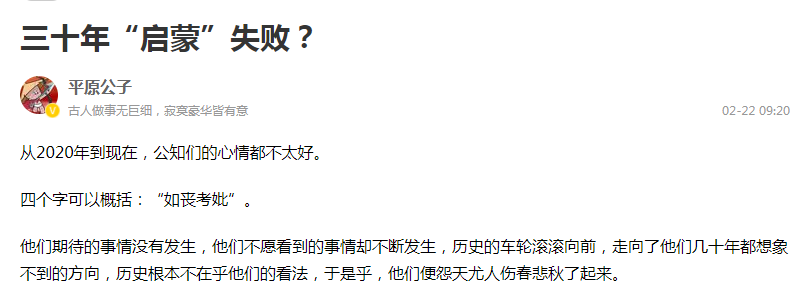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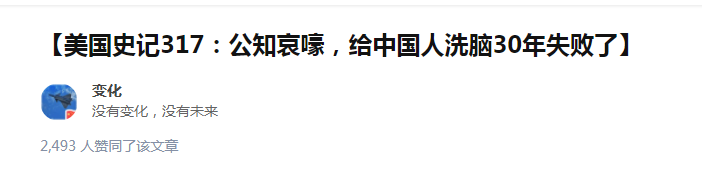
這是高那一羣人所不能接受的。
對西方的失望,對中國的失落,是他們悲觀的根源。
這是一種小布爾喬布亞式的泡沫,如果它匯不進時代,就讓它隨風而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