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是怎樣算成的:與弦有關的偉大論戰丨展卷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03-21 12:37
偉大的作曲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曾説:“音樂這種形式和數學較為接近——也許不是和數學本身相關,但肯定與數學思維和關係式有關。”今天的文章圍繞着“弦”,講述了數學與音樂之間的親密關係。這場論戰對微積分之後的數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音樂仍然是音樂,是“靈魂的語言”。

撰文 | Eli Maor (以色列理工學院博士)
譯者 | 張嶺 (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
很久很久以前,也許是 5000 年前的某一天,一位不知名姓的獵人發現,當他撥動獵弓的弓弦時,弓弦發出的聲音具有某種特定的音高。大約 2500 年前,薩摩斯的畢達哥拉斯發現,在琴絃長度和其音高之間存在着一個定量關係,這是人們將音樂與數學聯繫起來的首次嘗試。但是,要想更為全面地理解兩者之間的關係,則要等到 18 世紀,那時,將有四位偉大的數學家致力於解決這一問題——他們試圖用新近創立的微積分來尋找答案。
如果我們撥弄吉他的琴絃,或者用琴錘敲擊鋼琴的琴絃,琴絃的靜止狀態就會受到擾動,那麼此時,問題的關鍵就是如何確定這條緊繃的、柔韌的琴絃的形狀。在前一種情形下,琴絃被賦予初始的位移;而在後一種情形下,琴絃被賦予的則是初始的速度。總之,這兩種情況均給出了琴絃的“初始狀態”。原則上,根據初始狀態就可以確定琴絃在未來任何時間的形狀。
我們撥弄琴絃的時候,會瞬間擾動其靜止狀態,琴絃會形成一個三角形,儘管這個三角形又長又矮(肉眼很難確定高度)。在我們放開琴絃的一瞬間,這種干擾會分成兩個脈衝,沿相反的方向順着琴絃傳播開來。它們傳播的速度取決於琴絃的物理參數,即撐住琴絃的張力和琴絃材料的線密度(單位長度的質量)。實際上,琴絃所起的作用相當於一個一維的波導,使信號沿着該介質傳輸。
如果琴絃無限長,那麼這兩個脈衝將沿相反的方向永遠行進下去—當然,這裏有個假設條件,即不存在遲滯運動的摩擦力。但實際上,琴絃的長度是有限的;其兩端被緊緊固定,導致兩個脈衝在兩個端點間來回運動,它們會週期性地組合成“駐波”(standing wave),即一種上下運動,而琴絃上的每一個點都參與其中。這種週期性運動只能是一種以琴絃的最低頻率,即基頻,振動的純粹的正弦波,或者是若干頻率為基頻的2、3、4、…倍的正弦波的疊加組合。這就是我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諧波,它們將琴絃分解成單個的部分,其波長分別為基本波長的1/2、1/3、1/4、…,並且每一部分的振動都彼此獨立。琴絃的實際運動則是所有這些波的總和或者疊加。
18世紀的數學家面臨着一個困境:如何確定琴絃被撥弄時所形成的初始三角形的形狀?該三角形有一個尖鋭的頂角,它會演變成許多—也許是無數個—正弦波彼此疊加在一起,每個波的形狀都異常平滑。這個問題成了一場激烈辯論的焦點,幾乎每位數學家都不遺餘力地參與其中。他們之中,有四個名字脱穎而出:丹尼爾·貝爾努利(Daniel Bernoulli, 1700-1782),萊昂哈德·歐拉,讓·勒朗·達朗貝爾(Jean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和約瑟夫·路易·拉格朗日(Joseph Louis Lagrange,1736-1813)。下面,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四位主角。
丹尼爾·貝爾努利是一個顯赫家族的第二代,他的家族數學家和物理學家輩出。這個家族來自瑞士巴塞爾(Basel),一座安詳寧靜的大學城。經過五代的傳承,貝爾努利家族至少出過八位傑出的成員。這些家族成員之間相互競爭,彼此嫉妒,他們做出了很多的發現,也不斷捲入因這些發現而引起的諸多論戰之中。他們會就工作中的技術細節激烈辯論,而家族成員之間的論戰對此更是火上澆油。
丹尼爾的父親約翰[Johann,也被稱為讓(Jeanne),1667-1748],及其兄長雅各布[Jakob,也被稱為雅克(Jacques)或者詹姆斯(James),1654—1705]是貝爾努利家族在數學領域取得非凡成就的第一代成員。老貝爾努利們充分利用新近創立的微積分理論,在連續介質力學的幾個領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其中包括彈性力學、流體力學以及振動理論等。雅各布還撰寫了一篇關於概率理論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即《推想的藝術》(Ars conjectandi,該書在雅各布去世後於 1713 年出版)。丹尼爾·貝爾努利繼承了父輩的事業,他在 1738 年發表的論文《流體力學》(Hydrodynamica)中提出了一個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著名定律(即“貝爾努利定律”),為飛行理論奠定了基礎。丹尼爾和父親經常投身於相同問題的研究工作,他們分享各自的見解,但會為某些細枝末節而爭吵不休。有一次,約翰由於不得不和丹尼爾一起分享巴黎科學院(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項殊榮而大為光火,最終將兒子永遠逐出門牆。在家族中,丹尼爾是唯一一位在數學理論及實驗物理學方面均取得不朽成就的人,而其他人的最主要成就都是成為數學家。
在四人當中,萊昂哈德·歐拉顯然是成果最為豐碩的一位。他的成果如此繁多,以至於儘管尚未全部出版,就已經堆積了大約 70 卷專著,涉及當時已知的所有數學和物理學領域,包括數論、力學、流體力學、天體力學,以及他所開創的拓撲學。以歐拉命名的定理和公式比其他任何科學家都多,其中最著名的公式有兩個。一個是方程 V - E + F = 2,數值 V 為任意簡單多面體(由平面圍成,且不存在任何孔洞的固體)的頂點數目,E 為邊的數目,F為面的數目,該方程解釋了這三個數值之間的關係。另一個是謎一般的 eπi + 1 = 0,它將數學中最重要的五個常數融為一體。該公式中的三個符號裏,有兩個,即 e 和 i,是因為歐拉才出現在數學表達式的。另外,他還引入了函數的表示方式 f(x) 。他所發表的影響力最大的專著是兩卷本的《無窮小分析引論》(Introductio in analysin infinitorum,1748),被認為是現代數學分析的奠基之作。從廣義上講,此書探討了連續性的問題。
歐拉出生在巴塞爾,他先師從約翰·貝爾努利,之後於 1720 年入讀巴塞爾大學,僅用了兩年便從大學畢業。1727年,歐拉移居到俄國聖彼得堡,並在那裏待了 14 年。此後,他接受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邀請加入柏林科學院 (Berlin Academy of Sciences)。但是,國王和他的這位學者相處得並不融洽,腓特烈更喜歡那種誇誇其談的人,而不是性格羞怯的歐拉。因此,1766 年,年近六旬的歐拉又回到了俄國,並在那裏度過餘生。晚年的歐拉厄運不斷:他先是失去了一隻眼睛的視力,接着另一隻眼睛也失明瞭;他的房子毀於火災,許多手稿都因此遺失;但他的厄運遠不止於此,5 年之後,他的妻子撒手人寰。百折不撓的歐拉再次走進婚姻的殿堂,失明也未能阻止他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他具有強大的專注力,這使他能夠完全憑藉心算進行最複雜的計算。在生活中,歐拉謙遜大度地讚揚他人的工作成果,這一特點使他與學界中的其他人迥然不同。
讓·勒朗·達朗貝爾是巴黎城裏一位玻璃匠收養的私生子;這個剛落地的嬰兒是在聖·讓·勒朗教堂(Church of St. Jean-le-Rond)被人發現的,於是長大以後,他就用教堂的名字為自己命名。像同時代的大多數數學物理學家一樣,他在連續介質力學和天體力學領域涉獵廣泛。1743 年,達朗貝爾發表了《動力學》(Traité de dynamique),在該書中,他提出了一條公式化的定理(“達朗貝爾原理”),即任何處於外力影響下的動態系統都可被視為處於靜態平衡。達朗貝爾通過改寫牛頓的第二運動定律得到了自己的定理,將廣為人知的 F= ma 改寫成 F-ma = 0,並將該公式解釋為作用於系統上的所有力的總和為零。憑藉該定理,達朗貝爾順利解決了當時困擾眾人的諸多問題,包括流體力學以及地球的分點歲差問題。
達朗貝爾曾擔任《德尼·狄德羅大百科全書》(the Great Encyclopedia of Denis Diderot)的編輯,這部作品旨在涵蓋當時人類全部的知識。但天主教會顯然對此書相當不滿,也許主要原因在於它以理性而非靈性作為要旨。所以,他最終放棄了自己的編輯身份。後來,達朗貝爾設法陸續得到了法國國王路易十五(Louis XV)、普魯士統治者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以及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的青睞。從某種程度上講,達朗貝爾的性格頗為傲慢,有着強烈的自我意識,這無疑與他和當權者之間的聯繫有着密切的關係。
約瑟夫·路易·拉格朗日伯爵是四人之中最年輕的一位;當他捲入到有關振動弦問題的論戰時,還是個寂寂無聞之輩。儘管他擁有法國姓名,但是在意大利都靈出生和長大的。他是家裏十一個孩子中年紀最小的,也是唯一活到成年的。拉格朗日很早就展示出對數學的濃厚興趣,並在年僅 19 歲時便成為都靈皇家炮兵學校(Royal Artillery School of Turin)的教授。1766 年,他遷居德國,接替歐拉的位置成為柏林科學院的院 長。1794 年,他被任命為著名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 of Paris)的教授。拉格朗日的暮年備受抑鬱症困擾,還未及 50 歲,他的工作成果就直線下降。於是,他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管理事務方面。1793 年,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拉格朗日被任命為一個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負責向全世界推廣重量及測度的公制度量系統,這是法國對科學界最偉大的貢獻之一。
拉格朗日的主要貢獻是差分方程(differential equations),以及與離散介質和連續介質相關的力學領域。他在代數和數論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對牛頓的三大運動定律做了公式重構,即用差分方程以及變分法(calculus of variations)的形式重新構建。原有運動定律的關注點是作用於系統的力,拉格朗日卻將焦點轉移到系統的能量上。拉格朗日引入了 T-U 這個量(即系統的動能與其勢能之間的差值),並使其成為力學的核心概念;它也因此被稱為“拉格朗日函數”(Lagrangian)。憑藉這一方法,力學定律被他用一種完全通用的方式進行公式構建,而與特定座標系的選擇無關。事實上,拉格朗日將牛頓力學變成了一個純數學的分支。他從 19 歲起就開始動手撰寫,直到 52 歲時才全部完成著作《分析力學》(Mécanique analytique,1788),這部作品在理論力學領域具有里程碑般的意義。此書的寫作方式更像一本抽象的數學專著,全篇沒有一幅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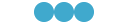
第一個挑起論戰的是丹尼爾·貝爾努利。早在 1732 年,他就認識到琴絃具有基礎頻率,除此之外,若干其他純音的頻率為該基頻的2、3、4、…倍,它們均能通過琴絃的振動被彈奏出來;他甚至推測存在無窮多個這種純音。1740 年,他寫道:
有多種方式能讓一根繃緊的琴絃發出許多同步產生的顫音,在理論上,其數量甚至可以是無窮多個……當[通過撥動]琴絃形成一個弧形時,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模式就出現了;接下來,琴絃會呈現出最為緩慢的振動,併發出該琴絃能產生的最低沉的樂音,此音即為所有其他樂音的基礎音。另一種模式是讓該琴絃產生兩個弧形,則振盪將加快兩倍,琴絃會發出比基礎音高出一個八度的樂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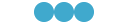
達朗貝爾在發表於 1746 年的一篇論文中,發現了波動方程的解可以用兩個波來代表,它們從初始擾動開始背向傳播。這兩個波的形狀是由弦的初始狀態,即在t = 0 時,弦上每個點的位移和速度決定的,但擾動自身可能具有任意形狀。這隨即就引發了一個矛盾:彈撥琴絃的時候,琴絃最初會呈現為一個三角形,即兩條直線在一個尖點處(此處,曲線的斜率無法定義)連接在一起;而波動方程有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即琴絃的任何位置均處於光滑狀態,那麼該方程的解怎麼能是一個三角形呢?很快,這一矛盾便將爭論轉移到更加寬泛的話題:到底應該如何定義一個方程。方程能否包含一個尖點,即斜率會從一個值瞬間變成另一個值的點?函數的圖象是否必須連續變化?當然,方程的概念如今已經得到了清晰的闡釋,但是在 18 世紀,人們對方程的瞭解還很貧乏,導致相關的解釋眾説紛紜。
針對這一問題,貝爾努利和歐拉給出了一種不同的答案:琴絃的形狀是琴絃振動所包含的所有正弦波的總和。這就完全避免了尖角問題,也更加符合振動的物理性質:畢竟,當人們彈撥吉他時,可以聽見樂音,但並沒有看到波沿着琴絃傳播。至此,這場爭論引發了一個新的問題:達朗貝爾提出的波傳播的理論,以及貝爾努利提出的正弦波觀點,這一對截然不同的基本事實如何才能成為同一個方程的答案?此處,我們不必討論具體的技術細節,這會讓今天的讀者失去耐心;我們只需要挑出這場爭論的幾個片段:
作為主編以及法國大百科全書的首席數學權威,達朗貝爾從未忘記自己的這個身份,他在《弦的振動》(Vibration of Chords,1745)一文中寫道:“大體上……我堅信我是第一個解決該問題的人;在我之後,歐拉先生給出了幾乎完全一樣的解決方法,唯一的區別就是他的法似乎更冗長一點。”貝爾努利在一封寄給歐拉的信(1750)中寫道:“我沒法弄清達朗貝爾先生到底想説什麼……除了摘要,他給不出任何一個具體的例子。依據他的觀點,一根琴絃的基本聲音[頻率]為1,而其他的聲音[頻率]分別為[基頻的]2、3、4等整數[倍],我很好奇他如何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在試圖模仿你,但是在他的文章中,除了他的[這種行文]風格,我找不到一點事實。”
即使是一貫温文爾雅的歐拉也逐漸失去了耐性,沒心思和達朗貝爾周旋下去。1757 年,在一封寄給法國數學家皮埃爾·莫佩爾蒂(Pierre Maupertuis)的信中,他寫道:
達朗貝爾先生通過論戰讓我們火冒三丈……他對自己的觀點確信不疑,還炫耀在當初和[丹尼爾·]貝爾努利先生就流體力學進行的論戰中獲得了最終的勝利,儘管每個人都同意實驗結果站在貝爾努利先生這邊。如果達朗貝爾先生有克萊羅先生[亞歷克西斯·克萊羅(Alexis Clairaut),在差分方程方面有所貢獻的法國數學家]那樣的坦率,他就該立刻繳械投降。但就事情的發展來看,如果法國科學院公開表示會將他的觀點記錄下來,那麼數學科(這一章節)在很多年內都將充斥着關於振動弦問題的爭論,而這些東西沒有絲毫意義,因此在最後的合集中最好還是將達朗貝爾先生就該話題發表的言論壓制下來。他還要求我承認從他那裏剽竊了很多東西。但是,我的耐心已經耗盡了,我要讓他知道,我什麼都不會做,他隨便到什麼地方去發表他的東西,我才不會出面阻止。在《百科全書》裏,他有足夠多的東西填滿《聲明》(Claims)那篇文章。
這之後,“達朗貝爾先生不再騷擾我了,我已經下定決心,無論他發表什麼針對我的言論,我都不會和他兵戎相見。”
表面上,達朗貝爾和其他“幾何學家”(這是他給予自己同行的稱呼)之間的分歧並不完全與學術相關。由於達朗貝爾與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關係特殊,而且他是柏林科學院的院長,同行們或許都曾試圖與他維持良好的關係。但是,當歐拉最終與達朗貝爾決裂時,出於打擊報復,後者勸説腓特烈把身為科學院首席數學家的歐拉轟走,換上拉格朗日。
在論戰的後期,拉格朗日也加入戰團。儘管作為一名數學物理學家,拉格朗日的聲譽日隆,但在其他人已經得到的成果之外,他幾乎沒有任何新的進展。有時,他的數學推理難以讓人信服,特別是在那篇從離散介質談到連續介質的有關弦的論文中,他使用的邏輯漏洞百出。為掩飾這些問題,他用了大段的冗詞贅句[據數學歷史學家莫里斯·克萊恩(Morris Kline)所言,“基本空洞無物”]。但是,我們或許還是可以稍微諒解一下他,因為當時,拉格朗日的精力主要放在他的代表著作《分析力學》(Mécanique analytique,1788)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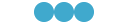
有意思的是,量子理論的好幾位先驅者在其大半生中都鍾愛音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他那把標誌性的小提琴已經成為一個傳奇(很少有人知道他還彈奏鋼琴),馬克斯·普朗克和保羅·埃倫費斯特(Paul Ehrenfest)都是不錯的鋼琴家,而維爾納·海森伯最初是想投身音樂事業,之後才轉入理論物理領域。他們與這些 18 世紀的數學家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喋喋不休地爭論着讓他們着迷的弦問題,大概除了歐拉,無人對音樂保持着基於藝術的終身愛好。他們演奏着或可被稱為“數學音樂”(mathematical music)的樂曲,將畢達哥拉斯學派對數值比例的痴迷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青年時期的歐拉,年僅 23 歲時就撰寫了一部關於音樂理論的長篇大作——《一種新的音樂理論》(Tentamen novae theoriae musicae,1730)。在文中,他嘗試依據“愉悦”的程度給不同的和絃標定某個數字尺度。這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工作,不過,據他的助手和未來的女婿尼古拉·菲斯(Nicolas Fuss)所言,“這篇論文造成的影響非常有限,對音樂家來説,它包含的幾何知識過於龐雜,而在幾何學家看來,它囊括的音樂知識又太過繁複。”
最終,這場關於弦的偉大論戰並沒有完全解決引發這一討論的問題:如何用數學公式來確定以及表徵振動弦的形狀?儘管四位數學家已經接近問題的答案,但是,人們不得不再等上半個世紀,直到另一位法國人給出了最終的解決方案。關於他的故事,我們將在下一章講述。
毫無疑問,這場論戰對微積分之後的數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探索了應對連續介質問題所要使用的技術手段,而振動弦正是這類問題最簡單的範例。這場論戰也起到了跳板的作用,人們由此開始研究其他諸多的連續系統問題,從質量分佈不均的琴絃到振動的梁、膜、鍾以及氣柱。簡而言之,這場論戰導致了人們稱之為理論聲學(theoretical acoustics)的誕生。但是,它對音樂是否產生了影響?畢達哥拉斯主義者的夢想就是將音樂置於數學的規範之下,但是音樂遵循着自己的道路,特立而獨行,儘管存在一些明顯的例外,卻對數學這位睿智夥伴的影響具有免疫力。兩者之間存在的親密關係為眾人稱道,但這種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