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人「不賺錢」_風聞
壹娱观察-壹娱观察官方账号-2021-03-22 1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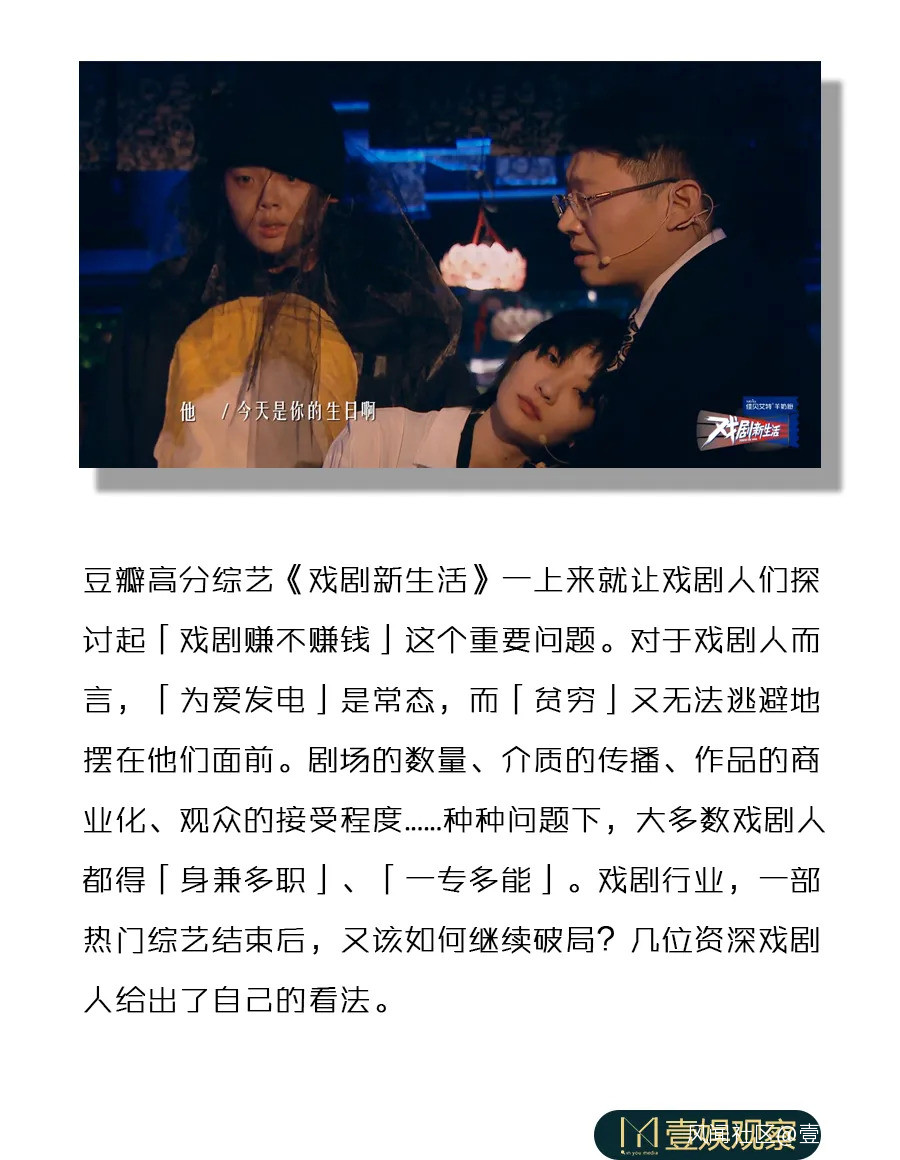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壹娛觀察(ID: yiyuguancha),文/明小天。
3月12日,文旅部發布消息,“對處在疫情低風險地區的劇院等,上座率不再統一限制”,引發戲劇人集體“狂歡”——這意味着,持續多時的“75%上座率”限制即被打破。
近年來,戲劇行業頻頻“出圈”,受到市場青睞,戲劇演出也漸漸成為文藝生活的“剛需”:高分綜藝《戲劇新生活》熱播、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搶票靠秒殺……另一方面,“拮据”“貧窮”這類標籤始終伴隨戲劇人的生活出現在大眾面前,戲劇人的生活狀態惹人注目。
戲劇人“拮据”狀態並不罕見。
戲劇產業結構諸如演出場所、演出方式、售票方式等都決定了戲劇人無法像音樂人、電影人一樣依靠現代傳媒手段、通過一部作品獲得“一勞永逸”收入;戲劇的即時性、現場性特點,也決定了戲劇人必須依靠一場場重複的體力演出,才能獲得相應收入。

經典話劇《四世同堂》
誠然,依靠贊助費、廣告費等名目戲劇人的確可以獲得部分增收,但另一方面,有些作品的票房等收入也需要多方分賬:劇院、出品方、演出方三足鼎立,戲劇行業“僧多肉少”的局面就此形成,以至於不少戲劇人需要依靠翻譯、培訓等其它手段以獲取更多收入來源。
而作為戲劇行業下游的演出者們,日子也並不好過。
與百老匯、倫敦西區等可以週期性復排、有穩定票房收入的戲劇作品相比,國內戲劇行業還缺乏相對“出圈”的商業戲劇。這進一步導致戲劇演員需要不斷試鏡、面試,以謀求更多演出機會和收入,這種不穩定的狀態也使得戲劇新人無法僅靠演出生存。
戲劇人們通過《戲劇新生活》發出“沒錢”的呼喊,戲劇行業現狀才被放置聚光燈下被大眾看見,但這檔綜藝的意義遠不止於此。

《戲劇新生活》劇照
戲劇人的生活狀態如何?面對困境,他們如何破局?壹娛觀察(ID:yiyuguancha)採訪了三位與戲劇有關的從業者,他們既有戲劇圈頭部導演、演員,也有在象牙塔頂端北京大學工作的戲劇製作人,還有在一線直面戲劇市場環境的資深戲劇運營人。一起來聽聽面對與戲劇有關的問題,他們是怎麼回答的……

劉曉邑:我做了20部小作品後,才開始做商業戲劇
導演、演員,代表作《戰馬》《悟空》
去年,《戲劇新生活》節目組找到我,説要拍一部關注戲劇人的綜藝,我覺得很有趣,就決定加入他們。
其實在沒參與節目之前,這部綜藝中的很多人我們都彼此認識了,我想這與戲劇本身就是一個很小眾的圈子有關。
比如節目中的吳彼,我們之前已經是好朋友了,所以加入這檔綜藝,對我來説更像是體驗一種“與相識的人共事參與新活動”的經歷。

吳彼
事實也的確如此,在烏鎮錄節目的這段時間,的確為我帶來很多有趣的人生體驗。我們八個男人在一個屋子裏睡了兩個月,大家都重新回到剛開始做戲時的狀態:兩個月的時間創作了十部戲,這是挺“瘋狂”的事兒,但我們衝勁十足……這些經歷讓我覺得這是我生命中該遇到的一些事兒。
通常我們的創作時間只有三到五天,三五天時間需要把舞台調度記住然後把台詞、動作等貫穿在裏面,所以我們節目的很多作品是拿現有劇本進行改編的。
我很喜歡《一個絕望的人》這部作品,是法國作家嘉布里埃·迪莫瑞的作品,這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劇本,通過台詞推動故事情節發展,非常考驗演員基本功,但我很喜歡這種作品。
錄完節目後的第二天,我就馬不停蹄趕回上海,沒時間休息,因為手裏的幾部戲劇要繼續排練,這也讓我覺得,做戲劇的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其實也不是一開始做戲劇就有這麼大的工作量,剛入行那會兒也一直是自己花錢做戲劇。
我是那種“我喜歡的事兒即便別人不給我錢我也會做”的人,包括現在我好多劇也是自己投資自己做。我本科期間一直在做舞蹈相關的工作,接了包括當時央視很火的幾檔節目的編舞,2010年本科畢業之後想嘗試一些未知領域,就轉到了戲劇領域,直到2015年國家話劇院《戰馬》(中文版)演出之後,我的工作量才漸漸飽和。

2015年國家話劇院《戰馬》(中文版)
所以《戰馬》應該算我戲劇生涯的一個分期,不僅是因為這部戲讓我有了更多工作機會,在此之後我也開始漸漸學着如何與團隊相處。
作為《戰馬》的木偶導演,當時一匹戰馬需要三個人控制,這就很考驗大家的團隊合作能力,而我們是一個由五十多人組成的團隊,就好比帶領一幫兄弟打仗,我得挑起責任,照顧好團隊的每一個人。
後來的音樂劇《悟空》也算我戲劇生涯的一個新階段。《戰馬》之後,我做了挺多戲劇,其中也有很多實驗性作品;但《悟空》之後,我算正式進入了商業戲劇階段,這意味着,我的戲劇可以直面觀眾,而且可以持續演出了,而持續演出則意味着這部作品可以有比較穩定的票房收入。
所以,年輕戲劇人應該多去參加藝術節,嘗試更多演出形式,只有足夠量的積累,才有可能出精品。這些經驗會體現在導演如何與團隊合作,如何對時間、資金進行把控,這些事兒很重要,需要實打實的訓練,最終也會體現在戲劇人的作品中——我就是做了20部小作品之後,才開始漸漸做起商業作品的。

《戲劇新生活》劉曉邑
幸運的是,現在給年輕人創作戲劇的平台也越來越多,年輕戲劇人們上升的管道會越來越多元,不像我們那個年代,可能就只有一個戲劇組,現在放眼望去,會看到很多戲劇組。所以,只要作品足夠好,戲劇人足夠努力,就會有很好的上升通道。
但也可能要經歷很多事情,需要戲劇人們堅持。
在前些年,我們也做過商業的運營。但有商業投資,就需要KPI,要帶着團隊賺錢,而且沒有選擇的餘地。有一次,我問製作方,身體不舒服,可不可以請半天假,製作方沒有立刻回答,而是説需要“申請一下”,結果申請之後告訴我不能請假,也是從那次之後,我不想繼續在這裏工作了,後來我就離開了那個團隊。
前不久,我們在《戲劇新生活》裏提到“戲劇人不賺錢”這個話題。我覺得,戲劇人“賺不賺錢”,與戲劇產業結構有密切關聯:劇場數量有限,意味着每次只能賣幾百張票,收入也不會像電影一樣,一次演出就一勞永逸,而是需要戲劇人每天排練、演出,才能有與之匹配的收入。
這幾年,因為我們樂於嘗試新鮮事物,也有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收穫。“公共空間表演”是一種近幾年在國外興起的新戲劇形式,戲劇人走出劇院,去到廣場、美術館或者街頭表演。

烏鎮戲劇節
這種形式在國外很流行,在國內卻剛剛開始,我們看到了這種新的藝術形式,在疫情之前就開始排練這種類型的劇目,因此疫情期間,我們被政府、藝術節等機構邀請到户外進行表演,所以説我們受到疫情影響不算大。這也給了我一些啓發,我們在安全的地域、安全的時間,選擇做一些新的、未知的甚至説是“不安全”的嘗試,但恰恰是這些嘗試,讓我們在疫情期間活了下來。

李實:“一專多能”讓我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
戲劇製作人、任職於北京大學外國戲劇與電影研究所
我是個title有點兒多的人,除了戲劇製作人這個職業外,我還是一名老師,在北京大學外國戲劇與電影研究所工作,負責帶着學生們排戲、表演。
因為北大學生比較忙,所以通常上課都是我與大傢俬下調解,一場戲除了一兩場羣戲外,其他的分角色的場次,都會和演員單獨約時間。不過,因為很多同學是沒有表演基礎的,所以我們除了排戲之外還要教大家表演基礎知識;此外,我們排練很多莎翁作品的時候,裏面很多英文發音和我們現在學到的英文還是有一定區別的,這也是一個挑戰。

國家大劇院製作莎士比亞話劇《哈姆雷特》
一部作品成型之後,我們會在後期參加藝術節,也會進劇場演出,這個時候劇目操作方式就會像一個專業院團了。通過這些,也能讓這些非專業的同學們感受到一部作品從幕後到台前,從排練到商演的完整誕生過程。這種實踐也是我帶的這門課亮點之一,我也很慶幸的看到,越來越多學生通過這門課瞭解戲劇、愛上戲劇,並想繼續在這個專業中深造。
和他們一樣,我一開始接觸戲劇也是從聽約瑟夫-格雷夫斯老先生在北大的課程開始的。當時我還是攝影師,因為這部劇需要攝影,我通過朋友介紹參與了這部劇的創作過程。
雖然只是拍照,但看完那場演出後,讓我關注到戲劇演出這種有趣的藝術形式,於是我在暑假報名參加了格雷夫斯在北大暑假學校開設的戲劇課程。
那年夏天,我也正式加入了《一個人的莎士比亞》這部劇的演出隊列,開始了自己的戲劇生涯。之後幾年,我一直在北大幫助格雷夫斯做劇務,並開始學一些表演和導演的知識,漸漸開始從事戲劇幕後工作,偶爾也會被安排一些莎士比亞劇中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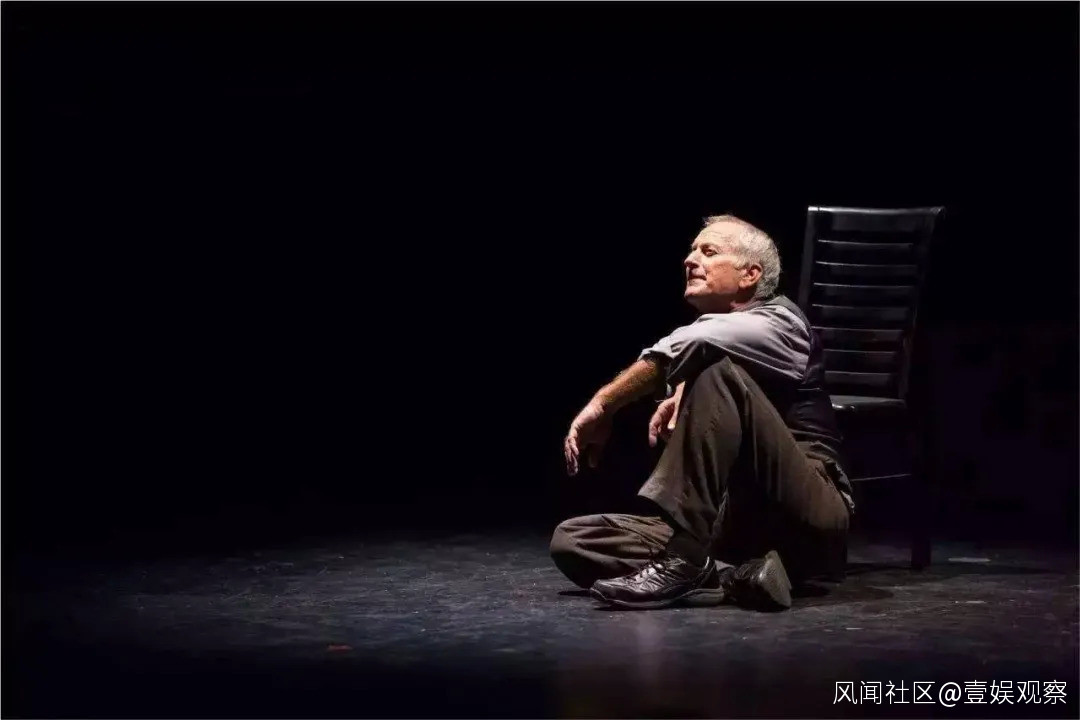
《一個人的莎士比亞》
我負責這部作品的“演出統籌”,可以把這個角色理解為“項目經理”,主要工作是負責花錢,並在每個具體的工種上找到合適的人。
因為這部作品的設計、導演這些演出排練環節已經完成,所以去外地演出時,我就要負責舞美、道具準備、技術合成、工作人員安排、燈光音效控制、字幕翻頁以及外地食宿交通等工作。
但坦白講,作為戲劇工作者,雖然有着豐富的精神世界,但物質上並不能算特別富裕,就像最近在戲劇圈很火的一部綜藝《戲劇新生活》第一期裏面提到的,戲劇人進圈前幾年還是要忍受一種比較拮据的狀態。
這與國內戲劇的“小眾”有很大關係。國內戲劇“不出圈”,無法像很多經典外國劇目一樣呈現週期性排演,這就導致演員需要不斷試鏡、面試,這種狀態給演員帶來一種“漂泊感”,也是戲劇新人無法靠演出生存的一個重要原因。
像很多戲劇人一樣,如果單純作為一名戲劇工作者,我可能也會處在一種拮据狀態之中,所以我除了是一名戲劇工作者外,還兼職教師、翻譯這些工作,它們能確保我靠着自由職業生存,過上一份相對體面的生活。
去年上半年,劇院停工、學校也不能開學,有戲劇陪伴的生活好像一下子陷入停擺狀態,我就在課堂上發動大家在線上做“廣播劇”,用聲音表演,也希望大家一直與戲劇相伴。

2020年國家大劇院演出項目《王者之舞》因疫情宣佈取消演出
這段時間,我們在排練一部名為《把褲子穿上》的美國話劇。劇本講述了在1942年戰時狀態中美國戲劇工作者的生活,他們在一個異常艱苦的環境中堅持排練、鼓勵民眾,讓我覺得特別應景——在疫情壓力尚存的今天,戲劇在有的人眼中可能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存在,但對我們而言,它是一種生活伴侶,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這就是戲劇存在的意義,也是對我們而言的價值。

阿慌:專業的戲劇運營團隊,可以改變一座城市的氣質
資深劇院運營策劃人、八年戲劇行業策劃運營經驗
進入這個行業其實挺偶然的。
我本身不是戲劇管理或者傳媒相關專業畢業的,但畢業之後卻選擇了戲劇專業,更偶然的是竟然被劇院錄取了,可以説這的確是一件挺抓馬的事情。但其中也有很多必然因素,比如我很喜歡看電影,對藝術行業有一種天然的興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加入劇院從事運營工作也是一種必然。
作為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我並沒有以賺錢為目的,在戲劇行業工作也並不是一份賺錢的差事,所以當時完全是用愛發電,也是興趣使然。現在回望八年前第一次進入劇院的時候,還能想起那份“看什麼都是新的”的好奇和新鮮感。

圖片來源:網絡
我的確特別熱愛這份工作,加上我剛畢業那幾年“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也有精力、有衝勁,當時劇院裏的所有演出我都會看,看完之後又會連夜寫推文,和觀眾分享現場圖片,不厭其煩的做推廣,也不會覺得加班、“996”是多痛苦的一件事兒,相反,我還挺樂在其中的。
這份工作需要做的內容有點兒雜,除了做宣傳,還得負責演出團隊的接洽等工作,甚至後台一些問題也需要搭把手,也因此讓我發現到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我所在的這座城市,大家普遍有一種心態,認為“面子”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兒,很多熟人熱衷找我索要演出票,可能對於他們而言,贈票要比自己買票更讓他們有“面子”吧。當然,這也與演出行業的特殊地位有關係,很多人可能認為“演出”不能算一種商品,我之前在書店、房地產商工作的時候並沒有人找我要房子、書籍,或許是因為大家覺得房子、圖書是實體存在,而戲劇是一種帶不走的虛體,所以把錢花在這上面有點不值得。
每次經歷這些事情,我都會暗戳戳地想,我們戲劇行業從業者已經夠難了,能不能給我們留口飯吃?

《戲劇新生活》丁一滕、劉曉邑等人在烏鎮的路邊賣唱
雖然從事戲劇行業工資不如其他行業,但我依舊喜歡這裏。
這個行業與我而言,有點兒“月亮和六便士”:我不想因為滿地的六便士,而忽略了頭上這顆叫“戲劇”的月亮。
不過好在,這幾年戲劇也越來越“出圈”了。
乘着“小眾藝術上綜藝”的風帆,有別於《聲入人心》《舞蹈風暴》《中國新説唱》這類紅到爆炸的綜藝節目,《戲劇新生活》讓觀眾瞭解到,“原來做舞台劇是這樣一種體驗!”
這同時也帶給演出運營人員一種更寬的思路——宣傳這些小眾劇目時,怎麼把自己的劇目推薦、展示給觀眾,有了這檔綜藝的呈現,我們後續也會開始更多形式的工作坊、劇院開放日活動。
另一方面,當我們再向觀眾提到“舞劇”、“話劇”的時候,觀眾會對這個概念更瞭解,這些藝術形式會像畫面一樣在他們頭腦裏閃過,方便我們更好做營銷,這些都是這檔綜藝帶給我們的紅利。
戲劇從業者也不必擔心《戲劇新生活》“出圈”帶來煩惱。

《戲劇新生活》劇照
有別於之前綜藝出圈源於對觀眾的“迎合”,《戲劇新生活》很“佛系”找來八位戲劇人做一些有關戲劇的嘗試,呈現的是戲劇人真實生活狀態。這個形式與之前的綜藝有了本質區別:這個劇不是為了尋求認同,而是展現戲劇人的生活狀態。
從這個角度來講,它也不太適合做粉絲運營角度的出圈。
而且這種“出圈”效果也無法與今年年初《你好李煥英》帶來的出圈效應相提並論,也就避免了不少為了“賺快錢”而進入這個行業的人對戲劇行當帶來“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有利於戲劇圈慢慢發酵,形成“長尾效應”。
從事戲劇行業的確是一個細水長流的事兒。
這些年,我也真的感受到了戲劇帶給一座城市和這座城市居民的改變。
我剛來的時候,劇院附近是一片荒蕪,進入這裏要先經過村落,這個地段可想而知,但我們通過努力,包括做一系列形式活動,包括在熱門商圈的快閃、藝術工作坊和其他形式的藝術形式,漸漸感覺到這座被稱為“戲劇荒漠”的城市不斷復甦,人們的戲劇熱情不斷高漲,甚至有了劇院自己的粉絲。
劇院周邊的環境也越來越好,這是在我剛開始工作時難以想象的,也真的讓我感覺到,一個專業的戲劇運營團隊,真的可以改變一座城市的氣質。
去年,疫情給戲劇行業帶來很大的損失,但其實也有不少劇院探索了線上新模式。
比如廣州大劇院就做了雲放映,上海文廣更是和天貓合作,把戲劇角色和天貓商品融合,這些活動甚至超過了演出帶來的效益。
我覺得,戲劇人能在疫情期間激流勇進,開拓出一些商業模式和邏輯,對我們戲劇從業者來講也有很深的啓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