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血《頂樓》告訴我們,可以來點“灰”的女性角色了_風聞
娱乐产业-娱乐产业官方账号-带你了解行业的“热点”“盲点”“痛点”2021-03-22 1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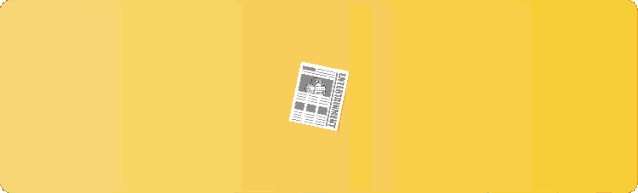
作者 / 順玉
昨晚微博熱搜的首位:“露娜沒死”。

你可能對露娜這個名字不熟悉,但從去年年底至今,應該感受過神級狗血韓劇《頂樓》引發的熱烈討論。
狗血到令人髮指的《頂樓》,除了靠不停反轉的狗血吸引眼球,還貢獻了極為精彩的“惡女”角色。
交叉出軌的千瑞真、在被害者和施害者之間切換的吳允熙、校園暴力瘋批魔女朱錫京、神經兮兮情緒極其不穩定的夏恩星以及嬌慣但悔改的劉珍妮等等。

從故事設定的角度,第一季的《頂樓》還算有邏輯可言,可到了第二季整個劇情故事,像蚊帳一樣,四處都是漏洞。卻還是硬靠着難以企及的狗血和突出的人設,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要給編劇“順玉”寄刀片的好奇觀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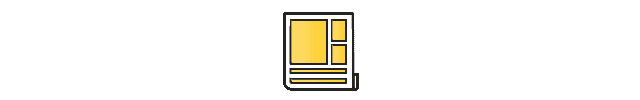
國產“惡”女的困局——工具人、污名化
先不提韓劇是否在狗血中呈現出了日漸頹敗的趨勢,或者對國產劇相比,其成熟工業流程是否還具備顯著的優勢,相比國產劇那些關於“女主角設定不能愛過兩個男人”的傳言調侃,《頂樓》全員惡人的設定,確實足夠吸引眼球。
一方面是輿論環境對傻白甜的厭煩;另一方面則類似於角色補充,帶來的視覺新鮮感,國產立體“惡”女人設的稀缺,讓易怒且利益至上的惡女千瑞真,一下就抓住了觀眾的視線。

雖然這兩年,女性題材與女性角色不斷迭代,受眾的確不再只是被動的消費者,也成為了大眾文化的生產者,他們通過互聯網得以參與更廣的議題討論,積極利用輿論場,試圖改變既定的敍事形象,挑戰着傳統文本中的刻板形象。
但就女性角色形象的整體豐富度而言,國產劇依然十分單一,其中關於“惡”女的刻畫,甚至是不斷在退化的。
曾輝煌一時的大女主,最大的作用也不過是靠被男人爭搶的戀愛主角身份獲得上升渠道的偽大女主。在這種框架下,惡女設定都是什麼樣子的?
——推動愛情線的工具人。
最為典型的就是大喊大叫,歇斯底里彷彿失了智的女二。最新的代表角色——《錦心似玉》喬蓮房(何泓姍)。

這個瞪大眼睛,智商不高,露出全部瞳孔彷彿隨時準備要跟眼白分家的角色,配合着恨不得把“執掌中饋”四個字題在屏幕每一幀的台詞和畫面,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某一段時間裏國產影視劇“惡”女角色的縮影——嘰嘰喳喳,腦子彷彿從未開封過。
大女主的設定,如今基本失去了市場號召力,以此前大家對《上陽賦》的吐槽為例,除了不合時宜的扮嫩,本質上是對行大女主之名的戀愛故事的厭煩。可如今滿屏關於獨立女性的塑造,卻又淪落為了扁平的“有錢有顏等於成功女性”的模式化循環。
“惡”女也直接進入了承擔觀眾炮火的定向靶子,貼上白蓮花、綠茶的標籤,拿下熱搜就行。
——白蓮花腹黑型:爾晴。
——綠茶無辜型:林有有。
爾晴類浣碧,卻遠不沒有浣碧的立體,咬牙切齒從頭吵到尾,彷彿只是為了送上臉讓女主打一巴掌,以襯托瓔珞的特別。

而林有有這個角色,年輕、幼態、無辜、踏着道德破壞他人家庭、情緒化特徵突出、污名化別人的糟糠之妻等等種種行為與設定,幾乎是所有類似角色的模版整和,再配合着那段時間網紅屆八卦食用,將綠茶論調頂到了巔峯。
但也很遺憾,林有有除了捱罵,基本沒有承擔任何值得分析的作用。
《三十而已》的設定是值得肯定的,通過三個女性來構建成一個社羣,傳達出不同社會身份的女性在婚姻、愛情與事業裏遇到的現實問題。但整體而言,角色的扁平與後期輿論的走向,與其説是描繪羣像,更像是精準踩點熱搜詞條,本身並沒能帶來更鮮活的建設。
這不禁讓人想起此前戴錦華在造就Talk的演講中關於 “為什麼流行女性向作品中,女性卻結構性缺席其中?”一問中提及的耽美文學盛行與厭女情緒的反思:
婦女解放運動200年,女性仍然沒有創造自己社會性的模版,一旦進入社會性表述的時候,要麼就是花木蘭式處境,要麼她就必須在她的社會表達當中,退回到女性的模版或者女性的規範之下。
“惡”女形象的單薄和匱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大眾媒介中女性美學建構的缺失和偏見。從過去傻白甜到現在的半真半假獨立女性之間,需要一朵足夠立體的“惡”之花,來一點灰色。而不單純地複製粘貼樊勝美她媽媽和林有有。
想起不久前《流金歲月》在改編上對朱鎖鎖整個人設改動上的刪減。

原著當中,這個角色獨自在燈紅酒綠中打拼,擅以朱顏換鑽石;而影視化在改編上則儘可能的弱化了朱鎖鎖對物質的強烈追求。就連“李先生”的“包養”,也變成了朱鎖鎖與葉謹言“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隱忍虐戀。
邏輯上也圓得過去,説不上多麼糟糕,但也的確單薄又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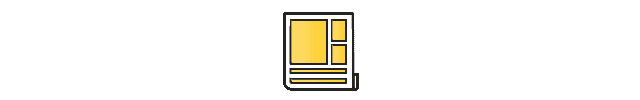
出彩的“惡”女刻畫,我們曾有過的
娛sir印象深刻地記得一部女性犯罪劇,名叫《紅蜘蛛》,並至今仍然認為,這部劇具有超前的女性意識書寫。

通過犯罪刑偵題材將社會議題放置其中,這是韓國電影鍾情且得到了很大程度肯定的操作方式。而事實上,不提製作工業成熟度,國產早期的犯罪劇集在這一方面,出類拔萃地作品並不少。
以女性犯罪為主題的《紅蜘蛛》,在女性犯罪心理結合時代背景與現實的刻畫上,是即便今日再打開,都依然可以讓人驚呼“大膽”的程度,打破了特定虛構角色的刻板印象。20集的篇幅,10個故事,都改編自真實犯罪案件,而每個案件的結尾,都會附上一段對女罪犯的採訪,以此警示觀眾。
當時第一部當中,取材的10個案件裏,在逃的罪犯只有一個——勞榮枝,也已經於2019年被捕。
這部透着幾分軟色情氣息的偽紀實犯罪劇,從故事選材、海報,甚至劇中角色的打扮穿着,都非常具有先鋒性。要知道,2020年了,熱依扎還因為穿吊帶被“蕩婦羞辱”,可打開2000年的《紅蜘蛛》,主角們幾乎全員吊帶,花式展示one piece的時尚魅力。
這些美麗、時髦的女性形象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關鍵所在,而在這過程中,也展現出各不相同的個性和命運,並藉此揭示社會問題和人倫道德。

當你還在為社會主義兄弟情和美好的雙女主友誼感嘆的時候,《紅蜘蛛》已經拍過了喋血百合的故事,甚至還有吻戲。
在《紅蜘蛛3》之《危險愛情》篇當中,沈丹妮暗戀發小上官燕,併發起追求,上官燕的男友(陸小峯)得知此事,以此為由對上官燕百般羞辱還實施家暴,沈丹妮為愛暴走,聯合暗戀自己的表哥陳斌對陸小峯痛下殺手。
之後,沈丹妮和上官燕一路逃亡,化身末路狂花,最後被警方在一家青年旅社裏抓獲,主犯沈丹妮則因殺人被判死刑。

不提這在下線邊緣瘋狂蹦迪的禁忌之戀,《紅蜘蛛》當中的犯罪女性角色,與東野圭吾筆下的“惡女”形象十分相似——都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剖析了女性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危機。比風靡一時的美劇《Why women kill》,絲毫不弱。
這些女性罪犯,或是文化水平有限,家庭困難,一步錯步步錯,或是被害之後破罐子破摔的可憐人,也有殺敵一千自損一千的復仇悲劇。
《紅蜘蛛》的大部分故事,都展示了罪犯從施害者深入發掘出其曾經受害者身份的思考。故事與角色本身,並沒有站在性別、職業與出身,站在道德的至高之巔刻意進行刻板的污名化,反而更多的帶了悲憫與無奈的反思。
坐枱小姐陳蓮紅,夥同同伴殺害了一個有錢的老闆被捕後,向鏡頭暴露了自己因何對人懷有深深的恨意——被父親家暴,逃出家門卻又遭到了強姦。她説:夜裏走在路上,身上有血,卻沒有一個人上前去問問她,發生了?怎麼了?
施暴者被捕之後的暢快,夾雜着人生悲劇的無奈情緒,主題一下就立起來了。
反觀當下,女性“惡”一點的角色,要麼被愛情線包裹成叫嚷咋呼的無腦女二;要麼就是就是毫無背景交代的純粹惡意刻畫,《安家》裏,女主角吸血的媽媽,和讓人無法忘懷的樊勝美媽媽均是此類。

雖然也曾有過明明是吃人的老妖怪卻長着一張蘿莉臉,殺人如麻卻因為愛吃糖經常抱怨牙疼的嶽綺羅。
但整體的“惡”女退化,可太明顯了。
同時,輿論空間對“惡”女角色的反應,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這個類型的生存空間。直白來講,在張月因為林有有這一角色被滿屏辱罵之前,飾演安陵容的陶昕然、魏嬿婉的扮演者李純、凌玲的扮演者吳越等等,都曾因為角色設定遭遇過謾罵和侮辱。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大青衣類型的女演員幾乎沉寂,幼態佔據主流,惡與灰色的角色,就更沒人願意探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