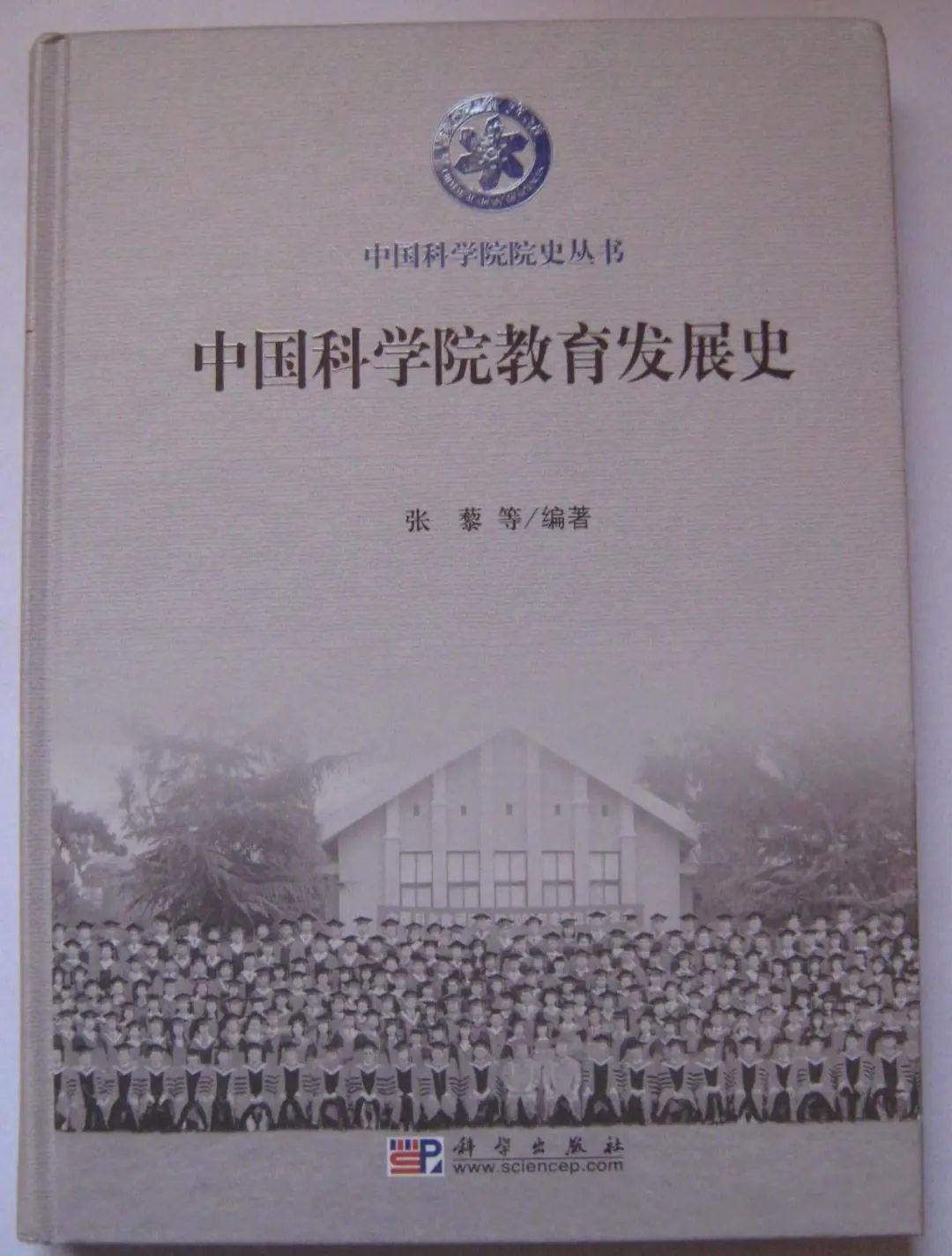中國科學院內的高等教育——餘翔林教授訪談錄 | 熊衞民訪談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03-26 13:52
中國科學院不但是中國最重要的科研機構之一,還是一個重要的高等教育機構——事實上,它是全國最大的培養研究生的法人單位。它不但能培養學生,還能頒發學位,這在世界各國的科學院系統中也是很獨特的。可這些事實不但在國際上鮮為人知,就算是在國內,知道的人也不多。中國科學院做過哪些教育工作,到底是如何培養高級人才的,和大學相比有哪些優勝或不足之處?這是值得廣大考生和教育史研究者知曉的。
圖1 中國科學院教育史研究座談會(2008年3月13日攝於中國科學院院部)
為撰寫中國科學院教育史,2008-2009年,張藜教授(圖1後排右2)、筆者(後排右3)和其他一些同事召開了幾次專題座談會,並在會後對中國科學院人事教育局及其前身的多位老幹部,如羅偉、王漢石、馬先一(前排右1)、任知恕(前排右4)、餘翔林(前排右5)等作了系列訪談。在本訪談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前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教育局前局長餘翔林教授介紹了他的教育理念,尤其是他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科學院的教育工作的認識。相比教育部所屬高校的龐大體量,中國科學院的高等教育規模要小得多。但船小好調頭,小也有小的好處。中國科學院過去是,現在仍然可以是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先驅。
受訪人:餘翔林教授(以下簡稱餘)
訪談人:熊衞民(以下簡稱熊)
訪談時間:2008年6月24日
訪談地點:中國科學院離退休幹部局
受訪人簡介:
餘翔林(1940-),江蘇江陰人。1959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1964年畢業留校,長期從事電磁場理論、電磁輻射及毫米波技術的研究,特別是在毫米波引信雷達及導彈末端制導實驗系統的研究中,獲得過一系列重大成果,1991年被國家科委聘為國家863通信高技術戰略研究專家組成員。1984年後歷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研處長、副教務長、副校長、黨委書記等職,1998-2001年先後任中國科學院教育局、人事教育局局長。
圖2 餘翔林教授(熊衞民2008年3月13日攝於中國科學院院部)
熊:聽説做中國科學院教育局局長之前,您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工作了很長的時間。請簡要介紹一下您的經歷。
餘:我於1959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無線電系,1964年畢業留校,接着下鄉參加“四清”運動,兩年多之後,“文革”開始,1969-1970年時,科大又下遷,直到 1972年招工農兵大學生時,我和其他一些同事才回到教研室工作。也就是説,我們被耽誤了七、八年時間。雖然在“文革”期間,我並沒有完全放棄專業,數學、物理等方面的書還在看,但為了教學生,我還是又花了一兩年時間,把大學所有的數學、物理和英語課程重新複習了一遍。
我先後在教研室做副主任、支部書記,一方面教學,一方面搞科學研究,在毫米波技術上做出了一些成果。1984年時,開始擔任科大科研處處長。後來,我又擔任了副教務長、教務長、副校長、黨委書記等職,1998年時被調到院裏。中國科大的辦學理念
熊:您主管教育多年,不知持有何種教育理念?
餘:科大在1958年創辦之時,就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思想——理工結合,而不是理工分離。建國以後,尤其是院系調整之後,在蘇聯的影響下,中國大學的理科和工科是分離的,如清華大學的理科被調整到北大去,北京大學的工科都被調整到清華去,而科大則把理和工結合到了一起。與此同時,科大還強調科學和技術的結合。不僅要有科學,還要有技術,特別是新興、邊緣、交叉的科學技術,辦了很多這樣的系。科大還強調教學和研究的結合,教師要在科學研究的第一線。這與過去的大學也是有區別的。過去的高校教師以教書為主,很少開展科學研究,而我們是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科學院”)辦的大學,很注重科研。理工結合、科學和技術結合、教學和研究結合,這是科大的特色。所以,這所大學一開始辦就具有非常強的時代性,既反映了國家的需求、社會的需求,又體現了老一輩科學家、革命家對教育的深刻理解。
那時候,給我們上課的都是科學上的大家,目的是打好我們的基礎。另外,我們的畢業論文是在科學院的研究所做的。比如,我的論文是在電子所做的,曾用中國最早的電子計算機來幫助計算數據。後來我想,全國那麼多學生做論文,有幾個人有我這樣幸運?在1964年就能使用最先進的計算機,只有科大才有這種可能。這充分體現了科大的特色:基礎紮實,在科學研究的第一線來培養,教學和研究緊密的結合。
我在學校工作時,不管是當教務長還是當副校長,基本上是傳承這種傳統。當然也要不斷發展。那時特別重視交叉學科,我協助谷超豪校長辦了非線性科學的試點班。這是新興學科,沒有學位授予權,學生來自數學、物理、生物等學科的不同專業,後來做論文時,又回到原來的學科去。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嘗試。另外,我還很重視全面素質的培養。早期,我們國家曾流行“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説法。這個概念不全。後來強調實踐,不僅要會讀書,還要善動手。可光會讀書,會做實驗,不瞭解社會、國情、歷史等也不行,沒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思維狹窄、境界低下,那也不行。還必須有很好的文化素質、很好的道德素養、寬廣的專業學科知識、健壯的身體、健全的心理素質。教育的功利性不能否定,但在這些東西之上,我們教育工作者還要追求對人的全面培養。
在逆境中也基本能按教育規律辦學
熊:1958年“教育革命”時,科大辦過工廠、農場嗎?
餘:科大辦過工廠,我有印象,但規模很小。影響大的是“大鍊鋼鐵”,可那時我還沒來,我來之後,鬧騰得比較厲害的是“超聲波運動”,説超聲波可以加快化學反應,可以煮飯等,到處做試驗。但這個運動並沒有持續太長的時間,我們仍把主要精力投在學習上,我們的學習任務非常重。我對這些運動的印象不深,説明它們對我們影響不是特別大。
熊:它們對北京大學的影響很大。我訪問過該校的一些老學生,他們説1957-1960年這幾年,天天搞政治運動、搞勞動,沒學到什麼東西。
餘:北大、清華都是中央直接過問的重點院校。
熊:科大是在“教育革命”的背景下創辦的,那時候“批白專”、“拔白旗”,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您剛才提到的幾個“結合”和注重打基礎等,既是1950年代初一些改革措施的反動,又違背“大躍進”時的潮流。現在看來它們當然很正確,但令我困惑的是,為什麼科大當時能做到這一點?
餘:科大確實有很強的傳統。1970年代我們招工農兵學員時,社會上也正在搞“教育革命”。當時我是教研室副主任,管教學。學員們有的是老高中,有的初中還沒畢業,又都在勞動第一線幹了那麼多年,科學文化基礎普遍很差,怎麼教?當時有個爭論。無線電、微波技術涉及麥克斯韋方程,它有積分形式和微分形式。積分形式只要有最基本的微積分基礎就可以學了,而教到微分形式,則還要學向量分析、特殊函數、數學物理方程、場論等,要難很多。別的高校都只教到積分形式,而我們幾個年輕教師和兩個從美國回來的老教授提出,為了讓學員們打好基礎,無論多困難,都要教他們微分形式。最後我們真的咬牙教了下來。我們絕不搞當時流行的“以產品帶教學”那一套,因為簡單地以一個產品來代替整個的教學過程,肯定會很失敗的,絕對培養不出人才來。我們還是堅持科大的傳統,基礎寬、厚、實,專業精、新、活,強調必須把最基本的知識教給學生。我們培養出來的一些工農兵學員還是不錯的,其中有一個正在擔任上海光機所的副所長,當然他後來又去唸了博士學位。
為什麼科大堅持這樣的傳統呢?因為這是老一輩科學家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此外,科大的創辦還有“向科學進軍”的背景。1956年,我們國家制訂了十二年規劃,提出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於1958年創立科大。在開學典禮上,郭沫若校長説:我們現在開學了,可頭上飛的還是蘇聯的衞星。這使我們感到一種緊迫感。創辦科大的那些科學家們深切瞭解,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絕不能靠説大話,只能靠紮紮實實打基礎。那些老前輩是真正懂教育的。
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吳有訓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們當然是懂教育的。可他們並未分工管理科大。至於別的前來任課的科學家,對於辦校方針,他們能有很大的發言權嗎?那個時候特別強調黨的領導……
餘:科大當時的校長是由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兼的,黨委書記早期為鬱文,實際長期主管科大工作的是劉達。他畢業於北京大學[1],對教育有很深的理解,既貫徹中央的精神,又非常尊重科學家。鬱文也是這樣。他們對科學家都非常尊重。研究所內的高等教育
熊:現在高校實行的仍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科學院的各研究所是不是也類似?黨委書記是不是各所的教育負責人?
餘:研究所實行所長負責制,有一位副所長分工管教育,書記一般不太參與。科學院總的體制是所長負責制,與高等院校的不一樣。高校曾經做過校長負責制試點,但很快就取消了。
熊:研究所在教育方面自主性大不大?
餘:在成立科學院研究生院以前,各所有招生權,並由所學位委員會獨立授予學位,只是有一段時間集中到研究生院去上學位課,其自主權是比較大。成立科學院研究生院後,研究所不再具備獨立的招生權和學位授予權,招生、學位授予和教育管理都被統一到研究生院。統一後也有好處,在向國家爭取資源,要求增加招生指標、增多教育經費、增加學位點時,更方便一點。
熊:除科大外,科學院每年還招多少學生?
餘:我任局長時科學院每年招收5000多位研究生,現在擴大了招生規模,每年招收的人數超過了1萬,而在科學院系統內,能帶研究生的副研以上人員有7000多人,平均起來,現在每位導師每年也只帶1.5位學生。相比較而言,高校教師帶的研究生通常要多得多,而其課題和科研經費要少得多,所以,一些高校的研究生是讀書讀出來的,而不是通過科學研究鍛煉出來的。所以,不同來源的研究生質量差異很大。當然,一些好的高校和好的教師不是這樣的。普遍來講,擴招帶來了很多問題。
熊:教育部對科學院各所管得多不多?
餘:現在他們不怎麼管了。過去其實也管得少,只是控制招生指標。他們並不給我們撥教育經費,課程安排之類也就不管。我們跟大學有很大區別,他們受教育部有關制度、政策的影響特別大,自由度比較小。所以,路(甬祥)院長説,在研究生教育這一塊,我們科學院有很大的自主性,可以做很多探索。他很希望我們有所創新,摸索出一些新經驗出來。
熊:那麼,科學院是否利用這個優勢,培養出了更多的特別優秀的人才?
餘:在培養優秀科研人才方面,科學院可能比高校要略強一點。畢竟各研究所都是以研究為主的機構,受教育行政部門的束縛小一點,國際交往較多,跟國際科學研究主流結合得更緊密一點。但二者也有一些共同的不足之處,比如,我們還受“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類老傳統的影響,對“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鼓勵不夠。很少有研究生獨立選題,選與老師的方向、領域不一致的,與老師的理念不一致的題的尤其少。所以,我們這兒的博士論文,在創新性方面依然比較弱。這跟應試教育也有很大的關係,從小學到中學,我們的學生所接受的一直都是應試教育,甚至到大學、研究生階段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這當然會非常影響培養質量。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學生的功利性也很強。他們讀研究生,很多並不是因為對研究有興趣,而只是為了找到一個好點的工作,謀得更好的就業條件和工作待遇。他們對這些因素考慮得多,對學術考慮得少,而能在學術上真正有所成就的,是那些把科學真理作為終身追求的人。不管是在科學院還是在高校,真正獻身科學的人還是少數。
熊:您的意思是説,因為生源不佳,受一些不良傳統的影響,再加上功利考慮太多,科學院在培養創造性的人才方面,依然存在較大的欠缺?
餘:當然科學院還有很多優秀典型的,前面説的只是普遍現象,特例哪裏都有,大學也有。
熊:民國時期,兵荒馬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非常少,能夠進一步出國深造的更是少之又少,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裏,仍培養出了陳省身、華羅庚、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錢學森等一批世界級的科學家。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快60年了,改革開放也已進行了30年,上過大學的人非常多,出國留學的更是超過百萬,可其中又有幾位能入得了世界一流科學家行列?從這個角度看,科學院的研究生教育還是不夠成功的。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餘:你説的都是事實。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國家的教育太注重功利。以前是政治,改革開放後是經濟,它們對教育的衝擊太大。西方雖然也是市場經濟,但有些科學家的精神追求仍然很高,而我們現在一些科學家及大量年輕人主要是追求物質,高尚的情操非常缺乏,人生的價值大大降低,這是很致命的。
熊:倡導以啓迪智慧、發揮潛能為主的素質教育已經很多年,可現在的學生從小到大所接受的依然是高強度填鴨為主的應試教育,放學回家之後,還要接受各種家教、培訓,好苗子很容易就被毀掉了。為什麼那些人人都説不好的做法偏偏能長期盛行?
餘:主要因為教育是稀缺資源,重點小學、中學、大學,每一個層次都是稀缺資源,存在非常激烈的競爭,而社會所提供的上升渠道又非常少,只能走這樣的獨木橋。像其他有些國家,職業教育很發達,許多人去讀那些學校,出來之後,待遇不一定比教授低,那些能解決實際問題的高級技師,在社會上很受尊重。而我們的有關政策沒有配套,工人的待遇很低,被人看不起,那些農民工、打工仔,受剝削最重,待遇最低,完全得不到社會的尊重。這就使得人們不願意去當藍領工人,而沒受過職業培訓的普通高中畢業生若上不了大學,是很痛苦的,並且令整個家庭都很痛苦。只有國家逐步提高工人、農民的待遇,才能改善教育的結構,使職業中專、職業高中等真正發展起來,繼而使素質教育真正落到實處,大量優秀的高端人才得以培養出來。這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
熊:不好的根基、不良的傳統、太強的功利性,除了這些不利的外在因素,各研究所自身在教育方面還有哪些不足?
餘:在教育方面,各研究所的發展很不平衡。有的做得非常好,如北京的物理所、化學所,上海的有機化學所,瀋陽的金屬所,合肥的固體物理研究所,等等,他們有成套的經驗,培養的研究生有很多都取得了好的成就。為什麼能這樣呢?他們有很好的人才培養理念和傳統。英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有一個非常自豪的地方: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具有一般智力的人培養成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在這個實驗室,得諾貝爾獎的太多了。為什麼呢?他們重視打好基礎,重視學科交叉,有良好的學術氛圍,經常組織學術討論,而且老師對學生非常尊重,鼓勵他們創造性的提出問題、探索問題,給他們指引前進的方向。我們一些好的研究所也有類似的傳統,能夠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所以比較成功。而有一些研究所則不太成功,他們的教育理念比較陳舊,學生往往只是讀幾本書,看幾篇文獻,做做導師現有的課題,寫篇論文,不行的話老師幫忙改改,然後再畢業找個工作。
科學院研究生院的高等教育
熊:1998年您主持教育局的工作後,做了哪些重要事情?
餘:第一件是幫助科大進入“985”工程。1998年5月4日,江澤民在參加北京大學100週年校慶時提出,我們國家應當建設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然後教育部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開始搞“985”工程。我們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終使得科大成為了第一批院校(共九所)之一。爭取到了國家3個億,安徽省3個億,科學院3個億,一共9個億的支持,幫助解決了科大的一些問題。
第二件是更名組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我寫過一篇專門的回憶文章[2]。這件事情還是很有意義的[3]。因為全世界的研究生,幾乎都是在大學裏授予學位,只有我們和日本開創了科學研究機構獨立招生、授予學位的先例。這件事情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像俄羅斯科學院、德國馬普學會、法國科學院,都很羨慕我們——他們可以培養研究生,但授學位必須去大學。
第三件是組建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將5個單位重新組建成1個法人單位。這件事情,院裏交給人教局負責。路院長曾經想把(科學)島上的研究所跟科大合併起來。島上問:是研究院辦大學,還是大學辦研究院?科大問:是大學辦研究院,還是研究院辦大學?結果他們都不買帳,最後院裏只好下決心先將島上的單位合起來。
還有一件事,就是把人事局和教育局兩個局合併起來成立人事教育局,這裏面也有一些麻煩事,主要是幹部的安排,做起來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熊:您當三年局長,幹成這麼多大事,很不簡單。更名組建研究生院後,在招生方面……
餘:招生時我們報計劃,交教育部審批,建立研究生院後,招生人數增加了很多,但審批起來還是很嚴格,不是説你自己花錢培養就不審批了。
以前科學院各所都有獨立的學位授予權,教育部直接把招生指標(每個所幾十人)分到各個研究所,院教育局只起一個統計的作用。這些分散的單位想增加指標,可上報到教育部去時,經常得不到批准。我任局長時,曾陪白春禮副院長去教育部找管研究生招生的某位副部長,請他們批。但他們不太同意科學院擴招,主要是因為基本理念不對——他們認為,研究機構招研究生,目的只在於更替自身人才,而為社會培養人才,是教育部各大學的事。實際上,現在大學在培養人才的同時也開展科學研究,科學院在開展研究的同時也培養人才。兩大方面軍嘛,應充分發揮各自的積極性。
我們成立科學院研究生院之後,調整了各所的學位授予權,集中到研究生院來。這就把資源全部集中了,我們因此變成了全國最大的培養研究生的法人單位:擁有幾千位導師,一年授予幾千個博士學位(佔全國理學博士的1/3)。力量一強,跟教育部去談時,他們就十分重視了。
熊:在成立研究生院之前,科學院的畢業生一般去什麼地方?是大部分都留在研究所嗎?
餘:不,除了少數留所外,大部分都不留所。他們之中,一部分去了高校、其他研究機構、企業等,還有相當一部分出國。過去60-70%以上不留所,現在90%以上不留所。我們現在每年招生1萬多人,畢業7、8千人,其中兩三千在就讀學位期間到國外去了,各所留用的加起來不到1千人。
熊:1950、1960年代科學院的畢業生去向如何?
餘:那時候研究生極少,“文革”爆發後,多數下鄉去了。科大於1963年有了第一批畢業生,有相當多被分到科學院工作,還有一部分留校,從1963年到1965年,每年留100人,三年共留了300人。1980年代初,科學院每年大約接收畢業生2000人,其中來自科大的約200人,佔10%。到1980年代之後,科學院新進人員中,來自科大的只有5%左右。所以中國科學院、科大培養人才都是面向全國的,如果僅為自己培養人才,根本不需要現在這麼大的規模。
圖3 《中國科學院教育發展史》書影(科學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註釋
[1] 劉達(1911-1994)於1935年考入輔仁大學,因為參加一二·九運動,在入學當年就被開除了。次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了職業革命家。1948年8月以來,他先後擔任東北農學院、東北林學院、黑龍江大學院長兼黨委書記,對領導高等教育很有經驗。1963年5月,他受調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黨委書記。1977-1983年,他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或革委會主任)。
[2] 餘翔林.對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更名組建的回憶與思考.2018-10-1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24937
[3] 任春曉,徐曉慧等.一位重要親歷者眼中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更名——餘翔林教授訪談錄.2021-01-25.https://mp.weixin.qq.com/s/3xoXe8f0qOXQUUJ13DBU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