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和説唱新世代的施鑫文月聊了聊,《丁丁貓兒》底是怎麼寫出來的_風聞
跳海大院-跳海大院官方账号-2021-04-29 13:23

許多人認識施鑫文月(SHI),得益於去年那檔口碑極佳的hiphop節目《説唱新世代》:
作為無名新人,SHI並沒有像理想劇本中的“黑馬”那樣脱穎而出,節目剛進行一半他就被莫名淘汰,但卻因為一首怪誕單曲《丁丁貓兒》而成名,MV和現場視頻在B站收穫了總計約200w的播放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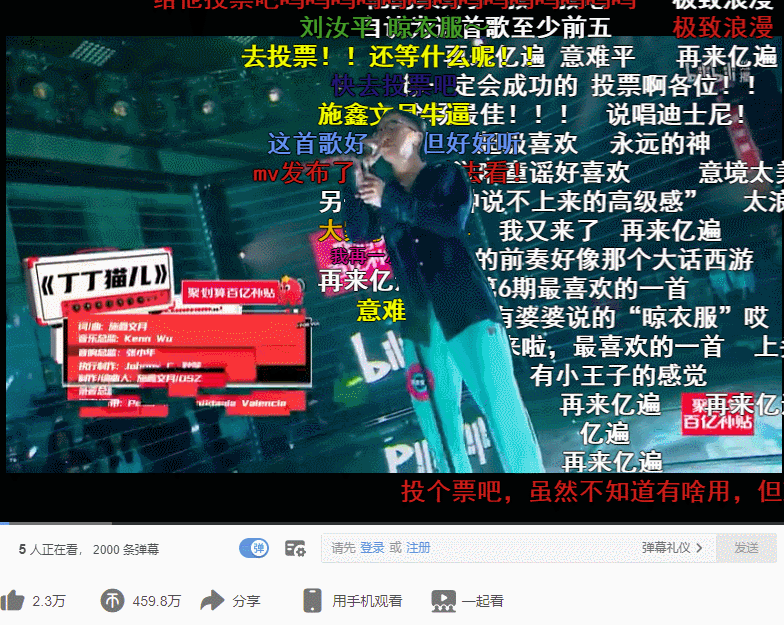
當其他選手都在為peace、love、社會議題真誠rap時,SHI則把自己比作成了蜻蜓背上的一個小孩,一會在成都蘭桂坊裏聞桂花香,一會則又飛去了加州錄音室裏睡午覺,最後還沒醒過來,就被帶去了月球和嫦娥約會,還不忘在蜻蜓翅膀上提前掛了甘蔗和臘肉當作給玉兔的見面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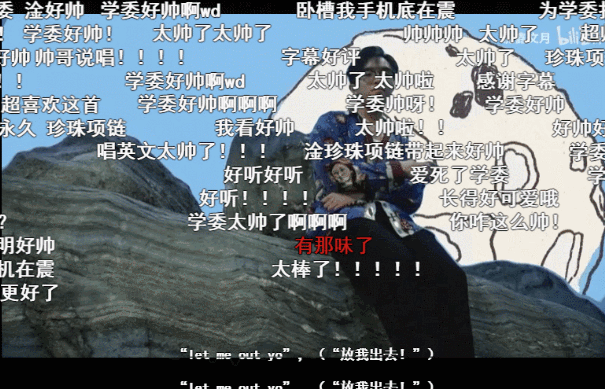
Rich Brian高情商地點評SHI“十分有戲劇性”,旁邊的海爾兄弟和熱狗則似乎只希望能快點淘汰掉這個幼稚鬼,直言“不清楚這到底是哪種音樂範疇”、“這就是騷(瞎)整。”
但觀眾們顯然對這段點評並不買賬。在第六期播出後,因為淘汰了SHI和其他兩位選手過於令人意難平,這檔原本口碑9.7分綜藝在B站評分直線下降到了9.4分。
在現場,大眾評審團甚至直接調侃熱狗老了,不喜歡丁丁貓兒不是音樂的問題,而是“新世代的問題”
直到最後公佈唯一的晉級名額時,為了製造足夠的“氛圍”好促使選手“情感自然流露”,導演組還故意安排17名待定選手一起上台,再讓導師按照得票倒數挨個點名“淘汰”,無限拉長選手們等待裁決時的焦慮時刻。
面對最後四位留在台上選手,特寫鏡頭本希望捕捉到SHI“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時的模樣——
結果馬思唯剛唸完他名字,他就掉頭想立刻解脱於此,半秒後他才猛然記起台下還有觀眾,回去接過麥,但只説了一句話:“外婆,我做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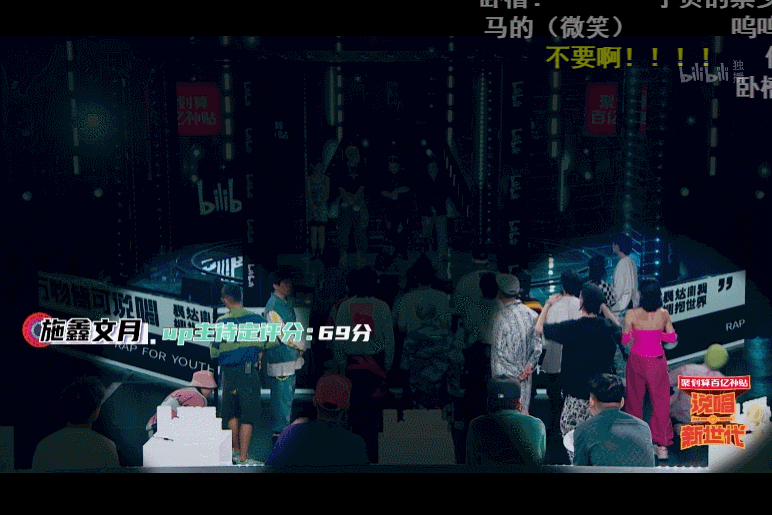
在粉絲畫像裏,SHI是標準精英,他似乎天生就有不在乎節目輸贏的底氣:
SHI的父親是作曲家,母親是音樂系教授,本人既是“蘿莉臉腹肌猛男”,又是“穿搭教主和學霸本尊”,粉絲稱他是學習委員,英語好到“能區分authenticity和know-it-all的區別,聽他英文rap像是做文化課題研究。”
但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卻被眼前一個彷佛盜版的SHI給幹蒙了。

打來成都前開始,這哥們就反覆給我發消息,要請我吃當地一家叫“順姐”的館子,非常神秘,甚至提前囑咐我中午少吃點,要給晚上的大餐留點肚子。
當時我在內心嗤笑,這有什麼神秘的,順姐嘛,一聽肯定就是本地人才知道的火鍋店。
結果落地後,當我還在猶豫要吃紅湯還是鴛鴦鍋時,他卻把我拐進了一家街角快餐店裏。我四處尋找順姐的身影,卻只看見了一個禿瓢大叔,他面前的快餐車上寫着“順姐”二字。

那一刻,我看着SHI,想到自己因為中午沒吃飽、下午在路上餓到低血糖都捨不得吃飛機餐的經歷,一時無語凝噎。
結果等我真餓急眼一口氣點了四個菜時,SHI卻又在旁邊瞪大了雙眼,嘴唇微微張開,被淘汰時都沒見他這麼慌:
“你居然…吃這麼多嗎?”
明白,高情商的我定然不會讓採訪對象為難,於是立刻告訴SHI,“沒事,我自己付錢,公司報銷。”
幾乎是一瞬間,他表情又恢復了管理。我問他要一起吃嗎,他居然説自己已經吃過了——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順姐對他來説已經是“一週才能吃一次的美食”,平時他為了維持身材,只能頓頓吃一塊17元的三明治。另外,由於不願意再花家裏錢,只好對自己摳一點。

包括買鍋巴的時候,他一次也只捨得買一兩塊錢
不過在另一方面,SHI花錢卻顯得“大手大腳”,比如在拍MV這件事上,為了新專輯他一口氣就拍了四支。
為了省錢拍MV,不惜放棄美食,我調侃他,“你這生活簡直比苦行僧還慘。”
結果我剛調侃完,他真來了句:“對,你怎麼知道我對佛教感興趣?”
原來,他不但對佛教感興趣,而且還真的“很相信因果報應”,這麼多年來每週都堅持要給水滴籌捐錢。
我曾經以為在節目上,面對導師們的不屑是SHI叛逆的表現。
但如今路燈打在SHI身上,卻讓我產生了他在散發佛光的錯覺,那一瞬間,我悟了,他那哪裏是叛逆,根本是真佛系。

苦行僧一般都有着一個遠大理想,SHI也有,他的夢想是復興巴蜀地區hiphop:
“我要像kanye west復興黑人靈魂樂一樣復興巴蜀説唱”,讓川普成為全球流行的rap語言。”
復興巴蜀説唱?我本想忍不住問他“那你知道CDC嗎”,沒想到之後再聊天,SHI無意間竟説:
“我做音樂時唯一的目標和對手就是我自己,你別笑,但我以前真的對國內説唱圈不太瞭解。”
半信半疑中,我打算跟他開個玩笑,告訴她范曉萱是成都最屌的女rapper。沒想到SHI居然放了真,拿起手機開始找范曉萱的歌。
原來,印象中那個學委,在某些方面卻是白紙一張。而這與他的人生經歷直接關聯。

SHI選擇做音樂可以説是一場意外。
儘管爸媽都是音樂從業者,但SHI從高中到大學都主動選擇了物流專業,理由是他“喜歡有邏輯的東西,可以在不規律中找到規律,保證事物儘可能被自己掌控”。
直到今天,他聊到自己對音樂的理解,都離不開他學習物流專業時的思路:
“比如説歌是一個產品,那它的編曲、混音母帶,包括配器的選擇其實都是一個做產品的過程。然後封面和後期,就是包裝。而產品做完就需要一些marketing…”

初中畢業,SHI就已經盤算好了要出國學習物流專業。還是未成年的他對寄宿家庭萬分期待:“我以為會和電影裏一樣,會有一個國外“媽媽”。每天早上她給你親手倒上牛奶麥片,然後家裏幾個小孩一起蹦蹦跳跳上學,氛圍非常陽光包容。”
結果到了後,“媽媽”卻連洗衣機都不讓SHI用,還得給她親生兒子刷馬桶。後來他又換了個家庭,以為擺脱了魔窟,結果“繼母”更狠,只許他三天洗一回澡,上廁所都不能超過五分鐘,否則會像《貓和老鼠》裏女主人那樣瘋狂砸門,把SHI一路從廁所攆去雪地罰站。後來SHI才知道,之所以自己只能享受最低標準的母愛,家裏每月支付給中介的2000刀“買媽錢”裏,有1400刀都被中介拿去給自己買媽了。

不止在家裏,在亞裔面孔長期遭受歧視的波士頓,在學校SHI也經常被本地學生當作沙包,被控制住雙臂在更衣間玩真人快打。
面對這些屈辱經歷,當年的SHI只能一再忍耐,夜晚只有將醫生開的褪黑素量翻倍,他才能停止胃痙攣和噩夢入睡。
無力反抗的背後,一是當時他只有42公斤,體型孱弱。二是父親只教過他該如何向善,沒教過他如何教育帶惡人。唯一一次在學校和室友爆發衝突,他的攻擊方式竟是“直接喝了一大口洗腳水,然後噴對方臉上。”

或許是過於迫切想要融入新生活,SHI越是努力發展社交,越是被邊緣化。有一回他“非常enjoy的和一個老黑聊了一下午,我感覺他也很enjoy,走時想加好友,他卻説自己沒手機。結果五分鐘後我再回去,發現他正在和女友打電話。”
再之後,SHI開始明白:作為一顆種子,他必須走哪都能紮根才算成活。
以暴制暴是SHI最先掌握的遊戲邏輯。為了把揍他的小逼崽子踩在腳下,他開始拼命健身,光是練出大塊頭還不夠,完事還得去橄欖球場上摔打一番提高耐用度。肉身膨脹後,SHI內心也隨之強大起來——

留學第三年時,又有人在課堂上日常拿黃種人開涮。shit算SHI的諧音梗,對方一直對着SHI大喊“holy shit! holy shit!”,他以為SHI拿他沒轍,結果SHI直接抄起他的頭就往桌上砸,再也沒給他開口的機會。後來SHI才知道自己原來打了個富二代,強龍壓不過地頭蛇,SHI險些被搞退學。之後他認真反思了自己是否過於衝動,結論是“對不起,我錯了。但下次還敢。”
這一次SHI一戰成名,好處是沒人敢招惹他了,壞處是校園霸凌從熱暴力升級成了冷暴力,他被扭曲成了gangsta問題少年,結果卻引起了真gangsta對他的興趣。

當年SHI最好的朋友和他一樣是外籍留學生,但同時也是另一個小國幫派老大的兒子。
作為一個有文化的Gangsta,他喜歡沒事就整點匪幫Trap,來紓解一下自己孤獨的內心世界。
遇見他認為同樣是Gangsta的SHI,他就像遇見了久違的同類感到歡喜,而喜歡他,就要和他分享自己最重要的東西——Hiphop,以及和他一起搞Hiphop的朋友們
就這樣,SHI就在gangsta大佬的安排下,開啓了自己的rapper生涯。但真實的是,或許是因為gangsta大佬們也沒啥名氣,所以在做音樂這件事上,SHI在波士頓八年間主要還是靠自己摸索。
那時比起音樂製作技術,SHI從他們身上汲取到更多的東西,是純粹的友情。
而SHI帶給他們最多的東西,則是麻辣香鍋。

那時他最愛做的事情就是帶着老黑朋友一起去吃四川菜,結果老黑朋友對麻辣香鍋一見鍾情,就像一個地道成都人遇到家鄉菜一樣,聲稱這種味道比自己髮量還濃郁的食物才是天菜。
對SHI來説,當好友盛讚家鄉菜時,他會產生一種微妙的成就感。
這種欣慰既來源自一個骨子裏對成都local文化的自豪感,也來自於他終於在異國他鄉逢到了知己:
剛到波士頓時,他就不止一次向周圍的留學生朋友們慷慨介紹過各種成都美食、成都文化,“但卻根本沒人對成都感興趣”,甚至有一次,他和一個老外交談時,自以為非常enjoy的聊了半天,結果臨行想加個好友時,對方卻婉拒:“對不起,我還小,沒有手機。”
結果過了五分鐘,SHI再回頭路過時,發現對方正在用手機和女友聊得熱火朝天。
那之後SHI一度很傷心,他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一個成都人想要融入波士頓,為啥偏偏就這麼難。
但如今,隨着麻辣香鍋教的傳教大成功,SHI終於感受到了自己和家鄉一併被認可的感覺。

或許是因為對SHI來説,成都生活就是他留學前人生的全部,也或許是在波士頓漂泊的日子總讓SHI倍加思念家鄉,總之不知道是何時起,SHI的腦海裏便有了一種莫名的使命感——
他要用自己最拿手的音樂製作,來傳播巴蜀文化,讓更多的人像愛上麻辣香鍋一樣愛上巴蜀。
如果説曾經他是一顆漂泊的種子,那麼如今,他便要決心通過耕耘巴蜀音樂來開闢一方讓自己足以紮根的土地。

在做音樂這件事上,SHI頗有一種亂拳打死老師父的狠勁。
儘管身邊都是一羣做老黑音樂的國際友人,但SHI最早的説唱啓蒙和精神導師,卻是一位聽了後讓我一時間滿頭問號的名字:廖健。
在百度上,我搜廖健,第一個出來的確是四川本土笑星李伯清的名字。而廖健則是他的頭號大弟子,主要成就是獲得了第二屆巴蜀笑星獎。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歡樂喜劇人,在05的時候居然發行了一張説唱專輯《時事播報-亂劈柴》,封面聲稱這是一張“全球最為流行的HipRap專輯”,但曲目列表卻讓人懷疑這到底是不是一張相聲曲目盜版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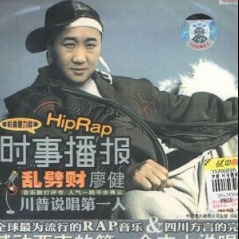
但仔細聽了一遍後,我理解了為什麼SHI那麼rescpect廖健:
從《我不是網蟲》裏反思網蟲缺失家庭教育、到諷刺社會到處都假的《假打》,再到《人狗歌》裏痛斥現實裏“自古多見人變狗,如今想看狗變人”
在這張專輯裏,“廖健批判時事、直抒胸臆,融方言俚語於荒誕派一爐,有一種互聯網才有哩狂放色彩”。
按05年的目光來看,這些歌或許最多隻算是網絡逗樂歌曲,但正是這張HipRap大碟裏的《素芬兒》,成為了SHI《丁丁貓兒》和《素芬兒,別走》的靈感源泉。

用SHI的話説,“老黑的歌裏用SHAWTY形容女神,那我就用素芬來代替SHAWTY”。
可能正是因為受廖健影響最深,所以SHI打一開始做音樂,就半隻腳邁上了喜劇人的不歸路——
《丁丁貓兒》裏乘在蜻蜓身上飛往外太空和嫦娥約會只是小兒科。
在《錦江愛情故事》裏,他直接遁入土味十八層,腳踩白襪拖鞋,牽手美嬌娘,一起搖擺在了錦江公園上30元/客的小船上,一起搖搖晃晃在人間舉辦了場浪漫婚禮。
因為拍攝經費比較拮据,所以這艘小船隻裝了120元的人,除了新郎新娘,就只剩下一個主持人和伴郎:

但看似chill的婚禮畫面裏,其實還藏着另一個悲傷的故事。
或許是因為太窮了,也或許是用來做婚車的卡車太顛簸,就這樣把新娘和愛情一起顛到了馬路牙子外,總之老SHI這趟車還沒開到洞房,就被急剎車了。
新娘沒了,還因為戀愛欠了3w塊,頭頂着大紅喜字,SHI眼淚CHUA CHAU往下流,只想對擄走新娘的富二代懇求:
“你是高富帥請你不要拆了我的家,這世界是你花園那就不要採我花。”

但最後,高富帥還是沒有答應他的請求。
儘管他使完了愛情三十六計,可最後素芬還是放棄了他“排氣管長青苔”的夏利,轉頭還是選擇了高富帥的寶馬,過起了去“太古裏一次花五六萬”的快樂生活。
到最後,SHI終於認清了現實,啃着白麪饅頭,結束了這場愛情之旅。

這就是SHI在新專輯《巴蜀文藝復興:第一章》裏講述的第一組成都愛情故事。儘管是個悲劇,但SHI卻用一種成都式的chill腦回路化悲傷為荒誕幽默。
再或者就和《竹林搖》一樣,SHI講述了一出和心愛女孩隱居竹林、日日砍柴做飯,一起聽歌搖擺的神仙愛情故事。
那天我本想提問SHI為什麼能想到這個故事,但當他帶我去他找靈感最常去的望江公園時,我進門一抬頭,答案似乎便一切盡在不言間:
在這裏,竹林中的柱子個個直插雲霄,一排排竹林了公園每個角落。行走在竹林之中,我唯一的感受就是“好渺小,我好渺小,煩惱一瞬間也變得好渺小。”

而旁邊的成都叔叔阿姨們,也一個比一個chill。
老頭們在這裏每天練習花棍,還專門做了一面錦旗,上面繡着“快樂花棍隊”,走哪帶到哪,一看就快樂得狠:

而老太太們也毫不羞澀,在碧雞坊的門口,興致來了就會放下茶杯,立刻邀請身邊的老頭一起跳一曲“快三”。

就是在這樣一處飛地,SHI汲取了靈感,做完了他回國後的首張專輯《巴蜀文藝復興:第一章》

在二十出頭的年紀,SHI曾經童年記憶在成都,成人記憶在美國。在成都,他第一次認識了世界,在美國,他通過hiphop結交了摯友,打開了另一個世界。
如今,他終於從波士頓回到了成都,嘗試用自己過去修煉出的“絲滑Hiphop”解封對老成都街頭巷尾的全部回憶,掀起一場中西合併、推陳出新的“巴蜀文藝復興”

目前,這張專輯裏從《丁丁貓兒》到《素芬兒,別走》、《竹林搖》好幾首歌都已經在網易拿下了999+,對他來説,這或許算是實現了他要復興巴蜀音樂大計的第一步。
但更重要的是,無論復興巴蜀音樂大計走到了哪,伴隨在節目結交了新朋友以及新專輯發行,SHI終於結束了曾經在國外的漂泊,他終於在國內站穩了腳跟。
在新專輯裏,很多朋友都幫他的單曲進行了feat,比如在講述他在國外被校園暴力的單曲《Grab》裏,地磁卡就幫他唱了hook,而中文敍事那段,則是夏之禹替他講述了那段“生活一塌糊塗,需要救心丸”的日子:
而圈子裏其他一眾好友們,從直火幫到愚月,力也都紛紛和SHI合作,願意一起幫他完成這場復興巴蜀音樂的夢想。
社交屬性對説唱歌手非常重要,因為hiphop本就是一場源自街頭的battle遊戲。單打獨鬥很快就會被淘汰,背靠廠牌和兄弟們才能走得更長遠。

而如今,SHI不僅邁出了第一步,更是徹底紮根,未來的每一步都註定走得會更穩、更遠。
當然,音樂對他來説或許也還有着更重要的意義。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原來當年被淘汰時,SHI説“外婆,我做到”時,其實他外婆已經病逝許久。但在臨走前,外婆錄給他最後一段語音裏,卻先是鼓勵了他的音樂“我給你點贊!”,再是希望SHI一定“要快樂,要高興。”
外婆走後,SHI一度消沉,但等緩過勁後,他第一時間就重製了自己每首歌前奏會出現的水印,改成了“劉汝平,晾衣服”。
這是外婆生前總是對爺爺説的話,如今SHI把它做成了水印,對他來説,這是“能夠用音樂的方式,繼續延續婆婆的生命”。

在創作中,SHI總是需要一次又一次和自己對話,一次又一次剖析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當他把過去一切痛苦最終能唱出來時,不知不覺間,便也完成了與自己的和解。
如今他不會再輕易被兩句話激怒而揮拳,但這種和解,偶爾也來的並沒有那麼輕鬆。
在《新世代》那場淘汰賽上,在《丁丁貓兒》的結尾,方才還唱着無厘頭的SHI突然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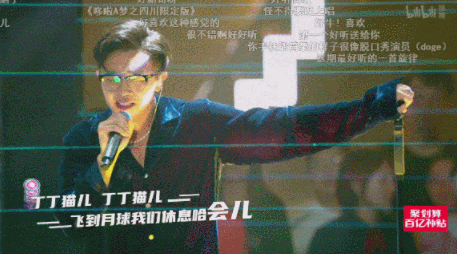
很多粉絲都在評論區裏揣測當時SHI為什麼要哭,我也感到好奇:
“丁丁貓兒這麼快樂的歌,為什麼你會唱哭呢?”
“因為…能像丁丁貓兒那樣不用考慮現實,不用關心任何事情,和兩三個好兄弟就這樣飛去太空玩其實是我總是幻想的生活。但最後唱到結尾,我終於發現這一切只是一場夢。”
“夢醒了,我還是要繼續活着對吧。
可活在這個世界上,又總是有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