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布衣》的敍事和風格_風聞
日本通-2021-05-08 15:34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邯鄲文藝評論(ID:gh_89369f8bfc95),作者:李紹山,日本通經授權發佈一部小説鉅著。通俗演義故事書。小説涉及宮廷鬥爭,傳奇情緣,橫跨朝野之間一部布衣傳奇,一男二女的愛情故事,多次遭遇險情。主人公可以立於朝堂而卻步,可以安享榮華富貴而甘願固窮清高,可以得到皇帝的賞識或為駙馬而為信念拋撇不顧。可以為輔宰的女婿飛黃騰達而鄙睨拒絕。為了正義,為了匡扶社稷,多次挺身而出,置個人榮辱度外,小説完成了這位旬布衣的傳奇描寫。小説屬於傳奇體的小説,也屢屢運用傳奇的筆法。開頭就是宮內延及庭外的兇手之鬥,兩撥刺客刺殺一個文靜女子實是當今天子的女兒。連帶主人公旬謨差點不測。長安城外旬謨又見義勇為,掩護了搭救自己的寧義士,回報救命之恩。小説寫寧義士,三入宰相府刺殺殺父仇人,反被仇人屢次追殺,險遭毒手,九死一生。寧義士刑場救旬謨,眼看劊子手的大砍刀舉起落下,人頭就要落地,疾馬而來的寧疾雲飛身一枚石頭呼嘯而來,救下鬼門關上人。小説中寧義士飛檐走壁,殺貪官,除惡霸,百步穿楊功夫,瞬間無影蹤,寫的叫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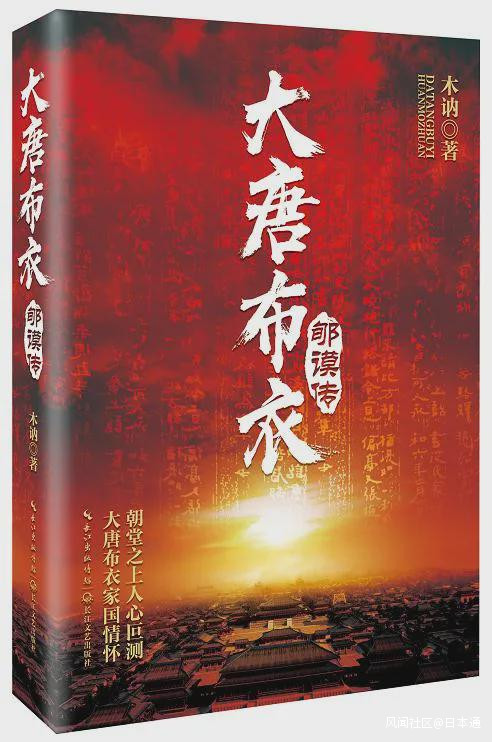 作為傳奇體小説,不僅僅這些帶有噱頭的細節場景,也表現在宮廷鬥爭的諸多情節中。比如寫扳倒大奸魚朝恩這樣的亂臣賊子,元載為首的一撥臣子,與李棲筠為代表的這樣的清廉正直的官員,三股勢力,朝堂之上一來一往,庭下暗裏劍拔弩張,計計連環,撲朔迷離。比如寫元載一黨的京兆尹黎幹,辦案過程中搜出了魚朝恩手下禮部貪官郭德全的一封信,魚朝恩的乾兒子魚令徽為討好乾爹迫不及待的燒燬檔案室,企圖毀信滅跡。不料魚朝恩非常生氣的狠揍這個乾兒子,因為這本身是一封偽造信件,是元載對魚朝恩的栽贓而已,本可以對照筆跡在皇帝李豫那裏得以澄清。這麼一燒,反倒弄巧成拙,説也説不清了。這封信果然是元載手下幕僚偽造,元載向來是“用過的”就廢掉不留痕跡,於是派寧疾雲去殺掉急於領賞的幕吏,而寧疾雲其實是被仇家元載迷惑,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也成了個“用過就廢掉不留的”,被元載的手下黑衣人多次追殺,身受重傷差點丟命。小説廷內庭外,朝野之間,故事連為一體,上下其手,步步緊湊,目不暇接,帶有強烈的傳奇性。 小説的傳奇性還表現在小説的情感戲之中。郭子儀救下昏倒在路上的沈夢蕪,安排她住進長安望月樓客棧,其出色的技藝,很快成了長安城的有名藝伎,結果旬謨為元載不彈劾魚朝恩舊部劉希暹為非作歹之事而煩亂惆悵,到望月樓買醉,恰逢沈夢蕪,沈夢蕪感戴旬謨的救命之恩,自然心不能已,主動為旬公子獻藝歌唱,驚動長安城一條街。小説抓住這個望月樓,寫了禮部侍郎楊綰的偶遇沈珍珠女兒,成為宮廷正直官員與權臣元載鬥爭的一個反覆爭奪的端緒,元載設計喬騙沈夢蕪獲取“貴人”的信任,也是他挾持並愚弄今上的法寶。元媛也來到望月樓追尋旬公子而與美女沈夢蕪有一番情色的過招,從此一個荀公子,兩個大大的美女由此三角牽扯不斷,波及整個小説的情節。寧疾雲也在這個為沈夢蕪沉迷其情色,心不能已,最終在望月樓與前來劫持沈小姐的打手一番激戰終而不敵而陷入元載府的囚禁暗室。
作為傳奇體小説,不僅僅這些帶有噱頭的細節場景,也表現在宮廷鬥爭的諸多情節中。比如寫扳倒大奸魚朝恩這樣的亂臣賊子,元載為首的一撥臣子,與李棲筠為代表的這樣的清廉正直的官員,三股勢力,朝堂之上一來一往,庭下暗裏劍拔弩張,計計連環,撲朔迷離。比如寫元載一黨的京兆尹黎幹,辦案過程中搜出了魚朝恩手下禮部貪官郭德全的一封信,魚朝恩的乾兒子魚令徽為討好乾爹迫不及待的燒燬檔案室,企圖毀信滅跡。不料魚朝恩非常生氣的狠揍這個乾兒子,因為這本身是一封偽造信件,是元載對魚朝恩的栽贓而已,本可以對照筆跡在皇帝李豫那裏得以澄清。這麼一燒,反倒弄巧成拙,説也説不清了。這封信果然是元載手下幕僚偽造,元載向來是“用過的”就廢掉不留痕跡,於是派寧疾雲去殺掉急於領賞的幕吏,而寧疾雲其實是被仇家元載迷惑,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也成了個“用過就廢掉不留的”,被元載的手下黑衣人多次追殺,身受重傷差點丟命。小説廷內庭外,朝野之間,故事連為一體,上下其手,步步緊湊,目不暇接,帶有強烈的傳奇性。 小説的傳奇性還表現在小説的情感戲之中。郭子儀救下昏倒在路上的沈夢蕪,安排她住進長安望月樓客棧,其出色的技藝,很快成了長安城的有名藝伎,結果旬謨為元載不彈劾魚朝恩舊部劉希暹為非作歹之事而煩亂惆悵,到望月樓買醉,恰逢沈夢蕪,沈夢蕪感戴旬謨的救命之恩,自然心不能已,主動為旬公子獻藝歌唱,驚動長安城一條街。小説抓住這個望月樓,寫了禮部侍郎楊綰的偶遇沈珍珠女兒,成為宮廷正直官員與權臣元載鬥爭的一個反覆爭奪的端緒,元載設計喬騙沈夢蕪獲取“貴人”的信任,也是他挾持並愚弄今上的法寶。元媛也來到望月樓追尋旬公子而與美女沈夢蕪有一番情色的過招,從此一個荀公子,兩個大大的美女由此三角牽扯不斷,波及整個小説的情節。寧疾雲也在這個為沈夢蕪沉迷其情色,心不能已,最終在望月樓與前來劫持沈小姐的打手一番激戰終而不敵而陷入元載府的囚禁暗室。 小説在傳奇的寫法上有較大變化。清末武俠傳奇,還是傳統寫法,一個故事展開,但是故事與故事之間勾連穿插。比如《施公案》《彭公案》《三俠五義》之類。也能寫出案中案等,算是故事中套着故事。不過總體看那算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結構吧。民國傳奇,比如張恨水的通俗演義小説《啼笑因緣》之類,更多運用偶遇和巧合,打破清末公案英雄傳奇故事而切入人生日常場面了。《大唐布衣》有驚心動魄的英雄故事(寧疾雲殺貪官,旬公子勇闖陝西節度使皇甫温,共舉大計。又入神策軍府買通將領周浩等。還有考場舞弊案中的冒着掉頭的危險為清除弊案而奮臂一呼。最後又為了扳倒權臣元載而在春闈考場血書大曝“冤”情,從而推波助瀾,推開了“元載夜醮案”權臣倒掉的大門),也有不少的日常生活敍事,比如元載家庭的夫妻,父女,父妾,種種關係中的家庭矛盾及其周折等來來回回的諸多事件,旬公子與兩位女子的愛情糾葛等,寧公子與沈夢蕪前前後後的情色迷離及其最後因為明白了其“公主”的身份而放棄。問題是作家沒有沿用傳統寫法,而是用一種現代人生視角來敍述。多側面,多角度,比較立體化的,綜合各種信息流,主觀上也不想重複那種舊傳奇的簡單寫法。希望通過信息集束的方式,通過閭里耳目、道聽途説的現代人生方式,藉着唐代宮廷官場的鬥爭史實框架鋪敍延展,展示一種類似現代人生方式的傳奇故事。也可以説,小説的敍事是那種英雄傳奇融合了都市市井傳奇的混合式的寫法,後者比如現代海派小説張愛玲、無名氏之類的都市男女愛情流離人性變異生活變遷等的現代傳奇(吳福輝成為現代都市傳奇)故事等。具體的行文過程中,作者還不斷用用交叉疊加敍事的方式,不用回目,事件單元之間,不設句讀空格,直接連段進行場景敍述轉換,這種敍事的目的顯然是把各種人間事端穿插疊加在一起,讓讀者產生一種急遽的空間轉換,有些目不暇接,類似電影蒙太奇手法,別人還沒有過(不會是排版印刷失誤吧)。當然,這是一種敍事形式方面的嘗試,是不是成功,有待閲讀者的檢驗。
小説在傳奇的寫法上有較大變化。清末武俠傳奇,還是傳統寫法,一個故事展開,但是故事與故事之間勾連穿插。比如《施公案》《彭公案》《三俠五義》之類。也能寫出案中案等,算是故事中套着故事。不過總體看那算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結構吧。民國傳奇,比如張恨水的通俗演義小説《啼笑因緣》之類,更多運用偶遇和巧合,打破清末公案英雄傳奇故事而切入人生日常場面了。《大唐布衣》有驚心動魄的英雄故事(寧疾雲殺貪官,旬公子勇闖陝西節度使皇甫温,共舉大計。又入神策軍府買通將領周浩等。還有考場舞弊案中的冒着掉頭的危險為清除弊案而奮臂一呼。最後又為了扳倒權臣元載而在春闈考場血書大曝“冤”情,從而推波助瀾,推開了“元載夜醮案”權臣倒掉的大門),也有不少的日常生活敍事,比如元載家庭的夫妻,父女,父妾,種種關係中的家庭矛盾及其周折等來來回回的諸多事件,旬公子與兩位女子的愛情糾葛等,寧公子與沈夢蕪前前後後的情色迷離及其最後因為明白了其“公主”的身份而放棄。問題是作家沒有沿用傳統寫法,而是用一種現代人生視角來敍述。多側面,多角度,比較立體化的,綜合各種信息流,主觀上也不想重複那種舊傳奇的簡單寫法。希望通過信息集束的方式,通過閭里耳目、道聽途説的現代人生方式,藉着唐代宮廷官場的鬥爭史實框架鋪敍延展,展示一種類似現代人生方式的傳奇故事。也可以説,小説的敍事是那種英雄傳奇融合了都市市井傳奇的混合式的寫法,後者比如現代海派小説張愛玲、無名氏之類的都市男女愛情流離人性變異生活變遷等的現代傳奇(吳福輝成為現代都市傳奇)故事等。具體的行文過程中,作者還不斷用用交叉疊加敍事的方式,不用回目,事件單元之間,不設句讀空格,直接連段進行場景敍述轉換,這種敍事的目的顯然是把各種人間事端穿插疊加在一起,讓讀者產生一種急遽的空間轉換,有些目不暇接,類似電影蒙太奇手法,別人還沒有過(不會是排版印刷失誤吧)。當然,這是一種敍事形式方面的嘗試,是不是成功,有待閲讀者的檢驗。 其實,敍事不僅僅是人事行為的過程與情節,鋪敍與交叉,延展和轉換,也是作家的寫作價值觀對情節故事的敍寫機制對故事情節設置方方面面的干預問題。敍述一件事,什麼角度,什麼個氣脈,什麼姿態,什麼意趣,什麼品格品味,甚至用什麼樣的言語實現一種什麼樣的話語價值等,就是通過情節故事呈現出來的。這是敍事的本質,也是敍事的本體。説清楚一件事並不難,這就是個故事。但是要想通過這個故事呈現一個什麼藝術價值觀才是藝術的本真方面。從這個角度更深入的看小説,也能發現可以商榷的所在。比如小説藉助唐代中後期的歷史史實作為整個敍事的框架,從閲讀期待來説,顯然這是一部宮廷內鬥朝野爭端的歷史演義,既然如此,作家在創作方面,宮廷禮儀,官衙制度,公務之規,禮儀進退之階,朝堂空間態勢,應當有大約的敍述準備,可是這方面幾乎是空白,這是出人意料的。小説裏也寫到了長安街頭,藝伎歌女,茶樓酒肆,市井痕跡,江湖之流,那麼是不是也應該有一些較為專業的名稱指稱,讓閲讀稍稍進入即便是模擬的歷史的虛擬的情境也好,這方面也顯然準備不足。既如此,那麼小説構思就應當把歷史泛化和虛化,把地名國名朝堂衙署街道宅邸樓宇也都另外的給予重新的主觀性命名,就好比當今的各種網絡傳奇小説那樣的。但是有意思的是,作家又竭力的在人的身份稱謂稱呼方面回到歷史的具體情境中。比如“宰相”“阿耶”“阿郎”“郎君”“娘子”“兒”等等,可是,這種稱謂又顯得不倫不類,匪夷所思,摸不着頭腦……其實這個很好解決,看看唐代傳奇小説中怎麼使用這類稱呼就行了。總不能“娘子”用作一個未出閣的姑娘的稱呼。“阿郎”“郎君”這種親暱用語用作普通人之間的關係稱呼。宰相是官位官階,根本就不是稱呼。旬公子作為元載的門人,怎麼能以“宰相”稱呼主人元載呢。就小説的語言看,言語完全當代化淺白俗套化甚至官方化,那這些稱呼何妨就直接切換成爹孃,阿哥阿妹,夫啊妻啊的更切當呢。這都是敍事中的問題,我説了,這都關聯到敍事的藝術價值觀,藝術姿態品位,藝術情境的呈現。不要忘了,藝術,總是訴諸人的精神知覺靈魂深處的東西,不僅要細節處不能含糊,一個話語詞語口吻也不能粗疏。因為藝術的魅惑和真諦也許就是在那“一發而動全身”的細膩處,是整體性的。如果僅僅是寫寫故事,編織點所謂的“傳奇”,那不就成了故事匯,就是鳳姐那種低層次的粗疏人所好的東西了。作者簡介
其實,敍事不僅僅是人事行為的過程與情節,鋪敍與交叉,延展和轉換,也是作家的寫作價值觀對情節故事的敍寫機制對故事情節設置方方面面的干預問題。敍述一件事,什麼角度,什麼個氣脈,什麼姿態,什麼意趣,什麼品格品味,甚至用什麼樣的言語實現一種什麼樣的話語價值等,就是通過情節故事呈現出來的。這是敍事的本質,也是敍事的本體。説清楚一件事並不難,這就是個故事。但是要想通過這個故事呈現一個什麼藝術價值觀才是藝術的本真方面。從這個角度更深入的看小説,也能發現可以商榷的所在。比如小説藉助唐代中後期的歷史史實作為整個敍事的框架,從閲讀期待來説,顯然這是一部宮廷內鬥朝野爭端的歷史演義,既然如此,作家在創作方面,宮廷禮儀,官衙制度,公務之規,禮儀進退之階,朝堂空間態勢,應當有大約的敍述準備,可是這方面幾乎是空白,這是出人意料的。小説裏也寫到了長安街頭,藝伎歌女,茶樓酒肆,市井痕跡,江湖之流,那麼是不是也應該有一些較為專業的名稱指稱,讓閲讀稍稍進入即便是模擬的歷史的虛擬的情境也好,這方面也顯然準備不足。既如此,那麼小説構思就應當把歷史泛化和虛化,把地名國名朝堂衙署街道宅邸樓宇也都另外的給予重新的主觀性命名,就好比當今的各種網絡傳奇小説那樣的。但是有意思的是,作家又竭力的在人的身份稱謂稱呼方面回到歷史的具體情境中。比如“宰相”“阿耶”“阿郎”“郎君”“娘子”“兒”等等,可是,這種稱謂又顯得不倫不類,匪夷所思,摸不着頭腦……其實這個很好解決,看看唐代傳奇小説中怎麼使用這類稱呼就行了。總不能“娘子”用作一個未出閣的姑娘的稱呼。“阿郎”“郎君”這種親暱用語用作普通人之間的關係稱呼。宰相是官位官階,根本就不是稱呼。旬公子作為元載的門人,怎麼能以“宰相”稱呼主人元載呢。就小説的語言看,言語完全當代化淺白俗套化甚至官方化,那這些稱呼何妨就直接切換成爹孃,阿哥阿妹,夫啊妻啊的更切當呢。這都是敍事中的問題,我説了,這都關聯到敍事的藝術價值觀,藝術姿態品位,藝術情境的呈現。不要忘了,藝術,總是訴諸人的精神知覺靈魂深處的東西,不僅要細節處不能含糊,一個話語詞語口吻也不能粗疏。因為藝術的魅惑和真諦也許就是在那“一發而動全身”的細膩處,是整體性的。如果僅僅是寫寫故事,編織點所謂的“傳奇”,那不就成了故事匯,就是鳳姐那種低層次的粗疏人所好的東西了。作者簡介 李紹山,邯鄲學院文學院副教授、《九月》雜誌編輯、邯鄲學院全國大學生詩賽評委、臨漳曹操杯詩歌大賽評委。致力當代文學、邯鄲地方文學研究。迄今發表學術論文近30篇。編輯:高影新校對:艾亞南審核:王承俊
李紹山,邯鄲學院文學院副教授、《九月》雜誌編輯、邯鄲學院全國大學生詩賽評委、臨漳曹操杯詩歌大賽評委。致力當代文學、邯鄲地方文學研究。迄今發表學術論文近30篇。編輯:高影新校對:艾亞南審核:王承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