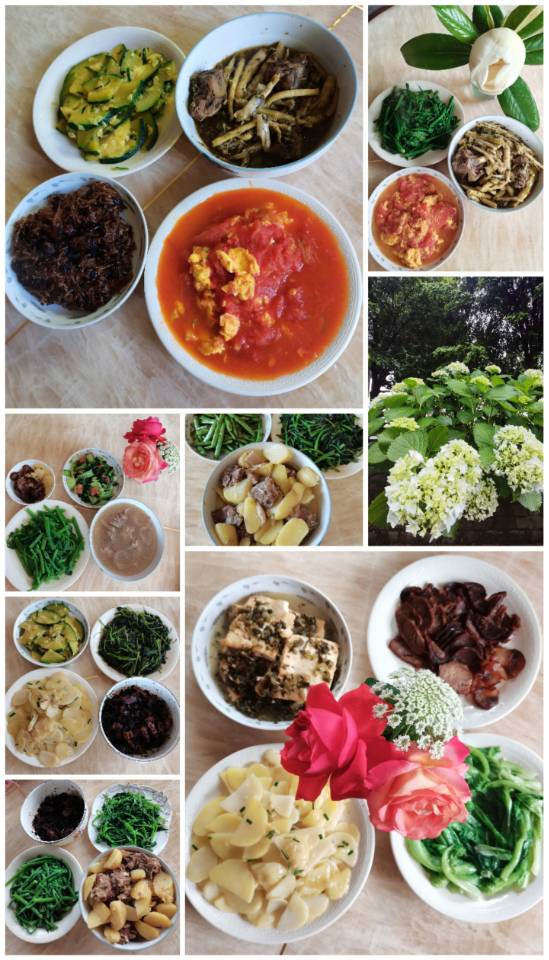你聽,《詩經》在説“不”_風聞
来者建强-仁者见智2021-05-15 10:11
距今2500多年至3000年左右的《詩經》(亦稱《詩》或《詩三百》)是記錄華夏世界早期歷史的一份證件,相傳由孔子領銜、編撰刪定而流傳於世的有300餘首,按作品年代的先後大致可分為頌、雅和國風三部分(國風或是漢朝再編輯的分類)。
然而,師出孔門、另立門户的墨子給出的描述彷彿是另一個星球上的事,據説,孔老師“篩選”的底本有“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如此算來,刪存比高達七三開。

更有記載稱,春秋時期還有詩三千首,分為“南、頌、雅、風”四個部分。今天,我們能有幸閲讀到《詩經》的第一篇《關雎》便是屬於“南”部樂歌之一的《周南》篇。不幸的是,《周南·關雎》似乎已被今人誤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本意也許並不是魯迅開玩笑説的“郎才女貌好登對”,而更可能是描述3000年前以舞樂通神的女巫(淑女)在祭祀中與祖先神靈(君子)的對話場景。
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文化的嬗變一如歷史的曲折,蜿蜒往復卻不可再現。而歷經大浪淘沙的詩三百是燈火闌珊處的歲月遺留給後人的一份無聲的交代。
(一)
孔子依據什麼標準刪定《詩經》,如今只剩傳説。漢末的達儒曾指出,即便是這詩三百中能夠稱之為“正經”作品(歌功頌德)的只有三十四首,其餘多少有些變味,或者説慢慢地唱作成了變奏曲。
《詩經》是早期歷史的寫真,卻往往被人忽視,它還是一部華夏最初思想變化的記錄,深刻反映變化的就是那些後期大量產生的變“風”、變“雅”之詩。
如何“變味”?簡單地説,在“伐殷、踐奄”(奄,殷的附庸)險勝之後,周人自以為,在祖先神靈“天人合一”的護佑下,建設新國家前途一片光明、蒸蒸日上。但是,天有不測,周初因無法徹底消滅殷族舊勢而採取維新的社會制度已埋下悲劇的基調,新的最終難以壓制住舊的,而舊的又死死拖住了革新,諸多社會矛盾產生並激化,維新被迫變換成維穩,終而“天降喪亂”,一己之福變奏為自求多福。變“風”、變“雅”之詩正是由社會悲劇的真實矛盾,反映而為矛盾的真實悲劇。
對比同時代的古希臘,《詩經》可以被視作一部中國特色的悲劇史詩,不知名的創作者們不厭其煩地述説着一個又一個的“不”——這是特色鮮明的中國式的政治勸諫——主觀上企圖從衰微的命運中解救自己,卻無法打破維新維穩的桎梏,所以註定迴天無力,但這一切又在客觀上造就出壯大諸子百家思想花果萌芽的土壤。
這就是《詩》中深潛不露的秘密,與其説“《詩》亡,然後《春秋》作”,毋寧説“《詩》亡,然後諸子出”。

孔子生平“述而不作”,卻將自己很想説的不同意見,通過巧妙精心的選擇,以獨特説“不”的形式,保存在了詩三百中。今人如果不能充分理解詩中説的“不”,即使不至於誇張淪落到“不學詩無以言”,至少也會留下某種缺憾。
那麼,《詩經》中説了哪些“不”,暴露了當時社會哪些矛盾問題,對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又有何意義呢?
早期史料已披露,維持三百年的西周,其間能稱得上是盛世的好景並不長久,昭王、穆王時代的開疆拓土已遭遇軍事上的大失敗,昭王南征時連命都丟了。到了西周末年,周族不得不率領族人東遷,犧牲地域而維持宗族,“遷國”本身折射周族社稷基礎不穩固的末運。
於是,集中反映東遷前後的變“風”、變“雅”雖有所顧忌但還算放開大膽地痛斥了腐朽的社會現實,其中暴露出的現實矛盾與問題可粗略地歸納為六個方面。
(二)
1、暴露“不可救藥”的社會危機
在周厲王時代以後的《大雅·板》詩中,一位舊貴族的老詩人形容當時社會矛盾實在是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指出城市統治階級成了孤家寡人,城市國家就要被破壞了。該詩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曰:
“上帝闆闆,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上章詩句中,“闆闆”意為違背常道,“猶”通“猷”,意指決策謀劃。句意是,上帝昏亂背離常道,下民受苦辛勞多病。説出的話太不像樣,作出決策缺乏遠見。無視聖賢而剛愎自用,不講誠信而是非不分。謀劃行事太沒遠見,所以要用詩來勸告。
第四章曰:“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其中,“灌灌”即款款,表示誠懇的樣子;“蹻蹻”則為傲慢的姿態;“熇熇”意思是像火勢熾烈的樣子,一發而不可收拾。
句意是,天下近來正鬧災荒,不要一味縱樂放蕩。老人忠心誠意,小子卻如此傲慢輕狂。不要説我倚老賣老,被你當做昏憒荒唐。多行不義一發而不可收拾,不可救藥病入膏肓。

據史載,當時周厲王在國內對敢言者採取了監視和屠殺的嚴厲手段,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們還是用種種不同的形式來宣泄不滿。僅從《板》詩前半部分揭露的,原先具有強大威懾力的上帝既然變得那樣反常,人民(奴隸)也就不聽話了,因此,照詩人的邏輯來講,周代王朝是“不可救藥”的了。
這首《板》與另一首《蕩》同以諷刺周厲王失德暴政著稱於世,以至“板蕩”一詞成為形容政局混亂、社會動盪的專用詞。
《桑柔》是《大雅·蕩之什》中的一篇。此詩共有十六章,幾乎章章説“不”,形容社會因了不平,大亂將起,統治階級就是造成大亂的禍首。前兩章曰: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可直譯為,茂密柔嫩青青桑,下有濃蔭好地方。桑葉採盡枝幹禿,百姓受害難遮涼。愁思不絕心煩憂,失意淒涼久惆悵。老天光明高居上,怎不憐憫我驚惶。
四馬駕車好強壯,旌旗迎風亂飄揚。社會動亂不太平,舉國不寧人心慌。百姓受難少壯丁,如受火災盡遭殃。長長聲聲心悲哀,國運艱難太動盪。
(三)
2、諷刺氏族貴族的沒落
周人將自己描繪成是被上帝天神選中的氏族,使得氏族宗子曾孫世代“受民受土”(分配到奴隸與疆土),開萬世之太平。然而,貴族統治階級很快走到了人民利益的反面,《詩經》揭露這一現象的同時,貴族君子也被形容為兇惡人物!
在《小雅·十月之交》詩曰:“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污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此詩共八章,每章八句,以上節選自第五章。意思是,嘆息一聲這皇父(周幽王時的一名高官),難道真不識時務?為何調我去服役,事先一聲都不招呼?拆我牆來毀我屋,田被水淹終荒蕪。還瞎扯什麼“不是我殘暴,禮法就是如此”。
《十月之交》開篇記述了當時發生的一次日食現象。據現代天文學家考訂推測,詩中記載的日食發生在公元前776年9月6日,即周幽王六年夏曆十月一日,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記錄。

詩人從天昏地暗可怕的災異,説到朝廷的壞人專權和國家的岌岌可危,然後説到個人去從上的選擇,顯示詩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情懷,也算是為楚國詩人屈原開了“伏清白以死直”的精神先河。
同樣諷刺周幽王的昏庸,《小雅·節南山之什》開篇的《節南山》一詩有云: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説的是,老天爺真是不光明,降下如此的大禍亂。老天爺實在不聰慧,降下如此的大災難。君子執政如臨淵履冰,才能使民眾心安。君子執政如碗水持平,憎惡忿怒才能被棄捐。
老天爺實在太不良善,禍亂從此再無法平定。一月連着一月競相發生,使庶民從此無法安寧。憂國之心如醉酒般難受,有誰能掌好權平理朝政?如不能躬親去施政,受勞受苦的仍是百姓。
(四)
3、揭露戰爭中人民的痛苦
《小雅·何草不黃》便是一首反映常年在外勞苦行役的征夫的哀怨之作。此詩全文如下: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直譯為,哪種草兒不枯黃?哪一天兒不奔忙?什麼人兒不出徵?勞苦奔忙在四方。哪種草兒不腐爛?什麼人兒像光棍?可憐我等出征者,唯獨我們不是人!
不是野牛不是虎,曠野裏東奔西走。可憐我等出征者,起早貪黑不得休!狐狸尾巴蓬鬆松,深草叢裏來躲藏。役車高高載征夫,匆匆行在大路上。

要知道,西周社會的勞動奴隸的來源主要依靠對外戰爭的俘獲,周王朝對東西南北的征伐,不但和緩不了內部矛盾,反而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和勞動力的危機,以致貴族內部也有人以反對派的身份發出警告。
《鴇羽》是《詩·唐風》中的一篇。全詩三章,重複第一章的意思。這是一首反徭役剝削和壓迫的詩作,農民長期服役,不能耕種以養活父母,於是歌以此詩表抗爭。第一章曰:
“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詩經》之所以説是中國特色的悲劇史詩,不同於希臘古代史詩,原因在於最初的史詩具有特別的形式(統治階級祭祀祖神),而沒有國民階級的活動史料,僅有先王創業的傳奇,比如較早的詩有《周頌》和《大雅》的《文王》與《生民》,它直接以“先王”代表了“生民”。
其次,即使後來出現了一些像《鴇羽》《碩鼠》這樣的反映底層奴隸生活的作品,但是西周的維新社會性質終究不可能產生像古希臘那樣的雅典民主制度和雅典市民,也就不可能出現古希臘那樣偉大的悲劇藝術。而揭露社會矛盾和人民痛苦的,依靠的是壟斷文化的極少數貴族中的持不同意見者。
(五)
4、掀開“民不堪命”的蓋頭
周代勞動力主要是集體族奴或公社農民的形式,勞動力的單位一般是按氏族貴族的家室計算,如“百室盈止”,《春秋》記載的賜室、奪室、兼室等,即指勞動力的讓渡與爭取。西周中葉以後,勞動力(奴隸)已到“民不堪命”的境地。
如《大雅》的最後一篇《召旻》章中有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老天暴虐難提防,接二連三降災荒。饑饉遍地災情重,十室九空盡流亡……);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欺詐攻擊心藏奸,卻不自知有污點……);
“池之竭矣,不雲自頻。泉之竭矣,不雲自中。”(池水枯竭非一天,豈不開始在邊沿?泉水枯竭源頭斷,豈不開始在中間?)

類似上述的詩句很多,揭開了當時社會勞動力的危機。在此危機下,所謂“小民難保”等遺訓真正成了現實的問題,周初治民的神誥逐漸不靈了。結果是什麼呢?《大雅·桑柔》中最後兩章的詩句説得很明白: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雲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意思是,沒有準則地擾民,只因你背棄了良善。盡做不利人民的事,還嫌做得讓自己不爽快。百姓要走邪僻路,也只因你施暴太多。
百姓內心感到恐慌不安,而執政者卻在忙着偷盜劫掠。誠懇的勸告聽不進,背後反罵我荒唐。雖遭誹謗,我終究還要作歌唱。
這首詩分明是説出了奴隸面對統治者的“不仁”要鋌而走險,將威脅貴族君子們的統治,這豈不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
(六)
5、反映生產遭受的破壞
如果説“瘨我饑饉,民卒流亡”反映的是奴隸因饑荒而逃亡,那麼接下來的“我居圉卒荒”(《大雅·召旻》)和“哀恫中國,具贅卒荒”(《大雅·桑柔》)中提及的“卒荒”便是對生產的破壞。
因此,在“蟊賊內訌”(《大雅·召旻》)的時候,連田野上的草都像水中的浮萍,生產力的衰落是嚴重的。甚至國家滅亡——所謂“邦潰”也出現在此詩中:“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大雅·雲漢》是《詩三百》中唯一一篇寫大旱求雨的詩歌,作於周宣王所謂的“中興”時期。周宣王二年至六年(公元前826年—前822年),連年旱災,周宣王求神祈雨,此詩即周宣王向上天求雨的禱詞。全歌八章,每章十句。前兩章曰:
“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藴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梗。”

意思是説,高大顯著的那銀河啊,光明迴旋在上天。君王仰天長嘆息,為何降罪於今人。上天陡降災禍亂,饑饉再次到人間。無一神靈不祭祀,並未愛惜那犧牲。祭神圭璧已用盡,難道神靈都不聽?
旱情既然很嚴重,酷暑悶熱似火燻。並未斷絕祭祀禮,從那郊祭到王宮。敬酒埋玉祭天地,無一神靈不尊敬。后稷不能來享祭,上帝也不來光臨。虧損敗壞我下土,難道是我活該有此遭遇?
這些詩句不僅指出自然的災害(大旱),而更重要的指出連上帝也管不着國家的毀滅了。而稍早在《周頌》中自以為傲的創業盛景還是“綏萬邦,履豐年”、“萬億及稊,為酒為醴”,此時已然一去不返,難道這不是君王咎由自取的結果嗎!
在過去的歷史循環中,不管生產力如何低落,“食我農夫”是傳統不變的剝削關係,生產力愈降低,其“不稼不穡”而“素餐”的剝削程度更要厲害,如《魏風·碩鼠》對此的描述那樣。
(七)
6、揭示社會階層的變化
由於勞動力危機和生產力破壞,社會階層(或階級關係)也就隨之發生巨大變動,沒落的君子與貴族大人不得不力田代食,而“小人”(非貴族)居然可以富人姿態出現了。貴族的一部分沒落者心態就像《大雅·桑柔》所描述的這樣:
“如彼溯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雲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意思説的很明白,(國家敗壞)好像就在逆風而行,連呼吸張口都變得困難。百姓本有肅敬心,但卻無處獻力量。重視農業生產事,百姓辛苦代耕養。耕種收穫乃是國寶,原來代耕之民最善良。
反之,在世人的世界觀中,“小人”倖進,顯得是太不體面的事情了。詩中有不少由階級感情出發的悲傷調子,如《大雅·瞻卬》説的:
“天何以剌?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雲亡,邦國殄瘁!”
“不富”,不福佑也。沒落者感嘆,蒼天為何責罰苦?神靈為何不庇護?元兇頑敵全不顧,只是對我相忌妒。人們遭災不憐憫,綱紀敗壞裝糊塗。良臣賢士盡逃亡,國家危急無救助。
詩句顯然對於舊貴族寄存了憐憫,以至於把他們的沒落説成人類的沒落,把新興階級的人物説成“不類”。這種認識的侷限性不但表現在古代的詩歌裏,而且也陳列於後世中外的文學作品中。比如,堅信“一花凋零,荒蕪不了整個春天”的巴爾扎克(法國19世紀偉大小説家)主觀上擔心封建貴族的滅亡,客觀上卻把他們描寫成沒有前途的掙扎者。

《國風》中也有諷刺“威儀不類”小人的詩句,但這並不減少對階級關係的暴露,如《曹風·侯人》有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説的是,鵜鶘停在水壩上,翅膀乾乾滴水不沾身。那些平庸官僚吶,與所穿的衣服也太不相稱了吧。
在西周初年,土地與勞動力都是“公”有的(王公所有),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財富的絕對權力和神的絕對權力相適應,此時居然由於財富權力的變動,第一次的階級分野便被破壞了。一方面新興的富人,顯得“威儀不類”,另一方面舊氏族貴族感到了“人之雲亡”。
在這樣階級關係變化下,貴族君子也要與民爭利了。所以《大雅·瞻卬》説:"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好比奸商發橫財,君子有目共睹,學着照做。)
上述詩句已暗示了西周末年社會從氏族專權城市向着地域經濟城市的轉變傾向。在古希臘社會,“貨幣的凱旋行軍”,把城邦的貴族送到墳墓,因而產生了古典社會的國民之富;中國古代社會既然走着維新路徑,私有財富是在氏族制度的破壞中夾縫生長起來的,這個不完全的私有財富,畢竟在周厲王“失國”與周宣王“中興”之交發生了。問題之沒有徹底解決,則另當別論。
(八)
綜上所述,作為古代中國首部經典的《詩經》揭露當時社會矛盾與問題,不能不説這是巨大進步的體現。《詩經》中還有不少作品明顯指出,在大命告終之時,祖先神對子孫沒有一點援救,人對天失去了敬畏,也就敢於推翻祖先。
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不少詩句,為了挽救沒落的階級,依然苦口婆心地拿“以德報德”的話來規勸上面,如《大雅·抑》章有云:
“闢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於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這有點像貴族元老説的話,意在勸進統治者,努力修明你的德行,使它完美無倫比。言談舉止要慎重,切莫馬虎失禮儀。不犯錯誤不害人,人們無不效法你。有人贈我一隻桃,回報他用一隻李。羊崽無角説有角,實是忽悠你小子。
統治者怎麼可能聽的進去,道德在他們的鼓掌中變成了專門框縛他人的工具,先王德治已然漸變為霸主們的“以力服人”。所以,這樣的規勸當然是不會收到任何效果,可能作詩的人也不相信自己的話會有用。
歷史一再重複的是,貴族統治階級越近沒落,就越放肆起來。在《國風》中,這些王公氏族的形象被描繪得下流不堪了。而至於“國人”,如果他們有點財產,出門來顯擺門面,那就會遭到貴族譏笑,沒落者仍可依賴這些精神勝利法,依然能讓自己享受到夕陽無限好的陶醉。

於是乎,南宋理學集大成者的朱夫子看了詩風如此不正能量,生氣之餘,大筆一揮,梳理刪減,重新註解一番。
誠然,僅剩不多的《詩經》所揭示出的問題僅僅是早期中國的一個“縮影”。時至兩千多年後的晚清,在最後迫於現實不得不承認立憲的時候,抱着舊傳統不放的王公與士大夫們依然不放棄最後的抵抗,在頒發堂皇的天賦民權的詔文,同時又説愚民難信,先讓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下再另行決議。
歷史的社會性質,前後不同,但傳統精神卻相似到一絲不改。什麼“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改良主義者龔自珍的這句名言在悲觀者或者革命者那裏一樣都是不切實際的白日夢話。
需要特別補充一點,“不”字可能是《詩經》中被使用到最多的一個字,但早期的詩中,這個“不”並非是否定意涵。如在《周頌·清廟之什·維天之命》中有這樣的句子“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其中,“不顯”的“不”意思近似於非常,“不顯”表示非常明確、很明白的樣子。整句話的意思是,想到天神之命,任何的恭敬都顯不夠。啊,多麼耀眼、熠熠生輝的文王之德!
又如《周頌·清廟之什·烈文》還有:“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可以理解為,光芒無限的先祖美德,周之百官應該遵循。啊!勿忘先祖周王之美德。
歷史煙雲,滄海桑田,近代百年的華夏世界經歷了史無前例的鉅變,但是與民族偉大復興要求仍顯不夠,仍需今人不忘初心,不息奮鬥,譜寫新世紀最壯美的新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