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起底黑窯廠,我出500塊把自己給賣了”_風聞
一本黑-一本黑官方账号-公众号:【一本黑】专扒互联网灰黑产。2021-05-18 11:56
熟悉老黑我的人都知道,我早些年做過獨立調查記者,寫過不少互聯網灰黑產相關的文章。
在這些調查中,很大一部分得歸功於讀者爆料,再硬核一點的就是利用計算機基礎知識拿一波後台數據。
在某些時候,調查過程有一定危險性。比如我曾經寫過一篇稿子,結果得罪了某位黑產大佬,他在網上扒了我的全部個人信息;
也有人因此懷恨在心,揚言要幹掉我。好在他們多半都是口嗨,我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還有一些記者,在實地調查的過程中,冒着極大的風險。我稍稍舉幾個例子你們就能明白:鴻X藥酒、地溝油、X鹿奶粉。
他們為傳播真相都付出了巨大代價。
今天講的就是這麼一個記者,他叫崔松旺。他為了能獲得一手資料,心甘情願被賣進黑窯廠當奴工。
這一套操作下來,把新聞工作者都看得目瞪口呆。
01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2007年以後,各大媒體陸續報道有關黑心窯廠的新聞。
這些黑心窯廠,會專門搜刮社會上的智障人士,把他們拉進廠裏打工。
這個打工並不像我們現在意義上的打工,現在打工人動不動就是五險一金、週末雙休。如果不爽,還可以各種吐槽老闆。
而這幫被賣進窯廠的智障工人,由於存在着語言智力上的缺陷,所以就成為窯廠老闆肆意盤剝的對象。
他們工作的時候有監工監視着,稍有懈怠就拳打腳踢;睡覺的地方就是一個簡易毛坯房,就像豬圈一樣,吃喝拉撒都在裏面。
沒有空調暖氣,居住環境極其惡劣。
在吃的方面,都是一些最為低劣的伙食,比如清水煮麪條、水煮冬瓜等,吃完飯後又被監工壓着回去做工,每天在悶熱的窯廠裏面連續從事着7、8個小時的體力活。
有些智障人士工作5、6年,卻一分工資都拿不到。
説白了他們就跟美洲黑奴差不多,所以他們也被稱為窯廠奴工。
後來這件事是怎麼被發現的呢?
由於某些窯廠“安保”措施不太好,使得有一些奴工逃了出來。
他們在警察、好心路人的幫助下,回到了家中。家人看到已經走丟一年多的兒子突然回來,喜出望外。
然而再一看,發現他渾身上下都是傷痕,比如説耳朵滲血、手指頭、腳趾頭骨折、後背有被鞭打的痕跡、頭上流膿,像是被鈍器打過。

因為遭受過殘忍虐待,他們看到生人就有了一種條件反射性的恐懼,問話也是渾渾噩噩半天答不上來。
這類事情多了之後,大家逐漸意識到,這些智障人士,極有可能是被被拐賣到窯廠裏,當了奴工。
不僅如此,圍繞着這些智障奴工,還形成了一條帶血的產業鏈。
首先當地司機或者商販充當代理人,留意街上無家可歸的智障人士。如果碰到合適的,他們會以介紹工作為由把他們騙走,然後賣給窯廠包工頭。
合適與否,得看智障人士的具體情況。太老的不行、殘疾的不行,手腳不靈活的不行,太憨的也不行。
最理想的奴工,是那種既有強壯的體力,而智商又不高的,他們不會想到反抗,同時幹活也比較多。
代理人賣掉智障人士,出價在每個人200-500不等,簡直比一頭牲口還要便宜。
包工頭買到這幫人後,會再轉手一波,把它們出租或者賣給窯廠。
之前有新聞指出,這些租到窯廠的智障人士,每人每月就能給包工頭賺到1500,而如果手上有10個人,那麼一個月就能淨賺1萬5000。
而窯廠老闆,則進一步盤剝,給他們最低的生活保障,然後讓他們開足馬力幹活,賺取更多的收益。
當時誰也沒想到,在文明程度如此之高的社會,還藏着這種讓人背脊發涼的罪惡。

02
這裏就要説到一個記者,崔松旺。
崔松旺2007年於天津體育學院畢業後,進入河南電視台都市頻道工作。
2011年,電視台收到不少相關投訴,於是他們想到要做一期窯廠奴工的節目。
不過當時最大的問題是,他們非常缺乏第一手材料。
比如説這些受害者都是些智障人士,在採訪的時候,很多人口齒不清,就連自己住在哪裏,在窯廠裏面幹什麼工作都答不上來。
其次,窯廠當然知道自己從事的是非法勾當,所以面對外界總是諱莫如深,對兩類人防範最深,一是警察,二是記者。
如果有人過來窯廠調查,窯廠老闆會事先把奴工運送到隱秘地點,接着又招一批臨時工,裝作正常生產的樣子。
在他們的層層防範下一般人難以接近。
電視台把目標放在駐馬店的一家黑窯廠,為了能打入內部,他們策劃了非常多的方法。
比如説他們假裝是買磚的農民,想要到窯廠參觀;又或者是偽裝成為一個逃避警察追捕的犯人,甘願來窯廠當黑工。。
而這些伎倆最後通通都被包工頭識破。
最後不得已,崔松旺想到了一個辦法,那就是假裝成為一個智障人士,打入敵人內部。
不過這個提議,遭到了大家的極力反對,“之前去暗訪的人,在窯廠被活活打死的都有。”
但是他力排眾議,最終得以推行這個計劃。
03
假裝智障,是一門很深的學問。
崔松旺花心思好好打扮了一番,蓬頭垢臉出現在了駐馬店火車站附近。
他揹着個破包,穿着也顯得破破爛爛,在車站、賓館、餐廳等人流量大的地方來回轉悠。
每隔半小時他就去門店討要吃的,吃完在路邊倒頭就睡,看到大街上丟棄的煙頭,也像個傻子似的,拿起來就抽。

終於,第二天下午,有個人主動向他搭話:“有活幹不幹啊?”“幹,幹啊”“窯廠幹不幹?”“給錢就幹。”
本來崔松旺都做好了被帶走的準備,沒想到這個男子問完話後,就轉身離去了。
第三天,又有一個人過來向他搭話。崔松旺故意表現得吞吞吐吐,答非所問。
“你上哪去啊,坐車不坐”
“有煙沒”
“坐車吧”
“給根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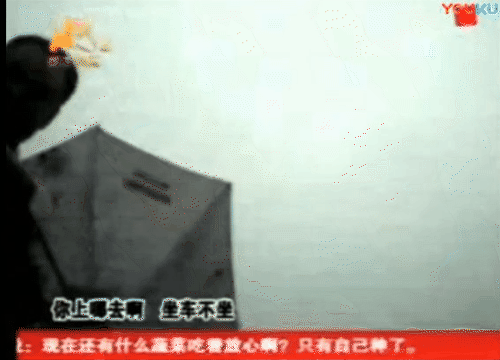
而這個男子問完話後,也轉身離開了。
又過了一天,他當時假裝在草叢邊睡覺,有個人把他踢醒,並把他拉上了出租車。崔松旺定睛一看,這人正是第一次主動向他搭話那個男人。
最後,崔松旺如願以償被賣進了窯廠。代理人要價500,可能崔松旺也沒想到自己竟然會這麼便宜。

根據他事後描述,他在進廠的時候出現了很多困難。他身上有幾套拍攝設備,在搜身的時候為了避免被發現,於是乎他假裝摔倒,順勢把設備丟到了一個角落。
當時他帶了一個小手機,藏在了鞋襪裏。窯廠搜身檢查的時候,他就裝傻擤了一把鼻涕抹到鞋子上,這才矇混過關。
整個過程非常考驗他隨機應變的能力。
下午六點多進入窯廠,在簡單吃了一波煮冬瓜後,監工立馬趕他去開工,稍有怠慢就是一頓毒打。
當時他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這種鬼地方,進來難,出來更難。
那天晚上,他進行了兩次逃跑的嘗試。一次是假裝上廁所,不過監工盯梢很緊,不讓他上廁所,只能原地解決。
就這樣,他一直工作到了大半夜,由於口渴難忍,他苦苦哀求監工讓他喝水。他趁着喝水的空當,翻過伙房的圍牆逃了出來。
在整個逃跑的過程中,他可以説使出了吃奶的勁。如果窯廠發現他已經逃跑,被抓回去的話,後果不堪設想。
在這一片漆黑的晚上,他先是奔過一片玉米地,最後來到一條河邊,他趴在地上,等待夥伴的接應。
此時公路又傳來陣陣摩托車的轟鳴,不出意外這些都是窯廠派來的車隊。
這時候就變成了一個夥伴與窯廠的時間賽跑遊戲,一邊是自由,一邊是牢籠,一邊是天堂,一邊是地獄。
最後夥伴找到他的時候,已經是凌晨。由於過於緊張,被夥伴從地上拉起來的瞬間,崔松旺忍不住顫慄哭了起來。

後來,電視台根據崔松旺的珍貴素材製成了紀錄片《智障奴工》。
隨後崔松旺又協助警方,解救窯廠30餘名智障奴工,磚窯老闆以及招募人被逮捕,最高被判刑6年。
由於紀錄片的曝光,使得越來越多的人瞭解到這一罪惡的存在,黑窯廠開始日漸式微。
04
崔松旺這個調查,轉眼間已經過了10年。這10年間,新聞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們有了更高清更隱蔽的微型拍攝設備,有了更好的調查手段。但是新聞質量跟以前比起來,卻跟個陽痿似的。
要是放現在,如果同樣出一期《智障奴工》節目,還會像崔松旺這麼調查嗎?我覺得已經不太可能了。
不需要採訪,裝模作樣寫一通文案,隨後在網上隨便找一段素材進行剪輯,非常簡單就能完成一個節目的製作。
然而這種節目,無論是真實性又或者是嚴謹性,跟之前都是沒法比的。
所以,崔松旺的卧底調查,顯得難能可貴,在之前如此,在現在更是如此。
向敬業的調查記者致敬,pe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