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把離婚自由還給她_風聞
柳飘飘了吗-柳飘飘了吗官方账号-2021-05-19 08:38
作者 | 柳飄飄
本文由公眾號「柳飄飄了嗎」(ID:DSliupiaopiao)原創
馬上快520了。
有另一半的,開開心心過節,也是件高興事。
可有些地區的婚姻登記處卻過於熱心,直接宣佈當天暫停受理離婚登記。
這可好,一石激起千層浪。
網上對“離婚自由”的討論,越演越熱。
最後,以兩地道歉撤回這一決定而結束。
“離婚自由”,註定是引起熱議的字眼。
它不僅涉及大眾對婚姻的自由權;在道德層面上,也揭開傳統婚姻觀念的複雜與隱痛。
而在這些紛紛攘攘的離婚話題裏,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農婦離婚。
尤其是,一名寫詩的農婦。
這一標籤,賦予這一普通的離婚事件,一點女性意識覺醒的味道。
最近,就有一個寫詩農婦,因為離婚被關注——
在短視頻平台寫詩的韓仕梅。
事情很簡單。
成名的韓仕梅,瞞着丈夫,和律師去縣法院立了起訴離婚案。
可老公和女兒都不同意。
考慮到女兒馬上高考,不想影響她學習,韓仕梅於是撤了訴。
但由於身份特殊,“準備離婚”和“離婚撤訴”這兩件事,卻使她陷入了輿論紛爭。
既有罵她:“寫詩迷失了自我”“性別對調就是陳世美”;
也有同情她:“生了娃就被捆綁住的只有女性”……
飄並不想就這些聲音,辯個對錯。
跳出話題之外,觸動飄的,反而是“寫詩”這件事。
寫詩,對一個普通的、忙於生存勞作的中年女性來説。
竟是一道進入她生活裂隙的光。
而藉由這道光,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她們的痛苦與掙扎。
誰説農婦就不能擁有詩性與浪漫。

去年4月26日,韓仕梅在快手上發佈了第一首詩。
不但有錯別字,有些字還是用拼音代替的。
詩下方的文字簡介中,她寫道:
女人一定要找一個你愛的人在(再)嫁
要不然這一輩子就瞎了
這首詩她覺得“悽慘悲涼”,更像歌詞。
本來沒抱什麼希望,沒想到發表後有人評論,還有人點贊。
這就像往她生活的這潭死水裏,投入一顆小石子。
從而發出聲音,盪出漣漪,激出更多回聲和共鳴。
韓仕梅自此寫詩入了迷。
她説“好像我上癮了”。
紀錄片裏,説着這句話的她,臉上泛起微笑,眼裏閃着光。
圖源|澎湃新聞,下同
通過寫詩,她在近50年的人生裏,第一次找到了快樂、成就與自我。
韓仕梅的前半生, 被一條條鎖鏈困住。
她一出生就差點被迷信的母親溺死在尿桶裏,僅僅因為脊背朝上,被説是不仁不孝之人。
她讀書時成績很好,總能拿到考試前三名。
可因為交不起每年18塊錢的學費,初二便輟了學,被母親領回家種地。
她三個姐姐都被賣給了村裏的老光棍,韓仕梅也逃不開相同的命運。
反抗三年,她還是被賣給了外村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
3000塊彩禮被母親拿來裝修老房子,韓仕梅只落下四身新衣服。

婆家情況並不好,為娶她欠了近5000塊錢。
公公婆婆有病,老公不踏實又好賭。
韓仕梅被迫成為家裏的頂樑柱,種地,做小工,修路打樁……啥活都幹,回家還要洗衣做飯。
還錢,蓋房,生兒育女,就是她全部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熬過去,疲憊,黯淡,無望。
像被拴在石磨上的驢,圍着卸不下的生活打轉,卻沒人可以交流。
村裏人只會誇這個三千塊買來的媳婦壯實、能幹、會持家。
和她生活了快30年的男人,只懂悶頭吃飯、幹活。
在她的詩裏,丈夫就像是一顆樹,一面牆。
沒有情感交流,不懂對方悲喜,更別提噓寒問暖,完全沒有被愛的感覺。
半生蹉跎,一肚子冤屈。
所以她開始寫詩,壓抑太久的痛苦、表達、思緒和愛慾,傾瀉而出。
詩成為她的哭牆。
從去年四月迄今,不算零星的動態,她一共發佈了168首自己寫的詩。
儘管這些詩配着中老人專用背景,不太押韻,也會有錯別字。
品起來,卻都那麼愁苦與淒涼。
濃縮的,是一代代底層婦女欲哭訴而無人聽的苦。
她寫:“為奴不問紅塵事,淚已流乾兩鬢霜。”
她寫:“雖是雙人枕,獨撐上下天。”
她還寫:“待我春年少,還我芳華可好。”
網友用詩,鼓勵她跳出去,“天地遼闊任君行,跳出三界無形中”。
她起初不敢,對:
金箍一戴已定型 必保西天去取經
上有公婆八十多 下有兒女要上學
怎能跳出三界外 樂得逍遙又自在
圖源|局外人視頻
在她看來,自己如同被戴上金箍的大聖,從五指山下跳出,仍有漫漫取經路要走。
韓仕梅的微信名,是XX家長。
她是母親、妻子、奶奶……
一個個身份,把自我壓得極小、極低。
被“囚禁”的日子裏,詩歌是她唯一的避難所。
可****成名後,她卻被困得更深。
村民視她為異類。親戚勸她要安分。
老公怕她跑,把她當囚犯,寸步不離地監視。
她想過離婚,最終還是認了命,繼續守着家和沒有感情的丈夫。
我一輩子 一肚子委屈一肚子冤
不就是為了女兒 為了娃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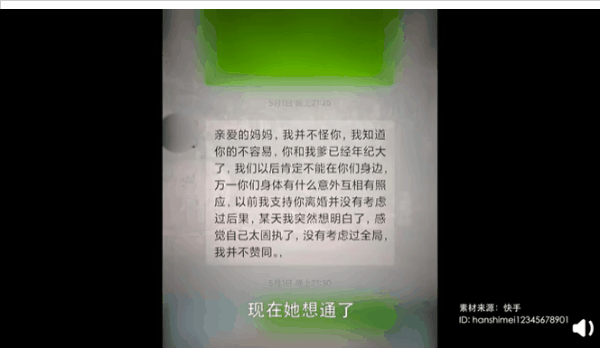
韓仕梅的詩稱不上多好。
但她詩裏的真誠,卻讓人看到了活在陰影裏的農村婦女,有多昂揚不屈的生命力。
詩歌為她沉悶封閉的生活,打開一個縫隙。
她在《為你讀詩》的邀約活動下面留言:
我在生死的邊緣線上遇到一縷縷曙光
那就是你們
讓我有了生的希望 愛你們
圖源|為你讀詩
飄一直記得紀錄片的結尾,她在牆上寫完詩,轉身大步走出鏡頭。
這首詩的詩名叫《覺醒》——
我已不在(再)沉睡 海浪將我擁起
我奮力走出霧霾 看到清晨的暖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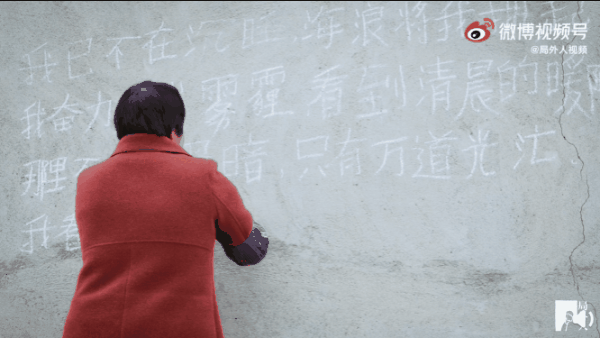
詩這個夥伴,雖然沒有拉她走出霧霾。
卻起碼,讓她看到了暖陽,讓她不再“懵懵懂懂地過了”。

詩歌對韓仕梅的影響,是開啓了她內心情感抒發的閥門。
成為她乏淡無味的生活中,一點精神慰藉。
相比起韓仕梅,另一個農婦詩人餘秀華,被詩歌影響的人生,改變得更為徹底。
寫詩,完全激發出餘秀華內心對情感的渴望與需求。
比起韓仕梅,餘秀華的身份還多了一重標籤:病人。
在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裏。
餘秀華走在鄉間小道上,步伐搖搖晃晃,臉部不自覺抽搐,是腦癱帶給她的影響。

疾病將她與常人區隔開,從落地那刻開始,將伴隨她終生。
在報道中,她是大家印象裏一夜走紅的鄉村腦癱詩人。
對此,餘秀華曾在博客裏寫下這樣一段話:
我身份的順序是這樣的:女人、農民、詩人。
這個順序永遠不會變,但如果你們在讀我詩歌的時候,忘記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將尊重你。
來源|餘秀華博客
詩人的靈魂被困在逃不掉的肉身。
她形容她和生活都是“狗”,只能“死皮賴臉地活着”。
唯有詩歌如枴杖,讓她理解到活着很重要。
因為它支撐着我一直往下走
如果沒有詩歌人生真的很空洞
當我寫詩的時候
我覺得詩歌讓我安靜下來
和韓仕梅一樣,餘秀華的婚姻,也與愛情無關。
結婚時,餘秀華才19歲,倒插門的丈夫尹世平大她12歲。
她媽媽覺得他身體可以,又“瞧得起我女兒”,那就可以同意。
在婚姻中,她和韓仕梅都過着“無愛”的生活。
走在泥路上,丈夫從來不會去接她們一下,扶她們一把。
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折射出的卻是丈夫的疏離、遲鈍、冷漠。
她成名之後要離婚,可丈夫並不理解,把這一切歸因於錢。
甚至附和他大哥的話,認為“女人就是個豬,只靠你會哄(就可以)”。
幾千年了,他們還是習慣把女人視為商品,當做物品。
用物質來衡量一切的價值。
恥於或不懂去談愛。
和這樣的人一起生活,對於敏感的餘秀華們,這種痛苦是加倍的,更猛烈也更熾熱。
所以餘秀華最終不顧家人的反對,選擇用自己掙來的金錢,結束了無藥可救的婚姻,也是必然的選擇。
紀錄片導演範儉説:“過去二十多年,餘秀華最想得到的就是愛情、由愛情產生的情慾。但都沒真正實現過。當她有能力掌控人生時,她就想去實現。”
而,“首先要解除不自由,就得離婚。”
離婚,是餘秀華不甘心被命運捉弄,走出的第一步。
她的今天,也許就是韓仕梅們的明天。
詩歌或許並不能徹底改變她們的命運。
餘秀華依然會為得不到的愛情而痛苦。
圖源|出圈
依然覺得孤獨。
依然會被她不喜歡的標籤捆綁和界定。
但詩歌讓她們與外面的世界交流,讓她們有了掌舵人生的力量。
同時,她們寫的詩歌也讓更多的“村外人”,學會平視廣袤的另一半。
沉默的大多數,開始發聲。
她們的浪漫、反叛、對愛和尊嚴的抗爭。
開始被越來越多人看見,並且懂得。

田埂裏的女詩人火了。
這一幕既讓人欣喜,細想起來又覺得悲涼。
我們總是以為,詩性和浪漫,只屬於一波小眾羣體。
年輕的,有才的,讀過很多書的。
卻忘了,不管是何種身份、年齡的女性,都擁有可以浪漫的權利,更可能會有追求詩意的內心。
許鞍華導演的《姨媽的後現代生活》裏,斯琴高娃飾演的姨媽就是市井小人物。
從老家鞍山逃開,一個人生活在上海。
她有虛榮和世俗的一面,亦有情調和優雅的一面。
家裏掛着字畫,閒來餵魚養鳥,小小的家裏滿是花草。
她會正宗的英式英語,會國畫,會京劇。
對潘知常(周潤發 飾)的好感,源於她在公園舞劍時,聽到他在唱京劇《鎖麟囊》。
之後被他吸引,也是因為這個男人談吐不凡,出口成章。
還有《立春》裏的王彩玲(蔣雯麗 飾)。
她在小縣城學校教授音樂。
每年的春天一來,心裏總是蠢蠢欲動,總覺得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夢想並未矇蔽住她的頭腦。
王彩玲清醒地知道,自己一貧如洗,又不好看。
除了一副好嗓子,就是個廢物。可她堅信憑自己的天賦和努力,能唱到北京,甚至唱到巴黎歌劇院去。

儘管這些底層小人物的文藝夢想最終破滅,可創作者,依然會把温柔的關懷投射到她們身上。
《立春》的故事來自真實人物。
結尾字幕是,“謹以此情此景獻給王彩玲”——
想象裏,穿着盛裝的王彩玲果然來到了巴黎歌劇院,在舞台上縱情獨唱。
而《姨媽的後現代生活裏》,素來有底層視角的許鞍華,在姨媽最落魄無助的時候,賦予她最夢幻的場景。
一輪巨大的滿月照亮她的臉和身體。
象徵着人間總有美好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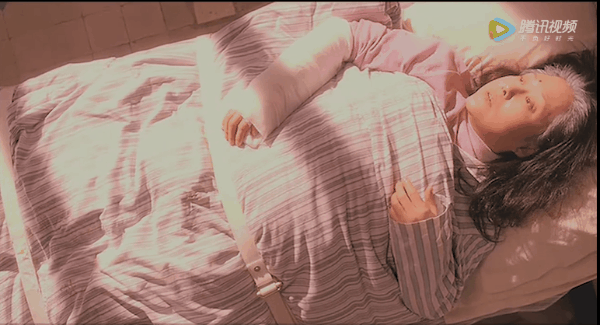
如今的信息時代,相比以前,有了更多跳板。
底層的普通女性尚可以藉此打破壁壘,追逐並實現自己的夢想。
越來越多農村媽媽,學會化妝,有了更好的工作,笑容自信又明亮。
圖源|《人物》
然而,滑稽的是,在國產影視劇裏,這樣豐富又鮮活的普通女性形象,卻消失太久了。
前段時間毛尖有個演講在網絡瘋傳。
她剖析了國產劇裏的一個套路:最講出身論。
“上個世紀,左翼電影千辛萬苦把清白的良心還給了底層,一百年不到,我們的影視劇又把心機和窮人,天真和富人進行了鏈接。”
而慕富慕強,審醜窮人的現象,也影響着現實劇裏,普通女性形象的塑造。
窮,意味着勢利。
從《歡樂頌》到《三十而已》,沒錢還要找條件好的,就是虛榮又拜金的“撈女”。
《三十而已》裏的王漫妮迷上了梁正賢,又為他是不婚主義者而苦惱。
她去尋求閨蜜意見,中產階級的顧佳諷刺她就是圖錢。
兩人吵架,觀眾紛紛站在顧佳這邊,誇她一針見血,説得好。
連劇裏的王漫妮都為顧佳辯護,感嘆“就是顧佳看穿了我,所以我才生氣”。
窮,代表着不講理。
國產劇裏的惡婆婆和怪媽媽,現在十個裏面有九個,掛着窮人的標籤。
《親愛的自己》裏劉芝芝的婆婆,從鄉下住進他們家。
她重男輕女,最信的就是“女子無用論”。
逼劉芝芝喝催子的中藥,取消孫女訓練班,為省錢甚至給孫女吃過期薯片……
騷操作一套接着一套,氣得觀眾牙根癢癢。
窮,也和愚蠢掛上鈎。
邏輯是,把窮歸因於短視、懶惰、貪婪等“窮病”,最後得出“活該”的結論。
《你是我的城池營壘》後半段,給男主邢克壘安排了一對貧窮姐妹花。
她們是邢克壘已故恩師沈隊長的女兒,花完撫卹金後,進城賴上了邢克壘。
姐姐不光想讓邢克壘幫她把傷腿治好,還要鳩佔鵲巢,拆散邢克壘的愛情。
邢克壘在時百般示弱,乘機要製造身體接觸;邢克壘不在時就作天作地。
而妹妹也想傍着他,享小姨子的威風。
卻是個十足的蠢人,靠姐姐指點使壞,反而經常損人不利己。
最後大鬧醫院,差點被保安帶走。
越來越固化和狹隘的國產影視劇裏,幾乎看不到底層女性正常生活的樣子。
郝胥黎的小説《美麗新世界》中,人被嚴密科學控制,出生前就被劃分為五個階層。
最高級的阿爾法,是天生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伽瑪以下的都是體力勞動者;
最低級的厄普西隆甚至“不需要有人類的智慧”。
誰能想到,科幻小説裏荒謬的出身和家庭決定論,居然到國產影視劇裏成了真。

十幾年前,我們還有愛好聽曲,追求浪漫的姨媽;也有夢想登上大舞台的小鎮女性王彩玲;
現實生活中,也有用詩歌改變生活的餘秀華們。
只要對普通底層女性多一些關注與關懷,就能明白:
再貧瘠的土壤上,也能孕育詩意和遠方。
可在國產劇裏,改變不了宿命的底層女性,已經不配擁有愛情、夢想和浪漫。
套在刻板印象裏的她們,真不真實沒人關心。
她們的精神世界,也無需照拂。
鍍金的天空中,再也容不下她們彎曲的倒影。
多可悲啊。
什麼時候,當窮不再變成製造焦慮,販賣負面情緒的工具。
或許才能看到這些女性,真正鮮活的面目,和豐富的人格。
更會被她們內心那一輪籠罩一生的圓月打動。
精神追求,從來都與財富、身份無關。
這麼簡單的道理,可惜在國產劇裏,卻被偏見淹沒太深,再也看不見。
本文由公眾號「柳飄飄了嗎」(ID:DSliupiaopiao)原創,點擊閲讀往期精彩
https://mp.weixin.qq.com/s/AwRvL4qnXN0cPUd5XPoRY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