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殺了23年,他一回歸還是頂流_風聞
她刊-她刊官方账号-提供最潮流的时尚和娱乐资讯,陪你遇见最美的自己2021-06-28 08:11
作者| 她姐來源| 她刊
先講一件2016年的事。
有一個年輕人去濰坊出差。吃早飯的時候,他對面坐了位老大爺。
這位老大爺看着着實眼熟。他仔細瞅了瞅,把人認出來了。
年輕人順嘴便説了句台詞,「是你把鬼子引到這來的?」
老大爺竟也立刻回了句,「是老子我!」
那句台詞出自小品《主角與配角》,它於1990年登上春晚的舞台,表演者之一正是那位老大爺——
陳佩斯。
小品演完的第26年,其中的台詞變成了一句“暗號”。
年輕人説對了,人便對上了,尋到了。

知乎@水晶咕咾肉
又2年之後,在問答平台上,年輕人把遇見陳佩斯的經歷發了出來。
底下的回覆竟也像是一場大型的“對暗號”現場

知乎留言
網友們從《主角與配角》唸叨回《羊肉串》《胡椒麪》,又説到《警察與小偷》《王爺與郵差》……
離開主流鏡頭近30年,觀眾們沒忘了陳佩斯。
可若是去翻看陳佩斯的演藝經歷,你會覺得,沒忘了他,真的值!
他不糊弄觀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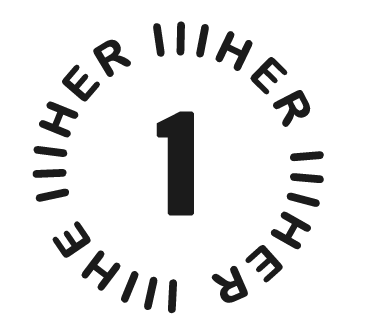
那個陳小二
在陳佩斯的作品裏,有一個人最愛“出現”。
不是朱時茂,而是“陳小二”。
陳小二,別名:二子。
普通人一個。
他幹過各種各樣的“職業”,沒什麼大成就。偶爾有點傻,大部分時候挺機靈。
初次登場,他是“夕照街”衚衕裏沉迷養鴿子的待業青年。
光着膀子,褲腿挽到膝蓋處,天天琢磨着怎麼加入信鴿協會。

《夕照街》
等他真正和觀眾們熟悉起來,還是在1984年,因為小品《吃麪條》。
他一蹲,一挑,盛了滿滿一碗麪條。

《吃麪條》
偶爾有一兩根麪條耷拉在碗沿上,他直接上手就給提溜起來,送進了嘴裏。
末了,嗦一下手指,還把沾了點口水、麪湯的手往衣服上一蹭,這才嬉皮笑臉地看向導演。
明明桶裏、碗裏都沒面,湯汁也沒真蹭到衣服上,可偏偏讓人覺得二子是真邋遢、不講究。
當時只顧着笑,尚且未覺出什麼。
如今才知道,他的動作裏有細節,更有生活。

《吃麪條》
這些細節和生活不是憑空出現的,靠的是一點點調整,一次次修改。
他和朱時茂演小品,台詞細節往往要改上2、3遍。
有時候朱時茂已經覺得改得差不多了,陳佩斯還是認為不夠好,就趿拉着布鞋繼續改。
這些觀察、努力、不糊弄積攢在一起,才有了被記住的作品和被看見的喜劇天賦。
她姐最愛的《警察與小偷》便是這樣磨出來的。
先看細節。
小品裏,小偷二子還是那個“反派”。他被同夥留在外面望風。
好不容易定下心來想點支煙,警察朱時茂來找他借火了。
你看他哆哆嗦嗦,下意識地便轉身想往旁邊溜,半個眼神不敢往朱時茂那邊瞟。
可就是這不敢直視,才最是畫龍點睛。

《警察與小偷》
《演員請就位2》裏,辣目洋子演《小偷家族》,人物表現、整體效果都很好。
李誠儒誇獎之後,唯獨提了一點小建議,説的便是這個“不敢直視”。
「基本上犯罪嫌疑人是很少用眼睛直視警察的。」

《演員請就位2》
再看結構。
第一重,小偷二子假扮警察,結果遇見了真警察,陷入窘境。
第二重,真假警察聊天,兩個人分明在説不同的事,結果你來我往,話恰到好處地接上了。
一個小偷把真警察“騙”過去了,“小人得志”。
第三重,對話過後,洋洋得意的二子陷入了自己是“真警察”的幻想,開始給路人指路,甚至逮小偷同夥。
最後兜頭一個收尾。“得志”是短暫的,小偷從幻想的美夢中醒來,鋃鐺入獄。
整個過程一氣呵成,情節層層遞進。
沒有關於正義、是非的説教感嘆。
可該懂的,觀眾都懂了。

《警察與小偷》
這是陳佩斯1991年的作品。
它不僅僅有細節。
也不僅僅會用語言去甩包袱,不過分鬧騰,也沒有強行悲情。
它有人物關係的變化,有值得細品的內涵,也有完整的結構和過程。
好的喜劇當如是。
它可以有結構套路,但那些結構套路像是搭建房屋的鋼筋,鋼筋巧妙地藏在內裏,並不粗糙。
我們曾經,是見過這樣的喜劇的。
《金牌喜劇班》
偶爾,陳佩斯也不再是“二子”。
他是頂着七彩莫西幹頭,帶着長項鍊的前搖滾圈製作人。
《96搖滾指南》
《96搖滾指南》至今仍是一些人心中的cult片神作
是腦筋不會急轉彎、愛闖禍的小學徒。

《修路燈》
是去富豪家做菜,但卻被各種沒見過的裝潢、食物迷了眼,變得侷促不安的廚師。
但他還是草根,是茫茫人海中的普通老百姓。
正如編劇史航曾説的,「(陳佩斯)其實為時代浪潮中的普通人們做了《起居注》。
他選擇陪着眾生在一起。」

《木匠廚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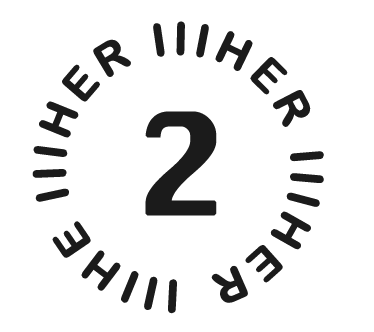
去“大道”上
陳佩斯覺得,其實是歷史把他推到了如今的位置。
「我們就是一個節點,一個契機。人還是普通的,只能説我是幸運的。」

《我的青銅時代》
陳佩斯第一次“非正式的登台”,是在他5、6歲的時候。
那次“登台”其實是一次誤打誤撞。
但也像是一次命中註定。
當時,陳佩斯的父親、演員陳強正和其他人一起排演話劇《日出》。
演到結尾,劇中人該唸完台詞,悄然“離世”了。
陳佩斯遠遠看見台上有光,便尋着光站到了舞台邊上。
不知從哪裏飛進來一隻蝴蝶,闖進了光源裏,然後又一直往前飛,飛到了舞台的一處鏡子上。
年幼的陳佩斯被光和蝴蝶吸引了,也追着它一路跑,跑到了鏡子旁,跑到了舞台上。
等他下了舞台,演員機智地救了場,陳佩斯仍然是捱了一頓揍。
《我的青銅時代》
彼時的陳佩斯沒想到自己會做演員,甚至他一度非常想轉行,哪怕去做和演藝相關的導演也行。
一方面,他覺得自己並不是做演員的料,
另一方面,他也曾親眼目睹,作為演員的父親遭受了何種的苦難。
20世紀60年代末,文革開始了。
演了許多反派角色的陳強,常常是穿着白衫出門,帶着一身血印回家。
左鄰右舍也開始“仇視”他們,仇視的理由顯得莫名其妙:
「如果你(陳強)不是壞人,你為什麼能把黃世仁這類反派演得那麼像呢?」

《楊瀾訪談錄》
還沒等陳佩斯緩過勁來,仔細思考未來。如火如荼的上山下鄉運動就把陳佩斯帶往了內蒙古建設兵團。
細胳膊細腿的陳佩斯和大家一樣扛起幾十塊磚,只能咬着牙晃晃悠悠地往前走,疼痛感順着骨頭往心裏頭鑽。
想要回城,陳佩斯沒有其他路可以走,只能去考表演。
4年之後,他考入八一電影製片廠,正式開啓了自己的演藝生涯。
而父親陳強又把他往喜劇道路上推了一把:
「中國老百姓苦了太久了。」
在那個肆意大笑不太被允許的年代,父子倆想讓觀眾笑起來,把快樂的權利還給老百姓。
「創造喜劇就是創造笑聲。」

《我的青銅時代》
後來的故事,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從1984年的《吃麪條》到1998年的《王爺與郵差》,14年間,陳佩斯上了11次春晚,讓觀眾們一次又一次地笑出聲來。

微博@大道文化
可漸漸地,他發覺那已經不再是一個適合創作的環境。
每一年,他要花出半年多的時間去創作、審查、修改,最終的呈現結果卻並不讓人滿意。
他開始主動告別春晚。
隔年,他發現央視下屬公司在販售他的小品的盜版光碟,卻沒有通知他,也沒有支付版權費。
他找負責人理論,得到的回應卻是,「我們就出了,你和朱時茂不也是我們捧起來的?」
這話聽完,兩人憤怒地把對方告上了法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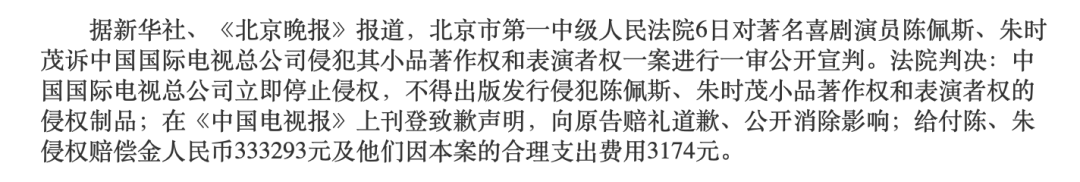
關於這件事,有人覺得陳佩斯傻,何必為了版權費跟電視台對着幹。
可陳佩斯覺得,那其實是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
他靠創作養活家庭,現在有人把存摺偷走了。

《楊瀾訪談錄》
「幾十年後,後人看我們今天是這麼生活的,他們會憤怒。他們會憤怒每一個接受強權的人。
這個世界應該是一個有規矩的世界,這樣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好,這不是一個成人世界的遊戲。」
有的人,權貴面前,提鞋遞水,想要活着,可以理解。
有的人,盡力爭取,仍需低頭,頗識時務,也算俊傑。
還有的人,如陳佩斯,他看見了,看清了,曾經拿到了,最後説放下便放下了。
他想給自己留一塊清淨地。

《易見》
離開春晚之後的那一年,他在妻子的勸説下,承包了一處荒山,在那裏種樹、種花,尋找生活的寄託。
在那之前,他為了創作、發行自己想要的作品,建立了一個公司,取名為“大道”。
“大道”之前,白茫茫一片,無比荒蕪,無道可走。
但它清清白白,乾乾淨淨,那條道又無比廣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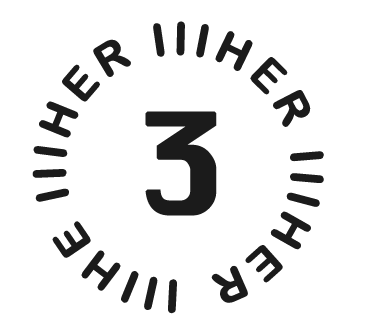
還有明天就行
陳佩斯又重新上路了。
很多人覺得他走得艱難,那種難應該和普通人的難不一樣。
拒絕、反抗看似輕巧,可它意味着一條重要的財路被毀了,沒準兒還會因此遭受些其它的打壓。
一段時間裏,陳佩斯確實從電視屏幕上消失了,似乎印證了人們的猜想。
沒辦法盡情在電視上演喜劇,他就拍電影,去大銀幕演。
為了有足夠的資金能拍完,為了電影能上映,他也着過急,舉過債,困難過。
「我沒資格叫難,我就是能撐過去,每次都能撐過去。」
《易見》
在他眼裏,那些社會新聞裏的主人公,甚至如今的年輕人都比他要難。
「現在的年輕人比我苦,畢了業等於失業,必須到處求職、找出路。我看起來很難,其實不難,我還有津貼,這幫孩子沒有這些。」
你看,這麼多年過去了,他還是和你我這樣的普通人呆在一起。
那些情感不用分辨,仍然是共通的。
所以他看得見,也感受得到普通小人物的生活,有精彩歡樂的,也有窘迫不堪的。

《孝子賢孫伺候着》
更重要的是,在荒山上,在大自然裏,他回到了一個無比自在的狀態。
那是他曾經苦苦追尋的。
是他在上山下鄉時,一邊吃着苦,一邊感受到的——那麼強烈的關於美的教育,和人性的光輝。
「雪地裏你踏上了第一個腳印,那種興奮。
走那種路不會害怕的,因為你知道沒有人會害你的。」

《我的青銅時代》
緩過勁來,他還是對喜劇有執念。
見過了大銀幕背後的一些“苟且”,他乾脆利落地又換了地方。
這次,換到了話劇舞台上。
彼時是2001年,話劇市場遠沒有今日紅火。
他便又去做了那個喜劇界趟路的人。
他照樣守規矩,乾乾淨淨地掙錢。
一些戲為了上座率高、觀看人數多,會拿出一部分贈票,在各種渠道上打點。
到了陳佩斯這裏,多大的官、某某總都不好使,別管是誰來看戲,都得自己花錢買票。
他仍然會有些“老派”地對學生講前輩們傳下來的話,「幕布是舞台的臉面,要敬畏舞台。」

《主角與配角》
而當年《主角與配角》裏的台詞,像是關於陳佩斯演藝生涯的一句讖言。
「你管得了我,你還管得了觀眾愛看誰嗎?」
他在話劇舞台的第一部試水作品《托兒》,首場上座率就高達95%,迄今為止演出了120餘場。
之後的《陽台》,被上海戲劇學院選為教學案例。
如今正在上演的《戲台》,豆瓣評分達到了9.1,評分僅次於《茶館》《譁變》這類經典劇目。

《戲台》
他寫好的地方,也寫不好的地方。
**他從背光的地方寫,**寫透了,便見到了光。
那裏有歡笑,有作品該有的結構,還有對過去,對現在,對文化藝術的思考。
影評人週黎明看完説,「多數國人對陳佩斯的印象停留在當年的春晚小品,哪知道,他早已超越逗笑的階段,成長為不折不扣的喜劇大師。」
微博@大道文化
有時候,他的老朋友們也勸他,「你畢竟也是60多歲的人了,個人精力一年不如一年。還有那麼多人搞喜劇,你也給自己放放假。」
每次聽見這話,陳佩斯都會跟着點頭,笑一笑,這些老朋友們也都知道,其實根本沒勸住。
他不知道自己能在舞台上演到那一天。
他總説,他沒想那麼多。
「就堅持到明天,還能再掙扎一天就行。
還有明天,就行**。**」

《為明天而堅持》

在採訪中,易立競問他,希望若干年後,人們怎麼評價陳佩斯。
他想都沒想,回了一句,「很多年之後,一定不記得(我)。」
「那個時候要是還有人記得這個名字,那可太糟糕了,那是後人的不幸。
我希望那個時候還會有比我更強,強十倍、百倍,而且有千百個這樣的人,讓人把我完全忘記了,那是最好的。」

從這個角度看,自他離開春晚的舞台,到如今的近30年。
我竟不知道,我們還記得他是幸事,還是不幸。
監製 / 她姐
作者 / 小怪獸
微博 / @她刊iii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