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職養老育兒記(52)兩個“我”:非不可,是不行_風聞
来者建强-仁者见智2021-07-14 09:38
很久以前,當歐洲傳教士第一次踏上澳洲大陸時,看到膚色黝黑的當地土著人生活在極為原始的狀態而感到異常驚訝。傳教士深入到圍成一圈的土著人當中開展工作,説道:“我並不像你們想象的那樣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話還沒説完,就引得土著人大笑不止。
待笑聲銷停後,傳教士接着説道:“你們愛怎麼笑就怎麼笑,但我要告訴你們,我是兩個人合二為一的,你們看到的我這個大身軀是一個我,裏面還有一個看不見的小我。”聽到這,一些土著人連連點頭:“是的,是的,我們也是兩個人,我們胸中也有一個小我。”
上面的故事出現在英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J.G.弗雷澤(1854年—1941年)的傳世鉅著《The Golden Bough》(《金枝》)中,“大我”、“小我”即指人的外在肉體與內在靈魂。而我認為,這個故事還向人們證實,文明與野蠻在肉體和靈魂方面無差別,若有差別,僅顯現為外在的“塗層”。
撇開靈與肉的神秘主義,我也點頭承認,我這個中等身軀裏也擠着兩個人,與上面微小的差別是,一開始,兩個“我”不分大小。

(一)
第一次告訴我有兩個“我”的這一“神奇”的事實的,不是弗雷澤先生,而是眼睛雪亮的我的小學同學們。
小學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歡樂的時期,能夠和同學們玩在一起,特別是我不戴眼鏡也不戴有色的性別眼鏡,能夠深入女同學當中與她們打成一片。在那個男女同學之間保留着“三八線”還有“授受不親”遺風的1980年代,作為男同學的我和女同學們打成一片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是,可以簡單地説,在外部條件上,要和女同學打成一片只須擅長一些女同學的玩藝。
那個時候,廣大的孩子既沒有課外興趣或特長培訓班,也沒有像現在可以輕鬆買到這麼多的玩具,大家的玩藝兒大多數是自己動手製作的。
打彈弓、打彈珠、打陀螺、打火槍、打煙盒紙牌等,是男同學的玩藝;跳皮筋、綁手帕、抓骰子、踢毽子、織毛線等,是女同學的玩藝。
男同學的玩藝我自然都會,女同學的玩藝,我也樣樣精通。
男孩女孩們各自的玩藝對我來説幾乎沒有分水嶺。直到今天,偶遇昔日的小學女同學,她們除了記得我跟她們一起玩的風采別的什麼都不記得了,“我們一直慚愧,女孩子玩的東西怎麼就玩不過你了?”説這些話時,她們的神情裏不見了羞澀,但仍不失可愛。
確確實實,跳皮筋,十有八九的女同學比不過我;綁手帕,十有八九的女同學贏不了我;抓骰子,十有八九的女同學快不過我;織毛衣,十有八九的女同學巧不過我。
我簡直無所不能,於是,同學們贈我一枚雅號“大姑娘”。後來,也有同學改口稱我“賈寶玉”,那是一位早年就博覽過羣書的女同學。
不過,牙尖嘴利的女同學秉性難移。前兩年,一位女同學從杭州過來順道往家看望我,她屁股剛坐下,就嘖嘖地感嘆起來:“你現在也變成一個小老頭了。”女同學被辣了眼睛,我真是很抱歉,歲月何曾饒了我。
當年,雅號為我塗了一層油漆似的,讓我閃閃發亮,成為浙中盆地裏一個大型國營農場子弟學校的耀眼人物。同時,也像在我的身上貼了個標籤,走到哪都有認識或不認識的同學向我高呼。
每天被同學喊作“大姑娘”,使我切身地感到自己小小的身軀裏真的有兩個人。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既來之則安之。我學會平靜地接受,努力地對兩個“我”一視同仁。唯一作了一點區分是,讓其中一個繼續去和男同學扎堆搗蛋,刷刷我壞壞的存在感;讓另一個繼續與女同學好好玩耍,保持我的超人魅力不掉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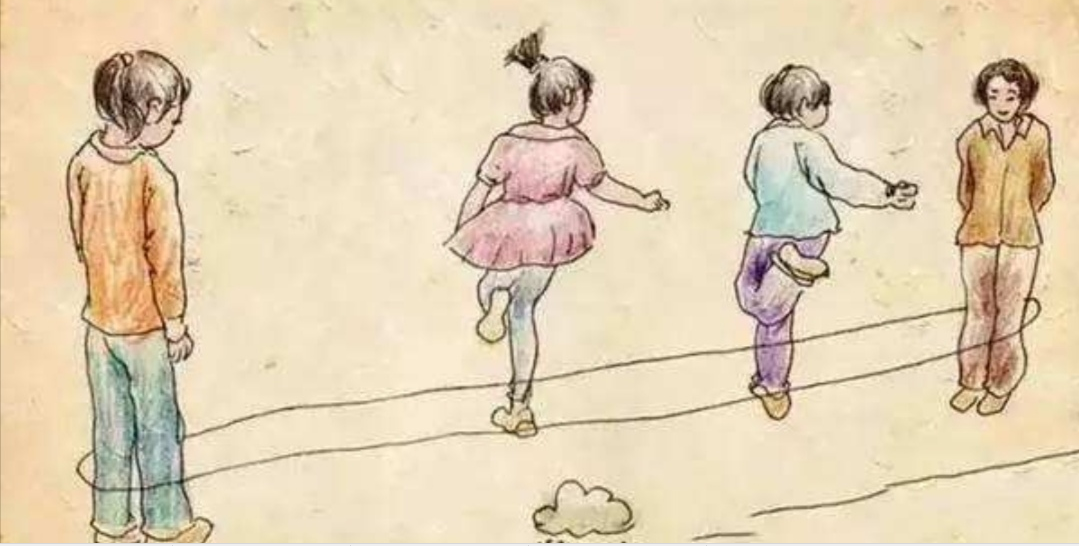
把兩條戰線上得來的成果對比一下發現,口頭禪“男孩越壞,越像男人”、“男孩不壞,女人不愛”,並非是女孩不可捉摸的小心思,可能僅僅是男孩朦朧的性幻想。
這樣歡樂的時光從小學三年級開始,直到臨近中考的初中三年級才被迫宣告結束,接下來,大家沒空也沒心思再玩了。直到十年後,赴廈大讀研究生,一顆愛玩的心面朝大海之時再度春暖花開。
如今仔細想想,我温柔細膩的一面在上小學之初就顯露出了馬腳。
記得,一放假,我匆匆做完作業就往隔壁鄉鎮的外婆家跑,路過熱鬧的鎮上,我通常會被各種售賣小首飾的攤鋪子所吸引,摸一摸口袋裏的銀子,然後挑選幾件諸如戒子、耳環、項鍊之類的小東西送給舅舅家的表姐和表妹,有時表弟也會收到這樣的禮物。
(二)
兩個“我”誰也不欺負誰快樂地成長着。然後,第一次讓我感受到兩個“我”合二為一的,是我的母親。
大概是1990年吧,母親要調去農場下屬效益最好的製藥廠上班了。這對我們家來説,是一件大喜事,意味着家庭的經濟條件將會有較大的改善。
好歸好,隨之而來一個新問題,是母親怎麼去上班。一開始,母親是走着去的。過去,農場有不下十個劃片分區,我家原在果木栽培片的住宅區,而製藥廠則在相距3公里的中心工商區。
新工作讓母親勁頭十足地走了兩個月。可是,一天上下班至少來回走兩趟,而且不論嚴寒酷暑、颳風下雨,久而久之走在路上就不見風光了。更何況,母親偏胖,天一熱,走得一身淋漓大汗,一進空調車間就有苦頭吃了。
解決問題不能給公家添麻煩,廠車不可能只為接送母親一個職工而拐個老大遠的彎,只能靠自己手腳並用。母親決定騎自行車上班,我為母親這一躋身當時時代先進行列的抉擇鼓掌。但是,母親還不會騎車。
不會騎,當然要學會騎。活人豈能被尿憋死。
學校與製藥廠毗鄰,我去上學先是靠走後來靠自行車。我騎自行車完全是摸爬摔滾中自學的,母親想學騎車的時候,我已具有3年的騎齡。母親的自學能力不行,腳踩縫紉機,針頭扎手指,手剪裁布料,剪刀尖又會插到腳背上,自學裁縫就曾讓年輕的母親吃盡苦頭。母親感嘆自己笨手笨腳。
我想母親是不善於操縱機械吧,據説到製藥廠上班,母親也是遠離操縱枱的。於是,我自告奮勇,當母親學習“自駕技術”的教練。
沒有一顆勇敢的心,是不可能擔當母親的教練。當時,我剛好平視半價火車票的刻度線,體重三四十公斤,而需要我手把手教練的“女大學生”光體重就達70公斤,加上質量不賴、份量不輕的車輛,對我儼然形成巨大挑戰。
母親事後回想起這段學車的經歷,目光總是包含歉意,她説:“那個時候學車,真是老鼠拖着貓上路啊。”
“老鼠拖着貓”,就是這幅景象連續一個半月,每天的傍晚時分至夜幕降臨之際,在我家附近的石子路面上演。母親連人帶車翻倒的時候,我也難免不被波及,我們母子倆常常是流汗又流血,精疲力盡地結束一天的練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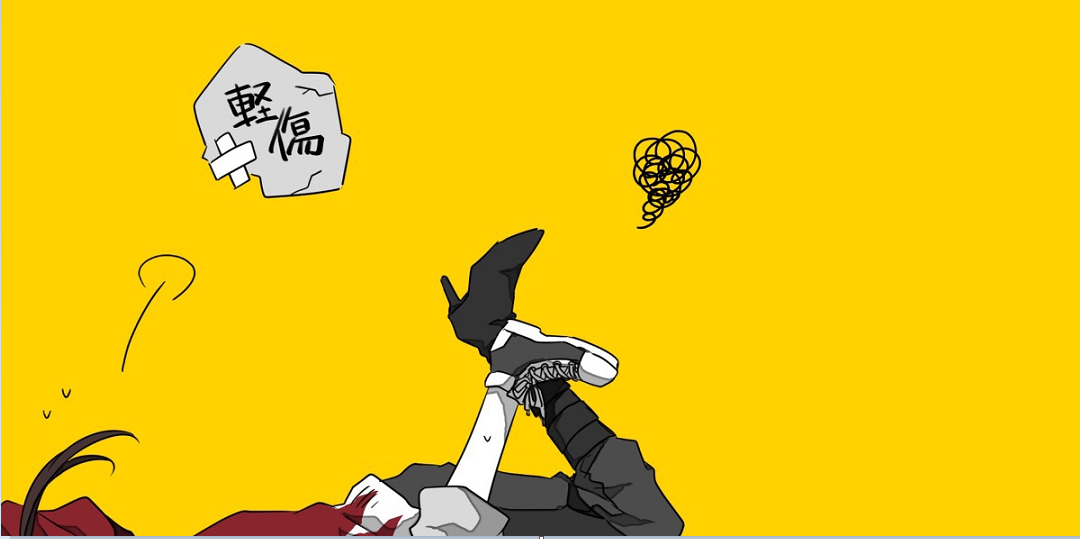
鄰居們撞見了,他們總會笑呵呵地説:“強強真能幹,把‘老牛’都教會了。”就這樣,我被升級為了能拉車的“小牛”。
現在,再回想起這段母親學車的往事,我真覺得有如神助,手把手教會母親騎車,不僅僅需要小小男子漢的力量(可是一個毛孩子能有多大的力量呢),更需要有類似女性的細緻耐心,就是需要兩個“我”合二為一,變作一條心,一股力,才能辦到並做好的。
我也覺察到,自從母親學會騎車,她很少再像以往那樣兇巴巴地對我,除了偶爾幾次火氣上來剎不住車。老佛爺的脾性大體上沒改,但微細處卻慢慢變得比我嬌氣了。
研究生畢業前夕的2004年暑假,我趁進京實習的機會租了房子,然後帶母親一起上去體驗皇城的生活。母親不習慣寬得走斷腿的馬路,兩週就回家了。中途,我在一個站台上買了幾個素餡包子充當午餐。我吃得津津有味,母親咬了一口卻把包子還給了我,然後面朝卧鋪閉目養神。多年之後,母親提起火車上的包子,驚訝地説:“那麼難吃,你怎麼能吃得下呢?”我呵呵地笑答:“我吃了三個,還把您剩的那一個也吃了。”接着,母親感嘆道:“我是不是越老越變修了啊!”呵呵,不知何時學會的矯情。
(三)
畢業後參加工作,我的人生開始起飛。漸漸的,兩個“我”失和了,外在的膨脹壓迫內在的靈魂。
2007年以來,房子、孩子接連降落到我的世界,等着我的供養。工作很忙,身子很累,在外地為奴的十餘年間,回老家與父母團聚次數屈指可數,母親請我不要惦記。
我驅使着兩個“我”合二為一,快馬加鞭,爭當新聞界裏的“打工皇帝”。追求功名利祿,靈魂陷在了俄羅斯套娃裏,自我掏空,杯套着杯。
忙碌奔波中,我分明能感到兩個“我”在大多數的時候是一堆晃晃悠悠的重影,魂不守舍,言不由衷,力不逮心,一不謹慎還弄得靈魂出竅而找不回來。

為了安定形神,2009年,我勒緊褲腰帶再買了一套現房,然後鼓動父母來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團聚。母親苦苦堅持了兩年,實在不習慣怎麼都聽不懂的異鄉方言,還是捲起鋪蓋打道回府了。事後,母親開玩笑説:“她在福州坐過兩年牢。”
2017年,年老體弱的父親出門不慎跌倒住院了,我也終於下定決心按下工作的暫停鍵,回老家陪伴父母。攜帶妻兒回老家的這一路,起初也是充滿艱辛,但我感到兩個“我”完全是牢不可破地合一的,因此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
回家陪父母養老的故事,在過去幾年來持續受到朋友們的關注,收到很多朋友的鼓勵。
前些年,閩西的一位企業高管聽説了我的事,他毫不掩飾對我的欽佩之意。我説,那是我剛好運氣,經濟條件許可了,也就可以放下工作,返鄉奉老。那位高管不認可我説的,他説現在像我這樣的很少,不是因為人們不可以這麼做,而根本是不能做到。
那位高管説到激動處,將此上升到了“做人良心”的高度。我從中受到一點啓發,兩個“我”,一個叫作“可不可”,一個叫作“行不行”。
在與那位高管愉快交談的時候,我們正走在紅色古田八個閃閃發光的經典大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標牌底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弱火能夠做到燎原,勢必要藉助一陣恰到好處的風。比如我返鄉奉老,算是那一點星火,但這陣風現在還沒有流行起來。
上週,一位在福建省委機關的朋友看到我的文章《尷尬的芒果》才得知我悄悄地回過福州,她專門來電囑咐下次一定要到辦公室喝茶一敍。通話期間,她再次談起我的事,説道:“我現在經常拿你的例子教育我們的那些弟弟妹妹,在外面錢是掙不完的,不如多出點時間常回家陪陪老孃。”
這位來自“媽祖故里”的大姐在電話那頭反覆地算賬:一個人在外從參加工作到成家立業站穩腳跟,再到六十歲退休,期間就算每個雙休日都能回家陪伴父母,加起來也才僅僅兩年時間。等到自己退了休,空閒了,卻已經“子欲養而親不在”。

“及時對父母盡孝心,太重要了!”
大姐她以身作則,忙着繁雜的公務,每兩週必定要抽出一個雙休日從省城趕回200公里外的老家陪伴老母親。
大姐對我的關懷和鼓舞,讓我感受到連接彼此的不是無形的電波而是伸手可觸的暖流。
過去,我們已經習慣把為社會發展而奮鬥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卻很少靜心思索社會發展歸結到底是人的發展這一根本課題。
今後,這方面如有更多的思考與實踐措施,或許能夠蔚然成風,人們的精神面貌將大為不同。
內人心情好的時候也會毫不吝嗇地讚美我。有一次,她含情脈脈地對我説:“老公,你真是我的‘寶藏男孩’。”
她之所以有此詩性,估計是我們當時正坐在一起觀看一檔名為“寶藏歌手”的電視節目。
恭維還是嫌肉麻的,兩個“我”一起打了個哆嗦,其中一個還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
我側過頭去,對着正站在電視機前方企圖打劫電視信號的小寶説:“求你別吵啦,還不學點好的,像爸爸一樣做個安靜的‘媽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