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閉關鎖國説給誰聽?--傳教士、天文曆法與清朝欽天監_風聞
文渊紫光-2021-07-17 11:42
大清閉關鎖國説給誰聽?------
傳教士、天文曆法與清朝欽天監
李景屏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明中葉以後,伴隨着地理大發現以及歐洲對印度洋新航路的開通,越來越多的基督教傳教士來到中國,在當時最先踏上中國領土的是耶穌會傳教士。
同基督教的其他教派相比,耶穌會士最大的特點就在於普遍具有淵博的學識,伴隨着耶穌會士的來華也就開始了中西學術文化的交流,而中西合璧的歷書的產生以及清王朝在鴉片戰爭前任命西方傳教士擔任欽天監監正的做法,都是中西文化相互交流所結出的耀眼奇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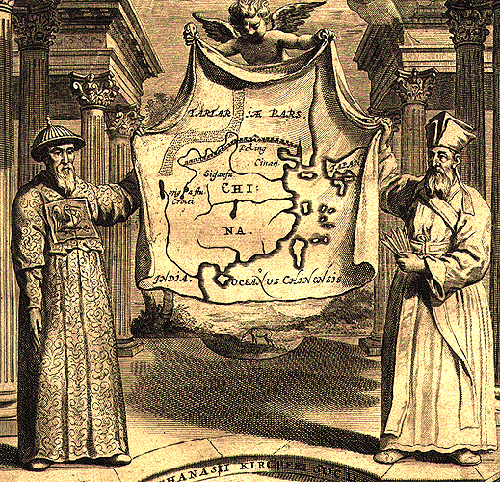
一、開路先鋒
第一個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是意大利人羅明堅(Michel Ruggieri),而在華傳教取得令人矚目成就的卻是利瑪竇(Matleo Bicci)。
利瑪竇在1582年(明萬曆十年)到達澳門後開始學習漢語,一年後到達廣東肇慶。利瑪竇意識到最好的傳教方法“莫若以學術收攬人心”,與人“所談者天文、歷算、地理等學”,“其學術既為華人所器重,所制之地圖復為華人羨賞”,“遂進兩製造天體儀與地球儀,並製造計時之日晷”。為了能融入中國社會,他率先給自己起了一箇中國名字;為了縮短兩種不同文化的差異,“特意換上和尚的袈裟,自稱來自佛祖所在地‘天竺’(即印度,傳教士來華途中的確經過印度,此言亦不為虛誑),並在教堂門口懸掛起‘仙花寺’的橫匾;為了吸引入們光顧‘仙花寺7,還在‘寺內’陳列自鳴鐘、渾天儀、三稜鏡以及世界地圖等來自歐洲的稀罕之物”;
為了同士大夫交往,這位洋和尚又脱下袈裟,換上儒服。
利瑪竇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嚮明朝的政治中心——北京進發,適逢傳教士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攜帶大小自鳴鐘、鏡子、手琴等物品抵達南京,利瑪竇遂與龐迪我攜帶上述物品從南京啓程,並於1601年抵達北京。享有萬乘之尊的萬曆皇帝,對於自鳴鐘一類的貢品愛不釋手,由於當時的北京“無入能修理自鳴鐘”,兩位傳教士便被留在京師,萬曆帝把北京南城宣武門一帶的房屋、土地賜給利瑪竇作為居住與傳教的場所。
利瑪竇很快就發現了中國傳統天學思維。
自從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以後,“天人合一”就成為官方的統治思想,所謂“天人合一”就是強調“天意”與“人事”的和諧、統一。這種統一,一方面表明君主受命於天,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天人感應”——“上天”對“人事”的干預,即“天象示警”,以及君主通過“省改”挽回“天意”。“天”己經不是純粹的自然天體,而是指一種神秘的“天意”,強調“天意”與“人事”的統一。用董仲舒的話來説就是:“天亦喜怒之氣、哀樂之心”,“國家將有失敗之道,而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省改,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倘不知變,而敗傷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為了體現天道與人事的和諧,歷代中國統治者特別需要一份準確無誤的歷書,以表明自己的統治受命於天,一旦曆書上關於天象的預測與實際情況不符,必然會認為是“天象示警”而引起恐慌。因而各朝各代都要對曆書不斷地進行修改,以期與天象相符。儘管中國的歷法屢屢修訂,但曆法的不斷完善實際是有賴於自然科學整體水平的提高,而這恰恰是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所不能提供的。
明代所實行的“大統歷”是在元代“授時歷”的基礎上制定的,到明成化年間後修訂後“交食往往不驗,議改歷者紛紛”。利瑪竇在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就呼籲羅馬教皇“火速派遣天文學家、懂得歷算的人到北京來”。天文曆法將溝通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使西方萬能的上帝與中國承天受運的皇權握手言和,“若無天文,則並傳教之事亦無矣”。為傳教打頭陣的,就是同曆法有着直接關係的天文、歷算。
明清之際來華的傳教士熊三拔、龐迪我、鄧玉函、羅雅谷、利類思、安文思等都精通曆算,龐迪我、熊三拔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就成為修歷的人選,只是因明內部阻力大修歷未能付諸實施。但熊三拔不僅同徐光啓合作把《行星説》翻譯成漢文,還把在歐洲、印度所測日食同在中國的預測進行比較;龐迪我也測算過朔望。而在四川I傳教的利類思、安文思,在張獻忠佔領四川后被俘獲,因精通天文不僅保住了性命,還奉命製造“天體儀”。

二、任職欽天監的逆向反饋
由於西方傳教士在一定程度上對“天人合一”的儒學體系進行了補充,入主中原的清朝統治者才能允許耶穌會士的繼續存在。繼明而立的清王朝要用傳教士修訂的歷書,來證明自己定鼎北京是承天受運。攝政王多爾袞還以順治皇帝的名義任命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令其“掌治術,數典曆象、日月、星辰,宿離不貸”。儘管欽天監監正僅官居五品,在權貴雲聚的京城也算不上顯赫,但任命西方傳教士擔任欽天監監正在中國歷史上畢竟是空前的。而且,這一任命也反映出在清初的20餘年,互補一直是中西之間文化交流的主流。
清代欽天監下設四個科,分別是時憲科、天文科、漏刻科及回回科。
時憲科“掌度驗歲差,以均節氣,制時憲書”。時憲科相當明末成立的“歷局”,而其與“歷局’’的區別就在於該機構不是特設,隸屬於欽天監;時憲書就是曆書。
天文科‘‘掌觀天象”,“率天文生登觀象台”進行實際觀察,“凡晴雨、風雷、雲霓、暈珥、流星、異星,匯錄冊簿”並立即向監正彙報,並由監正根據政務予以解釋。
漏刻科則負責為朝廷及皇家的“祭祀、朝會、營建覯吉日,辨禁忌”,“推算陰陽”以及為皇室成員的墓地佔卜風水、擇吉時下葬。相當今天的國家授時中心。
至於回回科,純粹為安排前明留下的回民天算家所設。
按照教規及耶穌會的規定,傳教士不能擔任教會以外的職務,但湯若望繼承了利瑪竇的“以學術”傳教的靈活路線。欽天監監正畢竟給傳教士提供了一個接觸清朝上層人物、展示自身在天文、歷算方面優勢的舞台。鑑於漏刻科的“淑吉日,辨禁忌”、“推算陰陽”等同基督教的信仰不符,湯若望在上任伊始就向清政府提出,只負責時憲科、天文科的事務,不負責漏刻科的事務(漏刻科直接向禮部彙報),也不過問回回科,以保證在觀測天象、制訂時憲書之餘有傳教的時間。在湯若望等傳教士的心中,傳教是第一位的,天文曆法不過是用來傳教的敲門磚;又由於清朝統治者永遠把制訂準確無誤的時憲書放在第一位,因而傳教士就不能扔掉手中的敲門磚。
伴隨着湯若望擔任欽天監監正,本來就存在的中西文化差異也就曰益凸顯出來。負責在華傳教的龍華民就堅持要嚴格遵守教規,傳教士必須遵守不在教外任職的誓言。他認為湯若望擔任欽天監監正、主持修訂曆法已經違禁、背叛自己的誓言,應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制裁。為此,龍華民聯絡十幾名傳教士聯名向羅馬教皇控告湯若望在華傳教違規。湯若望出任欽天監監正,首先面對的就是來自教會內部的阻撓。為了在華的傳教能得到清朝統治者的保護,湯若望也一再修書羅馬教皇進行申辯,強調自己出任欽天監監正“對於基督教在該國之傳佈與保護以及教會之尊嚴,均有重大關係”,在中國這樣一個君權至上的國家:“皇帝總理萬機,傳教自由系焉。脱意有不悦,發一語即足驅一切傳教士於國外。朝中諸耶穌會士(即指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筆者注)所行所為,無非在阻止此語之發出,而保障國內會士(指在中國境內的傳教士)傳教之自由”。湯若望同龍華民的這場筆墨官司,拉開了“禮儀之爭”的序幕。
經過十幾年的爭論,羅馬教皇終於認識到“湯若望擔任欽天監監正之職務,原懷有極大之圖謀,就是他要藉這個職權,漸次把欽天監完全置入基督教徒之手中,而使中國之曆書化為基督教之曆書。如果他定要將這個職權辭退,那麼呈帝對於北京有傳教士與否就決不會在意……而其結果必將大不利於傳教,教會之將受壓迫,自是意中事了。”
從形式上看,是否擔任欽天監監正、是否為清朝政府修訂曆書的問題解決了,但能否沿襲利瑪竇所開創的允許中國教徒保留祭祖、祭孑L習俗的做法,在來華傳教士中依然繼續爭論。爭論的實質就是,來華傳教士是否尊重所在國的文化背景、風俗習慣的問題。
以傳教士為欽天監監正以及傳教士的佈道,在中國的知識界不僅引起正向反饋——歸依基督、接受洗禮,也形成了逆向反饋——對上帝體系的質疑。儘管順治一直同湯若望保持誠摯的友誼,視“瑪法”為良師益友,但作為傳教士的湯若望卻始終未能引導順治接受洗禮。順治在十四年(1658年)為湯若望所在的南堂立碑,並親自撰寫碑文,一方面對“瑪法”在制定曆法方面的功績予以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明白表示:“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至於玄笈、貝文,所稱‘道德’、‘楞嚴’諸書,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況西洋之書、天主之教,朕素未覽閲,焉能知其説載!”。作為一箇中國皇帝,順治絕不可能皈依基督教。
湯若望在他的《回憶錄》中詳細記載了“怎樣努力以天然宗教與道德為基礎,而將基督教底道理建於其上,以不知不覺地引皇帝入教。”湯若望總是“把非常的自然現象解釋為上天(即“上帝”、“天主”筆者注)底警戒與警告”,順治卻對此提出了質疑:“如果天上星宿軌道,可以能預先測算時,那當然是顯然的了,他們的道路是必須要這樣行走的,所以,那預言的災禍(即天象示警),自然也是不可轉移的了”。這樣一來“天象示警”以及君主通過“省改”挽回“天意”也就行不通了。雖然儒學的“天人合一”需要西方天文曆法的支持,但傳教士把中國觀念的“天”解釋為天主教的“上帝”、“天主”,這是不可能被清朝統治者所接受的。
令湯若望最先感受到逆向反饋衝擊的,恰恰就是任命他擔任欽天監監正的順治。而把這種逆向反饋推向高潮的是楊光先。從順治十六年(1659)起,楊光先就針對湯若望、西方天算學及基督教教義陸續撰寫了《摘謬論》、《辟邪論》、《正國體呈》,並羅列湯若望新曆的所謂“十謬”,呼籲清朝統治者對傳教士要有所防範,指出傳教士以曆法為掩護,“呼朋引類,外集廣澳,內官帝掖”,對“國家有莫大的危險”。在楊光先看來,儘管傳教士帶來了西方鐘錶、望遠鏡等精緻物品,若“只愛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幹禁”就無異於“愛虎豹之文皮,而豢之卧榻之內”。
而為逆向反饋推波助瀾的卻是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他們為駁斥《辟邪論》所寫的介紹基督教的小冊子《天學真詮》宣稱:中國文化源於西方,中國傳説中的祖先伏羲是亞當的後裔,中國在很久以前也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國古代就崇拜上帝,那時稱作天或上帝”,對上帝的崇拜“在周朝即已亡佚,是利瑪竇等傳教士把它復興起來的”。這種把基督教神學凌駕儒學之上的歐洲中心論的觀點,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會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強烈的反感。
平心而論,撇開天文曆法而糾纏於天主教是不是邪教的論戰,是捨本求末。但傳教士中相當一部分人一涉及到宗教信仰就變得極其敏感與固執,這種近乎偏執、與史實不符的以歐洲中心論為基礎的宗教觀,只能為對手提供批駁的材料。楊光先在《不得已》中就對《天學真詮》的觀點予以批駁;利類思等又寫出《不得已辯》。如此辯來辯去,只能使論戰的雙方情緒化,到順治去世後這起唇槍舌箭的筆墨官司,便釀成一起教案,包括湯若望在內的傳教士在康熙三年(1664)七月二十日鋃鐺入獄,從而也失去了展示自身價值的舞台——在欽天監的任職。一年後楊光先出任欽天監監正,清朝統治者也第一次下達禁止傳教的命令。

三、天文歷算——解決湯若望教案的契機
楊光先可以取代湯若望的監正,卻解決不了傳統天算學在制訂曆法、預測日食、月食等方面所存在的問題。充分顯示出,傳教士所帶來的“天文、歷算”對於清朝統治者的確“不可須臾離也”(25)。
在湯若望等傳教士被關押期間,將發生一次日食。陷入牢獄之災的傳教士,把在刑部牢房預測這次日食作為爭取扭轉局面的一次難得的機遇。73歲高齡的湯若望,在入獄前就已經半身不遂,語言含混不清,且常常處於昏迷之中,便由湯若望的助手——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負責此次預測。雖然南懷仁只能通過牢房狹小的窗口觀測天象,但他還是完成了對此次日食的預測,指出:在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發生的日食,是一次日全食;北京地區將在下午3點26分開始見到這次日食。而楊光先及其欽天監的同僚卻一致認為是一次。僦如日食在北京出現的時間也比南懷仁的推測要早半個多小時。此次日食的發生的實際情況,與南懷仁的預測完全吻合。南懷仁抓住成功測試日食的機會,以湯若望的名義寫了一份申辯材料,重申自入華傳教以來,始終遵紀守法,從未組織過叛黨。
由於康熙祖母孝莊太后的干預,奄奄一息的湯若望在康熙四年四月初四(1665年5月18日)才被從刑部大獄抬出,但此案被平凡卻是在他去世後,而推動轉折契機出現的最直接動力還是天文歷算。
楊光先自接任欽天監監正以來,在預測日食、月食、均節氣、制定時憲書等方面接連出現問題:對康熙五年五月十六月食及六月初一日食的預測都與實際觀測的情況不符,制定的歷書也存在“金、水二星差錯”、候氣不應等問題。已經焦頭爛額的楊光先在在康熙五年二月就因“中氣不應”,而請求“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與之制器測候”。能制器測候的西洋人當時就羈留在北京,但楊光先卻堅持他自己提出的“寧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這也就難怪他打算採用“載在司馬遷《史記》而用法失傳”的“候氣之法”了。
已經親政的康熙不想倒退到“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的漢代,而是決心恢復順治時期所開創的以西洋天算制歷、以傳教士主持欽天監的局面。於是,南懷仁在康熙七年十二月疏劾楊光先主管的欽天監所造康熙八年曆書的種種差誤—康熙八年閏十二月,應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兩春分、兩秋分”。
康熙為此頒旨:“曆法關係重大,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確議具奏”。議政王大臣等經過實地觀驗向康熙彙報:經觀象台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與南懷仁所指諸款皆符”,並提出“應將康熙九年一應歷日交與南懷仁推算”。
康熙在八年(1669)三月十七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並令其對康熙八年曆書中的謬誤予以訂正,南懷仁取消了原曆書中在八年十二月設置閏月的安排,把閏月移到康熙九年二月,而按照原來的置閏,雨水將發生在正月二十九。
康熙的任命,意味着楊光先四年來把持欽天監局面的結束,西方天文歷算又重新取得支配地位。從表面上看,欽天監又恢復到楊光先發動湯若望教案之前,實際上這並非是一個簡單的輪迴。康熙堅持:議政王大臣會議必須對“楊光先前告湯若望時”,“以楊光先何處為是,據議準行;湯若望何處為非,輒議停止;及當日議停、今日議復之故”,予以確議。既然涉及到是非,就要辯出一個結果。
康熙要求議政王大臣必須對九十六刻歷日與歷代實行百刻歷日的孰優孰劣以及湯若望推算天象時該不該“遺漏紫炁”、“顛倒觜、參”、“顛倒羅計”進行確議。在國人的觀念中,“紫炁”附會帝王及聖賢出世的先兆,不是從純粹的天文學焦度去評判可否“遺漏紫燕”,而九十六刻歷日,又有別於歷代實行的百度刻目。因而議政王大臣會議就集中到這兩個核心問題討論,在覆奏中明確表示:九十六刻歷日“即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應將九十六刻歷日推行”;對於“無象推算、歷日並無用處”的“紫炁”,也明確表態道“應自康熙九年始將紫羆星不必造入”曆書。上述問題在四年前是向湯若望發難的子彈,現在卻由議政王大臣會議奏請實施,被平反的不僅是湯若望個人,還有西方的天文歷算。
經過這樣一番會議,採用西方天文歷算制歷以及在欽天監中任用傳教士的做法得到確認,因而起用南懷就不是偶一為之的權宜之策,而是一項具有延續性的做法。繼南懷仁之後掌管欽天監的有閔明我(Philippe-Marie Crimaldi)、龐嘉賓Gaspard Kastener(Ou Castner)、紀理安(Bernard—Kil ianStumpO、戴進賢(Igrannace Kogler)、劉松齡(Augustin de Hallerstein)、傅作霖(Felix de敝站ha)、高慎思(Joseph d’Espinha)、安國寧(Anore Rodrigues)、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e)、畢學源(Pires Pereiru)。
欽天監中的西方傳教士人數最多,除了監正,還有兩名監副以及得不到監副空缺而“入欽天監辦事”的人。自湯若望任監正以來,“監副二人亦常為西士”,就連南懷仁也是從擔任監副開始的。得到南懷仁推薦的閔明我在抵達北京後,協助監正南懷仁工作了十幾年,直到南懷仁去世才擔任監正。頗受康熙器重的紀理安在抵達北京十幾年後,才因監正龐嘉賓去世而得以補缺。在欽天監供職29年的戴進賢,剛到北京時連監副的空缺也沒有,康熙只能令其佐理歷政,直到6年後才就任監正。精通曆算的劉松齡在乾隆四年(1739)被召入京“佐戴進賢神甫治理歷算”,在乾隆十年(1746)戴進賢去世出任監正。而高慎思在到京後的10餘年,一直給監正劉松齡、監副傅作霖當助手,直到傅作霖升任左監副,高慎思才被任命為監副。安國寧到京後就到欽天監辦事,幹了16年才出任監副。而索德超在到北京後“治理歷算22年”,才得到出任監副的機會,在擔任12年的監副後才升為監正。至於沒有沒機會熬到監正、監副的更是大有人在,如在欽天監效力多年的安多、徐茂德、高嘉樂、鮑友管、金濟時等。
此外也有編制不在欽天監,卻在比較長的時間參與了欽天監工作的傳教士,精通音樂的徐日升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在閔明我擔任監正期間,當其奉命外出時康熙就令徐目升令與監副安多代司其職,最長的一次長達7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徐目升奉命出使俄國,由於種種原因直至康熙三十三年(1697)才回到北京,在此期間就由徐日升、安多負責欽天監的日常事務。
四、“禮儀之爭’-----嚴厲禁教的導火線
在是否允許中國教徒保留祭祖、祭孔等習俗的問題上,來華傳教士及羅馬教廷內部始終存在着意見分歧。康熙末年,來自羅馬的多羅(de Tournon)、嘉樂(Jean——Ambroise Mezzabarba)到中國傳達教皇命令:禁止中國教徒保留祭天、祭祖等習俗,而由此所釀發的就是:禁止傳教命令在康熙末年頒發。康熙四十四年(1705)多羅主教來華,下車伊始就讓在京的傳教士通知中國皇帝:“主教業以抵華,經教皇陛下賦予全權,前來各傳教區視察”。這樣一種居高臨下、藐視所在國主權的口吻,雖然可以被在京的傳教士給翻譯掉,然而特使所提出的:.要“在京派駐教代表”、“其身份是歐洲傳教之總會長”、其人選由羅馬教廷選派的要求遭到康熙的拒絕。接下來,特使又提出“想在北京買一所房子”。康熙則一語破的地指出:“此舉,旨在得寸進尺:得到房子後再要求派駐代表,派了代表再要求設總會長”。
而當康熙任命白晉作為欽差把送給教皇的禮品押送到羅馬時,多羅又節外生枝,要讓自己的隨從沙國安負責此事。對此,康熙長子胤裎就不客氣説道:“這個外國人多管什麼閒事!白晉神父確是我們的欽差,主教的侍從豈能與他相比?我們怎能選他擔任我們的使臣?”儘管康熙當着沙國安的面把國書交給了白晉,禮部也派人把禮品箱的鑰匙交給了白晉,但多羅仍“打算用自己的權威,甚至以越權的方式處理此事”,並強迫白晉把禮品箱的鑰匙交給自己。當多羅得知白晉在廣州向沙國安索要禮品箱的鑰匙後,立即給沙國安寫信,指使他“寧肯把禮品扔到海里,也不能把鑰匙交給白晉神父,還説他將囑咐白晉神父的上司張誠神父,讓他命令前者辭去(皇帝交辦)的差使。”多羅狂妄到企圖凌駕康熙命令之上的做法,自然要激怒康熙。
在傳教士看來,康熙的性格可以寬容柔軟的緞子,但卻會粉碎堅硬的鑽石,康熙毫不客氣地令多羅“出示國書和特使的信物”,以證明特使身份。多羅只“提供了寫自羅馬的信件:一封寫給北京主教先生,另一封是給科農主教先生的,以此證明特使身份。”但就連得到羅馬信件的兩位主教“都認為這還不足為憑”。因多羅未能提供羅馬教皇“充分授權”的證明,康熙派官員火速到廣州向白晉及沙國安宣佈命令:攜帶禮品返回北京。多羅則被押往澳門,交葡萄牙人監禁,直至其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死於澳門獄中。
安多神父在寄往歐洲的“備忘錄:中曾對多羅之行的失敗原因進行了剖析:“君主對多羅先生始終不失慷慨大方,而且後者離京的費用仍由宮廷負擔——正如他自廣州來京時一樣”;“多羅先生暴躁激烈,中國皇帝冷靜堅定”,“在中國,對君主稍有不恭便罪不可恕;那麼,屢屢抗旨不遵同時又缺乏殷勤,會導致何種後果呢?“‘多羅先生本人是談判失敗的唯一原因”。安多的分析不無道理,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羅馬教皇試圖凌駕一切世俗君主的野心以及把神權凌駕君權之上的思維方式。羅馬教廷所宣揚的“教皇絕對權力”、“一切世俗君主均須服從教皇”的神學體系,同中國兩千年來至高無上的君權發生激烈的碰撞。
神權凌駕君權之上的觀點,同中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勢同水火,中國統治者絕對不會容忍一個凌駕君權之上的神權的存在,也不會聽任羅馬教皇的發號施令。
在多羅北京之行失敗後,羅馬教皇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再次下達命令:禁止中國教徒保留祭祖習俗。為了避免“接受歸化便是向西方的霸權敞開了大門”,康熙在五十九年(1720年)頒佈禁止傳教的命令。曾負責辦理禁教的怡親王胤祥就曾對前來求情的馮秉正神父説道:“你們的事十分棘手……你們關於我們習俗的爭執對你們損害極大。要是我們到了歐洲也像你們在這裏一樣行事,你們該怎麼説?你們能忍受嗎?……我們不會強行留住你們任何人,不過也不允許任何人在這裏踐踏法律並竭力取消我們的習俗。”。
繼康熙之後的雍正皇帝,於雍正元年年底(1724年年初)再次重申禁令,明確規定:除了在京為清朝統治者服務的個別傳教士外,“餘俱安插澳門”,“天主教堂改為公所,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
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人都能意識到:康熙末年以後的禁教,具有明顯的政治因素。雍正在二年六月(1724年)召見北京的傳教士時就明確指出:
目前情況不同於利瑪竇來華時,當時傳教士“人數極少,簡直微不足道,你們的人和教堂也不是各省都有”,但現在已經“各地建起了教堂,你們的宗教迅速傳開”。
“如果朕派一隊和尚喇嘛到你們國家傳播他們的教義,你們該怎麼説呢?你們如何接待他們呢?”
“你們想讓所有中國人都成為基督徒,這是你們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這一點。但這種睹況下我們將變成什麼呢?變成你們國王的臣民。你們培養的基督徒只承認你們,若遇風吹草動,他們可能惟你們之命是從。朕知道目前還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但當成千上萬的船隻到來時就可能出亂子。”
供職內廷的汪達洪神父在給友人的信中客觀地談了自身的狀況及清朝統治者禁止傳教的原因:“我們在宮中幹活很安穩……我當着異教徒官員毫無顧忌地背誦日課經和其他禱文……皇帝和大臣承認我們的宗教是好的,如果説他們反對公開傳教而且不允許傳教士進入內地,那只因為政治原因,他們擔心我們藉口傳教而別有所圖。他們大致知道歐洲人對印度的征服,擔心在中國發生類似的事情。”
對中國統治者來説,上述擔心絕非杞人憂天。自明末清初以來,歐洲列強迅速擴張,“各殖民國家瘋狂地開闢和爭奪海外市場,殘酷地掠奪和剝削非洲、美洲和其他落後地區,他們的魔爪也伸向了印度、中國和遠東其他地區。他們一方面實行‘炮艦政策’,直接出兵侵佔掠奪各落後國家的領土和人民;同時又用軟的一手在思想形態方面實行滲透”。楊光先所説的“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於積薪之下”,也並非空穴來風。
康熙末年延至雍、乾時期禁教的最大特點,就是不涉及天文曆法以及欽天監的人事安排。在同多羅主教發生激烈的衝突後,康熙依然在五十七年傳諭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對於到達廣州的傳教士“若有各樣學問或行醫者,必着速送至京中”。精通天文的嚴嘉樂、戴進賢等都是在經康熙批准來京的(48)。而嘉樂在從羅馬到達廣州後,經兩廣總督請旨,他的十幾名隨從人員中的畫師兩人、雕刻師一人、能做自鳴鐘的一人、懂天文的一人、通音律的兩人、內科大夫一人、外科大夫一人、藥劑師一人——累計10人,均批准同嘉樂一起來京,而其餘5名無技能的傳教士令送往澳門。
而當乾隆四十年(1775)羅馬教廷取締耶穌會後,乾隆在四十六年五月初三特為此頒諭兩廣總督:“西洋人在京者漸少,着再傳諭巴延三,令其留心體察,如有該處人來粵,即行訪聞奏聞”。此後又再次傳諭廣東官員:如遇西洋人情願來京“即行奏聞,遣令赴京當差,勿為阻攔”。乾隆晚期以及嘉道時期的三位欽天監監正安國寧、索德超、畢學源,都是經廣東督撫請旨後送到北京的。
五、為秘密傳教而繼續供職欽天監
在欽天監供職的傳教士,始終把天文作為傳教的輔助手段。欽天監監正劉松齡,在乾隆十四年(1749)給兄長的書信中就坦然言道:“吾人之蒞此,不在推進改正天文圖表,顧為保障救護吾教,不得不假手於天文,因此吾人盡其所能為之”,因而“天文測驗時常有之……除日月食外,尚須測驗木星諸衞星之出沒,恆星、行星之受月食,與恆星比較所知行星之運行……”
乾隆十五年(1750)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ct)也曾直言不諱地指出:“在監治理歷算之傳教士,不編天文記錄”“僅將華員之推步審核改正而已”。
顯而易見,欽天監中的傳教士的主要心思不是治歷而是傳教。然而,清政府在康、雍之際已經下達禁止傳播天主教的命令,劉松齡的所謂“保障救護吾教”究竟還有多大的實際意義?換言之,已經被禁止傳教的傳教士為何還要留在北京的欽天監?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已經來華的傳教士——無論是供職京城的,還是分散在各省、躲過押送出境的,一直在秘密傳教,被押送到澳門的傳教士以及從歐淵’l抵達澳門的傳教士,也千方百計潛入內地秘密傳教。法國傳教士徐日生(Jean Baborier)在康熙五十年來華(1712),在江浙一帶傳教,教禁之後被押解到澳門。“日生謀入內地,乃矯為垂危之人”,令人準備一口棺材,“藏於其中,如是偷渡關津”,“發自佛山,逾梅嶺”,“所遭受之飢渴、寒熱、窒息種種困苦不待言也”。“至Tchong—chan(很可能是浙江象山,筆者注)”,“匿居於教民某所營之旅店中”,“天明後附舟至杭州,復由杭州至蘇州”。不久,徐日生又到常熟,“遍歷其傳教區,為303人受洗”,雍正十三年(1735)“經其授洗者352人”,乾隆五年(1741)僅8個月“經其受洗者572人”。“嗣後日生復秘赴浙江,繼續執行教務”。到乾隆十一年(1746)“江南有教民約六萬”。中國教區“副區長陳善策曾讚譽徐日生為江南傳教士中最勇敢最熱心之一人”。
為了躲避官府緝拿,到偏僻地區傳教的傳教士更是大有人在。法國傳教士胥孟德(Joseph Labbe)康熙末年抵華,在禁止傳教的大氣候下到湖北山區開闢傳教區,把當地劃為八個區,每個區設一名宣講教義之人,至雍正十二年(1734)該地已有教民600餘人,“教務目見發達”,到乾隆十一年(1746)教民已經超過6000。法國傳教士紐若翰(Jean.Sylain de Neuvialle),在乾隆五年(1740)來華後到湖北山區傳教(距離轂城70裏)。該地山勢險峻,幾乎與外界隔絕。為避免被官府發現,紐若翰“終日伏處草棚中,命可以信任之教友探訪消息來報。草棚附近有一森林,吏役搜捕時可以藏伏其中。”奧地利傳教士南懷仁(Godefi-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乾隆三年(1738)到達澳門,因“赴京治歷”得以順利進入內地,教會方面令其前望湖北傳教,僅四年時間秘密“勸化1700人入教”,為躲避搜捕,其居無定所,經常藏匿舟中,“服履如同鄉民”。乾隆四十三年(1778)南懷仁還到崇明島教區視察。而供職內廷的傳教士更是利用為皇帝服務的條件,秘密在京城及其周圍地區傳教。意大利外科醫生羅懷忠(Jean—Joseph da Costa)在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入耶穌會,康熙五十四年(1715)來華,以精通醫術奉召進京,並開一診所。他居住北京三十年,始終在治療疾病的同時宣講教義,“有時領病者赴諸神父所,俾受勸化,領洗入教”。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成為康熙御醫的法國傳教士安泰(Etienne Rousset)在行醫的同時傳教,當雍正明令禁教後,安泰在診所為教徒“舉行聖事”,“不為人覺”。在京負責教授八旗子弟拉丁語的法國傳教士宋君榮(Antoinne Gaubl)在從康熙六十年(1722)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37年裏,堅持對同他交往的王公大臣宣傳教義,並給內大臣趙昌及其家人洗禮。以精通音律供職內廷的德國傳教士魏繼晉(Florian Bahr)在到達北京後的三十多年,堅持去距離北京五天路程的寶坻縣秘密傳教、主持宗教儀式。至於擔任欽天監監正的戴進賢、傅作霖等儘管公務甚繁,依舊擔任教職,即使在嚴厲禁教期間依舊巡視教區。
秘密傳教一旦被告發、被各級官吏破獲,就不免發生教案。供職欽天監的輿地利(現在屬於斯洛文尼亞)傳教士劉松齡,在給友人的信中談到:“乾隆帝曾雲:‘北京西士(指在皇宮為皇帝服務的傳教士)功績甚偉,有益於國,然京外西士(指違禁在各省秘密傳教者),毫無功績可言。’揆帝之意,似欲留前者兩逐後者。”他已經從乾隆的態度,預感到嚴厲禁止秘密傳教的風暴即將來臨。
此後不久就發生了“教難”,乾隆十一年(1746)7月,福建巡撫周學健在福安縣破獲秘密傳教一案,他在給皇帝的奏摺中特別強調“西洋人精心計利,獨於行教中國一事,不惜巨費”,“中國民人一入其教,信奉終身不改”,僅福安一縣的教徒就多達2600人以上。周學健不僅逮捕費若望、德方濟格、施方濟格、白多錄、華若亞敬五名西方傳教士,而且力勸皇帝對違禁秘密傳教的西洋人“明正國典”。為此,乾隆密令地方官員大力查辦秘密傳教,再次重申:“如有天主教引誘男婦,聚眾誦經者,分別首從,按法懲治,其西洋人俱遞解廣東,勒限搭船回國。”
一年後(1747年1在江蘇傳教的意大利傳教士談方濟(Tristand’Attimis)、葡萄牙傳教士黃安多(Anotoin—Joseph Hemiques)被江蘇巡撫安寧逮捕,關進蘇州監獄。
乾隆十七年(1753年)馬朝柱在湖北與江南交界山區以開山燒炭為名聚眾謀逆被清政府破獲,但馬朝柱負案在逃。因彼等稱有西洋人相助,而被抓獲的馬朝柱親屬又供出一些頭目逃往四川峨眉山的西洋寨,湖北、江蘇、江西、四川等省遂成為緝拿馬朝柱的重點地區。因受此案牽連,秘密傳播天主教的西洋人也接連被抓。
乾隆十八年,葡萄牙神父郎亞瑟(Jseph Ataujo)、衞瑪諾(ViegasEmmanuel)、林若瑟(Joseph da Sylva)等五名傳教士在江南被捕,而且有800多名中國教徒及其家人遭到審訊。此後由於清查白蓮教,在陝西、四川也逮捕一些天主教徒與傳教士。
尤需一提的是發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一起牽連到在欽天監的秘密傳教的案件。該年九月底河南巡撫阿思哈奏道:本省桐柏縣的民人劉天祥、項得臣等傳播天主教被查獲。其中劉天祥原籍湖廣,祖上信奉天主教,乾隆十七年(1752)在馬朝柱一案後被禁止信奉天主教。與劉天祥同是天主教徒的有一個綽號為袁鬍子的人,居住京城天主教南堂,在欽天監中幹事,此人回湖北時隨身攜帶乾隆四年監正戴進賢給天主教會長的“諭單”以及“洋佛”、“齋單”,用以秘密傳教。乾隆遂令步軍統領衙門追查欽天監中的“袁鬍子”。欽天監滿監正不敢怠慢,立即表態:對於“為患最烈者莫過於基督教,當全面和永遠禁止”,並在欽天監內部清查“袁鬍子”,“恐長期供職欽天監的歐羅巴人引誘欽天監監士”而“秘密細查”,查出欽天監有二十二名監員是天主教徒,彼等“不以頂帶、袍子等以示其高貴之裝飾為榮,恬不知恥,信奉迷信之宗教”。違禁傳教案件的頻繁發生,就需要在京供職的傳教士憑藉同皇帝、官員有較為密切的交往予以斡旋。儘管在乾隆身邊從事繪畫、燒製琺琅彩、設計噴泉的傳教士都能承擔斡旋的使命,但皇帝的西洋情趣“時有變遷,有如季候,昔好音樂、噴泉,今好機械與建築”,惟有供職欽天監的傳教士能在清帝國有穩定的地位,不會因帝王個人“好尚”的改變而受到影響。戴進賢、傅作霖、劉松齡等都充分利用能見到皇帝的機會或力求減輕教案的震幅,或儘量能對鋃鐺入獄的傳教士援以一臂。
欽天監監正傅作霖不止一次對陷於教案的傳教士進行營救,當郎亞瑟等五名傳教士入獄後,傅作霖多次拜訪宰輔傅恆,使得五名傳教士避免像福建教案中的費若望、德方濟格、旖方濟格、自多錄、華若亞敬以及江蘇教案中的談方濟、黃安多被秘密處死的厄運。乾隆三十四年,在四川秘密傳教的艾若望(M.Glayot)被逮捕,傅作霖得知後立即給四川總督文綬寫信,而當傅作霖在乾隆四十二年奉命去金川繪製地圖時又特地拜訪總督,經過他的多方努力,已經在押九年的艾若望獲釋。而且艾若望不僅避免被押往澳門、廣州驅逐出境,還可以到宜賓繼續傳教。
而欽天監22名監員信奉天主教一案,由於監正劉松齡給朝廷上書、拜訪傅恆,並未形成大案。誠如傅恆對劉松齡等所分析的“這件事不會有壞結果”,他會“向皇帝轉告”。由於劉松齡的多方努力,當刑部第二次將開庭時只有族長接受訊問,其他成員無需到庭。最終的判決是:“剝奪官職,打扳子若干下”,以及再次重申禁止傳教。
乾隆在禁教問題上的態度很明朗:不禁止在內廷當差的傳教士信教,“僅命中國臣民不許入教而己”;然而,就職欽天監及在內廷當差的傳教士也明確表態道“臣等蓋為傳教而來”。這就使得雙方陷於一個循環往復的怪圈——朝廷需要傳教士當差卻禁止傳教,傳教士為了堅持秘密傳教或到宮廷當差,或就職欽天監,由於清政府需要在北京的傳教士為其服務,因而對秘密傳教的西洋人的處理也就比較低調、平和,嚴厲的懲罰最終還是落在信教的中國人特別是旗人身上。支撐這樣一個循環往復怪圈的就是天文曆法,傳教士不僅憑仗天文曆法到中國傳教、乃至堅持秘密傳教,而且開創了由傳教士就職欽天監監正的時代。
參考文獻:
(1)耶穌會士系天主教的一個修會。基督教在在流傳過程中逐漸形成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三個大的派別,只有天主教派承認羅馬教皇的權威地位。
(2)據《“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一書所載,截止到16世紀末耶穌會在歐洲所辦的學校有245所,笛卡爾、伏爾泰、狄羅德等思想家都曾受教於耶穌會學校。
(3)【法】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呂一民、沈堅、鄭德弟譯,上冊,中文版序,002頁,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4)參見:張國剛《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169頁—·17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5)李景屏:《“瑪法”湯若望》,《請初十大冤案》第198頁,東方出版社,1993串版。
(6)【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鈞譯),上冊,第38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7)《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8)“授時歷”取“敬授人時”意,該曆法由郭守敬等人所制訂,在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開始實施。“授時歷”以“弧矢割圓術”來進行黃經與赤經、赤緯的換算,以“招差法”推算太陽、月亮、行星的運行度數:一年定為365.2425天,把一年的1/24作為二十四節氣中的“一氣”,在沒有“中氣”的月份設置閏月。該曆法最大的特點是以實測代替以前曆法的推測。
(9) 《明史》,卷三十一,歷志。
(10)恩斯特·斯托莫:《通玄教師湯若望》(達素彬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1990年版
(11)《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80頁。
(12)“夏曆”,西周末年流傳的一種古歷。
(13)“太初曆”,在漢武帝太初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頒行,故名之。由鄧平等人創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歷法,規定一迴歸年為365.250162443日,將一日分為81分,也稱為“八十一分律歷”,第一次把二十四節氣編入曆法,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
(14)“大明曆”,祖沖之創制,因在南朝劉宋大明六年(462)年成書,故名之。經過測算一迴歸年為365.2428天,把以前的19年7閏改為391年144閏,推算的“交點月”為27.21223日與近代測出的27。2122日極為接近。
(15)“大衍曆”,唐代一行和尚創制,包括平朔望、平氣、七十二候以及日月星辰在天體中的運動位置、對日、月食的預測。
(16)“統天曆”,宋帶楊忠輔創制,規定一年為365.2425日,與現行公曆相同,只比地球繞太陽運行一週差26秒。
(17)《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三。
(18)《清史稿.職官志》。
(19)《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327頁。
(20)《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349頁。
(21)魏特:《湯若望傳》,第二冊,第299頁。
(22)《清世祖實錄》卷一O九。
(23)魏特:《湯若望傳》,第二冊,第451頁。
(24)魏特:《湯若望傳》,第二冊,第316頁。
(25)《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80頁
(26)《清聖祖實錄》卷十八。
(27)《清聖祖實錄》卷二十七。
(28)《清聖祖實錄》卷二十八。
(29)“紫炁”即紫氣,指祥瑞之光,附會帝王及聖賢出世的先兆。
(30)“觜”,即“觜宿”,二十八星宿之一,屬西方白虎七宿中第六宿的三顆星,即今獵户座的九、f 1、f2三星。“參”,即“參宿”,二十八星宿之一,屬西方白虎七宿中第七宿的七顆星,即今獵户座的昏e、d、a、K、B七星。
(31)“羅”即“羅喉”,印度古代天文學把黃道、白道的降交點稱為“羅喉”,因日食、月食多發生在黃道、白道的降交點附近,印度把“羅喉”稱為“食神”,認為“羅喉”能主宰福禍兇吉。“計”即“計都”,印度古代天文學把黃道、白道的升交點稱為“計都”。印度古代天文學把“羅喉”、“計都”同目、月及金星、木星、水星、火星一起稱為“九曜”,認為“九曜”支配人間福禍。上述觀點在唐代傳入我國。
(32)《清聖祖實錄》卷二十八。
(33)詳見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書目編補》,下冊,第760頁。
(34)《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934頁。
(35)(《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781頁)。
(36)《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VI,《耶穌會中國副省長安多神父寄往歐洲的備忘錄》,下卷,VI,123頁
(37)《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下卷,VI,135頁。
(38)《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下卷,VI,133頁。
(39)《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下卷,VI,145頁。
(40)《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上卷,中文版序,002頁。
(41)伯德萊:《清宮洋畫家》,耿舁譯,序言P9,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1月版。
(42)浙閩總督滿保在奏摺中就以天主教徒不供奉祖先、作禮拜時男女雜處而提出禁止天主教傳播。
(43)(《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上卷,II,327頁,《馮秉正神父致本會某神父的信》。
(44)《清世宗實錄》卷十四。
(45)《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上卷,II,338。
(46)《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下卷,V,212——213頁)
(47)《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編補》中譯本序言。
(4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廣東巡撫楊琳為西洋人嚴嘉樂等來粵請求來京效, 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初十。
(49)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兩廣總督楊琳等為西洋教化王使臣及其隨員送京事折,康熙五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5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兩廣總督舒常為護送西洋人羅廣祥等人入京效力事奏摺,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5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兩廣總督舒常為西洋人德天賜等進京效力事致軍機處諮文,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52)《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782頁
(53)錢德名1772年9月18信札,《關於中國之記錄》卷六,317頁,轉引自《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934頁。
(54)《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639_—“40頁。
(55)《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645頁
(56)《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750頁。
(57)《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793頁。
(58)《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651頁。
(59)《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678頁。
(60)《天主教流行中國考》354頁,轉引自《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691頁。
(61)《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第783.784頁。
(62)郭弼恩:《中國皇帝敕令史》,183頁。
(63)《清高宗實錄》卷二七五。
(64)(詳見《錢德明神父致本會德.拉.圖爾神父的信》,《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下卷,V,03D頁)
(65)據《史料旬刊》所載:最終查清袁鬍子真名為袁花青;而據當時在京的汪達洪神父給友人的信中記載:戴進賢派遣了一個叫“光鬍子”的人在湖北‘重建了基督教”。
(66)《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840頁
(67)《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傅作霖傳記載:傅作霖利用去金川繪製地圖營救在四川關押的傳教士名劉德勝(M。Gvlevo),傅作霖曾因此事在乾隆四十年(1776)給總督去信,在乾隆四十一年時特地在成都拜訪總督,在傅作霖的努力下關押九年的劉德勝才得釋放。其情節與艾若望(M.Glayot)相同,而在傅作霖轉中並未提到營救艾若望,劉德勝(M.Gvlevo)與艾若望(M,Glayot)似系一人。
(68)詳見《一位在華傳教±的信》、《艾若望先生對其在四蹦聲遭受迫害鵠敍述》《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下卷,VI,10卜107頁,167頁)
(69)(《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筒集》下卷,V,晁俊秀神父致某貴夫人信,153頁)
(70)《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6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