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他,我都替娛樂圈文盲臉紅_風聞
柳飘飘了吗-柳飘飘了吗官方账号-2021-07-23 13:55
作者 | 柳飄飄
本文由公眾號「柳飄飄了嗎」(ID:DSliupiaopiao)原創。
《覺醒年代》又上熱搜了。
這幾天河南的暴雨汛情,牽動着全國人民的心。
災情面前,不斷有普通人挺身而出。
素不相識的人,團結在一起,互援互助,盡力傳遞着自己的光與熱。


不由想起《覺醒年代》裏,辜鴻銘老先生的演講:
温良是一種力量
我們中國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
是因為我們完完全全
徹徹底底地生活在一種
心靈的生活裏
是這種力量催使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而續燃它的《覺醒年代》,亦自帶温良的餘力。
以至於,在劇完結幾個月後,它的片段、幕後、演員仍不停被人提及,念念不忘。
比如這個名字,在飄後台就不斷被cue——
扮演李大釗的張桐。
名字聽着生,但其實他演的劇,你都看過。
《歡天喜地七仙女》裏,跟橙兒組CP,戰鬥力滿格的黑鷹。
《亮劍》裏李雲龍最信得過的警衞員,魏和尚。
又一個説起來大家會驚呼“原來是他”的演員。
像這樣的演員,很多。
他們隱身在各種角色背後,不見經傳。
還好這回,他終於碰上了一個能被記住的角色。
飄這就來還債,聊聊張桐。
李大釗
前段時間的白玉蘭,《覺醒年代》靠八項提名、三項中獎,成為最大贏家。
導演張永新,編劇龍平平、主演於和偉,都榜上有名。
但還是有很多觀眾,為張桐沒入圍感到意難平。
近40歲的張桐在《覺醒年代》裏,飾演的是青年李大釗。
在風起雲湧的歷史舞台上,他既是旁觀者,也是參與者,更是推動者。
從學成歸國的愛國志士,到歷經運動洗禮的革命先驅。
六年的時間,足夠讓一個人迅速成長、成熟。
僅看眼神,就是一齣戲。
年輕的時候,神馳色飛,含着蓬勃朝氣。
人至中年,因親感了家國的沉痛。
目光雖仍炯炯,卻帶着幽鬱。
對自己飾演的李大釗,張桐用魯迅的一句詩形容: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橫眉,是讀書人與愛國志士的氣節。
對敵,要有“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的鬥志。
俯首,是對熱愛的國民、朋友與家人,又要有為蒼生立命的悲憫與柔情。
這構成張桐完成表演最重要的兩個支點。
具體怎麼表現,來看細節。
妻子趙紉蘭不放心李大釗在動亂的北大,於是來看望他。
張桐演出了李大釗的複雜情緒。
一開始,外面環境亂,加上怕懷孕的妻子冒雨生病。
他緊鎖着眉頭,説話快,急得壓不住嗓子,一臉嚴肅和擔心。

學生們走後,他和妻子二人相對。
在小家庭的氛圍裏,他的語氣變得柔緩。
內裏含着的,是由於投身革命,對妻兒心生愧疚。

兩人互相打趣時,隨着柔軟和温情流出的,甚至還有一絲小男孩的俏皮。
在大他5歲的趙紉蘭面前,感受着亦妻亦姐的照顧,李大釗亦會暫時放下負累,享受片刻輕閒。

談到以後想教夫人識字時。
他眼裏含淚,熱切期盼着那樣的未來。
但他也好像預感到,這是彼此的訣別。
他用吃飯來極力剋制自己的悲慟。
卻在妻子起身後,忍不住肩膀抖動。

再一個正面鏡頭打過來,嘴唇顫動,臉上已然落淚。
這是吃透了人物關係和台詞,理順了要轉換的情緒邏輯。
好的演員,都得能做到這一點。
在“好”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則是要讀懂戲裏每一個典故。
戲裏有一幕,是李大釗在戲台上看《挑滑車》。
他的眼神從專注。
逐漸到滿眼淚光。

因為他看見了戲台上,高寵的倒下。

《挑滑車》這出戏,取材於《説岳全傳》第三十九回。
講的是岳飛與金兀朮會戰被困,手下大將高寵犧牲自己、讓岳飛突破重圍取勝的故事。
那一刻,他看見的不是戲。
而是看到了自己和革命夥伴,雖千萬人吾往矣、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並進的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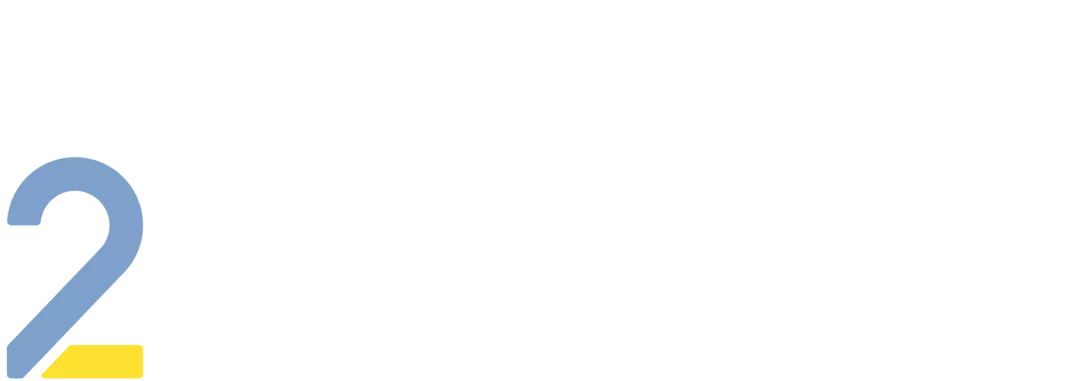
張桐的前時代
在李大釗之前,張桐是誰?
《亮劍》裏的魏和尚。
《歡天喜地七仙女》裏的黑鷹。
説起來,都似曾相識。
但演員的名字,卻陌生。
《歡天喜地七仙女》是張桐在跑了幾次龍套後,首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他飾演的是一個凡間的高冷捕快,黑鷹。
而他的官配橙兒,則在七仙女中排行老二。
橙鷹感情線只有13分鐘,卻讓觀眾嗑了十幾年。
一仙一俗的副線愛情,能讓觀眾念念不忘。
玩的是,兩個鐵桶雙雙破防的真香反轉性。
大多數國產戀愛劇裏,男的負責搞事業,女的則多為戀愛腦。
孰強孰弱,性別首先就定了位。
橙鷹則不同,是比較早期的雙A配對。
而且,飄之前講過,比起如今流行的互補型cp,《歡七》主打屬性相投的愛情。
橙兒,一心搞事業。
黑鷹,熱衷查案子。
當事業型女性橙兒遇到事業型男性黑鷹,畫風變成了這樣。
綠兒和妹夫山盟海誓,橙鷹在打架。
青兒和妹夫你儂我儂,橙鷹在打架。
紫兒和妹夫死去活來,橙鷹還在打架。
總之,別人相愛,他們相殺。

小時候看不覺得,現在飄才發現,橙鷹才是霸道總裁小嬌妻的正確打開方式。
只是這性別,默默地顛倒了個位置。
黑鷹落入壞人手裏,是橙兒及時趕到,美救英雄。
黑鷹要面子,不肯跟她走,橙兒就用法力綁他走。
不打不相識的老套戲碼,如今再看,又能挖出人物的另一面——
黑鷹魯直的性子下,有細膩的思量。
表面上看,黑鷹隨橙兒走得不情不願,背地裏卻偷偷換手拿劍。
飄看啊,黑鷹這就是故意的,要橙兒牽手才肯走。

霸總橙兒步步緊逼,傲嬌黑鷹卻再三拒絕。
不是因為他欲拒還迎,而是他真的在為橙兒考慮未來。
不敢輕易許諾,是因為人仙速途,也是因為捕快身份的羈絆。
一個愛得隱忍,一個愛得肆意。
才有了下面這段經典的告白。
—我人在江湖,在刀口上討生活
很可能明天就會身首異處
—我為你還魂續命
—我居無定所,四處漂泊
—閒雲野鶴,樂得自在
—我自由來去,不受牽掛
—默默相隨,無慾無求

張桐在李大釗之前最出名的角色,當屬《亮劍》裏的魏和尚。
戲份不多,卻被觀眾蓋章為“夢中情人”。
憑的,是魯直性子下,別有任俠氣的豪情。
魏和尚是獨立團團長李雲龍的部下。
在少林寺當過十年和尚(段鵬口中的:打雜和尚),勇猛善鬥。
不僅屢屢在寺外大打出手,還喝酒吃肉。
是為粗,所以李雲龍又稱他“花和尚”。
比起後來的警衞員段鵬,和尚多了一份“蠻楞”。
而,粗之外,又有細。
他身手高強,能“徒手乾死四個鬼子”。
卻乖乖地願意追隨李雲龍左右,是不折不扣的忠心“小弟”。
就説他和李雲龍第一次打照面。
最開始,不服。
一掌拍翻李雲龍,毫不給面兒。
眼神裏盛滿了倔強。

可下一秒,他望向李雲龍的眼神。
就亮得有火苗在跳動。
笑得合不攏嘴。

高興,是因為知道他就是李雲龍。
那個“敢和坂田硬對硬地拼刺刀,還一炮幹掉坂田”的傳説。
英雄慕英雄,強者惜強者。
認定兄弟就能賣命。
這是一層。
還有一層。
藏在李雲龍問他的話裏。
李雲龍問他為啥不在寺裏繼續當和尚,魏和尚答:“外頭不安生,沒心思念經”。
遠離塵世,心繫蒼生。
跟着李龍雲懲奸除惡、實現志向,是他在義氣與慕強基礎上認定的理。
老版《亮劍》雖然劇組窮,但窮得有風骨。
劇中有一幕戲,魏和尚和李雲龍,去日軍宴會大鬧。
台上,平田一郎聲淚俱下,懷念去世的母親。
台下,魏和尚用手抓燒雞,還端起盤子往嘴裏倒花生米。

吃相粗魯,除了因為他是個時常餓肚子的粗人。
更因為,骨子裏對日軍鄙夷不屑。
沒讀過什麼書的魏和尚,自有底層人素樸的道德觀,與亮烈的民族根性。
新版《亮劍》,也有一模一樣的橋段。
但這版魏和尚用起了筷子。
多了分慢條斯理的從容,卻沒了那股子豪橫勁兒。

都説民以食為天。
往往越日常的橋段,越透着一個劇組、一個演員理解角色的精、氣、神。

張桐的後時代
談及演員對角色的理解力,飄説過,演員需要不斷積累對生活的慾望。
塑造人物能夠鮮明到什麼程度,得看心裏積累了多少東西,眼裏又能看得出劇本多少東西。
這一方面與自身的經歷與閲歷有關。
另一方面得多讀書,集韻增廣,見多見聞。
兩方面,張桐都不缺。
他曾考上南開大學計算機系,又去了法國里昂藝術戲劇學院學表演。
兩年的留法生活,他學到的是質疑和批判。
“比如塑造一個人物時,他們會從多個側面,甚至是角色的缺陷、不足和迷茫來塑造,而不僅僅是塑造光輝的正面形象。他們認為,在抓住人的本質的前提下,這樣可以讓人物更加立體和飽滿。”
來源|《北京日報副刊》
學習了要“抓住人的本質”,文化人張桐肚裏是有貨的。
所以,連寧靜給他的評價都很高:“有東西、認真、喜歡讀書,演戲又很較勁。”
這樣的張桐,在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內娛,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
這樣的張桐,亦難免產生鶴立雞羣的自矜,對走紅抱有熱切的執念。
演員張光北曾爆料過《亮劍》的一些幕後故事。
説當時張桐作為這行的新兵,急於表現自己,老搶他和李幼斌的戲。
不光如此,為紅還險些鬧出人命。
有場戲是李雲龍打擺子,走不得路,怕拖累大部隊,執意自己留下掩護。
魏和尚把李雲龍打暈了,揹着他往山上跑。
拍戲當天,來了記者。
張桐一見長槍短炮,興奮了。
急於在記者面前,證明自己敬業,“各方面能力都很強”。
於是走戲的時候,他起步猛了。
腦子裏又只剩下閃光燈。
沒注意地上有冰,一摔,直接把背上的李雲龍彈射下了山。
後來李幼斌跟張光北訴苦:“這和尚越來越不聽話,為出名把我給扔出去了。”
這個險事兒,李幼斌記了好幾年,提起來就後怕。
即便如此,學過表演的張桐畢竟是有表演天賦的,加上拍戲認真又肯吃苦,劇組的演員都很喜歡他。
那是個把戲看得比天大的年代。
只要你有本事,有態度,就能獲得尊重與熱愛。
因魏和尚一夕成名後,這柄亮劍卻也成為張桐的雙刃劍。
證明了他的實力,同時限制了他的戲路。
之後張桐接的,大多都是戰爭戲、年代戲。
非但知曉度並未提升,戲路包括演技也老在原地踏步。
從這一階段的履歷表上,看不到張桐對跳出舒適圈的認知。
他小紅後的前半生,讓飄想起了張桐合作過的另一個演員——楊志剛。
同樣老在年代戲與戰爭戲裏打轉,同樣是偏向大齡觀眾的熟臉。
不同的是,楊志剛有個做導演的哥哥郭靖宇,形成了比張桐更深的路徑依賴。
以及,用相似模式產出固定角色,在一定範圍內反覆得到認可,由此更加確認自己演技的自信。
楊志剛去參加《演員請就位》,狂妄到首期表演除一次聯排外,拒絕和對手戲演員排練。
他給出的説法是,基於經驗主義,不希望過多投入,耗盡演員的情感。
可演出結束,他糟糕的表現甚至讓爾冬升直言,看楊志剛十幾部劇的戲,“其實表演的方式都差不多”。
演員最難挑戰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拋開習慣的固化套路,或許會面臨失敗,但亦能推動自己攀另一重險峯。
之於演戲,其時的張桐不缺能力與熱情。
缺的,只是打破自己再重來的勇氣與決心。
殘酷的是,這場重建由徹底摧毀開始。
2010年,拍攝一個新人導演的電視劇時,張桐遭遇了嚴重的打壓。
當着全劇組的面,導演不停斥責他“演技太差”“太垃圾了”。
相反,對其他演員,讚不絕口。
當引以為傲的演技被罵得一文不值,像江湖高手被廢掉了武功,1米83的張桐崩潰了。
兩年的重度抑鬱症,他適當停下了腳步。
看世界,也看自己。
“沒有經過反思的人生不值得活。”
大學時《理想國》裏他讀到的這句話,多年後,終於照進了生活。
他開始用“如履薄冰”形容演員二字。
低下高傲的頭的麥穗,接觸到的是更廣袤的大地。
2018年,張桐“爆冷”拿下飛天獎影帝(《絕命後衞師》),卻根本沒準備獲獎感言。
當時候選人除了他還有張譯(《雞毛飛上天》)、於和偉(《刑警隊長》《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等人。
宣佈得獎名單時,他笑容一秒消失,表情凝重。
接過獎盃後,鞠了兩躬,面對舞台又鞠了一次躬。
他説他沒準備感謝詞,因為壓根沒想到能得獎。
説到底,學歷高低不是對一個演員素養的絕對評判標準。
太多的明星不是輸在無知,而是輸在缺乏敬畏。
張桐演李大釗,帶着敬畏之心。
把自己的靈魂敞開,去迎接另一個靈魂的到來。
發自內心的敬畏是怎樣的?
首先,是怕。
張桐拒絕過《覺醒年代》的戲約,因為怕自己能力不夠。
然後,是敬。
或者説,怕本就是因為敬。
但既然決定演了,就盡力做到最好。
接戲後,他默默把《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吃透,並走訪了李大釗的後人。
開機第二天,他迎來了一場對學生講課的重頭戲。
三四頁的台詞,半白話半古文,差不多有15分鐘長度。
張桐一條過後,在場的導演帶着演員情不自禁地鼓掌。
但他自己並不滿意。
因為他説,這些掌聲只是因為台詞不好背,而他對李大釗先生那時的理解還不夠深。
這才是一個演員對鏡頭的敬畏。
敬它的包容,畏它的殘酷。
見識過羣星的浩瀚,意識到自己渺小如塵埃。
敬畏職業,敬畏生命。
敬畏先驅者。
也敬畏角色——另一段人生。
而時間,終於也回饋給這個苦渡者,認可和掌聲。
本文由公眾號「柳飄飄了嗎」(ID:DSliupiaopiao)原創,點擊閲讀往期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