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後,一羣脱口秀演員在音頻裏復刻了實話實説_風聞
花儿街参考-花儿街参考官方账号-财经作者,曾任职中国企业家杂志、21世纪经济报2021-07-23 08:54
花兒街參考 · 出品

作者 | 林默
1
喜脈
大學畢業,工作了一個月,周奇墨決定辭職。
為了投身藝術嗎?
不,他只是要考研。
他在學校附近租了個小房子,每天以食堂為中心攝入各種粗茶淡飯,勤勤懇懇複習了大半年,英語詞彙量得到了400%的增長。
在如此努力之後,周奇墨,落榜了。
聽完周奇墨的講述,坐在邊上的郝雨表示,自己當年的經歷非常相似。
18年前,創作了那首風靡全國校園的《大學生自習室》後,郝雨躍升中國初代説唱歌手。
然而,才華投生錯了時代,比從來沒有過才華,更讓人憂傷。
在國內大眾普遍不知道説唱歌手是啥的20年前,在家人的壓力下,郝雨一遍遍勸自己,當歌手就餓死了。
“真的,我特別理解奇墨,當時我也在北京租了個小房子,晚上去酒吧演出掙點錢,白天就複習。當時就是焦慮,萬一考不上可咋整,跟周奇墨似的,就怕自己考不上,當歌手肯定就餓死了,破釜沉舟了都。”
“然後,就考上了。”
現場一陣爆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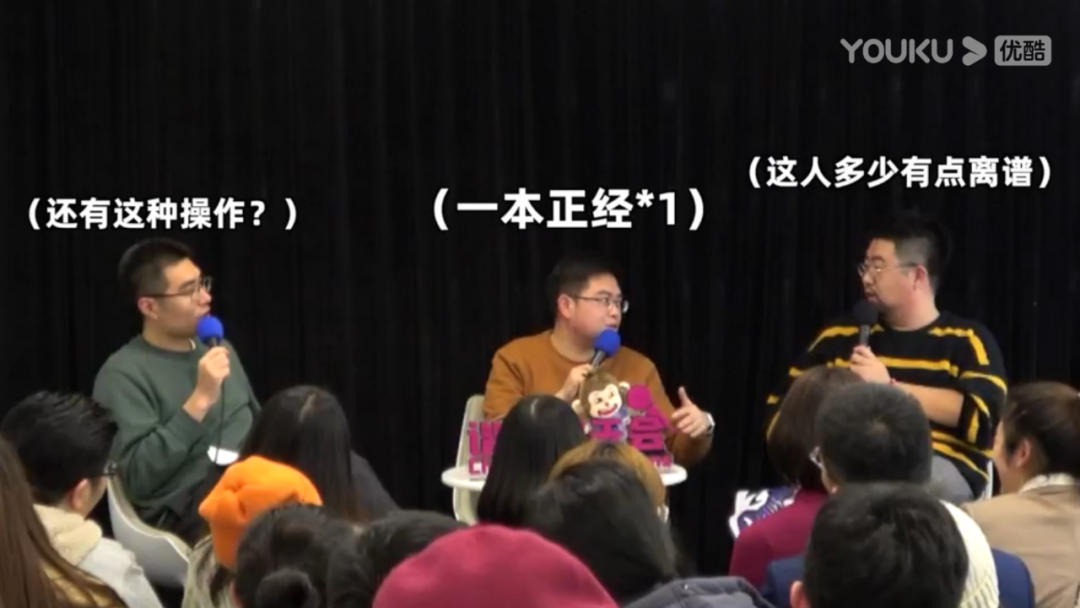
這段對話出自一檔叫《諧星聊天會》的播客,當期主題是“生活中的脱序脱軌”。
三位來自單立人喜劇的脱口秀演員作為主持人,引導話題,台下的幾十位觀眾都可以發言,分享自己的脱序脱軌經歷。
觀眾中有一半是通過在微博上圍繞當期主題投稿,稿件被選中即可來現場參加錄製。另外一半觀眾,則經歷了“秒空”的搶票大戰。
他們大多是脱口秀愛好者,或者乾脆是單立人的鐵桿粉絲。
這一期錄製現場,有人分享了畢業後去非洲工作的經歷;有人講述考研期間視網膜脱落,治療期間連上廁所都不能用力;有人類學者疫情期間去道觀體驗生活;也有失業後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每天假裝去上班,度過了比上班還累的失業生活。
每個站起來的人似乎都在説,你看,我也活成過一個笑話。
直到一位中年女士站起來,“我現在的情況是胃癌晚期”。
“其實那個觀眾想盡量展示一些開闊的生命觀,但當時我就覺得,這期節目完了”,那場的主持人表示。
本來熱鬧的現場,在這段發言之後,再無歡脱的氛圍。
場子冷了。
後期的剪輯中,節目製作人呂東思慮再三,還是剪掉了這段發言。
《諧星聊天會》的初衷,是找到意義對面站立的荒謬,用喜劇幫大家卸掉一些沉重。
可生活中總有一些什麼,是喜劇也無能為力的。
那期冷了場的“脱序脱軌”,後半段只能以演員們讀觀眾來信的形式,完成了錄製。
意外的是,這期製作團隊不看好的節目,卻成了70多期節目中收聽量最高的前三名之一,全網收聽量80萬,這樣的數字在播客圈裏並不多見。
節目如人生一般諷刺,不知道哪句話、哪個橋段就搭到了聽眾的“喜脈”上。
當年考上研究生後,郝雨又考上了體制內的公務員。業餘時間在線下説説脱口秀,他愛上脱口秀的時間,早於國內很多一線脱口秀演員,但限於公職,他也只能偶爾説説。

如果沒有這些順利的學業和仕途,他也許是中國最top的説唱歌手,或者是光芒更閃的脱口秀演員。
在“脱序脱軌”的開場,他説“現在想想,當時要是真沒考上(研究生),沒準人生軌跡就改變了,就跟張傑籤一家公司了。真的,冥冥之中沒準哪條軌道就接上了,無從判斷好壞。”
2
二十年前的實話實説
這檔由單立人製作出品的播客節目《諧星聊天會》,上線一年多,單期收聽量達到64萬,節目訂閲數達到14.8萬,每更新一期都會佔到喜馬拉雅、小宇宙、蜻蜓等平台播客熱門榜的前幾位。
幾個主持人,除了郝雨和周奇墨,還有曾經供職於錘子科技的六獸,至今仍在互聯網公司上班的兼職喜劇演員毛冬、以及單立人喜劇的創始人石老闆。
聊的話題,從童年美食到中年算命,從教育焦慮到養老規劃。

奔赴現場的人中,有律師、公務員、作家、科研工作者、淘寶店主、音樂人、藝人經紀,以及最頻繁出現的,來自各大廠的互聯網人。
為了能來到現場參加錄製,有人寫了上千字的稿子參加投稿,有人飛了四個小時來北京。
有人帶着女友,也有人在這兒找到了女朋友。

一個退休的大爺在被孩子帶來參加過一次現場錄製後,有些激動,“我想起了二十幾年前的實話實説”。
不同於只有演員在台上講段子的脱口秀表演,在《諧星聊天會》觀眾也會分享自己的經歷,大家在一個喜劇的屋檐下,互換生活中的哭笑不得。
如果你還不能get到什麼是《諧星聊天會》,可以聽一小段。
有女生在這裏吐槽情人節,男朋友送了自己一包散裝的徐福記巧克力。男友就在現場,當場表示不服,這跟那些齁貴齁貴的大牌巧克力有多大區別,為啥明知火坑還要往裏跳。
一個海淀媽媽,在孩子考試前複習的半年,曾情緒失控到從孩子肩上咬下一塊肉,“我不知道這個會不會給孩子留下什麼心理陰影”,一向温和的主持人六獸忽然尖細了聲音,“還給孩子留下什麼心理陰影?先看看自己吧”。
有人説自己考試前用易經八卦,看了半天迎面而來的公交車都是幾路,以此起卦,推演出考試能不能通過。遭到主持人的吐槽,“有這時間為啥不多看兩道題呢”。
那個失業了,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假裝去上班的姑娘,每天都去家旁邊的書店泡着,“之前上班的時候,每天都會路過這個書店,那時候就想,要是能天天來看書多好啊。現在看了一個禮拜的書了,發現自己是真的不愛看書”。
一期吐槽直男消費的節目上,一個女孩指着旁邊的男朋友,“我男朋友是程序猿,996已經消磨掉他所有的消費慾望了。兩年前我們認識的時候,我送給他四條內褲,現在他有三條內褲,因為一條在上個月磨出了一個大洞”。
在一期關於養老計劃的節目中,一位中年大姐説,兒子18歲上了大學那年,她終於又跟老公單獨出去旅遊了,“之前所有的精力都在照顧孩子身上,到了旅遊景點,我就發現這台階怎麼這麼多啊,那一刻我忽然覺得自己老了”。
3
大廠
一期討論“斜槓青年”的節目裏,主持人讓現場的50個觀眾都介紹一下自己的職業,當聽到第15個人説自己的本職工作是“互聯網運營”時,郝雨站了起來,“不是,咱們這些互聯網公司為什麼需要這麼多運營”。
對大廠人來説,在本該躺平的週六,他們爬下了牀,從西二旗,從望京,從亦莊趕到東城77文創園。他們是幸運的,更多的人因為搶不到票,只能聽着手機裏的諧聊播客跟着傻樂。
王磊每週都會準時守在諧聊的搶票界面,如果搶不到,他就會在大家票務流轉的羣裏,繼續守望。
王磊畢業八年了,最初在一家小的互聯網公司,後來作為聯合創始人,跟前領導進行了一場激情滿滿到無疾而終的創業。創業失敗,進入小米當起了產品經理。
在王磊看來大廠是一種氛圍,每天要開各種拉齊會、勾兑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份,不能有太多情緒,不能有太多個人色彩,你得凹出一個職場人設,“13號地鐵都有很多人戴着工牌”。
“在諧聊,就不用裝了。”
諧聊的現場,有一種天然地對“裝”的排斥,大家是平等的,都是來分享各自經歷的,如果有人戴着“面具”,帶着“光環”在裝腔作勢,會很容易被識別出來,在現場遇冷或被吐槽。

有人曾因肺結核被迫休學,有人孩子剛出生就被查出先心;有國企人吐槽自己的同事,唯一擅長的工作是每次去KTV,都把領導的歌單爛熟於心;一個姑娘站起來説,自己和男朋友都996,累到沒有什麼性生活的願望。
大家更喜歡聽到各自真性情的一面,哪怕這一面有些難以啓齒。
“就有一次吧我突然有了屁意,然後我就開心地把它放了,這種事我沒想到發生在我一個39歲女性的身上,我以為是個屁,然後就。。。這時候我老公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我就呆若木雞地看着他説‘老公,我chuasai了’,然後他的第一反應是狂笑,因為這事兒有個前情,幾年前他有一次生病也拉過褲子,結婚7年半,我們成了chua sai家庭了。”
如果不怕刺激,可以聽一下音頻。
王磊的女朋友是在諧聊認識的,對方也在大廠工作。錄製現場聽過兩次彼此的發言,後來王磊在粉絲羣裏,認出了對方的頭像。
“能在諧聊的現場遇到,就總覺得是一種調性的契合”。
4
站在知識付費的對面
在第一次關於《諧星聊天會》的策劃會上,單立人喜劇的創始人石老闆提出了一個原則,“想教別人點兒什麼的那種音頻太多了,我們就做一個,讓大家沒有任何負擔的播客節目。如果你能在我們這兒學到點兒啥,就算我們輸了。”

節目火了之後,想要在內容上有所合作的金主紛至沓來,希望能圍繞自己的品牌定製軟廣,都被製作團隊一一回絕。
目前比較深入的一次商業合作,是雀巢冠名的十二期“諧星聊天會巢媽團獨播季”。對方並沒有將合作的目標侷限在軟廣,而是將這十二期聊的話題,拓展至當下女性相關的“雞娃”,“生育帶來的職場斷檔”,以及“得是多好的婚姻能讓人放棄單身”等等。
令製作團隊沒想到的是,這十二期節目的收聽率竟然沒降反升,單期達到了72萬,最高一期竟然101萬。
在錄完那期與“雞娃”相關的話題後,羅丹想了很長時間,大人們為孩子籌劃的,一定是他們未來需要的嗎?就像大人為自己籌劃的這些,真的是必要的嗎?
她還是個單身的姑娘,在字節跳動工作。
這家互聯網公司在過去一年,員工數迅速從6萬人突破10萬人,因為許多員工在地鐵上依然佩戴着工牌,在網上被調侃“戴着字節的工牌,是不是能光宗耀祖”。
去聽諧星聊天會之前,羅丹幾度試圖約過字節跳動內部的心理輔導項目,想去跟心理專家聊聊自己的壓力。但系統每次都提示她,專家的時間已經被其他同事約滿了。
其實最大的壓力並不來自於繁忙的工作,而是源於開始思考,“真的需要這麼大的工作壓力嗎?我做的這些工作,真的對這家公司是有意義的嗎?”
她沿着播客摸到了諧聊的錄製現場,但歡樂的現場並沒有帶走這些漩渦,而是把她捲入了更深處。
“你在大廠工作,社交圈會變得越來越窄,個人的愛好都會變得越來越少。但是在諧聊,忽然見到了平時生活中很多見不到的人,人家做別的工作,沒有996,當然也沒有賺那麼多錢,但是大家都生活得很好啊。回家之後會問自己,年輕人生活的答案,就只有996和大廠嗎?”
996和大廠,彷彿時代架在年輕人面前的一塊宏大幕布,包裹住他們生活的全部。他們疾呼苦逼,旁觀者以為他們要掙脱,但更多的人已經和幕布長成了一個有機體——
在羅丹供職的字節跳動取消大小周前,公司內部曾進行過一次調研,只有三分之一的員工贊同取消大小周,理由很赤裸,“取消了大小周,一年要少賺十萬元”。
5
卸妝油
在百度做運營的李翔,已經第六次來到諧聊現場。作為喜劇愛好者,之前他會聽着郭德綱入睡,現在上班、下班、午休、在家的碎片時間他都會打開諧聊,有些節目反覆聽了N遍,笑點在下幾秒會出現已經瞭然於心。
不同於羅丹,在諧聊找到了衝破信息繭房,由陌生帶來的新奇感。李翔享受的是被同路人簇擁,如同看着《老友記》般的陪伴感。
李翔上學時的專業是植物學,總覺得與植物打交道,會比跟人類壓力小得多。
“我也有過喜歡的女孩,但是不太能去開始。我跟世界只談過兩次戀愛,第一次是跟植物,第二次是脱口秀”。
諧聊是他跟人羣舒適的距離,大家分享各自的經歷,有身在人羣中的安全感,卻沒有任何的社交負擔。

許多來諧聊的聽眾,是帶着追愛豆的感受來的。
有人喜歡永遠要給喜劇也上個價值的郝雨,有人是周奇墨的鐵粉。
某個現場,一個女孩拿過話筒的時候,激動得有些磕巴,對台上的毛冬説,“毛書記,我特別特別喜歡你,我為了能來見你一次,每期都寫很長很長的稿子投稿,這期我終於被選中了”。
李翔是石老闆的鐵粉,後者是單立人喜劇的創始人,曾經放棄金融工作,投身彼時讓他一貧如洗的喜劇事業。去年以來,因為要履行一個管理者的職責,已有漸漸淡出演出的趨勢。
元旦特別節目,每位主播在開年之際給自己寫一封信,在現場念出來,聽完石老闆唸的信,李翔回去也給2021年的自己,寫了一封信,希望能在新工作中順利轉正,希望也許能有一個女朋友,希望有一天能有自己的房子,把那套最喜歡的樂高買回家,希望諧星聊天會能越來越好。
信的最後一句,李翔寫道,“我會很遺憾,如果有一天,石老闆只是成為一個有錢人”。
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在文字,影視,短視頻,真人秀環繞的今天,旁觀別人的時間不要太多,人們為什麼願意每週花三四個小時的時間,奔赴一場陌生人的現場錄製。為什麼依然願意花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守在一檔播客前,聽別人聊天?
25年前,一檔把一羣普通人組織到一起聊天的節目,由於節目形式新穎,主持風格幽默,紅遍大江南北,那檔節目叫《實話實説》。
在那個經濟打開、社會轉軌的時代,所有的命題都很宏大,普通人需要一個渠道去表達自己的需求,聽見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發出的聲音。
可是,在有各種渠道可以發聲的今天,為什麼人們依然需要一個現場版的“實話實説”。
大概是因為一切又不太真實了。
在這個剪輯過度,一切都有台本的時代,做人務必有人設的時代,這樣臨場的、即興的,由當事人自己發出的聲音,提供了這個內容產品極大豐富的時代,最稀缺的奢侈——真實。
喜劇的視角如一瓶卸妝油,在燈光並不明亮的諧聊錄製現場,每個人都身在人羣,每個人都得以卸掉苦苦維繫的光環,或者只是微弱的光暈。
諧聊創造了一個場,把陌生人的生活交織在一起,然後每個人都在原地騰空而起,向下審視那個生活裏的自己。
在這個場子裏,時間沒有了價值,價值沒有了意義,意義沒有了重量。
李翔喜歡去現場,每次他都會盡量坐在第一排,看着台上的主持人,聽着身後的故事。
他感謝這裏的每一個人,他們認真地聽他説話,真誠地給予回應,就像坐在一羣老友中間。
但他從不回頭看,那些講話的人長什麼樣子。每次錄製結束,他會低着頭,不跟任何人交流,頭也不回地離開。
錄製現場的燈滅了,馬車就變成了南瓜。
幾分鐘以前那個場還在,幾分鐘後即便身在現場,一切又都回到了現實。
那兩個小時只有傾訴與傾聽的錄製時間,彷彿只是繁忙人生中的一段脱序脱軌。
可是又有誰能説的清,脱序脱軌的究竟是那兩個小時,還是緊鑼密鼓週而復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