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字長文揭秘!什麼是“舉國體制”?當今中國還需要嗎?_風聞
西方朔-2021-07-27 05:20
中科大胡不歸7月23日 19:43 來自 微博 weibo.com此文最明顯的一個推論就是,中國現在壓根就沒有舉國體制,對芯片也是一個稀裏糊塗得過且過的態度,因為並沒有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來主抓這件事瞭望智庫 1周前
瞭望智庫 1周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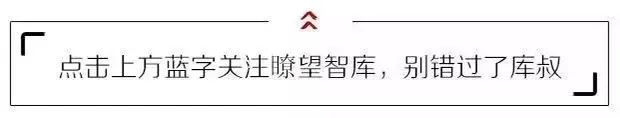

近年來,中國崛起的趨勢與外部遏制壓力之間的矛盾加劇,標誌着中國的發展進入一個挑戰最大、任務最艱鉅的階段,但同時也是一個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最有希望的階段。
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中國“取得重大突破,實現重大發展”,也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歷史階段的關鍵使命。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政治領導層提出了實施**“新型舉國體制”**的設想。這個“語境”展示了一個清晰的邏輯:“完成重大任務”是目標,而採取“新型舉國體制”是手段。
但是,這個概念迄今尚未被討論清楚,也引起一些誤解和爭議。許多人把它簡單地説成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對其持負面態度者懷疑這是重回計劃體制;還有許多解讀文章把計劃體制等同於“舊的舉國體制”,然後集中揣測“新型”的含義,但迴避解釋“舉國體制”到底是什麼。
實際上,不管是舊的(如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還是新的(未來打算實行的),澄清“舉國體制”的內涵是理解“新型舉國體制”的關鍵。
本文回顧中國的“兩彈一艇一星”項目,並考察美國在二戰期間成立的戰時生產局、曼哈頓計劃,以及至今仍活躍的DARPA,來説明“舉國體制”的本質與意義。
對於當今的中國,新型舉國體制又意味着什麼?
文 | 路風、何鵬宇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本文授權摘編自《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刊發的《舉國體制與重大突破——以特殊機構執行和完成重大任務的歷史經驗及啓示》。
1
外部危機四伏
“兩彈一艇一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但領導這些項目獲得成功的決定性力量卻鮮為人知,它就是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專委)。
【注:原子彈、導彈、核潛艇、人造衞星是新中國在極端困難條件下開發出來的戰略武器和尖端技術,對中國的大國地位以及捍衞國家安全具有重大意義。現在流行的“兩彈一星”提法是在改革開放後才出現的,在此之前的官方內部提法是“兩彈一艇”(均受中央專委的管轄)。本文采用“兩彈一艇一星”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機構不僅獲得黨中央的授權,而且直接執行項目並對結果負責。**權力級別如此之高的機構直接抓項目,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中國決策層於1955年初決定發展核工業,其方針是首先用於軍事目的。根據中國與蘇聯在1956年8月、1957年10月、1958年9月簽訂的幾個協定,蘇聯援助中國建設一批核工業項目和技術實驗室,並將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1987)。
但隨着兩國之間產生“分裂”,蘇聯於1960年6月宣佈暫停向中國運送原子彈模型和相關技術資料,同時撤退所有的專家。當突然的“斷供”使中國的核工業建設陷入困境之後,國防工業的領導人開始感到需要對開發“國防尖端武器”(特指“兩彈一艇”,與常規武器相對)進行集中統籌協調。
1961年1月,聶榮臻在《關於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科學技術工作安排的彙報提綱》中提出:“要發奮圖強,集中力量,把各方面的力量統統組織起來,通力合作來完成國家任務……國家科委、國防科委、科學院、教育部和其他有關部門,從中央到地方都要扭在一起,共同商量,統一安排”。
同在1961年1月,**黨中央正式決定對面臨困難的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於是引發了要不要繼續幹原子彈的爭論。**分歧在1961年夏天的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上達到高潮,“上馬”還是“下馬”的爭論形成尖鋭的意見對立(聶力,2006)。
在暫無定論的情況下,1961年11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成立國防工業辦公室的決定》,建立直接對中央負責的國防工業辦公室(簡稱國防工辦),由羅瑞卿任主任,以確保原子彈工程不會陷入停滯。它“作為國務院的一個口(國防工業口),在黨內向中央書記處和軍委負責”,權限範圍為管理國防工業系統內的“二機部、三機部和國防科委所屬範圍的工作”。
為了判斷中國是否能夠繼續研製原子彈,黨中央、中央軍委派副總參謀長張愛萍牽頭調查原子能工業在蘇聯“斷供”後的狀況。張愛萍是開國上將,調研方式同樣“殺伐果決”,每到一個單位只問4個問題:一,你們原定的計劃是什麼?二,你們現在所做的事情,按計劃還差多少?三,完成原定進度的困難是什麼?要講得具體。四,如果我給你解決了困難,你多長時間能完成?
1961年11月14日,張愛萍向中央提交了《原子能工業建設的基本情況和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認為原子彈的科研工作有了很大進展,當前的困難更多屬於工程性的問題,而工程性的問題是可以通過組織協作解決的;**雖然原子彈工程看起來盤子很大,但實際上很多東西都藴涵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之中。因此,報告的結論是:由中央和國務院出面,統一協調,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大協作、大會戰,在1964年進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張愛萍,1994)。
1962年,中印邊界和台灣方向迅速加劇的安全威脅最終促使中央決策層下定決心研製原子彈。當年6月,毛澤東在聽取東南沿海形勢的彙報時明確表態,“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製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鬆或下馬”(毛澤東,1993)。
但是,對全國各個經濟部門進行集中動員的工作已經明顯超過了國防工辦的權限範圍。同年10月19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彙報,指出“導彈和原子彈都需要中央有個專門的機構來抓,做組織工作、協作工作,下命令的工作。這兩彈要搞個小的機構,不這樣抓,這裏一拖,那裏一拖,時間過去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6)。
於是,**建立中央領導的全國性機構來主抓“兩彈”被提上中央決策層的政治議程。**10月30日,羅瑞卿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上報《關於建議成立中央專門委員會的報告》,建議“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隨時檢查、督促計劃執行情況,並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進行具體調度,及時解決在研究、設計和生產建設中所遇到的問題”(羅瑞卿,2006)。11月3日,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一錘定音。
2
中央專委成立
1962年11月1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第一次會議,**宣佈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正式成立,**主任為周恩來,成員有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七位副總理和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傑、孫志遠、段君毅、高揚七位部長級幹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
12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向中央軍委及全國範圍的黨的系統發出《關於成立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了中央專委的地位和職責。《決定》指出:“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更有力地促進原子能工業的發展,力爭在較短時期內取得更大成果,遵照主席‘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的指示,中央決定: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成立一個十五人專門委員會”;“委員會是一個行政權力機構,主要任務是:組織有關方面大力協調,密切配合;督促檢查原子能工業發展規劃的制定和執行情況;根據需要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及時進行調動。委員會的決定,由有關方面堅決保證,貫徹執行”(宋炳寰,2018)。
在中央專委第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對專委委員們説了這樣一段話,“你們都是從高級崗位上調來的首長,現在要動手動腳,是首長也是‘腳長’,權力最小也最大。你們個人沒有任何權,但問題一經專委決定,你們檢查執行,權力又最大”(奚啓新,2011)。
根據《決定》和周恩來的話,我們可以簡要歸納出中央專委的組織性質:**中央專委實際上是黨中央在“兩彈”上的“全權代表”。**它獨立於現有部門體制之外,根據任務的需要而設立,一方面它得到黨中央的直接授權和直接領導,有做出戰略決策的權力,決定原子彈和其他管轄的任務“幹不幹”和“怎麼幹”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專委承擔對項目成敗負責的重任。如果任務不成功,它必須向黨中央承擔全部責任。
因此,專委的組織性質決定了它必須以任務成敗為一切工作的檢驗標準,以組織和協調各方面力量為核心職責,在全國範圍動員一切力量完成國家需要的重大任務。
中央專委成立後,圍繞原子彈研製的各項重大問題召開過多次專委會(見表1)。在專委的協調下,26個部委,20個省市、自治區,9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參加了攻關會戰(聶力,2006)。原先在二機部和國防工業系統內無法解決的事情,中央專委直接聯繫相關部門和地方解決。
例如,分離高濃度鈾必須用到一種氣體分離膜(“甲種分離膜”),科研攻關遇到很多困難;聶榮臻知道情況後,調集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瀋陽金屬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冶金部的有關單位進行集中攻關,下“死命令”要求上海市領導必須完成任務,最終在1964年研製出符合技術要求的元件(聶力,2006)。
後來錢學森回憶説:“那時中央專委的決定,要哪一個單位辦一件什麼事,那是沒有二話的。那決定也很簡單:中央專委哪次哪次會議,決定要你單位辦什麼什麼,限什麼時間完成……也不説為什麼,這就是命令!中央專委的同志拿去,把領導找來,命令一宣讀,那就得照辦啊!好多協作都是這樣辦的,有時候鐵路運輸要車輛,一道命令,車就發出來了”(何立波,2012)。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於1964年試爆成功後,中央專委的體制延續下來。
1965年2月3日、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專委會第十次會議,提出增加七機部、四機部、五機部等部門的有關人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3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的決定,將導彈納入了中央專委的工作範圍,相應增加餘秋裏、王諍、邱創成、方強、王秉璋、袁寶華、呂東(替換王鶴壽)參加中央專委,並正式改稱“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以下簡稱不變)(宋炳寰,2018)。
自此,圍繞原子彈(氫彈)、核潛艇、導彈、人造衞星和核電站的一系列尖端科技工程項目的研製、試驗的許多重大決策,幾乎都是中央專委或是經由請示黨中央做出的(見表2及表3)。
周恩來逝世後,中央專委逐漸停止了活動。1979年的專委會是能在公開報道中找到的最後一次中央專委活動情況的記載。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曾經出現過另一個意義上的“專委”,即中央為了加快武器裝備發展在1989年10月成立的“國務院、中央軍委專門委員會”,由總理李鵬擔任主任(懷國模,2014)。但是,這一機構僅限於國防工業系統,甚至在1993年“降格”為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實際職能則由國防科工委承擔。
因此,在“兩彈一艇一星”的時代之後,新中國歷史上也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和中央專委一樣,由黨中央直接指揮、在全國範圍統籌協調、以實現重大任務為目標的權力機構。
3
決策上的分散
理解為什麼中央專委能夠對重大任務的結果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再具體看中央專委領導中國核潛艇工程的案例。
核潛艇工程幾乎與原子彈工程同時期上馬。
中國第一座核反應堆(即蘇聯援助的重水試驗堆,代號101堆)剛一運轉,聶榮瑧元帥就於1958年6月18日召集一個研製導彈原子潛艇的座談會;27日,他向中央提出中國自行設計和試製導彈原子潛艇的報告。兩天之內,報告得到毛澤東的批准(聶力,2006)。此後,赫魯曉夫拒絕向中國提供核潛艇的技術援助,反而使毛澤東下決心“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因此,中國的核潛艇工程從一開始就走上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
上馬之初,核潛艇工程是一個典型計劃體制下的項目,採取了領導小組協調、各部門分工負責的方式來推進。領導小組由海軍副司令羅舜初任組長,包括主要協作部門的負責人;分工則由海軍負責全艇佈局的總體設計,第一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一機部”)分工負責船體、主輔機、電機、儀表以及工藝設計的設計和製造,第二機械工業部(後改稱核工業部,以下簡稱“二機部”)負責核動力反應堆的研製,國防部五院負責導彈的研發。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的事實,中國在決定上馬核潛艇工程時,**雖然在潛艇艇身製造和核反應堆方面都有了點基礎,但技術積累還遠遠不夠。**核潛艇是一個技術上極端複雜的系統,主要由艇身系統、核動力系統和作戰系統(魚雷或導彈)等組成,而這些“子系統”本身就足夠複雜。使問題更嚴重的是,分工負責開發這些“子系統”的各個工業部門都基本上沒有掌握各自負責的“子系統”技術,所以各個工業部門都只能先推進各自負責的技術系統,然後再考慮核潛艇的總裝(系統集成)工作。
但是,核潛艇工程從開始進入設計階段就陷入“搖擺”狀態,問題出在組織體制上:**領導小組不是一個權力機構,而是一個協商機構,牽頭的海軍領導人對於各個工業部的負責人沒有領導關係。**因此,領導小組實際上缺乏對核潛艇工程進行全盤計劃的權限,項目的進展深受各個協作部門內部決策的影響。
潛艇核動力研製團隊的遭遇充分反映出這個問題。核動力反應堆是核潛艇的“心臟”,但是從1958年至1962年底,核動力研究團隊的組織關係一直處於頻繁調整的混亂狀態,原因在於二機部對核潛艇工程的“搖擺”態度,同時又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機構能夠干預或扭轉二機部的內部決策。
核潛艇工程上馬後,二機部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秘密組建了一支研究核動力反應堆的團隊,其做法類似於今天常説的“孵化”。1959年2月,原子能所十二室正式成立核動力研究設計組,並在當年年底發展到200人的團隊。經請示部領導同意,研究設計組從1959年年底開始,按照核潛艇的實際要求進行了設計一座動力堆的“設計練兵”,並於1960年6月底完成了《潛艇核動力方案設計(草案)》。
27年後,官方的《當代中國的核工業》(第302頁)對此評價説:“該方案設計當時是作為草案上報的,但在後來的實踐中沒有什麼重大的反覆,這證明它在總體上是可行的。這就為以後的研製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1987),之所以稱為“練兵”,是因為當時並不具備能夠滿足設計動力堆所要求的試驗條件。但是,隨着核動力堆研發的進展,體制問題也暴露出來,於是該團隊的負責人向二機部領導提出設立獨立核動力研發機構的想法(孟戈非,2002)。二機部領導並沒有接受建議,而是“藉助”這個機會於1960年12月做出兩個決定:(1)將大多數技術骨幹(60多人)調離原子能所,合併到二機部設計院;(2)在原子能所保留少數研製人員,後來成立一個新的獨立設計組(47-1室)。
**在中央調整經濟的方針下,核潛艇工程於1962年7月下馬。**但同時,中央決策層要求保留動力堆的研究設計機構,繼續工作並保留少數必要的研究項目(周均倫,1999)。但是,二機部其實在此之前就醖釀解散潛艇核動力的研發團隊,以便將其全部集中到生產堆工程。
1962年5月,為了保住這支隊伍,團隊負責人繞開行政上級直接向海軍政委蘇振華反映情況。幾天後,二機部接到國防科委正式通知,將潛艇核動力設計人員和建制劃歸國防部第七研究院(孟戈非,2002),實際上是軍方把核動力研發團隊收編到國防科委保存起來。由此,核動力研發隊伍分散到二機部(47-1室)和七院兩個不同的部門,並且在各自的部門都處於邊緣狀態。
這段歷史可以表明,核潛艇動力堆的研究設計工作一直受到部門體制的不利影響,甚至連研發團隊的隸屬關係都難以穩定。在計劃體制下,無論聯合開發的項目多麼複雜(如核潛艇工程),各個部門也很難自發地“付出”超過本部門利害關係範圍的努力,甚至對份內的任務都有可能“三心二意”;部門分工不會自動地產生協同合作(系統集成),也沒有哪個部門願意承擔整個項目的責任。
例如核潛艇工程,無論是領導小組還是作為用户的海軍,都沒有權限和能力制止核動力研發組織的混亂狀態;海軍不能要求二機部保留核動力研發團隊,只能走國防科委的途徑“收留”二機部想打散的隊伍。因此,核動力堆研發出現的混亂源於部門體制在決策上的分散——這是計劃體制無法自動解決的問題。
4
全面接管工程
“扭轉”核潛艇工程命運的關鍵是中央專委的成立,**它全面接手這個工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全研究隊伍,**將分散於各部門的核潛艇研製力量重新集中起來,並要求繼續開展總體方案的設計工作。
1963年8月,中央專委決定將二機部的50多名潛艇核動力技術骨幹與七院已有的核動力隊伍合併,正式成立艦船動力研究所(楊新英,2016)。研究所由七院和二機部雙重領導,以七院為主,建制在七院,番號為國防部七院15所(簡稱715所);任務是開展潛艇核動力裝置總體方案的論證,進行核動力裝置的方案設計。至此,中央專委結束了核潛艇工程的混亂狀態,核動力研發隊伍被重新“攢”在一起,成為一個有明確任務和編制的研發機構。
**715所正式成立後,潛艇核動力的工程設計進度開始提速。**1964年5月10日,七院召開09-1反應堆動力裝置主方案和主參數的論證會。10月,主方案確定,開始了對核動力裝置的初步設計和技術設計(即系統設計和詳細設計)。1964年下半年,國防科技體制發生了“部院合併”的變化,潛艇核動力研發團隊擔心在七院併入六機部(船舶工業部)之後會被徹底邊緣化,因而做工作把隸屬關係又轉回到二機部,並更名為北京15所(孟戈非,2002)。
這是組織隸屬關係的第三次變化,但這次調整再也沒有帶來技術隊伍的“分裂”或被生產堆設計“吃掉”的結果,因為這次二機部上面有一箇中央專委在盯着,它只能堅決執行專委的決議。
1964年10月,中國試爆成功第一顆原子彈。**在經濟全面好轉的情況下,核潛艇工程再次提上議事日程。**毛澤東正式表態,重申國防尖端技術“要有、要快、要超”(劉華清,2004)。
1965年3月,中央專委召開會議做出決定,批准核潛艇工程(09工程)重新上馬,指派二機部負責在1965年下半年提出核動力堆的具體規劃並報中央專委;工程的具體運行事宜由聶榮臻直接領導,併成立一個新的核潛艇工程聯合辦公室,由時任六機部副部長的劉華清負責,直接向聶榮臻報告(劉華清,2004)。
1965年8月25日,中央專委會議決定,同意二機部黨組關於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建在四川省夾江縣境內、1970年建成陸上模式堆的計劃。二機部隨即決定於1966年底在夾江縣境內先建一個比較完善配套的反應堆工程研究綜合基地,代號909。
在解決了“幹不幹”的問題後,中央專委接着就要解決“怎麼幹”的問題。核潛艇重新上馬後,首要事項是論證潛艇的總體方案。中央專委不是放任科學家和工程師們去“自由探索”,而是明確要一艘什麼樣的核潛艇,然後根據目標來選擇技術。
中央專委在1965年8月的會議上明確了關於研製核潛艇的3項原則:(1)認真執行大力協同的方針;(2)立足於國內,從現實出發,分兩步走,先研製反潛魚雷核潛艇,再搞導彈核潛艇;(3)第一艘核潛艇既是試驗艇,又要在主要戰術技術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為戰鬥艇交付使用。
這表明了中央專委對核潛艇工程提出的目標是要造出一艘真正的、能用的核潛艇。儘管負責牽頭的聶榮臻元帥沒有技術背景,但他能夠從戰略的角度來判斷問題。他在把握方向和目標的前提下,讓科學家和工程師對特定的技術問題進行充分討論,提出各自的意見,最後再由他拍板選定一個最有可能實現核潛艇總體目標的技術方案。一旦確定,各方面必須統一開展行動。
許多具體的決策細節充分展現了中央專委的決策原則——選擇技術的標準不是先進或落後,而是以達到目標為根本依據。
例如,(1)關於艇身構型方案的討論,在技術人員中形成了**“常規艇型加核動力”與“水滴線型加核動力”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案。**
“常規”論認為國家的技術和工業基礎薄弱,應當先仿照較為成熟的蘇聯潛艇的構型,按照“普通線型核動力→常規水滴型→核動力水滴型”的路線漸進發展;
而“水滴”論認為,核潛艇和常規潛艇是性質不同的兩種潛艇,不應該在常規潛艇的結構上加裝核動力,“水滴”型並不是技術上的冒進,而是已經有調查研究和一定的實驗基礎,在技術上能避免不必要的彎路,做出一個成熟的核潛艇型號。
聶榮臻專門召集有關負責人開會,並在充分詢問情況和商量探討後做出結論:“總體不要用常規潛艇的艇型,要重新設計,不然搞得兩不像……應該是‘好馬配好鞍’,搞‘核動力水滴線型’!”(聶力,2006)
(2)**關於建立陸上模式堆的討論,**反對者認為反應堆可以先上艇後再試驗,這樣能節省大筆支出和縮短試驗週期。支持陸上堆的觀點則認為,在沒有搞過艇上模式堆的情況下,直接上艇風險過大,在艇上調整反應堆也極為不便,建造陸上堆的目的就是保證核潛艇能夠直接建造成功。
最終,聶榮臻認為核動力潛艇應該一次建造成功並且能安全運行,因而必須建立陸上模式堆進行充分實驗(彭子強,2005)。
敲定技術方案後,中央專委開始採取措施推動核潛艇工程的具體執行。
**第一,設立明確的工作任務和完成期限,將各部分研製任務在全國範圍內的科研機構、院校及企業進行了分配與協作。**其中,二機部負責核動力裝置的設計與建造,必須在1970年建成陸上模式堆;七院負責魚雷核潛艇的總體研究設計。
**第二,進行跨系統、跨部門的統籌協調,**當各有關部門的基建施工力量不足時,中央專委就指令有關軍區派部隊幫助施工,滿足核潛艇研製所需的經費和物資器材;同時啓動對導彈核潛艇研製工作的部署,指令七機部四院開始導彈總體設計的準備工作(董學斌、賈俊明,2009)。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對核潛艇工程造成衝擊。陸上模式堆是一個集全國26個省市1200多個工廠、研究所和院校所生產和研製的29000多台件設備、儀器、儀表、管道、閥門於一身的複雜裝置,但文革爆發後,許多工廠和研究所停產,各級領導幹部和技術專家被批鬥,協調09工程的系統面臨癱瘓威脅。
為了防止工程遭到破壞,由聶榮臻建議並經毛澤東批准,國防科委於1967年3月將涉及國防的各個科研院所進行軍事接管。當這些調整仍然無法阻止政治運動對核潛艇工程的衝擊時,身陷政治漩渦的聶榮臻決定在北京召開核潛艇工程的協調會議,還特別要求註明,凡是接到通知的廠長、書記,不論是否正在接受批評和審查,任何人都不準以任何理由阻擋。但協調會依然無法從根本上扭轉態勢,參會的廠長、書記一回到各自單位,就再次受到衝擊。面對全國各地的告急情況,聶榮臻決定冒着極大的政治風險,在1967年8月30日簽發了一份史無前例的、以中央軍委名義發出的“特別公函”,明確指示“核潛艇工程是毛主席親自批准的尖端國防工程。任何單位、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藉口和理由衝擊車間,更不能以任何藉口停產停工”(聶力,2006)。
這份文件具有極高的效力,使全國各有關單位紛紛恢復了生產科研秩序。事情過去了40多年後還有老人記得,當時就是因為這份《特別公函》,所以909基地的一個電報,就能把正在運往其他地方用户的設備中途調到夾江。
中央專委的領導使核潛艇工程能夠在艱難局勢下繼續前進。1968年,因牽扯“二月逆流”的聶榮臻被徹底邊緣化,此後的工作由周恩來直接出面組織。
1970年7月1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議,聽取現場領導關於陸上模式堆的彙報,批准啓堆試驗,並決定派清華大學、二機部二院專家和有關部門領導趕赴現場,跟班工作。陸上模式堆於7月16日開始試車,於8月30日達到滿功率,驗證了中國第一座核潛艇動力堆的成功。
**1970年12月26日,艇上安裝核動力裝置工作完成,中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經過試航和調整,1974年8月1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入列,被命名為“長征一號”。此後,以“長征一號”為基礎,1978年中國第一艘彈道導彈核潛艇動工,1981年4月下水,1988年9月成功發射潛射彈道導彈。**這標誌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海基核威懾力量的國家。**核潛艇工程的成功證明了中央專委在完成關係國家命運的重大任務上的關鍵作用。
5
美國也存在這種機構
雖然中共中央設立中央專委是為了克服部門體制不利於推進重大項目的弊端,**但仍然不足以證明這種機構不是計劃體制國家的特有產物,**除非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也有這種由國家最高決策層授權來完成重大任務的特殊機構。
歷史的事實是,美國雖然是一個資本主義市場體制國家,但在每一次遇到危機時,都同樣會設立這樣的機構來完成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任務。以下回顧美國從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設立的3個特殊機構:戰時生產局、曼哈頓工程區和至今仍在活躍的國防先進研究計劃署(DARPA)。
1.戰時生產局領導合成橡膠的生產
美國的強大工業生產能力是同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法西斯軸心國的主要原因之一。僅僅在參戰後的第二年(1942年),美國的飛機產量就高達4.7萬架,是日本的6倍。但在直到宣佈參戰的那一刻,美國的工業動員能力還是一塊巨大的“短板”。
在軸心國的威脅急速擴大的1940年,美國成立了諮詢性質的“緊急狀態辦公室”、“國防諮詢委員會”和職權分散的“生產管理辦公室”等機構,想盡辦法加強軍備生產(Morgan,1994);但當年的飛機產量也不過2000多架,還不到日本飛機年產量(超過5000架)的一半。
在決定戰爭勝負的時刻,美國通過緊急立法設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經濟動員機構——戰時生產局(War Production Board),由它全權負責協調全國的經濟生產活動,包括制定全國的工業生產計劃、調配戰略物資和協調各個大型私人企業的生產活動(Levine,1944)。
儘管戰時生產局的領導人也曾是企業家,但是他們對企業直接採取了“蘿蔔加大棒”的行政手段,一方面給予私人企業大量的國防訂單,以經濟利潤激勵企業轉產戰爭物資;另一方面制定戰略物資分配和金融貸款的優先順序,給予積極配合政府生產計劃的企業以高優先級,對不配合戰時生產計劃的企業不給予相應支持。
通過這種方式,戰時生產局把市場中分散決策的私人企業迅速動員到統一規劃的戰爭生產計劃上,使大型工業企業的技術和生產能力充分投入到軍事裝備和物資的生產研發上,在極短的時間內扭轉了美國戰爭生產能力低效的局面。戰時生產局於1945年10月被撤銷,但這個機構是美國打贏戰爭的一個關鍵。
戰時生產局的最大功績之一是解決了橡膠的“斷供”危機。
日本在偷襲珍珠港後迅速奪取天然橡膠的主要產地——南太平洋地區,切斷了美國97%的橡膠進口來源(Tuttle,1981)。天然橡膠是重要戰略物資,美國當時極度依賴進口,橡膠斷供意味着美國的工業生產將在一年之內全面癱瘓。毫不誇張的説,當時美國被“斷供”橡膠比中國今天被“斷供”芯片更加嚴重且致命。
在難以找到天然橡膠替代來源的情況下,**生產合成橡膠是唯一的出路。**美國企業在技術上有開發合成橡膠的基礎,掌握着兩種製造合成橡膠關鍵原料的工藝:一種是從石油中提取,標準石油公司通過戰前與德國法本公司的協議而持有這一工藝的專利;另一種潛在路徑是從穀物或土豆轉化來的酒精中提取(Wendt,1947)。
然而,美國的政府機構和企業卻在合成橡膠的生產上陷入了長時間的扯皮和推諉狀態,在橡膠斷供後的大半年時間內毫無進展。
戰時生產局的介入最終扭轉了困局。它在接管橡膠資源調配權限後,把生產合成橡膠列為“第一計劃”,並於1942年9月設立“橡膠主任”的職位,統一負責動員和協調有關企業開展合成橡膠的研究。戰時生產局給生產商下達的任務就兩條:第一,生產出可用的合成橡膠;第二,按最快的速度生產出來,產量要足夠滿足工業生產的需求,誰能生產出來就給訂單,不然一分錢都沒有(Wendt,1947)。
有趣的是,戰時生產局原以為生產合成橡膠原料的“主力”是標準石油公司。但出乎意料的是,標準石油沒有生產合成橡膠原料的積極性,因為戰爭期間對石油的需求太廣泛,特別是航空汽油的需求過於龐大,所以它只是不緊不慢地生產合成橡膠原料;反倒是因為受制於戰時管制條例,賣不出酒精的酒精加工企業更有動力去生產合成橡膠原料(Tuttle,1981)。
到1944年底,酒精加工企業提供的原料產能已經增長180%,但是石油企業只有90%(Tuttle,1981)。到戰爭結束時,美國的合成橡膠產能已經從1940年的4500噸提升到超過100萬噸,保證了美國的工業體系能夠全力生產所需的戰爭物資,並且在戰後產生了一個全新的合成橡膠工業。
2.曼哈頓計劃是工程,不是科學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經常被視為“大科學”的典範。但是,**美國最初把對核武器的研究交給科學家自由探索的時候,甚至都沒有明確的原子彈研製任務。**直到美國參戰之後,決策者才意識到不能再沿用毫無應用目標的實驗室研究方式,而是必須交由軍方來專門領導原子彈的研製和生產(格羅夫斯,1991)。
1942年,由美國總統直接領導的“最高政策小組”(美國戰時的最高決策機構)決定指派陸軍工程兵團負責原子彈的生產工作,並直接對最高政策小組報告和負責,而且明確了研製原子彈的任務目標:第一是要造出能用於實戰的原子彈,第二是趕在任何敵國之前造出來(格羅夫斯,1991)。
然而,主要由科學家組成的國防諮詢委員會評估認為,生產原子彈是一個簡單的工程問題,只需要不到1億美元的經費。甚至有實驗室的科學家提出,只要派給他們50~100個初級工程師和繪圖員,就能很快建起可以正常運轉的鈈工廠(格羅夫斯,1991)。因此,決策層最初只派了一個校級軍官格羅夫斯來牽頭執行。
等到格羅夫斯接手後才發現,所謂的成熟技術都還處於實驗室階段,根本沒有辦法用於滿足研製原子彈需要的批量生產。例如,能夠用於實戰的一顆原子彈所需的核材料是以公斤計的,但當時在實驗室使用迴旋加速器生產原子彈所用的鈈元素,一個月只能生產2毫克,且耗費巨大(格羅夫斯,1991);其他方法包括實驗室採用的同位素分離技術,無論是氣體擴散分離、還是物理離心分離,都無法直接拿來進行大規模生產,甚至沒有任何企業或機構設計或建造過可以大規模生產核材料的反應堆和分離裝置(格羅夫斯,1991)。
最關鍵的是,核裂變的原理(鏈式反應)只是在理論上成立,但是從來沒有被實際驗證過,甚至原子彈的爆炸原理在理論上都是空白。
因此,儘管有科學家的充分參與和支持,但原子彈工程實際上並不能建立在想象中科學自由探索的基礎上,而是必須從頭幹起,必須動員各個政府部門、大型工業企業和科學家的力量一起來幹。
但是,**這些工作的權限已經遠遠超過陸軍工程兵團的職責範圍。**例如,沒有任何人事先知道應該怎麼建反應堆的生產流程和工廠,格里夫斯只能找在電氣和化學工程領域最有經驗和能力的斯通—韋伯斯特工程公司和杜邦公司來承包建造(格羅夫斯,1991);鈾礦石原料要從剛果進口,所以格里夫斯又找到了國務院請求協調鈾礦石的進出口(格羅夫斯,1991);稀缺戰略物資在戰時受到管制,因此要與戰時生產局協商優先供應關鍵材料(格羅夫斯,1991)。
在這種情況下,1942年6月,美國總統批准了核武器計劃報告,同意設立“曼哈頓”工程區(Engineering Division)來執行原子彈計劃,明確給予壓倒其他任何計劃的最高權限(格羅夫斯,1991)。直到這時,著名的“曼哈頓計劃”才正式成形。
格里夫斯在發現科學家們並不靠譜後,決定採取明確的工程原則來推進項目——不管技術上是先進還是落後,只選擇能夠滿足產量和時間要求的工藝和裝備。
原子彈爆炸要用的鈾-235需要從同位素鈾-238中分離出來,氣體分離法是最可能支持大批量生產的工藝。但是,有人提出氣體分離法只有採用純鎳部件才能抵抗加工過程中氣體的腐蝕作用。如果按照這個要求執行,全世界一整年的鎳金屬產量都不夠用。這時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工程師提出,汽車工廠在生產過程中也需要用鎳來抗腐蝕,但在裝備上鍍一層鎳就可以,其效果與純鎳部件沒有區別——這就是以結果為導向的工程思維解決問題的辦法(格羅夫斯,1991)。
最終,舉全美國之力實施的曼哈頓計劃用時超過3年,耗資數十億美元(約等於現在的300億美元)。事前科學家們認為可以“輕而易舉”建造的鈈工廠,到實際完工時已經耗時超過1年,動用超過4萬人進行工程建設(格羅夫斯,1991)。雖然科學原理預計到了製造原子彈的可能性,但如果聽任科學家的自由探索,美國能不能搞出原子彈都尚未可知。
與之相反,隨着曼哈頓工程的展開,許多在自由探索中懸而未決的科學研究才取得了突破。例如,為了驗證核裂變是不是真實可行以及計算需要多少核材料用量,只是在軍方的要求下,美國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才組裝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核反應堆進行試驗,科學家們也才第一次證實了大規模可控鏈式反應的存在。甚至計算機時代的出現都與曼哈頓工程有着密切聯繫,為了進行大量工程計算,軍方動員科學家設計新的計算機,奠定了計算機的基礎架構和基礎運算方式的“二進制”。
6
以國家力量促進創新
3.創造技術領先的DARPA
第二次世界大戰促使美國聯邦政府採取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做法,除了上述兩個例子,另一個就是對科學技術的直接支持。
在戰爭迫近的1940年,MIT的工程師和科學家範內瓦·布什(Vannevar Bush)成為羅斯福總統的科學顧問,他幫助建立了最高領導層與科學界可以直接聯繫的國防研究委員會(NDRC),並與同事們在MIT設立了研究雷達的輻射實驗室(the Radiation Laboratory)。為完成緊迫的任務,該實驗室創造出“有聯繫的科學和技術挑戰模式”——即技術突破從基礎科學階段就與技術開發、樣機和生產等後續階段密切相聯,併成為其他實驗室(如開發核武器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模型(Bonvillian,2006)。
布什在戰爭期間又創立了美國科學研究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動員科學家為戰爭服務。該局在戰爭期間直接與大學和企業簽訂合同,其中最大的資助和合同接受者是MIT,共得到超過1.16億美元的75份合同(Mowery and Rosenberg,1998)。
在戰爭結束前,範內瓦·布什應羅斯福總統的要求,組織一批科學家起草戰後美國的科學政策。1945年7月,他向杜魯門總統提交了著名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Barfield,1997)。
這份報告在總結科學研究對戰爭的作用後,提出的核心建議是國家應該大力支持科學家的研究,但不應該掌握約束科學家自由探索的權力。也許是預見到政府在戰後對科學的投資會被大幅削減,也許是不希望科學與軍方永久結盟,布什報告從“有聯繫的科學”立場後退,提倡了一個線性理論:只要大力支持科學研究,就可以自動產生技術和工業的優勢(Bonvillian,2006)。
但是,布什報告關於科學家自治並主導戰後科學研究的主張沒有被杜魯門總統接受,報告建議的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NSF)被拖到1950年才成立,而且由它來協調美國科學研究的建議則被完全忽略。但在布什報告產生的巨大影響下,聯邦政府在科學事業方面採取了高度分散和集中資助基礎研究的體制(Bonvillian,2006)。
1957年10月,蘇聯發射了世界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斯普尼克1號”。這個事件對美國社會產生巨大沖擊,引起落後於冷戰對手的恐慌。“斯普尼克危機”使美國最高決策層意識到,要加速技術突破並重新領先,就不能依靠分散的、自由探索的體制。
因此,艾森豪威爾總統發起成立先進研究計劃署(後來又在前面加上“國防”,即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本文以下統稱DARPA),隨後又成立了專門負責太空任務的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
美國政府對這兩個機構的撥款沒有走常規渠道,而是通過“例外撥款”(Other Transaction)的方式,使得它們的活動和預算不需要按法律要求對外公開並設立機構的章程,從而賦予它們在選擇和執行項目方面具有自主權。美國決策層對DARPA授予的任務非常明確——建立在尖端技術領域對蘇聯的領先。DARPA完成任務的方針同樣簡潔明瞭:防止再出現意外的最好辦法是自己創造意外,即研發在人們視野之外的“藍天”技術。
DARPA不僅全面繼承了“有聯繫的科學和技術挑戰模式”,而且在制度上有更多的創造。它的最初任務是監督太空研發活動,以避免各軍種的競爭(這種競爭被認為是美國太空技術落後的原因)。
到1960年,DARPA有關太空的項目全部移交給NASA,然後集中於彈道導彈防禦、核試驗探測、推進劑和材料的研發(Fuchs,2009)。由於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出現嚴重的指揮和控制問題(特別是在獲取及時數據和與現場指揮官互動方面),所以DARPA的研發重點從20世紀60年代初轉向信息技術,它也是從這時形成了其關鍵的組織模式和管理風格。DARPA迎接挑戰的方式是利用大學和企業的信息技術研究力量,在全國範圍內網羅最好的科技人員,以合同為手段建立起一個研發支持網絡。正是這種做法為計算(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技術突破奠定了基礎。
DARPA也與國防部的研究機構建立起合作而非競爭的關係,它把自己的機構保持在最小的限度,利用軍方現有的研發機構來執行自己的任務;軍方利用DARPA的投資參與解決共同的問題,而DARPA則為軍方提供了靈活的、跨機構、跨學科的研發榜樣。**美國軍方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創造的“新軍事革命”就建立在DARPA支持的許多信息技術突破之上,**而最初用於軍事的信息技術創新又促進了美國經濟在90年代的創新浪潮(Bonvillian,2006)。
在幾十年的時間裏,DARPA一直保持着較小的機構,通常只有大約100名從學術界和工業界“借”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擔任項目經理,以及大約120名財務、人力資源、法務和保安方面的支持性人員(Dugan and Gabriel,2013)。
DARPA自己不做研究,也沒有實驗室,而是授權項目經理提出特定的研究項目,建立以任務結果為導向的“臨時項目小組”,而項目執行則由大學、各種企業、實驗室的科技人員承擔。每個項目和項目經理的任期只持續3~5年。DARPA立項沒有評審委員會,因為對突破性的技術項目不會存在共識(Dugan and Gabriel,2013);項目經理只需要説服兩個人就可以為項目獲得資助——他們所屬辦公室的主任和DARPA的主任(Fuchs,2009)。但這些項目不是開放研究或自由探索,而是明確闡述需要的產品和任務目標。項目經理對項目直接負責,管理具體的技術細節,制定項目的具體方向和所有相關的重大決策。考核方式簡單明確,以在項目期限內是否達到設定的任務目標為標準。
DARPA每年召開兩次項目經理彙報會,審查項目進展和預定目標的完成進度。在項目年限內,不管採用什麼技術和方法,只要拿出來的產品或技術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則項目繼續;如果沒做出來成果,或者證實目前做出來的可能性很小,則項目終止,但也不會追究研究者的責任。
用通俗的話來説,這就是一種“揭榜掛帥”的機制,對項目負責人、企業和科學家都有強烈的刺激作用。項目經理必須充分組織調動力量才能延續項目,科技人員在項目經理的驅動下開展有目標的研究,通過與不同領域和行業研發人員的合作來找到完成項目目標的特定方法,而不是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中閉門造車。
DARPA的領導人們認為,整個國民經濟都要擁抱創新來使國防部門強大(Bonvillian,2006)。因此,DARPA把研究活動建立在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之中,吸引企業和研究機構參與投資能夠軍民兩用的技術研究項目(Weiss,2014)。DARPA為前期研究提供經費和項目運營支持,使企業界以儘量小的前期投入來探索有市場應用前景的新產品和新技術,但最終要由企業生產能夠符合DARPA的技術要求、同時又能投入市場為企業帶來利潤的產品(Weiss,2014)。
通過這種方式,DARPA充分利用企業的財務能力和技術能力,避免直接耗費鉅額財力投入高風險的基礎研發。如果產品失敗了,DARPA損失的是少量的前期投入,但依然能夠積累前期獲得的技術;如果產品成功了,DARPA就完成了預定的任務,既為企業提供了經濟利益,更為軍方提供了能夠直接在市場上大批量購買的產品,產品還能在市場競爭中進行技術迭代與升級(Weiss,2014)。用DARPA自己的話來説,“讓一項技術能夠被國防部使用的最佳方法,是先讓它成為一個經濟意義上的產業,這樣就能夠以現成的商業產品或服務形式直接提供給國防部”(Weiss,2014)。
同時,儘管企業承擔了從技術到產品的大部分研發費用,但研發出來的產品能夠從市場獲得經濟收益,所以企業自身也沒有出現損失,而且會有更強的動力繼續參與DARPA的研究項目。最終,**DARPA的研究能夠對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循環產生正向的經濟效益,**即使項目不成功,相關技術成果也“外溢”到更廣泛的商業用途,使得美國的前沿技術研究處於高投入但可持續的狀態。
通過這種運作方式,DARPA作為一個強有力的機構領導美國的前沿技術開發,能夠把作為公共產品的科學知識充分應用起來,成為美國二戰後許多突破性技術創新的策源地。
雖然DARPA每年的預算列支只有30億美元左右,但每年都在運營200個左右的前沿技術項目,做到了“花小錢辦大事”。DARPA為美國創造了巨大的技術優勢,從軍事上的隱形戰機、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數字化指揮系統、高能激光、全球定位系統(GPS)等,到從軍事技術成果外溢民用的互聯網、機器人和計算機軟硬件及芯片製造等等,都是DARPA的直接成果或源於它所開創的研發項目。
**DARPA是美國以國家力量促進創新的主要標誌。**美國為什麼不依靠“萬能的”市場機制而需要由國家設立的DARPA來領導創新?曾任DARPA領導人的Dugan和Gabriel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將DARPA的工作性質解釋為“巴斯德象限”的研究任務——具有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見圖2)。
Dugan和Gabriel説,私營企業在巴斯德象限進行研發的情況是罕見的。大多數企業的研發還是遵循線性的邏輯:探索性的基礎研究→將發現轉化為某種實際用途的應用研究→開發應用新技術和能夠大規模製造產品的商業化。一般來説,企業認為基礎研究的風險較大,所以會要求研發部門遵循公司業務單位的要求,但“公司的業務單位幾乎不可能選擇那些會挑戰甚至威脅現有產品和服務的研究項目”,所以“大多數公司的研究預算都投入到對保持公司在現有行業中的競爭力至關重要的創新”(Dugan and Gabriel,2013)。於是,研發部門和業務單位往往相互妥協,結果是雙方都做出最糟糕的工作,即落在“沒有意義的研究”象限。
一句話,**市場機制不會自發地產生突破性創新。**因此,設立DARPA的意義就是克服市場機制的“弊端”,以國家的力量動員“市場”的資源和科技力量,使其有意識、有組織地在巴斯德象限進行創新,從而產生帶來技術優勢的重大突破。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