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然評《爪牙》等|轉變中的帝國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21-08-05 14:04
編者按
上世紀末,隨着新檔案的開放,美國的一批中國研究學者以清代法律問題為切入點,對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社會從不同側面進行了嶄新的研究。保馬今日推送彭慕然老師的書評《轉變中的帝國:評蘇成捷<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白德瑞<爪牙>和麥柯麗<社會權力與法律文化>》。文章挑選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及其作品並予以述評:晚清的性、官吏以及訟師作為社會現象,都在各自的層面上展現出一個進入社會轉型期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生態。三本著作資料翔實,邏輯縝密,角度新穎,相互配合起來閲讀有助於跳出現代西方學者在中國研究中的固有思維陷阱,那就是將中國視為國家與市民社會分離失敗的國家-形成產物。
感謝譯者王立秋老師授權保馬發佈!
相關鏈接:
每日一書 | 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與差役
每日一書 | 貿易打造的世界
每日一書 | 衰世與西法: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和社會脱榫(增訂本)
每日一書 |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
李伯重 | 技術與國運:清代中國成功與失敗的一個關鍵問題
轉變中的帝國:
評蘇成捷《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白德瑞《爪牙》和麥柯麗《社會權力與法律文化》
文|彭慕然
譯|王立秋
二十世紀晚期,一羣美國大學教員和研究生開始在新開放的檔案的基礎上研究清代(1644-1912)的法律。現在的這幾本書,就是這些學者產出的第一批博士論文。和其他關於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的修正主義作品一樣,它們也推翻了長期以來清代儒家和現代西方學者都一直在提的一些老生常談,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更復雜、更富於動態變化的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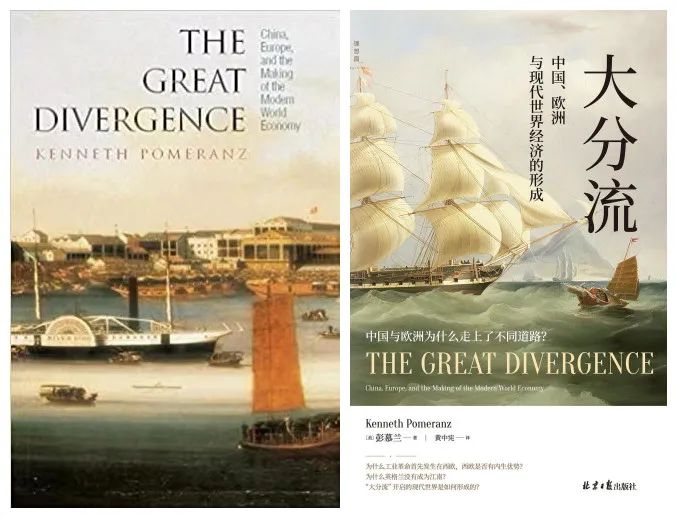
《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彭慕然著,英文及中文版書影
第一個被推翻的刻板印象是,中國老百姓是如此害怕和政權打交道,如此重視和諧,以至於他們極不情願打官司。如麥柯麗所示,官員面對大量的訴訟和申訴,各級衙門的積案持續引發官員的議論。而做幫助人們在地方官員面前表述自己這門嚴格按事實來説非法的生意的訟師,雖然在政府的文件和精英的寫作中備受詆譭,但在大眾媒介(如民間戲曲)中,他們的形象要正面得多。同時,十八世紀快速的商業化和社會變革(蘇成捷特別強調了這個),不安穩的法律地位和跟不上節奏的習慣、法定規則,也進一步助長了訴訟潮。雖然政權肯定希望少一些官司,但它也需要一些訴訟:正如白德瑞展示的那樣,從訴訟當事人那裏搜刮來的錢財,對維持數十萬法外工作人員來説,絕對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這些工作人員的存在,使大約一千五百個地方官統治一個(到1800年的時候)大約三億人口的帝國成為可能。事實上,和這些工作人員本身一樣,在十九世紀期間,這些資費也日益變得正式並受到管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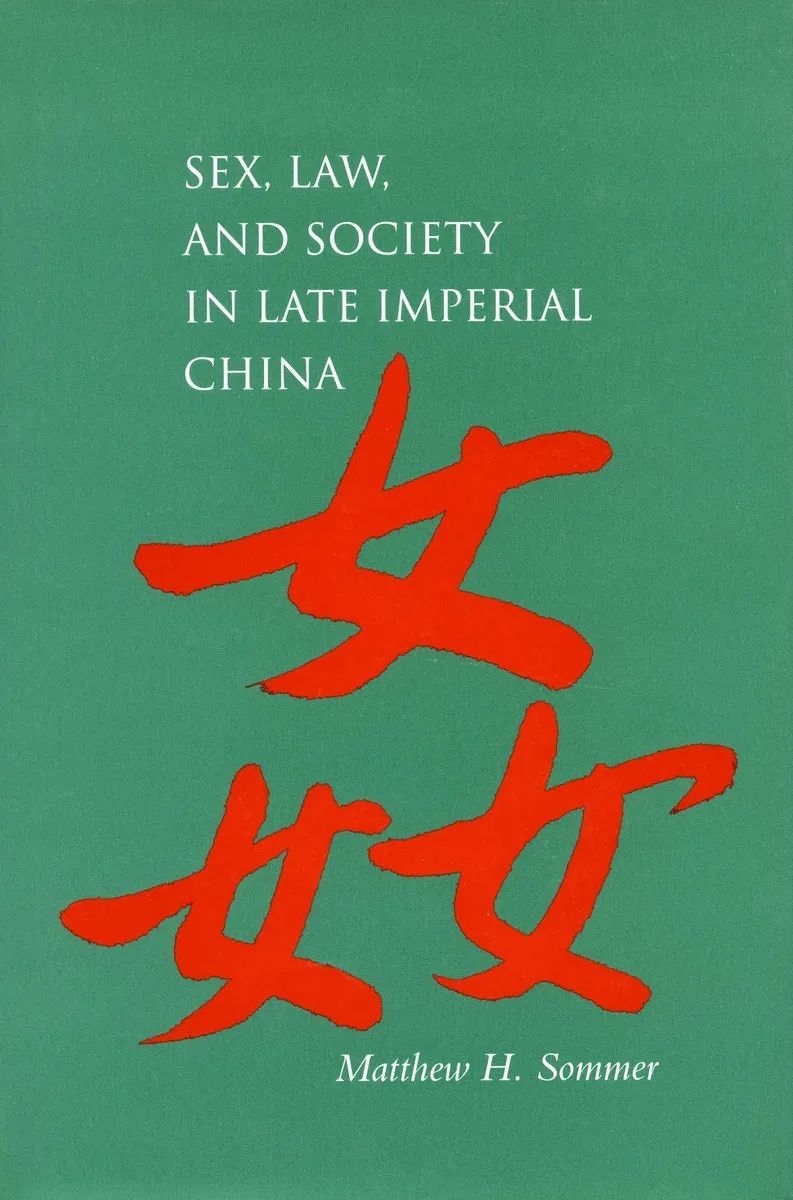
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蘇成捷細緻地記錄了影響各種性問題(強姦、通姦、賣淫、雞姦)的法律變革,但相較於政權或法律本身,他對其中反映的社會變化和態度更感興趣。就像其他兩位作者做的那樣,他也把十八世紀定位為中國長達數世紀的商業化進程行將結束之際,這個進程的結果,是幾乎所有的約定奴工和形式上的法律不平等都被廢除了。他隨之而看到一個性的變化和一個“農民化”的進程。在前一個變化中,性變得不再是“地位的表演”。在那樣的表演中,你會預期屬於不同正式羣體的人有不同的性本質和性行為,這樣,同樣的法律就不可能適用於所有人。而所謂的農民化,則是指為所有人而設的社會和法律規範變得越來越像是為普通老百姓而設的。因此,比如説,在明代就有一個世襲的、在法律上獨特的藝人階級,她們提供的服務往往包括性;這個階級起源於(經常是作為一種懲罰的)強迫而非選擇,但它的成員,卻被認為與她們被貶低的身份相符的性質。因為這些女人從定義上説就是不貞的,而強姦首先被認為是對婦女貞節的攻擊,而婦女的貞節反過來又被認為是其父親或丈夫的財產,所以,起訴對這樣的女人的性攻擊,在法律上就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因為這些女人無貞節可失,所以,把她們固有的亂交屬性商業化也就不成其為罪行——實際上,明代和清初都沒有針對這個階級的女人的賣淫和皮條官司。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清代抹除了大多數剩餘的,平民之下的地位羣體,把同樣的保護和約束擴大、施加於幾乎每一個人。比如説,婢女也得到了不受主人侵犯的保護,也更能預期最終能有“正常的”婚姻。同時,非正統家庭裏的人——同性戀夫婦,容忍妻子與其庇護者通姦的男人,偷情的寡婦——經常發現,他們的活動變得非法了,蘇成捷充分論證了民眾的態度也和法律一樣,朝着相同的方向演化。是否屬於“良人”(這個用於平民的術語一度指一個被賦予的地位)也日益成為一個意願問題,評判人的標準,也變成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被認為普遍的準則。在這些概念演化的同時,關於哪種人可能成為性侵者,哪種人可能成為受害者的觀念也在變:具體而言,蘇成捷以這樣一種日益增長的恐懼為焦點,即,人們越來越害怕,過於貧窮以至於無法娶妻的人,會對“良家”的婦女和年輕男性構成威脅。(他認為,因為人口過剩和經濟“內卷”,這樣的人也的確變得越來越多了。但這個假設在我看來是站不住腳的。)
蘇成捷的論證大多是其他學者,特別是伊懋可在其關於“德性的民主化”的作品已經預見到的。但他的確為這些假設提供了一個比以往更堅實的經驗基礎,重要的是,他把關於性的不同領域的發展關聯到了一起。在這麼做的時候,他檢驗了一些老生常談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一些精英案例提出的過於簡單的概念;除其他方面的貢獻外,他還大大增加了以下觀念的複雜性,即,明代人們在性方面享有廣泛的自由,後來,在道德上極其嚴格的清代破壞了這個自由。這是一本重要的書,它把對中華帝國晚期的性的研究,放到一個比以往更堅實的基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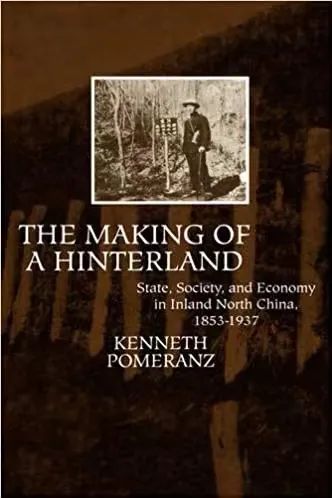
《腹地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彭慕然著,英文版書影
白德瑞則對政府本身給予了最敏鋭的關注,他考察了書吏和差役的隊伍,正是這些人,維持了中國地方政府的運作。在先前的王朝,這個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理論上)是一種短期的,強制性的勞役:在清代,它變成了一個自由選擇的全職工作,雖然大多數參與這個工作的人既沒有得到清代行政法典的認可,也不領受政府的俸祿。地方官員——只在轄區任職數年的外人——發現他們幾乎不可能控制這些所謂的下屬,而當代和現代的學者,也把富裕的儒家士紳的道德標準之下的各種壞事怪到這些人頭上(要不是有這些人,治理中國的就是那些士紳了)。但白德瑞表明,這些工作人員會在很大程度上自我管制。他們演化出各種行為規則和執行方法,這些規則和方法限制了他們的強取豪奪,使他們比我們先前想的更像其他公務人員。事實上,他認為,在清代,他們變得越來越“職業化”了。他們把自己的工作看作一個光榮的職業,這個職業要求大量的訓練和專業技能,也應得到經濟保障的回報。他們還創造了一些有先例價值的規則,用這些規則來管理自己的工作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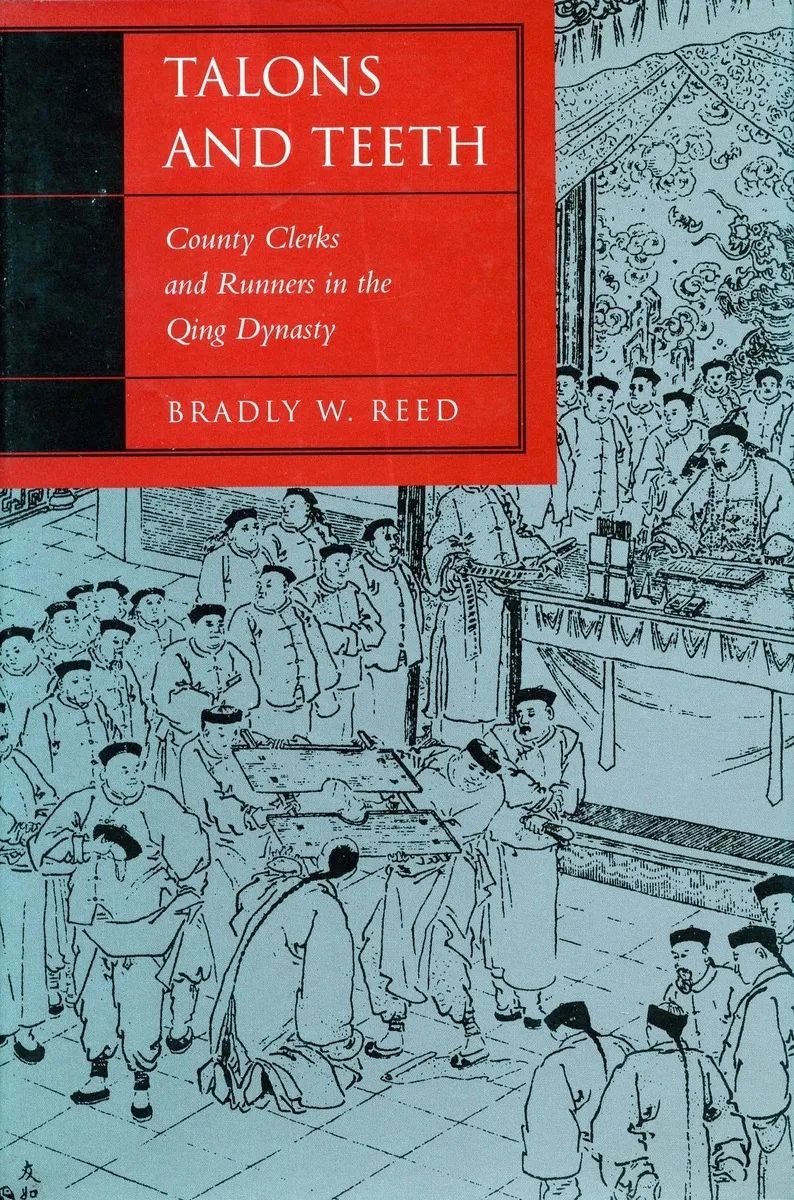
白德瑞(Bradly W. Reed):《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和差役》(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尤陳俊、賴駿楠譯本,實踐社會科學系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
長期以來的刻板印象要麼認為他們極度貧窮,要麼把他們描繪為通過腐敗致富的機會主義人渣。但實際上,這些人大多出身體面(包括小商人,不那麼成功的讀書人等等);收入很可能總的來説充足但不豐厚;他們發展、傳承重要的技能;並且,至少按文吏和差役自己的修辭,他們從事的工作也符合儒家的仁政理想。
白德瑞首先向我們詳細描述了文吏和差役為分工、解決關於僱傭和升職的爭議等而創造的系統。特別驚人的是,哪怕這些規則不具備法律地位且大多涉及明確非法的辦事程序(比如説,特定的收費),地方官員自己,在被要求解決衙內爭議的時候,也會(以書面的形式)援引它們。但因為這些規則從根本上説沒有法律效力,所以,你不能只靠它們來維持工作上的秩序和安全:你還需要各種基於親屬關係、恩庇關係等等的人情網絡來加以補充。在這裏,白德瑞正確地堅持,我們不應認為,有個人主義的跡象,就説明官僚化“失敗了”或“沒有完成”:這種思路假設主要行動者渴望沿着韋伯式的軌跡,把清代地方政府儘可能遠地往前推,但這些人心裏想的,其實是別的事。這種思路也忽視了,從許多方面來看、在許多情況下,特殊主義的網絡和非個人的統治(不講人情的統治)可能是互補的,而非對抗的。(他可能也注意到,一切已知的官僚體制都有特殊主義的部分,不管它表面上怎麼説。)他最迷人、(至少在我看來)最新的發現之一在於:到十九世紀中期,一些縣城演化出士紳經營的勢力,這些勢力會管限制向找文吏辦事的人收取的費用並管理這些費用的支出,這樣,對這些每個人都認為必要的費用的收取,不會對案件的解決本身產生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説明了,首先,當時的人們是接受那些經常被污名化為“貪污”的實踐的;其次,被認為停滯的中國國家機器一直在持續演化;再次,政府底層的低級文吏和有社會聲望卻無正式職位的士紳這兩個經常被認為互相抱有不可消除的敵意的羣體之間也存在微妙的互動。就像白德瑞像我們展示的那樣,就中華帝國晚期地方政治而言,以往的,凸顯對抗的模型往往反映了這樣一種不正確的信念,那就是,必須相對明確地,把“國家”和“社會”分開——那才是西方的正常狀態。但中國的國家-形成的邏輯完全不一樣,它的起點是這樣一種觀念,即,政府是道德和宇宙過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功利主義的沒有意志的行政“工具”。而我們應該做的,是去追問這個邏輯的含義。在簡潔的結論中,白德瑞提出了一些假設,試圖對在關鍵那幾個的世紀——在這一時期,人口的增長和快速的商業化創造出傳統官僚制不能滿足的需求——裏,那種政府觀是怎樣限制清廷的選擇的做出説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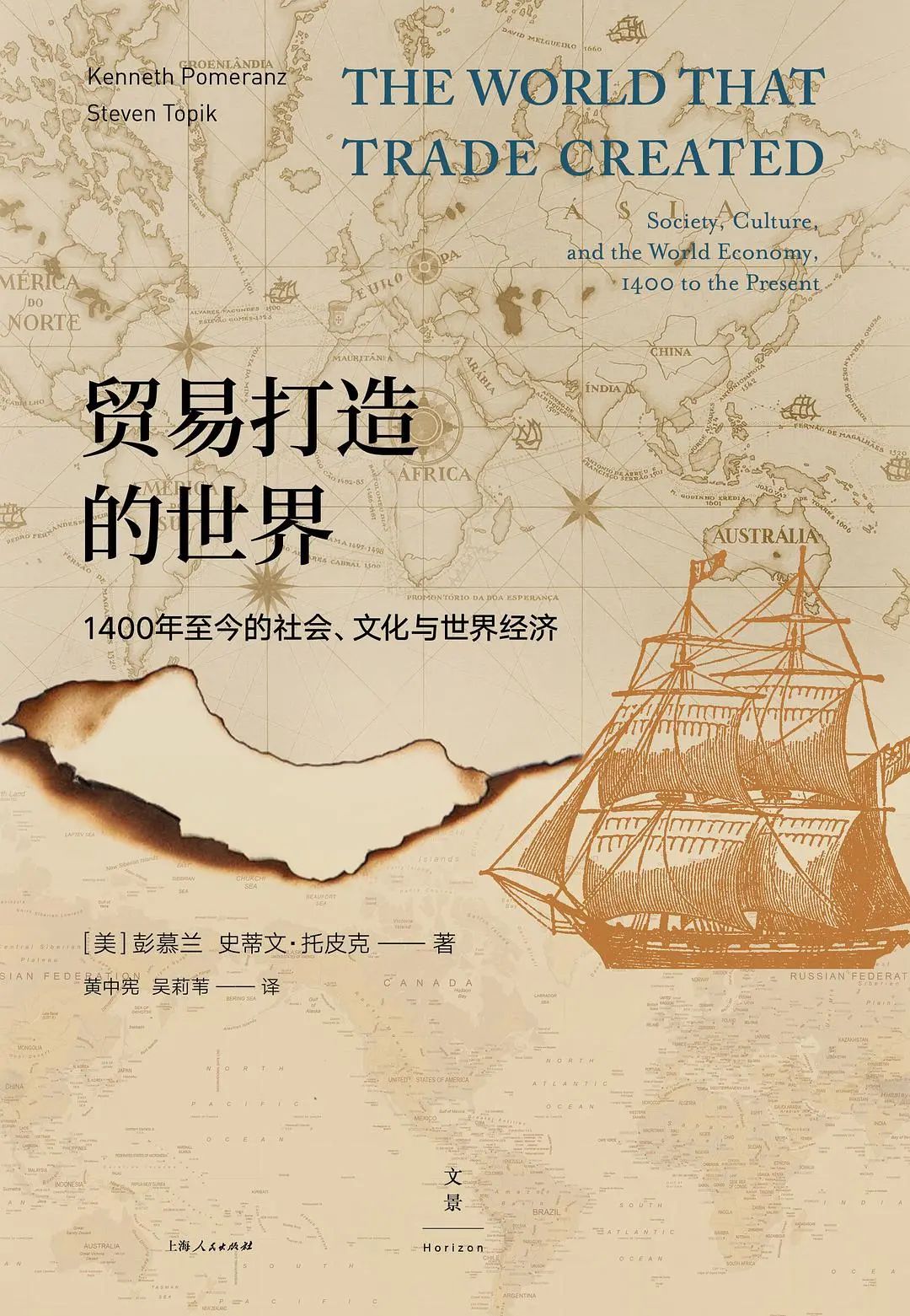
《貿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會、文化與世界經濟》。彭慕然、史蒂文·託皮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這也正是麥柯麗的那本充滿抱負的書的起點:政權太小,以至於沒法治理如此複雜的社會,但它又不肯擴大自己的規模,哪怕在十八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它一直有大量的預算盈餘。她拿晚期中華帝國來和許多殖民政權比較,後者也決定儘可能地降低治理成本,依靠地方精英通過習慣法來解決爭議。(她也正確地指出,這個類比在其他許多方面都不成立。)的確,地方衙門經常會把來告狀的人趕走,讓他們去找村長、有功名的人或其他地方貴族調解糾紛。但因為很多人覺得,那樣的調解會對他們不公平,所以,他們對專業的人有強烈的需求,後者知道怎樣寫狀子官員才願意聽審案子。許多狀師的慣用手段是誇大,讓案子看起來嚴重到需要官員介入(訴狀中的陳述以後還可以再改);這經常涉及不實地指控對方暴力犯罪。明代的立法一直以壓制訟師的這一惡習為目標。然而,清代卻從使這一惡習非法,發展到使訟師本身非法:除那些需要親戚來代表自己的人外,告狀的人都要自己準備狀子。
講道學的官員和士紳一直貶低幫人打官司的人,這倒是讓人想起今天美國的一些極端保守派,只是後者的辱罵性沒那麼強。但在麥柯麗發現的案子裏,訟師經常代表案件中更弱的一方;有充分理由擔心地方貴族的調解會對自己不利的人。看起來,幫人打官司的人是知名人士(這樣需要的人才能輕而易舉地找到他們),但他們又能躲過官員的追究(這表明社羣在給他們打掩護)。在案子被駁回,交由地方調解的時候,訟師往往也會參與這個過程——這表明,他們往往頗具地方聲望,受當地人尊重,這樣,他們才能創造和執行非正式的約定。就像上文指出的那樣,他們經常成為民間曲藝的主角,不過,和其他不按規矩辦事的志願罰惡者(freelance avangers)一樣,他們也被視為一股危險的、不可控的勢力。(在一個太過於複雜以至於沒法在這裏總結的迷人章節中,麥柯麗考察了這些作為“另類男性氣概”的原型的英雄。)而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士紳的仁政,要是還有的話,還是更可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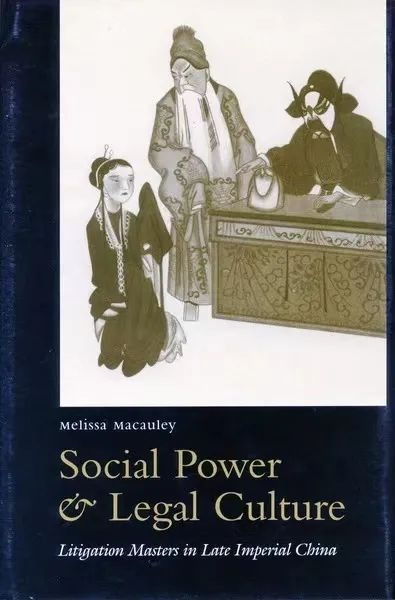
梅麗莎·麥柯麗(Melissa Macauley):《社會權力與法律文化:中華帝國晚期的訟師》(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明輝譯本,法律與社會譯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訟師最常見於這個國家商業化程度最高的區域,比如説長江三角洲。同樣高度商業化的福建則提供了另一個有趣案例。如麥柯麗所述,在那裏,快速的商業化,與還在把土地當作難以出讓的遺產的習俗(這就導致,比如説,許多賣地的人會在幾十年後再把“賣出的地”買回來)嚴重齟齬。這個衝突引發了棘手的官司和械鬥,所以政權也不再維持習俗(在這裏,維持習俗不利於低成本的治理),而是致力於推行以某種類似於土地絕對所有權的東西為目標的,不得民心的、在社會的層面上看激進的變革。但甚至在這種情況下,政權也不願擴大官僚系統(在這裏,要取代習慣法,這樣的擴張是必要的),並因此而未能成功。在這裏,麥柯麗在白德瑞提醒我們當心的那種思維陷阱——把中國的國家-形成當作西歐韋伯路徑的一個不成功的實例來看待——周圍打轉。若非如此,她的比較是敏鋭而發人思考的,在説明中國案例的同時,又不堅持它符合外國的軌道。和白德瑞一樣,她展示了,她的研究主體正在逐漸職業化——這是近來晚期中華帝國研究中的一大主題(近來,蘭道爾·道金[Randall Dodgen]在研究治水專家時也提到了這點)——也展示了,這裏的法律職業化必然和西方截然不同,因為政權不會承認那個職業是合法的。至少一些早期現代歐洲國家參與為擴大其法庭的管轄範圍而展開的持續鬥爭,因此,雖然也經常對律師表達出強烈厭惡(原因和中國的同行差不多),但它們也在穩定地擴大、勉強地承認一個留給由專家組成的自治體的空間,這些專家在把人們引進法庭的同時,也系統地安排他們在那裏的衝突。雖然我不確定説到底麥柯麗的“殖民”類比有多大幫助——在我看來,白德瑞的一些表述(這些表述又反過來和王國斌的想法相似,後者認為,中華帝國是一個“分形國家(fractal state)”)更有幫助——當然,她正確地注意到,清代的國家-形成過程和早期現代歐洲的情況不同,它並不以為那同一種為從“社會”那裏奪取對特定爭議的控制的持續鬥爭為特徵。訟師的世界和律師的世界有着極為相似的經濟動力機制,但它們的政治動力機制卻截然不同,如此,二者的演化也大不一樣。麥柯麗令人着迷地敍述了在中國,國家與社會實際上是怎樣重疊的。和上面討論的其他兩位作者一樣,她也提出了一些複雜的論證,這些論證將指引中國法律與社會史領域的下一輪檔案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