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鐘內吃掉50根熱狗?想贏大胃王比賽也需要創新|展卷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08-22 11:16
創新與生命一樣,是宇宙中非常不可思議的現象,因為它是“逆熵”的,它能從混亂中衍生出秩序,從簡單演化出複雜,是整個宇宙避免熱寂的希望。可創新又是如何產生的?人類歷史的偉大創新總被人們包裹在一層神秘注意的面紗下,瓦特、達爾文、巴斯德、喬布斯……創新總是與個體的成就相關。
但創新有它自己的規律。即使這些聰明的人物不幸夭折,蒸汽機、進化論、疫苗和蘋果手機依然會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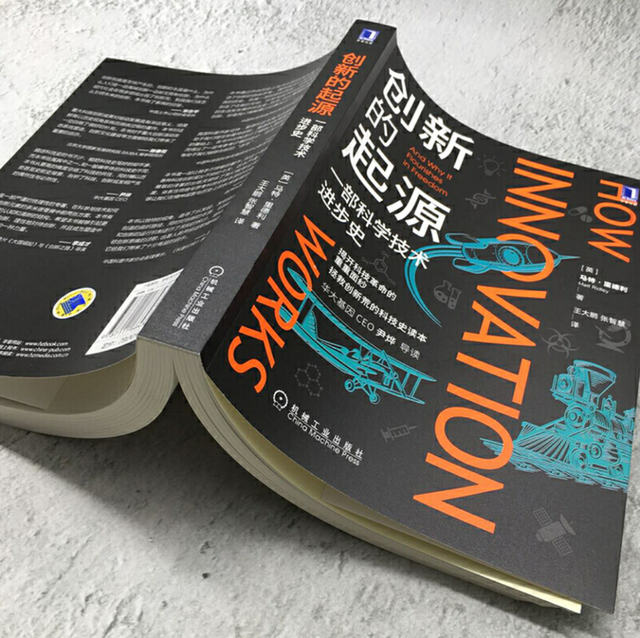
撰文 | Matt Ridley
翻譯 | 王大鵬、張智慧
自由是科學和美德之母;一個國家的偉大與自由成正比。
——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
創新是漸進式的
在我前述的故事中,不同領域的創新史揭示出的模式驚人一致,即無論它發生在昨天還是兩個世紀前,無論它是高科技還是低科技,無論它是一個大設備還是一個小設備,無論它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無論它的影響是破壞性的還是有益的,成功的創新通常遵循大致相同的路徑。
首先,創新幾乎總是漸進的,而不是突然發生的。所謂的“尤里卡時刻”是罕見的,甚至可能是不存在的。要麼是事後諸葛亮,要麼是經歷漫長且迂迴曲折的征途之後的歡慶一刻。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阿基米德並沒有喊着“尤里卡”從浴缸裏跳出來。這個故事可能是他後來為娛樂人們而編造的。
你可以用很多方式來講述電腦的故事。從提花織機開始,或者從真空管開始;從理論講起,或從實踐講起。但你觀察得越深,你就越不太可能看到一個突變的時刻,反而只有一系列的小步前進。你不可能説,具體哪一天是在它之前計算機不存在過後卻存在的日子。正如,你不可以説,某個類人猿是猿但她的女兒是一個人一樣。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可以將無意識的“自然”創新的故事也作為現代技術創新的一部分,諸如火、石器和生命本身的起源。它們在本質上是相同的現象:進化。以汽車為例,其早期版本就像前期技術的老版本,如馬車、蒸汽機和自行車。這提醒我們,人造技術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從更早的人造技術進化而來的,而非從零開始發明。這是進化系統的一個關鍵特徵:移動到“臨近可能”的步驟。
也許我在誇大其詞。畢竟存在1903年12月17日萊特兄弟的飛機在空中飛行的那一刻。當然,這是一個突破性時刻。對嗎?不,當然不對。如果你瞭解這個故事,就會明白沒有什麼比它更漸進的了。那天的飛行只持續了幾秒鐘,僅是一跳而已。如果那天沒有強勁的逆風,就不可能發生,並且在此之前是一次失敗的嘗試。這源於幾年的艱苦努力、實驗和學習,逐步將動力飛行所需的所有能力彙集在一起。
澳大利亞早期的航空實驗家勞倫斯·哈格里夫斯(Lawrence Hargreaves)在1893年寫道,他的愛好者同行們必須根除這樣一種觀點,即“把他們的勞動成果留給自己,他們將得到一筆財富”。萊特兄弟的天才恰恰是他們意識到自己處於一個漸進的、迭代的過程中,沒有指望首次嘗試就建造一架飛行器。在基蒂霍克高光時刻到來之前,是好幾年的艱苦努力以及不斷摸索和反思,直到萊特兄弟搞清楚如何讓一架飛機在空中飛行幾個小時,如何在沒有逆風的情況下起飛,以及如何轉彎和降落。越是深入審視飛機的發展歷史,越會發現這一過程是漸進的。事實上,起飛這一刻本身也是隨着機輪重量的逐漸下降而漸進實現的。
到目前為止,你從本書中看到的每一項發明和創新都是如此,還有很多我沒有提到的案例。雙螺旋結構也是如此。1953年2月28日,詹姆斯·沃森(Jim Watson)突然發現兩對鹼基具有相同的形狀,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意識到這解釋了DNA的兩條子鏈方向相反。他們都看到了線性數字代碼必須位於生命的核心。這一發現看起來似乎是一個清晰的“尤里卡時刻”。但是,正如加雷思·威廉姆斯(Gareth Williams)在他的著作《解開雙螺旋》(The Unravelling of the Double Helix)中對此前工作解釋的那樣,“這只是一個漫長的、牢騷滿腹的發明故事中的一段插曲”。
另一項例證是口服補液療法,這是一項在近幾十年裏拯救了很多生命的醫學創新。在20世紀70年代的某個時候,孟加拉國的一些醫生開始使用糖和鹽的溶液來阻止兒童死於腹瀉引起的脱水。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個突然的創新。但是,你越仔細地研究歷史,你就會發現更早的類似實驗與想法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的菲律賓,而菲律賓的這種嘗試是基於50年代的大鼠實驗,以及對40年代的靜脈補液療法的逐漸改進。
沒錯兒,那是1967年,在東巴基斯坦的達卡(即現在的孟加拉國的達卡),大衞·納林(David Nalin)博士領導的霍亂研究實驗室的科學家們在一次突破性的實驗後意識到,在含鹽的混合物中添加葡萄糖可以改善鈉的存留。但他們無疑只是重新發現了前期研究中的線索,並對其進行了一定規模的測試。同期加爾各答的類似結果也證實了這一發現。即使在那時,達卡實驗室也遲遲不能將這個想法推廣到醫生和援助人員身上。一些專家認為,口服補液療法或許有些幫助,但並不能替代靜脈補液療法,傳統的觀點是,口服補液必須空腹。1968年,當一項在東巴基斯坦農村地區嘗試口服補液療法的計劃(在那裏靜脈注射是不現實的)被提出時,它遭到了首次發現葡萄糖效應的菲律賓科學家羅伯特·菲利普斯(Robert Philips)的強烈反對。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特別是在孟加拉國獨立戰爭期間,口服補液療法的價值得到證明,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治療霍亂和其他腹瀉的最佳方法。可以説,創新已經到來。
如果創新是一個漸進式的演變過程,為什麼它經常被描述為革命性的、卓絕的突破或頓悟?兩個答案:人性與知識產權制度。正如我在本書中反覆説明的那樣,任何取得突破的人都太容易也太愛放大他的重要性,而忘記了競爭對手和前人,忽略了那些將突破變成現實的後繼者。
將真正的“發明家”這樣的桂冠戴在頭上是難以抗拒的誘惑。不過,喜歡將創新描繪成“突然改變世界的東西”的人不僅僅是發明家。記者和傳記作家也常如此。事實上,很少有人,甚至連剛剛未能擊敗發明者的極度憤怒而失望的競爭對手,也沒有理由去爭論發明和創新是漸進式的。正如我在《自下而上》(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一書中所述:這就是“偉人”歷史理論的一個翻版,即歷史的發生是特定的首領、牧師或小偷使然。一般來説,這當然不是真實的歷史,更不是關於創新的歷史。大多數人想對生活有更多的控制,而不是基於客觀情況:認為人類的力量是果斷和不連續的想法,這既是奉承又是安慰劑。
民族主義加劇了這一問題。通常,引進一個新想法與發明一個新想法會混淆在一起。“零”並不是斐波納契發明的,也不是阿爾·花拉子密或其他阿拉伯人發明的(斐波納契從他們那裏引進了“零”),而是印度人發明的。瑪麗·沃特利·蒙塔古夫人沒有發明疫苗接種,或許奧斯曼的醫生也不是發明人(她從後者那裏學到了接種)。
不過,正是專利制度的存在讓“英雄的發明家”這個問題變得更糟。在本書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記錄了為建立或捍衞創新專利而鬥爭的創新者是如何在身體和精神上遭受沉重打擊的。
薩繆爾·摩爾斯、伽利爾摩·馬可尼等人多年來在法庭奔波,試圖反駁對他們的優先權的挑戰。在某些情況下,專利的確立過於廣泛,從而阻礙了進一步創新。薩弗裏船長關於使用火來取水的專利就推動了紐科門蒸汽機,而瓦特在高壓蒸汽上的專利則在幾十年中減緩了技術改進。我將在第9章中聚焦這一點,即知識產權已成為現代創新的障礙而不是助力。
創新不同於發明
因發明激光而在1964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查爾斯·湯斯(Charles Townes)喜歡引用一幅老漫畫。它描繪了一隻海狸和一隻兔子在看胡佛水壩。海狸説:“對,這不是我造的,但它是基於我的想法而建成的。”大多數時候,發現者和發明者總覺得他們從一個好主意中得到的實惠或利潤太少,而忘記或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要把某個想法或發明轉化為一種可行的、負擔得起的、能切實為人們帶來利益的創新,需要付出相當多的努力。

弗裏茨·哈伯利用壓力和催化劑發現瞭如何從空氣中固氮,這是一項偉大的發明。但更是因為卡爾·博施多年的艱難嘗試,解決了一個又一個問題,並借用了其他行業的新想法,才最終使氨以社會可承受的成本進行大規模生產。你可以説類似的例子還有曼哈頓項目或紐科門蒸汽機,但這條規則並非僅適用於大規模工業創新。在創新的歷史上,正是那些一次又一次地找到降低成本和簡化產品方法的人,最終實現了產品的重大改變。20世紀90年代,幾乎無人能預見移動電話會出人意料的成功。這並非由於任何物理或技術上的突破,而是由於其價格的突然下跌。正如約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説的那樣:
“對於那些有錢買足夠多的蠟燭和足以僱用僕人照顧他們的人來説,電燈並無太大好處。廉價的布料、棉布和人造絲以及靴子、汽車等,是工業化生產的典型成就,而不是一項對富人來説意義重大的改進。伊麗莎白女王擁有很多長筒絲襪。但是,工業化生產的成就不在於讓女王擁有了更多長筒絲襪,而在於讓工廠女工憑藉日漸降低的勞動量也能擁有長筒絲襪。”
創新包含試錯
大多數發明家發現他們需要保持“去試試”的心理。因此,對錯誤的容忍至關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技術(例如鐵路或互聯網)出現的早期,破產的企業家遠遠多於發財的。英國化學家漢弗裏·戴維(Humphry Davy)曾經説過:“我最重要的發現是由我的失敗啓發的。”托馬斯·愛迪生完善燈泡靠的不是靈感,而是汗水:他和團隊測試了6000種不同的燈絲材料。“我沒有失敗,”他曾經説,“我只是剛剛找到第10000種行不通的方法。”亨利·布斯幫助喬治·史蒂芬遜利用試錯改進了“火箭號”機車;克里斯托弗·利蘭德幫助查爾斯·帕森斯利用試錯完善了汽輪機的設計;基思·坦特林格通過試錯幫助馬爾科姆·麥克萊恩設計出了與貨船匹配的集裝箱;馬可尼在無線電實驗中不斷試錯;萊特兄弟通過墜機試驗發現機翼側面輪廓的高寬比小一些更好。水力壓裂的先驅們意外發現了正確的配方,然後通過無數次的實驗逐漸改進。
玩耍的因素可能也有幫助。喜歡到處玩的創新者更有可能發現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亞歷山大·弗萊明説:“我喜歡玩微生物。”雙螺旋的共同發現者詹姆斯·沃森將他的模型描述為“遊戲”。石墨烯的發明者安德烈·海姆(Andrew Geim)説:“玩耍的態度是我一貫的研究風格。”
一個基於試錯的創新小例子是這樣的:來自初創公司“成長部落”的里根·柯克(Regan Kirk)講了著名大胃王小林尊(Takeru Kobayashi)的一個故事,小林尊在2001年的康尼島吃熱狗大賽中創造了一個驚人的新紀錄:在10分鐘內吃掉了50個熱狗。小林尊又瘦又小,看起來很不像一個吃熱狗冠軍。但他的秘密是,通過系統實驗,他發現如果把香腸從麪包中拿出來,他可以更快地吃掉香腸,然後他把麪包在水中浸一下就可以迅速吃掉。這並不違反規則。
迪克·福斯貝里(Dick Fosbury)的故事也許不是那麼微不足道。他是俄勒岡州立大學的年輕運動員,發明了“福斯貝里背越式跳高”。憑藉此招,他在1968年奧運會上贏得跳高金牌,令更受青睞的競爭對手和興奮的觀眾感到意外。他用背部翻越了杆,頭先通過,頸部着地。福斯貝里後來描述了他幾個月來如何通過試錯獲得這項正確的技能。“它不是基於科學,或分析,或思想,或設計。這些東西都沒有……我從未想過如何改變它,我確信我的教練會發瘋,因為它在不斷變化。”
艾奧瓦大學的愛德華·瓦瑟曼(Edward Wasserman)也使用了類似例子來説明人類的大多數創新都是通過一個看起來非常像自然選擇的過程進化而成的,而並非由智能設計產生。瓦瑟曼展示了小提琴的設計是如何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化的,不是由於突然的改進,而是由於一些有用的微小偏差被傳承下來。如果偏差無效果,則不能被傳承。如小提琴中心的孔開始是圓形的,然後變成半圓形,然後拉長,最後以這種漸進的方法形成f形。瓦瑟曼認為這種創新觀與生物學中的自然選擇一樣,也面臨同樣的心理阻力:
“根據這一觀點,我們做的許多事情—比如小提琴,都是由一個符合效果定律的變化和選擇過程產生的。與流行的觀點相反,這一過程既沒有神秘感,也沒有浪漫感;它與自然選擇法則一樣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與生物進化中的自然選擇法則一樣,在人類發明的進化中,對效果定律存在着頑固的抵制。”
如果説錯誤是創新的關鍵部分,那麼美國最大的優勢之一就是它對商業失敗採取相對温和的態度。美國大多數州的破產法允許創新者像硅谷早期的口號那樣“快速失敗,頻頻失敗”。在一些州,依據破產法第7章中的“宅基地豁免”政策,基本上允許企業家在生意失敗後保留他的家。那些擁有宅基地豁免政策的州比那些沒有此政策的州表現出更多的創新活力。
創作的炒作週期
在我看來,以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家及未來研究所長期負責人羅伊·阿瑪拉(Roy Amara)命名的那條“定律”是有史以來最具有遠見的關於創新的預測。阿瑪拉定律是這麼説的:人們總是高估一項新科技所帶來的短期效益,卻又低估它的長期影響。我們不清楚羅伊·阿瑪拉是什麼時候第一次有了這樣的想法。不過他的前同事告訴我,阿瑪拉在1965年前後就相信這個觀點了。就像大部分創新一樣,這條定律不是隻由羅伊·阿瑪拉一個人提出的。早在20世紀初,我們就發現了類似言論。它經常被認為是亞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功勞,但毫無疑問,阿瑪拉在這件事上是最值得稱讚的。
我們有大量支撐阿瑪拉觀點的事例。20世紀90年代時掀起的對互聯網的狂熱追捧,似乎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時以讓人失望告終。這不禁令人發問,當時人們預測的線上購物、線上新聞,以及所有線上產品的增長都去哪裏了?在10年之後,這些預測都實現了。這些線上產品對零售業、新聞媒體、音樂以及電影業的諸多商業模式都產生了毀滅性打擊,互聯網產業的繁榮程度超出了任何人的預期。同樣,在2000年第一個人類基因組測序完成時,人們普遍認為終結癌症以及推出精準醫療的時候到了。也是10年之後,基因組學領域的進展出現了意料之中的強烈抵制:人們看到基因組相關的知識似乎對藥物的發展沒有太大的影響,因此以《基因組醫學到底怎麼了?》為標題的文章開始湧現。在這之後又過了10年,該領域有了起色,一切都向最初的預測看齊。
從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轉型成企業家的羅德尼·布魯克斯(Rodney Brooks)將GPS(全球定位系統)列舉為阿瑪拉炒作週期的經典案例。從1978年開始,為了讓士兵能在戰場上準確定位到補給點,24顆衞星被髮射上天。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這個計劃沒有如期執行,有好幾次都差點被取消。GPS計劃貌似是擱淺了,但軍方最終還是決定相信並依賴這個系統。GPS的使用很快延伸到了大眾生活中。到今天,它是如此無處不在。對於徒步旅行者、地圖閲讀器、農用車、輪船、運貨卡車、飛機以及幾乎所有人來説,GPS都是不可或缺的。
阿瑪拉炒作週期可以用來解釋很多現象,同時也意味着我們在初期對科技的高估和在後期對它的低估之間,一定有一個時間點,預測是接近真相的。我個人認為這個時間點是在一項科技出現之後的第15年。在頭10年,我們對一項科技抱有了過高的期待,而以20年為時間點,我們的期望值又過低了。所以最正確的應該是對15年之後的預測。當然,這種解釋更適用於直到很多年後才轉化成實際可靠且價格合理,但還是沒有達到預期作用的產品。
在當下,適合用阿瑪拉炒作週期解釋的科技創新應該就是長期沒有達到人們預期的人工智能。多虧了圖形芯片、新算法和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研發大概不會有始無終。這次也不會再出現打消人們對機器智能的興趣的“人工智能冬天”。
和人工智能形成對比的是,我認為區塊鏈正處於阿瑪拉炒作週期的早期高峯中:我們高估了它的短期價值。區塊鏈被普遍認為可以帶來剔除中間商的、有高信任度以及低交易成本的智能合約。但是,在環境複雜的服務業經濟中,區塊鏈不可能一夜之間就達到這般效果。在10年之內,人們對於區塊鏈取得的成就,以及區塊鏈企業倒閉數量的負面情緒將會爆發。不過話説回來,也許有一天,區塊鏈的規模會變得很大。像臉書發佈的數字貨幣Libra雖然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區塊鏈,但可以算是一種前兆。消費者有什麼理由不轉向一種不受制於通脹和政客們制定的高昂税收的影響,並且可以與世界上1/3的人口做交易的貨幣呢?
自動駕駛汽車是另外一個非常恰當的例子。我一直在與這樣一羣人交談,這些人認為在短短几年內,卡車、出租車或豪華轎車的司機會大量失業,而我們現在就需要採取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現在考慮這些為時過早。自動駕駛的實現是可能的,但會在相當受限的情況下,而在現實世界中,它所帶來的變化可能不會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快。現在到未來肯定會出現一大批電子駕駛助手讓車輛可以探測障礙,在高速路上巡航,自動泊車,以及避免堵車。但是在我們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駕駛操作交給汽車之前,我們還需要讓智能行車助手學會在交通規則和駕駛禮儀的制約下,以及惡劣天氣的影響下,自主解決在擁堵的街道以及偏遠的鄉間小道間遇到的一系列的問題。完全自動駕駛的汽車面對的問題可比自動駕駛飛機遇見的要多得多。如果全都變成自動駕駛,我們還需要重新建設所有的道路基礎設施以及培育保險市場,這些事情都需要時間來完成。
我並不是説自動駕駛汽車不會出現,只是在孕育它的路上我們會經歷更長時間以及更多困難。我敢打賭,10年後,媒體上會有很多關於20世紀20年代無人駕駛汽車預測失敗的報道;到那時,人們還會説這個星球上的職業司機將比今天更多,而不是更少。等到2040年以後,它就會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希望我能活到看到這條預言結果的那一天,不管它是對是錯!
創新傾向於分散管理
歷史上,中央集權的帝國都不擅於創新。儘管他們擁有富有和受過教育的精英,但這些帝國政權往往會導致創造性逐漸衰退,使得政權最終滅亡。埃及、波斯、羅馬、拜占庭、漢朝、阿茲特克、印加、哈布斯堡、明朝、奧斯曼、俄國和大英帝國都證明了這一點。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權力集中造成的僵化,技術發展趨於停滯,精英階層對新奇事物開始有抵制傾向,於是他們的資金消耗在奢侈品、戰爭或腐敗上,企業則得不到資助。帝國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單一市場”,而創意只得在其內部傳播。意大利最富創造力的時期是文藝復興時期,當時由商人經營的像熱那亞、佛羅倫薩、威尼斯、盧卡、錫耶納和米蘭這樣的小城邦推動了創新。分散管理的政體比統一的政體對創新更為友好。古希臘也告訴我們同樣的道理。
在1400年以後,歐洲相當迅速地採用了起源於中國的印刷術,徹底改變了西歐的經濟、政治和宗教。當時歐洲在政治上的分裂為印刷術的流行創造了條件。譬如,約翰·古騰堡本人不得不離開他的家鄉美因茨,搬到斯特拉斯堡,尋找一個可以允許他工作的政權;馬丁·路德成了一個非常成功的印刷業企業家且沒有被迫害,只因為選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在瓦特堡給予的保護;威廉·廷代爾(William Tyndale)躲藏在低地國家中出版了他極具顛覆性、充滿美感的《聖經》英譯本。以上的每一項工作都不可能在中央集權帝國裏實現。
相比之下,印刷術在奧斯曼帝國和莫卧兒王朝被禁止了長達三個世紀之久。伊斯坦布爾作為一個位於歐洲邊緣的文化大都市以及一個由基督徒和穆斯林組成的大國,也在抵制印刷術,只因為它是帝國的首都。1485年,蘇丹貝耶茲二世(Bayezid Ⅱ)下令禁止印刷術的使用。1515年,蘇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頒佈法令:穆斯林使用印刷術將被處以死刑。這些後果都是由一個卑鄙的聯盟帶來的:當時的書法家與牧師聯手捍衞他們的商業壟斷,成功地遊説帝國當局停止印刷。在奧斯曼帝國,外國人最終被允許在國內印製外文書籍,但直到1726年,一位匈牙利的皈依伊斯蘭教的名叫易卜拉欣·穆特費裏卡(Ibrahim Muteferrika)的人才設法説服帝國允許用阿拉伯語印刷世俗書籍(非宗教書籍)。如果當時由蘇丹們統治的土地分散成不同的政治和宗教領地,那印刷術很有可能會更早也更快速地傳播出去。
美國看似是一個例外,但它其實也證明了這一規律。它的聯邦結構為各種創新實驗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不算是單一的帝國體系,而是一個由不同的規則、税制、政策和習慣組成的實驗室。在這裏,企業家們可以自由地遷移到最適合他們項目發展的聯邦州。現如今,聯邦政府的權力日益增強。與此同時,許多美國人都在想,為什麼美國在創新方面不如以前那麼敏捷了?
對創新來説最有利的狀態就是當一個政權分散成城邦的時候。在孵化創新方面最好的地方是由一個城市主導政府的地方。至少1000年來,創新不均勻地散佈在城市中,尤其是自治城市。聖塔菲研究所的物理學家傑弗裏·韋斯特(Geoffrey West)有一個關於城市的驚人的發現。他發現,城市規模是根據一個叫作冪律的預測性數學公式來衡量的。也就是説,光從一個城市的人口來看,他就能以驚人的準確度告訴你城市裏有多少座加油站、多少英里長的電纜、以及多少英里的道路,甚至還能告訴你這裏有多少家餐館和大學,以及該地的工資水平。
而真正有趣的是,隨着城市規模的擴大,人均對加油站和電纜或道路長度的需求越來越少,而對教育機構、專利數量和工資卻不成比例地增加。也就是説,基礎設施以次線性速度增長,而城市的社會經濟產物以超線性速度增長。傑弗裏·韋斯特和他的同事認為這種規律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都是適用的。但是對於企業來説卻不然。當企業規模擴張到某一個程度之後,它就會變得效率低下、難以管理、創新性減少、資源消耗增大,以及風險承受能力低下。韋斯特表示,這就是為什麼企業總是會倒閉,但城市不會消失。即使是底特律和迦太基這樣的城市都還依然存在。錫巴里斯(Sybaris)是最後一個完全消失的城市,不過那已經是公元前445年的事情了。
作者簡介
馬特·裏德利(Matt Ridley),英國科普作家、科學家,英國上議院議員,紐卡斯爾英國國際生命中心的創始主席,紐約冷泉港實驗室客座教授。他同時還是英國皇家文學會會員、英國皇家醫學會會員、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以在科學、環境學與經濟學領域的著作而聞名。